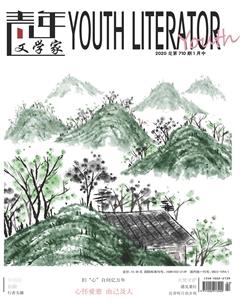試論雪萊浪漫主義詩歌中的自然意象對徐志摩詩歌創作的影響
摘? 要:將自然提高成為詩歌美學觀注的主位對象是十九世紀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一大特點。本文將通過比較中國古典山水詩與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自然意識的不同,結合雪萊與徐志摩的創作比對,說明雪萊浪漫主義詩歌中的自然意象對徐志摩的詩歌結構及其中的自然精神產生的巨大影響。
關鍵詞:雪萊;徐志摩;浪漫主義;自然意象
作者簡介:游洋陽(1989-),女,漢族,江西豐城人,碩士研究生,上海師范大學天華學院通識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02-0-03
一首詩之所以為自然詩,不能僅僅依靠其中對自然物象的描寫,而應讓自然超脫出其他題旨的背景陪襯作用,成為詩中美學的主位對象。[1]十九世紀在英國興起的浪漫主義詩歌運動承襲了來自歐洲大陸上反對十八世紀傳統的普遍風氣。為了對抗拿破侖正在建立的世界大帝國的宏大野心,歐洲各國都在有意識地從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中尋找重振自身的力量。在英國,風靡上流社會的法國文學影響正在被清算,曾經的世界主義感情被強烈的民族情緒所取代,詩人們把目光重新投回自己生長的鄉野、迷信、與歷史,如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司各特等人,或是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通俗題材和歷史題材的創作中,或是表現出對此前從未真正關注過的社會最下層的巨大關心。而在他們創作分歧的表象之上,卻呈現出一種共同的英國式的本源,把英國的浪漫主義詩歌氣質與他國顯著地區分開來,這就是其中獨特的自然意識。隨著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興起,英國浪漫主義自然詩的影響力遠渡重洋,改變了中國新詩人對自然的觀照與表現。
一、中英自然詩中自然意識之不同
拿英國浪漫主義自然詩與中國古典山水詩作比,一些相似點很容易被研究者注意到,譬如詩人“回歸自然”的創作主張,自然物是詩歌的主體、在美學觀注中居于主位等等[2]。但究其根本,中英詩人在觀物應物表現程序上存在較大分歧。
葉維廉曾用詩人面對現象時產生美的不同感應形態對詩人的視境進行了分類。若一類詩人在創作之前已化身為自然現象或自然事物本身,他發起的美學觀注便不再依循人為的邏輯,而是從自然現象或自然事物本身出發,以非分析性的、非演繹性的、非邏輯性的自然秩序,展現出不沾染人類知性活動的自然本身。這叫做“以物觀物”[3]。中國唐代山水詩人王維正是這一類型的絕佳代表。在他的《辛夷塢》中,“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4]芙蓉花從開放到凋零的全過程毫無人為的痕跡,詩人既無意干涉花朵生長變化的進程,也無心渲染自己內心的主觀情感。讀者因此無法聆聽到詩人對此花的解說,必須主動參與到對美的感應當中,反而拉近了讀者直接感受自然的距離。而另一首《鳥鳴澗》,“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5]詩人依然沒有介入自然景物的興發,而是溶入自然本身,將春夜山景花落鳥鳴的原始本樣直接置于讀者眼下,不經由詩人的思維演繹,而交由讀者自己自發地去應物感物。因此,中國古典山水詩中少見如“我”“你”這樣的人稱代詞,“無我”的詩人的個體經驗由此超脫于語言的限指之外成為一種普遍性的純粹情境。在這情境中,過去、現在與未來也不必假諸人為的時空觀念,而以同時共置的關系達到一種靜態的平衡。所以自然在中國古典山水詩中更多以物象的原樣同時呈現在讀者目前,勿需借助隱喻或象征,因為自然本就是“道”的外顯,是天然完整的存在,詩人唯有剔除刻意的自我方能從對自然的觀察中感應到玄妙之境。
但在英國浪漫主義自然詩中,詩人的智心主導了其對自然觀察感悟的全過程。在雪萊的《西風頌》里,詩人的視線全程追逐著西風,看它橫掃“枯死的落葉,/將色和香充滿了山峰和平原”[6],看它幫流云掙脫“天空和海洋的糾纏的枝干,/有如狂女的飄揚的頭發”[7],作雷霆風暴的使者,劈開大西洋的洶涌波濤。山巒——陸地——天空——海洋,讀者從詩歌中所見的風景以單一定向的方式移動,全都遵循詩人視覺觀察的有意安排,最終復歸于詩人的智心之中。在這如“游覽”般呈現的風景里,詩人的心靈與身處的自然始終進行著交流,在內在心智與外在物象的互相應答中盤旋上升,不斷發展,派生出新的意義。
因此,從詩歌結構的角度來看,中國古典山水詩對自然的呈現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共置;而在英國浪漫主義自然詩往往以山海風景為發端,以情感體悟為結束,自然往往被詩人按照時間發展的順序來觀察、體悟、表現。
二、雪萊浪漫主義詩歌中的自然
雪萊作為十九世紀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首先在他的詩歌中展露出的是詩人對大自然的細致的觀察與平等的熱愛。無論是高天之上自由的飛鳥、云朵、西風,還是地面奔騰的尼羅河、巍峨的亞平寧山,甚至于一株嬌弱的含羞草、一朵枯萎的紫羅蘭、一頭洞穴里的變色龍,詩人都把它們等一視之。不再是中世紀式的獵人與獵手的冷酷關系,也不是浪漫愛情與歷史上演的舞臺風景,而是當作與自己一樣的親密的平等的兄弟姐妹。面對自然,雪萊毫無遮掩地驚嘆山河風貌的壯麗,稱贊風云運動的磅礴,既悲悼生靈的凋亡又歌頌生命的堅韌。毫無疑問,雪萊最優秀的抒情詩大多是優秀的自然詩,都從那些人類社會以外的蘊藏性靈的自然物身上獲得了靈感。
在這形形色色的自然物中,“大海”是能代表英國氣質的典型意象。雪萊詩歌中對大海的贊頌、對航海的熱忱、乃至于詩人遭逢海難的死亡結局,都彰顯著英國文學中對大海如傳承般的熱愛。上溯至十世紀時,無名的古英語詩人已經對航海生活作出了抒情性的詩意表現。神秘莫測、浩瀚無垠的大海占據了英國文學家們描摹自然的絕大篇幅。待到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詩歌中,無論華茲華斯還是拜倫,無不把“大海”看作自由的偉大象征。除了對大海的熱愛,雪萊還鐘情于天空里的“風”與“飛鳥”。《西風頌》中,藍色的地中海被咆哮的西風從沉睡中喚醒,把自己劈開洶涌的波濤,袒露出淵底萎縮的花草和泥污的樹林,回應著西風變革的話語。云雀則是一團與整個大地和天空共鳴的火云,歌唱著明光、希望、與歡愉。
詩歌中的意象不能孤立存在。辛·劉易斯認為意象“不僅僅反映主題,而且賦予主題以生命和外形,它們足以使精神形象可見”[8]。雪萊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詩人,在他的身上有著十九世紀英國詩人特有的強烈的道德觀。對正義的渴求與實用主義精神推動著詩人必須在詩歌中對生活做出回應。當“孤獨時,或是雖在人群之中卻處于得不到任何同情的被遺棄狀態時,我們便愛花、愛草、愛水、愛藍天”[9]對不公社會的憤怒、對污濁現實的厭惡,以及對理想世界的呼喚,化作澎湃的海波、化作狂暴的西風、化作消融的冰山和新墾的荒漠等等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顛覆性想象。客觀的自然物與詩人的主觀情感纏繞上升成為一種激進的自然精神。因此,自然意象在雪萊的詩歌中不是對外在世界的單純再現。詩人不描寫風景,也不癡迷于描摹具體的形狀和顏色,而是把自己看作它的“琴”,振起巨大合奏的樂音。自然與詩人的獨立精神和戰斗意志融為一體,與強烈的道德意愿合而為一,成為了自由與正義的象征。
三、雪萊的自然意象對徐志摩浪漫主義詩歌的創作影響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展,白話詩歌創作逐漸興起,詩人們為了與所謂的中國“舊”詩歌相區別,刻意追求著與古典傳統不同的表達與審美。及至三四十年代,隨著浪漫主義詩歌等的譯入,浪漫派詩人們將自我投入自然并通過智心與自然的不斷對話來建立關系的習慣逐漸為中國的白話詩人們所接受。徐志摩顯然也是其中的一員。詩人正式的詩歌創作始于留英以后。雪萊為代表的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幾乎影響了徐志摩全部的創作生命。不過,在徐志摩詩歌創作的早期還是可以看到中國古典山水詩歌傳統在其中留下的痕跡。譬如寫于1922年的《私語》一詩,“秋雨在一流清冷的秋水池,/一棵憔悴的秋柳里,/一條怯憐的秋枝上,/一片將黃未黃的秋葉上,/聽他親親切切喁喁唼唼,/私語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詩情節,/臨了輕輕地將他拂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暈里,/一渦半轉,跟著秋流去。”[10]表現的是秋雨從天而下打落柳樹枝葉發出響動的瞬間。秋水清冷,秋柳憔悴,秋枝怯憐,秋葉半黃,詩人沒有直接表露出哀愁或愛憐,也沒有介入其中去干涉必然一任雨打風吹去的命運。他沉默著把自己經歷的一個蕭瑟濕冷的秋天放置到讀者的目前,讀者任憑自己的經驗去感受聆聽這個秋天傳遞的“私語”。
然而,在徐志摩更多更后來的詩中對自然所作的美感觀照比起中國古典詩歌傳統,更趨近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心靈與自然的對話。其中,雪萊的詩歌對徐志摩歸國后的創作尤其有著顯而易見的影響。下文將通過對《西風頌》與《自然和人生》,《致云雀》與《黃鸝》的比較分析來說明徐志摩在詩歌結構與自然意象上對雪萊的浪漫主義詩歌的接受。
在《自然和人生》中,詩人是一位站立于山頂的觀察者,從陽光朗照的山頂俯瞰烏云沉沉的下界。隨著時間的流逝,山間劇烈的大氣運動不斷變幻著風云雷電的形態,以雷霆為先導,山谷內一時風卷云涌;繼而狂風暴雨電閃雷鳴天地變色;直到雨收云霽,山谷內重新恢復了安寧幽靜。這瞬息間暴烈與和平的轉換讓詩人的心緒也隨之沉浮跌宕,久久沉吟。整首詩歌完全從詩人自我的角度出發,按照時間發展順序,全景再現了詩人目擊的山谷間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的全過程,狂暴的自然力力量在摧殘山谷之時同時作用在了詩人的心頭,讓他體悟到“烈情與人生”。于是山間就是人間,人生就是造化的游戲,自然的物理時間和詩人的心理時間保持了線性的一致性。至此,詩人對自然的觀照與感應已與中國古典自然詩分道揚鑣,而更向雪萊的《西風頌》靠攏。
更能體現徐志摩與雪萊浪漫主義自然詩關系的是他在詩歌中對雪萊的自然意象的接受與改造。雪萊在他的名篇《西風頌》中以激情洋溢的筆調歌頌“狂暴的西風,秋之生命的呼吸!”[11]隨同西風摧枯拉朽的聲息,詩人似在用整個的靈魂呼喊著“把昏睡的大地喚醒吧!要是冬天/已經來了,西風呵,春日怎能遙遠?”[12]西風這樣橫掃千軍的氣勢當然感染了徐志摩。早在《灰色的人生》里,徐志摩就立誓要“唱一闋荒唐的、摧殘的、彌漫的歌調”,而在稍晚的《自然與人生》中,雪萊的強勁的戰斗力量將得到更為完整的再現。不過,徐志摩的狂風沒有劈開雪萊所鐘愛的洶涌“大海”,而是駐足在了巍峨的“岱岳頂巔”,在那里,“風,雨,雷霆,山岳的震怒/猛進,猛進!/矯捷的,猛烈的:吼著,打擊著,咆哮著;/烈情的火焰,在層云中狂竄:/狂風,暴雨,電閃,雷霆:/烈情與人生!”[13]
詩人在表情達意之時需要借助適當的外在物象,必然會優先考慮本國的風物,因為民族文化本就是詩人個體經驗的一大來源。上文曾論及海洋之于英國浪漫主義乃至英國文學的意義。而對于中國這樣的典型大陸國家,古詩中的海洋常常表現為一種虛指:或是以其博大神秘引申為仙山秘境,或是以起遙遠疏曠作為野蠻荒蕪的代稱。如曹操《觀滄海》中將大海本身當作詩歌描述的主體的情況并不多見。與此相對,對山岳的審美觀照才是普遍實在的傳統。中國最早的自然詩歌正是從對山水的觀物之中誕生出來的。徐志摩作為一名中國詩人,對山岳的熟悉與審美,應當遠遠超越于海洋之上。所以,當他選擇在自然中思考尋找寄托人生的永恒之所在時,他習慣性地進入到中國的幽谷與岡巒與森林,而不是雪萊的劈開的藍色的“大西洋”。
再來看兩位詩人筆下的飛鳥。徐志摩的黃鸝是“一掠顏色飛上了樹,/艷異照亮了濃密——/但它一展翅,/沖破濃密,化一朵云;/它飛了,不見了,沒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熱情。”[14]而在雪萊筆下,云雀是“歡快的精靈!/你從大地一躍而起,/有如一團火云,在藍天/平展著你的翅膀,/你不歇地邊唱邊飛,邊飛邊唱。”[15]很明顯能看出徐志摩選擇的“黃鸝”與雪萊的“云雀”近乎如出一轍,都屬于同一類足以代言詩人自身自由精神與戰斗意志的自然意象。
云雀是英國鄉間常見的晨鳥,與光明同行,宣告新的一天的開始,標志著光明對黑暗的驅逐。云雀在飛行中鳴叫,優美的歌聲既是為暖夏的預告,又是對寒冬的終結,在英國文學傳統中是自由、希望、與歡樂的象征。而黃鸝是中國本土常見的鳴禽,同時也是在溫暖季節活躍的勤勞的鳥類,是中國古代詩人用以象征美好的常見意象。兩者在棲居地理范圍上雖然東西有別,但在生物習性上相近,在兩國文學傳統中的喻旨類似,徐志摩正是據此將雪萊的云雀所象征的自由與幸福移植到中國黃鸝的身上,發出了對熱情、對光明、對自由,奮不顧身的鳴啼。
結語:
詩人對自然的觀物應物表現流程的差異可以用以區分中國古典山水詩與英國浪漫主義詩歌表現自然的不同創作。徐志摩在以雪萊為代表的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影響下,把詩人的智心介入客觀的風景,用主觀情感與哲思與自然展開交流與問答。這樣固然使得自然因與詩人心智的交融失去了某種直接性的呈現,但同時也重新構建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打破了舊詩中“天人合一”的靜態平衡,加深了對人的內心在理想與現實、物外與自我之間的思辨,豐富了白話新詩抒情表意的方式。
注釋:
[1]葉維廉. 中國詩學[M].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6, 85.
[2]葉維廉. 中國詩學[M].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6, 83.
[3]葉維廉. 中國詩學[M].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6, 263.
[4]王維. 王維詩集[Z].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0, 74.
[5]王維. 王維詩集[Z].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0, 75.
[6][英]雪萊. 雪萊抒情詩選[Z]. 查良錚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3, 72.
[7][英]雪萊. 雪萊抒情詩選[Z]. 查良錚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3, 73.
[8]汪耀進. 意象批評[M]. 四川文藝出版社, 1989, 96.
[9][丹]勃蘭兌斯. 十九世紀文學主流:英國的自然主義[M]. 徐式谷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4, 268.
[10]徐志摩. 徐志摩全集:詩歌[Z].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26.
[11][英]雪萊. 雪萊抒情詩選[Z]. 查良錚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3, 72.
[12][英]雪萊. 雪萊抒情詩選[Z]. 查良錚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3, 76.
[13]徐志摩. 徐志摩全集:詩歌[Z].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148.
[14]徐志摩. 徐志摩全集:詩歌[Z].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371.
[15][英]雪萊. 雪萊抒情詩選[Z]. 查良錚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3, 102.
參考文獻:
[1][丹]勃蘭兌斯. 十九世紀文學主流:英國的自然主義[M]. 徐式谷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4.
[2]高咪. 異質文明視域下的中國山水田園詩與英國浪漫主義詩歌[J]. 蘭州教育學院學報, 2017, (6).
[3]王維. 王維詩集[Z].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0.
[4]汪耀進. 意象批評[M]. 四川文藝出版社, 1989.
[5][美]奚密. 現代漢詩中的自然景觀:書寫模式初探[J]. 揚子江評論, 2016, (3).
[6][英]雪萊. 雪萊抒情詩選[Z]. 查良錚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3.
[7]徐志摩. 徐志摩全集:詩歌[Z].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8]葉維廉. 中國詩學[M].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6.
[9]葉維廉. 論西方文學中美感意識與意義嬗變的軌跡——以英國浪漫主義前期自然觀為例[J]. 外國文學評論, 1988,(4).
[10]趙光旭. 鳳凰與夜鶯:中英浪漫主義情感美學思想比較[J]. 中國比較文學, 2003, (3).
[11]朱光潛. 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J]. 中國比較文學, 19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