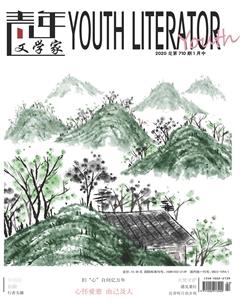沈從文湘西小說中的人性追尋
高小晴
摘? 要:選取湘西這個獨特的背景,沈從文把對人性的深刻思考寓于其中。自然健康、充滿活力的生命形式,湘西兒女自然美好的品格,人與自然契合的生命理想構成了他定義理想人性的基本內涵,生命因真、善、美而張揚,呈現一種自然、鮮活的形態。
關鍵詞:湘西;人性;自然;生命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02-0-02
對沈從文來說,“湘西”是一個能喚起深刻情感的詞,作為他靈魂深處獨一無二的存在,“湘西”于他是情感和精神上的歸屬。人杰地靈,山水相契,仿佛一個超脫于世俗之外的世外桃源,他的湘西小說向我們展現了迥異于中國大地上任何一個地方的奇異景致,一幅充滿神秘,野性和詩意的水墨畫。人性歷來都是中國文學史上表現的一股潛流,深得作家青睞,而沈從文小說中所追尋的人性卻與其他作家追求的泛化層面的人性不同,深植于豐沃的地域土壤,承接文化雨露的浸潤,他洞徹人性的思想中有一種熠熠奪目的獨異特質。
以廣闊的湘西世界為背景,獨特風俗人事為表現對象,沈從文向我們訴說的是他對人性理想的追求。他帶領我們走進神溢原始的神話中感知自然純樸的生命,水手們簡單而充滿危險的生活,山水間成長的少女們羞澀而健康的情感,吊腳樓妓女的歡樂和哀愁……獨特的群體,不一樣的生存狀態,他所理解的人性,因而蘊含了不同的指歸和意義。沈從文曾在《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中說:“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杰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這廟里供奉的是‘人性。”[1]
人性作為生命的內核,承載著豐富而廣闊的內涵。它在湘西這片地域的表現形式便有所不同。沈從文想要供奉在他的希臘小廟中的人性,與湘西本土有著特定的文化關聯。他對人性理想的追求來源于他所生活的湘西,有了湘西才有他對人性的完整理解,不管是對于他的創作還是個體本身的生命才得以圓滿。從他創作的眾多湘西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所追求的人性是自然人性,甚至是原始人性。那種未被現代文明侵襲的、處在自為狀態下的自然人性。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然健康、充滿活力的生命形式
人性在湘西自然淳樸的生命形式的包裹下,豪放、自然地坦露,是一種野性、甚至是帶點原始意味的無節制的生命揮灑。一切都不受壓抑、摧殘,鮮活、豐滿的生命順利地走向一種非人為的自然狀態,那是多么難得的一種生命存在。
《邊城》中“翠翠在風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健康活潑的翠翠,在湘西自然萬物的浸潤下成長,善良溫柔,不是小家碧玉的柔情似水,而是有點自然野性的活躍之美,恬淡中帶有些許原始生命的氣息。《三三》中的三三與翠翠有異曲同工之處。“媽媽隨著碾槽轉,提著小小油瓶,為碾盤的木軸鐵心上油,或者很興奮地坐在屋角拉動架上的篩子時,三三總很安靜的自己坐在另一角玩。熱天坐到有風涼處吹風,用苞谷稈子作小籠,冬天則伴同貓兒蹲到火桶里,剝灰煨栗子吃。或者有時候從碾米人手上得到一個蘆管作成的嗩吶,就學著打大儺的法師神氣,屋前屋后吹著,半天還玩不厭倦。”小女孩的天真活潑,在自然環境中成長起來,心性健康,明媚開朗。沒有過多的欲望,只為生活本身的需求而存在。每天的生活簡單平淡,卻有發自內心的歡樂和滿足。《阿黑小史》中的阿黑,“長得像觀音菩薩,臉上黑黑的,眉毛長長的”她聰明可愛,大膽直爽,身上洋溢著真、善、美的光芒。
湘西世界中的女性是沈從文對于女性塑造的一種理想,他們汲取了山水之靈氣,聰明智慧、純潔質樸。集心靈美與外形美于一身,活潑健康,又不乏女性的柔美。男性是誠實勇武,擁有陽剛與雄壯的血性,凸顯生命的張力。
《邊城》里的二佬,“儺送美麗得很,茶峒船家人拙于贊揚這種美麗,只知道為他取出一個諢名為‘岳云。雖無什么人親眼看到過岳云,一般的印象,卻從戲臺上小生岳云,得來一個相近的神氣。”知明事理,剛毅頑強,長相與性格俱佳。《龍朱》里“族長兒子龍朱年十七歲,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這個人,美麗強壯像獅子,溫和謙馴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權威。是力。是光。種種比譬全是為了他的美。其他的德行則與美一樣,得天比平常人都多”。美貌與力量,被人敬仰,是近乎神一樣的存在。《神巫之愛》的神巫,《油坊》里的岳珉,《媚金、豹子與那羊》里的豹子也都屬于此類。在他們的身上,體現了古樸的蠻性力量,生命與活力,同時又剛中帶柔,流淌著情感的柔和,呈現了湘西世界健康、優美、自然的生存狀態。
二、湘西兒女自然人性的美好
沈從文的湘西小說中,人們呈現出來的樸質、善良、忠誠、重義輕利互相關愛,美好的品行與青山綠水的明凈澄澈相輝映,如一幅優美鮮活的民情風俗畫,閃現亮麗的人性光輝。比如《邊城》里樸實的老船夫,一輩子擺渡都忠于職守,對人有情有義,他不要坐船人的錢,有人非給不可,他便把這些錢托人買了上等草煙,掛在腰帶邊,過渡時慷慨奉贈給別人。在他的世界中沒有邪惡和虛偽,只有安然的生活,自然簡單,身邊的人開心健康便是他的所有追求。在他身上呈現的是一種生命最為本真而原始的樣貌。掌水碼頭的龍頭大哥順順急公好義,樂于助人。天保、儺送都為人和善、豁達豪放。當他們得知彼此都愛上翠翠時,公平競爭,都擁有善良仁愛的品行。甚至連住在吊腳樓里的娼妓,也是知情知意,善良淳厚,正如沈從文自己所說“這些人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知羞恥的城市中人還更可信任”[2]
湘西人擁有真誠善良的心靈,按照自然的原則生存,無需壓抑,只需呈現最本真的生活面目與情感狀態。即使生長于原始生態的蒙昧狀態中,他們也不乏勤勞、善良、勇敢等美好人性,她們的身心自由卻因為社會惡習、封建觀念的迫害而受到束縛,陷入了悲慘的人生。他們的生命健康而富于活力,他們人性中的美并不會因為其他任何因素的滲透而褪去。在道德與人性的對峙中,自然真實的人性是超越于道德的框架而存在的,在此沈從文深入到了生命存在的深度層面,展現了對生命終極關懷的訴求。
《柏子》中的水手和妓女,身份卑微,都處于社會的下層,他們有愛與生理的需求,于是在一起,享受愛與被愛,滿足性欲,真誠地投入到炙熱的情感中。水手愿意把一個月冒著生命危險掙來的錢花在妓女身上。盡管蒙昧、粗野,但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相互溫暖,這種情感可以游離于道德之外,完全只因為自然的生命需求,簡單而狂烈的生命原動力。《蕭蕭》里的主人公蕭蕭“風里雨里過日子,像一株長在園角落里不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葉,日增茂盛。這小女人簡直是全不為丈夫設想那么似的,一天比一天長大起來了。”在自然的浸潤下漸漸長大的蕭蕭,擁有健康活躍的生命力,她的生命只因生命本身的躍動而勃發,她需要愛,那么當她的小丈夫給予不了她所需要的東西時,她從花狗那所得到的也正是合乎人性的,縱然站在道德的立場上是有違道德倫理的,但從小說中蕭蕭婆婆一家對她的態度可以從一定程度上窺見作者對于人性的態度,主張生命本身的自由發展,不束縛,不譴責,而是一種寬容和理解。這些被倫理道德排斥的行為在沈從文眼里,是自由生命未受壓制而噴薄出的人性的至真狀態,是一種野性的、真實的美,該是一種理想的人性的呈現。
與其形成鮮明的對比,我們可以聯想到他的都市小說中的人物,《都市一婦人》中成為上流社會遭人玩弄的犧牲品的婦人,以糟蹋男子獲得一種復仇的滿足,后與一個年輕帥氣的軍官結合,因為懼怕失去愛情,設計弄瞎了軍官的眼睛,展現了一個愛與仇恨交錯的復雜靈魂。《八駿圖》中虛偽的道德意識滋生了教授們背離生命本質的“都市病”“文明病”,那些壓抑扭曲的靈魂,偏離自然、和諧、健康的生命狀態,在作家看來是社會和民族的墮落。截然不同的人性呈現,湘西人和諧、健康的生命境界是作者力圖追尋和認可的,其中有作者對民族命運的深刻反省和思考,表達一種精神性的回歸。
三、人與自然契合的生命理想
湘西這片神奇的土地,如詩如畫的恬靜與壯美,擁有蕩人心魄的魅力,從自然中來,到自然中去,“皈依自然”是沈從文生命旨歸的一個重要向度,大自然承載著生命通向靈魂的渠道,人性美與自然美同在。青山綠水間生長的個體,與自然的融合,夾雜著野性與詩意,呈現了一種開放的,完美的生命理想。這是一種融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精神歸宿,一種更高遠的生命延展性和無限性。
在沈從文的筆下,有一個與自然最接近的原始的生命世界。《龍朱》中“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的龍朱,受人敬重,身上有神性的特征,誠實、熱情、勇敢,代表了湘西土著民族的精神特質,健壯的體魄,美好的品質,自然向上的生命力正是都市文明人所缺失的,他用歌聲打動了黃牛寨主女兒的心,得到了愛與美完美結合的婚姻。開放、自然的男女戀愛、婚姻方式,這種人與自然和諧相契的完美狀態正是作者所追尋的理想,一種似乎只存在與想象構建之中的美好,卻在沈從文的小說中真實地展現在我們面前。真、善、美以一種具體的形貌凸顯。自由、張狂的流動,率真、粗野而又健康、純凈。《媚金·豹子·與那羊》中豹子的一諾千金,熱情執著,媚金的癡情、忠烈,最后雙雙殉情于洞中,兩個擁有美好品格的靈魂因愛而生,因愛而死的凄美。可以義無反顧的愛,為自己所看重的東西而死,這種美好的品行已不復存在于真實的世界,然而與自然存在某種內在聯系的靈魂,野性、蒙昧,卻擁有鮮活的生命亮色。《月下小景》中二十歲的小寨主儺佑與一個美麗的女孩相戀,族人有 “女人同第一個男子戀愛,卻只許同第二個男子結婚"的陋習,如若不遵守習俗,便會被綁上石磨沉入深潭喂魚,為了忠于愛情,兩人喝下毒藥,在鋪滿野花的石床上相擁而死,留下不朽的愛情傳奇。展示了生命不可褻瀆的神性和莊嚴。《雨后》《采厥》展現了敞開式的,與自然響應和的情欲和性愛,在大自然的懷抱中肆意揮灑青春、熱情,合乎人性,享受生命和自然賦予人類的歡樂。人與自然合二為一,生命力與自然力交疊于瑰麗優美的景致中,人性與神性交錯互繞,靈魂便接近了最本真的存在,生命的終極意義蘊含其中。
綜上所述,沈從文所構建的“湘西世界”,飽含著他深厚的情感寄托和對理想人性的探求,自然健康的生命形式,美好善良的品格,人與自然的契合是他所追尋的理想境界,湘西的自然萬物沁染著湘西人的身心,而湘西人身上自在、躍動的美也映潤著大自然。一曲曲田園牧歌中演奏著人性至純至美的生命旋律,縹緲而真實,回蕩在作家和我們每個人的心田。
參考文獻:
[1]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A].沈從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2.
[2]沈從文.邊城.沈從文文集:6卷[M].廣州:花城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82.
[3]沈從文.沈從文小說集[M].時代文藝出版社.2009.
[4]沈從文.從文自傳[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
[5]吳投文.論沈從文生命詩學的內在構成[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9(1):9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