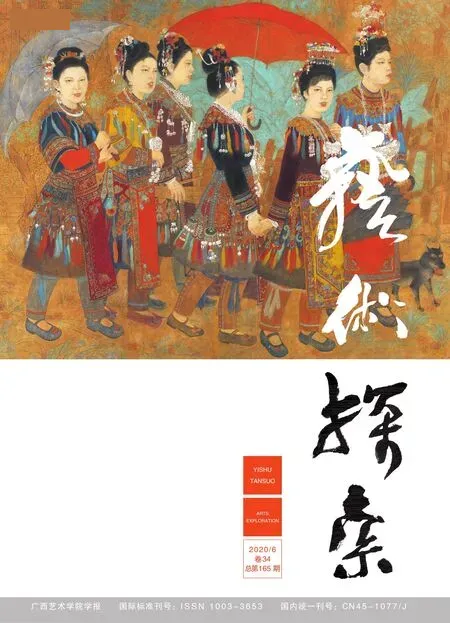如何理解后現代主義:關于邁克爾·弗雷德極少主義藝術批評的接受與演繹
(中央美術學院 藝術設計研究院,北京 100102)
距離邁克爾·弗雷德1967 年發表《藝術與物性》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之久,但是直到今天,當我們在談論有關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藝術及其理論問題的時候,仍然繞不開這個經典的文本。①《視覺文化雜志》在2017 年初發行了一期以“《藝術與物性》50 年:溯源、影響與批判”為主題的專刊,收錄了8 篇最新的研究文章,所有這些文章都是對《藝術與物性》的一種拓展性閱讀,基本超出了學界對于這個文本的常規理解的范圍,進入到了我們現在認為是視覺文化的領域。Alison Green and Joanne Morra,"Introduction:50 Years of 'Art and Objecthood':Traces,Impact,Critique",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Vol.16,No.1,2017.實際上,在剛剛過去的半個世紀,幾乎每隔一段時間,歐美學界都會將邁克爾·弗雷德及其批評文本進行集中討論和重新梳理。譬如,1987 年由迪亞藝術基金會主辦的“當代文化探討”研討會,會集了邁克爾·弗雷德、羅莎琳·克勞斯、本雅明·布赫洛、哈爾·福斯特等批評家,其中一個討論板塊的題目為“1967/1987:藝術與理論的譜系”。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專為《藝術與物性》而設置的討論環節,克勞斯和布赫洛等人圍繞《藝術與物性》的寫作、它所引申出來的理論問題及其與近20 年來藝術發展的對應關系,發表了他們的看法,弗雷德也對自己20 年前的某些論斷和思考給出了進一步的解釋。誠如克勞斯所言,弗雷德的《藝術與物性》是“我們討論的一種潛臺詞,因為它在60 年代的藝術話語中插入了一個理論楔子,以某種方式將那個時期分為前和后兩個階段”[1]59。毋庸置疑,弗雷德的文本作為“潛臺詞”對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以及兩者之間關系的理論認知產生著持續而重要的影響,W.J.T.米切爾、羅莎琳·克勞斯和哈爾·福斯特等人在發展和完善他們的藝術理論體系,尤其是在如何理解后現代主義的問題上都受到了弗雷德極少主義藝術批評的啟發。本文試以米切爾、克勞斯和福斯特的相關文本為例,說明這些代表性的后現代藝術理論家是如何在批評和接受弗雷德關于極少主義藝術批評思想的基礎上,發展出他們對于后現代主義的不同理解的。
一、“語言在美學領域的爆發”
1987 年,在芝加哥大學主辦的一個有關抽象問題的討論會上,W.J.T.米切爾發表了一個題為“作為圖像的理論:抽象繪畫與語言”的主旨演講,幾年之后,他將演講的內容進行了略微改動,收入其最重要的視覺文化研究成果《圖像理論》中,用以說明他所關注的圖像中的文本問題。如題所示,米切爾的這篇論文是對抽象繪畫的研究,但這種研究既不是格林伯格和弗雷德的形式主義批評,也不是T.J.克拉克的藝術社會史敘事。實際上,米切爾是以抽象繪畫為基點,從作為圖像的抽象藝術和作為文本的語言之間的關系的角度,論證在抽象繪畫的現代主義藝術時期,圖像對文本的有意壓制和否定,這種論述的最終落腳點是他所提出的圖像學理論。關于米切爾的圖像學理論,學界已有較為清晰的認識,即他所建構的圖像學既不是采用語言學模式來分析圖像的語言符號圖像學,也不是將圖像視為文化的象征形式的潘諾夫斯基圖像學,更不是將圖像視為一種形式風格的沃爾夫林圖像模式,因為這些模式都對圖像作出了限定,附加了太多的意涵。米切爾的圖像學是將圖像視為圖像本身,擺脫已有知識體系對圖像的束縛,是“對圖像的后語言學、后符號學的再發現”[2]16。筆者提及這些,并不是想就米切爾的圖像學理論闡述一二,而是特地指出《作為圖像的理論:抽象繪畫與語言》這篇論文背后的理論支撐,正因為此,米切爾才將抽象繪畫僅僅作為圖像提煉出來,辯證地看待作為圖像的抽象繪畫與作為文本的語言之間的關系。而正是在這個邏輯中,作為純粹主義者的格林伯格將造型藝術排除在文學和主題之外的非歷史態度,以及弗雷德在《藝術與物性》中有關極少主義藝術的實踐者采用語言系統闡述極少主義的觀點,成為了米切爾論證其理論合理性的有效證據。正是在闡述作為現代主義的抽象繪畫壓制和否定語言的基礎上,受到弗雷德的劇場性理論啟發的米切爾從現代主義的對立面得出了一個有關后現代主義的混雜性的結論,即“語言在美學領域的爆發”,雖然他并沒有展開論述。
首先,米切爾關于抽象藝術壓制文學、文字話語或語言本身,偏愛純視覺性的觀點,并不是他自己提出的創見,而是源自仔細的觀察、歸納和總結。他注意到,在20 世紀有關抽象藝術的主流敘事中,視覺和語言往往被描述為一種敵對的關系。比如,羅莎琳·克勞斯在收入《前衛的原創性及其他現代主義神話》的第一篇文章《網格》的首段中提到:“本世紀初,先是在法國,繼而在俄羅斯和荷蘭,出現了一種結構,從此一直作為視覺藝術中現代主義理想的標志。網格在戰前立體主義繪畫中初露鋒芒,隨后日漸犀利明朗。在其他各種藝術中,網格宣告了現代藝術沉默的決心,以及對文學、敘事和話語的敵視。就這樣,網格以驚人的效率完成了它的工作。它在視覺藝術和語言藝術之間設置屏障,差不多完全成功地把視覺藝術圈在絕對視覺性范圍之內,使之免受言論的侵襲。”[3]198—199克勞斯的這種表述并不是孤例,而是在有關現代主義的敘事中反復出現,最典型的就是現代主義和抽象藝術的代言人格林伯格。
教條主義與當今繪畫中的“非客觀主義”或“抽象”純粹主義處于尖銳對立之中,不能因為這種對立是對藝術的宗教崇拜式的態度就不予考慮。純粹主義者對藝術提出過分的要求,因為他們一般將藝術看得比其他事物重要得多,出于同樣的原因,他們對藝術也更為焦慮。純粹主義主要是轉換一種極端的焦慮,一種對藝術命運的憂慮和對其地位的擔心。我們必須尊重這種心態。當純粹主義者堅持在現在和將來都要把“文學性”與題材從造型藝術中排除出去的時候,我們大多數人都會立即指責他是一種非歷史的觀點。要說明這點并不困難,抽象藝術也和其他每種文化現象一樣反映著社會和藝術的創造者所在時代的其他事物,脫離了促使藝術從一個方向走向另一個方向的歷史,藝術本身便一無所有。但輕易否定純粹主義的主張也不容易,當代最優秀的造型藝術是抽象藝術。純粹主義者在這兒并沒有以形而上的托詞來支撐自己的地位。當他堅持這樣做的時候,我們中間那些沒有全盤接受其主張而又贊賞抽象藝術價值的人必須對它在當今的優勢地位作出我們自己的解釋。[4]27
在《走向更新的拉奧孔》的開篇,格林伯格提出了藝術純粹性的命題,他指出,作為純粹主義者的抽象藝術家將傳統繪畫所表現的客體排除在外,就是抽象藝術更為顯著的姿態。在格林伯格看來,傳統繪畫所表現的客體并不是簡單的純粹寫實主義的客體,“這在本質上不是寫實主義的模仿,不過是在服務于傷感和雄辯的文學中破壞現實主義的幻覺”[4]36。傳統繪畫的圖像顯然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很多文學的聯想,甚至成為文學的附庸,格林伯格在此基礎上指出從庫爾貝和印象派以來的藝術家將視覺作品的文學聯想剔除,將圖像視為直接的感官數據,這些成為現代主義發生的基礎。對此,米切爾顯然贊同,“與富于軼聞和寓言的傳統藝術截然不同,抽象繪畫中沒有可供‘閱讀’或破譯的時間序列:其形式被控制在瞬間的直覺感知之中——成形于空間中的某一特定時刻”[3]211。圖像與文本的這種復雜關系顯然一直存在于藝術史的脈絡之中,至少從文藝復興開始,視覺藝術就與文本糾纏不清,而且畫家的努力目標不是作為一名畫家的成就,而是作為一位詩人的名望,繪畫的這種意圖一直蔓延到了19 世紀,直到將焦點純粹聚焦于視覺的印象派,這個局面才真正被打破。
格林伯格有關藝術純粹性的敘事似乎為現代主義抽象藝術壓制文本和語言提供了一個符合邏輯的說法,但米切爾卻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抽象藝術自稱排除了語言,實則卷入了語言之中,證據是湯姆·沃爾夫對抽象藝術的堪稱“突破”的理解:
這些年來,和其他人一樣,我站在一千、兩千,天知道幾千波洛克、德·庫寧、紐曼、諾蘭德、羅斯科、羅森伯格、賈德、約翰斯、奧利茨基、路易斯們面前……時而瞇起眼看,時而瞪大眼看,時而退到遠處,時而湊向近前……等待著什么東西從千篇一律的純白墻壁上掛著的畫中……直接照射到我的視交叉。這些年來……我一直以為,如果不是在別處,那么在藝術中就一定是眼見為實。如今,我終于……可以明白了。我一直是反向理解的。不是“眼見為實”,你這個傻瓜,而是“實為眼見”,因為現代藝術已經徹底變成了文學:繪畫及其他作品只為說明文本而存在。[3]203
用米切爾的話來說,“由抽象主義的網格豎立起來的針對語言和文學的墻壁,只擋住了某種文字污染,與此同時,它又絕對依賴繪畫與另一種話語的合作,由于缺乏更好的名詞,我們且稱其為理論的話語”,格林伯格、弗雷德和克勞斯的文本都可以被視為一種圖像的理論,“如今,若沒有與之相應的理論,我就看不見一幅畫”。米切爾引用了阿爾弗雷德·巴爾的例子來說明這個事實,雖然巴爾關于“藝術家已經厭倦于描畫事實”的表述體現出了抽象藝術對于語言的壓制,但他所畫的一幅從印象派到1936 年的現代藝術的演化圖(圖1)卻明顯表現出了對于“現代主義‘網格’是視覺與語言之間的屏障這一觀點的圖表式批駁”。[5]204—218
在現代藝術中,視覺與語言之間的屏障看似嚴格,但實際上兩者之間一直維持著一種看不見的聯系,隨著抽象藝術的深入,隨著傳統繪畫的客體被徹底消解,隨著“畫家以標題、敘事線索或主題形式提供的文字提示越少”,語言的浮出水面似乎成了一種越來越強烈的需求。這就形成了一種悖論,即純粹視覺上呈現出來的越少,似乎要說的卻越多。這種悖論在極少主義這種藝術形式中最早表現出來,也表現得最為徹底。米切爾在弗雷德有關極少主義的描述中找到了最為直接的呼應。
以極少藝術、初級藝術、基本結構與特殊物品等等說法而著稱的事業,主要是意識形態的。這種意識形態的事業想要宣布并占據一個立場——這個立場可以用語言加以表述,事實上它的某些主要實踐者也確實已經這么表述過了。如果說這個立場一方面讓它區別于現代主義繪畫和雕塑,那么,另一方面,則還標出了極少藝術——或者,我更喜歡稱之為實在主義藝術——與波普藝術或光效應藝術之間的重要差異。[5]155—156
弗雷德在《藝術與物性》的開篇即宣布了一個有關極少主義的事實:極少主義是一種用語言加以表述的極少主義,而非純粹視覺的極少主義。從20 世紀50 年代末被稱為極少主義先驅的弗蘭克·斯特拉的條紋繪畫實踐到1967 年《藝術與物性》發表,從極少主義的早期發展歷史可以看出,極少主義確實是一步步被語言和文本建構出來的,不僅存在“極少藝術”“初級藝術”“基本結構”與“特殊物品”等眾多說法,還有一個更為顯著的現象就是極少主義的創作者變成了針對極少主義的闡釋者,“他們一只腳踩著形象,一只腳踩著語言”,唐納德·賈德、羅伯特·莫里斯、卡爾·安德烈、馬克·迪·蘇維諾等人就自身的極少主義創作書寫了大量文字,他們的作品和文本共同造就了后來的極少主義。②比如Donald Judd,“Specific Object”,Arts Yearsbook,1965,8:74-82; Robert Morris,“Notes on Sculpture”,Artforum,1966,4(6),5(2); Carl Andre,“Preface to Stripe Painting”,in Dorothy Canning Miller (ed.),Sixteen Americans,New York:the Museum of Modern Art,1959; Richard Wollheim,“Minimal Art”,Arts Magazine,Vol.39,No.4,1965,pp.26-32; Barbara Rose,“ABC Art”,Art in America,1965; Mark Di Suvero,“The New Sculpture”,transcript of a symposium on “Primary Structures”,The Jewish Museum,New York,May 2,1966,Archives of American Art,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米切爾非常敏銳地抓住了弗雷德表述的重點,即極少主義藝術家自己成了作家這個事實,使得視覺藝術與語言藝術之間豎立的那堵墻被徹底推倒了。正如哈羅德·羅森伯格所言:“從沒有一種藝術形式曾經被熱心的文學合作者冠以更多的標簽……從沒有一種藝術比這些保證成為沉默的物質的作品更依賴于詞語……要看的越少,要看的越多。”[6]306此外,弗雷德有關極少主義的表述對米切爾的另一個啟發表現在“文字主義者”(Literalist)③《藝術與物性》的中文譯者將“Literalist”譯為“實在主義者”,筆者認為這個譯法不甚準確,詞根literal的意思是文字,應譯為“文字主義者”,更加符合弗雷德的原意。這個稱謂上。相較于極少主義,弗雷德更傾向于用“文字主義”來描述1960 年代的新藝術,其原因在于“極少主義”只能體現形式層面的意義,而“文字主義”卻能清晰地說明極少主義是被文字建構起來的極少主義,它代表了一種視覺與文字的混合。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弗雷德才將極少主義稱為一種劇場性藝術,除了藝術家可能蓄意營造的面向觀者的場面調度之外,與純粹視覺無關的文字話語可能也構成了劇場性的一個維度。
在有關極少主義的認知基礎之上,米切爾進一步發展出了它對后現代主義的獨特看法,即以極少主義為始的視覺與語言的混雜構成了后現代主義的典型特征,而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關系就是純粹與混雜之爭,所以,它在以羅伯特·莫里斯為例進行闡釋的時候作出了如下總結:“后現代主義本身始終貼著探索藝術與語言新關系的標簽。現代主義——至少在克萊門特·格林伯格的經典陳述中——尋求從視覺藝術領域清除語言、文學、敘述以及文本性。那么,后現代主義藝術被定義為否定之否定,‘語言在美學領域的爆發’也就不足為奇了。”[3]228—229
二、擴大領域的后現代主義
米切爾從圖像與文本之間關系的角度來認識弗雷德的批評文本,因為弗雷德明確指出極少主義是一種早就被其實踐者闡述過的藝術,而不是在純粹視覺的范疇內自行發展的結果,所以,他更傾向于稱其為“文字主義”。但這顯然只是有關弗雷德極少主義批評認知的一個方面,米切爾還沒有(當然他也不需要)進入弗雷德極少主義批評的核心。在吸收和消化賈德與莫里斯等人有關極少主義藝術的批評文本的基礎上,弗雷德提出了他的核心理論,即極少主義追求和突顯物性“只不過是對新型劇場的一種追求罷了,而劇場如今已成為藝術的否定”。極少主義之所以是劇場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關注觀者遭遇極少主義作品的實際環境,而這種遭遇不僅是視覺上的,更重要的是身體上的。這種觀者的身體上的遭遇致使極少主義作品的意義溢出了個人的私密范圍,而變成了一種公共模式。
較好的新作品將關系帶出作品,使這些關系成為空間、光線與觀看者視閾的一種功能。物品只是新美學中的術語之一。某種意義上它更具反思性質,因為由于作品比先前的作品更加強有力,帶有大量內部關系,人們就能注意到自己存在于與作品相同的空間里。人們比以往更清醒地意識到,他自己正在確立諸種關系,當他從各個不同的位置,在不斷變化著的光線與空間脈絡的條件下,去把握對象的時候……正是我們的身體與空間中的客體這種必要的、更大的距離(為了看到它的全部),產生了這種非個人的或公共的模式。但是,也正是這種介于客體與主體之間的距離,確立了一種更為廣泛的情境,因為身體的參與成為了必要。[5]161—162
弗雷德將極少主義作品(主要為雕塑)解釋為一種關乎空間中的身體的藝術,不僅是因為作品的意義訴諸觀者的身體,同時,作品本身也具有擬人的屬性。這種觀點給幾乎與他同時代的藝術批評家羅莎琳·克勞斯帶來了巨大的啟發,但克勞斯并沒有囿于弗雷德的判斷,而是將這種認識發散到了整個現代雕塑的歷史,從而得出了一種不同于弗雷德的對于極少主義屬性的認知,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他對后現代主義的理解。
1977 年,克勞斯在《藝術論壇》上發表了《雙重否定:雕塑的新句法》一文,這篇論文隨即被收入1981 年出版的《現代雕塑的變遷》,作為這本專論現代雕塑的專著的收尾章節。在這篇論文中,克勞斯花了大量篇幅對極少主義雕塑的典型特點(如重復性和序列性)及其意義進行了分析,最后得出了與弗雷德大致一樣的結論:“極少藝術家是要在根本上重新判定意義特定來源的邏輯,他們要求將意義視為發生在——繼續與語言的類比——公共空間,而非個人空間。”[7]262但與弗雷德不同的是,克勞斯并沒有據此認為極少主義是對現代主義的徹底背離,而是指出,這種藝術因為與空間中的身體的關聯而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現代雕塑的更新和延續。

圖2 以“黑”和“白”這組對立的語詞義素構建的格雷馬斯符號矩陣
如果我一直把過去十年中以極少主義為基礎的作品描述成雕塑歷史中意義深遠的新發展,那是因為它與之前剛發生的(現代主義)主流風格的決裂,再因為其構想中深刻的抽象性。然而,在另一個層面上,這些作品可以被視為對現代雕塑早期歷史中兩位關鍵人物——羅丹和布朗庫西——思想的更新與延續。這兩位藝術家的作品都代表了對身體意義原點的再發現——從位于內部的核心轉至表面——這種去中心化的激進作為中,包含了身體顯現的空間,以及顯現過程的時間。一直以來,我據理力爭我們這個時代的雕塑延續了去中心化的課題,但是,是通過一種極度抽象的形式語言。[7]278—279
克勞斯在羅丹和布朗庫西等人的現代雕塑中發現了一種為后來極少主義雕塑所共有的特點,即作品的擬人性以及空間中的身體。羅丹等人在現代雕塑中已經認識到作品表面對身體的指涉,而后來的極少主義雕塑不過是對這個特點的進一步抽象的延續。“極少主義的抽象性,使這些作品中的人體難以識別,因此很難放下所有的成見,設身處地把自己放進雕塑的空間。但我們的身體和我們對自己身體的體驗,繼續作為這些雕塑的主題。”[7]279—280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克勞斯認為,極少主義是現代主義雕塑發展的必然結果,雖然它自身也蘊含了與現代主義主流風格的斷裂。針對這種不是悖論的悖論關系,克勞斯在翌年發表的《擴大領域的雕塑》中進行了更具說服力的理論建構。
1978 年,克勞斯發表了其關于極少主義的著名論文《擴大領域的雕塑》,這個文本的最重要目的是從理論上厘清有關雕塑的概念與認知。因為克勞斯發現,到了20 世紀60 年代,我們已經很難憑借傳統有關雕塑的定義來認識當時出現的新作品,比如,狹窄的走廊、擺在廣場上的鐵片、劃入沙漠地表的臨時邊線等等,這些所謂的作品顯然已經超出了審美經驗的范疇,就像克勞斯所說,面對它們,我們似乎已經不能確定它們是什么,而只能確定它們不是什么了。1960 年代極少主義作品的出現導致的一個直接結果是有關雕塑概念的混淆,似乎“我們既知道又不知道什么是雕塑”[8]279。所以,克勞斯在這篇文章中的第一要務是建構一種新的有關雕塑的概念圖式。
借用一種克萊因群的指示關系,即格雷馬斯符號矩陣的一個版本(源于形式邏輯上的對當關系),克勞斯提出了“擴大領域的雕塑”概念。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是根據二元對立的原則發展起來的,最初由一組對立的語詞義素產生(圖2)。這兩個對立的語詞位于一根所謂“語義軸”的兩端,組成了意義的基本結構。譬如,S1 ?S2(比如黑與白、大與小等),它們之間是絕對否定的反義關系,于是兩者就構成了一根反義的語義軸。格雷馬斯認為,任何意義都不能單獨存在,而是有賴于它的對立面,兩者共同構成了意義的生發區域。④參見(法)格雷馬斯《論意義》(上),吳泓緲、馮學俊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年;(法)格雷馬斯《結構語義學:方法研究》,吳泓緲譯,三聯書店,1999 年。但是除了反義關系,語詞義素還存在矛盾關系和蘊含關系,比如,“黑”與“非黑”就構成了一對矛盾關系,“白”與“非白”也構成了一對矛盾關系,其中,“非黑”占據了語義軸上“黑”之外留下的全部位置,而“非白”占據了語義軸上“白”之外留下的全部位置。因此,“黑”與“非白”、“白”與“非黑”之間又存在蘊含關系。

圖3、4 克勞斯根據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原理構建的有關雕塑意義的符號矩陣
通過矩陣的演示,格雷馬斯將索緒爾有關語言的“價值”在于“結構性的差異之中”的籠統表述進一步系統化。意義不是來源于個別語言符號自身的規定性,其在符號矩陣中的位置決定了它的意義所在。克勞斯正是從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出發,將這種意義分析的模式應用到了雕塑的領域。按照克勞斯對結構主義的理解,雕塑的意義存在于與風景和建筑的結構主義關系之中,她以“風景”和“建筑”這對對立的義素為基礎構建了一個有關雕塑意義的符號矩陣(圖3、4)。如圖所示,建筑與風景之間構成了一根反義的語義軸(complex),建筑與非建筑、風景與非風景之間構成了矛盾關系,而風景與非建筑、建筑與非風景也構成了蘊含關系。通過這個矩陣,我們不僅能夠理解傳統雕塑和1960 年代的新作品,也能弄明白它們之間的關系。
現代雕塑由于其形式自律的屬性,擺脫了古典雕塑對于特殊場地的表征性的符號訴求,因而屬于非風景和非建筑的范疇(既不是風景也不是建筑),在克勞斯的雕塑符號矩陣中處于“neuter”這個語義軸之上。隨著雕塑的歷史發展到了極少主義,一方面,藝術家不希望他們的作品與古典雕塑一樣處于厚重的符號語境之中;另一方面,極少主義也擺脫了現代雕塑對本體形式的關注,而側重表現作品所在的真實空間及其光線,以及觀者的視野。在對雕塑本體形式的拋棄中,極少主義藝術更多與場地發生了聯系,但這種場地并不是古典雕塑的那種特殊場地,不涉及符號意義,而是對場地的直接涉及,這就使極少主義作品被置于建筑與風景這根反義的語義軸之上,既是風景又是建筑(site construction)。但是,在克勞斯看來,極少主義這類新的作品也可以利用這個符號矩陣中的其他關系予以界定,比如建筑與非建筑之間的矛盾關系,即建筑之中的非建筑,此乃一種“自明性結構”(axiomatic structure);風景與非風景之間的矛盾關系,即風景之中的非風景,此乃一種標記性方位(marked sites)。總之,極少主義雕塑的意義處在建筑和風景之間構成的各種結構性差異之中。[9]588
我們可以對克勞斯的拓展領域之后的雕塑的發展趨勢進行劃分:一種介于建筑與非建筑之間,另一種介于風景與非風景之間。如果按照后來的藝術史術語來看,介于建筑與非建筑之間的雕塑更傾向于與建筑融合,這類作品或多或少都對真實的建筑空間進行了干預,有時是通過部分重建的方式,比如羅伯特·莫里斯、唐納德·賈德、卡爾·安德烈和索爾·列維特等人的作品。而介于風景與非風景之間的雕塑則進入到了更為自然的空間,最終衍化為大地藝術的形態,比如邁克爾·海澤、理查德·塞拉、理查德·朗,以及羅伯特·史密森等人的作品。[10]45
通過對比1977 年和1978 年的兩個批評文本,我們似乎發現了克勞斯有關極少主義認知的轉變,即從作為現代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到作為與現代主義的歷史性斷裂,從這點來看,克勞斯與弗雷德的分析殊途同歸。但無論態度如何轉變,極少主義帶給克勞斯的最大遺產在于,它極大地拓展了定義雕塑藝術的參數,這也使她沒有像弗雷德那般認為極少主義是對藝術的否定而對之予以拒絕,相反,因為極少主義對藝術的革新和拓展而予以大力支持。擴大領域之后的藝術是什么呢?即后現代主義。“為了對這種文化領域的歷史性斷裂與結構轉型進行命名以便描述,我們不得不求助于其他術語,一個已經在另一個批評領域中被使用的術語就是‘后現代主義’。似乎沒有理由不去使用這個術語。”[8]287顯然,在克勞斯的批評領域,后現代主義站在了現代主義的對立面,這種觀點與弗雷德無疑又是一致的。
三、作為新前衛主義的極少主義:通向后現代主義的范式轉換
無論是賈德、莫里斯和弗雷德在20 世紀60 年代與極少主義藝術發展同步的有關這種新藝術的元批評,還是后來克勞斯站在結構主義的立場對極少主義藝術所進行的后現代主義的理論定性,這些文本無一例外都將極少主義視為與晚期現代主義藝術具有一種延續和斷裂的辯證關系。但是,對于極少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關系,這些文本卻鮮少涉及。克勞斯的《擴大領域的雕塑》只是使用了當時頗為流行的后現代主義這個概念作為描述極少主義的術語,卻并沒有深入闡釋極少主義作為后現代主義的邏輯依據。道格拉斯·克林普的《圖畫》和克拉格·歐文斯的《寓言的沖動:朝向后現代主義的理論》只是顛倒性地利用了弗雷德提供的劇場性以及相關的時間性概念來描述1970 年代的后現代主義藝術現象。對于極少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邏輯關聯這個問題,只有哈爾·福斯特給出了一種大膽、新穎而又令人信服的回答,當然,他的寫作仍然是建立在弗雷德《藝術與物性》以及其他針對極少主義的元批評文本的基礎之上的。
1986 年,剛過而立之年的哈爾·福斯特撰寫了一篇題為《極少主義的關鍵》的文章,此文后被收入其1995 年出版的代表作《實在的回歸:世紀末的前衛藝術》。在此文中,福斯特為了證明極少主義在邏輯上為后現代主義藝術實踐開辟了一片新的領地,而對有關極少主義的批評文本進行了細致的解讀和批判,并從中得出了一種反記憶或對抗主流的理解模式,以此來定義極少主義與晚期現代主義和新前衛藝術的辯證關系,并由此提出一種從極少主義所在的1960 年代到福斯特寫作此文的1980 年代的藝術譜系。“在這一譜系中,極少主義不是一條遙遠的死路,而是當代的一個關鍵,是通往今天仍然繼續苦心經營著的后現代主義實踐的一種范式轉換。”[11]46
福斯特首先指出,自1960 年代出現以來,極少主義及其重要性并沒有得到應有的正確認識,在1960年代由于被認為是現代主義本質的還原而遭到諸如格林伯格和弗雷德等人的嚴厲批評,在1980 年代則由于新保守主義的政治背景而被視為過時。針對這個現象,福斯特首先為極少主義給出了一個新的定位:“極少主義不但舍棄了大部分傳統雕塑中的擬人化基礎,也拒絕了大部分抽象雕塑中毫無地點限定的方式。簡言之,有了極少主義,雕塑不再孤立地站在一個基座上或者被看作純藝術了,而是在各種物品之間重新定位,根據地點而重新定義。在這種轉化中,觀者拒絕了形式藝術向來保有的安全的、獨立自主的空間,退回了此時、此地;不是要審視作品的表面,尋找其媒介屬性的地形分布,而是受到激發去探索在一個既定地點的某個特別的介入所造成的知覺效果。這就是極少主義所開辟的根本性的新定位。”[11]148
福斯特所說的“極少主義所開辟的根本性的重新定位”并不是他的創造性觀點,而是從1960 年代針對極少主義的元批評文本中總結出來的。福斯特重新梳理的文本是1960 年代主導極少主義批評的三個元文本,即賈德的《特殊物體》、莫里斯的《雕塑札記》和弗雷德的《藝術與物性》。正是對這些文本的重新梳理和結構主義的閱讀,使他發現了一直以來為人所忽視的有關極少主義的重要方面:賈德、莫里斯、弗雷德乃至后來的克勞斯都提到了極少主義是與現代主義的斷裂,但這種斷裂是如何發生的,卻極少得到有效的認識。在福斯特看來,賈德描述的物品對美學范疇和既定形式的越界,莫里斯提出的雕塑超越認知的拓展領域及其意義從物品到觀眾的轉向,以及弗雷德提出的劇場和情境等概念,都只能作為極少主義與現代主義斷裂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那天在路上的體驗是某種被籌劃的東西,只不過尚不為社會所認識而已。我心想,應該清楚的是,那就是藝術的終結。打那以后,大多數繪畫看上去都只是漂亮的圖片。你沒有辦法給它加上框,只能體驗它。”[5]166在托尼·史密斯有關自己曾經在一段未完工的高速路上夜行的文字中,弗雷德敏銳地指出,托尼·史密斯體會到了繪畫之為繪畫或藝術之為藝術的本質在于藝術的慣例性質或本質(體制),而極少主義顯然是對這種慣例性質的否定。在福斯特看來,極少主義對藝術慣例性質的否定和拒絕,不僅僅是弗雷德反對極少主義的關鍵所在,更是極少主義與晚期現代主義的決裂之處,它構成了兩者之間決裂的根本原因。極少主義對藝術慣例性質(體制)的否定,使得它被歸入了前衛主義的行列,這是福斯特在弗雷德基礎上的進一步深入。弗雷德雖然認識到了極少主義是對藝術的拒絕,但他并沒有踏前一步為其勾勒一個藝術史的譜系,但福斯特做到了這一點。
極少主義從晚期現代主義中發展出來,只是為了破壞它,污染它,正如極少主義已經被劇場所毀壞、污染一樣。但是這劇場所代表的,不僅僅是與視覺藝術不相容的對時間的關注。作為“對藝術的否定”,它也是前衛主義的一個代名詞。于是我們得出了以下方程式:極少藝術與晚期現代主義的斷裂,是通過對歷史前衛藝術的部分重復,尤其是重復歷史前衛對于體制藝術的形式范疇的破壞。要理解極少主義——也就是理解它對于以后的高級藝術的意義——就必須同時領會這個方程的兩個部分。[11]64—65
福斯特所說的方程式的兩個部分,其中一個是極少主義與晚期現代主義的斷裂,另外一個就是極少主義為后現代主義藝術的來臨做了準備。前一個部分自不必說,賈德、莫里斯和弗雷德等批評文本的發展演變早已說明了這個特點。至于后一個部分,即極少主義為后現代主義藝術的來臨做了準備,這個譜系說成立的關鍵在于極少主義作為新前衛主義的定性,因為后現代主義主要是對現代主義藝術體制的批判。福斯特不僅從弗雷德的批評文本中獲得了結構主義的發現,極少主義者的藝術實踐也予以了充分的證實,因為他們指望從越界的前衛藝術中借鑒藝術實踐的其他可選模式,比如“安德烈轉向了亞歷山大·羅德琴科和康斯坦丁·布朗庫西,弗萊文轉向了弗拉基米爾·塔特林,還有很多藝術家轉向了杜尚”。[11]66
正是這個方程式使得極少主義成為了歷史的一個關鍵點,因為它提出的不僅是一個關于現代主義藝術的觀點,還是關于后現代主義藝術的一段譜系,因為后現代主義藝術正是在作為新前衛主義的極少主義反思和批判藝術體制的基礎上展開敘事的。福斯特的《極少主義的關鍵》一文為我們理解極少主義打開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他從弗雷德對于“極少主義是一種新型的劇場,而劇場是對藝術的否定”這一宣言出發,將極少主義如波普一樣歸入戰后新前衛主義的行列。雖然這種解讀的有效性仍然有待歷史的檢驗,但不失為一個有關后現代演繹的好的范例。
綜上所述,米切爾在對現代主義理論的修正中發展出了他的關于后現代主義的混雜性理論;克勞斯將后現代主義理解為有關藝術概念及參數的拓展;而福斯特以極少主義為關鍵的分界點為后現代主義構建了一個藝術體制批判的新前衛系譜。所有這些后現代藝術理論家的不同觀點詮釋了他們對弗雷德理論的不同理解,同時,這些多元的結論也揭示了批評的自主性與主觀性。無論這些針對后現代主義的不同見解有著多大程度的合理性,毋庸置疑的是,弗雷德的《藝術與物性》及其劇場性理論作為一種獨立而客觀的存在,最早從批評和理論的角度間接提出了后現代主義這個復雜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