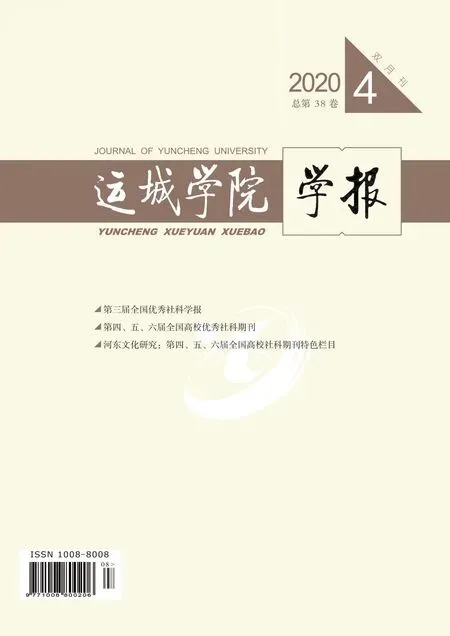“村政建設”與近代山西鄉村社會變遷
——兼論“村政建設”的失敗原因
張啟耀,馮婉婷
(1.運城學院河東文化研究中心,山西 運城044000;2.山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山西臨汾041000)
到目前為止,學界關于閻錫山“村政建設”的研究成果并不少,所論述角度也較為廣泛,從“村政建設”的起因、內容、實施過程到基層政權建設等,如肖君的《閻錫山村政建設之實踐》著重論述以“村本政治”、“用民政治”和“土地村公有”為中心的運動內容;成新文在《評閻錫山的村鎮建設》一文中著重敘述了“村政建設”的發展階段和實施過程;謝泳在文章《山西村政建設中的“制度設計”》中認為,雖然閻錫山的鄉村建設計劃在實踐上沒有成功,但在理論上卻有著獨特的“自治”制度設計;祖秋紅的博士論文《“山西村治”:國家行政與鄉村自治的整合(1917—1928)》在分析山西“村政”性質的基礎上,論述了國家與基層社會的融合滲透狀況;任念文在《民國時期山西“村政”改革績效透視》中探尋運動過程中出現的主要問題,以此分析運動的體制建設與實際功能之間的巨大差距等[1-6]。
以上成果從不同方面對“村政建設”予以闡釋,極大豐富了相關研究內容,但關于這一運動對近代山西鄉村社會的影響以及運動最終無果而終的原因至今在學術界并無定論,也很少有人專門論及,即使有學者提及,也語焉不詳。在當前國家日益重視“三農”問題的背景下,深入探討近代山西鄉村的相關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基于此,筆者以相關資料為基礎,經過深入分析,在前人評價和學界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村政建設”在近代山西鄉村社會變遷中的作用以及運動的失敗原因,以期促進這一研究領域獲得新的進展。
一、“村政建設”內容及時人評價
從20 世紀20 年代初開始,在偏僻落后的山西社會,閻錫山以“村政建設”的制度設計與實踐曾吸引過眾多學者和政客到山西考察和研究,山西省也因為這個運動而一度被譽為“模范省”,成為其他省份實施自治的榜樣。
“村政建設”是閻錫山從民國初年開始推行的新政措施,包括最初的“六政三事”“村制”改革到后來的“土地村公有”,從農村的生產技術到風俗習慣都在改革范圍之內,因此是一個系統的農村改制計劃。
關于這場改制,當時有學者曾夸耀它是“中國改造之先驅”[7]4,就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也在運動初期認為它“開創了中國下層政治重心之先河”,并通過互助合作的方式去解決民生經濟問題[8]6-8。因為直至滿清時期,中國的農民仍然是“向來沒有聯絡,像一片散沙一樣”[9]463。閻錫山執政山西以來,隨著“村制”的實施和“編村”的組建,農民的團結意識得到開發,農民也具備了團結起來對社會不平進行抗爭的組織條件。20 世紀20 年代中期,晉南臨汾地區曾發生了一次反苛捐雜稅的斗爭,農民在斗爭中破天荒團結起來,提出了自己的抗稅口號,說:“我們只要頂得硬,一成也可以不捐的,恐怕村長副們頂不住,我們大家走,走!走!走!給村長副們助威走!”[10]14這一事例表明,山西農民在傳統時代只關心自己幾畝薄田的分散狀況已得到較大改觀。
閻錫山“土地村公有”主張雖沒有付諸實施,但它的提出卻在整個中國引起巨大反響。當時著名社會學家李景漢稱贊說這是一個“革命式”的主張,“把握住農村的根本問題,其識見之遠大,負責之精神,殊足令人欽佩”[11]145。連一向極力鞭撻南京政府財經政策的近代經濟學家孫曉村也認為,“國民革命就有耕者有其田的原則,經政府承認但沒有辦到……于是山西閻百川先生‘土地村公有’來補充這個辦法”[12]65。
不過,隨著運動的推進和情況的變化,后來批評“村政建設”的人越來越多。太原鄉紳劉大鵬以親身體驗在日記中記述:“吾晉省稱模范之省,而群黎百姓十室九空,受政苛虐,迥異尋常……家家戶戶無一不嘆,無一不窮也。”[13]285-286較激進的人士更評論說,山西村政是“在封建制度的本質上,加了一件‘村治’的新裳而已”[14]58。尤其是土地村有“把土地的分配權屬之于村民大會和村公所,這無非為握有村政大權的地主階級多一層政治上的保障而已”[15]1-2。此外,如從他個人的主觀目的來看,“實際上他是完全為了他們本身集團利益著想的”。“與其保有那日漸落價的地權,何勝把它變成錢用呢?”[14]60
另外,閻錫山在《土地公有案辦法大綱》第九條規定:土地村公有“推行之初,耕農對省縣地方負擔仍照舊征收田賦”[16]5。所以,“地主田地由村公所收買之后,與田地所有權連在一起的田賦等負擔也移到農民肩膀上去了”[17]55。更為嚴重的是,實行“土地村公有”也有讓農民失去人身自由之虞,因為“土地因村有而分配權完全掌握在大地主手中。從前土地私有,則有田的農民尚是一國獨立自由的公民,而土地村有之后,農民都變成村長們的奴隸或附庸,農民因為要領田,不得不忍氣吞聲的向大先生們屈服,而大先生們也借此更可以作威作福了”[18]1。
二、運動對山西鄉村社會變遷的影響效果
山西省地處內陸地區,雖然在封建社會末期由于“晉商”的崛起而聞名于世,但前近代以來,整個山西社會便一直處于封閉落后的狀態,當時就有一個非常典型的事例,清朝中期推行的“攤丁入畝”制度,直到光緒中后期才在山西全省范圍內開始實施。
辛亥革命后,閻錫山逐漸控制了整個山西政局,并隨后在全省范圍內開始實施“村政建設”,但這些“村政”措施在實施過程中到底效果如何?這場運動與近代山西鄉村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又是怎樣?這是拙文首先重點探討的問題。以下從幾個方面分別予以論證。
(一)農村經濟與農民生活
對于“村政建設”早期的實施效果,曾有學者給予高度贊揚,認為運動的實施使山西全省“盜匪絕蹤,窮乞罕見,社會秩序為各省所不及”[19]56。即使在進入20 世紀30 年代之后,類似這樣的贊揚仍不絕于耳。
不過,通過對史料的全面分析,筆者認為,以上對運動的正面評價有些是處在20 世紀30 年代早期以前,有些是從某一特定方面,如軍工行業發展、政府對鄉村社會控制等來進行評價,并不能完全、真實地反映當時運動實施的效果。
1929 年,時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趙戴文在講話中不無憂慮地說,現在“民生困窮,達于極點,不事設法救濟,則弱者轉于溝壑,強者鋌而走險,其禍自不敢設想也!”[20]27全省整體情況可見一斑。下面分區域詳細分析。先以晉西北為例,當地農民甚至在三四十年代時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依然十分簡陋,“絕大多數農民終歲辛勞,也只能維持最低層次的生活標準”[21]86。山西中部的太谷縣,上世紀20 年代中期,當村政人員調查該縣時,當地鄉民愁容滿面地說:“你們是整理村范的,你們是調查太谷社會情形的,但是敝村這般沒有生氣的樣子,真是教人凄慘!”[22]2太谷縣北堡村原來較為富裕,人口有一千三百戶,商號有三十六家,但到了30 年代中期,就“只有六十戶,商店連一家也沒有了”,因為這些人家“絕少遷移,大部分都是死亡了”[23]73。而晉中農村的情況是,到30 年代,“斷炊之家,大批地在農村里面出現了”[23]75。即使是較為富足的地方如晉南的永濟縣,在30 年代初也是“哀鴻遍野,窮黎失業,民間困苦情狀不堪言喻”[24]1391。就連閻錫山本人也說:“年來(指1935 年以來)山西農村經濟整個破產,自耕農淪為半自耕農,半自耕農淪為佃農雇農,以至十村九困,十家九窮。”[25]898
除此之外,閻錫山的建設目標在很多時候往往落空,尤其是改革方案中提到的對鄉村下層民眾的承諾多未實現。例如,閻錫山曾于1920 年10 月把自己的改革方案遞交給大總統,提出了改革的具體步驟,認為鄉村要實現自治必須經過四個階段。在其中的第二階段,閻錫山提出的目標是“以編村為撫恤團體單位,救濟那些鰥寡孤獨疲癃殘疾,實在無自覓生活能力,而又無親屬可依賴的貧乏之人”[26]83。但政策實施的結果“卻是少數的當局要人”成為最大的利益獲得者[17]55,廣大貧苦農民在日益沉重的稅費負擔之下生活更加苦不堪言。太原縣鄉紳劉大鵬在1927 年1 月31 日的日記中記載:“山人見予即言:支應軍差,攤派甚巨,即極貧之家亦攤十余元大洋,苦甚矣。”[13]350因此,閻錫山連那些普通農戶的基本生活都沒有保證,更不用說那些“鰥寡孤獨疲癃殘疾,實在無自覓生活能力”之人了。
以上農村經濟和農民生活狀況正是當時山西鄉村社會的真實寫照,體現了閻錫山鄉村建設的基本成果。這期間,“村政建設”從發端時期對農村社會的美好設想最終走向破產,其結局令人唏噓,個中原委容后再詳細分析。
(二)鄉村財政管理狀況
晚清時期,中國官場貪污成風,嚴重影響著基層社會的管理和運行。清末民初,雖然各地自治機關紛紛成立,但官場的腐敗惡習仍舊存在。由于閻錫山的縱容和自身特殊的用人制度,“村政建設”實施過程中財政管理的腐敗現象并沒有較大改觀,極大阻礙了近代山西鄉村社會的發展和變遷。
閻錫山搞“村政建設”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從農村獲得更多的財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不惜默許村政領導階層胡吃亂喝。閻錫山自己在講話中曾以府十縣為例說,雖然村費花得很多是一件壞事,“但村人樂于當糾首,為在社會上吃一年好飯,因而把村中應辦的亦就辦了”;如若不讓“糾首”在社會上吃飯,這些人“便不到社會上,為公家辦事之心亦懈矣”。[27]102
20 世紀20 年代末和30 年代初,山西村財政管理一度較腐敗,各地村長副貪婪成性,村中公款耗費有增無減。如山西省民眾監政運動會主辦的期刊《監政》在1934 年第4—5 期的第3 頁到第10 頁就多次提到:渾源村長之魚肉鄉民,祁縣村長之營私舞弊,介休村長之以暴易暴,武鄉村長之剝削貪婪,屯留村長之無恥敲詐,汾陽村長之黑幕重重等等。類似這樣的腐敗現象愈演愈烈,嚴重影響著閻錫山政權的聲譽和統治秩序,以致政府不得不對腐敗行為采取一定的約束措施。1933 至1935 年的清理村財政報告中就曾說到:“村款糜濫,為數極巨,切膚之痛未除,固不足以言建設而圖救濟。”[28]
閻錫山的用人制度在某些方面又對基層管理人員的腐敗行為起著縱容作用,導致基層腐敗現象越來越多。閻錫山曾公開表示:“使功不如使過。”他認為一個人在犯罪或者犯錯時重用他更能使他為己所用。如晉南夏縣縣長趙良貴因貪污腐敗情事被民眾捆縛,身插白紙旗,游街數十時,沿街自叫“我是貪官趙良貴”,轟動全省。但如此貪官被重新任為縣長后因不知悔改而再以貪污陷法網[29]9。再例如,閻錫山掌握了曾任平遙縣長的孫煥侖的嚴重腐敗行為后,孫痛哭流涕,請求赦免死罪。令其始料未及的是,閻不僅免其死罪,且在幾年后大升其官,又將此犯擢升為省民政廳廳長[30]8。如此腐敗的用人制度直接導致了政府官員貪污行為的盛行,加劇了行政制度的黑暗。
基層腐敗愈演愈烈,但閻錫山把這一切都歸因于鄉民對村長副選舉的不慎。他自己在《告示各縣人民慎選村長副文》就提到“近年以來,控告村長副的案子,各縣常有”,但“與其選出壞人,受了他的害,再去控告,何如未選之前,大家斟酌誰是本村的好人,到村民會議,親自投票,就把他選出來”[31]《告諭》9-10。如此這般,腐敗源頭得不到根除,鄉村社會的財政秩序也不會有大的改觀。
此外,雖然“村政建設”第一次真正將國家權力下移到村一級,但必然造成官僚機構不斷膨脹[32]297。結果,隨著政府官僚機構的日益龐大,再加上前述閻錫山本人對地方官員任命的隨意性,幾個因素共同加劇了行政腐敗的發生。因此,“雖然政府在近年來,高唱‘廉潔政治’,其實全屬空談”[33]16。
(三)山西的民風和社會秩序
南京政府前期,“村政建設”對山西鄉村行政體制的完善起了一定作用,再加上當時整個山西基本上一直處于閻錫山統治之下,軍閥勢力單一,統治權相對集中,使得山西農村的生產和生活秩序相對其他很多省份來說較為安穩[34]120。從民風來看,20世紀20 年代,山西社會“人知自好,鮮蹈法犯刑之事”,因此“有模范省之譽”[35]77,曾有一些學者對民初山西與鄰省的治安環境做過比較,如梁溯溟先生在1929 年考察鄉村社會時就對照山西、廣西、廣東、湖南、四川、陜西等地方,并贊揚“山西在這方面,無論如何……有一種維持治安的功勞”[36]445。還有學者認為“山西一隅,村村有制,鄰鄰相安,符蓬絕跡,民無游惰”,“有此治績,亦非一朝一夕之力所可幾及也”。[37]242
不過,以上所言都是“村政建設”早期曾經出現的社會秩序,從整個運動來看,“村政建設”的正面作用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就連一向極力對之稱贊的梁漱溟后來也說這一運動基本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38]892。而那些到過山西的名流,“由他們言辭間很可以看出,是出于至誠,謂山西政治前途無望”[39]5。之所以“名流”們有這樣的看法,是因為當時山西的所謂“秩序”正體現了閻錫山嚴密控制的行政網絡。閻錫山曾毫不掩飾地說:“大凡世界各國,其行政網愈密者.其政治愈良好、愈進步。”[40]1通過縣、區、鄉、村、閭、鄰的層級結構,閻錫山構建了嚴密的組織和警察力量,“好像能把每個人都置于他的控制之下”[41]139。鄉民從婚喪嫁娶到吃喝拉撒,從婆媳吵架到種地打柴統統有人監視著,哪里還可能做破壞“秩序”的事?
另外,雖然山西的軍火工業發展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增加了,但貧苦百姓的生活依舊,所謂的某些“建設”對窮人來說也是“禍民”。如以當時對晉南河津縣的一份調查報告中所提到的保衛團為例說明。調查提到當地的保衛團“實為空增負擔、無裨事實之秕政。蓋所謂團丁者,皆點驗時臨時雇傭之夫”,“間有少數長雇之人,亦不過供村長驅使”[42]427。所以,當時梁漱溟先生分析說,長此以往,“村民一面對于村政,亦有疲累厭煩之意……而村中所辦唯一的一件事,即那小學校,近看不生利,遠亦望不到好處。此外更無什么于他有好處的了”[43]272。即使如劉大鵬那樣生活條件較好的鄉紳也在日記中說:“閻錫山系晉人,而其把持晉政,無一非禍晉人之政。予向乎閻錫山,人皆惡聞之,今乃皆謂閻禍山西日甚一日,較甚于前矣。”[13]463
隨著這場改制的推行,農村貧困百姓的負擔日重一日,這也從各縣呈送省府村財政清理報告中可知一二。據1933 年省政府統計,全年全省“各村支出總數為一千一百三十五萬六千一百八十七元,按全省總戶數二百一十七萬七千八百八十六戶計,平均每戶負擔五元二角一分,其中徐溝、榆次、太原等縣每戶竟負擔在十五六元以上,乃至二十四五元,似此情形,民何以堪”[44]。
通過以上三方面的論述可以看到,閻錫山“村政建設”的實施成效并不明顯,很多措施并沒有落到實處,所以,“村政建設”并沒有給山西鄉村社會帶來明顯的變化,山西社會封閉、落后的狀況也沒有較大的改變,尤其是農村中下層民眾的生活并沒有什么改觀,甚至到20 世紀30 年代中期,整個山西鄉村社會陷入了普遍的貧困化。[45]針對最后的結局,閻錫山本人曾說:“各縣辦理村政人員,忙于辦差籌款,不暇顧及村政,以前成績難免退步。”[31]4-5而整個村政“創辦以來,因時會上種種關系,未能收圓滿效果為可惜耳”[27]10。
三、運動失敗原因簡析
由于歷史進程的復雜性,任何對于歷史事件的分析和評論都不免帶有一定的偏差性。以現代人的眼光來探析“村政建設”失敗的原因當然也不免會“走樣”,但是,帶著審慎的態度盡量多地搜集和研究相關史料以做到盡力貼近史實,算是對歷史應有的尊重,也是對自身辛苦付出的一點安慰。由于近代中國社會的轉折性和復雜性,研究山西近代“村政建設”失敗的原因就具有了一定的挑戰性。
由于篇幅所限,雖然這場運動失敗的原因可能很多,但筆者在此想重點闡述以下幾點,以作拋磚引玉之用。
首先,從農村和農民一方來看,“村政建設”并不具備實施和推動的土壤。
一方面,近代以來國家在掠奪社會資源過程中與基層社會已逐漸形成對立局面,尤其是農民對晚清以來各類運動具有了天然抵觸性。因為“自清季到民國歷次舉辦新政,卅余年間無一次不是欺騙農民,農民聽到新法新政就厭嫌頭痛”,“退縮逃避之不遑,則向前參加之機益以絕”[46]4。所以,農民從心底里并不認同政府倡辦的任何運動,對于政府的一切工作均不抱好感,反正都是迫害農民的東西。農民與政府人員打交道不是恐懼便是抵觸,如農民們說,“一聽見調查員到了,我們的大腿就發抖”[47]1。這一情況正是“村政建設”失敗的最廣泛的社會因素,而并非像政府人員所言“村制區制之設,事屬創舉,地方紳民,不明宗旨所在,難免疑慮叢生,有所阻礙”[48]20。
另一方面,從舉辦的內容來看,運動只涉及村容村貌、鄉民的日常舉止行為等,并沒有對鄉民的糊口問題過多關注和解決,而且閻錫山對農村發展也沒有投入多少資金,反而以各種方式加大對農村的剝奪力度,“村政建設”的結果可想而知。如當時梁漱溟就說過,“他所辦的事情,只不過籌經費、定章程、立機關、派人員,人員虛擲經費即完了”[49]162。比如說,1935 年山西省政府曾在《鄉鎮年度財政支出概算表》中大致羅列了鄉村主要年度花費。這些花費雖巨,但都為鄉民所繳納,并無政府撥款,可以說,政府是拿了鄉民的錢去辦了所謂的“自治”事業。這些冗繁的費用主要如下:教育費、警衛費、鄉鎮公所辦公雜費、差務費、建筑費、行政雜支、社事費等,每一項下面又分為若干小項,可以說,費用層出不窮[50]298。再如,自治機構人員的辦公薪金也由鄉民支付,一些新奇的機關不斷涌現,“像防共保衛團啦!主張公道團啦!棉花檢查委員會啦!”[51]80面對頻繁索取,鄉民哪里還有心思參與到運動中呢?所以,當局慨嘆,兩年來的“一切新興政治之設施,一般人多不了解,且多慣于多年舊習,安于偷閑放任,因之非難阻礙者多,而推動贊助者少”[52]26。
其次,失敗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地方上缺乏熱心能干的辦事人員。
縣長一職在閻錫山基層政權建構中占據主要地位,是省政府政策實施的關鍵核心,受到閻錫山高度重視,因為“我們山西的村政雖是由省府當局提倡起來的,但其著眼點也完全在縣上”,“村政是縣治的村政的精神”。[53]52但是,“清季以來,上下以公文相欺,吏治遂以日壞”[54]1。而縣長則首當其沖受到吏治敗壞的直接影響,這一情況直到民國時期依然如此,嚴重影響和制約了閻錫山“村政建設”的實施效果。閻錫山曾在訓令中說:“近聞各縣仍有蹈前積習,私做虎盤情事……似此上下相蒙,尚復成何事體?”[54]1對于“村政建設”的宣傳和推動工作,各縣縣長很多時候都是敷衍塞責、不甚認真,無怪乎政府在下達的訓令中指責“各縣縣長多不下鄉,以致諸政均形廢弛”[55]2。而左云縣“共有編村九十二,而表內僅列七村,足證該縣長對于填報表冊漠不關心,殊屬玩忽已極”[55]49。此外,“各縣對于村長副之人選,事先不甚注意,選舉之后,又不勤加指導,以致專橫舞弊者在所不免,敷衍塞責者,又復濫竽從事,阻礙村政,莫此為甚”[55]31。其他縣長在運動實施過程中的表現,令文里也多有批評,如興縣縣長楊希唐“辦事疏忽,輿論欠佳”、武鄉縣長白連三“能力薄弱,聲名平常”、夏縣縣長彭啟泰“才具平平,經驗亦差”、虞縣縣長趙聯珩“優柔寡斷,貽誤要政”等等。[56]64更有甚者,省政府派出視察村政的一些委員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實施腐敗行為,如訓令中記載,“各縣知事對于上級官廳委員到境,每多餞送筵宴及其他應酬情事,其不肖委員亦往往藉端需索,甚或折收車馬費希圖肥己,知事一有拒絕,遂敢不畢乃事,中道而返”[54]16。嚴重影響了“村政建設”的實施效果。
面對實施困境,山西省政府曾不斷對各地方官員予以引導、批評甚至處罰,試圖挽回頹局。從1928 年到1929 年期間省政府送達晉南猗氏縣知事的兩個公文中有明顯的表現。《山西村政旬刊》在1928 年第5 期第8 頁登載的《據報該縣第一區區長懈于下鄉飭據實報核并撤換王寮村閭長楊維長由》一文認定“該縣第三區王寮村一閭閭長楊維長品行不端,閭人反對并應撤換另選以順輿情”;吳樹滋和趙漢俊主編的《縣政大全》(第4 編)第123 頁登載的《山西省政府致猗氏縣知事對于煙禁應努力前進函》批評猗氏地方官員“因循敷衍,上下相蒙,各適其適,此正從前官僚積弊所在”。針對這些官場上的弊端,閻錫山痛心地說:“無論多少辦法,多少團體,知事心力不到,俱是假的!”[57]126閻錫山在這一點上的認識還是比較到位的。
區段村負責人的好壞,關系著最基層民眾的利害,影響極大,而不良區長、段長、村長副對“村政建設”實施效果必然產生極大負面作用。“右玉縣第三區區長閻傳不能遵章服務,竟派遣警士到各村詢問村長如無浮濫開支即行取結了事,并對吳家馬營村長韓英俊侵吞村款八十余元事前未能察覺,后經村民報告亦不予深究。”[58]8晉南絳縣“掾區各員多屬萎靡辦事,涉于敷衍,各項成績均無進步”[59]6。永濟縣“第二段主任展希惠、第八段主任尚友連懶于下鄉,廢弛村政。第九段主任祁居銓藉口下鄉時常居家,并有吸煙嫌疑”[60]4。如此這般,上面的命令一道接著一道,下面的地方辦事人員敷衍潦草、虛與委蛇,“村政建設”辦了十余年自然難有成績。
除了以上兩個重要因素之外,運動的失敗原因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從表象上看,“村政建設”是振興山西農村的一系列實施方案,但實際上,閻錫山賦予了這場運動以極強的“自治”色彩。既然其本質上是一場喧囂一時的自治運動,那就自然避免不了那個時代各類自治運動的相同命運。
民國初期,各地紛紛舉辦自治運動,“當局者尤其亟亟從事”,“國民政府督促于上,各省政府趕辦于下,即要‘克期完成’”。[46]1-2如此,自治運動辦了十多年,政府也是十分的努力,“可是我們若從實際方面去觀察,又覺得各省籌備地方自治的結果,確實沒有多大的進步”[61]7。究其根源,是因為“各縣的自治機關,等于虛設”,“只做些紙面文章,不與民眾接近。農民疾苦,向不知曉;公共事業,根本不問”。[62]36長此以往,所謂的“自治”得不到民眾真心支持,等待它的也只有消亡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