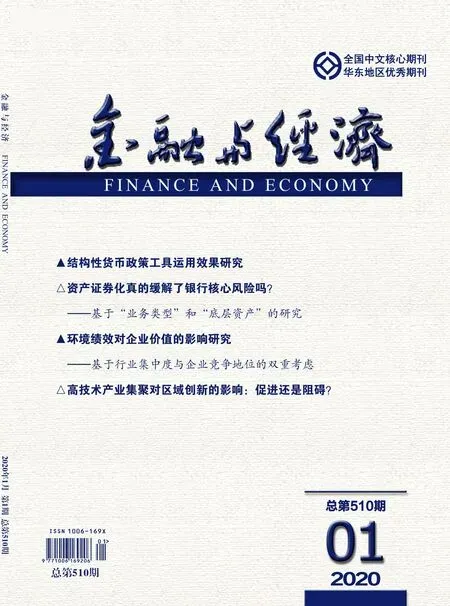資產證券化真的緩解了銀行核心風險嗎?
——基于“業務類型”和“底層資產”的研究
■郭子增,王福臣,王 龑
一、引言與文獻回顧
1968年,美國政府全國抵押貸款協會(GNMA)開全球資產證券化之先河,首次發行了資產支持證券(ABS)。此后,資產證券化逐漸得到各大經濟體的認可,在世界范圍內快速發展,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然而,關于資產證券化,我國監管當局一直持謹慎態度。直至2005年,我國才正式推行了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但之后受美國次貸危機影響,我國監管當局出于審慎考慮暫停了試點工作。2012年,為了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我國重啟了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伴隨著監管的放松、政策的利好,我國資產證券化實現了快速發展。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亞洲最大的資產證券化市場,僅2018年的發行規模就突破了2萬億元。
資產證券化作為商業銀行轉移風險的重要手段,其積極意義不言而喻。但是,次貸危機的經驗教訓也昭示著需要警惕資產證券化的潛在風險。黨的十九大更是提出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將防控金融風險列為當前階段我國金融工作的根本任務。那么,資產證券化真的可以緩解銀行風險嗎?
關于資產證券化與信用風險的關系,已有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兩類觀點:其一,資產證券化可以降低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Casu et al.,2011)。此類觀點認為,資產證券化是商業銀行重要的風險轉移手段,通過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商業銀行可以將信用風險轉移給投資者,從而降低自身的風險承擔;其二,資產證券化會加劇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Franke&Krahnen(2005)發現,商業銀行即使開展了資產證券化,后續投放同類貸款仍然會促使其信用風險的上升。Mendon et al.(2015)基于南美洲銀行業的數據發現,商業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會導致其信用風險的上升。
關于資產證券化與流動性風險的關系,主要有以下兩類觀點:其一,資產證券化可以降低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Bannier&H?nsel,2008)。此類觀點認為,資產證券化具有“流動性優化效應”,商業銀行將缺乏流動性的長期信貸資產打包重組,轉化為可以在市場上流通的資產支持證券,進而將其銷售給投資者,這一過程實現了非流動資產向流動資產的轉化,因而可以降低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其二,資產證券化會加劇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根據“穩定預期效應”(Loutskina,2011),資產證券化確實有利于盤活商業銀行的非流動資產。但是,隨著資產支持證券的穩定發行,商業銀行可能認為自己已經獲得了穩定的流動性來源,反而會減少表內的流動資產持有,這導致了流動性風險的上升。根據“利益追逐效應”(Peersman&Wagne,2014),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雖然有利于商業銀行獲得流動性,但在收益最大化的驅動下,商業銀行會利用新增的流動性進行信貸擴張,最終反而會加劇其流動性風險。
關于資產證券化與系統性風險的關系,主要有以下兩類觀點:其一,資產證券化可以降低商業銀行的系統性風險。Wu et al.(2011)利用美國銀行業的數據發現,資產證券化降低了商業銀行的系統性風險。吳成頌和王超(2018)利用我國銀行業的數據驗證了上述觀點;其二,資產證券化會加劇商業銀行的系統性風險(Haensel&Krahnen,2007)。André&Michalak(2010)發現,對于大型銀行以及多次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的銀行,資產證券化與系統性風險的正向關系更加顯著。本文認為,不恰當的資產證券化度量指標,既是研究結論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也是現有研究有待改進之處。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基礎
目前,關于資產證券化的度量主要有四種方法:其一,是“資產證券化指數”(Loutskina,2011);其二,是“ABS參與度”,即銀行當期“證券化的資產”占其“可供證券化的資產”的比例;其三,是“業務筆數法”,即銀行在當期開展的“資產證券化業務的筆數”;其四,是“虛擬變量法”,如果銀行當期開展了資產證券化業務,取值為1,如果銀行當期沒有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則取值為0。參考現有文獻(郭子增和王龑,2019),綜合考慮樣本數據的可得性和結果的準確性,本文采用“虛擬變量法”來度量資產證券化,并從“業務類型”和“底層資產”的視角進行改進。
其一,從“業務類型”的視角出發,商業銀行“以什么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具有本質上的區別。一方面,商業銀行以“原始權益人”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需要將信貸資產真實出售給特殊目的實體(SPV),從而實現破產隔離,信貸資產借此出表,因而會對其資產負債表造成實質性影響;另一方面,商業銀行以“承銷商”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只是承擔銷售責任,起到一個過手的作用,不會對其資產負債表造成實質性影響。
其二,商業銀行作為“原始權益人”的情況下,“以何種貸款作為底層資產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同樣具有本質上的區別。目前,我國商業銀行主要以企業貸款、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作為底層資產發行資產支持證券(抵押貸款包括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和個人汽車抵押貸款),其區別在于:首先,從風險集中度來看,“企業貸款”的單筆金額大,風險集中度高。“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的單筆金額小,風險分散性好;其次,從違約率來看,“企業貸款”的違約率通常高于其他貸款,是不良貸款的主要來源,尤其是經濟下行時,“企業貸款”的違約率會大幅上升。“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的違約率則較低,即使經濟下行,借款人的還款意愿依然強烈,而且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和個人汽車抵押貸款還具有足額擔保,屬于優質信貸資產;最后,從流動性來看,“企業貸款”的單筆金額大、期限長,會極大的占用銀行資金的流動性。“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的單筆金額小,在等額本息還款的情況下,會在每期形成源源不斷的資金回流,對銀行的流動性形成補充。
顯然,不同業務類型即商業銀行參與資產證券化時身份地位差異和ABS底層資產的不同,其對銀行的影響大不相同。然而,現有文獻并未對“業務類型”和“底層資產”做出區分,這可能導致研究結果的不準確。因此,本文將從“業務類型”和“底層資產”的視角出發,對商業銀行的資產證券化進行度量,進而研究商業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對其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和系統性風險的影響。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商業銀行在經營過程中面臨諸多風險,本文選擇現階段最受關注的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和系統性風險作為被解釋變量。本文選取不良貸款率作為商業銀行信用風險(credit-risk)的代理變量。流動性比例是重要的流動性風險監測指標,本文以100%-流動性比例作為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liquidity-risk)的代理變量。Brownlees&Engle(2010)提出了測度金融機構系統性風險的SRISK指數,即“整個金融系統發生危機時單個金融機構的預期資本缺口”,本文測算了SRISK指數作為商業銀行系統性風險(systemic-risk)的代理變量。
2.解釋變量
本文從“業務類型”和“底層資產”的視角出發,采用“虛擬變量法”對商業銀行的資產證券化進行了度量。具體如下:第一個層面是“業務類型”,即銀行“以什么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如果銀行當期以“原始權益人”身份開展了資產證券化,則ABS-equity取1,反之取0。如果銀行當期以“承銷商”身份開展了資產證券化,則ABS-dealer取1,反之取0;第二個層面是“底層資產”,即銀行作為原始權益人的情況下,“以何種貸款作為底層資產開展了資產證券化業務”。如果銀行當期以“企業貸款”作為底層資產發行了ABS產品,則ABS-firm取1,反之取0。如果銀行當期以“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作為底層資產發行了ABS產品,則ABS-other取1,反之取0。
3.控制變量
微觀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資產規模(size)、總資產收益率(ROA)、杠桿率(leverage)、資本充足率(CAR)和非利息收入占比(NIR)。宏觀層面的控制變量為:經濟狀況(GDP),即GDP的增速;貨幣因素(M2),即M2的增速。
本文選取我國上市銀行2011~2018年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銀行數據來自定期財報和國泰安CSMAR數據庫,宏觀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和中國人民銀行網站,資產證券化數據來自中國資產證券化分析網。
(三)模型設定
考慮到銀行風險可能具有持續性,本文設定的動態面板模型如式(1)所示。

其中:control是控制變量;risk代表銀行風險,分別為信用風險(credit-risk)、流動性風險(liquidityrisk)和系統性風險(systemic-risk)。
三、資產證券化對銀行風險的影響
本文的模型為動態面板形式,因而采用了系統GMM方法進行估計。表1、表2和表3中,Sargan檢驗與AR(2)檢驗的P值均大于0.1,符合系統GMM方法的要求。
(一)對信用風險的影響
關于商業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對其信用風險的影響,結果如表1所示。
模型(1)中,ABS-equity的系數顯著為正;模型(2)中,ABS-dealer的系數不顯著;模型(3)中同時放入ABS-equity和ABS-dealer,結果沒有實質性變化。這說明,銀行以“原始權益人”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導致了信用風險上升。銀行以“承銷商”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沒有影響其信用風險。原因在于:銀行以“原始權益人”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導致自身信貸規模和信貸結構發生了變動,因而會影響其信用風險。相反的,銀行以“承銷商”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只是承擔銷售責任,起到一個“過手”的作用,不會改變自身信貸規模和信貸結構,因而沒有影響其信用風險。
模型(4)中,ABS-firm的系數顯著為正;模型(5)中,ABS-other的系數不顯著;模型(6)中同時放入ABS-firm和ABS-other,結果沒有實質性變化。這說明,銀行以“企業貸款”作為底層資產發行ABS產品,導致了信用風險上升。銀行以“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作為底層資產發行ABS產品,沒有影響其信用風險。原因在于:“企業貸款”的單筆金額大、風險集中度高、違約率相對較高,是銀行壞賬的主要來源。尤其是經濟下行時,“企業貸款”的違約率會大幅上升。因此,發行企業貸款ABS,會導致“企業貸款”的規模和結構發生變動,顯著影響到銀行的信用風險。相反的,“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的單筆金額小、風險分散性好、違約率非常低。即使經濟下行,“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的借款人依然有著強烈的還款意愿,而且抵押貸款往往具有足額擔保,對銀行壞賬的貢獻很低。因此,發行抵押貸款ABS和消費貸款ABS,對銀行信用風險的影響并不明顯。

表1 信用風險
總的來看,商業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加劇了其信用風險。商業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將信貸資產轉移出表,理論上應當降低其信用風險。但檢驗結果卻恰恰相反,本文將原因總結如下:
其一,“風險自留效應”。資產支持證券通常會進行結構化分層,底層資產的現金流首先用于償付“優先檔”債券,然后是“中間檔”債券,最后才是“次級檔”債券。“次級檔”債券發揮著“損失緩沖”的作用,承擔了底層資產的大部分風險。根據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的規定,我國商業銀行作為原始權益人發行信貸ABS產品,必須進行風險自留,即留存一定比例的“次級檔”債券。因此,底層資產的信用風險并沒有通過資產證券化全部轉移出表,“風險自留效應”導致部分信用風險留在了銀行表內,弱化了資產證券化轉移信用風險的功能。
其二,“風險流轉效應”。我國商業銀行發行的信貸ABS產品,主要在銀行間市場進行交易,這導致“通過資產證券化出表的信用風險,仍然在銀行間市場上流轉”,即信貸ABS產品在銀行間流轉,這種“風險流轉效應”弱化了資產證券化轉移信用風險的功能。
其三,“聲譽維護效應”。商業銀行發行信貸ABS產品,會將底層資產真實出售給SPV,從而實現風險隔離。當底層資產發生違約時,商業銀行雖然不必承擔責任,但其“聲譽”會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因此,為了避免“底層資產違約損害自身聲譽”,商業銀行會將高風險的信貸資產留在表內,進而優先選擇優質的信貸資產進行證券化,這種“聲譽維護效應”也弱化了資產證券化轉移信用風險的功能。
其四,“資產置換效應”。近年來,監管環境繼續趨嚴,根據監管要求,表外非標業務要逐步回歸表內,加劇了商業銀行的資本壓力。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商業銀行通過資產證券化業務,將部分信貸資產出表,以釋放其資本占用,進而利用“釋放的資本”來承接非標資產回表。這一過程中,通過證券化出表的是優質信貸資產,而承接回表的往往是風險相對較高的資產,這直接加劇了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
其五,“逆向激勵效應”。我國商業銀行面臨的“逆向激勵”問題表現為:資產證券化可能對信貸業務條線的員工產生了“逆向激勵”,使其錯誤的認為“可以通過證券化轉移所有風險”。受此影響,信貸業務條線的員工會異常積極的發放貸款,不再對借款人進行審慎、客觀的評估,風險防控的松懈、放款標準的降低,最終會導致大量的低質量信貸資產進入銀行表內,直接加劇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
(二)對流動性風險的影響
關于商業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對其流動性風險的影響,結果見表2。
模型(7)中,ABS-equity的系數顯著為負;模型(8)中,ABS-dealer的系數不顯著;模型(9)中同時放入ABS-equity和ABS-dealer,結果沒有實質性變化。這說明,銀行以“原始權益人”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導致了流動性風險下降。銀行以“承銷商”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沒有影響其流動性風險。原因在于:長期信貸資產的流動性一般很低,銀行以“原始權益人”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是將“非流動資產轉化為流動性資產”,可以有效盤活存量資產、帶來大量現金流入,因而會對自身的流動性風險產生影響。
模型(10)中,ABS-firm的系數顯著為負;模型(11)中,ABS-other的系數不顯著;模型(12)中同時放入ABS-firm和ABS-other,結果沒有實質性變化。這說明,銀行以“企業貸款”作為底層資產發行ABS產品,導致了流動性風險下降。銀行以“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作為底層資產發行ABS產品,沒有影響其流動性風險。原因在于:“企業貸款”的單筆金額大、期限長,會嚴重占用銀行的流動性,發行企業貸款ABS則會帶來大量資金流入,大幅改善銀行的流動性狀況。因此,以“企業貸款”作為底層資產發行ABS產品,會影響銀行的流動性風險。“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則相反,一方面,以住房抵押貸款為例,單筆金額相對較小,采取等額本息還款時,大量的住房抵押貸款會形成源源不斷的資金回流,有利于銀行保持流動性;另一方面,消費貸款的單筆金額非常小、還款周期短,可以快速回籠資金,很少占用銀行的流動性。因此,以“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作為底層資產發行ABS產品,對銀行流動性的改善并不明顯。
總的來看,商業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可以緩解其流動性風險。資產證券化的本質,就是將非流動資產轉化為流動性資產。明顯的,我國商業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有利于盤活非流動資產、緩解流動性風險,發揮了正面的“流動性優化效應”,而不是負面的“穩定預期效應”(Loutskina,2011)和“利益追逐效應”(Peersman&Wagne,2014)。
(三)對系統性風險的影響

表2 流動性風險
關于商業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對其系統性風險的影響,結果見表3。
模型(13)中,ABS-equity的系數顯著為負;模型(14)中,ABS-dealer的系數不顯著;模型(15)中同時放入ABS-equity和ABS-dealer,結果沒有實質性變化。這說明,銀行以“原始權益人”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導致了系統性風險下降。銀行以“承銷商”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沒有影響其系統性風險。原因在于:銀行以“原始權益人”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會導致資產規模和資產結構發生變動,通過將表內的信貸資產出售給SPV,銀行的“風險敞口”發生了變動,因而會影響到自身的系統性風險。
模型(16)中,ABS-firm的系數顯著為負;模型(17)中,ABS-other的系數不顯著;模型(18)中同時放入ABS-firm和ABS-other,結果沒有實質性變化。這說明,銀行以“企業貸款”作為底層資產發行ABS產品,導致了系統性風險下降。銀行以“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作為底層資產發行ABS產品,沒有影響其系統性風險。原因在于,銀行的系統性風險取決于“風險敞口”的大小(Taylor,2010):“企業貸款”的單筆金額大、風險集中度高、違約率相對較高,尤其是經濟下行時,“企業貸款”的違約率還會明顯上升。因此,“企業貸款”是銀行“風險敞口”的重要來源。這種情況下,銀行發行企業貸款ABS會導致其“風險敞口”產生大幅變動,因而會影響到自身的系統性風險。相反的,“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的單筆金額小、風險分散性好、違約率非常低,即使經濟下行,借款人的還款意愿依然強烈,對銀行“風險敞口”的貢獻較小。這種情況下,銀行發行抵押貸款ABS和消費貸款ABS不會導致其“風險敞口”產生大幅變動,因而對系統性風險的影響并不顯著。
總的來看,商業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可以緩解其系統性風險。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源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金融機構之間的直接業務聯系,包括機構間的同業往來和債權債務關系,彼此之間的業務聯系造成了“相互的風險敞口”,一旦有機構發生違約,就會形成連鎖反應,造成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是金融機構持有了同質化的資產組合,這會造成“同質的風險敞口”,一旦有資產發生違約,就會引起大范圍的影響,造成系統性風險。因此,導致上述現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兩點:
其一,“風險隔離效應”。商業銀行作為“原始權益人”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需要將信貸資產真實出售給SPV,以實現風險隔離,因而原始權益人與SPV之間屬于“買賣法律關系”或“信托法律關系”。進一步,由SPV對外發行信貸ABS產品,其他銀行如果作為“投資人”購買了信貸ABS產品,只會與SPV之間形成債權債務關系。明顯的,作為“原始權益人”的銀行和作為“投資人”的銀行之間,并不存在直接業務聯系,SPV發揮了“風險隔離效應”。因此,商業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不會影響“相互的風險敞口”。

表3 系統性風險
其二,“風險分流效應”。商業銀行作為原始權益人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會將相應的信貸資產出表,降低“同質的風險敞口”。商業銀行作為“投資人”在銀行間市場上參與交易,又會導致信貸ABS產品入表,增加“同質的風險敞口”。但是,銀行間市場上還有非銀行金融機構、非金融機構法人和境外投資者參與交易,這對“風險敞口”起到了分流作用,即存在“風險分流效應”。在信貸資產出表和信貸ABS產品入表的過程中,銀行體系出表的“同質的風險敞口”大于入表的“同質的風險敞口”,因而系統性風險得到了降低。
四、資產證券化的自選擇問題
根據郭子增和王龑(2019)的研究來看,商業銀行是否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并非隨機事件,而是存在“自選擇問題”。受此影響,“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的銀行”和“未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的銀行”,其風險水平的差異,既有可能是“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導致的結果,也有可能是“促使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的前定因素”導致的結果。或者說,可能存在一些前定因素,使得“某些銀行”無論是否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其風險水平總是與其他銀行不同。
考慮到“自選擇問題”可能導致研究結果不準確,本文參考郭子增和王龑(2019)的方法,采用處理效應模型重復了上文的實證過程。處理效應模型需要設置協變量,且至少一個協變量外生,不包含在原方程的控制變量當中。因此,本文在原有控制變量的基礎上額外引入兩個外生的協變量:其一,是銀行業凈利差(spread);其二,是政策因素(policy),即我國政府是否開展資產證券化試點,開展之前取值為0,開展之后取值為1。
采用處理效應模型的情況下,以“承銷商”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ABS-dealer)、以“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作為底層資產發行ABS產品(ABS-other)的結果依然不顯著,因而不再專門列出。表4僅列出以“原始權益人”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ABS-equity)、以“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作為底層資產發行ABS產品(ABS-other)的結果。
處理效應模型既采用了OLS進行估計,也采用了MLE進行估計。可以看出,ABS-equity和ABS-other對信用風險(credit-risk)的影響依然顯著為正;ABS-equity和ABS-other對流動性風險(liquidityrisk)的影響依然顯著為負;ABS-equity和ABS-other對系統性風險(systemic-risk)的影響依然顯著為負。明顯的,利用處理效應模型解決“自選擇問題”之后,研究結果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

表4 處理效應模型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我國上市銀行的數據,從“業務類型”和“底層資產”的視角出發,實證檢驗了商業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對其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和系統性風險的影響,并對其影響機制進行了總結。研究結果表明:在信用風險方面,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存在“風險自留效應”“風險流轉效應”“聲譽維護效應”“資產置換效應”和“逆向激勵效應”。因此,我國商業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加劇了其信用風險;在流動性風險方面,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存在“流動性優化效應”。因此,我國商業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降低了其流動性風險;在系統性風險方面,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存在“風險隔離效應”和“風險分流效應”。因此,我國商業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降低了其系統性風險;從“業務類型”來看,以“原始權益人”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會對銀行風險造成影響。以“承銷商”身份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則不會影響銀行風險;從“底層資產”來看,以“企業貸款”作為底層資產發行ABS產品,會對銀行風險造成影響。以“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作為底層資產發行ABS產品,則不會影響銀行風險。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其一,監管部門應當構建“宏觀審慎+微觀審慎”的資產證券化監管體系。本文研究顯示,我國現階段存在“資產證券化加劇銀行信用風險、降低銀行系統性風險”的情況,這說明,我國資產證券化監管體系,不能僅限于“關注整體層面的系統性風險”,還需要“密切關注個體層面的信用風險”。因此,我國應當構建“宏觀審慎+微觀審慎”的資產證券化監管體系,以宏觀審慎防控整體層面的系統性風險,以微觀審慎防控個體層面的信用風險。同時,在宏觀審慎系統和微觀審慎系統之間實現分工協作和信息共享,確保二者的有效結合。
其二,商業銀行應當采取“積極創新+審慎經營”的態度推進資產證券化。一方面,商業銀行應當積極推進資產證券化創新,開發更多符合自身條件和市場需求的信貸ABS產品;另一方面,銀行員工必須對資產證券化建立正確的認識,審慎的推進各項業務,尤其是信貸業務條線的員工,更要從理性的角度看待資產證券化,決不能因為“逆向激勵”而降低放款標準,導致低質量資產進入表內。
其三,進一步放開交易限制,強化市場的信用風險轉移能力。目前,我國的信貸ABS產品主要在銀行間市場上交易,大量通過資產證券化出表的信用風險仍然留存在銀行體系內。因此,需要進一步放開交易限制,引入更多的非金融機構法人和境外投資者參與交易,為整個市場擴容,從而讓資產證券化切實發揮信用風險轉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