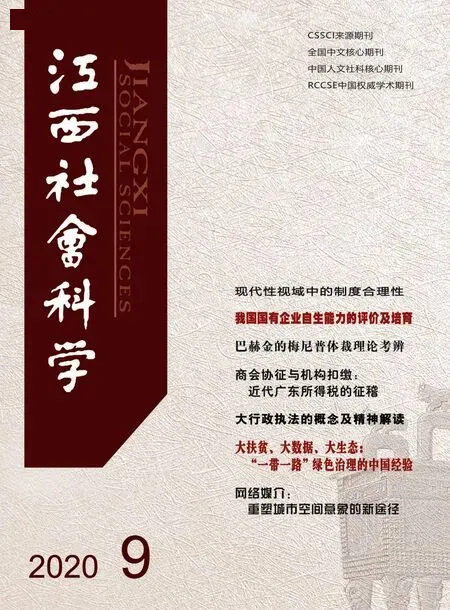文化記憶視閾中翻譯的再生產功能探析
文化記憶的書寫是文化傳播與文化傳承的重要方式,離不開回憶與記憶的運作。回憶與記憶是文化記憶理論中的兩個核心概念,表征了人類文化記憶中兩種不同的思維活動。在翻譯中,譯者擔負回憶者的職責,通過編寫前言和評注回憶文化的起源并對其加以解釋,整理出一套新的關于歷史和文化的記憶,翻譯則是譯者充分運用記憶進行譯介的再生產活動。以《古今越歌英譯與評注》為例,它是譯者用回憶和記憶的方式成功復活民族文化、傳承民族文化的范例,對儲存國家民族文化和傳播民族文化藝術有借鑒作用。
文化記憶理論是西方文學理論界從文本研究轉向文化研究的必然產物。文化記憶是一部寫滿人類生存史與發展史的巨著,因其適應性、變動性和重塑性的特征呈現出棱鏡般變化莫測的樣貌,吸引著國內外文化研究者的目光,又因其具有傳播性和傳承性的特點,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化孵化器。由于文化記憶的存在,歷史得以在我們的面前展開,然而,文化記憶是如何被書寫的?作為文化記憶書寫方式之一的翻譯是怎樣運作的?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問題。
一、文化記憶:回憶與記憶
20世紀70年代,揚·阿斯曼和阿萊達·阿斯曼提出文化記憶理論。該理論是對法國哲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記憶觀點的擴展,文化記憶理論將哈布瓦赫的記憶區分為個體記憶、集體記憶和文化記憶,文化記憶是一個涵蓋口傳和書面傳統的概念,指由一個社會建構起來的歷時的身份。根據阿斯曼的觀點,文化記憶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時間視閾,跨度長達兩三千年,文化記憶可以借助儀式、神話、圖像、舞蹈和文字保存下來,文字和書寫的傳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1](P1)學界關于文化記憶的書寫研究可分為三類,分別是文化記憶的理論研究、文學作品與文化記憶研究及翻譯與文化記憶研究。在文化記憶的理論研究方面,理論的創始人阿斯曼發表多篇論文及專著描述這一理論,從理論的形成與建構[1](P1-2)、文化記憶對以往集體記憶和交往記憶的超越[2](P18-26)、文化記憶的個案研究[3]三方面形成對文化記憶的理論勾勒。國內學者的工作則主要圍繞介紹、譯介、闡釋文化記憶理論及該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展開,具有代表性的是黃曉晨的《文化記憶》與金壽福的《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國外學者致力于對文化記憶的跨學科研究和前沿研究,《文化記憶研究——國際與跨學科的手冊》內容涵蓋記憶與文化歷史研究、記憶的跨學科研究(社會、政治、心理、哲學)、文學與文化記憶研究、媒介與文化記憶研究[4]。文化記憶研究的論文集中,將國外文化記憶理論研究的焦點集中在“非歷史的記憶”“敘事與回憶”“安置記憶”“回憶與復興”“作為創傷的回憶”五個板塊。[5]在文學作品與文化記憶的研究中,研究者多以文化記憶理論為視角探尋作為少數族裔的主人公對自我身份的掙扎與認同,考查記憶對主人公命運及人生選擇的影響,思考民族文化在文學作品中的傳承。在翻譯與文化記憶研究中,美國學者Bella Brodzki將文化記憶理論引入翻譯研究領域,出版了《這些骸骨能復活嗎?翻譯、存活和文化記憶》一書,書中以20世紀的各種文學文本為個案,用一種折衷的批評方式討論翻譯、生存與文化記憶之間的互動關系,揭示了翻譯作為一種文化記憶的模式在跨代傳遞和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英國學者Siobhan Brownlie的《繪描翻譯中的記憶》以記憶為理論框架,考察個人記憶、群體記憶、電子記憶、文本記憶、國家記憶、過渡記憶及世界性的集體記憶與翻譯研究的碰撞,為文化記憶理論與翻譯研究的聯結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中國學者羅選民在他的文章《文化記憶與翻譯研究》中注意到文化記憶中的功能記憶和存儲記憶與翻譯研究的相關性,可以從功能記憶的動機和存儲記憶的特點分析翻譯文本。他還在《大翻譯與文化記憶:國家形象的建構與傳播》一文中,提出翻譯在國家形象建構與文化傳播中的關鍵性作用,即倡導一種可以產生集體化記憶的大翻譯。閆亮亮在《嚴復選譯〈群己權界論〉的文化記憶》中,以文化記憶理論為視角觀照特定歷史時期的翻譯語境及譯作特征,分析文化記憶與翻譯語境之間互相影響、互相成就的互動關系。這些研究成果為此次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礎。
回憶(remeberance)和記憶(memory)是文化記憶中兩個重要術語,也是西方哲學家一直感興趣的論題。從西方哲學史來看,從柏拉圖到休謨、從亞里士多德到柏格森、從維特根斯坦到海德格爾、從艾賓浩斯到巴德利,回憶與記憶一直是哲學家們思辨的對象,生物學和心理學的加入使人們對回憶和記憶的思考更具科學性,到了20世紀80年代,文化記憶的興起讓人們把目光再次聚焦到回憶與記憶之上,關注二者在文化傳承中的重要作用。文化記憶理論的代表人物阿萊達指出,“回憶不是重新制造過程中被動的反應,而是一個新的感知的生產性的行為”[6](P113),回憶是恢復以前有過的知識或感受,是有意識地努力在記憶中尋找自己的道路,在記憶中獲取自身希望找到的東西,因此,回憶是主動性的、創造性的活動。那么,記憶是什么呢?揚把記憶定義為“(記憶)是一個建構性的、歷時性的身份,宗教、藝術和歷史都屬于這個范疇”[1](P2),記憶是一條吸納信息的長河,等待回憶去提取需要的內容。根據文化記憶理論關于回憶與記憶的定義可知,兩者有比較明顯的區別。首先,回憶是個體性的,記憶則不同。回憶是對記憶的篩選,其結果取決于回憶者的需求、情感及目標,因此,回憶呈現出個體性、選擇性和操控性,而記憶則總是受集體語境的影響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其次,回憶產生自記憶,沒有記憶就沒有回憶。這是說,記憶總是先于回憶存在并包孕著回憶,記憶的容量遠遠大于回憶,在文化記憶理論中,記憶就是文化本身[1](P1)。再次,回憶與記憶在文化記憶中的功能不同。回憶的功能在于提取信息和篩選信息,記憶則要對信息進行加工和建構,使信息生成歷時的身份并在時間長河中確立自身的位置、保持自己的文化本色。記憶與回憶是建構文化記憶的重要組成,兩者可以構建出一個相對完善的文化記憶體系。記憶是歷時的,而回憶總是共時的,兩者的結合可以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閉合。本文關注翻譯者在文化傳承與文化記憶中的創造性活動及重要作用。以《古今越歌英譯與評注》為例,考查譯者撰寫的前言和評注所起的回憶作用以及翻譯文本中如何發揮記憶的功能,進一步論述作為回憶的前言和評注與作為記憶的翻譯一道建構了《古今越歌英譯與評注》深厚的民族文化記憶。
二、作為回憶的前言與評注
作為民族文化的有聲藝術載體,越歌因折射出古代江南的社會生活、歷史文化、天文地理、語言和民俗等風貌,被譽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民族精神的檔案”。卓振英譯述的《古今越歌英譯與評注》是第一部較為完整的越歌英譯集,這本譯作收錄70首產生、流傳于百越之地的歷代民歌。文化記憶理論為文化史和文明發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由于文化記憶的方式直接影響到文化的主體性和內部組織方式,因此決定著文化的氣質和民族的性格。[7](P243)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用回憶(前言和評注)調取過去來儲存意義,用記憶(翻譯)去激活和傳達意義,以這種方式復活越歌的現世生命,去“勾畫出越歌之概貌,映射出越文化之輝煌”[8](P11),讓英語讀者隨著譯者的回憶與記憶走進中國古老的越歌文化,感受越歌文化的藝術魅力。
作為回憶的前言與評注是譯者用回憶的方法再現越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的成果,譯者的回憶體現出其在編譯活動中的自覺性與能動性。有學者指出:“回憶是回憶者在特定的社會背景與生活語境中的主體思想意識行為,或大腦追憶,或文字記述,過去在回憶者腦海進行一次次過濾和篩選,每一個過濾和篩選都是回憶者情感與思想醞釀的過程,也是對每一次過去的再塑造。”[9](P48)《古今越歌英譯與評注》的前言與評注將關于越歌的生動回憶帶到譯語讀者面前,為文學作品在未來的復活提供了可能。
前言是典型的回憶活動,是回憶者在篩選和過濾大量有形與無形的歷史文化資料之后的回憶書寫。《古今越歌英譯與評注》的前言主要包含三部分內容:譯者首先介紹了“百越”的地理、生活、歷史和文化背景,進而引出作為文化的有聲藝術載體,越歌內含的文化品格及翻譯的必要性,最后譯者說明了此次翻譯的目標、翻譯過程中的思考,并表達對促成此書出版的相關人員的感激之情。通過閱讀以上內容可以看出,作為回憶的前言在傳承民族文化、激活民族文化記憶時有以下幾個作用:
第一,追溯民族文化流變,儲存民族文化內容。回憶是過去的在場,是回憶者有選擇性地提取回憶、重組回憶的過程,譯者在《古今越歌英譯與評注》的前言中回溯越歌的“本”與“源”,“回憶”了“百越”的地理、歷史與文化起源。這些有關百越之地的民族文化內容是譯者在翻閱大量相關文獻資料后,按照時間順序和邏輯順序整理而來,不僅有相當重要的文獻價值和保留價值,還對讀者理解越歌的主題與內容有積極的作用。
第二,揭示民族文化品格,闡明傳播價值。回憶是回憶者從當下出發的重構,能夠體現重構者的回憶偏好及回憶目標,回憶者引用其他學者概括出的越歌文化品格:主體性品格(以自然為基礎的人生本位取向)、民族性品格(以家庭為基礎的群體本位取向)、規范性品格(以倫理為基礎的禮儀本位取向)、內向型品格(以個性為基礎的整合本位取向)。[10](P51-55)正因為回憶者對越歌文化品格的重視,他的譯本力圖再現這些內容,使其獲得了新的生命形態和生存空間,對民族文化的生存與發展、保存與傳承具有重大意義。
第三,解讀翻譯過程,弘揚民族文化。譯者在前言中回憶了翻譯前的準備工作,為了貼切妥當地翻譯出書名、盡可能精確地提供作者的生卒時間,譯者在經過一番認真查考之后方才動筆,譯文依據譯者本人提出的詩學范式理論(見《漢詩英譯論綱》)翻譯而成,力求遵循“以詩譯詩”的原則,最大限度地再現原作的美學效果,達到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翻譯目標。
評注包括評論與注釋,二者皆是對文本的解釋。在《古今越歌英譯與評注》中,譯者的評論用英語寫成,主要介紹該越歌的出處、主題、內容、文體和情感,譯者的注釋主要表現為對越歌中的修辭手法、文化意象及文化內涵的解讀。譯注的內容有利于譯語讀者了解越歌產生的生活背景和歷史背景,以劉三姐的《采茶歌》為例,譯者在評注中介紹了南方少數民族在勞作過程中喜愛唱歌的生活習慣,邊勞作邊唱歌可以驅除勞累、鼓舞人心,《采茶歌》表達出采茶女豐收的喜悅,描繪出勞動人民簡單、幸福的生活畫面。此外,如果該首越歌有其他譯本,譯者也會在評論部分列出,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互文網絡,方便讀者從不同視角觀照、理解譯作,實可謂用心良苦。漢學家余寶琳指出,選集不僅通過對作品的取舍而且也通過對個人作品的闡釋來確立經典。[11](P259)就是說,譯者對作品的選擇及評注都是重構經典的核心內容,在民族文化的翻譯作品中同樣具有重要作用。
同時,評注是譯者回憶的見證,讀者通過評注可以回望其回憶的文化內容。以《漁父歌》為例,譯者首先在評論中回顧了這首越歌背后的歷史故事,之后在注釋中對這首歌的歸屬問題做了考證,對于這首歌的歸屬問題,譯者在注釋中寫道:“根據歌者是‘楚地漁父’,歌的流傳區域是‘吳越大地’,且其形制風格與《采葛婦歌》《軍士離別詞》等越歌有‘前后呼應’關系等,《浙江歌謠源流史》一書的作者朱秋楓認為它‘可稱作楚歌’,‘也可稱作吳越間的古歌’。”[8](P20)從這段注釋中可知,譯者在評注方面反復查考,相當嚴謹。《漁父歌》的評注展示出譯者的回憶內容及解釋內容,其中,回憶內容反映出譯者對原作歷史背景的重構與想象,而解釋內容體現出譯者對原作的文獻學研究。揚·阿斯曼認為,解釋是保持文化一致性和文化身份的核心原則,對待經典重要的不是背誦,而是對其加以解釋:“只有對那些支撐身份認同的文獻不斷地進行解釋,相關的人群才有可能獲得它們所蘊含的規范性的和定型性的效力。解釋在這里儼然成為回憶的舉動,解釋者是提醒者,告誡相關的人不要忘記真理。”[3](P95)
可見,回憶是一種進行符號編碼的過程,翻譯是一種編碼行為。文化記憶理論認為,只有具有重要意義的過去才會被回憶,而只有被回憶的過去才具有重要意義。[3](P95)人類借回憶激活過去具有重要意義的文化,并在回憶中重構當下和未來,通過回憶性的前言,越歌的歷史背景才能得以保留。評注凝聚著譯者的心血,是譯者回憶的有形資料,對保護和傳播民族文學的文化記憶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三、作為記憶的翻譯
文化之所以在經年累月之后仍然保持本色,根源在于記憶的存在,記憶是一種創造性的、可變的知識。文化記憶理論認為,文化記憶涉及的是人類記憶的外在維度,即研究這種記憶所儲存的內容是如何被組織整理、形成傳統、指涉過去,并預示當下和未來的經驗,而人類的記憶在自然狀態下的最根本形式是遺忘而非回憶或記憶,因此,文字是永生的文化媒介和人類記憶的支撐。筆者發現,民族文化的翻譯可以起到記憶的作用,譯者通過組織整理過去的語言材料,用新的語言將民族文化儲存下來并傳承下去。記憶總是與記憶者的社會文化背景關聯,同時又要與譯語讀者的文化背景溝通,因此,翻譯反映出兩種語言文化框架下的記憶融合。
翻譯的過程即記憶的敞開,是譯者調用自己關于歷史、文化和語言的記憶,并用語言記錄下來的過程。文化記憶理論認為,詩人最原始的作用是保留群體的記憶[3](P48),換句話說,詩歌是記憶的載體,有儲存意義和重建意義的功能,翻譯的功能不外如此,人類通過有記憶功能的翻譯實現文化的持續性生產與交流。《古今越歌英譯與評注》是翻譯作為記憶發揮功能的具體寫照。作為記憶的翻譯有以下特征:
其一,永不知足地追求改變。翻譯是一種“熱記憶”,與具有消解效果和鎮靜作用的“冷記憶”不同,熱記憶永不知足地追求改變,通過復活沉寂的文化,達到促進文化發展與交流的目標。作為“熱記憶”的翻譯本質上是過去與現在的并立,因此是動態的、變化的,它不僅蘊含著譯者個人的文化記憶,還包含集體記憶與交往記憶,是不同記憶的總和。在《古今越歌英譯與評注》中,中英文字以對照的形式引發了越歌的復活與外化,催生著新的記憶的生成。
其二,文化記憶的“分有”是嚴格的。對翻譯來說,一般由學者、教師和詩人承擔翻譯任務,他們會根據文本的時間和主題重新組織記憶內容。以《古今越歌英譯與評注》的譯者卓振英為例,他從事典籍英譯幾十年,有豐富的翻譯實踐經驗,還依據實踐經驗編寫了翻譯理論研究專著和翻譯學教材,代表作有《漢詩英譯論綱》《漢詩英譯教程》等。在《古今越歌英譯與評注》中,譯者按照越歌產生的年代順序、歌謠涉及的事件兩種方式對越歌進行編排,有些越歌無法確定產生時間,譯者便按照主題類型分類,主要有創世歌、功德歌、刺邪歌、勸世歌、愛戀歌、交友歌、嬉戲歌、民俗歌、勞作歌等。以上反映出文化記憶的“分有”是十分嚴格的,無論是對譯者的選擇,抑或是對文本的歸類,都體現出記憶的規范性與嚴格性的一面。
其三,注重譯文美的呈現,加深讀者對記憶的審美感受。讀者對記憶的審美感受來源于譯文的美學效果。阿萊達·阿斯曼指出:“賦予美的形態是為了有助于回憶和記憶的形成而對其進行加深影響的改造。”[6](P83)卓振英注重譯詩的美學效果,他在前言中寫道:“英譯力求遵循‘以詩譯詩’的原則,最大限度地再現原作音韻美、形式美、風格美、情感美、思想美和意境美。”[8](P13)從譯詩來看,譯者運用押韻形成譯文的音韻美,嚴格控制詩行的音步構成詩歌的節奏美,譯文讀來朗朗上口;用增加感嘆詞、感嘆號和反問詞的方式深化譯文的情感美和對話美,將譯語讀者代入越歌的情感語境,有身臨其境之感;用擬人修辭法塑造譯詩的生動美,讓譯語讀者獲得與原語讀者相似的審美體驗。譯文美可以加深讀者對越歌記憶的審美感受,讀者欣賞完譯文再讀譯文后的評論和注,便能完成一整套關于越歌的文化記憶輸入。
從上述三種特征可以看出,作為記憶的翻譯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生命力。翻譯可以跨越國界和語言,翻譯的內容可以豐富多彩,譯者用文字這一媒介將文化內容保留下來并被讀者閱讀。翻譯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著被修改、被闡釋、被解構和被丟棄的命運,如果想要讓作為記憶的翻譯擁有長久的生命力,則必須嚴格規范記憶的“分有”:出版社需要找到合適的譯者人選,和他一起進行文化內容的選題、策劃和篩選,確定圖書文案的撰寫、敲定目錄和封面設計,完成編校和營銷等工作,為了深化讀者對異質文化記憶的理解和接受,譯者要創造出富有美感的譯文。
四、結語
綜上所述,翻譯是復活文化記憶的重要書寫方式,這種書寫離不開譯者的回憶與記憶。譯者經過回憶撰寫的前言、譯注和評論及譯者發揮記憶創作的翻譯是文化記憶書寫和傳播的重要內容,在這一過程中,譯者發揮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文化記憶的保存與傳承需要文字,用文字記錄記憶與回憶是人類關心自身過去的表現,而翻譯可以讓文化記憶傳播得更遠,生成新的文化記憶場域,促成不同文化間更深刻、更廣泛的交流。通過對翻譯文本中譯者回憶與記憶過程的描述,我們可以對文化記憶中的翻譯書寫產生新的、更為深刻的認識。翻譯絕不是簡單的語言轉換活動,而是一種復雜的回憶與記憶活動。介紹作者生平、作品背景及風格的前言和評注都是譯者的回憶活動,這種回憶活動會因譯者的回憶能力、翻譯目標和讀者群的不同而發生改變,譯者據此對大量信息進行過濾和篩選,因而譯者的回憶活動是一種主動性極強的編碼行為,回憶活動也因此不同。同理,翻譯活動因譯者的記憶能力和“分有”的不同也會產生差異,不同譯者產生的差異性的回憶活動及記憶活動構成了文化記憶與翻譯研究的另一議題,可以用來解釋人們面對同一文化產生不同文化記憶的緣由。
因此,對翻譯文本中譯者回憶與記憶過程的研究可以讓讀者對之前的人類文化記憶進行重新審視。在了解到人類文化記憶是如何生成之后,我們可以對以往的人類文化記憶進行再審視,發現其形成的原因、效果及影響,是否可以對其進行優化。在未來的文化記憶書寫中,譯者還可以有意識地運用文化記憶理論進行指導,更加靈活地調用回憶與記憶完成翻譯活動,為保留文化記憶、傳承文化精華和傳播人類文明貢獻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