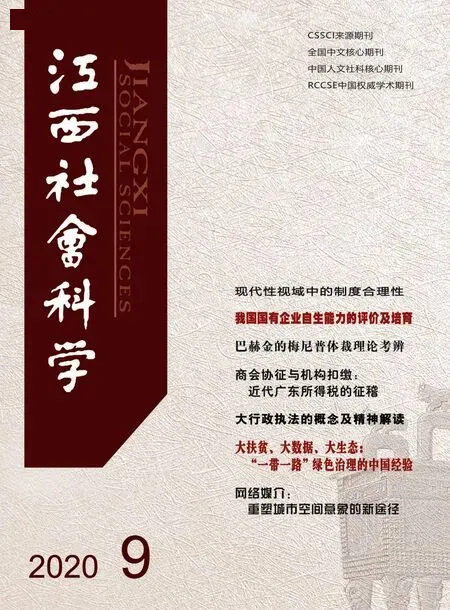比較哲學視野下心的標準問題
心與非心的區分標準問題既是重要的心靈哲學理論問題,又是重要的工程技術學實踐問題。西方心靈哲學圍繞它已做了大量探討,形成悲觀主義、單一屬性論、多屬性論、單一系統觀等大量理論,出現了包括比較研究在內的多種走向。盡管比較研究這一進路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西方已有的研究由于存在著對東方心理標準理論的誤讀、不到位的解讀乃至解讀的空白,因此中國哲學工作者有發出中國聲音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基于跨文化研究不難看到,作為整體的、矛盾統一體的心除了有樣式多樣性、性質差異性的特點之外,還有共同的本質,那就是所有心理現象都有其覺知性或能為主體自己認識的自知性,都有對物質實在的不同形式、程度的依賴性,都是同與異、生與滅、連續與非連續、變與不變的矛盾統一。正是它們,把心與非心區別開來。
心理現象肯定不同于非心理現象,即使三歲小孩也不會說桌子的運動是心理現象。但是,這不同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把心與非心區別開來?亞當斯(F.Adams)說:“在有心的生物系統與沒有心的生物系統之間存在著自然的界限。如果這不是幻覺,那么就能找到造成這種區別的東西。”[1](P54)這就是心理的標準或標志性特征,正是這些特征,使所有心理現象個例成為一個類別,同時使所有心理現象與別的現象區別開來。很顯然,這個問題與心是什么的問題(本質問題)密切相關,其現實的重要性在于,它既是重要的哲學理論問題,又是重要的工程技術實踐問題。就后者來說,如果不解決這一問題,人工智能就沒有前進的方向。因為關于心理標準的理論是人工智能的基礎性、前提性的理論。對它的回答不同,人工智能構建的具體的方向、思路、工程技術實踐就不同。心理的標準問題當然是一個極為困難、聚訟紛紜的問題。
西方哲學尤其是19世紀以來的心靈哲學自覺而明確地提出這一問題,甚至已將它建設成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這在今日的心靈與認知研究中表現得最為突出。為推進有關認識,人們絞盡腦汁,設想種種可能方案,甚至用上了比較研究。在筆者看來,盡管比較研究的進路在這里可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西方已有的研究由于存在著對東方心理標準理論的誤讀、不到位的解讀乃至解讀的空白,因此,我們可以在這里大顯身手。
一、中國哲學的心理標準探索
要想通過對中、印、西的心理標準理論的探討來找到對心理標準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對被比較方在這個問題上的真實思想有客觀到位的把握。首先,我們來考釋中國的心理標準探索及理論貢獻。
中國哲學的心理標準論主要包含在它的心性論中。“性”是中國心靈哲學獨有的課題。從詞源上可以看到,它指的是心一生成時所具有的東西。由此不難看出,如果說心有其不同于非心的本質構成及特點的話,那么,它在生成時就鑄就了這種區別,因為它所稟賦的東西不同于非心所稟賦的東西。從比較研究的角度說,這既是中國心理標準探討的特點之表現,也開創了心理標準研究的一個獨有進路。在中國哲學中,許多人都有從這個角度揭示心與非心區別的嘗試,如明代心學家汪俊說:“虛靈應物者心也,其所以為心者,即性也。性者心之實,心者性之地。”[2](P1144)意思是,心與性相輔相成,心是性的依存之地,而心之性是心的實質,即是決定心之為心的根本、初始條件和資源,例如,心之所以是有虛靈應物這一為心所獨有的作用和標志性特征,決定因素是心有其獨有的性。不難看出,心性論不僅包含顯明的心理標準理論,而且從內在本質的角度揭示了心的外在標志的內在根由,因此可看作深層次的、發生學意義的心理標準論。心性論的特點在于,一是從心的發生學(生)上揭示了心的特點,即它之所以為心,是因為它有非心所沒有的特殊的性。換言之,心的獨特性首先表現在它有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原初的性或心。二是像探礦學一樣,試圖在心中找到它的最深、最根本、最核心的東西,亦即區別于非心的深層本質。這個東西就是性。
中國哲學專門把心性作為一個對象來加以探討,肇始于儒家,而孔子又是其當之無愧的祖師。之所以說孔子的心性論是中國心性論的源頭,主要是因為他把性與天道、性與仁關聯起來。如果孔子所說的天道或天命是指道德的超越性,就不難理解孔子為什么把性與天道關聯在一起。徐復觀說:“性與天命的連結,即是在血氣心知的具體的性里面,體認出它有超越血氣心知的性質。這是在具體生命中所開辟出的內在的人格世界的無限性的顯現。”[3](P78-79)孔子認為,性就是人天生就有的道德本性。
正是基于這一認識,孟子的人性論才能夠開始對性做具體的開發和挖掘。他認為,心之性即是人心共同具有的道德本原,足以把人與非人、心與非心區別開來,是人之所以然,內容主要是道和義:“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此義、理不是現實性的東西,而是生時被先天賦予的“端倪”,即種子一樣的東西,具體表現為仁、義、禮、智四端。孟子不僅明確提出性善論,而且強調性與心的下述關系,即“仁義禮智根于心”(《孟子·告子上》)。牟宗三認為,孟子思想的綱領在于:“仁義內在,性由心顯。”(《孟子·告子上》)荀子也承認性是自然賦予人的本性,所不同的是,他認為此性是本惡的:“凡人有所一同,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榮辱篇》)不僅如此,人的諸器官先天就有其特定功能,如五官有其認知功能,這也是生而就有的本性。“目辨黑白美惡,耳辨聲音清濁,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癢,是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
朱熹的心性論全面而清楚地表達了儒家在心的深層本質特征問題上的看法。他認為,心是體與用、靜與動的統一體。而性則是心的體、理。如果說理是太極,那也可說,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性也可稱作明德。在凡圣心中,此明德是一樣的,在凡不增,在圣不減。之所以在凡夫身上看不到,是因為它被染欲等覆蓋住了,因而只以潛在的形式存在。這類似于萊布尼茲所說的真理的種子,它們以大理石花紋的形式存在。只要條件具備,可能性即能轉化為現實。朱熹說:“人皆有此明德,但為物欲之所昏蔽,故暗塞耳。”[4](P315)如果說情是心的已發,即現實表現出的實際心情,那么,性就是心的“未發”,即以天賦原則的形式存在。從認識上說,性不可見、不可言。情是可見可言的。因為發者情也,其本則是性。
朱熹還認為,心有兩個特殊標記,一是靈,二是性。而這兩者中,性是實,是本。他說:“靈底是心,實底是性。靈便是那知覺底。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5](P323)“主宰、運用的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4](P90)心是執行系統,其作用的根本之處是靈明,而性則像程序、條理一樣制約著心的運作。以莊稼為例,它們的種子是性,種子決定了一植物長成什么樣子。現實的莊稼即為心。“包裹的是心,發出不同的是性。”性與心的區別還表現在:性是心的靜的一面,而心有動有靜。朱熹對張栻下述思想的肯定也表達了自己的上述傾向:“自性之有動謂之情,而心則貫乎動靜而主乎性情者也。……心之所以為之主者,因無乎不在矣。”[6](卷二十九,P1129)心與性的差異還表現在:性決定了人與人的同一性,而心與氣、形一道決定了人的個體性、人與人的差異性。
心與性又有相互依賴、不可分割的關系。這首先表現在:“心以性為體,心將性做餡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以有性故也。”“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4](P89)不可分離還表現在,舍心無以見性,舍性又無以見心。性之所以是心的根本性的深層標志,是因為它是心的“餡子”。這個比喻恰到好處地體現了中國心靈哲學注重從內而非外揭示心的標志的特點。朱熹的這些思想代表的是中國哲學在心的標準問題上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根據這一標準論,心的內在的深層的、讓它與非心區別開來的本質特點是心的獨有的性,而心的外顯的、功能上的標志性特點則是心的靈明不昧的作用。
道教至唐代重玄學的成玄英,便加大了對心性問題的關注和探討的力度,從此以后,道教的心性學與中國佛教的佛性論、儒學的心性論并駕齊驅。重玄學之后的心性學的基本觀點是,性是心中的所藏,心是性的載體。“心者,神(性)之舍也。”(《道德真經廣圣義》卷四十九)而性就是真心。當然,這是有多種說法的。一,性即是神。“神者,性之別名也。”二,性指人的先天之神。如張伯端認為先天之性即“元性”。“神者,元性也。”“元神者,先天之性也。”(《道德真經廣圣義》卷四十九)三,性即道德修養功夫和心理的穩定狀態。
盡管有不同的心性論,但它們中一般包含這樣的思想,即心之性既是心的原初的東西,也是心之為心、心區別于非心的本質特點。不僅如此,有的人還更進一步探討心性之為心本、為心的標志性特征的所以然。如張載在論述性時,以氣來釋性。所謂氣有體、用兩面,體即氣的虛靜、本然狀態,換言之,氣的本體是太虛:“太虛者,氣之體。”(《正蒙·乾稱》)太虛之用即氣的聚散變化。此氣即質料性的氣。太虛相當于德謨克利特所說的虛空,質料性的氣相當于原子。物質之質有陰陽、剛柔、緩速、清濁等差異。就一般的性的起源和本質而言,它由氣所決定、所使然。他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正蒙·太和》)性本身不是心理,是無意識的,但作為體性的性可成為心理的基礎,知覺、情感就是如此。“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感皆出于性,性之流也。”(《橫渠易說·系辭上》)性只是心的基礎,如果沒有別的因素起作用,就不會有心出現,即只有性與知覺結合時,才會有心出現,故可說:“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正蒙·太和》)從性與心的關系說,心根源于性,性與知覺結合便有了心。性與神一樣,是氣所固有的東西:“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7](P63)“其成就者性也”[7](P187),有兩種性,一是天地之性,二是氣質之性。天地之性是由于稟賦了太虛本體之氣而成的性,氣質之性是稟賦了構成人身的具體的聚散之氣的性。心之所以不同于非心,主要是由它的特性決定。
中國哲學的心理標準理論除了上述重視從發生學和內在深層本質的角度加以揭示之外,還有一個特點,即強調把心與非心區別開來的標志性特征是多。這些特征的每一個都是心的必要條件,但單個地看,它們又可成為別的事物的特征。換言之,非心事物可以具有其中的某一特征,但不可能同時具有心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只有心才同時有這些特征。
中國心靈哲學所說的“精”有時是心的同義詞,有時指的是心中的、以動力資源形式表現出來的根由,有時指的是心的精微的特點。很顯然,精至少是心的一個必要條件,因為不具有精這一特點的事物肯定不是心,當然它不是心的充分條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哲學在論述精與心的關系時隱含一個有多重意義的寶貴思想,即現實地顯現出來的、在運轉和起作用的心一定有自己的能量之源或“心理力”,一定有其精,一定以精的形式存在,只是它極其微妙,看不見摸不著,但它們不僅有本體論的地位和作用,就像物理的電子信號等微觀實在一樣,是心的構成上的特點,而且是心現實存在和有作用的一個必要條件。這不僅以中國的方式回答了心的標準問題,即心一定有自己的獨特的能量形式、作用力,一定表現為精,而且解決了古今中外都沒有很好解決的心理因果性難題。
“神”像“精”一樣,也是一個極富歧義性的詞,其中有些意義表述的是心的標志性特征。就詞性而言,在很多情況下,它是作形容詞使用的,指的是事物的玄妙、變化、神奇、難以測知的特點。在人身上,神既指身體各部位的最佳狀態,如面有其神,又指整體的最佳狀況,有時也用來形容心、魂、魄、精神這些心理主體的神奇作用。就此而言,神也像精一樣,是心的一個必要條件,即一切心都有神的特點,當然有神的特點的東西不一定是心。神除了表現為高級的智慧作用之外,還有較低級的認知作用,其表現之一是,負責人的日常認知,如視聽言動,邵雍云:“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8](P372)中國哲學從心靈哲學角度對神的論述無疑有回答心理標準問題的意義,只是它用了中國特有的象征方式。根據有關的思考,心之所以不同于非心,是因為它有它不為其他事物所具的作用及其方式,即神或神妙,用今日哲學的話說,即有特殊的能動性、不可預測性、神秘莫測的變化性、創造性。例如,心能超越時空,與過去、未來發生關系,與身體沒法進入的空間發生關系,甚至與不存在的東西發生關系,如思考方的圓、創作虛構對象等等。神是心的能主宰一切的作用,如神能決定思想和行動。“故神制,則行從,形勝則神窮。”“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8](P374)質言之,看一個對象是不是心,可從它是否有神妙的能動作用這個角度加以觀察。
“靈”與“精神”除了有表述心理王國中具有主體性地位的實在的意義之外,還有表述心的特點與條件的意義。正是這一方面的意義,使中國對靈的說明有時具有心理標準理論的意義。“靈”作為名詞有時指能照、靈明之覺。這種明和覺的特性就是心區別于非心的特性。當然有兩種明性,一是真心的本明之性,二是妄心的低層次的反省特性。用西方心靈哲學的話說,這里的靈明相當于西方常說的自我意識中的一種形式,即不依賴于主客二分、無須通過反省或反思作用的前反思性自我意識。“靈”還常作形容詞用,指的是“靈活”“靈敏”等作用。用于描述心時,強調的是心識的不可思議的功能,如“六靈”說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識的靈明之性。這種特性是中國哲學發現的心具有的標志性特點,即心有靈的特點。盡管有的非心事物也有靈的性質,但心之靈的程度是他物所不具的。心之所以靈于萬物,是因為它具有非心事物所不具有至精至靈的作用。中國哲學所說的精神有時指的是心的一個標志性特點,即“有精神”。因為只要有心,只要心存在著、活著,就一定充滿著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心力旺盛的人,則精神充沛,人死了,則無所謂精神。陸九淵說:“收拾精神,自作主宰”[9](卷三十五,P454),意為把精神收攝向內,使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如果任其向外馳求,人就作不了主,就是凡夫一個。他說:“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9](卷三十五,P454)
總之,精、氣、神、靈、精神,特別是它們作為形容詞的所指,盡管也可為非心的事物所具有,但一方面,它們表現在心之上,在程度上乃至在實質上是根本有別于非心事物所表現的同類的性質的,另一方面,只有心才可能全部具有這些特點或條件,因此由它們的共具和高層次的表現所決定,心便與非心判然有別。質言之,根據中國一般的心理標準論,判斷一種現象是否是心理現象,一要看它是否有性這一初始的、內在深層的“餡子”,二要從外的方面看它是否有精微、彌散、形而上的存在方式和相狀,是否有神、靈這樣的作用方式和特點。
二、古印度的心理標準理論
心理現象的標準問題與心理現象的范圍及分類問題是密切聯系、相互糾纏的問題,尤其是范圍和標準問題之間似還存在著“問題循環”。古印度哲學對這些問題都有以特定方式表現出來的探討。我們這里關注的主要是佛教在這個問題上的哲學思想,而不涉及它的宗教內容。另外,這里之所以以佛教為考察印度思想的案例,主要是因為它繼承、囊括了古印度其他宗派的有關思想,同時又有自己的創新。我們將先考察佛教關于心理范圍的思想,再闡釋它基于它所發現的最為廣泛的心理樣式對心理標準的探討,最后討論佛教在這些問題上的理論貢獻。
我們在探討佛教的心理標準理論時之所以從心理范圍這個問題出發,是因為對心理范圍的看法不同,對標準的看法必定有別。佛教之所以有極其獨特的心理標準論,是因為它對心理的樣式、范圍的看法極其特殊,最突出的是,它看到的范圍是現今我們所知的最為廣泛的,同時還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強調心理現象本身具有變化性、生成性的特點,例如,隨著修行的深入,隨著由凡向圣的轉化,隨著成圣的心理過程的進步,會陸續派生出許多以前所沒有的心理現象,因此,心理現象的范圍不是固定不變的,例如今后還會有以前所沒有的心理樣式出現。
佛教關注的心的范圍大于世間心靈哲學關注的范圍,其表現之一是,佛教不僅像一般心靈哲學那樣承認人和高等物身上會出現心理現象,而且認為他們之外的許多生命體都有心理現象。世間心靈哲學充其量只關注人及高等動物的心,而佛教心靈哲學除了承認低等動植物有心之外,還廣泛論及三界范圍內的心。佛教心靈哲學認為,除欲界眾生有心之外,色界的天、無色界的圣者都有心。無色界的眾生盡管沒有有形體的色身,但也有一種特殊的心,甚至特殊的身,如意生身,更重要的是,超越三界的圣人也有其心,這心主要表現為無漏心以及帶有現象學性質的真心。“無色既無通(神通),唯是定力”,由入定力所變。因為神通力離不開色身,由“先加行思維方乃得生,故心引起變化事等,定力但是任運生故”。“無色現色,但定所生”,即是說無色界也可有所變身器,不過它們是無形質的,而且“內身多續,少分間斷”。[10](P325)
佛教心靈哲學關注的心理范圍大的第二個表現是,承認在死亡進行時仍有識神存在。從歷時的過程看,眾生的生命盡管是一個從生起到轉滅、再生再轉滅的循環往復的過程,但生命的心理和意識既有滅的方面,如許多念頭剎那生滅,又有不滅的方面,這就是神識或阿那耶識。由于有它的支撐、攝持,眾生的心理才能像流水一樣川流不息。這個過程也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如一期生命的意識可分為14個階段,覺音說,89種心“依十四種行相而轉起”。它們分別是:(1)結生,有情生于六欲天或人中,轉起8種有因的欲界異熟。其他諸界都有其結生、轉起:(2)有分;(3)轉向;(4)見;(5)聞;(6)嗅;(7)嘗;(8)觸;(9)領受;(10)推度;(11)確定;(12)速行;(13)彼所緣;(14)死。[11](P423)
佛教心靈哲學關注的心理現象范圍大的第三個表現是,由于佛教看待心理現象早就用上了現象學的視角和觀點,因此看到了自然、素樸觀點沒有看到的大量帶有現象學性質的心理現象。它們是自在世界所沒有的,是人在進入與世界、人、別的心理現象的關系時所派生出、突現出的心理現象。這些現象大致有兩大類:一是帶有現象學性質的妄心,這相當于今日西方心靈哲學重視的以感受性質、現象學經驗表現出來的心理現象,例如人當下經驗到的疼痛、痛苦、煩惱等;二是帶有現象學性質的真心,即在禪修等心理操作中出現的不同程度的真心顯現。
在心理標準問題上,佛教的看法十分特殊,同時根本有別于無限制地放寬標準的自由主義和只承認人有心理現象的沙文主義。由于佛教有有言之教和無言之教兩種表現,看問題有體與用和理與事兩個維度,因此佛教對心理標準問題的回答就自然有兩方面。一方面,從理體上說,佛所證的真理、法性、實際,看到的整個世界一如一體,眾生平等,沒有心與非心的差別,因此自然無所謂區分標準可言。如經云:“于菩提勝義諦中,即不能說。何以故?彼勝義諦,非語言、非詮表,亦非文字積集所行,尚非心、心所法而可能轉,況復文字有所行邪(耶)?”[12](P492)另一方面,佛出于大悲心,為救度眾生,又不得不說,于是便有了有言之教。經云:“為不可思議一切眾生大悲轉故,……于無文字、無語言、無記說、無詮表法中,為他眾生及補特伽羅,假以文字,建立宣說。”[12](P494)如此建立的宣說,即在有言之教中。從事上看問題,才有心與非心的區別,才有標準需要討論。在這個層面,佛教強調心與非心之間有明確的界線。這界線是什么呢?
佛教認為,心理現象有兩大類,一是真心,二是妄心或眾生能知覺到的處在生生滅滅中的表層的心,它們共有的不同于非心的本質性特點是具有明性,或覺性。所謂明是指心理現象發生時,心不僅知道它發生了,而且只要愿意,就能明白其發生的過程、相狀、特點等。這種明有兩種表現,一是真心的本明,此明與真心的寂然的特點一如一體。圓瑛法師說:“心以靈知不昧為性,有覺明之用。”[13](P12)寂然不動的真心之所以是心,是因為它也有明或知的特點。只不過它是一種極為特殊的明或知,即不依賴心之動變的知,可稱作良知或靈知。祖源禪師說得好:“真心靈知,以寂照為心。”[12](P593)其特點是,無知而知,知而無知。“真心應物,如鏡照像,無心而知故為真。”[12](P594)二是妄心的明或知,即依賴于心之動的明,亦即西方人常說的反思性自我意識。這種意識離不開能(主)與所(客)的關系,即只要有此種明發生,就必然有能明與所明。
從本質構成上說,所有心都有四分的構成。所謂四分,即把有意向特性的任何一個心理事件區分為這樣四種構成:相分、見分、自證分、證自證分。至少有見分和相分。應該承認,佛教內部對此問題是有爭論的。概括說:“安惠立唯一分,難陀立二分,陳那立三分,護法立四分。”[10](P320)四分說是“正義”,即被認為是正統的、標準的、正確的看法。根據四分說,所謂意向性、攀緣,其實是讓有關的境相顯現在心中。這顯現出來的東西盡管不是外在對象本身,但由于它是代表,心通過它可關聯于外在對象,因此至少是“似塵”,是心相。這顯現之相即相分,能識知此相分的東西即見分,對這一過程之結果的把握是自證分,清楚意識到全部過程尤其是自證分,則是證自證分。這就是關于意向性結構的“四分學說”。
嚴格地說,見分和相分等構成只是八識心王的行相。但由于其他心法,如情、意、信等以及被歸入心所法的大量心法,也都有一定的了別和被了別的成分,因此,在寬泛的意義上也可說它們有同心王一樣的行相。《成唯識論述記》云,“心、心所必有二相”[10](P317-318),即見分和相分。
另外,見分是能量,相分是所量,不是只有八識才有量的作用,所有心所法也是如此。故可說,心王、心所在量境之時,其行相有見分和相分等不同方面。佛心、清凈真心有無此四分呢?回答是肯定的。當然,這里沒有這樣的能所關系,即把妄心當作能,把真心當作所。因為佛心的特點是:自明、體明、本明,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但如果為言說的方便或教化的需要,我們是可以從外面對之作出分析的,如說它有能明與所明。不過,應記住的是,這樣的描述及說明,都是在俗諦、比喻的意義上說的。由于心理現象主要以妄心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佛教討論得較多的是這種心理現象的區分方法。基本觀點是,判斷一種現象是不是妄心,除了要根據上述標準區分,還可用這樣一些輔助性方法去做出區分。
心的第一個標志性特征可從整體性關系上把握。例如,世界上不可能有孤立的心理現象發生,在一個人身上,不可能只出現一種心識,而不同時伴有別的隨附性的心所法(情感、情緒、意愿、信念等)之發生。這就是說,心、心所法是和合而起、相輔相成的,就像束蘆(一捆茅蘆)“要多共束方能得住”一樣,單根不能站立。心、心所法也是這樣,“要多相依,方能行世”,其根源生于:“諸有為法性贏劣故,輾轉力持,方能起作。”[14](P80-81)質言之,一個人不可能只出現一種心理現象。有一心生,必有別的心同時生起。任何一種心理都是作為一心理網絡或系統中的一個有機的要素而出現,離開了它的系統,它便不復存在。這是心不同于非心的一個特點。“此心若依、若緣、若時起,彼心共俱心數法等聚生。”[15](P810)意為若某心在某時依某些緣出現了,與此心相應,一定還有別的許多心一同發生了。
心的第二個標志性特征是輾轉相因,即前心是后心的因,就像羊圈中只有一個小門,眾多羊必須一個接一個出來。這當然是從現象學角度說的。對于內覺知或意識而言,只能有心念的接續出現,而不可能有兩個心念同時出現。用現代心理學的話說,心具有“意識流”的特點,如不具有此特點,就不是心理現象。這至少是判斷具有現象學性質的心理現象的一個輔助性標準。
心的第三個特點是,心只要處在清醒狀態,就總要攀附在一個東西上。這個特點類似于西人所說的意向性。“一心不專定,心亦如是,前想后想所不同者。以方便法不可摸則(測),心顠轉癡,是故諸比丘凡夫之人不能觀察心意。”[16](P561)另外,心還有等無間、隨轉的特點,即隨別法的作用而生、住、轉,同時又作為因影響別法。心不同于有質礙性、占有空間的身體和外物,無形無相。這是佛教的近于現代量子力學本體論的思想。這種本體論對立于以有形體特性或以廣延性為判斷存在與否的標準的本體論,而認為無形之物也有存在地位。佛教還認為,心對身有一定的依賴性,但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一切心都離不開身,必依身而轉,而只能說在有色形的有情眾生身上有如此現象,在無色有情身上則不存在心對身體的依賴性,因為他們沒有色身,但照樣有心。他們的心依賴的是“命根、眾同分”。
最后,佛教還找到心的“遍行”特征。所謂遍行的特征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切心理現象的普遍特性,當然也是非心事物不具有的東西。從字面上說,“遍行”即遍在于、遍行于八識心王法之中。作為心所法,遍行心所法像別的心所法一樣,也是為心王所擁有的,是伴隨心王而發生的,因此是心王的隨附性現象。還要注意的是,遍行心所法,不僅遍行于心王,而且遍行于別的一切心所法,因此是一切心理現象中共同的、“遍行的”或普遍的特征。這樣說的根據在于:心所法必然伴隨心王而發生,既然如此,心王有遍行的特征,伴隨它們的心所法也一定如此,因此,遍行心所法也可理解為遍行于一切心所法之中。瑪欣德說:遍行心就是遍一切心,“一切心就是所有的心、任何的心,即89種心。遍(sadharana)的意思是全部都有”[17](P160)。大乘一般說有五個遍行,即作意、觸、受、想、思。上座部主張有七個,即在這五遍行之上增加了一境性和名命根,從而成七遍行。用現代心靈哲學的術語說,作意、觸、想有與意向性一致的內容,也有佛教獨立發現的東西。受也是如此,它近于西方心靈哲學所說的“意識”或感受性質。
總之,根據佛教關于心理標準的理論,只要抓住心的“明性”這一根本特點,再輔之以上述附帶的標準,就能建立說明心與非心之區分的標準體系,就能把心與非心區別開來。因此,心與非心的區分也是一種整體論性質的工作。
三、基于比較的思考
由于我們專門研究過西方心理標準理論的起源、發展與主要理論形態[18],這里只概述它的主要內容及其特點,以作為我們比較研究的邏輯鋪墊。毫無疑問,西方心理標準理論既有悠久而持續的歷史,又有十分發達的當下。另外,它在西方既被當作重要的理論問題來對待,又被當作重要的實踐問題來外置。許多人認為,心的標準因人而異,有的還持悲觀主義態度,如金在權認為,不可能形成關于心靈的統一的概念,進而就沒法找到它的區分標準。因為心理現象有不同的樣式,既然如此,就沒法在它們中找到共同的屬性。[19](P26-27)贊成能找到區分標準的人是以這一問題為出發點的,即它們是一還是多?換言之,有沒有所有心理共有的、非心理現象所沒有的屬性?如果有,這種屬性是一還是多?如果對第一個問題作了肯定回答,即為樂觀主義,作否定回答,即為悲觀主義。如果對第二問題說一,即為“單一屬性觀”。如果為心所共有的屬性是多或一組屬性,則為“多屬性論”。最后,有一種理論,可稱作“單一系統論”。它認為,有一組屬性是所有心靈必有的,但是,作為心靈系統的組成部分的某一個狀態或某一心理樣式不一定具有所有這些屬性。因為該狀態可能由于對整個系統的屬性有因果作用因此成了這個心靈系統的組成部分。[19](P56)
基于對中、印、西三種文化中心理標準理論的比較研究,我們有理由說,它們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理論建樹,可以互補,成為進一步探討的基礎和資源。中國哲學的心理標準理論最寶貴的地方在于,強調要揭示心不同于非心的標志或特征,既應從心理的構成、外在表現和所起的功能作用等方面加以探討,更應關注內在的特別是心的初始的東西。而這又是基于這樣一個極有見地的形而上學原則或預設:包括心在內的一切事物的共同性和差異性,在它們生成時,在由大自然塑造出來的那一剎那,就被鑄就了、鐵定了。因為每個事物在那一刻都被賦予了一種像種子或種子的集合一樣的東西,這就是“性”。它既決定了擁有它的事物后來的可能發展變化甚至不可能的范圍,也決定了該事物與別的事物的共同性,還決定了該事物與別的事物的不同。孟子認為,性是“天之降才”,荀子認為,性是人與物的“本始材樸”(與西方今日原初主義所說的心形成時的“原初的東西”何其相似!)。有此性,事物形成后就以此為規律、準則而運行,因此事物能各循其道,“各正性命”(《易傳·乾象》)。既然如此,要認識世界,按規律辦事,就必須認識這個性。既然性是本性,是體、是道,因此,認識世界的主要任務就是“窮理盡性”。總之,性與生密不可分,只要有產生的事物,就都有性。
這種形而上學的“性”論為探尋心與非心相區別的標準指明了前進方向,鋪平了康莊大道。這是因為,心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樣也有其生,而有生就一定有其稟氣而有的性,有其不同于別的事物的初始的東西。如果真的找到了這性,那當然等于找到了心與非心相區別的東西,至少找到一種條件或標志。按照這樣的邏輯,中國心靈哲學便開辟了一個獨有的探尋心理標準的路徑。換言之,著眼于性的探討,這既是中國心理標準探討的特點之表現,也開創了心理標準研究的一個獨有的進路。中國哲人認為,要找到把它們區別開來的東西,關鍵是到它們的生成過程和內在根底中去找那個最關鍵的“本始材樸”或“性”。心之所以為心,是因為它被大自然稟賦的東西一開始就不同于非心被稟賦的東西。
中國哲學從初始條件和內在根由對心理標準的探討,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要找到心的獨有的、客觀存在的標志性特點,不應忘記它生成的那一剎那,以及它最內在、最根本的東西。無獨有偶,這一道理在今天也為西方心靈哲學和認知科學中的原初主義者認識到了。原初主義者在對“天賦”這一從常識中借來的不嚴謹的哲學概念進行“自然化”時認為,天賦即個體在開始他的心理發生發展時最初為大自然所饋贈的、作為前提與出發點的東西。事實上,人出生后,心理都是有規律地發展的。這充分說明心在形成之初都被賦予了特定的東西,此即原初心理。[20]
印度和西方的許多論者如布倫塔諾等都認識到,心理標準的探討以對心理范圍及其包括的心理樣式的全面而準確的認識為前提條件。因為對范圍的認識不同,對標準的認識自然大相徑庭。印度看到的心理現象的范圍及樣式遠大于世間心靈哲學的認識,因此揭示的標準與后者相比就有極大的一同。由于有這樣的體認,他們在探討標準之前都花大力氣研究心理現象的范圍與樣式。當然具體進路又不盡相同,印度借助其基于禪定的地毯式的觀心方法和描述現象學方法,對心理現象的樣式做了全面的掃描,找到了生滅心的幾乎一切樣式,并從價值角度對它們作了分類,如有的歸納為89種,有的歸納為120或者160種,等等。布倫塔諾用的方法不同,即用的是抽取典型樣本的方法。他認為,由于心理的樣式太多太多,因此,揭示心理現象獨特本質的方法只能是先列舉明白無誤、誰都會承認的心理現象的“實例”,然后從中分析和抽象心的本質特點。很顯然,印度的方法更為可取,因為抽象心理標準所依據的樣式、個例越少,犯以偏概全的錯誤的可能性越大。
東西方心靈哲學還有這樣的共識,即要使對心理標準的探討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不僅要對心理樣式及范圍有足夠全面而充分的認識,而且要弄清它們有無統一性,即諸多心理樣式有沒有共同本質,或者說,個體或整體的心理世界是不是一個統一體。如果有統一性,就有望找到統一的標準,如果沒有,就必須改變揭示和概括心理標準的方法。一般而言,東方心靈哲學盡管承認心理世界有不同乃至異質的樣式和成員,中國哲學甚至認為里面有不同的主,如魂、魄、神、精、靈等,但由于強調它們有共同乃至唯一的體或本,如印度哲學強調它們都根源于真心和阿賴耶識,中國哲學認為它們根源于性或理,因此都相信心有統一性。既然如此,就能找到統一的標準,如中國哲學認為心之所以為心,是因為它有不同于物性的心性。印度哲學認為,心的最根本的標志是明性。西方哲學的看法則比較復雜。如前所述,有的認為有統一性,有的認為沒有。
從比較研究中,我們不難發現,心理標準問題探討必然會碰到“范圍—標準的循環問題”,這是一個兼有心靈哲學和形而上學雙重性質的問題。布倫塔諾已踩上了這個地雷,當然他沒有自覺地做進一步的形而上學探討,如他認為,要研究心理現象,首先要知道心與非心的區別,而要如此,又必須知道心的范圍。他的這一認識無疑是正確的,但不知道提出和探討進一步的問題:怎樣才能弄清心的范圍?其方法論程序是什么?而進一步思考下去又會陷入循環,即要如此,必須弄清心的標準或本質。布倫塔諾沒有認識到這里的麻煩,只是武斷地提出:通過考察典型的心理樣式或個例可找到心理的標準。
筆者認為,要想讓這一領域的探討取得真正的進展,就不能回避這里的問題特別是麻煩,回避是沒有出路的。這里必然碰到這樣的范圍與標準的循環問題,要找到心理現象的標志性特征,或找到心區別于非心的標準,要抽象出這樣的標志,首先必須有關于心理現象的大量樣本,有關于心理范圍的全面認識,而要如此,我們必須先確定它是否屬于待研究的那類現象,即在把它納入心理的范圍而作為其中的樣本或個例時,我們首先要判斷它是不是心理現象。要如此,又必須知道判斷的標準。而要揭示標準,又必須考察個例及范圍。如此遞進,以致無窮。
我們這里將省去具體分析的步驟和細節,直接表明我們的態度。我們認為,要跳出上述循環,消除有關麻煩,第一步是通過語言分析,澄清“心”一詞的基本詞義和指稱,進而建立關于心的本質和標志性特征的理論預設。第二步是據此去搜羅心的盡可能多的個例和樣式,并在這個過程中修正、檢驗前面關于以下的理論預設,建立進一步的理論預設。第三步再根據新的理論預設去做樣本、范圍研究,盡可能全面地找到心的個例,特別是樣式。這些樣式是心的主要表現形式,也可看作心的不太嚴格的子類。這種研究包括布倫塔諾所說的研究心的典型樣本。我們認為,經過前面的試錯性認識,我們可以在對心的基本認識的基礎上,努力完成這樣的任務,即盡可能全面地認識心的樣式和范圍。只有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對標準和本質的認識才會有比較扎實和可靠的基礎。因此這一步極為重要。大致說,可這樣開展工作:先運用描述現象學方法或類似于地理大發現的方法,對共時存在的一切心理樣式及其性質,進行心理個例的“普查”,對表層心理后的深層心理做進一步的勘探和挖掘,關注長期塵封的東方心靈哲學寶藏,再來做關于心理一般標準和共同本質的抽象。
在這里之所以應關注東方心靈哲學,是因為東方心靈哲學在這一領域確實做了大量工作,足以彌補西方哲學的不足。東方心靈哲學關注的心理范圍之大、涉及的個例之多都超過了西方。例如,中國心靈哲學在這方面就有不凡的表現。它對心、性、情、志、才、精、氣、神、魂、魄等的挖掘和探討就極具特色。盡管它對其所作的解釋、對其本質的揭示以及由此而建立的心理圖景還值得研究,但造出的這些詞絕不是無病呻吟,而有其真實的且不能為其他心理語言所涵蓋的所指。質言之,東方文化在這方面做了大量有價值的、遠超西方的工作,因此我們要推進這一研究,就應下大力氣挖掘其中的積極成果,然后在綜合西方心靈哲學成果和現代有關科技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心理世界的人口普查,或心理地質學、探礦學研究,直至建立全面而科學的心理地理學、地圖學。
怎樣看待西方人看重的意向性這一標準呢?我們知道,這一為中世紀哲學家提出、為布倫塔諾具體展開和闡釋的心理標準,盡管現在出現了一些爭論,但最低限度上,即使是批評者一般也不否認它是部分心理現象獨有的特征,因此可看作一種局部的標準。我們認為,只要深入研究下去,對心的每種個例和樣式的內在本質作出探討,就能發現許多心理現象的確具有意向性。但我們又同時認為,意向性只是心的淺表的特征,因此不是把心與非心區別開來的真正的標準。就此而言,一些人對它的非議是有道理的。在我們看來,一切心理現象里面都有這樣的本質,即以進化積淀的“前結構”為基礎的、主動有意識的關聯性或關聯作用。這種性質表面上看近于西人所說的意向性,其實有根本的不同。因為我們強調的意向性既以對心的深掘為基礎,也受到中國心靈哲學心性論的啟發。從發生學上說,每個人出生時被自然授予的東西(性或前結構),不僅確實存在(當然是傾向、稟賦或知識能力的種子,而不是先驗論所說的現成的知識或能力),而且決定了我們后天可能和不可能的范圍及程度,甚至決定了我們每個人與他人的區別,決定了心與非心的區別。
四、結語
綜上所述,作為整體的、矛盾統一體的心除了有樣式多樣性、性質差異性的特點之外,還有其共同的本質,那就是所有心理現象都有其覺知性或能為主體自己認識的自知性,都有對物質實在的不同形式、程度的依賴性,都是同與異、生與滅、連續與非連續、變與不變的矛盾統一。正是它們,把心與非心區別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