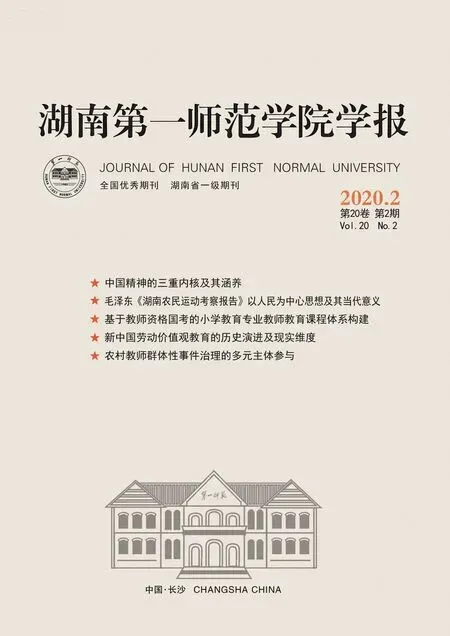佞妄與真實:學校教育形塑人的規訓策略與抗拒行為解蔽
——讀胡春光教授《規訓與抗拒:教育社會學視野中的學校生活》
謝泉峰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 教育科學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
一、問題的提出
1950年7月31日,一列滿載偽滿戰犯的蘇聯列車正緩緩駛進位于中蘇邊境的綏芬河車站,列車上有一位面容削瘦,戴著高度近視眼鏡的中年男人,他早已坐臥不安,對死亡的恐懼和對未來的絕望始終籠罩在心頭,圍聚不散。這個人是中國的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在接下來的9年多時間里,他被送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教育和勞動改造,直到1959年12月4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成為一名普通公民。他寫過一本自傳《我的前半生》,該書是以這句話收尾的:“‘人’,這是我在開蒙讀本《三字經》上認識的第一個字,可是在我的前半生中一直沒有讀懂它。有了共產黨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這個莊嚴字眼的含義,才做了真正的人。”[1]從此以后,他走上了新生之路。
之所以敘述上述這些情節和內容,是因為在讀到胡春光教授的《規訓與抗拒:教育社會學視野中的學校生活》(以下簡稱《規訓與抗拒》)一書時,這是腦海中一直聯翩不去的場景畫面。在這本書的末尾,有這樣一句話可作上述場景的對應:“我們的教育日益成為遠離‘人’的技術訓練,它高奏‘知識就是力量’的號角,打著‘科學主義’的旗幟,試圖用規訓的技術、規訓的道德、規訓的知識為人們裝備上最具生產力的功能,而人的德性和智慧的養成,人的生命和精神的提升,則被拋擲九霄云外了。”[2]336
這兩幅畫面的對比竟然如此鮮明。一方面,愛新覺羅·溥儀身在囹圄,卻恍如在學校進修學習。在一次全國政協座談會的發言中,他甚至公開明述:“是的,我住的監獄就是一個學校——改造靈魂,把鬼變成人的學校”[3];而另一方面,在春光教授的《規訓與抗拒》一書中,卻有這樣的文字:“學校是進行教育的場所,這種教育是有目的、有組織、有意識進行的,學校組織形式本身就包含著一種規范性的根源:把‘規定年齡’或‘規定身份’的人強行約束在‘規定空間’內,按‘規定要求’進行‘規定活動’。”[2]195此種學校何異于監獄?監獄看起來像學校,而學校卻又是看起來像監獄,這樣的對比不能不讓人自然反思:到底什么是佞妄,什么是真實?為什么我們的學校教育中有這樣的佞妄?以致于學校看起來并不像給人以自由的教育機構,而更像是管控人、改造人、訓練人的監獄?
《規訓與抗拒》采取近距微觀,選用日常生活的視角,通過批判民族志中參與觀察的方法,以河南省南部某縣宏橋小學的實地體驗與研究作為基礎,運用福柯的“規訓”理念,對教育場域下學校和教師的規訓策略及學校生活中學生的抗拒行為進行近距離審視和理性反思。從學校、教室這些微小的規訓空間中,彰顯那些被日常生活的瑣屑和細節遮蔽了的教育事實,進而通過教育之問,反思教育之徑,探詢教育之道,從中發現“人”存在的可能意義,以救贖現代規訓化的教育。這樣的努力著實令人欽佩。從表面上看,這本書只是在運用福柯的“規訓”理念批判學校中試圖形塑學生的努力及揭示學生的抗拒表現背后深層的理性邏輯,但通過解蔽各種形式細膩地施加于被監視、訓練和矯正對象的規訓策略與技術,并對其進行重新審視,作者實際上提出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應如何促進學校教育中“人”的回歸,使每個人可以成就自己,使學校可以成為“與人的生命狀態相結合,讓人性之花自由綻放”[5]335的學校?
二、學校或監獄:教育形塑人的佞妄與真實
學校和監獄都是形塑人的機構,它們之間的不同在于,人們設立監獄的目的是為了改造罪犯,而設立學校的目的則是為了培養新人。在《規訓與抗拒》一書中,“規訓化的學校”是作者批判的對象,在這里“人”被各種知識、技術、制度再造成為適應社會的“工具人”。這本書延續了福柯“規訓社會”的思路,通過詳盡的內容描述,透露出規訓化學校和監獄在本質上可以說是一回事:通過設計安排、制度規范、層級監視等規訓的手段,使人被馴服、被操控。所以書中呈現出一副近乎在監獄中才能遇到的場景:展示威權的各類莊重儀式,密織如羅網般的管理制度和各類教導、檢查、懲罰與監控的在場。《規訓與抗拒》借此揭開了學校教育中佞妄的側面,透露出許多校園里類于監獄的真實底幕。
(一)隔離的時空
隔離的表現之一是時間被精密安排。學校規定了嚴格的作息時間表,在時間表內明確規定身體在什么時間應該做什么事情、出現在什么地方,以此對時間進行切割,使身體按照時間的節奏適應生活作息,以達到規訓的效果[2]71。時間表規定了每日生活學習的節奏、所安排的活動和調節重復周期。例如把每個學年都劃分為上下兩個學期,每個學期又切分成若干個教學周,每周的課程表是節奏重復的單位。在課程表內,學生每天的時間都以分鐘為單位作了精密的切割和清晰的安排。伴隨這種統一標準而來的是每天的例行公事,而那些未被列入到標準時間表的其它自由時間常常被視作是沒有價值的,所以教師可以隨意侵占和搶奪[2]199-200。福柯在論及監獄對犯人進行時間表管理時,強調“這種教育占據了整個的人,占據了人的全部體力和道德能力,占據了人的全部時間”,是一種“全面規訓”[4],而學校嚴格的時間管理正使之不可避免地成為學生心目中的“監獄”。
隔離的表現之二是空間被“科學”分配。學校通過分配不同的空間位置來劃分等級,例如學生所在的班級和座次、升旗儀式中的角色和所占位置等等。首先是學校本身被孤立,分隔、封閉、靜謐被視為是所有學校的共同特征,通過圍墻、鐵門等,學校與外界隔離開來,學生的活動由此受到嚴格的限制和監管,形成暫時隔離的“孤島”,這在管理上可以避免那些“不期而遇的接觸所導致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其次是校園內部被分配,教學樓和運動操場、草坪、小花園、餐廳之間被宣傳欄和升旗臺所隔離,如果說運動操場象征著“自由”,張貼滿學校規章制度、學生先進事跡、違紀學生懲處等相關內容的宣傳欄則代表著“規訓”,而沿著走廊一字排開的教室更宛如一間間封閉的囚室。最后是教室內部被分割:正前方是高高的講臺,以方便教師進行居高臨下的監管和控制;中間的直列式的座位會根據成績表現好壞和維持紀律的需要進行安排,以促成班級中學生的學習競爭氛圍,最后一排則是專供犯錯學生使用的“專門座”,將這些學生隔離,可以同時達到屏蔽對其他同學的負面影響和懲罰犯錯學生的雙重目的[2]178-184。這種試圖通過空間分隔操作產生秩序的方法正是監獄的普遍做法。正如福柯所述,監獄的首要原則就是隔離。犯人與外部世界、與促成犯罪的事物和集團相隔離,并使犯人彼此隔離[4]。
(二)多重的賦權
首先是知識壟斷賦予的文化霸權。《規訓與抗拒》借助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對學校教育進行了抽絲剝繭式的解剖,強調學校教育中對知識的選擇、分類、分配與評估都被意識形態所預設,學生只有無條件接受學校的文化霸權,其“文化資本”才擁有合法資格,能得到社會的承認和保護[2]114-116。需要強調,這里的知識并非普遍化的、社會化的、甚至是專業化的知識,而只是學校場域內特定的“專門知識”,它決定了對應“思想一致,共同努力”的成語是“同心協力”,而不是“齊心協力”,對應“刻畫描摹得非常逼真”的成語是“惟妙惟肖”,而不是“栩栩如生”[5]。這使教育逐漸異化成了對獲取“標準答案”和高分數而施行的沖壓,將個體塑模成社會框定的“秩序人”。
其次是優勢地位賦予的話語霸權。斯圖爾特·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將“話語”的解碼劃分為三類:“主導—霸權”立場;協調符碼立場;對抗符碼立場。《規訓與抗拒》中的學校顯然采取了第一種立場。對此,作者批評了那種打著“為了學生的一切,一切為了學生”崇高使命的幌子從事規訓教育的學校,認為這種“愛”是一種極度隱蔽性的控制手段,看似為了學生的未來發展,實際上卻以侵犯學生的人格尊嚴、戕害學生的身體為代價[2]192-193。教師由于其在教育過程中處于優勢地位,掌握了話語霸權,從而成為編碼者,主導了整個規訓的過程,通過“一言堂”維持教學紀律,對那些抗拒規范,例如講小話的學生貼上“搗蛋者”的標簽,剝奪其發言的權利。在各種威言厲喝下,教師不斷將學生壓制成為王小波筆下“沉默的大多數”,完成了“馴化的教育”。
最后是教師角色賦予的裁決霸權。《規訓與抗拒》延續了福柯對傳統權力理論的批判,把對權力的關注重點由戰場、刑場、絞刑架、皇冠、權杖或紅頭文件轉移到傳統習俗、日常生活、閑談碎語、道聽途說和眾目睽睽中來[2]133-134,特別是關注著教育場域中教師對于權力的運用。在運用權力的過程中,教師成為“訓導者”,負責裁決各種矛盾和沖突,哪怕這些并不合理。例如如何分配空間、如何安排座位、如何施加懲罰、如何挑選校服、如何進行評比,乃至懲處誰、如何懲處等等。當“權力控制著裁決,裁決又包裝著權力”時,裁決本身就帶上了規訓的色彩,學生的表現好壞在“規范化”的裁決之下被任意判斷、描述和度量,學生成為隨時被檢查、被支配的對象[2]215-217。在此種情況下,規訓學校和監獄已經沒有本質的區別。
三、規范與規訓:教育形塑人的策略與技術
擁有隔離的時空和多重的賦權并不意味著學校就一定會變成“監獄”,因為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被監禁的愛新覺羅·溥儀同樣會經歷上述種種,后者卻從中找到了自我,獲得了自由。所以問題的關鍵仍然在于管理者如何對待被管理者,而被管理者又會表現出怎樣的反應。如果管理者善于運用一些策略和技術,監獄也會像一所學校,反之,學校就會像一座監獄。在《規訓與抗拒》一書中,通過宏橋小學教學日常的鋪陳和描述,我們能發現教育中從“規范”到“規訓”演化的趨勢,從中窺視到當前我國許多學校形塑學生策略和技術的冰山一角。
(一)莊重的儀式
儀式是形塑人的普遍手段。涂爾干說過,儀式服務于信仰,它能使集體意識復蘇,增強個體社會本性,把個體歸為群體[6]518-521。“在儀式中,人們受到外部約束或進行自我克制,以拋棄那些功用的東西,將所有尊崇的情感通過某些抑制作用在尊崇者的內心傳達出來”[6]425-431,以此形塑個體。《規訓與抗拒》展現了學校里幾種常見的儀式,如新生歡迎儀式、日常升旗儀式、課堂問候儀式等,這些儀式通過教師向部分學生賦予“宣誓人”“升旗手”“三好學生”等資格,塑造著主流意識形塑“好學生”的期望。問題僅僅在于對資格的選擇上,正如歐文·戈夫曼所言,人們會挑選那些有能力達到表演效果的可靠之人作為劇班演員[8]。在學校中,這些“可靠”的學生無一例外都是幾個“學習好”的學生,致使“儀式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少數人的事情”[2]152,或者更準確的說,成為少數符合規訓要求學生的特別“秀場”。這樣的儀式對大多數同學而言,自然是缺乏“情感能量”的,它成為蘭德爾·柯林斯言道的“強迫的儀式”“空洞的儀式”,那些“在教育體制中沒有前程機會的孩子,是學校里被迫的服從命令者,所以往往會直接針對那些屈服其名義的‘神圣物’,做出故意破壞和其他形式的‘越軌行為’。”[9]這解釋了《規訓與抗拒》一書中描述的,“學生總是想盡各種理由要拖上幾分鐘才肯進教室”,“學校每天最后一節課結束后,教室中轟然而響的歡呼聲”[2]200。
(二)密織的制度
制度使形塑過程容易計量。這種計量是通過對照各類標準來度測身體行為,以此對之進行全面而周密的管控來實施的。《規訓與抗拒》全文收錄了精細得近乎瑣碎的制度規范,包括《宏橋小學日常行為實施細則》《宏橋小學學生作業書寫規范》《宏橋小學三年級(3)班班級管理量化標準條例》等,這些制度規范對學生的時間切割、排隊隊列、穿著服裝、儀容儀表、坐姿坐態、書寫規范等都做了詳盡且細致的規定,幾乎囊括了學校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違背制度規范則必然伴隨著各種輕重程度不一的懲罰。書中所列的《宏橋小學日常行為實施細則》與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揭露的“巴黎少年犯監管所”規章如出一轍,甚至規定得更為細密。正如《規訓與抗拒》評價的,“倘若所有一切都需要規定,那的確是件不幸的事情。”學校本來是有目的、有組織、有意識進行教育的場所,其組織形式本身就包含著一種規范性,但教育的規范如果只是建立在警示、威脅、懲罰等基礎上,那只是“規訓”而已。呆板機械的規范追求“服從性”,它關注身體被操縱、被禁止、被規訓、被塑造,不是將個體作為一個真實、完整的人,考慮其現實生存境遇需要,而是希望個體在規章制度的控制下服從,成為的“秩序人”[2]157-163。密織的制度是違背基本的人性的,它使學生動輒得咎,久而久之,學校成為一個“壓迫的場域”,學生越來越疏離、沉默、甚至麻木,這其實也是一種無聲的抗拒。
(三)日常的管控
管控是形塑人的直接方式。幾乎所有的管控都是對學生身體動作的規訓,這些規訓源于被學校在管理和組織上控制著的各種有關規則、儀式和程序。為了有利于文化生產體制中的生產效率與管理,學校(教師)通過對學生的身體進行管控,使之獲得一種被馴化的意識[2]10-11。管控主要采取時間切割、姿勢控制、團隊規范和檢查考試四種技術來發揮作用,通過確立明確的標準,由教師對照標準來施行,這種做法被學校和教師視為對學生行為的“規范”,然而如果對其執行過程進行認真審視,就會發現它們其實更多的是“規訓”。以《規訓與抗拒》中宏橋小學制定的校服為例,它是校方的管理行為,是教育者用來規限學生身體的一個重要手段,它是站在教育者的立場,而非被教育者的立場進行的。所以,盡管服裝原本屬于身體,但是學生的身體卻被剝奪了為自己挑選校服的權力[2]211。這使學校的教育不是走向人與人之間的理解,不是以自己心靈體驗他人心理,而是把受教者視為必須塑造、改造和重造的對象,當作思想、靈魂、情感和人格的說教工具[2]9,使其演變成為“規訓”的教育。當學生被束縛在一種無形的宿命力量中,既無法體驗學習生活的樂趣和意義,也感受不到學校生活中的民主和自由,不再充滿激情的創造力和想象力,習慣于程序化和規范化的機械生活之后,他們就會被“馴化”[2]92-93。然而各種懲罰公示卻顯現出,上述目標并未完全實現。
四、在場和逃逸:教育形塑人的過程與效果
教育應該是身體在場的[10],因為只有身體在場才可能創造出臨場感,也只有身體在場才可以通過“具身認知”幫助學生嵌入環境,強化態度和行為,為“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打下堅實基礎。但身體在場并不意味著意識也必然在場,教育要培養人,只有身心俱在才有可能實現。《規訓與抗拒》以觀察者的立場,揭示了宏橋小學師生的博弈過程,其結果是學生的“身體在場”和“心靈逃逸”并存,它將教育中的佞妄面和學生中的真實面一覽于前,為讀者呈現出了一幅幅“靈魂脫殼”的鮮活場景。
(一)被迫的身體在場
懷特海曾說:“一種設計完美的教育,其目的應該是使紀律成為自由選擇的自發的結果。”[11]但在學校中,身體在場并不是一種本能的自發結果,而是一種必須的對學生的外在要求。為了確保身體在場,福柯在談到“規訓”時強調的幾種手段,如“全景敞視”“層級監視”和“檢查考試”在宏橋小學都得到了近乎完美地再現。例如:學校采取了“全景敞視”式建筑模式,教室安裝著敞亮的大窗戶,方便教師隨時“觀察”班級紀律情況,教室內的講臺位置處于正前方且高出地面,以方便教師全方位監控學生。管理采取了“層級監視”的相關做法,形成了“教師—班干部—班級學生”的科層制規訓結構,組成密密麻麻的監視之網。通過不斷地“檢查考試”,一方面使對學生的管理和教育有一個明確的量化和度量的標準,另一方面也使對學生的“規訓”過程和效果可以直接顯現出來,便于將學生嵌入統一的規范模板,最終實現“教育等級化、知識特定化、教學標準化”[2]219。為了確保學生的身體在場,教師采取了各種手段,例如通過隔離和限制相關人員接觸、通過宣示以強化自身的管控權、通過懲罰以彰顯自己的支配權等等,努力將學生限定在各自的空間內,并分別貼上不同的“標簽”,采取差異化的管控策略予以區別對待。這使絕大多數學生的抗拒都只能在有限的空間中進行,并在身體在場的情況下以靈活的方式加以應對。
(二)自由的心靈逃逸
身體的被迫在場會使學生心生抗拒,他們會用多種方式努力表現出其自身的主體能動性。《規訓與抗拒》一書中區分了“搗蛋型”“批判型”“調適型”“玩樂型”“變臉型”和“當前型”六種學生抗拒的形態,但就抗拒的方式而言,大致可以分為“話語脫域”“角落隱蔽”和“保持距離”三種,這也是其心靈逃逸、獲取自由的三種途徑。首先是“話語脫域”,由于話語意味著權力,話語交鋒是師生博弈的主要方式之一。作為對教師“一言堂”的本能抗拒,學生會試圖“依附教師的規范來試探”可能存在的管理縫隙。例如在正常的課堂討論中故意發言脫離主題或脫離引導,通過轉移焦點在“規范的邊緣中游走”,尋找自主的抗拒空間。如果說“話語脫域”帶有正面進攻的性質,“角落隱蔽”則是明顯的主動防御,學生在被監視的情況下選擇表面上的服從,但努力讓自己隱蔽在教室里某個不被教師關注的角落,或是看不到的地方,通過逾越規范的破壞行為彰顯自我的存在,再以裝聾作啞、陽奉陰違、找人代過(例如代抄作業)等方式規避懲罰,然后繼續我行我素。“保持距離”則是努力通過各種“安靜的沉默”拉開與教師之間的距離,采取消極防御的“自保策略”,他們只會偶而利用“搭便車”的機會短暫突破原來禁錮自己的空間,以尋求片刻的自由。上述的種種方式都表明:規訓化的教育非但并未能達到馴化學生的目的,甚至還使學生在對抗中逐漸形成了反學校文化。
五、評價
保羅·弗萊雷在《被壓迫者教育學》中說:“如果人是探索者,并且他們的本體使命是使人人性化,那么他們遲早會覺察到試圖控制他們的灌輸式教育所存在的矛盾,然后投身到解放自身的斗爭中去。”[12]《規訓與抗拒》以宏橋小學作為樣本,通過大量的一手資料,感性和生動地再現了現行教育體制下學校規訓化教育的無處不在和無孔不入,它發現了學校教育中教師通過規訓試圖控制學生和學生抗拒的矛盾,對當前規范化、制度化、標準化的學校教育進行了審問和反思,并站在學校教育和教學實踐的現場,提出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關于學校教育應該如何具體培養“人”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是有價值的,是因為過去在談到教育時,研究者多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宣示教育應該如何,鮮有站在教育現場,直面“事物本身”付諸行動,來反思教育現象的本質意義,判斷其合理性與正當性。這種親臨其境的洞察,使我們既有機會站在一個高度看清學校規訓教育的現實,思籌可能的解決之道,又使我們有機會坐在每一個教師和學生中間,聽他們理性地訴說自己的想法和認知,從中發現合理的部分,尋求共情的理解,而后者就是書中最后部分專門提到的“對話式教育”。總之,《規訓與抗拒》一書呈現出敏銳的洞察力、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創新的審視視角,為我們思考教育的本質及改進教育實踐提供了重要的思考與啟發,這使得該書成為我國近年來教育學領域批判教育學的力作之一。
毋庸諱言,《規訓與抗拒》只是一個開始,后續還應該有更多的問題需要深入探討和研究。例如王雅麗就反詰道,規訓教育真的就是一種惡嗎?教育要尊重人的天性,并不等于教育就必須要順從人的天性,因為整個教育過程,或者說文明化的過程本身就是人不斷擺脫自然性的過程[13]。在保羅·威利斯的《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一書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那些抵制權威、摒棄教條的反學校文化,讓這些工人階級的子弟走上了自我詛咒的道路”[14],使他們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陷入了更深的泥潭和輪回。以此而論,在學校教育中有一定程度的規訓是必須的。就連《規訓與抗拒》中也坦承:“規范的限制本身也是一種解放的力量。”[2]159那么,怎樣的規訓教育、什么程度的規訓教育才是規范的、合理的、科學的,能夠真正起到解放“人”的目的,這還需要做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此外,書中提及的對話式教育是否就真的可以幫助學校擺脫規訓教育的桎梏?雅思貝爾斯說:“教育是人與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傳遞的活動。而人與人的交往是雙方(我與你)的對話與敞亮。”[15]這里的“對話”與“敞亮”是分開的,因為對話僅僅只是引導交流和溝通的第一步,它并不一定能夠構建相互信賴的關系,也不一定必然促成彼此之間的理解和改變,實現內心的“敞亮”。在大多數現實生活中,不是只要雙方懷著真誠心態,以正確方式對話,就一定能達成相互之間的理解和接受[16],實現彼此內心里的“敞亮”。即便可以,也不是每個人都愿意在原來的基礎上作出相應的改變,所以交往仍然會存在隔閡。佐藤學把“學習”定義為和“客觀世界”“他人”“自身”三位一體的交往和對話[36],在“對話”之外如何實現深度的“交往”,實現“自由”的學習,這依舊是一個有待解決的課題。“你放心,共產黨的政權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國的黨和人民氣量是最大的。”負責押送愛新覺羅·溥儀到中國的阿斯尼斯大尉在離別前說了這樣一番話。它也是對話,但并未消除這位末代皇帝的疑懼,事實上,對他的教育和改造才剛剛揭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