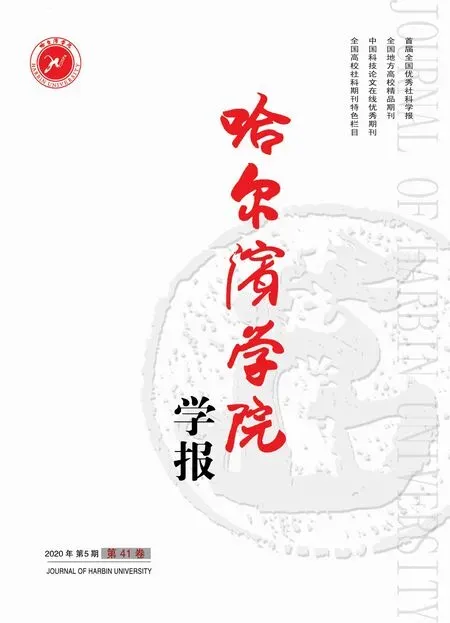“越少,就越多”
——以接受美學(xué)的視角透視《雨中的貓》
黃愛(ài)玲
(黃山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安徽 黃山 245000)
厄內(nèi)斯特·海明威是蜚聲世界文壇的美國(guó)現(xiàn)代著名小說(shuō)家,他的作品看似筆調(diào)輕松、瀟灑自然,實(shí)則觀察銳利、思想深刻,成為西方文學(xué)畫(huà)廊中一道獨(dú)特的景觀,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ài)。
20世紀(jì)30年代,美國(guó)建筑師羅德維希的名言“越少,就越多”開(kāi)始影響并改變著海明威。創(chuàng)作中,他刪除那些沒(méi)有必要的情節(jié),修剪作品語(yǔ)言,突出人物性格,使作品越來(lái)越趨于精練。其短篇小說(shuō)《雨中的貓》就因視角獨(dú)特、語(yǔ)言簡(jiǎn)潔、內(nèi)涵豐富,被認(rèn)為是這一理論應(yīng)用于寫(xiě)作的典范。而接受美學(xué)是當(dāng)代文藝學(xué)領(lǐng)域中一個(gè)重要的文藝思潮,在某種意義上,這一思想與“越少,就越多”的創(chuàng)作原則有相通之處,只不過(guò)海明威是從作家的角度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和欣賞,接受美學(xué)則是把接受者從客體轉(zhuǎn)為主體,重視讀者與作品之間的深度對(duì)話。故本文嘗試以接受美學(xué)的視角,從召喚結(jié)構(gòu)、期待視野及意義的不確定三個(gè)方面,來(lái)透視小說(shuō)《雨中的貓》的迷人風(fēng)采。
一、召喚結(jié)構(gòu)與未知的空白
接受美學(xué)產(chǎn)生于20世紀(jì)60年代末的德國(guó),是當(dāng)時(shí)一種令人矚目的文學(xué)思潮。它“反對(duì)作品中心論和單純的作家研究,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總體動(dòng)態(tài)過(guò)程的研究,重視讀者的接受和積極參與”,[1](P112)認(rèn)為沒(méi)有經(jīng)過(guò)讀者閱讀的文本只是一堆白紙黑字,如同沒(méi)有進(jìn)入流通領(lǐng)域的產(chǎn)品就不能成為商品一樣,作品的意義只有在閱讀中才能產(chǎn)生。
在此基礎(chǔ)上,接受美學(xué)代表人物伊塞爾提出了“召喚結(jié)構(gòu)”的概念。所謂召喚結(jié)構(gòu)是文本意義的不確定性與空白而促使讀者去尋找意義的文本結(jié)構(gòu)。他認(rèn)為,“文學(xué)作品只是為讀者提供了一個(gè)圖式或骨架,其中留下了許多未定點(diǎn)和空白要讀者自己去填補(bǔ)。”[2](P356)可見(jiàn),與召喚結(jié)構(gòu)聯(lián)系最緊密的要素就是空白和未定點(diǎn)。這些空白和未定點(diǎn)就暗示或隱藏在情節(jié)、線索、語(yǔ)言、結(jié)構(gòu)等各個(gè)方面,它們具有很強(qiáng)的藝術(shù)魔力,召喚著讀者去想象、創(chuàng)造和構(gòu)建,去填補(bǔ)文本的意義,從而挖掘出作者隱藏在文字背后的深刻內(nèi)涵。
小說(shuō)《雨中的貓》講述的是在意大利的一家旅館里,一對(duì)美國(guó)夫婦同旅館主人、女傭之間發(fā)生的幾乎沒(méi)有什么故事的故事,只是通過(guò)一只貓,把這些毫不相干的人聯(lián)系在一起。夫婦倆在旅館里無(wú)所事事,丈夫看著書(shū),妻子無(wú)聊地眺望窗外,看到雨中有一只貓,就想捉住它,但沒(méi)抓到。回房后,開(kāi)始嘮叨不停,終于引得丈夫不耐煩。最后,旅館老板派女傭送來(lái)了另一只大貓,故事到此戛然而止。
小說(shuō)只有兩千多字,若浮光掠影地看,你根本不能體會(huì)到它的妙處。然而,掠過(guò)表面,潛入“海底”,你就會(huì)發(fā)現(xiàn)這篇小說(shuō)意蘊(yùn)無(wú)窮、意味深長(zhǎng)。倚窗眺望的無(wú)所事事的妻子、旅館外“空蕩蕩”的廣場(chǎng)、“閃閃發(fā)光的青銅紀(jì)念碑”、被雨水肆意沖刷著的棕櫚樹(shù),以及“一路上碰到的他們都不認(rèn)識(shí)”的陌生人……這些看似與故事沒(méi)有什么關(guān)系的描寫(xiě),形成了一個(gè)又一個(gè)表層意義上的空白點(diǎn),好似“一種尋求連接缺乏的無(wú)言邀請(qǐng)”,吸引讀者繼續(xù)往下讀,直至潛入“冰山”底部,才能真正明白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
20世紀(jì)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剛剛結(jié)束。參加過(guò)一戰(zhàn)的海明威,在目睹了戰(zhàn)爭(zhēng)中人無(wú)意義、無(wú)價(jià)值的死亡后,意識(shí)到這是“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規(guī)模、最兇殘、指揮最糟糕的屠殺”。從死人堆里爬出來(lái)的海明威,同當(dāng)時(shí)許多美國(guó)青年一樣,美好理想徹底破滅,人生價(jià)值感喪失,取而代之的是無(wú)所不在的悲觀和虛無(wú)之感。小說(shuō)中,“空蕩蕩”的廣場(chǎng)、“陌生的面孔”無(wú)不象征著人們內(nèi)心的空虛,“在雨中閃閃發(fā)亮的”戰(zhàn)爭(zhēng)紀(jì)念碑更在暗示著他們心中永遠(yuǎn)揮之不去的戰(zhàn)爭(zhēng)陰霾,雨水的洗滌似乎讓?xiě)?zhàn)爭(zhēng)的傷痛觸目驚心。
再?gòu)恼麄€(gè)故事的發(fā)展來(lái)看,這位妻子看到貓的反應(yīng)是“我要下去捉那只貓”,當(dāng)她發(fā)現(xiàn)貓已經(jīng)不在時(shí),“突然感到大失所望”,并自言自語(yǔ):“我多么想要那只貓。”“我不知道我干嘛想要那只貓。我要那只可憐的貓。做一只待在雨里的貓,可不是什么有趣的事兒。”雨中這只可憐的貓不正是這位孤寂妻子的絕好寫(xiě)照,而這些不著邊際的話,不正折射出戰(zhàn)后的美國(guó)年青人心靈的空虛與苦悶。作為“迷惘一代”作家的領(lǐng)軍人物,海明威正是以其獨(dú)特的視角和犀利的筆鋒,言盡而意無(wú)窮地描繪出了戰(zhàn)后失去理想的年輕一代的精神困境。
二、期待視野的打破與重建
期待視野,是接受美學(xué)中另一個(gè)非常重要的概念,最先由接受美學(xué)家姚斯提出,主要“指讀者在閱讀理解之前對(duì)作品顯現(xiàn)方式的定向性期待,這種期待有一個(gè)相對(duì)確定的界域,此界域圈定了理解之可能的限度”。[3](P289)讀者的期待視野是文學(xué)活動(dòng)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文學(xué)活動(dòng)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影響著作家的創(chuàng)作。作家在進(jìn)行文學(xué)創(chuàng)作時(shí),如果不考慮讀者的期待視野,盲目創(chuàng)作,其作品必然被讀者拒絕接受,最終成為一堆廢紙。
德國(guó)美學(xué)家伊瑟爾認(rèn)為:“在文學(xué)作品的寫(xiě)作過(guò)程中,作者頭腦里始終有一個(gè)‘隱在的讀者’,寫(xiě)作過(guò)程便是向這個(gè)隱在的讀者敘述故事并與其對(duì)話的過(guò)程。因此,讀者的作用已經(jīng)蘊(yùn)含在文本的結(jié)構(gòu)之中。”[4](P78)任何閱讀都是懷著某種期待視野而進(jìn)行的,讀者從讀小說(shuō)的那一刻便下意識(shí)地對(duì)“中間”和“結(jié)局”進(jìn)行預(yù)測(cè)。如果作品與期待完全一致,這樣的小說(shuō)則缺乏藝術(shù)魅力;反之,如果讀者的期待視野在閱讀中不斷被打破,那么,讀者則獲得超越期待視野的神奇藝術(shù)空間,這部小說(shuō)就具有較高的審美價(jià)值。總之,“任何文學(xué)閱讀都是對(duì)本文的一種期待,但各種期待幾乎從來(lái)不曾在真的文學(xué)文本中實(shí)現(xiàn),否則就是一種缺陷,好的文學(xué)文本在喚起讀者期待的同時(shí)更應(yīng)否定它、打破它,而不是去證實(shí)它、實(shí)現(xiàn)它。”[5](P296)
小說(shuō)《雨中的貓》便是這樣的作品。初看題目時(shí),你以為這是一篇關(guān)于一只貓的故事,讀著讀著,你又會(huì)猜測(cè)妻子為什么要抓那只雨中的貓,貓會(huì)被逮住嗎?讀到最后,你又疑惑了,貓莫名其妙地沒(méi)有了,夫妻又在吵架,情節(jié)已經(jīng)無(wú)法再進(jìn)行下去了,作者到底要表達(dá)什么?故事的結(jié)尾完全超出你的想象。海明威就是以一種突破傳統(tǒng)的全新姿態(tài),將讀者原有的期待視野徹底打破。在閱讀中,當(dāng)這種期待不斷被打破,讀者也就融入到作品中去,產(chǎn)生閱讀和探究的興趣,從而真正理解作品。原來(lái),作者哪里是在講貓的故事,他只是巧妙地以一只雨中的貓為線索,展開(kāi)一對(duì)夫妻的日常對(duì)話,反映一戰(zhàn)后人們精神空虛的普遍狀態(tài)。站在窗邊的妻子,百無(wú)聊賴(lài),一只蜷縮在雨中的貓悄然進(jìn)入她的視野,并成為她眼中唯一的“風(fēng)景”,成為她最大的精神寄托。而對(duì)她視若無(wú)睹的丈夫則選擇逃避生活,在書(shū)中尋求慰藉,仿佛什么事都與自己無(wú)關(guān),什么事都不是自己的事。海明威正是憑借“陌生化”的藝術(shù)手法,不斷滿(mǎn)足又不斷打破超越讀者的期待視野,引領(lǐng)讀者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奇妙的心靈之旅,從而獲得豐富的審美體驗(yàn)和審美愉悅。
三、讀者的參與和創(chuàng)造
在召喚結(jié)構(gòu)和期待視野之間,最重要最活躍的因素是人,因此,閱讀的出發(fā)點(diǎn)和歸宿點(diǎn)歸根結(jié)底都應(yīng)該是人,是讀者。從某種程度來(lái)說(shuō),讀者如同作者一樣創(chuàng)造了文本,沒(méi)有讀者就沒(méi)有文本。讀者絕不僅僅是被動(dòng)的接受,而應(yīng)該主動(dòng)參與和創(chuàng)造,是調(diào)動(dòng)各種經(jīng)驗(yàn),通過(guò)自己的想象去填補(bǔ)空白、連接空缺,這也是接受美學(xué)最基本的特征。只有這樣,作品才能不斷被豐富和充實(shí),展示其價(jià)值和生命。
縱觀古今中外的優(yōu)秀文學(xué)作品,往往都會(huì)引起不同時(shí)代的讀者不同的闡釋。而且,由于每個(gè)讀者的生活經(jīng)歷不同,他們閱讀作品時(shí)產(chǎn)生的情感也不同,文學(xué)闡釋意義也必然不同。“一部作品的潛在意義不會(huì)也不可能為某一時(shí)代的讀者所窮盡,只有在不斷發(fā)展的接受過(guò)程中才能逐步為讀者所發(fā)掘。”[1](P341)魯迅先生當(dāng)年評(píng)《紅樓夢(mèng)》時(shí)曾說(shuō)道:“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jīng)學(xué)家看見(jiàn)《易》,道學(xué)家看見(jiàn)淫,才子看見(jiàn)纏綿,革命家看見(jiàn)排滿(mǎn),流言家看見(jiàn)宮闈秘事……”。
對(duì)《雨中的貓》的解讀也是這樣。小說(shuō)描寫(xiě)的只是一個(gè)再簡(jiǎn)單不過(guò)的故事,但作者卻以簡(jiǎn)練的語(yǔ)言使讀者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閱讀,從而賦予這部作品各種不同的主題。有的認(rèn)為該小說(shuō)刻畫(huà)的是一個(gè)“孤獨(dú)無(wú)助的女人”形象。所以,如果把作品的標(biāo)題改為“一個(gè)寂寞的美國(guó)女人”雖直露了一點(diǎn),但卻更切題。也有觀點(diǎn)認(rèn)為,“死亡才是故事的主題。在故事里,它既是婚姻的死亡(夫妻關(guān)系不和),也是人類(lèi)友誼的死亡(夫妻與他人隔絕)和生命本身的死亡(戰(zhàn)爭(zhēng)紀(jì)念碑的象征意義)。”還有觀點(diǎn)認(rèn)為,《雨中的貓》反映了女性在男權(quán)社會(huì)中得不到尊重和關(guān)愛(ài),提出反抗,試圖尋找出路,這是“鞭撻男權(quán)思想,關(guān)注女性意識(shí)”的作品。甚至有人認(rèn)為小說(shuō)中充滿(mǎn)孩子氣的美國(guó)妻子是以海明威第一任妻子哈德莉?yàn)樵停闹蟹蚱揲g的隔閡與不理解暗示了海明威當(dāng)時(shí)對(duì)婚姻的無(wú)奈。正是這些不同的主題詮釋賦予了這篇故事無(wú)盡的內(nèi)涵,使得小說(shuō)始終散發(fā)著迷人的藝術(shù)風(fēng)采。
在這種意義上,文學(xué)作品就如美學(xué)大師姚斯說(shuō)的那樣,“一部文學(xué)作品,它不是一尊紀(jì)念碑,形而上學(xué)地展示其超時(shí)代的本質(zhì)。它更多的是像一部管弦樂(lè)譜,在其演奏中不斷獲得讀者新的反響,使文本從詞的物質(zhì)形態(tài)中解放出來(lái),成為一種當(dāng)代的存在。”[6](P26)
四、結(jié)語(yǔ)
接受美學(xué)是具有現(xiàn)代意識(shí)的一種理論,它指出了文本中召喚結(jié)構(gòu)和讀者期待視野的雙向互動(dòng)關(guān)系,強(qiáng)調(diào)了接受過(guò)程中讀者對(duì)文本的創(chuàng)造性解讀。本文以此為視角透視《雨中的貓》,并非忽略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作品本體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從新的角度,即以前一直被忽略的讀者這一角度,來(lái)重新審視作品。
海明威以點(diǎn)石成金的圣手,將一個(gè)簡(jiǎn)單的故事寫(xiě)得如此意蘊(yùn)豐富,耐人尋味,就像“一座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其在水下的“八分之七”的巨大隱晦部分,需要讀者加以無(wú)盡的解讀和體味,才能挖掘出作品精神價(jià)值與深遠(yuǎn)涵義。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這篇小說(shuō)確實(shí)是“越少,就越多”,這也正是《雨中的貓》的魅力之所在。
- 哈爾濱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英語(yǔ)專(zhuān)業(yè)學(xué)生筆語(yǔ)語(yǔ)塊特征的對(duì)比研究
——以部分高校大一至大三年級(jí)學(xué)生為例 - 《一個(gè)目擊者的故事》修辭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分析
- 我國(guó)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損害賠償制度探究
——以《商標(biāo)法》的修訂為切入 - 南京市金陵飯店微信營(yíng)銷(xiāo)策略研究
- 綠色交通視角下車(chē)輛類(lèi)型與交通擁堵關(guān)系研究
——以合肥市為例 - 漢字圖形化在標(biāo)志設(shè)計(jì)中的應(yīng)用研究
——以南京博物院標(biāo)志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