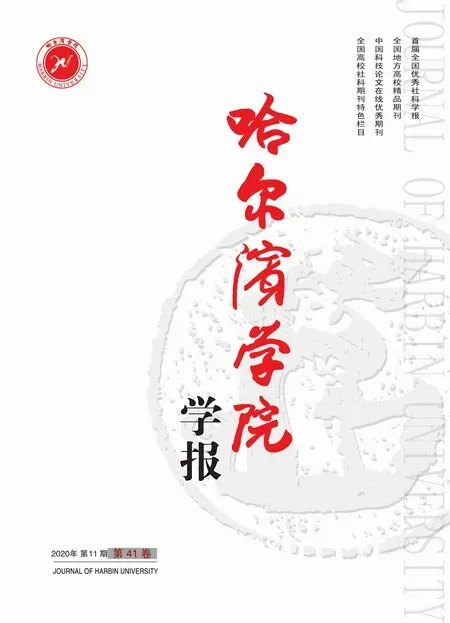《寄生蟲》的創傷性現代秩序隱喻
李金鳴
(黑龍江大學 文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韓國電影《寄生蟲》通過視覺符號和敘事策略,構建了一個攜帶了疾病與創傷的現代秩序主題,延續了自好萊塢影史之初就在探討的文明與秩序的命題。這部影片根植于韓國當下的社會現實,講述了一個關于欺騙和陰謀的故事,反映了貧富階層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沖突。但在更深的層面里還蘊含著一種關于現代文明與秩序的哲學反思,即金錢建立起的現代文明高度膨脹,將無法進入其秩序之內的群體擠壓至寄生狀態,而現代文明自身也充滿疾病和創傷,居于其中的個體在精神和情感關系上都變得脆弱。對比來看,游離在現代文明秩序之外的群體,他們雖沒有金錢的支撐,生活在城市的底層和邊緣,卻呈現出旺盛的生命力、粗糲但豐富的精神世界和親密的情感聯系。本文就《寄生蟲》的深層主題的表達方式進行探討,分析影片如何通過視覺符號和敘事策略構建這一隱喻性主題,以及本片如何延續和修正了好萊塢影史中的關于現代秩序的神話。
一、視覺符號與話語隱喻
視覺符號的運用是《寄生蟲》建立隱喻的第一步,克里斯蒂安·麥茨在《電影表意泛論》一書中闡釋了電影作為一種表意的符號系統與話語之間的異同。概括而言就是,話語在“形式”與“內容”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游離,語音符號與意義之間沒有天然的緊密聯系,因而時常出現“言不盡意”的情況;但電影的符號卻是形式與意義的天然統一體,視覺圖像與所指內容之間緊密相連。[1](P75)因此電影作為一種泛化的語言符號系統,在構建隱喻意義的層面上比純語言更依賴“語法”,也就是“影像化表達”,通過構圖、剪輯、攝像機運動等將各個視覺元素組合,產生深層意義的建構。電影《寄生蟲》就是“影像化表達”的佳作,在建立其深層的隱喻主題時,視覺符號的并置與并置方式作為“語法”,在具有隱喻意義的電影話語建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了具體分析《寄生蟲》中隱喻性電影話語的建構,我們選取影片中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視覺符號進行解析,這種視覺符號即經常被運用在別墅空間中的框形線條,其在影片中既作為象征現代性的意象,又作為結構人物關系的語法,達成了對攜帶疾病的現代秩序的隱喻。具體而言,影片中設計了三個主要空間:社長一家的別墅、別墅下的地下室、金基澤一家所居住的半地下室。“在差異空間下,社會底層民眾的日常生活被碎片化和等級化,而對這種空間分配普通民眾也只能被迫接受。”[2]兩處“地下室”空間意象的使用,展現了底層人生活空間的破碎、封閉,與“別墅”的意象形成強烈的對比,隱喻了微觀的權力滲透。別墅空間是現代秩序的寫照,不僅是因為別墅作為符號其本身所直接傳達出的金錢價值,更是因為導演在設計這一空間的時候采取了大量的平直流暢的框形線條,比如框形的走廊、平直的餐桌、低矮的方形沙發、層次整齊的儲物架,這一切線條使整個別墅空間成為了大小不一的框形的組合,給人以簡約、空曠、冷漠,但高度秩序化的視覺感。人類原始的、自然的、日常的視覺習慣是三維透視的,影片中被強化突出的框形線條則背離了三維透視的潛意識心理習慣,偏重對視覺圖像的二維提取,形成了一種反自然的、反日常的視覺效果,而這種效果就是現代性審美和感知的突出特性。
王才勇在《視覺現代性引導》一書中寫到:“(現代性感知的)這六種圖示不同程度地體現了對日常形式感知的離異。早期的平面化和抽象化指向的還是日常形式中的三維特性,即對這種特性的離異;后來的碎片化、動感化和超現實化則主要指向了現實形式的凝固性,即對靜止和固定形式的離異。”這里主要總結了現代性視覺審美的發展趨勢,即脫離日常的三維和靜止特性。導演奉俊昊將此特征應用于影片的空間設計中,通過對二維線條的強化營造了一種現代性的、秩序性的隱喻空間。其最為典型的一處空間設計是中間開有一道矩形門的儲物架,這道門漆黑深邃,平直的邊框線十分突出,它通向的是無人知曉的地下室,從這道門里走上來才能進入光明雅致的現代秩序中;同時,儲物架的結構是整齊分層的,橫向與縱向都被直線等分為相同的區域,上面的物件擺放有序且均衡,儲物架的背燈是暗調的、對稱的,這樣的視覺符號傳遞出高度的秩序感,達到了去情緒化的、距離感的空間構建,其直接反差于門后那個與地下室相連的過度空間,過度空間中也有一個儲物架,但上面凌亂不堪,沒有嚴正的分層,這個空間同地下室的意象一樣是反秩序的體現。
在影片中,線條不僅作為隱喻現代性的意象而存在,同時還作為結構人物關系,隱喻創傷的語法。具體而言,直線常被運用在人物關系的分割上,比如金基宇在社長夫人面前用偽造的學歷證明進行家教面試時,兩個人面對面坐著,其實際的空間是很近的,但導演采取了一條金屬門邊將兩人在視覺上分開,造成了人物心理上的距離感;社長家平直的餐桌總是將人和人的距離拉遠。這些線條將每個人物都劃分開區域,制造了人與人精神上的疏離隔閡,使觀眾意識到,在秩序井然的現代生活中人的情感關系是被割裂的,現代文明的高級感之下隱藏著對自然人性的破壞,這種損失就是高度的現代文明所攜帶的創傷。
二、古典敘事與主題隱喻
各種視覺符號的組合與運用使《寄生蟲》具備了表達現代秩序的詞組和句子,而主題的深化則更依賴于整體篇章的建立,即電影的敘事策略。敘事是古典主義電影的核心要素,路易斯·賈內梯在《認識電影》一書中總結了古典主義電影的風格:“古典主義電影通常避免極端的寫實或形式主義風格,而比較傾向于帶有一些表現風格,但影像的表面仍采取十分具有可信度的處理方法。”[3](P6)《寄生蟲》正是一部注重敘事的古典主義風格電影,既不過多偏重于紀實,也不十分傾向于形式,影片中的一切視覺符號都服務于敘事和幫助架構完整的篇章。電影中給出豐富的生活細節,使影片更具生活肌理,給虛構的故事融入了寫實感,帶來更加真實的觀影體驗,比如半地下室里那扇積滿灰塵的窗戶、掛在窗前晾曬的襪子、窮人與富人在飲食上的差異等,這些生活肌理給了整個影片濃郁的寫實氣息,使影片更好地完成了第一重關于貧富差距的現實批判主題的建構與對底層人生活境遇的書寫。
《寄生蟲》的第二重主題是關于創傷性的現代秩序的討論,這個主題在故事情節中得到了更系統的表達。首先,影片采取的是經典好萊塢的五部分敘事法,[4](P28)流暢地展開了故事情節:建置部分,貧困的一家人住在地下室,兒子金基宇通過朋友介紹和假造文憑進入社長家的別墅做家教;發展部分,窮人一家通過層層欺騙全部進入了社長家,成為了社長家的管家、司機和兩個孩子的家庭教師,并趁社長一家出游時肆意享樂;曲折部分,這里是反建置的部分,打開了一個新的必須處置的局面,也就是老管家藏在地下室里的丈夫被發現,窮人一家的陰謀也被老管家發現;高潮,生日會上的兇殺;尾聲,金基宇在地下室中幻想著未來能夠救贖父親。這五部分均以陰謀為核心展開敘事,分別是陰謀的誘發、進展、挫折、敗露和平息,而陰謀實際就是底層人試圖侵入上層秩序世界的計劃,陰謀的失敗也是反抗現代秩序的失敗,在現代文明的世界里階層的鴻溝是難以逾越的。
再者,與經典好萊塢敘事不同的地方在于,《寄生蟲》雖然是以陰謀為核心的犯罪類型片,但它并沒有設置正派與反派的較量,導演采取了一種中立的敘事態度,敘述中沒有加入前置的褒貶評判,只對人物進行客觀的呈現。在整體的情節敘事中可以看到,被騙受害的富人一家雖看似善良,但又隱藏著虛偽、冷漠、階層歧視,甚至是對毒品的渴望;實施陰謀的窮人一家看似利欲熏心,但還會為受到自己傷害的司機和管家感到歉疚不安,他們一家人相親相愛,充滿溫情。這種中立的敘事態度修正了好萊塢的正反派的情節設置,體現了韓國電影對社會問題一貫的思辨精神,也是韓國性與美國性在奉俊昊身上融合的體現。“未解決”式的結尾是對中立敘事的深化,其在奉俊昊的其他作品中都有體現,如《江漢怪物》《殺人回憶》等,這些影片的最后都使人重新思考,誰才是真正的怪物,以及誰才是真正的殺人兇手,而這些思考的答案往往指向時代與社會,真正的罪責并非只是在具體的個人身上。《寄生蟲》中的“未解決”式結尾也同樣起到了強化反思的效果,使觀眾意識到在現代秩序的勢力之下,窮人與富人都是秩序的寄生者,都在為資本所操縱,人性在秩序的規訓下變得薄弱無力。影片中別墅的主人多次易主,而作為現代秩序象征的別墅本身卻沒有發生過任何改變,這意味著現代文明是人類的宿主,寄居其中的人類已經失去了存在的主體性。
三、對秩序主題的繼承和修正
《寄生蟲》不僅是一部獨立的作品,更是作為關于現代秩序的進一步思考,存在于好萊塢歷時的電影譜系中。奉俊昊早年的好萊塢經歷使他深受好萊塢思維的影響,這部影片不僅在制作方法和敘事模式上吸取了好萊塢的經典范式,其主題更是從好萊塢關于現代秩序的思考中發展而來。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經典好萊塢時期,此時產生了四種好萊塢的經典類型片:西部片、黑幫片、偵探片、神經喜劇。西部片是好萊塢的第一種類型片,其中的“西部世界”是逃離現代秩序的烏托邦,牛仔作為反現代秩序的象征拒絕城市文明的馴化,向往回歸到充滿野性和生命力的自然世界。但隨著現代文明的不斷膨脹,城市空間愈發強勢地向人類生活中擴張,躲避現代秩序的烏托邦理想破碎,此時反思現代秩序的主題從西部電影走入了黑幫電影,失去了西部世界的牛仔轉化為城市中的黑幫分子,以對抗法律和道德的方式體現對現代秩序的反抗,城市在黑幫電影中呈現為黑色的意象,冰冷的街道、高聳的大樓、黑色的汽車等都在隱喻人類對城市空間的消極接受。進入偵探片以后,強大的現代秩序則以更加抽象化的形式展現,片中的謀殺和犯罪使原本的世界喪失表面的平衡,秩序化的世界受到破壞和挑戰,而偵探的推理不僅是緝拿兇手的過程,更是對罪的再分配過程,是將時代和社會之罪分配于個體之上,從而捍衛了秩序的力量。
在電影《寄生蟲》中,窮人一家是反秩序的代表者,他們的居住環境凌亂,沒有正經的工作,這都體現了他們拒絕進入社會的現存秩序之中。但出于欲望的驅使,一家人通過陰謀侵入了不屬于他們的上層空間,這里的“陰謀”相當于經典好萊塢電影中牛仔、黑幫和兇手的手槍,是試圖終結現存秩序的武器。然而強悍的現代秩序是個體所無法違抗的,“高處”作為電影視覺意象素來有象征權力的意味,同時也是脫離大地和自然的,“政治學中的權力具有高度統一性和一致性,在權力的組織和運行上講究有序性,也就是自上而下、等級制以及層級制”。[5]別墅是影片中唯一建筑在高處的空間,象征著現代秩序掌握著不可撼動的權力。而故事的最后,金基宇在地下室中幻想著通過努力拯救父親,這里回歸低處的情節表達了在現代秩序的勢力之下,窮人無自我救贖的可能性。影片中石頭的意象象征著窮人的欲望和計劃,而這塊石頭卻最終砸向了自己,成為自我毀滅的根源,這意味著現代秩序的違抗者最終走向自我毀滅的結局。石頭本是自然之物,人的欲望使其脫離自然狀態,成為了從上層秩序世界拋下來的誘餌,引起了窮人的欲望,又最終將其毀滅,一切平息之時石頭又被放回溪水之中,回歸了它的自然狀態,窮人也重新回到了地下室中。石頭作為隱喻的意象,傳達了在當下的時代中違抗秩序的個體是沒有自我救贖的希望的。這一隱喻也順應了經典好萊塢對現代秩序的最終維護和認可的態度,黑幫電影中的反秩序英雄幾乎都以死亡告終,偵探電影中的兇手也都難以逃脫,但《寄生蟲》的進展在于它的“未解決”式結尾將罪最終歸于了整個時代。影片在承認現代秩序不可動搖的同時,也揭露了秩序世界的腐化失衡的真相,以及現代秩序給自然人性帶來的創傷。
《寄生蟲》首先從視覺符號的使用與空間的建構理念上延續了經典好萊塢電影對城市意象的表達方式,即將抽象的現代秩序變為具體的視覺符號,構建出極簡化的、單一化的、去情緒化的秩序空間。同時《寄生蟲》的獨特性還在于,其呈現出了人為資本所馴化,人的自然情感聯系被秩序所割裂的狀態,由此隱喻現代秩序是一個腐化的、失衡的世界。其次,在關于現代秩序的敘事策略上,作為犯罪片的《寄生蟲》繼承了好萊塢的類型片敘事方法,延續了“無望的反抗”的故事模式,同時中立敘事的態度也使影片超越了好萊塢對現代秩序簡單認可的態度,將罪的分配從個人引向了時代和文明本身,表明了秩序之下的人性失常是現代文明的創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