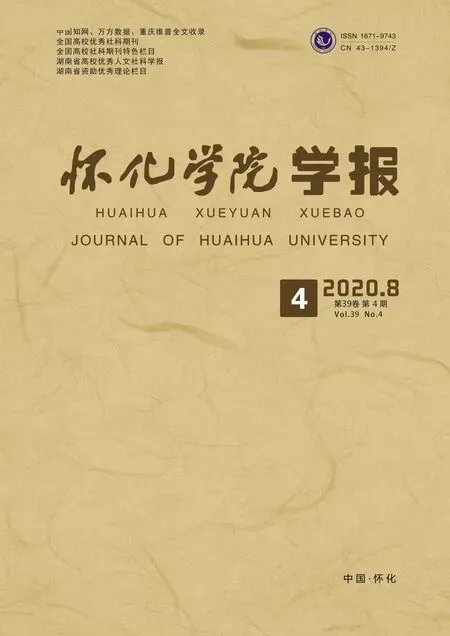消費語境下文學情感話語的癥候分析
左其福
(衡陽師范學院文學院, 湖南衡陽421002)
情感歷來是文學研究中不可忽視的理論問題和考察對象,也是我們認識和理解文學的性質、功能及其發展的重要線索。20 世紀80 至90 年代,隨著文學主體性理論的提出以及整個學界人文情懷的高漲,情感問題一度成為文學理論探索和文學批評實踐的著力點,甚至有學者以情感為主線,把握 “當代中國作家的特點,提出了中國新時期文學的主導發展脈絡”[1]序2。不過,這種對文學的觀察和思考不久便被資本、權力、市場、大眾傳媒等裹挾而來的更具時代特色的文學議題所覆蓋。如今,在日益強勁的全球性消費語境中,享樂主義主宰了文學的生產與消費,情感議題被拋到了文學的邊緣。但是,這決不是說情感被逐出了文學的領地,成為無足掛齒的殘存之物,更不意味著文學徹底告別了過去秉持的情感美學原則。在筆者看來,今天即便是那些對文學抱以純粹消費態度的讀者,也不太可能對無法滿足其情感需求的作品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換言之,在文學邁入消費時代的進程中,情感之于文學的意義并沒有改變,情感依然是我們觀察文學時代變遷的獨特窗口,我們有必要借助這扇窗口來窺探消費時代背景下文學的總體面貌與態勢,并且就其可能存在的問題與偏頗展開分析和診斷。
一、消費語境下文學情感話語的生產機制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從文學的立場來看,情感不只是某種內在的心理現象,更是外顯的言語活動,即情感話語。情感作為話語至少包括五個要素:一是情感話語的生產者,即作者;二是情感話語的接受者,也就是讀者或消費者;三是情感話語本身所包含的情感信息及編碼方式;四是情感話語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通過文學文本進行的情感溝通活動;五是情感話語所關聯的歷史文化語境。考慮到當今文學的產業化、商品化屬性,我們也可以將上述 “五要素” 稱之為文學情感話語的生產要素。只要對這些生產要素進行細致的梳理,我們便不難發現當今文學情感話語的生產機制和一般規律。
(一) “空心化” 的主體模式
主體一直被認為是文學情感話語的第一要素,主體不僅是文學情感話語的生產者,還是文學情感話語意義的創造者。在傳統主流的文學語境中,主體孕育了情感話語的生命,承載了情感話語的全部秘密。曹雪芹曾自述其創作《紅樓夢》 的緣起時說:“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2]7歌德晚年談到《少年維特之煩惱》 時也說:“我象鵜鶘一樣,是用自己的心血把那部作品哺育出來的。其中有大量的出自我自己心胸中的東西,大量的感情和思想……它簡直是一堆火箭彈!”[3]455正是這些作者- 主體的在場與出場,賦予了文學情感話語的真實性、現實的指向性以及傳播與接受過程的可詮釋性。同時也因為這些主體的在場,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才會突破時空限制在閱讀想象的空間尋找共情的力量。筆者以為,只要文學還有賴于人們的真誠感動,文學話語特別是情感話語就必須擁有一個確定而堅實的主體。
遺憾的是,這種標示了個體人生意蘊與時代印記的文學主體正在離我們而去,成為遙遠的記憶。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各種反傳統、反主體化思潮暗流涌動,主體之死、作者之死的聲浪不絕于耳。以今天的眼光看來,這些論調或許過于浮華夸張,甚至荒誕不經,但是這種修辭背后隱含的動機及其后果——將不可復制的體驗型的作者- 主體徹底改造成可以標準化生產的技能型的寫手- 工匠以適應迅速崛起的文學市場——不能不引起重視。
與過去的作者- 主體相比,寫手- 工匠的重大差異就在于自覺抽離了自我真實的情感體驗和人格內容,蛻變為羅蘭·巴特文本理論所描述的一個為語言的能指所裹挾的空心主體,或者說 “紙面的作者”(paper- author)[4]。如今大量充斥網絡空間和圖書市場的文學作品,尤其那些奔著消費目的而批量生產出來的暢銷作品就是有力的證明。即便是90 年代國內興起的所謂女性自傳體或半自傳體小說,對此也沒有多大的影響和改變。
(二) 市場的導向與制約
自文學進入消費市場以來,文學話語的權力已不可避免地由生產者讓渡給了消費者,文學被迫卷入從市場吸收潛在消費者的競爭性事務中,其根本的出發點不再是表征生產者自身念念不忘的精神困惑及其被壓抑的苦悶情緒,而是積極地構建文學消費者渴望得到的情感生活,最大化地與文學消費者的生活方式相適應,盡其所能地滿足大眾化的情感消費。
當前,以學生為主體的青少年群體構成了文學消費市場的絕對主體。就網絡文學來看:截至2019年底,中國網絡文學用戶為4.55 億,其中90 后、95 后、00 后已超用戶總量的70%。付費用戶中,三者之和超過用戶總量的66%[5]。在傳統的純文學領域,作為青少年的學生也是除專業人士外最主要的閱讀群體。以中國當代主流文學期刊《收獲》 為例,據統計[6]107,全日制學生閱讀該刊的比例達28%,專業人士僅為29.9%。在此情況下,不少文學期刊不得不調整一貫堅持的具有強烈啟蒙色彩的精英化思路,而以平等對話的姿態去擁抱雖歷練不足、涉世未深但極具青春氣息的年輕一代。 《收獲》 長篇小說專號(2010 春夏卷) 曾全文刊發郭敬明的20 余萬字的長篇小說《臨界·爵跡》, 《人民文學》 早在2007 年隆重推出 “青年作家專號”,發表了當時備受關注的80 后作家安意如、笛安、“打工詩人” 鄭小瓊等人的新作。
這些舉措盡管有辦刊者們主動發掘和培養文學新人之意,實際上是傳統文學市場衰落后被迫做出的反應。因此,當《收獲》 因發表郭敬明小說而引發了是否與其 “純文學定位” 不符的問題和爭議時,刊物執行主編回應說:“郭敬明多部小說銷量都已超過100 萬冊,是其他作家包括知名作家遙不可及的。郭敬明作品的吸引力在于切中了年輕讀者的脈搏,使年輕人在閱讀中得到了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7]由此可見,不論什么樣的文學刊物,主觀的自我定位最終難以戰勝客觀的文學市場,畢竟生存才是第一要務。
(三) 媒介化策略
現代社會媒介不僅僅是簡單的信息傳播工具,還是具備生成力、影響力和控制力的權力因素。特別是在消費時代,媒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滲透到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深刻地改變、重組了大眾的認知方式、思維方式乃至情感體驗方式。
隨著消費時代的來臨,我國居民消費已經呈現出由物質產品消費、精神產品消費轉向情感消費的發展趨勢。“消費既不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也不是交換價值,而是情感價值”,“人們消費的是‘夢想、影像和快感’,追求的是消費的激情和體驗,感情主義的表達異常強烈。”[8]350而在操縱情感生活、引導情感消費方面,大眾媒介無疑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有學者指出,大眾媒介既可以通過給商品和服務帖上情感 “標簽” 的方式引誘消費者,還可以通過多種媒介技術來強化情感,進而給消費者提供遠比現實情感更為緊張刺激的情感,即 “媒介化的情感”。媒介化的情感比現實情感更受歡迎,更具有傳播學意義,它們 “能夠有效地把象征性形象與人類情感和經驗聯系起來”[9]197,抹去觀眾與觀眾之間以及觀眾與媒介化現實之間的根本差異,實現情感在不同種族、代際、性別和社會階層之間的自由流通與傳播。
值得警惕的是,情感的媒介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彌散性效果,并不會增強觀眾對現實生活體驗的深度與廣度,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情感的生活基礎與現實內容,使之成為一種空洞化、形式化的“情感符號”。具體到文學領域,那便是情感話語的類型化、時尚化、淺俗化。
情感話語的類型化、時尚化、淺俗化是消費語境下文學生產的必然現象,也是文學走向市場、激發大眾消費潛能的基本策略。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通俗言情小說尤其是仙俠、玄幻、都市、校園類網絡言情小說,如《花千骨》 《太子妃升職記》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微微一笑很傾城》 《何以笙簫默》 等備受追捧,改編成影視作品后更是引起轟動效應,這些現象已經引起學界和文化管理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消費語境下文學情感話語的結構性缺陷
這里所說的文學情感話語結構不是前文分析過的文學情感話語要素的組合,而是指實際的文學生產活動中,不同情感話語的配置與分布,即文學情感話語的生態結構。它所要考察的是,在文學的整體格局中,哪些情感話語得到強化,哪些情感話語受到削弱,哪些情感話語發生了變異等等。文學情感話語的生態結構是文學情感話語的動態呈現,能夠真實地反映出文學的時代變遷與一個時期文學的總體風貌。
(一) 感傷話語的流行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感傷歷來是重要的文學主題,蘊含了創作者們體察個體生命與現實人生的復雜內容。感傷既可以表現為具體的身世之悲、家國之恨、功業之嘆,也可以表現為抽象的形上之思,如張若虛在《春江花月夜》 中對于人生有限、宇宙無窮的深沉思索。在現代文學中,感傷更是許多作家筆下基本的情緒底色。郁達夫的 “沉淪”、張愛玲的 “蒼涼”、沈從文的 “浪漫與溫情”、錢鐘書的“幽默” 以及魯迅筆下的 “吶喊與彷徨”,其情感范式都不是溫暖明媚的,而是令人感傷的。如果將感傷視為現代文學的一大特征,也許并不夸張。有學者指出,現代中國文學在 “革命” 和 “啟蒙” 兩大高亢雄壯的主調中,潛伏著一條低回感傷的抒情線索,只是現代中國文學的感傷并非西方現代文明衰落語境中的荒原式體驗,而是被壓抑在現代中國革命歷史進程中文人的 “痛苦” 與 “寂寞”,它源于感時憂國、獨立蒼茫的革命大我與荒涼孤絕的抒情小我之間的對立與糾纏。感傷既是現代中國革命歷史的產物,也是現代中國革命歷史的見證。“‘抒情’ 不是別的,就是一種‘有情’的歷史,就是文學,就是詩。”[10]65
與現代文學有所不同,從傷痕文學的 “血淚控訴” 到新寫實主義的 “煩惱人生”,當代文學的感傷恰恰是以放逐歷史、告別 “革命” 的姿態創造出來的,其精神意蘊已日漸消散。傷痕文學真正所要表現的并非歷史的傷痛,而是走出歷史的幸運;新寫實主義自然也不是簡單地訴說生活的煩惱,而是為后革命時代的凡俗人生進行辯護,它們用一種 “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 的平庸美學粉飾了同樣平庸的現實。隨著新寫實主義熱潮的消退,文學感傷在20 世紀90 年代的文壇難覓蹤跡,繼之而起的是王朔式的玩世不恭與嬉戲。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感傷卻在新世紀的文學消費語境中隆重登場,主角還是一撥稚氣未消、尚未脫離校園氣息的80 后文學青年。2001 年、2002 年,當不到20 歲的郭敬明兩次拿下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時,他沒有想到自己正在成為新世紀文學市場的寵兒,更不會想到流連于 “愛與痛的邊緣”、絮叨成長的孤獨和寂寞的憂傷敘述,很快成為頗受歡迎的青春寫作模式,并且在媒介與市場的合謀下成為文學的時尚。春樹、笛安、張悅然等都曾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這種時尚的代言人。青春文學由此實現華麗的轉身,被打造成 “金童玉女” 式的偶像派文學,“逐漸失去了當初的率真和非功利性,市場文學的特征越來越明顯”[11]341。如今,這些作者均已不再年輕,有的在文學市場上的影響力也日漸式微,但是由他(她) 們反復書寫的感傷體驗和 “無邊的輕愁” 已經成功融入了消費社會與都市生活的時尚文化,成為深受 “小資” 喜愛的流行符號。尤其在網絡文學敘事中,“小資” 式的感傷更是諸多唯美網絡愛情必備的美學元素[12]。
(二) 苦難話語的消解
苦難在日常語境中通常被理解為痛苦的經歷和磨難。對文學而言,苦難更多是指作家對于人生世界以及社會歷史的災難式體驗,比如自我人格的撕裂、人與社會的疏離、理想與現實的沖突、文明與野蠻的較量等等。文學中的苦難往往超越了個體的人生際遇,直指人類歷史與生活的本質。對作家而言,苦難猶如心靈之黑夜,蘊藏著尋找夢想與光明的堅韌力量。“惟心神的黑夜,才開出生命的廣闊,才通向精神的家園,才是要麻煩藝術去照亮的地方。”[13]118可見,苦難不是作家的心理負擔,而是寶貴的精神財富;苦難是一切偉大作家及其卓越創造的堅實基礎。
在傳統的文學語境中,苦難占據了文學情感表達的核心地位,同時也造就了文學輝煌的歷史。魯迅、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陀思妥也夫斯基、卡夫卡……這些已經被歷史銘刻的文學巨匠都是苦難的體驗者和書寫者,他們創造的文學世界本質上是苦難的世界,他們筆下的人物承載了不同民族、時代乃至整個人類對于苦難的最深沉的記憶。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學的歷史就是人類精神的苦難史,對人類苦難的書寫創造出了文學史上動人的篇章,并且在文學的歷史長河中標出了文學的高度。
從世界范圍來看,現實的創痛、歷史的災難以及文明的異化是人類苦難最深刻的根源,也是文學苦難書寫揭示出來的核心主題,哈姆萊特式的 “生存還是毀滅” 可以視為這類主題的典范形態。
中國文學是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文學對苦難的書寫既有世界性的一面,也有自身的獨特性。比較而言,中國文學更為重視人們的現實生存和歷史遭遇,較少關注人類精神層面的深層困境,它突出的是苦難的現實品格,而不是苦難的超驗形態。中國文學的苦難書寫根源于中華民族特有的歷史經驗與生存現實,體現的是中國文人觀照歷史、體察現實的憂患意識和救世情懷,“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便是這種意識和情懷的反映。近現代以來,中國文學的苦難書寫更是與中華民族的歷史滄桑和國家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是中國近現代民族國家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便是新時期以來直至20 世紀90 年代的中國文學也沒有根本性改變。有學者在考察這一階段的小說創作時指出:“在中國當代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我們無法逃離‘悲涼’的糾纏。現實與歷史、審美與啟蒙、傳統的羈絆與理性的向往……都把我們現實中的人拋入一種兩難境地,而難以獲得一種歷史的大歡喜,使那些最先意識到歷史的召喚和依稀聽到歷史未來聲音的人,感到蒼涼的苦難之情,新時期小說自始至今都貫穿著這一具有歷史性內容的情感。”[1]4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新世紀以來的消費浪潮正在遠離和消解除消費神話之外的宏大敘事,文學苦難書寫的使命意識、歷史擔當以及精神動力基本喪失。在消費文化背景下,苦難要么被邊緣化、碎片化,要么被作為生產要素整合到文學之中,成為文學消費的獨特景觀。新世紀以來,盡管文學對于苦難的書寫并未消失,尤其是在各種類型的現實主義小說中,苦難敘事從未缺席,但是苦難本身已經失去了歷史的深度和批判的力量,苦難的表面化、感官化傾向日趨明顯,苦難不再是歷史的總體性建構和民族的寓言,它更像是 “怨恨情緒的表達” 和“誠摯的自我傾訴”,苦難變成了 “無目的的反抗,被動的不滿,沒有結果的顛覆”[14]。換言之,苦難已經無法為當代文學提供有效的精神資源和本體性論證。
(三) 崇高美學與悲劇的衰落
崇高與悲劇是兩種不盡相同但又密切相關的審美形態。崇高主要是指對象以其粗獷博大、遒勁有力的感性形態給人帶來的心靈震撼以及精神境界的提升。“在審美體驗上,崇高往往給人以心靈的震撼,使人驚心動魄,心潮澎湃。在人生道路上,崇高總是給人以強烈的鼓舞,引人贊嘆,催人奮進。”[15]164悲劇則是 “在人生存在實踐中,由于人生與現實的矛盾而引起的沖突,以及在此沖突中人的力量、勇氣等情感的藝術表現”[15]176。在審美表現上,悲劇的情感體驗不是消極的悲傷和痛苦,而是超越于悲傷和痛苦之上的對于人生實踐和人類命運的深刻理解與感悟。崇高與悲劇的相關性在于,二者均肇始于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巨大沖突,都伴隨著由主客沖突而來的強烈的情感體驗,最后又都在情感體驗中獲得主體的升華與重塑。從本質上講,崇高與悲劇是力與美的結合,是主體在人生實踐的困境中努力發現自我、肯定自我并且不斷超越自我的情感表現,簡言之,是人性光輝的顯現和人的本質力量的確證。
文學是人學,文學在謳歌人性、贊美人情以及描繪人的理想化生存方面負有神圣的使命,這種使命決定了文學不可能無視崇高與悲劇。在文學的發生與發展歷程中,崇高與悲劇始終與文學相伴隨。從遠古時代的神話史詩到近現代的小說戲劇,崇高與悲劇從來都是共生共存、相互激蕩的,它們一方面展現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悲劇性沖突,另一方面又在悲劇性沖突中張揚了人性的崇高與壯美。在表現人性的深度與廣度上,崇高與悲劇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有美學家認為,悲劇是“文藝的最高峰”,悲劇既演出了人類的絕望、痛苦和悲傷,同時又讓我們看到了悲劇人物對生命意志的崇高放棄[16]350-351。王國維在《人間詞話》 中指出,有無崇高的悲劇情懷是衡量一部作品境界高低的重要標志。
當然,崇高與悲劇在文學中的表現不盡相同,本身也具有多樣性。尤其是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它們各自反映的現實內容和價值指向會有很大的差異。但是不管怎樣,文學對崇高與悲劇的美學追求,都是以對作為 “主體” 的人以及人的本質屬性的堅強捍衛為基本前提的,體現的是人對于自由與責任、價值與尊嚴、有限與無限等終極問題的嚴肅關切。而正是對這些問題的關切,文學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彰顯了文學自身的磅礴力量和寬廣精神,文學的道德意識、宗教意識以及哲學意蘊由此得到充分的顯現。
從審美層面來看,消費語境下的文學往往缺乏氣勢恢宏的力量感、崇高感及悲劇意味,文學難以震撼人的靈魂,引發人的思考。究其根源,崇高與悲劇賴以存在的 “主體” 形象及其超越意識的缺失是問題的根本。20 世紀90 年代以來,文學主體在商業化洪流的沖擊下土崩瓦解,主體意識、抗爭意識不復存在,市場意識、競爭意識、生存意識空前突顯,現實原則、合理性思維壓倒一切。與此相應,文學不再提出嚴肅的公共議題、回應時代的重大關切、并且直面人類的生存困境,而是以 “躲避崇高” 或者 “日常生活審美化” 的姿態迎接 “小時代” 的到來。因此,文學變得越來越輕靈、越來越精致、越來越重視趣味性和審美性。但是,文學也因此失去了自身的高貴與神圣,變得越來越不重要。
三、消費語境下文學情感話語的價值迷誤
文學活動是一種情感活動,也是一種價值活動。這不僅表現在文學情感本身就具有價值,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文學價值往往蘊含在文學的情感體驗和情感評價之中,需要通過文學的情感審美來實現。就此而言,消費時代背景下文學情感話語生產機制的變化以及文學情感話語生態的結構性調整,直接影響了文學價值的選擇與走向。
(一) 個體認同的強化與民族國家意識的消退
個體化原則是文學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也是文學從古典走向現代、從自發走向自覺的鮮明標志。如果拋開對個體自我意識以及個人情感的書寫與肯定,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或許不會發生,文學的多樣化發展更是無從談起。事實上,中國現代文學正是在個人主義的思想背景下拉開了序幕,“個人” 的發現往往被視為 “五四” 新文學的一項重要成就。20 世紀30 年代,郁達夫在剖析現代散文的發展狀況時指出,“五四運動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見。……現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現的個性,比從前的任何散文都來得強”[17]205-206。他高度肯定了現代作家在創作中將自己的性格嗜好、思想信仰、生活習慣表現出來,認為活潑有力的個性表現對文學來說是最可貴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首先是反傳統、反封建的啟蒙主義思想的重要體現,其根本任務是將個人從傳統的禁錮中釋放出來,實現人的自我解放。現代啟蒙主義知識分子認為,個體的解放是改造舊社會、建設新型民族國家的基本前提。正如魯迅所言:“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18]58因此,現代文學對個體的書寫與認同,不只是一種新的文學觀念的宣示,還是一種新的民族觀、國家觀乃至世界觀的清晰呈現。正是基于這一自覺的歷史意識,中國現代文學形成了歐洲某些學者所描述的 “抒情” 與 “史詩” 互為糾纏、辯證結合的獨特面貌:它既有中國傳統文人文學對個人主觀情緒和感受的高度關注,又有西方現實主義文學對社會生活、階級結構等的客觀再現[19]序言2-3。當然,如何在創作實踐中實現 “抒情” 與 “史詩” 的有機融合是一個有待深入討論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二者所形成的張力結構在現代主流作家那里得到了生動的體現,魯迅、郁達夫、茅盾等都是經典的案例。
遺憾的是,“抒情” 與 “史詩” 的二元結構并沒有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得到很好的延續,其內在的平衡已被打破。首先是建國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對革命歷史與現實成就的激情書寫抑制了文藝個性和作家的主體性訴求,個人抒情顯得不合時宜,其合法性受到質疑。20 世紀80 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重新肯定了人以及人的主體性在文學中的地位,開啟了文學抒情的新時代,文學的個人話語和個人化寫作漸成氣候。但是,80 年代的個人化寫作是文學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尋找自身規律并試圖確定自身獨立價值的實踐和探索,并沒有承接五四新文學的啟蒙精神和歷史情懷,反而表現出回避歷史、逃離現實的審美傾向。這一時期文學的 “抒情” 美學不斷強化,“史詩” 意識逐漸隱退,“抒情” 與 “史詩” 再次被割裂開來。
80 年代 “抒情” 與 “史詩” 的分離,意味著文學放棄了干預現實和參與現代民族國家歷史進程的意愿與能力,這在客觀上又造成了90 年代文學邊緣化的局面。進入90 年代,面對市場、傳媒以及消費文化的多重沖擊,文學在失去轟動效應之后似乎迷失了方向,要么 “龜縮于個體精神的小天地,尋找終極關懷”[20]194,要么打出個性化旗號來獲取商業性的成功[21]25,但無論是個人理想主義還是現實功利主義都未能改變文學的根本困境。新世紀以來,隨著文化產業化步伐的加速以及大眾消費文化的壯大,文學理想主義黯然退場,功利主義高歌猛進,文學的個體書寫越來越表面化、程式化。至此,文學失去的不只是寬廣的歷史視野,還有創作者自我的真實呈現。文學似乎變成了集體的假面舞會,為讀者提供短暫而虛幻的自我感覺與身份認同。
(二) 快感至上與消費意識形態的建構
文學可以表現快樂,也能夠給人帶來快樂。追求快樂是文學作為審美活動的應有之義,無須特別指出。不過,在傳統的文學語境中,文學與快樂又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話題,其爭議的焦點最終指向文學的價值與功能。
柏拉圖在《理想國》 卷十中談論詩歌與哲學的古老爭議時,曾借蘇格拉底之口說,詩人以及詩歌的擁護者們要想確立詩歌的合法地位,必須向世人證明,“詩歌不僅令人娛悅,而且有益于有序的管理和全部人生。……詩歌不僅帶來快樂,而且帶來利益”[22]631。古羅馬詩人賀拉斯則明確指出,“詩人的愿望應該是給人益處和樂趣,他寫的東西應該給人以快感,同時對生活有幫助。……寓教于樂,既勸諭讀者,又使他喜愛,才能符合眾望”[23]108。一般說來,“寓教于樂” 代表了傳統主流的文學觀念,但是這種觀念所要捍衛的并非文學的快感,而是借由快感所欲實現的道德效用和社會功能。快感經驗僅僅作為文學的一種工具性要素而存在,不可能居于文學價值的中心。這種狀況直到19 世紀依然沒有改變。
20 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后現代思潮和大眾文化的崛起,快感不僅被視為現代工具理性的對抗性力量在認識論層面受到重視和肯定,而且一躍成為經濟增長和文化消費的重要推力,得到資本世界的空前利用與開發。“與此相應,‘快感’正在取代‘情感’,成為文學藝術、審美活動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概念。”[24]104法國文論家羅蘭·巴特曾公開使用“享樂” 這一純粹感官性詞匯來描述文學閱讀的經驗,美國作家、藝術評論家蘇珊·桑塔格更是大膽地主張用藝術的肉欲來代替藝術的解釋。如今,被譽為 “世界四大文化現象” 之一的網絡文學早已打上“爽文” 的標簽廣為傳播,并且以其特有的爽感機制重塑了年輕一代的閱讀體驗。正如有學者在考察動漫、電子游戲等 “御宅文化” 時所指出的那樣,“御宅族感性的核心,是由‘即使知道是騙人的,還是可以真心被感動’的距離感所支撐的”[25]105。顯然,快感已經擺脫了來自于道德教化以及社會倫理的束縛,進而演化為一種獨立的美感形態。
總體上看,消費語境下的文學情感話語迎合了大眾傳媒和消費文化的旨趣,其目的不是打動人,而是娛樂人。快感決定一切成為重要的美學原則。但這并不利于文學的健康發展,其消極影響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學情感的真實性原則受到挑戰,二是文學情感的價值被不斷損耗。在大眾消費意識形態和快感美學的驅動下,快適度而非真實性已經成為文學情感話語優先考慮的問題,情感的商品化、技術化、代理化不只是影視傳媒、商業廣告、網絡游戲等特殊行業內的消費現象,也是包括文學在內的整個文藝領域廣泛存在的審美現象。有社會學家將此命名為 “后情感主義”,“‘后情感主義是一種情感操縱,是指情感被自我和他者操縱成為柔和的、機械性的、大量生產的然而又是壓抑性的快適倫理’……它追求的不再是美、審美、本真、純粹等情感主義時代的‘倫理’,而是強調日常生活的快樂與舒適”[26]。就文學而言,這種現象是嚴重的短視,它不僅混淆了文學與一般大眾文化產品的區別,漠視了讀者對于文學作為精神產品的美好期待,而且隨著情感真實性原則的消解,文學的感染力、共情力,或者說能夠使文學得以持久流傳下去的情感魅力也將難以復現。
四、結語
2015 年9 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為當前以及今后我國的文藝工作指明了方向。會議指出,當前文藝領域存在著價值扭曲、浮躁粗俗、娛樂至上、唯市場化等突出問題,強調文藝必須發揮自身在引領時代風氣、鑄造民族精神、傳播中國價值、凝聚中國力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自覺承擔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神圣職責。
文學是情感的表達,同時也是特殊的情感教育。情感是文學感染人、塑造人并且發揮各種社會功能的關鍵要素,文學功能的實現離不開情感話語的引導和激勵。基于此,對消費語境下的文學情感話語進行批判性審視,一方面是對我國文藝政策的積極響應,是努力克服當前文藝創作中的不良傾向、促進文學健康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激發文學的情感力和感染力,傳播文學的正能量,推動當今文學參與我國的文化建設,充分發揮文學的文化戰略功能。
然而上述研究表明,當今文學情感話語的生產恰恰是不盡如人意的,文學情感話語本身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根本癥結在于消費文化的侵蝕和主體意識的潰散,主體之魅、情感之魅不復存在。在此背景下,文學要想真正實現自身的社會文化功能,肩負起歷史賦予的神圣使命,首要的任務是必須抵御消費市場的誘惑,重建文學的主體性;其次,恢復文學與歷史語境、民族文化以及社會主流價值的緊密聯系,重建文學情感話語的 “宏大敘事”;最后,深入考察人類情感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積極探索文學情感的審美表達,避免文學的情感話語與大眾媒介的情感話語同質化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