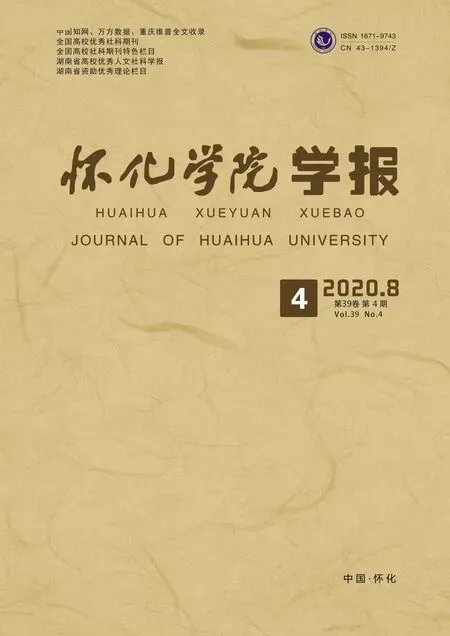從曾侯鐘銘 “申固楚成,改復曾疆” 談曾楚關系
李愛民
(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海南海口571158)
一、引言
2009 年為配合 “隨州東城區文峰塔還建小區” 的工程建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搶救性發掘了兩座春秋墓葬(M1、M2)。其中M1出土的銅器銘文中有 “曾侯與” 之名,結合墓葬規模,可以判定M1 的墓主即為曾侯與。M1 所發掘出土的遺物中,有8 件甬鐘,其中M1:1 鐘形體完整,在鐘體正背面的鉦部以及左右鼓上鑄有銘文169 字(合文1、重文1)[1]3-50。鐘銘內容與公元前506 年 “吳師入郢,楚王避難于隨” 的歷史事件有關,可補史載之闕,對于研究當時的歷史及相關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為了后面討論的方便,現將鐘銘全文移寫于下(釋文用寬式):
惟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伯適上庸,左右文武,達殷之命,撫定天下。王遣命南公,營宅汭土,君此淮夷,臨有江夏。周室之既卑,吾用燮謞楚。吳恃有眾庶,行亂,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荊邦既削,而天命將虞。有嚴曾侯,業業厥圣,親薄武功,楚命是靖,復定楚王,曾侯之靈。穆穆曾侯,莊武畏忌,恭寅齋盟,伐武之表,懷燮四方。余申固楚成,改復曾疆。擇辝吉金,自作宗彝,龢鐘鳴皇,用孝[以]享于辝皇祖,以[祈]眉壽,大命之長,其純德降,余萬世是尚。
鐘銘一經公布即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許多學者對鐘銘的一些字詞和斷句進行了新的考釋和釋讀[2]68-69,[3]74-75,[4,5],[6]118-120,加深了人們對鐘銘內容的理
解。鐘銘 “申固楚成,改復曾疆” 位于鐘背左鼓上,此句銘文亦出現于M1:2 鐘背左鼓上。鐘M1:2 出土時背面左右鼓部殘缺損失,其左鼓部分有幸被北京某收藏家收藏,曹錦炎先生2013 年已做過介紹,凡國棟先生在對鐘銘進行柬釋時已作合璧①。
關于此句銘文的意義,凡國棟先生認為大意是說曾與楚達成和解,同盟關系進一步鞏固,并重新光復了曾國的疆土[7]64。我們基本上同意凡國棟先生關于此句銘文意義的解釋,擬在其基礎上對其補說一二,并對學界討論熱烈的曾隨問題談一點自己不成熟的想法。
二、“曾隨之謎” 補說
關于曾隨問題,自20 世紀70 年代李學勤先生提出 “曾隨之謎” 的論題后,有關曾國族屬以及曾、隨是否一國的討論就一直沒有間斷過,尤其是近年來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以及隨州文峰塔春秋曾侯墓地的發現和發掘,使這一問題的討論更加熱烈[8]124-127,[9]58-66。討論分歧的焦點主要是西周早期曾國的地望、族屬以及與春秋戰國時期曾國的關系。至于西周晚期至戰國中期的曾為姬姓的問題,學界意見現已比較統一,矛盾主要在曾隨是否一國的問題上。目前雖然在此問題上仍有分歧,但大部分學者已傾向于春秋戰國時的曾隨一國之說,我們亦贊同春秋戰國時期曾即隨的意見,后面的相關討論即是以此為基礎的。
關于曾隨一國二名的問題,何浩先生認為曾應為國名,隨為曾都:
《左傳》 莊公四年載:“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 (武) 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 就文義分析,“以伐隨” 之 “隨” 為泛稱,指國名;“營軍臨隨”,其意當為 “楚師逼近隨都構筑營壘”。正如泛稱的 “成”、“許” 是國名,“衛師 入 成” 之 “成” 及 “鄭 伯 入 許” 之 “許” 是 特 指成、許都城那樣,此 “營軍臨隨” 之 “隨”,所指也應該是曾國的都城。很有可能,曾為國名,隨為曾都,因而又稱其國為隨。就象州國都于淳于又稱淳于、魏國都于大梁又稱梁、韓國都于新鄭又稱鄭一樣,曾——隨也是一國二名[10]288-289。
近年董珊先生對如何解釋 “曾” 又稱 “隨” 的問題時,亦有相似的觀點:
我認為 “隨” 是曾國都,國都名 “隨” 逐漸取代舊國名 “曾”,導致今天傳世文獻只見后起的新國名 “隨”。其國都名稱的演變為邦國名稱的過程,猶如戰國之魏遷都于大梁,邦國名就稱為 “梁”,新的邦國名稱 “梁” 雖因秦統一而一度中斷,但到了西漢初,又在戰國魏故地封建梁國,是對戰國時代新興的國名 “梁” 的延續。最近新發現春秋中晚期的楚王為 “隨仲羋加” 作鼎,以及新蔡簡所見的 “隨侯” (甲三:25),即是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楚國已開始稱姬姓曾國為 “隨”,這個新興名稱 “隨” 被戰國早、中期成書的《左傳》 《國語》 等傳世文獻繼承,舊名稱 “曾” 隨著此時曾國的衰亡,就湮沒不顯了[11]157。
二者都認為 “隨” 乃曾的國都之名,這應當是正確的。現在二者的基礎上對 “隨” 何以為國都名再略做補充。
《左傳·桓公六年》 載 “楚武王侵隨”,斗伯比言于楚子曰:“漢東之國,隨為大。” 關于此句中的“國” 之訓釋,杜注、孔疏均無說,亦未見后世訓釋之詞,大概是認為此句意義明了,無須申說。不過我們認為 “國” 字于此似不宜訓為形而上的 “國家” 義,訓為具體意義的 “國都” 也許更切合實際,斗伯比之言當是以國都之大小來指說國家之強弱。“國” 字《左傳》 習見,除作為人名用字及和其他字組合成專名外,其單獨使用時,除了訓義為 “國家” 之外,表示國都、都城亦是其常見之義。如《左傳·隱公元年》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大都,不過叁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都” 指都城,“國” 亦是都城,但專指天子、諸侯所居之國都,國大都小乃是常制,祭仲之言以國、都對比,則此處之 “國” 乃表示 “國都” 之義十分明顯。 《左傳·閔公二年》 有:“大都耦國”,亦是國、都并舉,則 “國” 亦指 “國都”。又《左傳·僖公三十二年》 中杞子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此 “國” 當指鄭之國都。不僅《左傳》 之中,在先秦秦漢的其他典籍中 “國” 訓為 “都城” 都是其常見之義,如《孟子·萬章下》 :“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趙岐注曰:“在國謂都邑也。” 《史記·周本紀》 :“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 張守節《正義》曰:“謂至朝歌。” 此處之 “國” 與 “郊” 對舉,其表示 “國都” 之義亦十分明顯。因為從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的正統觀念來看,周在滅商之前亦屬于商王國,故此句 “武王至商國” 即指武王的軍隊到達商都朝歌。
“隨” 為國都之名,在字形上亦有反映。“隨” 字隨仲嬭加鼎作 “”[12]68,隨大司馬戈作 “”[13]彩版七。新蔡簡甲三·25 “隨侯” 作 “”[14]圖版七九甲,清華簡《系年》 簡83、84 “昭王歸隨” 作 “”[15]81。以上所舉明確用作國名的 “隨” 字之形體,除新蔡簡外的其他各字都增加義符 “邑”,說明其字當與國名、地名有關[12]68-69。所以,“隨” 為地名應該沒什么問題,因地名而為國都名,進而因國都名而為國名,這可能即是 “曾” 又稱 “隨” 的原因所在,而且這種現象在先秦諸侯國的稱謂中亦是不乏其例。
所以,曾、隨一國二名,“隨” 為曾國國都之名應該是能夠成立的。而曾侯與鐘銘 “申固楚成,改復曾疆” 則為我們提供了關于曾(隨) 幫助楚昭王返邦復國的新的歷史史實,這對于研究探討相關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三、曾國的分封及疆域流變
20 世紀以來,在如今的隨棗走廊一帶不斷有曾國青銅器出土,其分布的大致范圍包括漳河上游地區、滾水中上游地區、涢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區這一三角形地帶[16]337。其中,漳河上游地區以京山蘇家垅銅器群為代表,年代主要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17];滾水中上游地區以棗陽郭家廟銅器群為代表[18,19],年代大致為兩周之際;涢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區則以隨州擂鼓墩和義地崗墓地為代表②,除卻葉家山西周早期墓地暫不討論外,墓地年代主要從春秋中期開始到戰國中期。三個地區曾國的銅器在年代上呈現一種前后序列的關系,正如張昌平先生所說:“春秋早期之后,漳河流域、滾水流域都未再見與曾國相關的遺存。”[16]338結合文獻記載所反映的當時歷史形勢來看,張先生的論斷很可能是正確的,說明春秋早期之后曾(隨) 的勢力逐漸退出了這兩個地區,這和當時楚國的四面征伐,勢力東擴的形勢相呼應。
我們知道,楚于周為異姓方國,楚之先祖在周初雖曾輔佐過周王,然在周初分封時卻只以子男的身份封于南土楚蠻的丹陽一隅,開國之初的國力是非常弱小的。所以在楚國的早期歷史上,除了熊渠時期曾 “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 之外,楚基本上是處于偏居一隅、蓄勢待發的狀態之中,勢力不出江漢之間。然至楚武王之時,周失其序,平王東遷,政出諸侯,此時的楚國經過幾代楚王的努力而國力大增,加上諸侯侵伐日繁,楚國亦開始于更大范圍內進行征伐,開土拓疆。 《左傳·桓公二年》載:“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這是中原姬姓諸侯患楚的開始。就現有文獻所載,楚始侵伐周之姬姓封國是從魯桓公六年(公元前706 年) “楚武王侵隨” 開始的,此乃春秋時期楚國對外侵伐的重要一步。曾(隨) 作為姬周同姓之國,是周王在南土江漢地區的王室代表,如按有的學者對于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族屬以及其與東周曾國關系的論斷[20]50-55,[21]41-45,則曾國在西周早期即已分封,并且是西周早中期周王南征的重要據點③。然而,隨著昭王南征而不返的失利,曾國的政治中心也可能發生了轉移。由于西周中后期曾國墓地還未發現,暫無法考論,而自兩周之際至戰國中期時段的曾國遺址則有相當完整的時間序列。張昌平先生通過對這一時段曾國中心政治區域的考察,認為曾國在此期間進行了兩次遷都,兩周之際位于滾水流域的吳店東趙湖一帶,其后遷至今安居一帶,至春秋晚期左右再遷至今隨州城區一帶[16]341-344。方勤先生在對曾國歷史進行考古學觀察時,把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一同考慮的同時,亦認為曾國都城不止一處,前后至少經過兩次遷徙,共有三處都城[22]109-115。二者都認為棗陽郭家廟一帶在兩周之際為曾國國都所在地,這亦和發掘者的意見一致[18]322-324。結合郭家廟和曹門灣墓區出土的大量兵器、車馬器的情況來看,此地在當時不僅僅是曾國的政治中心,更是一個重要的戰略據點,這可能就是曾國遷都于此的原因之一,目的可能就是為了監視楚國。而且結合京山蘇家垅銅器群的等級來看,此地亦當是兩周之際至春秋早期曾國在漳河流域的一個重要據點,正好和棗陽郭家廟分據大洪山南北,扼據隨棗走廊南北出入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然而此兩地于春秋早期之后未再見與曾國相關的遺存,結合文獻記載可知大概在春秋早期晚段楚國勢力已經進入這兩個地域。桓公六年(公元前706 年) “楚武王侵隨”,結果是 “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說明此時隨的勢力仍然很強。此次侵伐,楚軍 “瑕” 地,關于 “瑕” 的地望,待考④。兩年后的桓公八年(公元前704年) “楚子會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速杞,位于今湖北應山縣治西[23]122。“漢淮之間” 具體所指不明,但當離速杞不遠,在其附近一帶,說明此時的漳河流域及涢水下游一帶可能已在楚的勢力范圍之內。又莊公四年(公元前690 年) 楚武王伐隨,“除道梁溠,營軍臨隨”,此乃從北線征伐隨國,但從 “除道梁溠”“請為會于漢汭” 及 “濟漢而后發喪” 的窘迫情況來看,此次征伐相當艱險,楚國勢力雖然可能已涉入滾水流域,但此時當尚未占有漢東之地。不過此后不久隨著楚國對外征伐的進一步開展,楚國的勢力則逐漸深入這一區域[24]91-93。其后楚對隨國屢有征伐,隨的疆域亦逐漸萎縮,到春秋晚期以后大致僅保有涢水中游的均川以及隨州一帶較小的區域了[16]331-341。
四、“申固楚成,改復曾疆” 的內涵與曾楚關系
《左傳》 中共記載了四次楚對隨國的侵伐,雖未滅隨,但隨國則逐漸成為楚之附庸,并世有盟誓。公元前506 年吳師入郢時,昭王奔隨,隨人幫助昭王復國定邦,這與曾侯與編鐘銘文 “楚命是靖,復定楚王” 的記載相一致,對于我們了解 “吳師入郢” 的這段歷史具有重要的意義。 《左傳·定公四年》 在記載昭王奔隨之事時,最后只以 “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簡而言之,至于盟誓之內容則并未言及,其他文獻亦未見記載,以致我們無從得知其詳。然而鐘銘則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一些信息,讓我們可以從中一窺當時曾(隨) 楚盟誓內容之一二。鐘銘 “申固楚成,改復曾疆” 當是曾(隨) 幫助昭王的一種獎賞。“申固楚成” 說明重新鞏固了與楚國之間舊有的盟約關系,但是曾侯與鑄造此編鐘的原因最主要的可能是 “改復曾疆” 了。鞏固世代舊有的盟約固然值得稱揚,但能夠恢復舊有的疆土則更是值得大肆宣揚的功績,故曾侯與才作宗彝,置之宗廟。這些在文獻中卻沒有記載。雖然鐘銘提到恢復曾國疆土的事,卻并未說明具體內容,我們仍然不知道其具體恢復了哪些疆土。
然而結合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我們或許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對 “改復曾疆” 的具體內容探討一二。
首先,從 “西陽” 地望來看 “改復曾疆” 的內容。自宋代以來,有關曾國的出土資料不斷發現,宋代安陸出土的兩件楚王酓章鐘[25]27以及1978 年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楚王酓章镈[26]13,乃楚王為曾侯乙所作之器。銘文中有一地名 “西陽”,關于其地望,諸家多有分歧。吳良寶先生在考證天星觀楚簡“西陽君” 封地之地望時,結合諸家關于鐘镈銘文中“西陽” 地望的討論,認為:“曾國首都在西陽,即今湖北隨州的可能性非常大,與在今河南光山縣西南的楚國‘西陽’并非一地。天星觀楚簡‘西陽君’ 的封地應是后者。”[27]125-126吳良寶先生所論當是,但其認為 “西陽” 在今湖北隨州似可商榷。我們已在前文討論了曾國的國都為 “隨”,其地望當在今隨州市區一帶。然而由酓章镈銘可知 “西陽” 亦為曾都所在地,如其地望誠如吳良寶先生所說在今湖北隨州,這和我們所說的 “隨” 都地望一致,作為曾國都城而稱謂歧異,似有矛盾,除非二者為前后相承的關系。但是在傳世文獻中今隨州一帶未見有 “西陽” 之地名,而 “隨” 作為地名自先秦以來幾未中斷過。因此,“西陽” 之地當不在今隨州一帶,應另覓他處。由上文可知,今棗陽郭家廟一帶在兩周之際曾做過曾國國都,既然 “西陽” 不在隨州,是否在棗陽郭家廟一帶呢?如果是的話,則說明楚國在報答曾(隨) 的幫助時大概歸還了曾(隨) 在滾水流域的疆地,但是此推斷目前缺乏堅實的證據,而且和宋代酓章鐘的出土地安陸相距甚遠,這和一些學者所主張的 “西陽” 地望 “或不出今隨州、安陸間”[28]60的觀點矛盾,故 “西陽” 又似不在此地。不過 “西陽” 作為曾國先君宗廟所在地,似亦可作另一種理解,即 “西陽” 并非曾國國都,而只是曾國宗廟所在地,即曾國宗邑,猶春秋時曲沃之于晉、亳(薄) 之于宋的情況一樣。作如此理解的話,“西陽” 乃僅是曾國宗廟所在地,地望雖然仍不可確知,但可能離其國都 “隨” 并不遠,對其地望我們可根據考古發掘資料稍做推斷。石泉先生曾結合文獻記載論證曾(隨) 國的都城在今安居一帶[28]63-64。1984年,武漢大學荊楚史地與考古研究室對位于隨州市西十六公里的安居遺址進行了初步的考古調查。從采集到的遺物來看,此遺址的時代上限不晚于兩周之際,是一處貫穿整個東周和兩漢的遺址,而且在遺址內發現有建筑基址,調查者認為此處應是一處古代城邑遺址[29]5-6。安居遺址正處于溠水東岸,涢水北岸,和古人以水北為陽的情況相符,所以作為曾(隨) 國宗邑而稱之為 “西陽” 是很適合的。正因為它是曾(隨) 國宗廟所在地,所以莊公四年(公元前690 年) 楚武王伐曾(隨) 時 “除道梁溠,營軍臨隨”,渡過溠水后不但臨軍隨都,而且更是直逼曾(隨) 宗邑,故才令 “隨人懼,行成”。所以,如果以上推斷不誤的話,隨州西部的安居遺址可能就是曾(隨) 之 “西陽”,但這不是學者們所說的曾(隨) 國都,而是曾(隨) 國宗廟所在地。
其次,從楚國封君地域分布上來看 “改復曾疆” 的內容。楚國的封君制始于春秋戰國時期的楚惠王早期,而且封君的封邑基本上都處于開發較早、條件較好的地區[30]73。隨棗走廊乃中原進入江漢地區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然而從整個楚國封君封邑的分布上來看,隨棗走廊一帶未見有楚國的封君封邑⑤,這極有可能和曾(隨) 幫助昭王復國、曾(隨) 楚世有盟誓有關。曾(隨) 雖然在被楚國多次征伐后逐漸淪為楚國的附庸,但在 “吳師入郢” 事件之后曾(隨) 楚之間的關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從楚王熊酓鐘、曾姬無恤壺銘文我們可以知道,楚王不但為曾(隨) 侯作宗彝,而且楚王和曾(隨)之間亦有婚姻關系,由此可見兩國之間的親密程度。2012 年,在隨州文峰塔東周墓地發掘了一座編號為M18 的亞字形大墓,出土了帶有 “曾侯丙” 銘文字樣的銅器。發掘者推斷M18 的墓主應為曾侯丙,并根據文峰塔墓地中曾墓和楚墓的年代范圍認為楚滅曾的年代大致在戰國中期偏晚[31]32。曾侯丙乃現在所知最晚的一代曾侯,所以至少在曾侯丙之前隨棗走廊一帶當仍在曾(隨) 的疆域范圍之內。
然而問題是前面我們提到春秋早期之后,滾水流域、漳河流域未再見與曾國有關的文化遺存,似乎表明春秋早期之后曾國的勢力完全退出了這兩個地區。不過從棗陽周臺遺址的考古發掘來看,春秋早期之后與曾國有關的遺存雖然未再見到,但是姬周文化遺存直到戰國中期一直存在著[24]91-93。雖然不能斷定這些姬周文化遺存就是曾國的,但當和姬姓曾國有關。而且自春秋中期起周臺遺址開始出現楚式器物,說明春秋中期楚國勢力已進入該地區,正和當時的政治形勢相一致,即隨著楚國的不斷侵伐,曾國的政治中心逐漸退縮至隨州一帶,并逐漸淪為楚國的附庸。不過由于楚國并未滅亡曾(隨) 國,而且結有盟誓,尤其是公元前506 年曾(隨) 幫助昭王復國后二者關系更加親密,所以在滾水流域曾(隨) 國勢力和楚國勢力當是同時存在的,直到戰國中后期楚滅曾(隨) 之后,楚文化才完全占領這些地區,如九連墩戰國楚墓可能就是當時楚國滅曾(隨) 后占有該地區的一個最好的寫照[32]10-14。至于其他地區當存在著類似的情形,不過有待考古發掘的進一步驗證。
注釋:
①曹錦炎先生的論文最早見于2013 年夏安徽大學舉辦的 “紀念何琳儀先生誕辰70 周年學術討論會” 會議論文集,該論文集后結集出版,見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漢語言文字研究(第一輯)[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曹文結集出版前已作為特稿先予發表,見《江漢考古》2014 年第4 期,文中附有曹錦炎對殘鐘銘文的摹本;凡國棟先生之文亦見《江漢考古》2014 年第4 期,文中附有重新摹寫的鐘銘摹本。關于本文要討論的“申固楚城,改復曾疆”這句銘文,二者的摹本有所不同,此句參照M1:1 鐘銘來看,當以凡文所附摹本更接近實際,本文對此不做過多討論,讀者可自行查閱。
②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隨州市博物館.隨州擂鼓墩二號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曾國青銅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義地崗曾公子去疾墓發掘簡報[J].江漢考古.2012(3)。葉家山西周早期墓地暫不討論,故不列入。
③參中甗(《集成949》)、靜鼎(《近出》357)。
④關于瑕地地望,杜注曰:“隨地”,又《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師還,及瑕”,杜注曰:“楚地”。江永《春秋地理考實》卷二“瑕”字條曰:“《水經注》:‘肥水徑山桑縣故城南,又東積而為陂,謂之瑕陂。又東南徑瑕城南,春秋楚師還及瑕即此城也。’山桑縣,在今壽州蒙城縣北,屬鳳陽府。今按:楚師自鄢陵還荊州,不當回遠由今之蒙城,《水經注》誤也。桓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軍于瑕以待之,當是此瑕邑,蓋在今德安府隨州。”
⑤鄭威.楚國封君研究[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253。關于鄭威先生所列位于今湖北廣水至安陸北部一帶的“隨侯”是否為楚國封君,似可再商榷,鄭威先生之說可詳參其書第59-61 頁的相關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