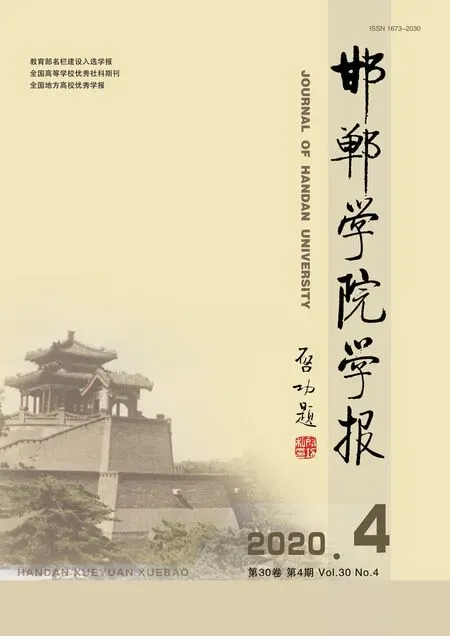焦循解《詩》立場再探
——以《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為中心
黃 睿,秦躍宇
(1.揚州大學 文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2;2.湖州師范學院 求真學院,浙江 湖州 313000)
對于焦循的治學立場,以往學者似乎有著相悖的觀察。近人劉師培指出,“自漢學風靡天下,大江以北治經者,以十百計。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能殫其業,或緣詞生訓,歧惑學者。惟焦(循)、阮(元)二公力持學術之平,不主門戶之見”[1]1896。張舜徽先生認為“焦氏對于做學問,提倡創造,反對保守。主張融會眾說,反對固執一家”[2]126。然亦有學者指其經學研究存在門戶之見。何澤恒《焦循研究》評價云:“里堂論學,極惡拘守門戶之見,其于時人專漢據守之習,亦屢加指摘,而己則不免于自陷。”[3]209-210又謂焦循“雖亦深惡乎漢宋門戶之相爭,力辟執一據守,而一代學術大趨之尊漢袒古者,終莫能脫身其外”[3]225。如果說劉師培與張舜徽先生強調的是焦循主觀治學論調,那么何澤恒教授則敏銳察覺出了焦氏論學主張與其治學實踐之間的矛盾性。
以往研究多認定焦循站在揚毛抑鄭的立場上研究《毛詩》。何澤恒《焦循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洪湛侯《詩經學史》(中華書局1999年)、趙航《揚州學派概論》(廣陵書社2003年)、陳居淵《焦循阮元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劉玉國《<毛詩補疏>探究》(臺北萬卷樓2016年)、孫向召《乾嘉<詩經>學研究》(揚州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魏菊英《清代詩經學研究》(蘇州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高婷婷《嘉慶時期<詩經>文獻研究》(沈陽師范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蔣倩《焦循<毛詩補疏>訓詁研究》(揚州大學2018年碩士學位論文)皆認為焦循《毛詩補疏》有宗毛傾向。在上述論著中,對焦循揚毛抑鄭問題分析較為詳盡者是趙航先生。其《揚州學派概論》將焦循《毛詩補疏》之內容概括為箋失傳義、箋不解傳義、箋迂曲、箋淺而傳深、辨箋誤謬五個方面。①趙航《揚州學派概論》,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第140-143頁。在趙航先生所列十個例證中,僅三則體現出揚毛抑鄭傾向。②第一,“箋失傳義”下有四例,焦循于此四處皆旨在辨析毛、鄭異同。第二,“箋不解傳義”下有兩例。“窈窕淑女”條,焦循意在駁正《毛詩正義》,實非責難鄭《箋》;“人尚乎由行”條,焦循于鄭《箋》僅曰“不協”,揚毛抑鄭傾向并不明顯。第三,“箋迂曲”下有兩例,存在揚毛抑鄭傾向,但尚未體現出回護《毛傳》之舉。第四,“箋淺而傳深”下有一例,有揚毛抑鄭但無曲護《毛傳》傾向。第五,“辨箋誤謬”下有一例,焦循認為鄭《箋》解“關關雎鳩”并無謬誤,趙航先生誤讀焦循。但三則例證所涉鄭《箋》對詩義確有揣測和引申,故焦循在此情形下的揚毛抑鄭只是一種客觀判斷,其主觀立場尚難得知。因此,進一步探究揚毛抑鄭是指焦循客觀辨析毛、鄭優劣,還是主觀曲護《毛傳》,便顯得尤為必要。
較而言之,其余著述對此問題之論證則稍顯簡單。洪湛侯先生與何澤恒教授并未對焦循揚毛抑鄭問題進行舉例分析。③洪湛侯《詩經學史》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512頁。何澤恒《焦循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第216頁。陳居淵教授證之以《毛詩補疏》卷三“今者不樂”條和“公之媚子”條,④陳居淵《焦循阮元評傳》上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4頁。孫向召所舉亦為“今者不樂”條,⑤孫向召《乾嘉<詩經>學研究》,揚州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然焦循于兩則條目皆云鄭《箋》“非毛義”,即僅辨析毛、鄭異同,未發高下之論。魏菊英所舉《毛詩補疏》卷一“窈窕淑女”條已見于趙航先生《揚州學派概論》,此條《毛傳》訓解不誤,焦循從《傳》實屬正常,難以證明其有揚毛抑鄭傾向。高婷婷僅據《毛詩補疏》卷二“招招舟子”條,認定焦氏存在十分明顯的揚毛抑鄭傾向,但焦循于此條實際只表明《箋》解“招招舟子”與毛異義。蔣倩同樣指出焦氏《毛詩補疏》存在過度依據《毛傳》之問題,并證之以卷三“俟我乎巷兮”條。《毛傳》此條訓解有誤,焦循從之確有不妥,然孤證不為定說,其解《詩》立場尚需深入探研。
焦循是否有意識地“揚毛”“申毛”甚至曲護《毛傳》,很難從短短五卷的《毛詩補疏》中找到足夠實例來證明。事實上,焦循本人也并不希望在考證中呈現出執守一家的姿態,其在早期著述《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中就反復申述自己“不敢為毛、鄭謟”[4],“毛、鄭有非者,則辨正之,不敢執一以廢百也”[5]。與《毛詩補疏》不同,焦循《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更加注重文字訓詁與名物考證,且該書長達十一卷,有助于我們圍繞經典文本中的語言文字對焦循解《詩》立場展開充分研究。《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不僅是焦循最早撰寫的一部《詩》學著述,也是其整個《毛詩》名物研究歷程的縮影。該書屬稿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寫定于嘉慶四年(1799),歷經十八載。此書撰就后,焦循便轉向《毛詩》天文、歷算、地理和經義之研究,并未在名物考證方面做過多拓展。因此,更具定論意義的《毛詩補疏》在探討名物時,仍然沿用了《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的諸多結論。從《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的考證內容來看,焦循解《詩》確實存在曲護《毛傳》之情況。前輩學者論證焦循宗毛,有時會圍繞《毛傳》本身訓解正確與焦循理解無誤者進行舉例,實際焦氏宗毛甚至曲圓《毛傳》問題,更應置于《毛傳》訓釋有誤與焦循誤發《毛傳》的范圍內進行觀察。茲以上海圖書館藏十一卷本《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為中心,類舉該書曲護《毛傳》實例如下。
一、曲圓《毛傳》抵牾之處
《毛傳》時有前后矛盾之處,焦循遂取其中有裨于《詩序》者釋之。例如《毛傳》于《召南》“騶虞”兩訓,既在“于嗟乎騶虞”后以“義獸”解之,又在“一發五豝”后釋“騶虞”為“虞人”。“騶虞”確實是傳說中的一種神獸,但詩于“一發五靶”和“一發五縱”后言“吁嗟乎騶虞”,自是贊美虞人射技,故此“騶虞”是指司“騶”之虞人,與獸義無涉。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即指出“騶虞”乃“虞人”,“義獸”之解是“牽合古書,欲創新義”[6]122。劉毓慶教授亦指出,“義獸”當是漢儒后增之文。①劉毓慶:《詩經二南匯通》,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521頁。然而,焦循僅列“義獸”之訓,刪棄“虞人”之說,又在按語中大量征引舊注以證“騶虞”為獸,全然不顧詩意。此舉顯然是為闡發《詩序》所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的思想。
《毛傳》又于《大雅·江漢》之“鬯”兩訓,云:“鬯,香草也。筑煮合而郁之曰鬯。”既訓“鬯”為香草名,又謂“鬯”是舂搗、合煮鬯草之后的成品,指代混亂。實際“鬯”是酒而非香草。殷墟卜辭載:“乙丑卜,酒御于妣庚,伐廿、鬯廿。”[7]481“御”即御祭,“酒”為薦祭之物,“伐”是砍頭以祭,可知“鬯”為酒。又,“丙申卜,即貞:父丁歲,鬯一卣。”“福,鬯二卣,王受佑。”“鬯五卣,有正。”[7]482“卣”為酒器,亦可知“鬯”為酒,且《大雅·江漢》即作“秬鬯一卣”。于省吾先生指出,甲骨文中祭祀用“鬯”而不用“郁”,“郁鬯”應是舂搗并合煮鬯草的鬯酒。②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本》,臺北:大通書局,1981年,第307頁。在西周金文中,祭祀用酒也多稱“鬯”,例如“易(賜)女(汝)鬯一卣”(西周《大盂鼎》)。《說文?酉部》云:“莤,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為莤。像神?之也。”[8]1302明言“鬯”為酒。考古學家何駑亦指出,“鬯是用郁金香草煮出來的香酒,因此郁金香或可因此而別稱為‘鬯草’,③按,何駑所言“郁金香”,當是“郁金香草”之誤。郁金香(tulip)大約在19世紀才傳入中國。意為制作香酒‘鬯’的草,但并非本是就是草”[9]245。
然而,在《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十“鬯”條中,焦循不顧詩意與《傳》文矛盾之處,強以本義與引申義解之。首先,焦循雖然羅列了與《毛傳》訓釋不同的鄭眾《肆師職注》、鄭眾《郁人職注》、鄭玄《郁人注》和鄭玄《鬯人注》,但對上述異訓皆不甚在意,未予解釋辯駁。其次,焦循根據《禮記·雜記》所謂“暢(鬯)臼以椈,杵以梧”,指出“鬯”可以搗,則必非酒名。事實上,“鬯”在漢代就已經開始指代混亂。第三,曲解《說文》“鬯,以秬釀郁草”,認為《說文》之“鬯”為香草,鬯與郁草和之才為酒,但《說文》明言“鬯”是用郁草和秬釀成的一種酒。第四,雖然焦循認為“鬯”應是香草,但也意識到《毛傳》所謂“筑煮合而郁之曰鬯”無法回避。且《文王》“裸將于京”,《毛傳》曰“裸,灌鬯也”[10]962;《旱麓》“黃流在中”,《毛傳》云“黃金所以流鬯也”[10]1004,是《毛傳》又以鬯為酒。無奈之下,焦循只能繼續曲圓《毛傳》,指出“鬯”作酒時是兼郁而言,“鬯”本身并非是酒。換言之,焦循認為“郁”和“鬯”都是可以和于酒之香草,故“以鬯為香草者,從其本也”。惜乎焦循所引兩條書證皆存問題:其一,焦循以《鬯人》“共鬯以沃尸”“共秬鬯以給淬浴”為據,認定斷無以酒共浴者。但賈公彥云“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11]513,是“鬯”與可飲之酒不同。其二,焦循據《鬯人》“臨吊,被介鬯”,認為酒不可以“被”。實際此處引文有誤,核《周禮·春官·鬯人》,可知該句應作“凡王吊臨,共介鬯”[11]513。要之,焦循并未指出《毛傳》抵牾之處,而通過擱置詩篇文辭之意、回避他說與強行彌合異訓的方式,勉強證成《毛傳》。
二、規避《毛傳》誤訓
對于《毛傳》訓解明顯有誤之處,焦循在《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中從不直言其非。具體處理方式有二,一是不列《毛傳》釋義,直接闡述己說。例如《召南》“麕”條,焦循并未提及《毛傳》對“麕”之闡釋。這不是因為《毛傳》沒有訓解“麕”字,而是其所謂“兇荒則殺禮”在焦循看來顯系牽強附會,《野有死麕》文本本身無法釋讀出荒災減少納幣之意。不過,這種通過刪棄《毛傳》訓釋以回避直指其非的方法,在《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中并不多見,更多者是對《毛傳》釋義有誤之處避而不談,徑以另外一種相對合理之訓解代替。例如卷六《秦風》“六駮”條,《毛傳》謂“駮如馬,倨牙,食虎豹”,但綜覽《詩經》“山有……,隰有……”之例,可知該句式空缺處皆以木相配,①“山有……,隰有……”在《詩經》中出現九次,涉及五個篇目,分別是:(1)《邶風?簡兮》:“山有榛,隰有苓。”(2)《鄭風?山有扶蘇》:“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橋松,隰有游龍。”(3)《唐風?山有樞》:“山有樞,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杻。”“山有漆,隰有栗。”(4)《秦風?晨風》:“山有苞櫟,隰有六駁。”“山有苞棣,隰有樹檖。”(5)《小雅?四月》:“山有蕨薇,隰有杞桋。”《毛傳》將“山有苞櫟,隰有六駮”之“駮”解作獸類顯然不妥。但焦循對《毛傳》誤訓不予置評,徑以木名釋“駮”。
卷六《陳風》“荷”條,《毛傳》釋“荷”為“芙蕖”。焦循認為《陳風·澤陂》“有蒲與荷”之“荷”本作“茄”,“茄”與“荷”音近可通借,故此處亦可作“荷”。鄭玄所見文本寫作“茄”,遂以“其莖茄”箋之。但《毛傳》訓“荷”為芙蕖,與鄭《箋》異義。焦循既然指出《澤陂》“有蒲與荷”之“荷”本作“茄”,則其無疑認為鄭《箋》之解為是。然若申述鄭《箋》,則自然與《毛傳》對立,故焦循只能含糊其辭,云“若本非‘茄’而解以為‘莖’,鄭不如是,舛也”。
卷八《小雅·鹿鳴之什》之“鱧”,《毛傳》訓為鲖,異于《爾雅》。對此,焦循認為《毛傳》多本《爾雅》為訓,《爾雅》:“鯉,鳣。鰋,鲇。鱧,鯇。”《毛傳》訓“鳣”和“鰋”皆從《爾雅》,②《衛風·碩人》“鱣鮪發發”,《毛傳》:“鳣,鯉也。”《小雅·魚麗》“魚麗于罶,鰋鯉”,《毛傳》:“鰋,鲇也。”則“鱧”也必定訓為“鯇”。并且,焦循還認為《毛傳》訓“鱧”為“鲖”,乃是后人據郭璞《爾雅注》妄改,竭力為《毛傳》開脫。
卷八《小雅?鹿鳴之什》之“蘋”,《爾雅》于“蘋”兩訓,一曰“蓱”,二曰“藾蕭”。《毛傳》取前者,鄭《箋》則取后者,《毛詩正義》指《小雅?鹿鳴》中鹿食之蘋非水中之草,故應為“藾蕭”。對此,焦循僅言《箋》與《毛詩正義》訓釋正確,卻不直指《毛傳》之非。
三、誤讀并比附《毛傳》
卷二《召南》“樸樕”,《毛傳》訓為“小木”,焦循認為“樸樕”具體應指叢生似櫟之槲樕。但“樸樕”實際是疊韻聯綿詞,此處可指小木。王引之《經義述聞》對孫炎“樸樕,一名心”作注時,指出“樸樕”與“心”皆有“小”義,并引《漢書·息夫躬傳》顏師古注與《邶風·凱風·傳》證明古人稱“小”為“仆遬”,稱“小棘”為“棘心”。由此可知,《毛傳》訓解無誤,但焦循將“小木”坐實為“槲樕”,顯系誤讀《毛傳》。
卷三《邶風》“燕燕”,《毛傳》訓為鳦。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謂“鳦”本作“乙”,表燕子,為象形,“本與甲乙字異,俗人恐與甲乙亂,加鳥旁為鳦”[8]1015。馬縞《中華古今注?信幡》:“書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曰以鴻雁燕鳦,有去來之信也。”[12]18可知《毛傳》所謂“鳦”即燕子。向熹教授認為“燕燕”重言大概出于兩種原因,一是增字以足四言,二是方言中的特殊稱謂,此說甚是。然焦循拘泥《毛傳》字面表述,認為“《傳》以‘乙’訓燕燕,則燕燕自非兩燕之迭稱也”,誤解《毛傳》之意。
卷三《邶風》“棘”,《毛傳》謂“棘,難長養者”。從《凱風》思母孝親之旨來看,《毛傳》訓“棘”為“難長養者”,是以棘之難長養興母氏之勞苦,故《箋》云“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10]795。然焦循所引《春秋元命包》、鄭玄《朝士職注》和《陳留耆舊傳》,皆是就棘之形態而論。一則未能闡明興意,二則所得“凡物心赤者堅。堅,故知其難長也”之結論,無論是從邏輯還是從書證上皆不能成立,實屬牽強附會。
四、回護《毛傳》的其他方式
焦循有時徑以《毛傳》為名物訓釋標準,并不列舉書證,亦無相關考證與推論。例如卷三《邶風》“流離”條,焦循謂“《傳》以‘少好’喻始而愉樂,‘長丑’喻終以微弱。梟之丑在強暴,《詩》之所取,必非此矣。《正義》所引,未得《傳》義”。其中,不管是對“流離”習性之考證,還是對《正義》之評判,焦循皆以《毛傳》為準。
此外,《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所載存疑待考之條目,也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焦循對《毛傳》之回護。例如卷八《小雅·鴻雁之什》“竹苞”條不附焦循按語,原因可能在于焦循無法圓滿解釋《毛傳》“苞,本也”這一訓釋。《小雅?斯干》:“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按此句式,則“苞”與“茂”當同屬形容詞,但《毛傳》卻訓“苞”為“本”。這一問題令焦循頗為疑惑,在該書三種稿本,即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二十卷本、上海圖書館藏三十卷本和上海圖書館藏十一卷定本中,焦循皆未作出任何考證與解釋。《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僅收名物詞條,焦循將“苞”列入此書,說明其認為“苞”是一種植物。但若貿然以植物作解,則可能違背《毛傳》“苞,本也”之訓,故只好存而不論。事實上,“苞”猶“葆”,“本”作“苯”,皆為草木叢生之義。王念孫《廣雅疏證》云:“葆、科為本?叢生之本。……本,或作‘苯’。張衡《西京賦》云:‘苯?蓬茸。’……葆、本一聲之轉,皆是叢生之名。葆猶苞也。《小雅?斯干》篇‘如竹苞矣’,《毛傳》云:‘苞,本也。’《箋》云:‘時民殷眾,如竹之本生矣。’”[13]354-355由此可見,焦循直以“本”字解“苞”顯然不可能,而以植物訓“苞”又有違《毛傳》,遂陷入兩難境地,只能擱置一旁。不過,這一問題不僅說明焦循對《毛傳》有刻意回護之意,還反映出其對同源詞和通假字之探求仍頗為有限。因為焦循在早期二十卷稿本卷一“棘”條中,即已搜羅出訓“苞”為草木叢生的關鍵材料:“《爾雅·釋言》云:‘苞,稹。’孫炎注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14]234惜乎焦循未能沿此繼續探討。此外,焦循對于同時期研究成果了解不足,也是導致其未能圓滿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原因。因為《廣雅疏證》成于乾隆六十年(1795),嘉慶元年(1796)已有王氏家刻本,而《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則成于嘉慶四年(1799),①上海圖書館藏十一卷本《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十一末題識:“本三十卷,今合為十一卷,而以考訂陸璣《疏》為一卷續于后,共成十二卷。時秋八月初三日,天陰雨,因次女病歸來,檢閱之,書記于此。”且焦循又于嘉慶九年(1804)檢查過自己的考證成果,②上海圖書館藏十一卷本《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十一末題識:“甲子九月閱。憶次女以庚申七月殤,今五年矣。”但期間焦循一直沒有查閱《廣雅疏證》對此問題之解釋。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也存在明確駁正《毛傳》者,但僅限于校勘問題。例如卷六《秦風》“苞棣”之“棣”,《毛傳》訓為“唐棣”。對此,焦循指出,“《爾雅》栘名唐棣,棣名常棣。《詩》專言棣,則常棣也。《傳》‘唐棣’,當是‘棠棣’之誤”。又如卷六《陳風》“椒”,《毛傳》謂“椒,芳香也”,焦循則認為“作‘芳物’為是”。
余論
綜覽《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可知焦循不加考證而徑本《毛傳》者較少,但在《毛傳》訓解有誤和前后抵牾處多加以規避或彌合。并且,即便《毛傳》訓釋無誤,焦循也往往存在誤讀和強行比附之舉。真正對《毛傳》進行駁正處,僅限于校勘問題。由此可見,雖然焦循撰寫此書意在“盡去詭說,獨存古義,遍覽典籍,就正有道”,并反復強調“不敢為毛、鄭謟”[4],“毛、鄭有非者,則辨正之,不敢執一以廢百也”[5],但其解《詩》實踐不盡人意處頗多,廣泛存在誤讀、曲解、回護與比附之情況。焦循撰寫《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是為了補正宋代陸佃《埤雅》和羅愿《爾雅翼》之不足,①上海圖書館藏十一卷本《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序》:“辛丑、壬寅間,始讀《爾雅》,又見陸佃、羅愿之書,心不滿之,思有所著述,以補兩家之不足。”但這一客觀辨析名物之理念,在實際考證中常常讓位于對《毛傳》和《詩序》的主觀推崇。焦循認為《毛傳》訓詁一本《爾雅》,頗可信從。“《爾雅?釋草》以下,多釋《詩》物類,毛公《詩詁訓傳》,率取于是”[4]。且焦循深信《毛詩》(包括《傳》《序》)傳自子夏,“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15]。據《論語·先進》“文學:子游,子夏”,可知子夏是孔門文學一科的代表人,故在焦循看來,子夏所傳《毛詩》(包括《傳》《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圣人之意。此外,焦循十分重視《詩》教,而《詩序》則是闡明《詩》教之關鍵。但宋明之人“以理自持,以幸直抵觸其君,相習成風,性情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故焦循認為“《小序》之有裨于《詩》,至切至要”[16]。
另一方面,焦循曲護《毛傳》也與其治學方法之弊端密切相關。例如卷十《大雅·文王之什》“菑”條,《大雅·皇矣》“作之屏之,其菑其翳”,《毛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為翳。”從焦循證明《毛傳》“木立死曰菑”之過程即可發現諸多問題。焦循認為“‘菑’為‘立’名,故通作‘栽’”。“菑”在上古屬莊母之部,“栽”是精母之部,二字疊韻準雙聲,確實存在通假之可能。徐灝《說文解字注箋》:“菑者,初墾辟之謂也。田久污萊,必就除其草木,然后可耕。因之災殺草木謂之菑。”[17]又《荀子·修身》“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楊倞注:“菑,讀為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18]21據此,可知“菑”與“災”為同源詞。“災”又同“烖”,但沒有文獻可以證明“菑”通作“栽”,焦循所言并無依據。其次,由于《爾雅》謂“田一歲曰菑”,即訓“菑”為田地初耕,故焦循又引入“茲”字以證“菑”有初始之義,甚為迂曲。最為關鍵者,書中所舉《素問》“青如草茲者死”,與《史記》“察之如死青之茲”之“茲”,前者義為草木滋盛,后者義為草席,皆與“菑”之立死義無關。因此,焦循考論看似征引繁密,實則缺少最為關鍵的證據,所得結論自然是對《毛傳》的一種曲護而非證明。又如前述卷二《召南》“樸樕”條,《毛傳》訓為“小木”,焦循又加以引申,指出樸樕即叢生似櫟之槲樕。但“樸樕”是泛指小木的疊韻聯綿詞,焦循將其坐實為槲樕,實際反映出他對聯綿詞之認識存在局限。再如卷五《齊風》“魴鰥”條,焦循認為《毛傳》訓“丱”為幼稚,是因為“卝”為《說文》古“卵”字,“毛以幼穉訓之,正取‘卵’之義”。然“丱”本為象形字,表兒童束發成兩角形,故可引申為“幼稚”義。焦循通過“卵”字輾轉相訓,殊為繁瑣,本欲證成《毛傳》,實際卻未得毛義。焦循解經之失,殆若上述種種,或可于后繼學者研究焦循有所補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