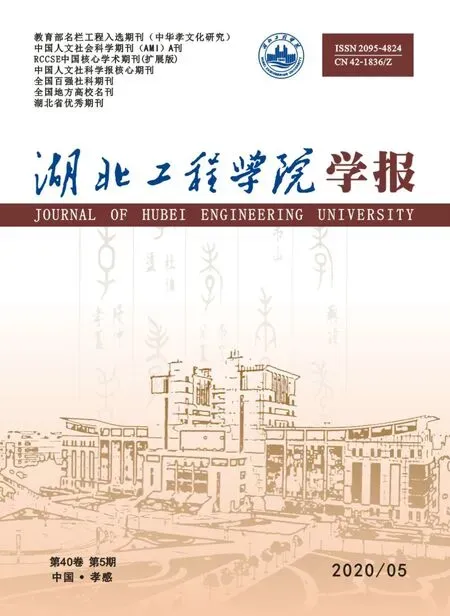約翰·斯坦貝克的圣經情結
何 英,雷佳娣
(隴南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外國語學院,甘肅 成縣 742500)
縱觀世界文學史,沒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圣經》那樣對西方社會產生如此巨大深遠的影響。《圣經》不僅是一部宗教、史學鴻作,也是一部文學經典巨著。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圣經》就是一部內涵豐富、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都能從中汲取養料——宗教學家可以從中探窺基督教的早期發展史,史學家可以從其記載的歷史資料、民族文化習俗、法規中考證猶太民族的發展史,其中的人物原型、故事母題、敘事結構、隱喻手法、語言風格也為文學家們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素材。美國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約翰·斯坦貝克的創作生涯更是深受《圣經》的影響,他在許多作品中引用圣經典故與隱喻,力圖鼓舞處于困境中的民眾,為他們提供精神慰藉,并為解決當時美國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提供方案,他對社會現實的客觀描繪與辛辣揭露使他備受勞動人民的愛戴,也使他的聲譽在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文壇如日中天,這一切都為他日后贏得諾貝爾文學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文擬從斯坦貝克作品的主題入手,探討斯坦貝克的創作與《圣經》的淵源,從而分析斯坦貝克的圣經情結以及該情結在其作品中的體現。
一、斯坦貝克與《圣經》之緣
1902年,約翰·斯坦貝克出生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薩利納斯山谷中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之家,父親恩斯特·斯坦貝克經營著一家面粉廠,曾擔任過當地蒙特利縣政府的司庫,母親奧莉薇·漢密爾頓為愛爾蘭后裔,是當地一所公立學校的教師。良好的家庭條件使得斯坦貝克從小便接受了系統正規的教育,在母親的精心教導下,斯坦貝克閱讀了《圣經》和大量世界文學名著,在這些作品中,他尤為喜愛情節豐富、主題突出、人物刻畫鮮明的圣經故事。正如他在回憶童年往事時所言的那樣:“我置身于文學的氛圍之中,《圣經》浸透了我的肌膚。……也許正是這本書,使我對英語語言產生了激情的愛。”[1]上述這段文字說明圣經典故中所蘊含的哲理、展現的價值觀念、傳達的人文意蘊、宣揚的道德取向不僅給予了斯坦貝克人生成長過程所需的養分,激發了他對文學創作的興趣,也為他日后的創作生涯提供了許多絕妙素材,以至于在他開始小說創作后,“作品里充滿了出自圣經典故的一些簡單又引人聯想的代表性主題和人物”[2]。這充分表明,童年時熟讀《圣經》的經歷使斯坦貝克具有了豐厚的文學積淀,使他在創作時能夠更為游刃有余地利用圣經典故來表達作品的主題思想,從而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寫作風格。
二、斯坦貝克的圣經情結及其作品主題表現
1.兄弟相爭主題的再現。家庭是最基礎的社會單位,家庭成員之間的人際關系,即夫妻關系、父母與子女的關系、兄弟姊妹間的關系等是一個很復雜的倫理問題。尤其是兄弟姊妹間的關系,由于涉及財產繼承,才智能力差異,以及爭奪父母關愛等矛盾,每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或許都有過與兄弟姊妹攀比,并感到心理不平衡的體驗,總會有人認為自己在家中沒有得到公平的待遇,覺得父母更偏愛其他孩子。在《舊約·創世紀》中,兄弟相爭的主題俯拾皆是:該隱殺死亞伯成為人類第一起兄弟殘殺之例;雅各和以掃爭奪繼承權;利亞和拉結爭奪丈夫雅各的愛;由于父親偏愛,約瑟遭到兄長們的敵視和仇恨,被賣到了埃及等。所有這些爭端都有個相似之處,那就是上帝或父母偏愛小兒子。
《伊甸之東》是斯坦貝克于1952年完成的一部長篇世家小說,書名出自《舊約·創世紀》中非常著名的“該隱殺弟”的故事,斯坦貝克以這個典故為藍本描寫了薩利納斯峽谷中漢密爾頓家族與特拉斯科家族三代人的生活經歷。特拉斯科家族的第一代塞勒斯憑借偽造在美國內戰期間的從軍經歷從而獲得了地位和名譽,過上了體面的生活。“他深信,軍隊即使算不上十全十美,仍舊是男人唯一體面的職業。”“認為他的兒子們除了參軍之外就沒有更理想的前途了。”[3]21于是,在兩個孩子還非常年幼的情況下,他便違背孩子的天性,開始對他們進行軍事訓練:“孩子們剛會走路,塞勒斯就讓他們學兵器教范。孩子們上小學時,已經把列隊操練當成呼吸那般自然、地獄那般討厭的東西。”[3]22長子亞當生性善良懦弱,懼怕暴力,他卻執意要讓他應征入伍;小兒子查爾斯天性好勇斗狠,渴望參軍建功立業,可他毫不理睬。他對亞當的偏愛招致了查爾斯的妒忌,差點給亞當帶來了殺身之禍。一天晚飯后,查爾斯誘騙亞當出去玩耍,結果卻將他毒打至昏迷,之后從家里取來斧頭,想要殺死亞當,幸好亞當蘇醒后,藏在路邊的排水溝中,躲過一劫。若干年后,亞當的兒子迦爾也因為妒忌父親對弟弟亞倫的偏愛,便將他們的母親沒有去世、而是在當妓女的事實告訴了善良的亞倫,亞倫因接受不了這一殘酷的現實,于悲痛中應征前往歐洲戰場,最終戰死疆場,亞當也因這一沉痛的打擊傷心而亡。這些情節與該隱殺弟的故事如出一轍,通過這些故事情節,斯坦貝克意圖告訴讀者:嫉妒是人的天性,但其根源卻是父母的偏愛,正是這種偏愛使得兄弟間曾經擁有的平和表象被打破。兄弟友愛的溫情面紗剝落后,顯現的并不是外人所見的那種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諧家庭關系,而是受冷落一方埋藏在記憶最深處的嫉妒、憤怒與傷害。
2.善惡對立主題的沿襲。善惡對立、或善惡沖突,是古往今來無數文學作品中經久不衰的永恒主題,《圣經》也不例外。具體而言,圣經中首次出現的善惡沖突是亞當夏娃受蛇的蠱惑而偷吃了“辨識善惡樹”的果實。此后,善與惡、上帝與撒旦、九大天使與墮天使之間的對立斗爭便一直此起彼伏。利蘭·萊肯就認為貫穿圣經的主要情節和人物沖突便是善惡沖突,表示“圣經文學中的每一事件在某種意義上幾乎都是這種善與惡的原型情節的再現”[4]。斯坦貝克也認為:“我們只有一個故事,所有的小說和詩歌都基于善和惡在我們身上的永不停息的搏斗。”[3]525正是由于擁有這樣的觀點,善惡對立的主題頻繁出現在他的作品中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人鼠之間》中,善的一方是以喬治、萊尼和坎德為代表的季節工人,他們四處打短工,所奢求的夢想不過是“以后可以靠微薄的積蓄蓋一間小屋,弄一片菜園子,再養上一些家畜,冬天下雨時就不去干活,在家休息”[5]。惡的一方則是農場主的兒子柯利及其妻子,柯利身材矮小、懦弱無能,卻仗著少東家的身份在農場中橫行霸道,經常對雇工非打即罵,是眾人都非常討厭的“混賬家伙”;柯利太太則舉止輕佻,四處勾引挑逗男人,是個不守婦道的壞女人。作為善的一方,喬治和萊尼,尤其是人高馬大、智力低下的萊尼,生性善良,膽小怕事,他們與惡的一方——柯利因誤會而發生沖突。柯利因四處尋找妻子而受到卡森的奚落時,看見萊尼臉上愉快的微笑,以為他在嘲笑自己,立馬暴跳如雷,把他打得滿臉流血,而嚇壞了的萊尼卻兩手垂在身體兩側,任其欺辱,其實萊尼之所以微笑,是因為他還沉浸在喬治之前描繪的未來農莊生活的美夢中。之后在喬治的鼓勵下,萊尼抓住了柯利揚起準備繼續打他的手,在無意之中將其捏斷。擔心別人知道這件事的經過會嘲笑他的無能,斷手后的柯利并未向父親告狀。作為極具社會責任感的現實主義作家,斯坦貝克通過故事情節上的推進,嘗試表達自己的善惡觀,即在善與惡的沖突中,善雖然會付出一定的代價,但最終必將戰勝惡。小說的最后,萊尼因失手殺死了柯利太太而遭到追捕,喬治一方面不希望萊尼被捕捉后受私刑折磨,另一方面也為了擺脫自己的嫌疑,只好忍痛親手將這個與他相依為命的朋友殺死。這也說明,即使是善的一方,在切身利益遭到損害或面臨風險時,為了確保自己不受影響,也會顯示出自己惡的一面,這種惡存在于人的天性中,是與生俱來的。這也是《圣經》中傳達的“人性本惡”的善惡觀在小說中的具體體現。
此外,善惡對立的主題也多次出現在斯坦貝克的其他作品中,如《勝負未決》中罷工運動的領導者與資本家之間的對立,《月落》中為人謙遜溫和、有學者風范的奧登市長與納粹占領軍上校蘭賽之間的對立,《珍珠》中善良敦厚的奇諾一家與貪婪奸詐的神甫、醫生及珠寶商之間的對立等,例子不一而足。《圣經》中善惡對立的主題對斯坦貝克寫作風格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3.出行主題的文本仿造。在《創世紀》中,亞伯拉罕一家最初居住在吾珥,后來北遷到哈蘭生活,最后又遵照上帝的旨意西遷至“流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迦南,從此,這里便成了希伯來人心中的“希望之地、富饒之鄉”。在《出埃及記》中,為了擺脫埃及人的壓迫與奴役,居住在埃及的希伯來人在先知摩西的帶領下,逃離埃及,渡過“紅海”,穿越荒漠,到達西奈山,最后由約書亞帶領成功抵達圣地迦南。由此可見,出行 (journey) 是《圣經》中又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這種主題范式通過描寫主人公的離家出走、旅途漂泊、探險征戰等活動,來表現人類獲取知識、謀求財富或者獲得對人性本質的發現。”[6]
在為其贏得了廣泛贊譽的小說《憤怒的葡萄》中,斯坦貝克以美國大蕭條期間大批農民破產、逃荒和斗爭的故事為背景,描繪了以無產階級為代表的破產農民與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農場主、銀行家、官員之間英勇斗爭、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20世紀30年代,美國發生經濟危機,加上百年不遇的旱災,中部各州農作物大量枯死,導致莊稼歉收、絕收,從而把生活本就極為艱難困苦的廣大農民推向了絕境。然而,貪得無厭的大莊園主、唯利是圖的銀行家以及腐敗糜爛的官員相互勾結,通過各種卑劣的手段,乘機大肆侵占農民的土地,使許多農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向西逃荒以謀求活路。在小說中,湯姆·喬德的爺爺在啟程前激動地說道:“讓我到加利福尼亞去吧,我到了那兒,看到橙子,就要伸手去摘來吃,葡萄也行……讓汁水順著下巴往下流。”[7]91地廣人稀、土地肥沃、果樹飄香的加利福尼亞顯然成為了流民們心目中“流奶與蜜”的希望之地迦南。不過,與《圣經》中希伯來人到達迦南后過上幸福生活的美滿結局不同,當他們歷盡千辛萬苦到達加州后,卻發現這里并不是想象中的樂園:這里提供的工作機會也非常少,許多流民仍處于饑寒交迫之中,不得不乞討求生。即使有了工作,仍然要遭受層層盤剝,雇主們攜手壓低工資標準,拼命榨取他們的勞動成果;資本家對他們的苦難境遇熟視無睹,為了哄抬物價,使自己的利潤最大化,不惜毀掉成熟的果實;當地的警察也時不時地來找他們的麻煩。為了打破不合理的現狀,牧師凱西帶領工人據理力爭、奮起反抗,結果被前來鎮壓的警察抓進了監獄。出獄后,他又四處奔走,號召工人組建工會,希望通過罷工運動與資本家進行斗爭,卻不幸被大地主豢養的武裝流氓殺害。對喬德而言,凱西就是啟發和引導他的先知摩西,讓他懂得窮人應該團結起來與剝削階級作斗爭,而不是坐以待斃的道理,當凱西被打死后,他憤然而起,將兇手殺死為凱西報仇。在逃亡的過程中,其思想也得到了洗禮與升華,他在和母親告別時說道:“到處都有我——不管你往哪一邊望,都能看見我。凡是有饑餓的人為了吃飯而斗爭的地方,都有我在場。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場……我們老百姓吃到了自己種出的糧食,住著自己造的房子的時候——我都會在場。”[7]487這充分說明,湯姆·喬德在思想上已完成了從“小我”到“大我”的轉變,他義無反顧地踏上為窮苦大眾謀利益的新征程,成為一個像凱西那樣為改變社會現狀而奮斗的先行者。
因此,在《憤怒的葡萄》中,出行主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破產農民從中部的俄克拉荷馬遷徙到西部的加利福尼亞謀求幸福生活屬于表層或空間上的出行,他們在西行過程中的種種遭遇則揭示了人生歷程的艱難曲折。湯姆·喬德從被壓迫的勞動者中的一員成長為一名具有高度革命意識的工人領導,原先自私自利的羅莎夏最后用乳汁救活了一個素不相識的路人,這些均代表著人類在精神上的“出行”,揭示了人類心理的自我認識和靈魂的洗禮升華,象征著人類尋求救贖的歷程。而這正是圣經所呈現的“一個既超越又身在的救世主形象”的具體體現,“形成一種‘創造——原罪——拯救’三部曲式極富張力和深度的人性觀”。[8]
三、斯坦貝克圣經情結產生的根源
從以上論述可知,斯坦貝克在作品中所展現出的圣經情結可以歸根于兩方面因素的影響。首先,斯坦貝克自幼熟讀圣經,對圣經典故表達的主題意向和價值觀念了若指掌,可以說《圣經》已自然而然地根植于他的思想與寫作之中,變為其文學素養的一部分,從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其作品主題的選擇與表達。其次,《圣經》在西方社會屬于大眾讀物,其中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對斯坦貝克而言,引用或借鑒其中的主題情節不僅有助于自己作品主題情節的推進與發展,而且耳熟能詳、平鋪直敘的敘事范式可以避免因主題晦澀難懂而使讀者敬而遠之。此外,世俗化的故事模式也更易于引發讀者的共鳴,從而更好地發揮文學作品批判丑惡社會現實、探索人性本質的作用。
四、結 語
綜上所述,斯坦貝克在創作的過程中經常援引或借鑒圣經文學主題揭示社會現實問題,其作品揭示的主題往往是對圣經文學主題的再現、沿襲與模仿。通過這些自古以來就存在于人類社會中的普遍性問題折射現代人類的生存窘境與危機,揭示人類社會的本質矛盾,向世人傳達人生的真諦。因此,在社會飛速發展的今天,斯坦貝克的作品仍然充滿著獨特的文學魅力和現實意義,值得我們深入研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