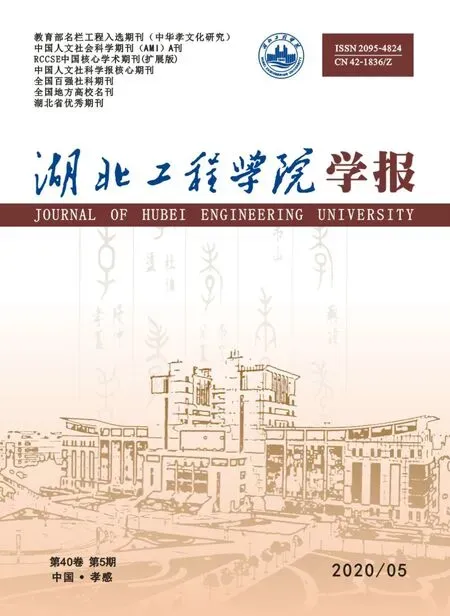儒家道德的“自我”與“他者”
孫旭鵬,趙文丹
(西安石油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5)
儒家道德思想之所以能夠對中國社會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一個最為根本的原因就是其通過根植于人性的方式,既為道德哲學的建立打下了深厚的理論根基,也為廣大民眾所廣泛接受提供了現實準則,這便是儒家道德的“自我”維度。儒家道德思想始終以“自我”為基礎,認為道德行為的確立并不是由外部的約束而致,而是以人性所本有的德性為根基,道德是可以通過內在的修為而成,人人具備成為“圣人”的條件。然而,儒家同時又認為,僅有“自我”的德性根基還不足以建立道德行為,必須經過“他者”的維度,通過“推己及人”的方式,將“自我”與“他者”結合在一起,在現實的人倫關系中道德才真正得以確立起來。儒家道德中的“自我”與“他者”共同支撐起儒家的道德體系。“自我”與“他者”之間充滿著一種內在張力,“自我”始終是通過“他者”加以關照的“自我”,而“他者”也始終是“自我”視域中的“他者”,二者在這種充滿張力的互動關系中,促使著儒家道德不斷發展完善,與時代發展相呼應,塑造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精神家園。
一、 道德的“自我”根基
儒家道德根植于“自我”,始終堅定地相信人所本有的德性,即人性向善的可能性;正是人性存在向善的可能性,才為儒家道德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孔子提出“為仁由己”開始,到孟子的“反身而誠”,再到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儒家學者無不承認人性中本有的德性基礎,這種德性基礎正是道德行為產生的源頭,這便是儒家道德的“自我”維度。美國漢學家倪德衛曾經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道德能否自學在儒家思想內部自始至終存著矛盾,這種矛盾集中體現在孟子與荀子二者的觀點對立上。倪德衛認為,孟子認為道德是可以自學的,而荀子則反之:“荀子一定會反對孟子的自然學習向德的人性論,并且,他很堅定地反對之。”[1]倪德衛固然注意到了荀子與孟子的差別,孟子更重人性內在善端的擴充,而荀子更重外在禮義的教化。但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在荀子與孟子之間存在著一個最為根本的相同點,那就是他們都認為道德行為的根基在于“自我”,荀子同樣肯定道德成立的基礎在于“心”對外在禮義的認知。
其實,儒家從“自我”出發來為道德行為奠定基礎從孔子就已經開始了,孔子講:“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仁”不是靠外在的約束而成,而是必須從自身出發依靠內在的修養來實現。孟子繼承了孔子從人自身來尋找道德根基的思維方式,明確提出了人心本有“善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既然人心天然具有這些“善端”,那么道德的確立自然就不假外求,只需要從自身出發就可以,所以孟子講:“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樂莫大焉”是一種道德自我覺醒之樂,也正是“孔顏樂處”的精髓;在實現這種道德之樂的過程中,自我作為道德的主體地位得到彰顯和提升。在孟子這里,“善端”其實就是他指出的人與禽獸的差異之處,這種差異是微乎其微的,但正是由于這微小的差異,道德才能夠成立,才將人類與禽獸分別開來。這種微小的差異,正是道德的發端處,也是人自身所本有的“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上》)。基于“良知良能”為人自身所本有,因而孟子堅信“人皆可以為堯舜”,“道德傾向(moral inclinations)與身體的成長發育一樣屬于自然”[2]。可以這樣講,孟子將儒家道德的“自我”維度發展到了頂點,充滿著對人性本有之德性的絕對自信。
然而,儒家思想發展到荀子這里似乎產生了一種重大的轉向,當然這種轉向主要是與孟子相比較而言的,與孟子的“性善”說針鋒相對,荀子提出了“性惡”說。荀子講:“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荀子·性惡》)荀子似乎完全否定了人本有之德性,并看到了順應欲望所造成的嚴重后果,提出以“禮義”來治“性惡”:“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后正,得禮義然后治”(《荀子·性惡》)。倪德衛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認為在荀子這里道德是不可以自學的,從而與孟子所堅持的人本具“良知良能”形成了鮮明對照。但倪德衛沒有注意到的一點是,荀子固然十分強調外在的“禮義”對于道德生成的重要作用,然而“禮義”如何可能才是問題的關鍵。荀子認為,“禮義”產生以及被接受的可能性仍然來源于“心”,荀子講:“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守道以禁非道”(《荀子·解蔽》)。荀子認為能否遵循“道”的關鍵在于“心”能否正確地認知,所謂的“道”其實就是“禮義”。徐復觀先生曾指出:“荀子一面以心為好利,乃就其欲望一方面而言;一面以心為能慮能擇,乃就其認識能力一方面而言;此亦為荀子言心之二方面,而非將心分為人心與道心兩個層次。”[3]荀子講“性惡”側重的是心“好禮”的一面,而從心具備“認識能力”這一面來看的話,那么通過心來知“道”,道德也是可以通過自學的途徑來實現的,因為人心本身就具備著對于道德的認知能力。
因而,不管是孟子講“性善”還是荀子講“性惡”,二者都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基礎,那就是道德的成立都是依賴于“自我”本心的,在孟子那里是“良知良能”,在荀子那里是“心知道”。從根本上來看,孟子和荀子都繼承了孔子“為仁由己”的思想,肯定了人自身具備道德成立的基礎,始終是從人自身出發來審視道德的生成。正是德性內在于人這一事實使得道德成為可能。基于此,孟子和荀子認為每一個普通人都具備成為“圣人”的潛質,孟子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荀子同樣認為“涂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正如錢穆先生講:“我們若承認圣人有善有德,便不該不承認人人皆可有善有德。”[4]但是“德”的成立只是“可以”,并非必然,這一方面肯定了道德的內在基礎,另一方面也從側面反映出道德的生成需要一個后天努力的過程。倪德衛認為的孟子“自學”的道德絕對不是一個自然生成的過程,同樣需要經歷一種后天“修為”的過程,如同荀子一樣,孟子肯定了“心”在道德確立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只有建立在“思”的基礎上,才能得到“德”,而“思”的器官正是“心”,通過“心”進行一種后天的修為。從這一點上來看,孟子與荀子并沒有本質的差別,只不過孟子的“心”更偏重于一種“反思”,采取的是“反身而誠”的路向,而荀子的“心”更偏重于“認知”,采取的是“心知道”的形式。
總之,盡管思想史上存在孟子與荀子關于“性善”與“性惡”的激烈對峙,然而這并不妨礙二者均將道德的基礎建立在“自我”之上,并且都沒有脫離孔子“為仁由己”的道德內在生成進路。道德是內在生成還是外在強加是儒家與法家的一個根本對立之處,荀子盡管重視“禮義”的外在約束,但是其仍然將“禮義”的認知根植于“心”,這是與其作為法家的學生韓非與李斯的根本差異之處。法家思想完全基于“趨利避害”的動物本性,利用外在的賞罰措施來看待道德的生成,忽略了人本有之內在德性,“荀子和法家最大的差別是:荀子的禮學是為了普遍的人而提出的,法家則僅僅是為了統治者并且是為了應對戰國末期的形勢而提出的”[5]。可以講法家的道德是無根的,如果說“趨利避害”是其基礎的話,那么這個基礎也是不牢靠的,因為利害關系隨時都在發生著變化,并且究竟應該順應何人之利也是說不清的,最終導向了法家學說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君主的權謀之術,更何談道德。先秦儒家所建立并強化的道德“自我”維度,對后世儒學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包括儒學發展史上的另一個高峰宋明理學,均沿襲著先秦儒家道德的內在生成進路。
二、道德的“他者”指向
道德的生成固然要有內在的根基,這一根基便是儒家所關注的道德的“自我”維度,然而只有將“自我”擴展到“他者”,在“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系當中,道德才能夠真正成立。儒家并沒有固守一種死寂的“自我”,而是面向現實生活將自我融入到群體之中,從而建立起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系。正是在日常人倫關系中,道德得以生成并展現。具體來看,儒家采取的是通過“推己及人”的方式,將自我內在的德性進行推擴,這在外體現出來的便是道德行為,正是通過道德行為,“自我”與“他者”之間實現了一種和諧互動,儒家所追求的和諧的人倫關系以及良好的社會秩序才有可能最終實現。
作為儒家思想的開創者,孔子正是基于“人”與“己”關系來規定“仁”的內涵,“仁”是一種聯系自我與他人的最高德性。當孔子的弟子樊遲問何為“仁”的時候,孔子只簡單回答了兩個字,那就是“愛人”(《論語·顏淵》)。那么又具體如何來“愛人”呢?孔子分別從“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來闡發。何為“積極”的“愛人”?即自己想要實現的也幫助別人實現:“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何為“消極”的“愛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強加給別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正如楊伯峻先生所言:“‘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有積極意義的道德,未必每個人都有條件來實行。‘恕’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則誰都可以這樣做,因之孔子在這里言‘恕’不言‘忠’。”[6]因而孔子的弟子曾參歸結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其實,不管是“忠”還是“恕”本質上都是一種“推己及人”,感同身受地站在“他者”的角度來思考問題,而不只是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孟子進一步將“自我”的內在德性向外推擴開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后來的荀子也講:“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荀子·非相》)儒家始終堅信,以“自我”的內在德性為基礎,通過“推己及人”的方式,就必然會建立起溝通“自我”與“他者”的道德行為。
儒家道德的“他者”指向絕不僅僅滿足于解決普通的人倫關系,而且還提供了一整套完善的社會治理方案。孔子講:“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孟子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荀子講:“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荀子·榮辱》)這無疑都是儒家以德治國思想的呈現,將道德的“他者”指向上升到社會治理層面,而不僅僅指向普通的人倫關系。在儒家看來,道德絕對不是毫無現實價值的玄談,而是進行社會治理的一種有效手段,因而孟子對梁惠王一開口就談“利”給予了針鋒相對的回應:“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認為實行“仁義”是治理國家的最好方式。杜維明先生指出:“儒家知識分子是行動主義者,講求實效的考慮使其正視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世界,并且從內部著手改變它。”[7]確實如此,儒家是有著深切現實關懷的,只不過這種現實關懷首先要從“內部”著手,通過內在道德進而影響他人并改造社會。也正是由于從“自我”到“他者”進行道德影響的過程是潛移默化的,有時候甚至是中斷的,因而才有了孟子“窮”與“達”之分。孔子周游列國的現實遭遇也充分說明,儒家的道德理想往往是不被理解的,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也說,孟子在當時就被認為是“迂遠而闊于事情”。這也充分說明,儒家從“自我”到“他者”的實現,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一個不懈努力的過程。
儒家典籍《禮記·大學》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治理思想,認為國家治理首先從“修身”做起,然后通過層層遞推來實現“齊家”,進而“治國”、“平天下”。也就是說,儒家的“推己及人”首先要從自己身邊的人做起,才不至于流于空泛的形式,這也是儒家為什么非常重視血緣親情的重要原因,以血緣親情為基礎,就邁出了“推己及人”的第一步,也是最為堅實的一步。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無疑,以血緣親情為基礎的“孝弟”便成為“推己及人”的開端。在儒家看來,如果遵循了“孝弟”原則,從某種意義上也就是為整個社會的和諧有序做出了貢獻,因而當有人問孔子為什么不從政的時候,孔子回答道:“《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正是從血緣親情的“孝弟”做起,儒家“推己及人”才具備了進一步向外推擴的可能性,甚至整個社會的治理也要依靠道德的感化力量,從而形成了儒家“家-國”同構的社會治理模式。
儒家道德的“他者”指向無疑包含著極為強烈的現實關懷,塑造著傳統儒家知識分子關愛他人以及服務社會的擔當精神,而絕不僅僅是封閉在書齋里的學問。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言:“儒家哲學,范圍廣博。概括起來說,其用功所在,可以《論語》‘修己安人’一語括之。其學問最高目的,可以《莊子》‘內圣外王’一語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極處,就是內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極處,就是外王。”[8]儒家道德由“自我”到“他者”的過程,無疑就是由“內圣”而“外王”的過程,“內圣”是“自我”的維度,做的是“修己的工夫”,而“外王”則是“他者”的維度,做的是“安人的工夫”。總之,在儒家的道德中“自我”與“他者”渾然融為一體,“自我”的道德修養最終也必然指向“他者”,通過道德行為實現著對他人的影響。這種道德“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在后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理念中得到了更精深的發揮,王陽明說:“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9]。如果說“欲行之心”關系“自我”的話,那么“行之始”必然指向“他者”,“知”與“行”的關系本質上表達的正是“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并且二者是融為一體的,“知”正是在日常待人接物的“行”中體現出來,道德的“自我”也正是在對待“他者”的過程中得以呈現。
三、“自我”與“他者”的張力
儒家從“自我”的維度出發,通過“推己及人”的方式,以道德行為來影響“他者”,不僅在理論層面具有自洽性,并且也在現實層面發揮著重大的作用,有效地處理著人際社會關系。這表明了儒家從“自我”到“他者”的道德體系具有極為強盛的生命力。然而,這是不是就說明儒家道德在從“自我”到“他者”的過程當中不存在任何問題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正是由于從“自我”到“他者”的“推”是一個由近及遠的過程,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種“差等之愛”,即對待不同的人“愛”的程度存在差異。甚至,在某些極端境況之下,“自我”與“他者”的利益存在根本對立沖突的時候,“推”的作用也往往失效。這一切都充分表明儒家道德中的“自我”與“他者”自始至終都存在著一種內在張力。
在儒家“推己及人”的道德體系中,“自我”與不同的“他者”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完全對等的,而是有次序差異的,正如荀子所言:“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荀子·君子》)正是由于存在著“貴賤”“親疏”“長幼”等種種差別,在“推己及人”的過程中必然產生對待不同“他者”的不同態度,這與墨家提倡“兼愛”,主張無分別地愛每一個人是截然不同的。費孝通先生認為:“其實在我們傳統的社會結構里最基本的概念,這個人和人往來所構成的網絡中的綱紀,就是一個差序,也就是倫。”[10]無疑,儒家道德所形成的人際網絡是具有差序性的,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要做到“愛人”,首先就要做到愛自己身邊的人,基于血緣親情來愛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就是“推己及人”的開端處,“老吾老”才能“以及人之老”,“幼吾幼”才能“以及人之幼”。這種根據與自身關系的遠近來逐步遞推的方式,自然就會產生一個問題,那就是與自己關系愈遠的人,這種遞推所產生的影響也就越小,人們將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與自己關系密切的人身上,尤其是放在血緣親情的關系之上,從而在某種意義上造成了“推己及人”的最終失效。也就是說,“推己及人”作為一種差序性遞推的方式,其主要的精力仍然是放在周圍人身上,費孝通先生曾經形象地把這種遞推效果比喻為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推出去的波紋,那么越往圈子的外圍這種影響力就越小。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正是這種遞推效果的生動表達,當一個人沒有能力推擴至“兼濟天下”的時候,那么他就只需要“獨善其身”,關心自己以及身邊的人就可以了。
其實,這種由近及遠的“推己及人”方式在孔孟那里就已經暴露出了其中的內在矛盾與沖突,集中體現為更近的“他者”與更遠的“他者”之間的矛盾沖突。何謂更近的“他者”?也就是與自己關系極為密切的他者,例如與自己有血緣親情關系的人;何謂更遠的“他者”?也就是與自己關系相對疏遠處于關系圈外圍的他者,例如彼此不熟悉的陌生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更近的“他者”即為一種變相的“自我”,比如我們經常在日常生活中講到的“自己人”。在孔子那里,“親親相隱”便是“自我”與“他者”沖突的集中體現,《論語·子路》中記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認為,即便父親犯了罪(偷了別人家的羊),作為兒子也應該替父親隱瞞,“推己及人”應該從與自己關系最為親密的人出發,很顯然在這種情形之下,父子之間從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自我”,而被偷羊的人便是“他者”。在孟子那里,同樣也存在這樣的問題,“竊負而逃”便是最為集中的體現:“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然,樂而忘天下。”(《孟子·盡心上》)孟子認為,舜的父親殺人之后,舜斷然放棄“天下”帶著自己的父親逃走是正當的。由此可見,某些特殊情境之中,儒家思想對血緣親情的關照遠遠壓倒了對整個社會的責任,這也預示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某種程度上的斷裂,“推己及人”在由“自我”到“他者”的過程中始終存在著某種緊張,具有一種內在的張力。
究其實質,儒家道德中“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緊張是“情”與“理”的沖突,我們知道儒家是以“情”為根基來構建整個道德體系的,盡管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夠實現既合乎“情”又合乎“理”,然而“情”與“理”又時常是不相容的,如前面提到的“親親相隱”以及“竊負而逃”。正是在處理“情”與“理”不相容的情況下,儒家道德陷入了一種內在矛盾,為了化解這種內在矛盾,儒家只能選擇認“情”為“理”,將“理”消融在了血緣親情之中。劉清平先生認為:“孔子哲學的主導精神是一種‘血親情理’精神,一種把血緣親情當作人們從事各種行為的終極之理的精神。”[11]而“血緣親情”未必就符合公理,儒家以血緣親情作為“推己及人”的基礎,這就注定了其無法圓滿解決“情”與“理”的沖突。其實儒家道德也并沒有否認“理”,只是在“情”與“理”只能選擇其一的時候,選擇了“情”舍棄了“理”,因為在儒家看來,“情”在整個道德體系中更具本根性,如果沒有了以“孝弟”為基礎的“情”,那么也就無法完成道德的推擴,至于“情”與“理”的沖突只能留待后人去解決。
儒家“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張力為儒家道德不斷發展完善提供了內在基礎,與此同時,儒家思想也并非一個封閉的系統,在與其他不同思想進行交流的過程中,儒家道德同樣也在完善自身,這是促使其發展的重要外部因素。與儒家處于同時代的墨家思想,就曾經針鋒相對地對儒家的“差等之愛”提出批判,主張“兼相愛”,也就是不分親疏貴賤無差別地對待每一個人。道家思想、法家思想也都分別從不同側面指出了儒家道德自身所存在的問題。道家思想認為儒家的“仁義”是“失道”之后的產物,莊子甚至認為“仁義”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謀取私利的手段,這從根源上指出了儒家道德以情感為基礎所導致的對公平性的損害,在道家那里“道”就代表一種客觀公平性。法家則進一步繼承發展了道家的思想,將道家帶有形而上色彩的“道”下落為現實具體可操作的“法”,主張不分親疏貴賤一律要按照“法”的標準來進行評判,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對儒家“差等之愛”的否定。這些不同學派的反對聲音也迫使儒家作出自己的回應,正是在這種回應的過程之中,儒家道德也在進行完善與發展。
如果說在先秦時期儒家對于當時不同學派各種反對聲音還是一種被動回應的話,那么現代新儒家們則是主動尋求化解儒家道德內在矛盾,開出民主與科學的方子,如牟宗三先生提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吾心之良知決定此行為之當否,在實現此行為中,固須一面致此良知,但即在致字上,吾心之良知亦須決定自己轉而為了別。……坎陷其自己而為了別以從物。”[12]究其實質,牟宗三的“良知的自我坎陷”就是為了解決儒家道德中“自我”與“他者”的矛盾與張力,就是他講的“亦須決定自己轉而為了別”,跳出道德“自我”的束縛而公正地面向整個“他者”。在當下,我們提倡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造性發展,儒家道德自然會被賦予更多新時代的內涵,其中“自我”與“他者”的內在張力正是我們對儒家思想進行發展的重要立足點,傳統儒家思想與當前生活的實踐相結合,儒家道德必然能夠獲得“日日新”的發展,從而充滿生機與活力。
四、結 語
儒家道德思想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為營造和諧的人際關系以及社會關系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家道德以“自我”之德性為根基,通過“推己及人”的方式,建立起“自我”與“他者”之間的聯系,構建起一套對現實生活影響深遠的倫理道德體系。“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問題是儒家道德所要處理的核心問題,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樣的道德教誨在當代社會依然沒有過時,依然是處理人際關系、社會關系甚至是國家關系的重要準則。然而,儒家道德也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與時俱進,回應時代的問題與挑戰,這就需要我們正視儒家道德中“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張力,從而化解儒家道德中不適應當代社會生活的部分,只有如此,儒家道德才具有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才能在傳承中得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