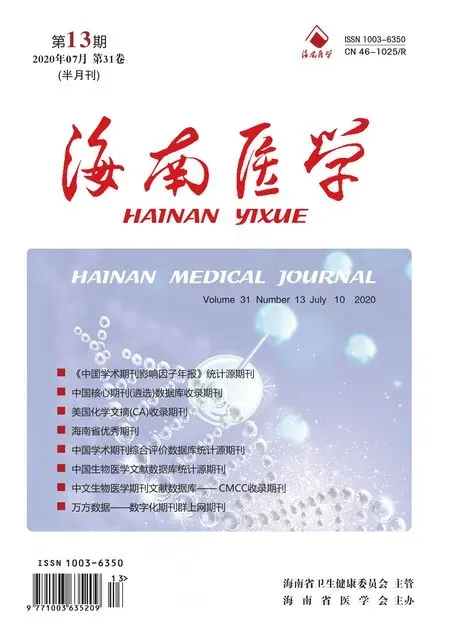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不良事件的臨床特征及風險預測的研究進展
張日光,陽柳 綜述 寧雪堅,陳紹俊 審校
1.廣西醫科大學第四附屬醫院腫瘤科,廣西 柳州 545005;2.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中醫醫院腫瘤科,廣西 柳州 545001
2011 年隨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Ipilimumab 獲批用于黑色素瘤的治療,開啟了腫瘤免疫治療的新時代。ICIs 已應用于腎癌、肺癌、結直腸癌、乳腺癌、淋巴瘤、頭頸部腫瘤等多種腫瘤的治療,且逐漸從晚期三線向一線、輔助治療推進。但是隨著臨床廣泛的應用以及新興的雙藥免疫聯合治療,免疫治療相關的問題如假性進展、超進展、療效預測、免疫治療相關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也 相 繼 涌現。irAEs 幾乎可以影響任何器官系統,常見的有胃腸道毒性(25%)、肺毒性(20%)、心臟毒性(10%)和肝毒性(10%)等[1],出現Ⅲ級以上的不良反應定義為嚴重irAEs。臨床試驗中報道與ICIs 治療相關的死亡率高達2%[2],而最近的一項回顧性研究表明,相比臨床試驗,現實世界的患者發生嚴重irAEs 的幾率更高[3]。因此在開始免疫治療之前識別和預測風險因素非常重要,如何預測相關不良事件是目前研究熱點,本綜述就ICIs 相關不良事件的臨床特征和風險預測的研究進展展開討論。
1 ICIs的類型
ICIs 主要包括程序性死亡-1/配體-1(specifically programmed cell death 1,PD-1/PD-1 ligand inhibitors,PD-L1)抑制劑和細胞毒性T 淋巴細胞抗原-4 (CTLA-4)抑制劑兩大類,不同藥物的irAEs 存在顯著差異。目前FDA批準的PD-1抑制劑有pembrolizumab、nivolumab、libtayo 三種,PD-L1 抑制劑有atezolizumab,durvalumab和avelumab,CTLA-4抑制劑只有Ipilimumab。研究表明結腸炎、垂體炎和皮疹在抗CTLA-4 治療中更常見,而肺炎、甲狀腺功能減退、關節痛和白癜風似乎更常見于抗PD-1治療。而聯合免疫治療相比于單藥PD-1治療,具有較高的毒性[4]。其中CTLA-4抑制劑相關毒性的發生率和致死率顯著高于PD-1/PD-L1抑制劑。一項Meta分析顯示CTLA-4抑制劑引起irAEs的發生率為53.8%,高于PD-1(26.5%)和PD-L1 (17.1%)[5]。毒性相關死亡率分別為CTLA-4 (1.08%),PD-1/PD-L1 加CTLA-4 (1.23%),抗PD-1(0.36%),抗PD-L1(0.38%)[6]。研究發現大多數irAEs發生在ICIs治療開始后3~6個月內,但延遲效應不能排除,有時在抗PD-1 治療開始后1 年內出現[7]。且irAEs 發生的風險似乎與CTLA-4 抑制劑呈劑量依賴性,而在PD-1抑制劑上未觀察到這一點[8]。這些可能與不同的ICIs類型作用機制不同有關。在敲除小鼠模型中反映出對兩種類型的反應差異,缺乏CTLA-4的小鼠死于淋巴細胞增殖,而缺乏PD-1的小鼠更多的出現自身免疫性疾病,例如關節炎和心肌病[9]。
2 臨床特征
2.1 腫瘤類型 不同的腫瘤免疫微環境不同,可能驅動組織學特異性的irAEs模式。在一項納入了48項ICI 單藥試驗、6 938 例患者的系統評價中顯示,與抗PD-1 治療的NSCLC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患者相比,黑色素瘤患者發生胃腸道和皮膚irAEs 的頻率較高,肺炎的發生率較低[10]。
2.2 腫瘤負荷 根據實體腫瘤的反應評估標準RECIST1.1 版本,腫瘤負荷定義為最多五個目標的最長直徑之和,其中每個器官最多兩個病灶[11]。之前的一項研究表明,治療前腫瘤越大,藥物誘導T細胞所需的活化反應越強[12]。由于相對較高的腫瘤負荷,可能更容易聚集活化的免疫細胞。NISHINO 等[13]研究發現NSCLC 患者的肺炎發病率高于黑色素瘤患者,推測與胸部腫瘤負荷大以及吸煙史和潛在肺部疾病相關。SAKATA等[14]回顧性分析了42例接受ICI治療的晚期NSCLC患者,發現高腫瘤負荷是嚴重irAEs的重要獨立預測因子,嚴重irAEs 和腫瘤負荷超過90 mm的比值比為8.62(95%CI=1.96~37.9,P=0.004)。
2.3 基礎疾病 JOHNSON等[15]的研究報道在患有預先存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黑色素瘤患者中,50%接受ipilimumab 治療的患者發生了潛在疾病或irAEs的發作。LEONARDI等[16]研究納入56例既往存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肺癌患者接受ICI 治療,其中55%發生了潛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虹膜炎,盡管大多數事件是輕微的。一項來自日本的回顧性分析提示預先存在的肺纖維化是NSCLC 患者抗PD-1 相關性肺炎的危險因素[17]。KIMBARA 等[18]也發現在接受nivolumab治療的168例晚期實體瘤患者中,具有預先存在的甲狀腺抗體和基線TSH 升高的患者甲狀腺功能irAE 風險升高。KEHL 等[19]回顧性分析了4 438 例接受ICI 治療的患者,通過嚴格標準和放松標準分別篩選了179例(4%)和283例(6%)合并預先存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結果發現都與irAEs 診斷住院治療和皮質類固醇治療相關。這些研究都表明患有基礎疾病的患者發生irAEs的風險升高。可能這些患者體內具有潛在抗原,而腫瘤新抗原和正常組織抗原可能是交叉反應的,導致了irAEs的發生[20]。
2.4 臨床獲益 多項研究表明,患有更多irAEs的患者也有更高的反應率。在出現甲狀腺功能irAES的受試者中,pembrolizumab的總體存活率顯著延長[21]。NSCLC患者出現免疫相關皮膚、甲狀腺功能irAEs也與治療療效有關[22]。HARATANI等[23]最近對134例接受Nivolumab 治療的NSCLC 患者的回顧性研究發現,irAEs的發展與總體存活率增加有關。一項關于頭頸部鱗狀細胞癌的研究也表明治療反應與嚴重的irAEs有關[24]。
2.5 放射組學 放射組學是一個新興領域,它是從標準醫學圖像中自動提取高保真、高維成像特征,并允許對組織和相應的微環境進行全面的可視化表征[25]。COLEN等[25]為每位接受ICIs的患者提取了1 860 個放射學特征,驗證確定了不同的放射學特征能預測免疫治療誘導的肺炎[準確性100%(P=0.003 3)]。
3 生物標志物
3.1 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NLR、PLR 很多研究表明,基線時的高嗜酸性粒細胞計數與ICIs治療反應 和OS 呈 正 相 關[26-28]。NAKAMURA 等[29]研 究 發 現基線時絕對嗜酸性粒細胞計數>240/μL,1個月時相對嗜酸性粒細胞計數>3.2%可能是預測接受PD-1 抑制劑治療相關內分泌irAEs的有用生物標志物。NLR和PLR 是指中性粒細胞、血小板分別與淋巴細胞的比值。FUJISAWA 等[30]回顧性分析了來自日本8 個研究所的101例接受ICIs的黑色素瘤患者,顯示G3/4 irAEs與總白細胞計數增加和相對淋巴細胞計數減少相關。而最近的一項研究評估了連續使用ICIs 治療的184例NSCLC患者,發現基線時的低NLR和低PLR與irAE的發展顯著相關[31]。
3.2 T 細胞庫的早期多樣化 OH 等[32]評估了用Ipilimumab治療的轉移性去勢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循環T細胞的全集,發現T細胞庫的早期多樣化和新克隆的產生與irAEs的發展相關。具體而言,與沒有irAEs的患者相比,Ipilimumab不是將T細胞庫縮小到有限數量的克隆,而是誘導irAEs患者的T細胞庫更多樣化。
3.3 全血mRNA 轉錄物 FRIEDLANDER 等[33]從210 例接受CTLA-4 抑制劑Tremelimumab 治療的黑色素瘤患者中,鑒定出16 個基因的特征(CARD12、CCL3、CCR3、CXCL1、F5、FAM210B、GADD45A、IL18bp、IL2RA、IL5、IL8、MMP9、PTGS2、SOCS3、TLR9 和UBE2C),通過這16個基因特征可以識別區分出2~4級和0~1 級腹瀉/結腸炎患者(95%CI 0.723~0.838,P<0.000 1),敏感性為57.1%,特異性84.4%。其中五個基因:IL-8、CCR3、CCL3、CXCL1及MMP-9與ICIs以外的病因引起的腹瀉有關。比如在食物過敏原誘導的GI嗜酸性粒細胞炎癥的小鼠模型中,阻斷CCR3 的表達可以降低腹瀉、嗜酸性粒細胞炎癥和黏膜損傷的嚴重程度[34]。鑒于Tremelimumab還未獲批,其調節免疫系統的方式不同于Ipilimumab,基于不同藥物治療條件下16基因標記的預測值很可能會有所不同。
3.4 細胞因子 TARHINI等[35]評估了與Ipilimumab作為新輔助治療的黑素瘤患者的irAEs相關的細胞因子,發現基線時IL-17水平與3級腹瀉/結腸炎irAEs的發生率顯著相關。TANAKA等[36]、OKIYAMA等[37]發現Nivolumab治療后IL-6的增加與irAEs的發展顯著相關。
3.5 人白細胞抗原(HLA)等位基因 HLA 編碼細胞表面分子將抗原肽呈遞給T細胞上的T細胞受體(TCR)。Ⅰ類和Ⅱ類HLA等位基因是多種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重要遺傳風險因素[38]。特別是HLA 等位基因已經為自身免疫的發病機制提供了明確的模型,例如類風濕關節炎(RA)[39]。CAPPELLI等[40]對26例ICIs誘導的有歐洲血統的炎性關節炎患者和726名健康對照者進行高分辨率HLA分型。在220個RA病例上進行共享表位(SE)基因座(HLA DRB1)的基因分型。觀察到SE 等位基因的存在與ICI 誘導的炎性關節炎之間存在潛在的風險關聯。
3.6 腸道微生物 腸道微生物可以通過免疫調節機制調節免疫應答。糞便微生物群移植(FMT)即遠端腸道微生物群落從健康個體轉移到患者腸道可以治愈一些免疫紊亂(主要是炎性腸病)[41]。DUBIN 等[42]研究表明屬于擬桿菌門的細菌的增加與Ipilimumab 誘導的結腸炎的降低率相關。隨后CHAPUT 等[43]對26 例接受Ipilimumab 治療的前列腺癌患者進行了前瞻性研究,在基線和每次Ipilimumab 輸注之前使用16SrRNA 基因測序評估糞便微生物群組成,他們發現微生物群存在擬桿菌的患者都沒有出現結腸炎irAEs。
4 展望
免疫治療已經成為腫瘤治療的新模式,irAEs 是這種治療模式下面臨的新的挑戰。與細胞毒性化療相比,ICIs 的治療反應模式是獨特的,其相關的irAEs通常具有發作延遲和持續時間延長的特點,并且有效的管理依賴于早期識別和快速干預免疫抑制和/或免疫調節策略[44]。免疫毒性的確切發病機制尚不清楚,可能與解除T 細胞抑制后,活化的T 細胞對抗正常的宿主細胞有關,據報道其中涉及許多其他炎性細胞,例如Th17和其他類型的細胞。故臨床報道療效好、腫瘤負荷大的發生irAEs 幾率高,可能與負責ICIs 治療效果的機制交叉重疊相關。
盡管有所不足,目前已經有許多ICIs 的療效預測標志物得到了公認和推廣,如PD-L1 表達水平、腫瘤突變負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TMB)、錯配修復(mismatch repair,MMR)基因表達狀態。而預測irAEs的生物標志物報道較少,一般都是回顧性小樣本研究,且很多研究的對象僅包括治療應答者,其中可能存在選擇性偏差,故目前還沒有公認的毒性預測標志物。應該鼓勵多中心、大樣本、前瞻性的研究,為irAEs的早期識別提供新數據和證據。
總之,未來應該綜合ICIs類型、腫瘤原發病、腫瘤負荷、基礎疾病、臨床獲益、外周血、細胞因子、mRNA、T細胞庫、HLA等位基因、腸道微生物等多因素開發臨床irAEs風險模型,識別高風險患者,進行個體化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