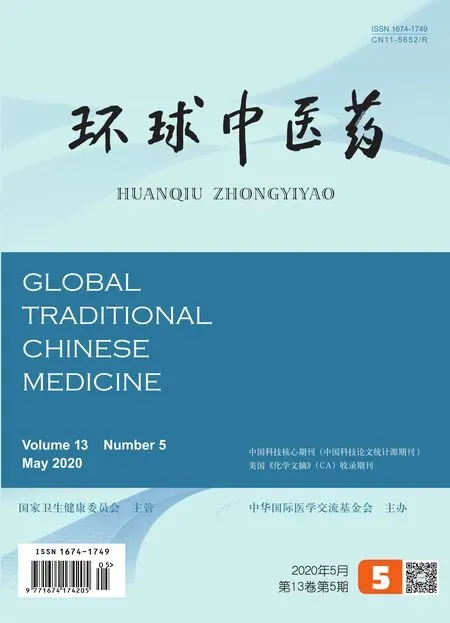脾氣虛證與神經內分泌相關的生化指標的關聯性研究概述
南夢蝶 程諾 賀倩 劉遠歐 劉玥蕓
脾氣虛證是由于脾氣虛弱,脾失健運而出現的以食少、腹脹、大便溏薄、神疲、肢體倦怠、舌淡脈弱等為常見癥的證候[1]。脾氣虛證常見于泄瀉、胃脘痛、水腫、痰飲、痿證、小兒疳積,以及西醫的慢性胃腸炎、慢性腎炎、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等疾病,在不同疾病中有不同表現。近年來,大量研究表明脾氣虛證會引起多系統多指標的改變,包括腦腸肽、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指標、能量代謝指標,以及酶學改變、腸道菌群紊亂等[2-4]。本文在通過中國知網(CNKI)檢索對脾氣虛證神經內分泌系統指標方面進行研究的實驗類文獻,比較與分析研究現況,并展望今后研究趨勢。
1 腦腸肽在脾氣虛證狀態下有明顯變化
胃腸激素是胃腸道(包括胰腺)中的內分泌細胞分泌的特殊化學物質,作為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中的一部分,與其他成分如細胞因子、化學遞質等共同發揮作用,影響著胃腸道的運動,維持著機體正常的生理功能。胃腸激素中,既存在于胃腸道又存在于腦中,被稱為腦腸肽,胃泌素(gastrin,GAS)、胃動素(motilin,MOT/MTL)、膽囊收縮素(cholecystokinin,CCK)、P物質(substance P,SP)、生長抑素(somatostatin,SS)、神經降壓素等均屬腦腸肽,腦腸肽在腦中由神經細胞合成,沿神經纖維傳遞到神經末梢釋放,調節神經支配的細胞活動。對胃腸運動起促進作用的有GAS、MOT/MTL等,抑制胃腸運動的有生長抑素、血管活性腸肽、CCK。研究發現,脾失健運與腦腸肽分泌水平紊亂密切相關。探討脾氣虛證與腦腸肽的關系,對深入認識脾氣虛證本質,尋找脾虛失健運的特異性、客觀性的定量性指標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際意義。
現有脾氣虛證研究涉及的腦腸肽有GAS、MOT/MTL、β-EP、SS、血漿降鈣素基因相關肽(caleitonin gene related peptide,CGRP)、神經肽Y(neuropeptide Y,NPY)、SP和生長素等。
1.1 GAS、MOT/MTL、生長素在脾氣虛證狀態下減少
魏彥明等[5]測得脾氣虛模型家兔血清GAS顯著降低。溫慶祥等[6]、劉鉞等[7]對脾氣虛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采用手法、隔藥灸治療后血清GAS明顯高于治療前,反向說明了脾氣虛狀態下GAS降低。多數動物模型研究[8-12]與此有類似結果。而研究結果與之相反的有:王小榮[13]、呂凌[14]得到脾氣虛大鼠模型GAS反而顯著升高。王洪海[15]研究結果表明GAS變化隨時間波動:脾氣虛證大鼠GAS第三周下降、第四周上升。呂琳等[16-17]、李楷[18]研究結果表明GAS變化因樣本不同而不同:脾氣虛證大鼠模型GAS在血清中含量降低,在下丘腦、胃、小腸中含量升高。
部分實驗研究年代已較久[5-8,11-15],所應用的檢測手段如放射免疫分析(radioimmunoassay,RIA)及其精準度也與近來研究[16-18]所用酶聯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 sorbent assay,ELISA)、免疫組化法等存在一定差異,且GAS在體內各組織中有不同活性形式,檢測時注意到不同亞類需要用到各自的抗體才能得到對于在脾氣虛證狀態下GAS含量變化趨勢更具價值的結論。
多數研究表明,MOT在脾氣虛證患者血清中出現下降趨勢[6,7,19],部分動物脾氣虛證模型研究[8-9,11-12,20]結果與此相似。劉凱[21]研究還發現脾氣虛證模型大鼠離體胃竇平滑肌對MTL引起的收縮反應敏感下降,下丘腦中MTL含量也有下降。王洪海[15]研究結果表明MTL變化隨時間波動:脾氣虛證大鼠MTL第三周下降、第四周上升。然而,也有研究表明MOT在脾氣虛狀態下出現上升趨勢。陳銳[10]、趙鋒[22]采用利血平注射液腹腔注射14天建立脾虛家兔模型,RIA法檢測血清MOT,造模后與對照組相比,MOT明顯上升,穴位埋線、捏脊治療或四君子湯治療后恢復到原來水平。
與GAS類似,MOT在調節胃腸道功能方面有正面的調節作用,較多研究[6-12,15]兼具兩者變化含量的檢測,故在研究檢測手段上均存在不一致性的局限性。值得一提的是,個別研究[21]不僅報告了脾氣虛狀態下MOT的含量變化,還對于脾氣虛狀態下靶器官對其敏感程度的降低也進行了分析。
脾氣虛證狀態下,中樞神經系統通過腦腸神經影響腦腸肽的分泌合成[23-27],一些研究表明脾氣虛證動物模型的下丘腦和胃腸道組織中生長素含量下降[25-27],其受體表達也有下調[26]。而楊可新[28]的研究提示脾氣虛證大鼠模型的血漿生長素含量反而明顯升高。
同上,個別研究[28]在造模方式上的明顯不同可能對生長素含量帶來不同影響,雖然同屬脾氣虛證動物模型,但也不除外疾病模型(慢性腎衰模型)因素對證型研究結果的干擾。
1.2 SS、CCK在脾氣虛證狀態下增加
張航向[19]RIA法檢測脾氣虛證患者血漿及胃竇SS含量明顯高于胃熱證、肝火上炎證患者。陳天娥等[29]用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檢測到脾虛證胃潰瘍模型的胃黏膜中SS陽性細胞分泌活性增強。多數動物模型研究[8,11-12,30]均表明脾氣虛狀態下,血或腸道組織中SS含量上升。呂琳等[16]研究表明SS的變化具有組織差異性,脾氣虛模型組垂體、血、胃、腸組織中的SS含量明顯高于對照組,而下丘腦低于對照組。陳旻丹[27]研究亦發現結腸平滑肌SS表達降低,而下丘腦神經細胞中SS表達無明顯差異。然而,楊可新[28]研究結果提示脾氣虛狀態下SS含量可能出現下降。
大部分文獻的方法學優勢及局限性同前。張航向[19]將脾氣虛證與其他證型患者對比而非與健康對照對比,難以明確SS的增加是否為脾氣虛證狀態下會出現的特異性改變。
多數研究表明脾氣虛狀態下,組織中CCK含量上升。脾氣虛組患者血漿和胃竇CCK明顯高于胃熱組[19],脾虛證模型大鼠下丘腦及結腸粘膜中CCK-8含量高于正常組[30]。與此類似,多數動物模型研究[23,26,31]表明在下丘腦、胃腸道、血清中CCK含量升高。而陳旻丹[27]研究表明CCK表達可能下降。但劉芳等[32]研究表明CCK隨時間推移而先上升后下降。
關于CCK的研究結論相對較新,來源包括臨床研究和實驗研究,故可以推測脾氣虛證狀態下,CCK在一定時間內各組織中均表現下降趨勢。
1.3 β-EP、VIP、SP在脾氣虛證狀態下變化不一
研究結果表明,β-EP變化因樣本不同而不同:呂琳等[16-17]用耗氣破氣中藥灌胃加饑飽失常法建立脾氣虛證大鼠模型,模型組β-EP在下丘腦、垂體、血漿中含量降低,在胃、小腸中含量升高。多數動物模型研究[8,18,23]與此有類似結果。而在魏彥明等[24]對脾氣虛雄性大鼠模型的研究中,血漿β-EP極顯著升高,四君子湯治療后恢復。
應指出的是,部分文獻[16-17]均來源于同一研究團隊時,研究結果一致性并不能完全代表可重復性。個別研究[24]有明顯不同的研究結果,但不除外其應用的造模方式(利血平注射法)與其余研究均有較大差異(耗氣中藥灌胃法、饑飽失常法等)可能造成干擾。
陳天娥等[29]用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得到,脾氣虛證胃潰瘍動物模型的下丘腦、大腦皮層和海馬等部位VIP陽性神經元分泌活性增強。陳倩[33]對脾氣虛患者的得出的回顧性結論表明脾氣虛狀態下血VIP升高。部分脾氣虛證動物模型研究表明[11-12,23,26],下丘腦、胃腸道、血清中VIP含量升高。與此相反,劉凱[21]研究表明,脾氣虛模型大鼠離體胃竇平滑肌對VIP的舒張作用反應敏感性下降,且平滑肌中VIP含量明顯降低。部分研究[27,31]得到與此類似的結論。
通過總結以上研究,難以得出與其他抑制性腦腸肽類似的結論,即VIP在脾氣虛狀態下呈增高趨勢。通常認為,回顧性研究所提供結論的可信度一般。其余實驗類文獻的造模方法類似,檢測手段明確,取材組織類似,而結論不一,可見VIP在脾氣虛證狀態下會出現一定變化,但其表達及作用效應是否會與其他調節因子發生相互作用尚待進一步明確。
不同研究表明,脾氣虛證狀態下SP含量可有不同的變化。陳倩[33]對脾氣虛型腸易激綜合征患者采用隔藥灸法,治療后血清SP均明顯下降。陳天娥等[29]研究提示亦其含量增加(脾氣虛證胃潰瘍模型中SP陽性細胞分泌活性增強)。而陳旻丹[27]研究提示其在不同組織內的變化趨勢不同,功能性腹瀉脾氣虛證大鼠模型結腸平滑肌細胞SP表達顯著減少,下丘腦神經細胞SP表達顯著增加。而其他研究如馮曉帆等[34](下丘腦和海馬)、李楷[18](海馬及小腸組織)均檢測到SP顯著減少。
大部分文獻的方法學優勢及局限性同前。脾氣虛證狀態下SP含量在各組織中的變化以及與其他調節因素的相互作用尚待進一步明確。
1.4 CGRP、NPY、5-羥色胺(5-hydroxytryptamine, 5-HT)、促胰液素(secretin, Sec)、亮氨酸-腦啡肽(leucine-encephalin, L-EK)在脾氣虛證狀態下的變化有待研究
魏彥明等[24]用RIA法檢測到脾氣虛大鼠的CGRP升高、NPY降低。龍奕文[25]的研究也發現脾氣虛證模型大鼠的血NPY的含量下降。陳旻丹[27]檢測功能性腹瀉脾虛證大鼠結腸平滑肌和下丘腦神經細胞中CGRP含量及表達mRNA的含量,分析得到CGRP的表達在結腸平滑肌細胞中降低,在下丘腦神經細胞中升高。陳倩[33]在脾氣虛型腸易激綜合征患者采用隔藥灸法治療后,檢測到血清5-HT明顯下降。李楷[18]用ELISA法檢測到脾氣虛大鼠模型海馬及小腸Sec含量顯著降低。李剛[35]用RIA法檢測脾氣虛證大鼠模型L-EK含量,血清L-EK顯著降低,額葉皮質、下丘腦、垂體L-EK水平顯著升高。
總結以上對脾氣虛證狀態下腦腸肽的研究可以發現,不同研究中腦腸肽受到脾氣虛證影響而發生的變化并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難以僅通過文獻學習而確定脾氣虛證特異性的腦腸肽改變。究其原因可能:一是脾氣虛證狀態下,為糾正胃腸道功能狀態,各種腦腸肽均有波動,組織性質(神經系統組織、胃腸組織、血液樣本)不同、時相(脾氣虛證出現時間、生物鐘)不同、腦腸肽之間協同拮抗關系復雜,但卻少有研究相互比較各種胃腸道對腸胃功能調節的作用差異;二是從檢測手段方面考慮,僅一類腦腸肽下就有多種分子形式,不同分子形式如果僅用一種抗體來檢測,不論用RIA、免疫組化還是ELISA等檢測方法,其結果不夠嚴密。
2 神經調節相關指標在脾氣虛證狀態下有不同程度改變
神經調節是在神經系統的直接參與下所實現的生理功能調節過程,是人體最重要的調節方式。脾氣虛證以食少、腹脹、大便溏薄、神疲、肢體倦怠為主要特點,尤其以胃腸道表現為突出,胃腸道由中樞神經系統、腸神經系統和自主神經系統共同支配,神經系統調節紊亂,因而在一系列指標上出現相應改變,如神經細胞成分、神經遞質等。
2.1 自主神經系統功能在脾氣虛證狀態下出現明顯紊亂
探究脾氣虛證在自主神經系統方面影響的研究常以乙酰膽堿(acetylcholine,Ach)或膽堿酶(acetylcholinesterase,AchE)、環磷酸腺苷(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cAMP)和環磷酸鳥苷(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cGMP)等為研究內容。魏彥明等[5]用間苯三酚顯色法測得脾氣虛證家兔血清AchE升高。祝淑貞[36]檢測脾氣虛證患者的血清AchE活性低于正常水平。脾氣虛證動物模型血漿cAMP含量升高、血漿cGMP無明顯變化、cAMP/cGMP比值升高[37-38]。張廣霞[8]測得脾氣虛模型組血清Ach降低、cAMP降低、cGMP升高、AchE升高,ELISA法測得骨骼肌乙酰膽堿受體M2受體降低。神經遞質(如Ach)可以通過激活G蛋白、激活腺苷酸環化酶(adenylate cyclase, AC)、催化ATP轉化成cAMP,cAMP進一步激活蛋白激酶(proteinkinase A, PKA),引起級聯反應或陽離子通道的開放。
脾氣虛狀態引起Ach降低、cAMP/cGMP比值升高,這表明脾氣虛模型植物性神經功能的異常,即交感神經功能低下和副交感神經功能偏亢,故產生涎多、腹痛、便溏等表現。但是cAMP/cGMP比值升高在脾氣虛證動物模型研究中并不統一。自主神經功能紊亂可影響胃腸平滑肌[5]、骨骼肌功能、體溫調節[8],可使機體表現出腸鳴腹瀉、乏力倦怠等脾氣虛證常有表現,目前還未見對于脾氣虛證狀態如何影響自主神經功能紊亂進而引起Ach、cAMP、cGMP水平變化的深入研究。
2.2 中樞神經系統功能在脾氣虛證狀態下出現不同程度紊亂
脾氣虛證對中樞神經系統的邊緣系統如海馬、側腦室以及下丘腦有一定影響,現僅有關于蛋白激酶C(proteinkinase,PKC)、去甲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NE)、5-羥基吲哚乙酸(5-hydroxyindole acetic acid,5-HIAA)、高香草酸(homovanillic acid,HVA)、3,4-二羥基苯乙酸(3,4-dihydroxy-phenyl aceticacid,3,4-DOPAC)、多巴胺(dopamine, DA)和堿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FGF)cAMP效應元件結合蛋白(cAMP 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CREB)等的研究。王淑娟[39]采用改良Takai法檢測到脾氣虛大鼠模型海馬組織的膜PKC活性升高、胞漿PKC活性明顯降低,衰老大鼠更明顯。王洪海[15]發現脾氣虛證模型組大鼠海馬的各項單胺類神經遞質如5-HT、NE、5-HIAA和HVA建模3周時明顯降低,3,4-DOPAC逐漸下降,而DA水平明顯升高,且與大鼠嗜睡、倦怠、少動的行為表現相關。卓緣圓[40]觀察到脾氣虛證大鼠側腦室下區、海馬齒狀回區被溴脫氧尿苷標記的神經干細胞受損,檢測到兩個腦區bFGF的表達增加。李楷[18]測得脾氣虛大鼠的海馬及小腸組織cAMP/PKA-CREB信號通路中cAMP、PKA的CREB的相對表達量降低。脾氣虛大鼠下丘腦葡萄糖轉運體1、葡萄糖轉運體3表達水平下降,與下丘腦、胃、空腸中的β-EP、CCK、VIP表達水平異常有相關性[23]。
多數文章來源于新近研究,且利用免疫組化標記的切片觀察或組織勻漿研究相關指標改變,檢測方法明確,造模手段成熟。但每項指標的同類研究較少,個別研究[15,18,23]同時對脾氣虛證狀態下腦腸肽的變化進行研究,并認為各信號通路的改變與腦腸肽變化存在相關性,但其變量過多,故結論的參考價值有待商榷。
2.3 腸神經系統功能在脾氣虛證狀態下明顯受損
劉凱[21]、丁伯龍[41]使用免疫組化法檢測到脾氣虛證模型大鼠胃腸各部位的神經型一氧化氮合酶增加,提示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的抑制作用增強。消化道的Cajal間質細胞(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ICC)是腸道慢波的起搏細胞,與腸神經系統末梢和平滑肌細胞構成胃腸運動的基本功能單位。丁伯龍[41]觀察到脾氣虛大鼠模型幽門、降結腸組織中神經纖維數量明顯降低,腸神經-ICC之間信號通路損傷,Ach、SP、VIP、NO、蛋白基因產物9.5和神經纖維數量明顯降低,提示腸肽分泌及腸神經功能均降低。趙璠[42]通過動物實驗發現脾氣虛大鼠小腸組織M2受體表達增多、控制平滑肌收縮的M3受體表達下降,抑制M2受體介導的陽離子內流,使小腸平滑肌收縮幅度變小,從而引起小腸運動減慢。宋囡等[43]測得脾氣虛證大鼠胃組織cAMP-PKA-CREB途徑整體均有下調。而中藥健胃合劑[44]能通過增加乙酰膽堿轉運蛋白、乙酰膽堿受體M1加快胃腸運動。
3 下丘腦-腺垂體系統在脾氣虛證狀態下出現功能紊亂
下丘腦-腺垂體系統通過神經-體液性聯系,即下丘腦促垂體區的肽能神經元通過所分泌的肽類神經激素(釋放激素和釋放抑制激素),經垂體門脈系統轉運到腺垂體,調節相應的腺垂體激素的分泌,進而影響靶器官(性腺、腎上腺、甲狀腺)的功能。
脾氣虛狀態下,下丘腦-垂體-性腺軸功能紊亂,現有研究對血清孕激素(progesterone,P)、雌二醇(estradiol,E2)、睪酮(testosterone,T)含量變化的研究結果不一致。黃雪琪[45]脾不統血證雌性大鼠模型E2下降,P升高。李志強等[46]的脾氣虛雄性大鼠血清E2上升、T下降。王立峰[37](脾氣虛雄性大鼠)、馬媛媛[38]檢測到血清E2、T均升高。王昕等[47]檢測到脾氣虛雄性大鼠血清E2、T下降。由此可以認為脾氣虛證會導致丘腦-垂體-性腺軸功能紊亂,但是考慮到性激素的周期性變化,無法確定性激素調節紊亂與脾氣虛證單一因素有關。
現有的脾氣虛證動物模型研究[15,37,48]的結果表明,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和皮質醇濃度均有不同程度降低,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功能減弱。
下丘腦-垂體-甲狀腺軸相關方面研究較早就集中出現。大量重復類型的實驗研究促甲狀腺素釋放激素(thyr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TRH)、促甲狀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三碘甲腺原氨酸、四碘甲腺原氨酸等指標的結果提示,脾虛狀態下甲狀腺功能降低[8,15,37-38,46, 49-50]。而甲狀腺功能低下又會進一步導致胸腺[51]、淋巴細胞等免疫器官和細胞的變化。脾氣虛證動物模型研究[35]提示L-EK可在中樞神經系統胺類遞質介導下,減少TRH、TSH釋放。
4 水鹽代謝相關激素及受體在脾氣虛證狀態下表達改變
脾主運化水濕,對其現代生物基礎的研究則著眼于抗利尿激素(antidiuretic hormone,ADH)和醛固酮(aldosterone,ALD)及其作用靶點,如水通道蛋白(aquaporin, AQP)等。張廣霞[8]RIA法檢測到脾氣虛大鼠模型血清ADH、ALD升高,ELISA法測定小腸及降結腸的AQP3降低、腎臟的AQP2含量升高。崔永霞[20]用免疫組化法測定回腸中AQP4,脾氣虛證大鼠模型回腸AQP4表達明顯減少,十二指腸中胃蛋白酶明顯減少。AQP4在結腸表達最豐富,小鼠剔除相關基因后,結腸水通透性下降,糞便含水量增加[52]。水鹽代謝和水轉運方面的調節異常,在水液調節方面為脾主運化水液的中醫理論提供指標依據。腸段AQP3低表達可引起結腸粘膜對水重吸收減少導致腹瀉便溏,符合脾虛不運,水濕內停的中醫證候病機。
5 其他指標在脾氣虛證狀態下的改變有待研究
段永強[11]檢測脾氣虛證大鼠血清胰島素、空腹血糖水平明顯下降。姜曉琳[53]用ELISA法測得脾氣虛大鼠模型血清及心肌中腦鈉肽和cAMP含量均明顯升高,用PCR檢測到心肌細胞bFGF和PKA的表達水平明顯升高。有關胰島和心肌細胞在脾氣虛證狀態下的分泌功能的臨床研究較為孤立,尚不足以確定有價值的結論。各項研究對于指標變化與脾氣虛證表觀癥狀和體征的關聯性的分析水平仍停留在推測其作用機制(如抓握力減退與骨骼肌Ach受體數量[8],單胺類遞質和倦怠少動[15],NO含量,Ach及受體與便溏[21]等),缺乏統計學上確鑿的證據。
6 總結與展望
探究脾氣虛證對神經-內分泌系統影響的實驗研究中,涉及腦腸肽的指標占多數,其余指標占比重較大的為中樞神經系統指標、下丘腦-垂體-腺體(性腺、甲狀腺、腎上腺)軸指標和植物神經功能指標。部分實驗將以上指標進行綜合研究后認為,脾氣虛證狀態下神經系統的遞質[21]、受體及細胞通路[18,23,41]與腦腸肽或與其他激素[20,35]均有相互作用。此外,脾氣虛動物模型各組織中酶學改變[11]、肌肉能量代謝相關信號通路[26]均與腦腸肽水平變化有關。可見,脾氣虛證狀態下,腦腸肽在各組織中的表達水平受到多方面因素影響而出現不同程度的改變,而且這種改變與其他神經內分泌調節的指標的變化具有相互作用,這其中的某些改變可以解釋部分脾氣虛證常見的體征和癥狀表現。動物實驗研究大部分造模方式大同小異,但部分研究模糊了脾氣虛證、脾陽虛證甚至是脾腎兩虛證的區別,還有一些研究的造模方法的合理性有待考量,推測這些研究與大多數研究得出不同結論[10,22]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造模方法的差異性。對照的設置上,大部分研究設置了空白對照組、各類治療手段(健脾補氣藥物、灸法、電針、埋線、捏脊)組和(或)自然恢復組進行對比相關指標。大部分治療組均在某些指標上相對于脾氣虛證模型組有恢復正常指標的趨勢,可以定性推測指標變化與脾氣虛證有一定的相關性,但由于干預措施的形式多樣,難以實現定量分析各指標的特異性或敏感性。早期文獻未關注到脾氣虛證模型各指標的水平變化具有時效性,后期的研究中還因此設置不同時間段檢測模型組別,部分指標在造模后一定時間內經歷先異常后正常的變化趨勢,但指標恢復正常趨勢開始的時間并不一致,難以確定先異常后正常的機制是否與代償性或適應性變化或其他未知因素相關。早期研究多單純對血樣或組織切片中有限個數的各物質指標含量變化進行報道,現階段已有著眼于細胞信號通路、基因表達調節通路在脾氣虛證狀態下所發生改變而進行的探索性研究。臨床研究數量較少,大部分臨床研究的方法學質量較低,均為小樣本量單中心研究,從對照組設置方面,僅有個別研究與健康受試者進行對比,或僅對脾氣虛證狀態下的指標改變做回顧性分析,涉及的指標集中而且亦較少,采集的數據有限,未與其他神經內分泌系統指標進行多因素分析,臨床研究的設計方面亟待更健全的方案以揭示脾氣虛證的生物學基礎。此外,盡管存在少數實驗類研究會以不同方劑對于不同指標及相關體征的影響為側重,但是大多數揭示針對脾氣虛證的癥狀和體征,如腹脹、便溏、神疲、乏力,還需要更多的研究探索出癥狀特異性的指標及其變化方向。
以腦腸肽為主,神經內分泌調節相關的指標在脾氣虛證狀態下存在表達水平的改變,這種改變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相互交叉、相互滲透形成復雜的神經內分泌調節網絡系統,有待于學者們的進一步深入嚴謹研究才能揭示。傳承數千年的中醫辨證論治思維體系具有多層次多途徑的特征,神經內分泌調節網絡的復雜機制與中醫的整體觀存在一致性,因此在調控神經內分泌的指標表達水平的過程中發揮中醫藥優勢、闡明中藥治療脾氣虛證的作用靶點和相關機制是值得關注的方向。以上內容是基于神經內分泌調節相關指標探討中醫藥治療脾氣虛證的實驗研究和臨床研究綜述,相信隨著學者們對脾氣虛證狀態下神經內分泌調節網絡認識的不斷深入,將會涌現出更多的精確至生物分子網絡層次的研究,為闡明脾氣虛證的生物學本質作出有益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