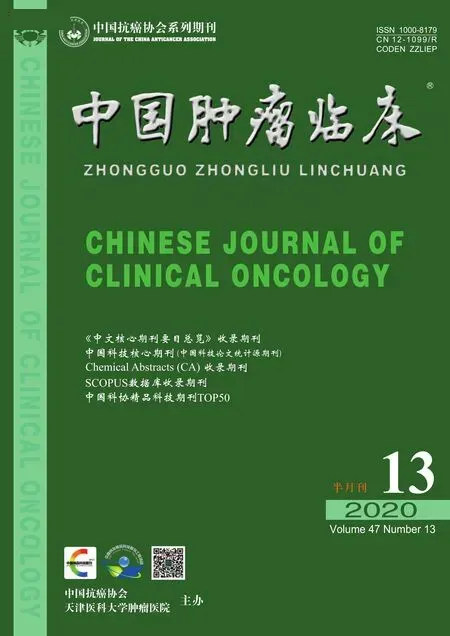Castleman病的臨床病理特征及可能的發病機制*
Castleman 病(Castleman disease,CD)是一類較為少見的淋巴組織增生性疾病,具有高度臨床異質性。特征性病理表現包括萎縮性或增生性生發中心、顯著的濾泡樹突狀細胞及血管形成、多克隆淋巴細胞增生和(或)多型性漿細胞增多癥[1]。CD既往曾被命名為巨大淋巴結病、血管淋巴錯構瘤或血管濾泡淋巴結增生。CD的致病機制不詳,具有與病毒、腫瘤及免疫等疾病相重疊的臨床表現及病理特征,使得該疾病易與其他疾病相混淆。本文總結近年來報道的CD 最新發病機制,包括CD 發病機理中涉及的病因、細胞類型、信號傳導途徑及效應細胞因子,旨在加深對該疾病的認識。
1 CD的分類及特征介紹
CD 在臨床表現和病理特征上存在巨大的異質性,從組織病理學特征的腫大淋巴結區域出發,根據臨床表現可將CD 患者分為單中心型(unicentric CD,UCD)和多中心型(multicentric CD,MCD)。UCD通常發生在20~30歲人群,發病率相對較高,涉及單個腫大淋巴結或淋巴結區域,癥狀輕,預后好,手術切除通常可以治愈。MCD 常發生于40~60 歲人群,發病率相對較低,累及多個腫大淋巴結區域,反復出現全身癥狀(體質量減輕、發熱、疲勞)、貧血、水腫、低蛋白血癥,并可累及多個重要臟器,如肝、脾、腎等,預后較UCD差[2]。
根據組織病理學特征,CD 可分為透明血管型(hyaline vascular,HV)、漿細胞型(plasma cell,PC)和混合型。HV 主要表現為生發中心退化和明顯的濾泡樹突狀細胞增生;PC 主要表現為生發中心增生及濾泡間區漿細胞增殖;混合型的組織學特征則介于上述兩型之間;3種病理類型均可見血管插入生發中心[3]。這些組織病理學特征并非CD 中所獨有,在其他疾病中也可以觀察到[4],如系統性紅斑狼瘡、類風濕關節炎等疾病。
根據病因學角度分類,2017年國際CD疾病協助網絡(CDCN)發表的特發性MCD的診斷標準中,根據是否感染人類皰疹病毒-8(human herpesvirus-8,HHV-8)將MCD 進一步分為HHV-8 陽性和HHV-8陰性,HHV-8 陽性可進一步分為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陽性和陰性兩種亞型,對于HIV 和HHV-8 均呈陰性的MCD 患者,稱為特發性多中心型CD(idiopathic multicentric CD,iMCD)[4]。iMCD 的臨床表現多種多樣,從輕微的臨床癥狀到危及生命的細胞因子風暴、器官衰竭和死亡均可能發生。實驗室檢查異常包括白細胞增多、貧血、血小板增多或減少、血沉升高、C反應蛋白和纖維蛋白原升高、高球蛋白血癥和低白蛋白血癥。該疾病的病程特點通常是對初始治療有較好的療效反應,但后期往往出現復發。此外,部分iMCD 患者可發展出一種稱為TAFRO 的特殊亞型,其特征為血小板減少、胸/腹水、發熱(>38℃)、骨髓纖維化、器官腫大(淋巴結腫大和或肝脾腫大)[3]。既往iMCD無標準規范的治療方案,大多數基于經驗性研究,僅有一項前瞻性隨機對照試驗研究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抑制劑司妥昔單抗(siltuximab)持續維持使用取得較好的效果。目前,尚無大樣本前瞻性研究數據的支持,且治療效果往往不盡人意。CDCN 于2017年至2018年相繼發表iMCD 的診斷標準和治療共識[4-5],為臨床研究與治療提供了理論指導。盡管近年來國內外研究發展較為迅速,但因其較低的發病率,使得對其發病機理認識不足,亟待進一步研究。
2 UCD發病機制研究
UCD 的致病細胞類型仍未被確定,其發病機制可能是由腫瘤間質細胞克隆性增殖及獲得性突變引起的。
濾泡樹突狀細胞(follicular dendritic cells,FDCs)的克隆性增殖可能是UCD 的病因驅動因素之一[6]。FDCs 對生發中心的形成至關重要,在引導淋巴細胞進入淋巴結內相應區域和促進B 細胞存活方面發揮重要作用[7]。在UCD中常可見到間質細胞過度生長、FDCs增生和發育不良[8]。UCD淋巴結內發育不良的FDCs 會強烈表達分泌趨化因子(C-X-C motif)配體13(CXCL13)(又稱為B 淋巴細胞趨化劑),該趨化因子起介導FDCs協調淋巴細胞運輸作用[9]。有研究報道,UCD 患者在同一淋巴結區域發展為FDCs 肉瘤的病例,這為腫瘤性FDCs增生作為UCD發病機制的主要驅動因素提供了證據支持[9-10]。
近期一項研究中,使用基因測序技術,發現20%UCD 病例淋巴結中有PDGFRB(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 B)體細胞突變,該突變位于非造血基質CD45 陰性細胞中。隨后,該研究在復發的UCD 患者中檢測到PDGFRB 編碼p.Asn666Ser 突變,這強烈提示間質細胞中PDGFRB突變可能在UCD的發病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11]。綜上所述,UCD 的發病機制很可能是由腫瘤間質細胞克隆性增殖引起的獲得性突變導致,但尚需更多的研究來證實[7]。
3 iMCD的可能病因
iMCD 的病因及發病機制目前尚未明確,在臨床表現和病理特征上與多種疾病相交叉,已經發現的較常見的致病因素包括自身免疫性因素、副腫瘤綜合征、病毒感染性因素以及炎癥因子的失調。推測iMCD的致病機制由多種病因綜合性作用引起免疫調節失調和細胞因子增加的共同途徑產生。
3.1 自身免疫性因素
自身免疫性疾病被證實與iMCD 具有相同的臨床和組織病理學特征。幾乎所有類風濕性關節炎和15%~30%系統性紅斑狼瘡患者的淋巴結都表現出CD 組織病理學特征[12-13]。大約30%iMCD 病例報告發現了自身抗體和自身免疫異常[14]。iMCD患者對用于治療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療法有反應,如抗IL-6 受體療法和環孢菌素[15]。iMCD的自身反應性抗體刺激抗原提呈細胞(如濾泡樹突狀細胞和巨噬細胞等)釋放炎癥細胞因子IL-1和(或)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上述細胞因子激活調控NF-κB 及JAK/STAT 細胞通路釋放大量IL-6 及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等炎癥因子,形成細胞因子風暴導致iMCD 的產生。然而,尚未明確的是這些自身抗體在病因學上對iMCD起作用,還是炎癥的廣泛傳播或繼發于原發疾病的驅動因素發揮作用。
3.2 副腫瘤綜合征
腫瘤性iMCD 可能是由于獲得性致癌基因突變導致,從下述方面可取得部分證實:1)iMCD的臨床和組織病理學特征與淋巴瘤的特征具有重疊性,而與年齡匹配的對照組相比,iMCD 患者的惡性腫瘤發生率明顯增加[14]。2)POEMS綜合征(多發性神經病、器官腫大、內分泌病、單克隆漿細胞紊亂及皮膚改變)的臨床癥狀和淋巴結病理組織學類型與iMCD 也有交叉,現已明確POEMS 綜合征的單克隆惡性漿細胞合成和分泌VEGF 有關[16-17]。3)iMCD 中發現單克隆突變。既往研究中,MCD 病例中的淋巴細胞通常是多克隆細胞[18],但在一項針對4 例iMCD 病例的小型研究中發現,所有病例均有多克隆淋巴細胞增殖和單克隆體細胞突變[19]。1 例未接受HHV-8 檢測的HIV 陰性MCD 患者在IL-6 位點(7p21-22)的淋巴結組織中發現體細胞易位(46,XY,t[7;14][p22;q22])[20]。一些研究也表明體細胞染色體突變造成良惡性腫瘤,促使淋巴結或結外淋巴器官釋放IL-6等細胞因子從而引起iMCD 樣癥狀[21]。近些年惡性血液系統腫瘤與iMCD共存的病例時有報道,提示惡性腫瘤和iMCD 之間可能存在特定的互為因果的機制,也提供了在診斷iMCD時排除潛在惡性腫瘤的必要性[11]。
3.3 病毒感染因素
iMCD 可能是由未知感染引起的。HHV-8 感染可以引起MCD,其機理為HHV-8病毒可以編碼病毒源IL-6(viral IL-6,vIL-6),誘導自身分泌大量人IL-6,產生炎癥風暴[6]。其他病毒或感染源也有引起iMCD 的個案報道,診斷iMCD 的同時發現合并EB 病毒、人類皰疹病毒6、乙型肝炎病毒、巨細胞病毒、弓形蟲和結核分枝桿菌等至少合并一種病毒感染[22]。這些感染是否為iMCD 的致病因素,還是巧合出現,或是繼發性于iMCD 免疫功能障礙,現仍有待商榷。HHV-8陰性MCD患者與HHV-8相關的MCD具有相同的臨床病理特征,但至今尚未發現其致病原因。是否可能有一種與HHV-8 同源的病毒驅動iMCD 的發病機制仍有待研究。
3.4 自身炎癥因子致病
部分研究證據支持iMCD的產生可能是由于調節炎癥的基因發生了遺傳突變。與健康對照相比,iMCD患者中IL-6受體(IL-6 receptor,IL-6R)基因多態性的比例增加。具有這種多態性的個體可顯著表達較高水平的可溶性IL-6R,而可溶性IL-6R可通過反式信號通路促進IL-6活性的增加[23]。有研究報告,1例患有MCD樣綜合征的兒童被發現在貓眼綜合征關鍵區蛋白1中具有純合突變,該蛋白1編碼腺苷脫氨酶2(adenosine deaminase 2,ADA2)[24]。腺苷A2B受體激活可刺激IL-6誘導,促使ADA2缺乏,進而導致腎纖維化[25]。目前,自身基因突變導致的炎癥因子尤其是IL-6相關通路的活化仍需進一步研究。
4 參與CD發病的重要細胞因子和信號通路
4.1 IL-6的致病作用
IL-6 作為一種參與炎癥、免疫及造血的多效性細胞因子,在許多iMCD患者的發病機制及臨床癥狀中起關鍵作用[26]。IL-6由單核細胞、巨噬細胞、淋巴細胞、成纖維細胞和內皮細胞等多種細胞分泌產生,作為漿細胞和淋巴細胞重要的生長和分化因子,導致淋巴結腫大、漿細胞浸潤、肝脾腫大和反應性骨髓漿細胞增多癥。IL-6可通過CD5+B 淋巴細胞的過度表達來調節體液免疫反應,導致約30%患者抗核抗體檢測陽性、免疫性血小板減少、溶血性貧血以及其他免疫現象[27]。IL-6與其他細胞因子共同誘導多克隆T細胞生長,主要反映在活化的CD8+T細胞的存在和可溶性白細胞介素-2 受體(soluble interleukin-2 re?ceptor,sIL-2R)水平的增加上。高IL-6 水平引起高炎癥反應期,從而引起一系列生理改變。IL-6 可增加肝臟產生鐵穩態的肽激素調節因子,使腸道鐵的吸收降低及巨噬細胞釋放鐵減少,從而導致貧血[28]。IL-6 可抑制肝臟產生白蛋白,導致低白蛋白血癥。IL-6還可誘導VEGF大量分泌,促進血管生成和血管通透性增加,引起全身性水腫及腹/胸水。
有較多證據支持IL-6 是iMCD 的主要致病細胞因子。IL-6水平會隨著臨床癥狀的嚴重程度的改變而變化。外科手術切除淋巴結可導致IL-6水平的快速降低和臨床癥狀的明顯改善[29]。其他惡性腫瘤過度產生IL-6 的患者,其腫大的淋巴結可能出現類似于CD的病理改變,可在手術切除或單克隆抗體介導阻斷IL-6信號通路后得以改善[30]。
動物實驗證實,IL-6 在iMCD 發病中的核心作用。HHV-8 編碼人IL-6 的病毒同源物,稱為病毒IL-6(vIL-6),其不需要細胞IL-6受體即可與普遍表達的gp130 受體亞基結合并產生隨后的JAK-STAT信號,繼而產生類似MCD 的癥狀。當病毒IL-6轉基因在IL-6 敲除的小鼠中表達時,可消除MCD 癥狀,這表明即使在病毒誘導的MCD 中,內源性IL-6仍然是一個關鍵的輔助因子[31]。正因如此,靶向IL-6 信號級聯的單克隆抗體治療具有有效的治療作用。抗IL-6或抗IL-6受體單克隆抗體通過阻斷IL-6信號轉導,如司妥昔單抗中和IL-6,托珠單抗(tocilizumab)阻斷IL-6R,從而改善iMCD 患者臨床癥狀并縮小外周淋巴結。
4.2 其他細胞因子
IL-6非iMCD的唯一致病驅動因素,其他細胞因子如IL-2、VEGF、TNF-a和IL-1亦參與了iMCD發病機制。免疫細胞中炎癥通路的過度激活會導致淋巴結的組織病理學改變和各種臨床癥狀的出現,使用這些細胞因子的拮抗劑或抑制劑均有報道治療成功案例[32-33]。沙利度胺為一種免疫調節劑,可以抑制IL-1、IL-6、IL-10、TNF-a及VEGF等多種細胞因子的產生,在個別報道中對iMCD患者治療有效[34-36]。
VEGF很可能在iMCD的致病機制中起重要作用。有研究報道20例iMCD患者中有16例VEGF升高[14],該發現在隨后1項17例患者的研究中被證實[37]。部分iMCD病例中觀察到的毛細血管滲漏綜合征和爆發性櫻桃血管瘤病的現象可以用VEGF升高來解釋[38]。mTOR具有調節VEGF表達的作用機制,有研究報道1例難治復發的iMCD-TAFRO病例在使用雷帕霉素(mechanistic target of rapamycin,mTOR)抑制劑西羅莫司后,病情得到了明顯緩解[39]。最近,Fajgenbaum等[40]研究表明,生長因子與受體酪氨酸激酶結合,導致PI3K、AKT和mTOR的下游活化。西羅莫司與他克莫司結合蛋白結合,可共同抑制mTOR活性,顯著減弱CD8+T細胞活化并降低VEGF-A水平。
IL-1β 也可能為iMCD 較為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據報道,IL-1β受體拮抗劑來那度胺已成功治療2 例司妥昔單抗難治性iMCD 患者[32,41]。IL-1β 在促炎級聯中位于IL-6 和VEGF 的上游,通過激活NFκB 通路導致IL-6 的產生,使用IL-1β 受體拮抗劑可阻斷IL-1β受體和NF-kB信號通路。
綜上所述,iMCD的發病是由多種病因機制參與,這些發病機制通過綜合作用引起細胞因子的分泌和自身免疫系統功能的紊亂,其細胞因子和自身免疫細胞通過正反饋環刺激效應細胞分泌大量的細胞因子(如IL-6、IL-1及VEGF等),從而形成iMCD的細胞因子風暴,這些參與的細胞仍未明確,亟需進一步研究驗證。
5 結語
CD作為一類異質性很強、預后較差的少見病,其異質性主要表現在臨床癥狀、組織病理學及實驗室結果方面。UCD的致病機制可能是由腫瘤間質細胞克隆性增殖及獲得性突變引起的,而iMCD很可能由多種病因綜合性作用引起免疫調節失調和細胞因子增加的共同途徑產生。明確CD的致病機制,將為臨床研究及治療方法提供理論支持,繼而幫助患者選擇更為有效的治療方案,改善患者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