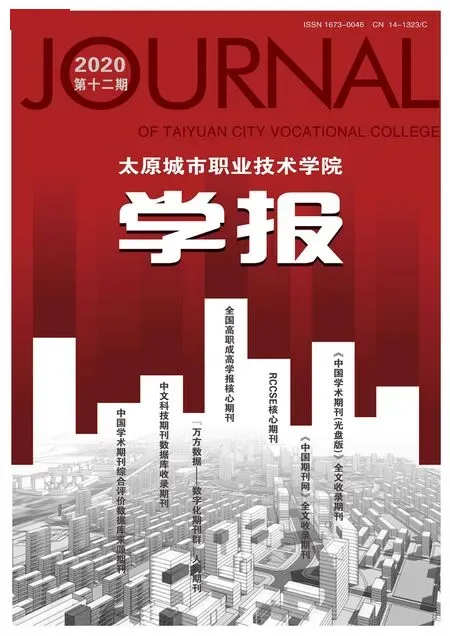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詩歌中的審美傾向探析
■武曉梅
(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山西 太原 030027)
文學界對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創作評價,通常按照他的創作時期劃分,將他創作的早期定位為意象派,將后期歸入客體派,但無論是哪個時期,他的創作影響力都在美國詩壇占據一席之地。也正因此,他被譽為美國后現代主義詩歌的鼻祖。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創作的詩歌較好地繼承了浪漫主義傳統,處處充滿了浪漫的情節,給人以豐富的想象力。他的詩歌創作不拘泥于格式和固有語言形式的限制,敢于在詩歌創作的語言和形式上追求自由。比起同一時期的維多利亞詩風,他更提倡用美國本土的語言進行情感的傳達,慣用通俗的本土語言拉近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同時,他大膽地通過詩歌創作實驗,將繪畫與詩歌進行了完美結合,表達出具有畫面感和沖擊力的詩歌意境,將細膩的情感蘊藏在詩歌作品的字里行間,表達出獨特的個人風格和審美傾向。具體來看,他的詩歌創作審美傾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剖析。
一、無處不在的浪漫主義氣息
美國浪漫主義文學的開端在18世紀末,是美國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這一文學的基本特征在于作者對于個人主觀感情色彩的表達,與現實主義文學相對,強調了創作者的個人主觀思想和情感體驗,往往以自然為主要描寫對象,對自然的美進行謳歌和贊美。浪漫主義文學的作者們常常將自身融入大自然的氛圍當中,追求返璞歸真的真實和淳樸,從而與現實社會的丑惡和扭曲形成對比。在語言方面,浪漫主義文學創作的語言通常是自由而真摯的,不追求矯揉造作,充滿想象力和創造力,強調藝術效果的展現。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詩歌創作較好地繼承了浪漫主義文學的傳統,他的詩歌創作善于運用豐富的想象力和樸實自由的語言謳歌自然與和平,他常常將自然景物作為描寫創作的對象,在《律動的形象》中,他寫到:“楊樹叢里的一只鳥,那是太陽!樹葉是黃色的小魚,在河里游動。那鳥掠過它們,白晝在它的翅膀上。”他用樸素常見的自然景物入詩,加入跳脫的比喻和靈動的動作,使得這首詩歌充滿了自然的樸素與美好,令人心生向往。他與眾多浪漫主義文學作家一樣,厭惡戰爭,認為回歸自然才是人類應當做出的選擇。然而他的詩歌并不是常規意義上對浪漫主義的模仿和絕對的傳習,他在自己創作的基礎上加入了更多的探索與突破,繼而發展成為了獨具一格的美學氣質。他的創作注重追求“真實”與“想象”之間的平衡點,讓讀者在真實與想象之間來回穿梭,形成獨特的浪漫主義體悟。正如他在《牧歌與自畫像》這組詩中的一首《古怪》中寫到:“城市有一排排奶頭,鄉村大部分是雄性的,它用又鈍又短的角頂我,迫使我抵抗它,或糟踐它。城市充滿奶水,大部分時間靜臥著。這些人在她肚子上,撞破頭顱,迸濺腦漿。”他將城市和農村以擬人化的形象形成對比,用置身其中的體驗感,想象身處城市和農村的人們所感所遇,在真實的遭遇和想象的體悟之間尋找支點,達到二者之間微妙的耦合,也使得讀者真實地感受到他的所感。他用具象化、擬人化的方式,將人類放置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用雌性和雄性來影射二者之間的表象化差異,用截然不同的對待方式和迥然的結局來告誡人們看清楚城市的現實與險惡,將讀者從想象拉回到現實,進而對現實進行了自我加工后的清晰判斷。人們在對他的詩歌進行評價的時候往往會忽略它的浪漫主義氣息,更強調他的后現代主義。實際上,他的作品當中浪漫主義文學的氣息是一以貫之存在的。
二、追求詩體語言的平易近人和形式的灑脫自由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詩歌,從語言上追求平易近人,從形式上追求灑脫自由,是獨具個人審美風格的詩歌實驗。他熱衷于詩歌創作的實驗性探索,不愿意墨守成規,更不跟隨前人設定的路途進行創作。在他看來,詩歌的創作應當是自由的,是平易近人的,而不應當是矯揉造作的,更不應當有所謂的格式化思維。他的創作風格與他職業醫生的身份密不可分,他工作的環境大多充滿了機械、臨床實驗和慎重的診療,這讓他的創作與勞苦大眾的日常生活距離很近,離精英和圣殿相距甚遠。他曾公開表示,他的創作理念與詩壇頗具影響力的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背道而馳。艾略特曾在《玄學派詩人》當中發表對詩歌未來發展的看法:“詩人必須變得愈來愈無所不包,愈來愈隱晦,愈來愈間接,以便迫使語言就范,必要時甚至打亂語言的正常秩序來表達意義。”艾略特認為,詩歌的格律是不重要的,甚至語言可以不按照正常的邏輯秩序。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則認為,艾略特和他的《荒原》是在“向后看”,而真正向前看的詩歌,應當是走近大眾的,不是用人們聽不懂的語言無病呻吟,更不是用不成體系的邏輯來體現詩人萎靡不振的情緒,詩歌應當是給人以指引的,他反對艾略特向后看的詩歌創作理念,并認為自己應當朝前看,他說:“只有新的,才是好的。”他認為:“詩歌就是要有格律、沒有自由的詩,但是格律必須是一種比以往允許的那些形式更可靠、更自由。”這也強調了他在詩歌創作方面的前瞻性和實驗性,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對詩歌語言和形式的突破實驗。他在他的詩歌代表作《紅色手推車》當中寫到:
“The Red Wheelbarrow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so much depends
upon
a red wheel
barrow
glazed with rain
water
beside the white
chickens”
從這首詩歌的格律來看,它顯然不同于以往詩歌的格律規范,往往一詞一句獨自成行,然而在這樣看似隨意不符合格式的斷字斷句背后,人們能夠看到屬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帶著自由靈魂的克制,他的創作并不是沒有格律的,反而他認為這樣的詩歌格律更具有突破性,他打破了原有英國詩歌的格局,加入了更加符合美國本土氣息的語言韻律,他所獨創的“variable foot”(中文譯名為:可變音步)以及其他一些新的詩歌韻律模式,獨具審美意趣。以上文提到的《紅色手推車》為例,他詩歌的每一行或長或短,都至少有一個重音,他提倡的是在詩歌朗讀中根據每句重音位置的不同,“行動場”(field of action)自然形成,他的詩歌也因此具備了更符合美國本土語言習慣和生活氣息的口語化,在美國本土得到大批的支持者,他詩歌中“本土語言”平易近人的美,以及對于詩歌的實驗也為美國詩壇發展打開了新的格局。
三、繪畫藝術與詩歌表達的完美結合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除了醫生和詩人的雙重身份之外,他還十分精通繪畫,甚至對繪畫藝術的追求到達了癡迷的程度,這讓他將繪畫藝術的構圖技法和色彩搭配沖突運用到了詩歌創作中,在繪畫藝術與詩歌創作之間創造了一種獨特的美感,往往在閱讀他的詩歌時,給人以色彩的強烈沖擊以及想象下視覺的美感。他曾創作的詩歌《spring and all》(中文譯名:《春天和其他》)就是其中繪畫藝術與詩歌藝術相互融合的代表之一,詩中描寫了早春時節的獨特景象。與大眾以往對春天溫暖、明媚、頗具生命力的印象不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這首詩歌當中描繪了一個雜亂、骯臟、生命力衰微的春天,在他的筆下,藍天不是澄明的,云朵也不似那般溫柔,他寫:“藍天之下洶涌云彩,斑駁著從東北吹來,通往傳染病院的路上”。詩歌的前半段,景象的內涵更偏向于描繪的是春天姍姍來遲時冬日遺留的景象,用詩人的視角看到了“褐色的枯草”“一塊一塊死水”“枯萎昏黃的樹葉”“脫盡葉子的藤蔓”“景色呆滯了無生趣”。他似乎是在創作一幅油畫,一幅冬日遲遲未走,春天遲遲未到的衰落景象。比起詩歌意蘊,前半段更倚重于繪畫技巧。然而正當人們摸不到春日的希望時,他卻筆鋒一轉,帶著姍姍來遲的春日登場,春日赤裸裸、慢悠悠、義無反顧地來了,帶來了新世界,也帶來了希望和美好的萌芽,使人從一顆野蘿卜的生根發芽,與詩歌的開頭呼應,春天就這樣帶著洶涌的云彩,順著東北風斑駁著來了,帶來了迅速萌發的新的希望。通過這樣的轉折對比,詩歌的層次感更加立體,帶來的繪畫沖擊力也更加強烈,感情上帶著飽滿的期待,帶給人新的世界和新的希望。與這樣的沖突技法不同,他還善用平和的筆觸,描繪沁人心脾的美好,正如《紅色手推車》中他寫到:“紅色手推車”“閃亮雨水”“白色小雞”,構圖祥和美好,色彩艷麗、明亮,讀者仿佛看到了淅淅瀝瀝的雨水在紅色的手推車上閃著柔和的亮光,白色的小雞依偎在一旁的景象,這就像是一幅色彩艷麗、表述到位的油畫,雖然這幅畫并不存在,卻具有極強的感染力和帶入感,讀者仿佛置身于畫中。
四、印象派創作的意象表達與主客體感悟的共情
對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評價當中,有太多的詞匯,“浪漫主義”“后現代”“實驗文學”等,其中對于他的詩歌意象表達,更貼切的莫過于“印象派”,這是集繪畫與文學為一體的一個藝術詞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詩歌創作絕對與“印象主義詩學”這個詞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正如法國印象主義大師讓·愛普斯坦所提出的“印象主義詩學”這個概念一樣,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詩歌創作來源于生活的原生態,但是又高于生活的本體,他善于利用生活中司空見慣的場景和景物、動物等來進行意象化的表達,以這樣來源于生活,客觀存在本體的事物來傳遞詩意,倡導通過對客觀事物本體的描寫和觀察,從生活中瑣碎的細節及稀松平常的日常和平庸來體味生活的哲理,傳遞詩意與作者的切身感受,這就是現象學哲學的美學思想,即“面對世界”“回到事物本身”。仔細閱讀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詩作不難發現,他的創作始終是建立在客觀世界本真的基礎上,沒有過分華麗的辭藻,也沒有莫名的情緒,一切源自于真實世界事物景觀的真實感受,傳遞的是樸素的情感,運用的是司空見慣的日常,然而正是這樣的意象傳遞,更拉近了詩人與讀者之間心靈的距離,這也正是他的詩歌被廣泛認可的原因之一。他通過印象主義詩歌的創作,首先是向人們傳遞了一種質樸的生活態度,在他筆下,他始終向往著自然質樸的生活,“樹木”“花草”“鳥獸魚蟲”“森林小溪”“藍天白云”都是源自于自然之美的質樸事物,透過這些意象,他傳遞出的是對自然生活的渴望,以及表達人類應當回歸自然、追求本真的生活態度。與此同時,城市生活在他的筆下往往是“黑灰色的煙囪”“滾滾的黑煙”“轟鳴和坍塌”“崩裂的腦漿”“頭破血流的結局”,顯然這也是對城市生活的真實寫照,取材也源自于真實質樸,然而傳遞的情感卻與自然生活大相徑庭,也由此反向呼號出了他對自然的眷戀和向往,以及對人們應當遠離城市,回歸自然的生活態度的表達。其次,他的印象主義詩歌創作有著明確的“觀者”與“被觀者”,印象主義詩歌往往從這樣的角度觀察生活,詩人本身將自己置身于詩歌內容和背景當中,作為“觀者”,他承擔著引領人們認識現實世界的責任,同時他又是“被觀者”,他的情緒和意識隨著詩歌的遞進不斷呈現在創作當中,使得讀者對他的情緒起伏逐漸建立看法,并形成新的體悟。有時,他會在作品中創造對立的兩個形象,正如前文提到的詩歌《古怪》中,他塑造了“雌性的城市”和“雄性的農村”這樣兩個對立的角色,與此同時他還將“我”置身于“雄性的農村”當中,發生了一系列的爭斗與自由的抵抗、融合。將“人們”置身于“雌性的城市”當中,展現了人們最終慘烈的下場。這里登場的角色,都是“觀者”,同時也都是“被觀者”,在關注對方表演的同時自己也即將登場表演,雙方在不同的場景當中被觀察,又在同一首詩歌當中觀察著對方,讀者在這樣的想象當中,既成為了“觀者”,也想象著自己的處境,仿佛置身在其中,成為了對號入座的“被觀者”。在整個過程中,二者的關系是微妙的,既是對立的,又是相互合作的,而二者之間這種微妙的關系就是作者憑借思想將客觀存在的事物表象進行了串聯,他對事物的使用和描繪,不單單是給客觀的事物下了一個定義,更注重的是個人感官對于事物的直觀體悟,正如他說:“沒有概念,除非身在事物之中。”簡言之,他的創作美就美在通過意象的描繪,引發讀者自身對于事物的經驗和感觸,通過創作,他給予了讀者蒙上雙眼、用心靈去感受世界、體會自然之美的機會,也引領讀者建立屬于自我的獨特感知,這就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始終倡導和追求的通過“實情”去探究和尋找“現實”。他堅信感知事物、探求現實,遠遠比肉眼看到的現實世界要崇高得多,在詩歌的創作當中,創作者和讀者之間始終是存在著某種關聯性的,這里也體現了他“客體詩歌大師”的認識真諦,即作者作為創作的敘事主體,讀者作為接受一方的客體,終將從最初的相對獨立,達到最終的情感融合,詩歌必須達到客體感知的升華,最終與主體共情。也正是如此,他的詩歌創作總能帶給讀者獨特的情感體驗。
學術界普遍認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詩歌創作,試圖掙脫19世紀詩歌程式的束縛,往往給人一種與眾不同的感傷情調,而且強調一種藝術、審美經驗與日常生活經驗結合起來的實用主義美學,他通過獨特的審美傾向,向讀者展示了一個“現實”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