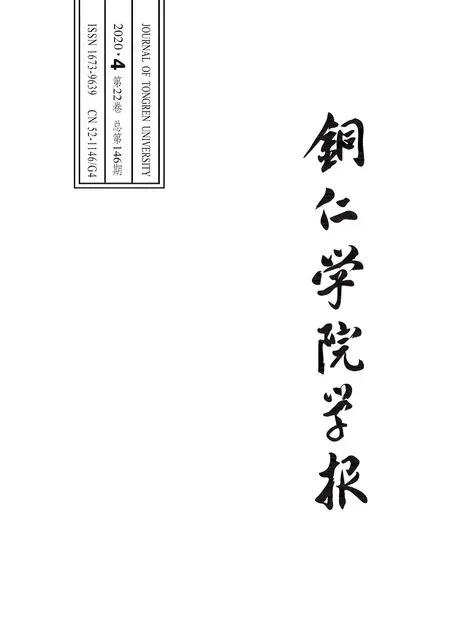周立波延安道路與文學創作
周思輝,高心怡
周立波延安道路與文學創作
周思輝,高心怡
(貴州師范大學 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1)
周立波從青年時期追求革命進步到最終走向延安成為重要的延安作家,其文學道路既有普遍性又有典型性。普遍性表現在其走向延安是當年大批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的選擇。同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延安作家在思想和創作上都發生了重要的轉變,周立波是其中之一。典型性表現在周立波代表了先前從事革命進步活動的作家走向并留在延安的堅定性,而且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在思想與創作上高度認同和執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在延安作家中具有代表性。延安文藝座談會成為周立波文學道路的重要分水嶺,后期《暴風驟雨》《山鄉巨變》的重大斬獲,與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理解認同與執行有密切關系。周立波的延安道路對其文學道路的嬗變意義重大,后期除小說創作外,在散文、報告文學等創作上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延安道路成就了周立波在中國當代文壇的地位。
周立波; 延安道路; 文學創作; 文學道路嬗變
周立波的文學創作與延安這塊熱土結下了不解之緣,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更成為他文學道路的重要轉折點。縱觀周立波一生的文學道路,他的思想與文學創作的變化脈絡彰顯著延安作家追求革命進步的共性與追求文學藝術審美特性的個性二者融合的顯著特征。1939年底,31歲的周立波接到周揚邀他到延安的來電,于是他結束了在《救亡日報》的工作,踏上了前往延安的道路。此前,周立波也從事了相當多的左聯文藝工作,但其主要成就在文藝評論和文學翻譯上,雖然他也創作了少量的詩歌與散文,但并未在當時引起太大的反響。正是在1941年到了延安之后,周立波才開始了小說的創作,并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中找到了自己文學進步的方向,深入群眾,將革命現實主義精神貫穿在之后的創作中。據周楊回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周立波的創作道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雖然周立波是最早下鄉的少數人之一,但因缺乏明確的認識,雖然與老鄉同住一個山坡上,但“雞犬之聲相聞”,卻“老死不相往來”。座談會后,周立波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為指導,深入群眾,走與工農兵結合的道路,由此孕育了《暴風驟雨》《山鄉巨變》等厚重有影響的作品。
一、1928—1939:上海亭子間里的文學青年
周立波出生于湖南益陽清溪村一個不富裕的農村家庭,第一次大革命發生時周立波正值青春,祖國的命運時刻牽動著青年周立波的心,接觸了新思潮和尼采等人的作品后,1928年新婚不久的他就在同鄉親友周揚的鼓動下,告別了家鄉,在上海開始了他的“左聯”革命斗爭生活。
(一)文學創作的前奏
在動蕩的時代背景下,個人的前途與祖國的命運息息相關,周立波在上海尋找了多種工作但都不足以謀生,為了緊跟時代潮流,周立波自學英文,進入勞動大學,接觸了許多和他一樣的進步青年,他開始積極參加左翼的活動,并在《申報?本埠增刊》上成功發表了自己的處女作散文《買菜》,署名“小妮”[1]27。這一篇戲作的散文帶有娛樂幽默的生活氣息,意外地成為周立波文學事業的開端。據其孫女周仰之回憶,周立波當時對文章能發表并拿到稿費一事十分高興[2]36。1930年周立波因為參與左派“飛行集會”的政治活動而被勞動大學開除,失意的周立波暫別政治而潛心于文學事業中。因為不懂俄語,所以他只能通過對照日譯本和英譯本轉譯蘇聯文學作品,就這樣完成了《大學生的私生活》《被開墾的處女地》等蘇聯文學譯作。1932年,在抗日救亡的熱潮中,原本做著校對工作的周立波因為組織工人罷工被捕,被關進了上海提籃橋的西牢,其后所作的短篇小說集《鐵門里》中的五個故事敘述的就是他在1932至1934年間的牢獄經歷。雖然承受了近兩年監獄生活的黑暗與痛苦,周立波并沒有放棄革命的信仰和進步的決心。周揚在秘密探監時曾給他帶了一本英漢辭典,周立波就在獄中繼續苦學英文,“他刑滿釋放后仍然積極地尋找黨的關系,沒有半點灰心,半點后悔。”[3]186周立波出獄后不久便在周揚的引薦下加入了左聯并成為了一名中共地下黨員。左聯自成立以來就十分注重對馬列文藝理論的譯介,作為上海亭子間里的文化人之一,周立波在20世紀30年代也發表了不少文藝評論文章,積極踐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方法,參與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并在兩個口號的論爭中擔當“國防文學”的積極倡導者,彰顯出普羅文學斗士的立場。
(二)翻譯家與文藝理論家
綜合考察青年周立波1929初到上海至1937年間的文學道路,不難看出他對革命文學的熱情。他將自己的筆名改為“立波”,取自英文的“Liberty”的發音,足見他對追求解放、要求進步的“革命的世界觀”的重視。在這一時期,他接觸了大量國外的文學和理論,還積極進行外國小說的翻譯和報告文學的評介,由他所翻譯的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及基希的《秘密的中國》在當時的文化圈內引起了較大反響,及時地為國內學界開闊了文學研究視野。周立波將《秘密的中國》視為報告文學的模范,其目的之一則是將報告文學這一表現形式納入到“國防文學”中去[4]67。有學者認為,“周立波作為《秘密的中國》的譯者,汲取了基希的報告文學觀和創作手法,將它融入了自己的創作中,因而成為了現代中國報告文學史一個重要的領軍人物。”[5]198周立波本人的文藝理論觀和報告文學作品也深受國外作品的影響,他在《我們現在的文學》一文中提倡勤于觀摩外國的作品,“首先應該引起注意的是蘇聯的碩果。”[6]5他的文藝評論里主要討論蘇聯文學,但也談巴爾扎克、歌德、易卜生等他國文學巨匠的創作經驗。除此之外,周立波在這一時期創作了一批詩歌和散文,大多以抒發自己在戰爭年代的感悟為主題,也有對鄉土生活的追憶與反思以及對追求自由的文人的悼念等,他的詩作及文章文辭熱烈、思想進取,“充滿著對人生、對社會的積極思考,表現出鮮明的革命傾向。”[7]104其散文《雨》及詩歌《海濱拾詩》都表現了他對陰柔、怯懦的厭惡,但偶爾也透露出青年知識分子的苦悶情緒。這種苦悶有對戰爭創傷的無奈,如《二等兵》中對山東傷兵不幸遭遇的同情與心靈的震動,也有對書本貧乏、生存不易的苦悶,如《科學小品文家高士其》中提到的無法滿足的知識欲的悲劇。
總體來看,周立波以翻譯家和文藝理論家的身份活躍在左翼文壇上,而他對散文和詩歌的嘗試性探索還處于較為稚嫩的階段。這一時期周立波受外國文學的影響較深,對知識分子的啟蒙任務有著自覺的認知,他主張用現實主義的手法表現生活、觀察世界,在語言的運用上,其譯作及詩歌散文作品用詞與語法歐化現象較為明顯。
(三)走向延安
1937年,國民黨軍隊抗敵御侮實力不濟,北平、天津相繼淪陷。同年,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擁眾百萬,周揚、艾思齊、何其芳、沙汀、徐懋庸等廣大愛國文藝人士紛紛奔向圣地延安,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抱著對革命的希望,渴望切實地感受前線的緊張戰事。大多數前往延安的文人,都是先體驗了延安的生活再馳往前線,而周立波卻是先隨軍進入晉察冀邊區前線又輾轉前往江南、湘西等地,在1939年底才踏進了延安的土地。在1937至1939年間,周立波完成了報告文學合集《晉察冀邊區印象記》,之后又出版了《戰地日記》一書,較為生動具體地記錄了八路軍在華北前線的抗敵情況,是“最先寫出報道八路軍英勇抗戰的報告文學”[8]14。這“兩記”中有對革命將士的崇敬與贊美以及對戰爭勝利的熱切向往,更有對被日軍肆虐過的土地的客觀記述,如《劫后的東冶頭》描寫被敵人毀壞的村莊:婦女被奸淫、投降的村民被虐殺、食物被敵人丟棄在沙粒中……周立波從他切身的體驗出發,表現對日軍的憤怒與質問:“我聽說日本人最愛清潔,為什么到中國來的敵人,竟是這樣的污臟”[9]17。同時,周立波在他的報告文學實踐中延續了《秘密的中國》“正確的事實、銳利的眼光、抒情詩的幻想”[4]65-66三個要素的使用。首先,他對人物的觀察相當細致,且十分擅長場景的描寫,尤其注重細節的表現。如《北冶里夜談》一文就記錄了與曾支隊長的一次漫談,“外面寒風在吹響,屋里卻是因為升了火,溫暖像春夜”[9]31。周立波抓住了夜談的氛圍,沒有將其渲染為一次嚴肅的對話,循序漸進地切入主題,不直接表現人物的情感,而是通過曾隊長表情的變化來捕捉他情緒的波動。其次,周立波不僅對人物有著敏銳的觀察,還對事件有著較為全面的分析。文中將國民黨督戰隊和共產黨戰士們進行對比,以突顯共產黨戰士的勇猛,將其擬喻為“民族精神可愛的泛濫”,理性與感性兼備。最后,《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往往賦予文章結尾以詩意的升華。如《滹沱河畔》的結尾,作者將滹沱河擬人化,他聯想到河水將流過中華大地,看過了日軍的肆虐,見證了共產黨人的奮勇向前,最后借滹沱河來表達中華必將勝利的預言,充滿了詩意的想象。這一時期周立波的報告文學藝術性與寫實性兼備,雖然語言仍然未能完全脫離歐化特點,但是無論是內容還是情感都更顯真實,寫作手法也更加從容。而《晉察冀邊區印象記》也影響了眾多文人更加堅定地加入革命的陣營,如沙汀便是在讀過了這本書后決心前往抗日根據地的。
二、1939—1942:沿著魯藝的道路出發
1939年底,正在桂林《解放日報》工作的周立波接到時任魯迅藝術學院(后簡稱“魯藝”)副院長的周揚的邀請,終于踏上了他心心念念已久的圣地延安。當時尚處于發展初期的魯藝缺少教員,因此周立波便在周揚的引薦下成為了魯藝文學系的教員,同時擔任魯藝編譯處處長職務。
(一)延安從教與魯藝講稿
在周立波的文學生涯中,他在魯藝任職的這一時期參與了許多重要的文學活動。其中之一即是他教授了兩年“名著選讀”的課程,深受當時魯藝學生的歡迎,被稱作是“魯藝校史上最具有浪漫色彩的篇章之一”,魯藝文學系的第一屆學生岳瑟形容他“舉止從容,說話輕柔,詩人的氣質,小說家的洞察力,學者的求實精神,在他身上融合得如此完美”[3]232。在眾多仰慕他的學生中還包括他后來的妻子林蘭。周立波廣闊的文化視野,天才般的翻譯才能,以及他作為戰地記者的敏銳觀察力和對話能力,在魯藝的講臺上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因此他的課在魯藝毫無懸念地成為了最受學生喜愛的課堂之一。雖然在1984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集結出版的《周立波魯藝講稿》中表明許多講稿已經遺失,但從這份殘缺的提綱中仍不難看出周立波教學的用心。首先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上,講稿中不僅涉及文學理論、作品內容分析,還包括美學介紹、哲學啟發等內容,探析了波德萊爾、艾略特、霍布斯等作家、哲學家的觀點,內容豐富且詳實;其次他的教學方式是討論式的,先讓學生在課堂宣讀自己的見解,最后由他來總結、講析,課堂靈活不死板,氛圍自由且濃厚。《周立波評傳》一書中認為周立波的魯藝講稿“相當完整地反映了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前的美學思想和文藝觀點。”[1]150的確如此,周立波魯藝講稿中體現了他對表現文學時代主題的追求,對典型藝術手法的看重,以及他真實、樸素的文學觀。在討論19世紀頹廢派、象征派時,他認為一個好的藝術作品應該達到讓人理解、引人共鳴的境界,而不是刻意制造理解的障礙,這與他1930年代的文學觀點是一脈相承的。這些講稿不僅幫助魯藝學生擴展了文學的視野,提升了他們的文學修養,同時在研究外國名作時,周立波自身也能從中獲取一些寫作的技巧和經驗,因此,這份講稿也可以看作是周立波為從事小說創作所做的準備。
(二)創立延安文學社團“草葉”
周立波還在這時期與一眾魯藝師生組織創立了延安的文學社團“草葉”,并于1940年9月編輯出版了《草葉》雙月刊。“草葉”一名取自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而1936年周立波曾在《我們應該描寫什么》[4]70一文中對五四時期盲目傾心于描寫大自然的“美國惠特曼式”的市民階級寫作表現出懷疑的態度,但在魯藝時期,“草葉”這一文學團體對惠特曼的推崇顯然透露出了初期魯藝作家群的精英知識分子的啟蒙姿態。同時,《草葉》發表的文章文學性也相對較強,多表現知識分子的個人生活。《草葉》的第一期就發表了周立波的短篇小說《麻雀》,在第二期發表了他的詩歌《我們有一切》,這兩個作品在周立波的文學創作中都顯得別具一格。《麻雀》是周立波對上海提籃橋的西牢監獄生活的書寫。這篇短篇小說情節簡單,描寫了久無生氣的牢房里,無意間飛進了一只麻雀,對于它的放和留引起了被關在監獄里的革命者們的爭論,最終決定將麻雀保留到第二天中午再放,并在小鳥的腿上系上了一封信,信中寫道:“請愛惜你的每一分鐘的自由,朋友。提籃橋監獄囚人啟”。獄友們紛紛猜測著這封信將會被誰看見,相互打趣著在囚房里度過了難得的愉快時間,但不久后,這樣的歡樂就被獄卒打斷,他不僅將麻雀踩死還懲罰了獄中的革命者,殘忍地打破了眾人對自由的幻想。小說生動地刻畫了被監禁的革命者們的形象,他們雖然經受了無數的暴力打擊,但仍然沒有磨滅對革命的熱情和自由的向往,他們身上既有革命的嚴肅也同樣有浪漫的幻想。小說的內在情緒充滿了變奏,前半段偶爾的詼諧反襯出結尾的悲傷,從愉快的討論頓時陷入絕望的沉寂,陡然的情緒變換引起讀者的心靈激蕩。小說中的麻雀既是自由的隱喻,也是一種浪漫的象征。麻雀在平常的生活里并不引人注意,但在囚房里“它變成了詩里的云雀和黃鶯。”[10]9身陷囹圄的革命者們對麻雀的愛惜與期待,代表著他們對生命的珍惜和對自由的渴望。嚴文井曾評論這篇小說,相比起周立波的某些后作反而有著永久的藝術魅力[11]104。同樣創作于1941年的短篇小說《牛》[12]45-53是周立波的小說處女作。小說筆調樸實自然,間或流露出田園詩意的審美情趣,全篇對話較少,圍繞著貧農張啟南和他的牛,表現了延安附近村莊里農民簡單而有趣的生活。作者筆下的張啟南和別的農民有些許不同,他有著普通農民的樸素情感,但也有著躲懶的脾氣和風趣的思想,是一個典型的圓形人物。雖然描繪的是簡單的鄉村圖景,但在平凡之中又嵌入了深層的思考。祥和的鄉村給人以溫暖安寧的心靈感受,但在這之后作者又想到了“牛、微笑和革命政權的意義”,正是因為共產黨的領導才能讓這個小鄉村享受著和戰火年代不同的寧靜,而中國廣闊的土地上還有無數的人們正掙扎在生死線上,因此作者在結尾發出警惕,不能被短暫的溫暖和喜悅麻痹,仍要有一顆戰斗的心。這兩篇短篇小說都有紀實的性質,但同時又在平凡中飽含了詩意,人物的生活場景生動而有趣,對革命精神的抒發也并不直露,而是從細微的小事著手,規避了假、大、空的敘事。1942年1月1日在《草葉》上發表的詩歌《我們有一切》[9]557則將快樂與痛苦的情緒混合,詩中寫“我們”不僅擁有美好的一切,也有“憂愁”“襤褸”“寂寞”“深仇”等負面的情緒折磨著“我們”的肉體和靈魂,但縱使如此仍不能使“我們”屈服,反而要以這種不屈的精神來嘲笑施虐者的悲哀。這首詩歌的整體主題是激情昂揚的,但并沒有一味地歌頌光明,而是將光明中潛藏的黑暗也暴露了出來,詩中不止有理想信念的抒發,同時也是一種心靈發展的記錄。
(三)長篇小說計劃的萌芽
周立波在這一時期已萌生了長篇小說的寫作計劃。他在短篇小說集《鐵門里》的前言中提到,原本打算用自己熟悉的監獄生活題材構寫一部長篇小說,但最后只完成了五個短篇小說,先后發表在《解放日報》等當時的延安刊物中[10]1。周立波在這一時期還創作了一部分詩歌,除了上述的《我們有一切》外,還包括《因為困難》《我凝望著人生》以及抒情長詩《一個早晨的歌者的希望》。在這一時期,他的文學創作鋒芒逐漸顯露出來,雖然已經有了創作長篇小說的內部動機,但仍未找到足夠支撐其完成長篇巨作的寫作材料。總的來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周立波在魯藝時期的寫作保留著歐化的審美特點,其詩歌有著雪萊式的抒情氣質,六篇短篇小說雖然帶有紀實性質且文學審美性突出,但內容上仍顯示出與當時革命斗爭環境的不合適宜,而且他所表現的依舊是熟悉的知識分子的題材,沒有真正地融入工農大眾的現實生活,“周立波小說和現實之間的脫節是新小說家未能成功進入新的革命場域和革命文學場域而導致的失語的證明”[13] 61。因此,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周立波作了深刻的反思,不久之后他發表了文章《后悔與前瞻》,反省了過去自己的三個錯誤,其中第一個錯誤就是“還拖著小資產階級的尾巴”[14]419,坦誠自己還在寫過去的東西。在此之后,周立波也曾多次后悔自己之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傾向。直到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周立波接受了毛主席“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的指示,積極響應文藝工作者上前線、下鄉的號召,從現實的農村生活中汲取了大眾文學的養料,構造了其長篇小說的藍圖,自此真正找到了他文學創作的方向,逐漸成長為一個人民的作家。
三、1942—1989:創造新世界的文學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作出《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規定學校在兩個月之內須熟悉中央指定文件的情況,魯藝的整風委員會由何其芳任主任,周立波等人任委員。4月13日,毛澤東邀請周立波、周揚、何其芳等魯藝黨員教師在楊家嶺的住處談話,了解魯藝文藝界的情況,收集文藝工作者們的建議,不久之后的5月2日在楊家嶺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周立波本來就對毛澤東相當敬佩,而他一直以來的文藝觀都強調文藝作品的現實性和典型性,這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謀而合,為時代而創作更是周立波心中的文學宏愿,通過這次會議,周立波準確地把握住了“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問題。于是1944年他告別了魯藝,調至《解放日報》編副刊,并于同年隨三五九旅南下開創抗日根據地,回到了軍隊前線中去。據周仰之回憶,周立波還列出了幾十部要完成的寫作計劃,《暴風驟雨》只是其中的一部[2]187。可見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周立波的澎湃之心,對于新題材有著強烈的寫作熱情,急切地期待著發揮自己的文學創作才能。
(一)報告文學《戰場三記》
自1944年11月隨軍南下到1945年9月回師中原,周立波與湖南同鄉王震、王首道帶領的部隊在戰火紛飛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對于已經熟悉部隊生活的周立波來說,這一次隨軍南征的經歷是一個相當珍貴的寫作題材。他曾寫道:“在這兩支軍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場之上,天天發生不平凡的事,這將是文藝寫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15]111直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周立波還計劃著以這段經歷為題材創作一部長篇小說。可惜的是他未能遂愿完成這部巨作,僅在1978年寫成了短篇小說《湘江一夜》(取材于他在南征途中強渡湘江的戰斗經歷)作為其文學生涯中的絕筆。但在這歷時近一年的戰斗中,周立波堅持記錄隨軍日記,在戰斗結束后他將這段經歷整理成了14篇報告文學,集結出版了《南下記》,1978年又將這段日記整理出版了《萬里征程》。不同于《晉察冀邊區印象記》的是,《南下記》寫作于抗日戰爭結束后,更加強調“黨性”的原則,脫離了“印象”的主觀性,而更注重戰斗的現實性,集中表現八路軍和新四軍將領的優秀品質和抗戰群眾的智慧,沒有了主觀抒情的詩意想象,偶有閑筆描寫一些特殊的戰斗情況,如在《沁源人民》一文中就對比了民兵與正規軍的區別,主要以歌頌共產黨領導下軍民團結一心、奮勇抗戰的情形為主,相對減少了對賣國賊等現象的揭露。1962年,周立波將《晉察冀邊區印象記》《戰地日記》和《南下記》合編為《戰場三記》,他的中國革命報告文學將部隊的經驗與民族命運融合,生動地記載了中華民族在抗日戰爭時期生存與發展的艱辛道路,兼有文學性與戰斗性,力求真實地反映階級的、民間的戰爭歷史畫卷。但周立波在此時仍然還未完成長篇小說寫作的宏愿,直到1946他跟隨土改工作隊參加了東北土地改革,去到當時的松江省(黑龍江省)尚志縣元寶鎮,這才醞釀出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巨作《暴風驟雨》。
(二)宏大敘事的開端:《暴風驟雨》
《暴風驟雨》以1946年至1947年間東北土地改革歷史為題材,一經發表即引起熱烈反響,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即獲得了解放區優秀作品的表彰。1950年初,周立波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成員之一訪問蘇聯,并于1952年與丁玲的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共同榮獲斯大林文學獎金,成為中國解放區文學中反映土改歷史的長篇小說代表作之一。這一光榮的成就并非意外,在創作《暴風驟雨》時,周立波早已有了長篇小說的寫作計劃,他走進東北的農村生活,大量地收集當地的真實故事。在《深入生活,繁榮創作》[15]94-96及《〈暴風驟雨〉的寫作經過》[15]128-132等多篇創作自述中,周立波寫到他在感到寫作材料不足時還曾多次帶稿下鄉跟著貧雇農學習,仔細觀察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總結他們的生活經驗,并且力求準確把握中央政策,寫作期間常常通過看報紙、讀文件來聯系政治實踐,以增強作品的政治性。因此,這部作品所展現出來的材料的豐富性,是一般作品難以達到的。除了注重對新題材的把握,周立波還力改了此前作品的語言風格。這個改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周立波本身是湖南人,他也曾在《后悔與前瞻》一文中吐露過由一個南方人來表現北方生活所碰到的語言上的困難,但在創作《暴風驟雨》的過程中,周立波長居東北與農民同吃同住,自覺追求用口語來表現生動簡練的農民語言,根據人物的身份來模仿他們的對話口吻,使用“半拉子”“跑腿子”“窮棒子”等方言土語來增強作品的真實風貌;其次周立波此前作為一個外國文學愛好者,其語言有著明顯的歐化傾向,但在《暴風驟雨》中他尤其注重避免強加多重定語,力求達到句式簡練而含蓄的效果,脫離歐化的句子結構,拋棄了精英知識分子的腔調,小說中還常常描寫農民間幽默的對話方式,語言機智且靈活,真實地呈現出了農民的氣質,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明突出。在積累了大量的生活和語言材料后,周立波僅用了3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暴風驟雨》的上卷,接著又回到鄉村繼續深入群眾,用6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下卷。這部長篇巨作借鑒了中國經典古代小說中刻畫人物的技巧,塑造出了諸多個性同中見異的人物形象,從豐富的生活場景中展現出了東北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雖然人物形象仍未脫離類型化的特點且下卷的情節稍顯松散,但這部作品準確地把握住了宏大的時代主題,展現了廣大農民群眾對土地改革運動暴風驟雨般的力量與決心,藝術上融古今之長,成大家之象,將周立波文學創作事業逐步推向頂峰。
1951年周立波又到了北京石景山鋼鐵廠,1951年至1953年間在工廠共呆了10個月,經過反復6遍的修改完成了他的另一部長篇巨作《鐵水奔流》,這部作品是“當代文學史上最早反映新中國工業建設和工人生活的作品”[8]10。1955年周立波回到湖南益陽老家,在他熟悉的家鄉繼續潛心創作,陸續完成了反映湖南鄉村農村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和多篇短篇小說佳作。無論在感情上還是語言上,周立波與他熟悉的鄉土都更加貼近,因此作品在語言的表達上更顯真實質樸,所表現的題材也更加廣泛,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周立波都在家鄉苦心孤詣,筆耕不輟。
(三)轉變中的矛盾
自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周立波一直遵循著“文藝工作的對象是工農兵及其干部”的創作指示。在他的文學創作中不但有奮勇無畏的共產黨戰士,有可親可近的廣大農民,還有鋼鐵意志的工人群體,同時也更加注重對相應群體生活的具體實踐,在部隊、農村和工廠中都有過長期的生活經歷,力求在事實的基礎上進行藝術的概括。他在小說創作中自覺追求民族的形式,著力突出人物的真善美。多年以來的外國文學滋養在他的作品中更多地成為了一種隱性的影響因素。雖然他在《生活、思想與形式》一文中否定了象征主義、印象主義和“意識流”等藝術形式,認為這樣的文學作品脫離了社會現實[16]11,但學者鄒理認為周立波在《山鄉巨變》中的景物描寫就具有象征性的意味[17],而《暴風驟雨》更是被認為與其之前所譯的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有一定的關聯,在人物塑造、情節矛盾的設置等多方面借鑒了外國文學的小說風貌。當然周立波的一部分作品也難免受到一些條框的束縛,正如茅盾所評價的《山鄉巨變》,周立波以方言形式來突顯小說的真實性,但“太多的方言反而成了累贅”[11]199。且因為作品的創作時間與歷史運動的發展并未拉開一定的距離,因此對整個歷史風貌的呈現還不夠完善,導致了作品的局限性,作品中的人物也主要采取的是階級分析法,矛盾沖突還不夠有張力,但不能因為這些缺陷而否定周立波是一個杰出的文學作家。
從初入左翼文壇到走向光輝的延安道路,再到暴風驟雨似的紅色年代,周立波經歷了很多人所不能承受的牢獄和戰爭的歷練,他近50年的文學生涯正是他豐富而多彩的一生的見證。非凡的文學成就也使他成為當代文藝湘軍的重要奠基人,影響了一大批后來作家,他的為人民寫作的精神,尤其是延安文藝座談后的創作精神被很好地傳承下來,在當代文壇產生了重要影響。
[1] 胡光凡.周立波評傳[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
[2] 周仰之.人間事都付與流風:我的祖父周立波[M].北京:團結出版社,2015.
[3] 程遠,主編.延安作家[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4] 周立波.周立波三十年代文學評論集[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67,65-66,70.
[5] 鄒理.周立波與《秘密的中國》在中國的傳播[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10):198.
[6] 周立波.亭子間里[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
[7] 莊漢新.周立波生平與創作[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
[8] 姚時珍,鄒理.百年周立波[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
[9] 周立波.周立波文集:第4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
[10] 周立波.鐵門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
[11] 李華盛.周立波研究資料[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2] 周立波.周立波短篇小說集[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
[13] 吳矛.周立波、丁玲延安早期小說創作的言說方式[J].鄭州師范教育,2015(3).
[14] 胡采,主編.文學運動:理論編2[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
[15] 周立波,劉景清,編.周立波寫作生涯[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6.
[16] 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周立波專集[M].武漢: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1979.
[17] 鄒理.周立波與外國文學[D].北京:北京大學,2012.
Zhou Libo's Yan'an Road and Literary Creation
ZHOU Sihui, GAO Xinyi
( School of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Guizhou, China )
Zhou Libo went from pursuing revolutionary progress in his youth to eventual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Yan’an writer. His literary path is both universal and typical. The universality is reflected the fact that it is the choice of a large number of intellectuals who pursue progress in Yan 'an. At the same time, before and after the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Forum, Yan 'an writers have undergone important changes in their thinking and creation, and Zhou Libo is one of them. The typicality is that zhou Libo represents the steadfastness of the writers who had been engaged in revolutionary and progressive activities and stayed in Yan'an, and after the Yan'an Literary and Art Forum, he highly recognized and implemented the spirit of "Speech at the Yan’an Literary and Art Forum" in terms of thought and creation. which is representative among the writers in Yan 'an. The Yan'an Literary and Art Forum became an important watershed in Zhou Libo's literary path. The major gains ofandin the later perio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Speech at the Yan’an Literary and Art Forum". Zhou Libo's Yan'an roa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volution of his literary road. In addition to novel creation, he also mad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prose and reportage in his later period. The Yan'an Road achieved Zhou Libo's statu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
Zhou Libo, Yan'an Road, literary Creation, the transmutation of literature
I206
A
1673-9639 (2020) 04-0094-08
2020-05-23
貴州省2018年度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延安作家群文學道路嬗變及當代價值研究”(18GZYB33)。
周思輝(1983-),男,河南周口人,副教授,文學博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高心怡(1994-),女,彝族,貴州貴陽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責任編輯 郭玲珍)(責任校對 肖 峰)(英文編輯 田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