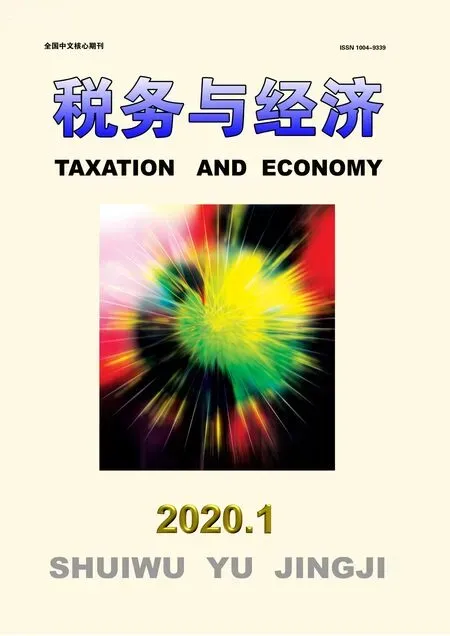環境規制、綠色技術創新與制造業轉型升級路徑
張 莉
(1.吉林大學 經濟學院,吉林長春 130012; 2.長春金融高等專科學校 經濟管理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8)
一、引 言
理論上,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的升級是一個動態演變、不斷循環的過程。[1]一方面,結構演進和制度改善等影響技術創新的因素也同時推動著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2];另一方面,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又會催生新的技術創新[3-4]。但實際上,綠色技術創新作為總體技術創新的一部分,有可能會對其他形式技術創新產生擠出效應[5],進而使得其與制造業轉型升級之間的關系變得較為復雜。因此有必要對綠色技術創新影響制造業轉型升級的路徑進行系統考察,并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進一步來說,其他因素也可能會影響綠色技術進步與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關系。已有的研究已經表明,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具有顯著的地區差異,即經濟發展水平會對技術創新與制造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產生重要影響。[6]而環境規制作為綠色技術創新的直接動因,其對于技術創新的影響更加復雜,Marcus(2007)發現環境規制的實施水平對于綠色技術創新具有積極的影響,但是對于企業的一般性創新活動具有負面影響。[7]李斌等(2011)、付強和喬岳(2011)也發現環境規制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區域的技術創新活動[8-9];衛平和余奕杉(2017)的經驗研究則發現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之間存在U型關系[10];許水平等(2016)的分析卻發現環境規制對于技術創新具有先抑制后促進的倒N型關系[11]。因此環境規制雖然對于綠色技術創新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其與技術創新的關系較為復雜,進而導致綠色技術創新影響制造業轉型升級的路徑隨著環境規制水平的變化而變化。所以有必要基于環境規制的視角系統地分析綠色技術創新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
二、變量測度與數據模型
(一)變量選取
本文在經驗分析的過程中主要涉及制造業的轉型升級、綠色技術創新和環境規制水平三個變量。對于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而言,我們主要是采用高技術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來表示,綠色技術創新采用環境科技課題經費來衡量,而環境規制水平使用污染治理項目本年完成投資來測度。此外,由于產業轉型升級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因此我們在考察綠色技術創新影響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還需要控制外商直接投資(采用各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年底注冊登記投資總額來表示)、固定資產投資(采用各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表示)、經濟開放水平(使用各地區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表示)和經濟發展水平(使用人均GDP來表示)。在具體的分析過程中,我們使用2002~2016年共15年28個省級行政區(由于數據可得性的限制,選擇的樣本不包括西藏、海南和青海三個省級行政區)的面板數據來進行。以上數據可以從《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各地區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中獲得。表1給出了相關變量的類型、名稱、符號、測度指標和數據來源。
之前的研究主要關注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而本文主要關注綠色技術創新與制造業轉型升級之間的關系。眾所周知,綠色技術創新是技術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受到環境規制的影響,正是由于環境規制的影響,綠色技術創新才得以出現。但是綠色技術創新的進步并不一定會促進總體的技術進步,這是因為與其他技術創新之間可能存在替代和競爭關系,進而導致綠色技術創新與制造業轉型升級之間關系的復雜化。所以在具體的實證分析中,我們將引入面板門限回歸模型。即將環境規制水平作為門限變量,考察其對于綠色技術創新與制造業轉型升級之間關系的非線性影響。根據上文分析,可以建立如下單門限回歸模型 :
ZSit=β0+β1LCit+ρXit+μit,HGit≤γ
ZSit=β0+β2LCit+ρXit+εit, HGit>γ
(1)
(1)式中,下標i表示個體,t表示時間,β1和β2分別表示不同環境規制水平下綠色技術創新對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如果這種影響的機制超過兩種,則我們可以繼續引入β3,其他以此類推。γ表示環境規制水平的門限值,即當環境規制水平處于γ及以下時,綠色技術創新對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是β1;但當環境規制水平超過γ時,綠色技術創新對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為β2。X為模型中引入的控制變量,詳見表1。此外,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非平穩性,在回歸檢驗中對各個變量取自然對數。在穩健性分析中,使用“污染治理項目本年完成投資(治理廢水)”來作為環境規制水平的測度指標,這些數據也可以從《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獲得。當然,在三機制門限回歸模型中,環境規制水平將會存在兩個門限值,其他以此類推。
在模型(1)的基礎上,可以引入示函數F(·),當HGit≤γ時,F(·)=1,當 HGit>γ時,F(·)=0,由此(1)式可以轉化為 :
ZSit=β0+β1LCitF(HGit≤γ)+β2LCitF(HGit>γ)+ρXit+ηit
(2)
(二)實證分析結果
在門限回歸模型中,首先要確定門限的數量。一般是在不存在門限、只存在一個門限和存在兩個門限之間進行選擇,通過計算F統計量和Bootstrap方法得到的臨界值以及P值,得到表2。
從表2可以看出,當使用工業污染治理完成投資(治理廢氣)的自然對數作為環境規制水平的測度指標時,無論是單一門限還是雙重門限的F統計量都是顯著的,而三重門限的F統計量在10%的水平上是不顯著的,因此我們使用雙重門限模型對數據進行估計,估計結果見表3和表4。

表2 門限模型檢驗
注 :***、**、*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顯著。

表3 門限值估計結果

表4 門限模型回歸結果
注 :***、**、*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顯著。
從表3可以看出,綠色技術創新對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將會在環境規制水平分別達到18.005和23.274時發生根本性改變。根據表4的估計結果,當環境規制水平較低(<18.005)時,綠色技術創新對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顯著為負,這表明在環境規制實施的初期,企業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來進行廢氣治理,這些投入雖然使得廢氣治理的效率提升,即綠色技術進步得以實現,但是其實現是以犧牲其他技術創新的投入為代價的,從而對其他技術創新形成擠出效應,進而不利于總體的技術創新和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而隨著環境規制水平的進一步提高(18.005

表5 門限模型檢驗(穩健性分析)
注 :***、**、*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顯著。

表6 門限值估計結果(穩健性分析)

表7 門限模型回歸結果(穩健性分析)
注 :***、**、*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顯著。
由穩健性分析結果可以發現 :首先,綠色技術創新對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仍然依賴于環境規制水平,且存在顯著的雙門限效應,當環境規制水平較低時,綠色技術創新不利于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而隨著環境規制水平的提高,綠色技術創新對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雖然呈現下降的趨勢,都顯著為正。其次,固定資產投資和經濟開放程度對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都是顯著的,且與表4的估計結果類似,前者不利于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后者有利于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再次,外商直接投資對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雖然也是不顯著的,但其符號為正,而經濟發展水平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雖然為負,卻不顯著,這與表4的估計結果存在差別,但是并不影響綠色技術創新對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穩健性。最后,在環境規制水平的門限值大小上,對于治理廢水的投資更早地有利于發揮綠色技術創新對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積極影響,且更晚地導致這種影響下降,因此相對于治理廢氣的環保投資,加大對于治理廢水的環保投資更有利于發揮綠色技術創新對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促進作用。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環境規制的視角系統地分析了綠色技術創新對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研究發現,在環境規制實施的初期,綠色技術創新對于其他形式的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擠出效應,因此不利于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但是隨著環境規制水平的提高,企業會將綠色技術創新與自身利潤增長有機結合,從而開辟出一條嶄新的轉型升級路徑,并逐步引導制造業發展到一個新的均衡狀態。與此同時,企業對于治理廢水的投資更早地有利于發揮綠色技術創新對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積極影響,且更晚地導致這種影響下降,因此相對于治理廢氣的環保投資,加大對于治理廢水的環保投資更有利于發揮綠色技術創新對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促進作用。
綜上,雖然在環境規制實施的初期,綠色技術進步并不利于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但是這只是制造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陣痛。隨著環境規制水平的進一步提高,綠色技術創新對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顯著促進作用就會凸顯。因此我們應該進一步提高環境規制尤其是在水污染治理方面的強度,倒逼企業將污染治理和成本降低與流程優化相結合,從而盡快推動我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