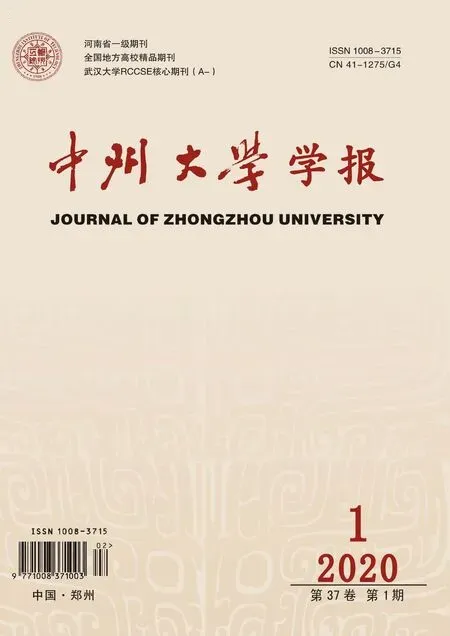康有為《大同書》的創作及其社會改造思想
曹發軍
(鄭州工程技術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4)
《大同書》是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康有為系統闡述其構想的“大同”社會理想的著作,乃康氏“本不忍之心,究天人之際,原《春秋》三世之說,演《禮運》天下為公之義,為眾生除苦惱,為萬世開太平、致極樂之作也。”[1]2在《大同書》書中,康有為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社會改造思想,希望通過社會改造,構建一個天下為公、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康有為考慮到他的一些激烈的社會主張遠遠超越了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擔心該書的出版會給自己帶來諸多麻煩和危險,故而在他生前沒有將該書完整出版,只是在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才在學生們屢次請求下僅僅在《不忍》雜志上發表了該書的前兩卷。該書的其他部分,也就是承載康有為最激烈的社會理想的章節,直到1927年,康氏去世8年后,才由他的學生錢定安送交中華書局出版。《大同書》是體現康有為政治理念的一本重要著作,也是研究康有為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獻資料,筆者多年前閱讀此書時,曾為該書的“奇談怪論”所震撼,書中觀點至今清晰如昨。今將該書中提出的社會改造思想簡單梳理一下,提交出來和大家交流,籍拋磚引玉之功效。
一、康有為及其創作的《大同書》
(一)康有為─—中國近代維新變法運動的倡導者
康有為,1858年出生于晚清廣東南海縣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幼年時期,康有為和同時代眾多官僚地主家庭的孩子一樣依例進入私塾學習,開啟了誦讀四書五經的讀書生涯。由于生活在清末民初這樣一個東西方文化激烈交流碰撞的時代,康有為可以很便利地接觸到一些來自西方的報刊書籍。在漫長的學習生涯中,在強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地驅使下,康有為在誦讀國學經典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同時,也廣泛涉獵那些來自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尤其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學習和研究,知識非常淵博,終成一代學貫中西的文化大師。強有力的“西學”背景,使康有為得以突破中國舊的思想文化的束縛,對當時的世界大局有了全新的認識。在清末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日趨嚴重的背景下,康有為從改造中國以挽救民族危亡拯救萬民于水火的良好愿望出發,綜合中、西方思想文化,構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維新變法理論體系。康氏一生著述豐厚,粗略統計其一生撰稿超過700萬字。他闡述維新變法理論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書》等。在這些著作中,康有為把來自西方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公羊》 “三世”說結合在一起,提出了自己的歷史進化論。他說,“《春秋》要旨分三科: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以為進化,《公羊》最明”[2]79。在康有為看來,人類社會的發展都要經歷“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個歷史時期,當時的中國還處于“據亂世”時期,必須先通過維新變法,實現君主立憲,使中國成為一個和英法美德日俄諸國并駕齊驅的強國,實現國家富強,徹底擺脫民族危機,進入“升平世”,然后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經過數代人的努力奮斗,最終和世界人民一起進入民主的“太平世”,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就康有為思想體系的內在邏輯來說,在中國推行變法,在不引起巨大社會動蕩和不對中國社會造成巨大破壞的前提下,實現國家的政治轉型,使中國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制的資本主義國家,只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環節,中國社會最終要融入世界發展潮流,和各國人民一道走向“大同”世界。
(二)《大同書》及其描繪的大同社會愿景
《大同書》是康有為旨在表達自己政治理念的著作,全書共30卷,約20萬字,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部是全書的總論,起著總攬全局的作用。在《大同書》的開篇甲部“入世界觀眾苦”里,康有為從他作為一個儒者與生俱有的“仁愛”觀出發,首先歷數了人們遭受的種種苦痛,并指出“總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所謂“九界”,“一曰國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級界,分貴、賤、清、濁也;三曰種界,分黃、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婦、兄弟之親也;六曰業界,私農、工、商之產也;七曰亂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曰類界,有人與鳥、獸、蟲、魚之別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傳種無窮無盡,不可思議。”[1]66在這里,康有為想要說明的是要去除人們的苦痛,“即在破除九界而已”。在《大同書》的甲部以后的九部里,康有為不僅詳細具體地論述了如何去除“九界”的問題,還勾畫了未來“大同”社會的理想藍圖:“大同之世,天下為公”,沒有階級、民族的區分,沒有國家,沒有政府,既無專制之君主,又無民選之總統,沒有官吏,所有人都平等;也沒有家庭、親屬,每個人都是獨立的自由的個人,男女“則以情好相合,而立合約,定有期限,不名夫婦”,所生兒女“均由公共之人本院、育嬰院、慈幼院、小學、中學、大學院以教養之”,“人民既受公共之教養二十年后,公家又給以職業。及其老也,又有公共養老院,疾病則有公共之醫病院,考終則有公共考終院”[1]2。在這個社會中,政治上實行高度的民主化,經濟上實行社會化的大生產,生產力水平高度發達,社會產品極大豐富,“每人都能充分獲得所需、所欲,而無痛苦或不安,生命乃是一連串的樂事。衣、食、住、行不僅提供高度的舒適,而且給與十分美感”[3]420。每一個人都能在大同世界中平等地過上“其樂陶陶,不知憂患”[1]50的生活。
在《大同書》里,康有為“懸想的大同社會是一個至公、至平、至仁、至治的極樂世界,它‘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是謂大同’,表達了人類的諸多美好愿望”[4]70。但是,由于康有為所勾畫的大同社會藍圖和他設計的政治路線圖沒有立足中國實際,不能適應彼時解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和完成歷史任務的需要,注定不會產生什么實際社會效果,以至于毛澤東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5]1471
二、《大同書》對社會改造問題的探討
(一)《大同書》對傳統制度的抨擊
為了給改造舊社會構建理想中的“大同”社會提供理論支持,康有為在《大同書》中對那個時代的社會政治制度進行了辛辣的抨擊。康有為首先對“國界”進行了抨擊,他說:“然國既立,國義遂生,人人自私其國而攻奪人之國,不至盡奪人之國而不止也。或以大國吞小,或以強國削弱,……其戰爭之禍以毒生民者,合大地數千年計,遂不可數,不可議。”[1]69因此,國家一日存在,戰爭便不會停止,人民的苦難也不會停止。他把國家的存在看成是通向大同之路的第一個絆腳石,在他看來,要實現人類大同,必須首先去除“國界”。去除“國界”實“為大同之先驅耳”[1]87。
“級界”是康有為抨擊的第二個目標。他說“人類之苦不平等者,莫若無端立級哉!”[1]126在這里,康有為尤其對印度的種姓制度大加鞭撻,并以此為例說明,“級界”的存在不僅損害了人們的平等權利,而且嚴重阻礙了國家社會的發展,使“其國一敗涂地而不可振救”。
依康有為所見,種族歧視是人類痛苦的第三個淵源。康有為認為“人類之生,皆本于天,同為兄弟,實為平等,豈可妄分流品,而有所輕重,有所擯棄哉!”,[1]126但他同時也承認世界上各種族在智力、體力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他明確地說“銀色之人種橫絕地球,而金色之人種尤居多數,是黃白二物,擁有全世界。白種之強,固居優勝,而黃種之多而且智”。而“棕色者,目光黯然,面色昧然,神疲氣苶,性懶心愚,耗以微哉,幾與黑人近!”[1]134由于人種之間在形體、智力等方面存在天然的巨大差異,這和大同世界的愿景相左,所以,康有為提出了要進行“改良人種”。
比較而言,康有為在《大同書》中對“形界”和“家界”的抨擊更為激烈。對于女子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用極強烈的字眼進行譴責,他說:“夫以男女皆為人類,同屬天生,而壓制女子,使不得仕宦,不得科舉,不得為議員,不得為公民,不得為學者,乃至不得自立,不得自由,甚至不得出入、交接、宴會、游觀,又甚至為囚,為刑,為奴,為私,為玩,不平至此,耗矣哀哉!”隨后,康有為進一步將歧視、壓抑婦女的行為上升到“損人權,輕天民,悖公理,失公益”的高度,指出此類現象“于義不順,于事不宜”[1]171。
在《大同書》中,康有為抨擊最激烈者莫過于家庭制度,在康有為眼中,中國的家庭生活簡直就是一幅凄慘的景象,“凡中國之人上自簪纓詩禮之世家,下至里巷蚩氓之眾庶,視其門外,太和蒸蒸,叩其門內,怨氣盈溢,蓋凡有家焉無能免者”[1]217。為了揭露家庭制度之罪惡,康有為總結出十四項有家之害,并得出“故家者,據亂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世最阻礙相隔之大害也”[1]225。
在《大同書》中,康有為對私有財產制度也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將它歸類為另一阻礙人類快樂的錯誤制度。不過,康有為抨擊家庭制度主要基于他對中國社會的了解,而他對私有財產制度的批評大都根據他所了解的西方工業社會的情況。
(二)《大同書》的社會改造規劃
在對傳統制度進行抨擊的同時,康有為也詳細地呈現了自己的社會改造規劃。康有為的社會改造方案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方面,是一套完整的社會改造方案。
在《大同書》的乙部,在歷數“有國之害”的基礎上,康有為提出了“去國界合大地”的設想,其基本思路就是“消除邦國號域”,現有“諸國改為州郡,而州郡統于全地公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由公民公舉議員及行政官以統之”。“各建自主州郡”在政治上“若美國、瑞士之制是也”[1]89。康有為認為,“初設公議政府為大同之始”[1]95,設置世界性的“公議政府”乃是走向“大同”社會的第一個具體的步驟。各級公政府的建立既是實現世界“大同”的首要環節,也是推行社會改造建設大同太平世的依托。接著,在《大同書》丙部以后的各部,康有為詳細論述了社會改造的各項措施。在丙部“去級界,平民族”里,康有為基于“人類之苦不平等者,莫若無端立級哉!”[1]126提出在未來的大同社會,“階級盡掃,人人皆為平民”[1]128。在丁部“去種界,同人類”里,康有為認為,“欲合人類平等大同,必自人類之形狀、體格相同始”[1]139,要通過“遷地”“雜婚”“改食”“沙汰”等措施,實施人種改造,淘汰“棕、黑人有性情太惡,狀貌太惡或有疾者”[1]143,消除白色、黃色、棕色、黑色人種之間的差別。在戊部“去形界,保獨立”里,康有為著重論述了男女平等的問題,設想在未來的“大同”社會“男女皆平等獨立”,“婚姻之事不復名為夫婦,只許訂歲月交好之和約而已”,“婚姻期限,久者不許過一年”[1]196。在己部“去家界,為天民”里,康有為詳細設計了大同世界中社會為婦女、兒童、老人興辦的福利教育事業,他設想在未來的“大同”世界里,“人人皆直隸于天,”“生育、教養、老病、苦死、其事皆歸于公”[1]227。
對未來“大同”社會實行什么樣的經濟制度,康有為也做了精心的安排。在庚部“去產界,公生業”里,康有為設想未來的“大同”社會將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凡農工商之業,必歸于公”[1]280。同時,由于實行了機器大生產,“機器日新,足以代人之勞”,“勞動苦役,假之機器”,人們每日只需要工作“三四時或一二時”,其余時間“皆游樂讀書”[1]289。
為了激勵人們上進,康有為認為在未來的“大同”社會,除了實行民主政治外,還必須實行一些重大的獎懲措施。在辛部“去亂界,治太平”里,康有為除了重申,“凡大同之世,全地大同,無國土之分,無種族之異,無兵事之爭”[1]297,“地方分治以度為界”,各地在政治上普遍設立議會,實行主權在民,地方自治,在經濟上實行公有制外,還特別強調,“為公眾進化計”,大同社會要實行“競美”“獎智”“獎仁”“禁懶惰”“禁獨尊”等措施。
當然,由于深受儒家的“仁愛”觀和佛家慈悲為懷思想的影響,康有為將其作為一個儒者所具有的民胞物與、悲天憫人的情懷也融入到了對未來社會的規劃中來。在壬部中“去類界,愛眾生”里,康有為不無動情地說“亂世親親,升平世仁民,太平世愛物”,在未來的“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殺矣”。對于“牛、馬、犬、貓”等,也應“親之、愛之、憐之、恤之”,[1]336要有仁愛之心。
在經歷一系列社會改造之后,康有為不無樂觀地提出“九界既去,則人之諸苦盡除矣,只有樂而已”[1]341。在癸部“去苦界,至極樂”中,康有為用了很大的篇幅,敘述大同社會的“居處、舟車、飲食、衣服及其他之樂”,描繪了一幅其樂融融的太平盛世景象。
三、余論
康有為作為政治人物,晚清時倡導維新,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后繼續忠于前朝,反對共和,其政治實踐與《大同書》中所倡導的政治理念反差極大。縱觀康有為一生,我們會發現康有為實際上具有雙重社會角色,一個是關注實際事務的社會改良運動的鼓吹者和推動者;另一個則是神馳于理論與想象領域、超脫現實的思想家。可見其政治理念和政治實踐之間存在一定的反差。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為康有為深知“社會結構不同理論的宣揚和實踐應配合人類進步的不同階段。”[3]39讀史使人明智,理解了康有為也許對理解康有為之后的政治人物有一定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