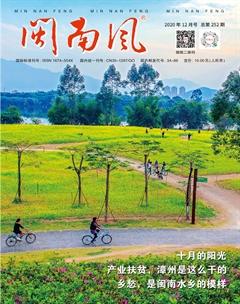月港尋月,仿佛時(shí)光隧道
蔡文龍
在月港,在我時(shí)間悠久的家鄉(xiāng),我一直在尋找那一輪圓圓的月亮。不知什么時(shí)候,我就把它丟了,丟在哪里了?是在我居樓的陽(yáng)臺(tái)上,還是在母親簡(jiǎn)陋的窗臺(tái)邊?
什么時(shí)候開始,我就很少抬頭去看那輪圓圓的月亮,更多時(shí)候一抬頭,只有黑夜伴孤星,或一枚彎彎的月亮,像失眠人的眼一樣無精打采地掛著,而天空是一本翻不動(dòng)的暗沉沉的書。
宇宙到底有多寬,遠(yuǎn)在億萬光年之外的星系,引人無限暇想,比神話小說迷幻。
我的陽(yáng)臺(tái)就在旖旎的九龍江邊錦江段。下游不遠(yuǎn)處,是九龍江入海處海絲文化月港。那是母親的原鄉(xiāng),兒時(shí)我隨母在鄉(xiāng)下外婆家長(zhǎng)大,老屋的陽(yáng)臺(tái),在狗尾巴草、咸草、蘆葦、麥田、菜園的掩映里。母親的窗臺(tái),只有小螞蟻常常緊鑼密鼓地行走,它們是天下最忙的行者,也是萬物最底層的一級(jí),像地球的胃一樣搬運(yùn)著萬物最后的食渣,或清道夫一樣掃除著所有的垃圾。那時(shí)候的日子,雖清貧卻富人情味,簡(jiǎn)單又快樂!母親慈祥的目光和勤勞的雙手,如兒時(shí)的月輝,用金針銀線編織著兒女未來人生的經(jīng)緯。
有天中午母親又打來電話,說是胸這邊有點(diǎn)悶,仿佛什么堵住了,想回月港老屋住。我有點(diǎn)怕,在這座城市里,每天早出晚歸,有時(shí)忙得精疲力盡時(shí),坐下來,才發(fā)現(xiàn)什么東西丟掉了,于是拼命地找,從手指間尋找那些縈繞的時(shí)間,它們細(xì)長(zhǎng)而脆,常常不經(jīng)意就斷了。后來我失眠了,常常看著窗臺(tái)慢慢地泛白,而我疲倦地爬起來,又繼續(xù)新一天的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