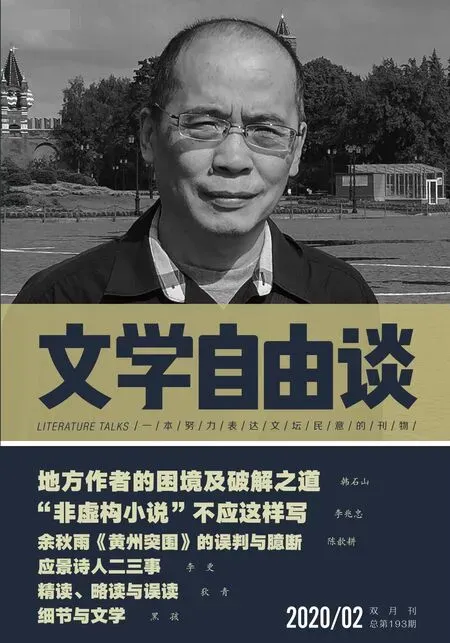過剩的字紙
2020-01-02 18:10:14□朱鴻
文學自由談
2020年2期
□朱 鴻
自臘月至正月,斷斷續續,我一直在整理房子。幾件玩好當然要打包裝箱,應該謹小慎微,急不得,怠不得。然而,這也不難,難的是書籍的搬運、分類和上柜。靠書籍為生,書多且雜,不過也終于安排妥切了。
在此過程,我發現一個問題——過剩的字紙。凡是寫有或印有文字之書籍和報刊,皆是字紙。我所見的字紙過剩,有兩種情況:一是足有一半的書籍堪為經典,我竟尚未讀過,惶恐自己的荒廢;二是一些他人所贈的書籍,不但未讀,有的還沒有開封,就窩在某個角落。這怎么辦呢?
我會繼續讀經典之作,也許可以讀完自己所購的那些。即使讀不完,轉贈他人,也不羞愧,因為,我給予的畢竟是經典。以此而論,這些字紙并非過剩。
過剩的字紙,實際上是指那些不管是在資料方面,還是在思想和藝術方面,都顯得虛浮和空洞的書籍。這種書籍裝幀得很是豪華,往往開本頗大,似乎欲以其異型脫穎而出,取得不朽。老子和司馬遷之作反而都是樸素的,柏拉圖和康德之作也不炫目,這樣的著作,才算得上巨著。以為豪華的裝幀可以亂為巨著,不僅是制造過剩的字紙,也是一種幻覺。
我罕送拙作給高士,是怕引起他們的不適。我只送幾個朋友,行往來之禮而已。劉錫慶先生曾經當面問我,怎么不把我的散文集送他,不禁驚心。回家反復想著,要盡快送,敬請他批評。然而終于沒有勇氣送他,先生就走了。嘗為獲獎送過書,現在知道那是瞎送。經常慚愧自己的文章,無甚價值,雖然成冊,也不過是過剩的字紙而已。……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