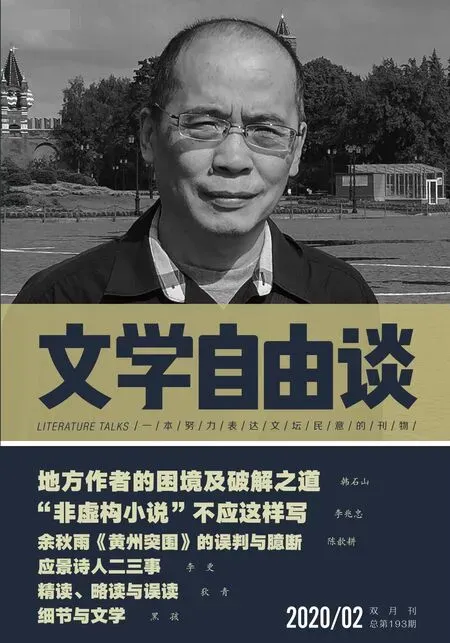《云中記》:一個猶疑、矛盾且誠意不足的儀式
2020-01-02 18:10:14□白草
文學自由談
2020年2期
關鍵詞:小說
□白 草
阿來的《云中記》立意甚好:大震后的幸存者遷至移民村,而那些埋在廢墟中的死難者成了孤魂野鬼,這令生者不安。四年后,先前的祭師阿巴決然返回棄村,挨門逐戶遍祭冤魂。幸存者自當生活下去,死者亦須得到安慰,應該說這體現了敘事者的一種良善情懷。
這也是小說的結構框架。
可問題在于,整部小說在敘事、情節、描寫等方面,與立意、結構、主旨呈現著的是一種“反對”的關系。隨著敘事進程的展開,小說的主題不是在逐漸豐富和強化,而恰恰是在被削減和弱化。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是祭師的身份。按敘事者的聲明,祭師只管祭祀山神,并不熟悉安撫亡靈之事,于行禮如儀等一概不知。這祭師倒也老實本分,不會顯擺出不懂裝懂的樣子。祭師決定返回村中,一方面出于自愿,活人自有活人來關心,死者由他去安撫一下子,尚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村民們也紛紛前來請求,祭師不去誰去?這里也牽涉到一個急需解決的社會問題:祭師的外甥,同時也是鄉上的領導,前來動員他回村做些安撫亡靈的法事,其目的其實在于“安撫人心”,重振村民意志,以利于今后村莊的重建工作。可是讓一個祭山的人去祭鬼,角色轉換未免有些突然,更何況祭師心中原也存在些許不痛快——在非物質文化傳承人培訓班上,那位人類學的教授不是說過么,“祭山要傳承,事鬼要揚棄”。可見,祭師雖自愿回村,確乎勉為其難。盡管小說多有彌縫,以自圓其說,比如祭師回憶幾十年前其父夜下祭鬼情景,算是匆忙間給自己補了一課。……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英語文摘(2021年2期)2021-07-22 07:57:06
文苑(2020年11期)2020-11-19 11:45:11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作品(2017年4期)2017-05-17 01:14:32
中學語文(2015年18期)2015-03-01 03:51:29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
小說月刊(2014年8期)2014-04-19 02: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