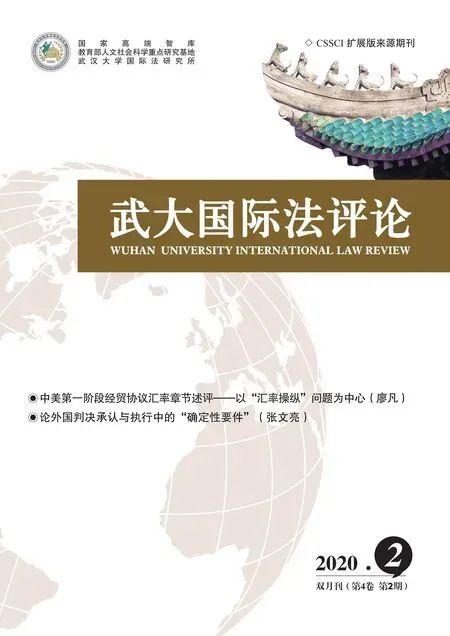論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中的“確定性要件”
張文亮
一、引言
任何判決都具有一定的狀態;根據判決作出地法律,某一判決所處的狀態可能是“最終的”、“再審中的”或“臨時的”,抑或是“可執行的”,甚或是“處于上訴中的”或“存在上訴可能性的”等。通常來說,一國判決若要發生其國內法所規定的完全效力,其必須具有“確定性”狀態。類似地,在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語境下,被請求國亦通常要求外國判決應具備適宜的狀態——“確定性”或“適宜”外國判決。①對于外國判決尋求承認與執行時應具有的確定狀態,馮麥倫教授用“適宜”(ripeness)來概括。See A. T. von Mehre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General Theory and the Role of Jurisdictional Requirements, 167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47-49 (1980).我國學者多采取“終局性”來表述“確定性要件”,如喬雄兵:《論外國法院判決承認與執行中的終局性問題》,《武大國際法評論》2017年第1期,第76頁等。對外國判決已經“確定”或“適宜”的要求便是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中的“確定性要件”。具體來說,外國判決的“確定性要件”是指由被請求國的國內法或有關國際性法律文件所規定的,外國判決尋求承認與執行時應具有“適宜”的拘束力或確定性狀態,該要件旨在確保已被承認或執行的外國判決不因其狀態在原審國之變化而被撤銷承認以及執行回轉。
雖然“確定性要件”是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的普遍條件,但是在沒有條約保障的情形下,各國通常訴諸其自有的“確定性要件”判斷外國判決的狀態且彼此之間對該要件尚不存在一致性表述及理解,②常見的表述方式有:外國判決是“最終的”(final),“最終的和確鑿的”(final and conclusive)以及“可執行的”(enforceable)等。參見下文第二部分“確定性要件”的國別差異及協調。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國家間判決的承認與執行。不僅如此,圍繞“確定性要件”產生的國別差異亦為當事人濫用相關訴訟機制創造了空間,比如利用“確定性要件”的國別差異,通過上訴或再審,破壞判決的確定性,阻礙判決在域外承認與執行。總而言之,外國判決的“確定性要件”深刻影響著判決承認與執行,是一項充滿訴訟策略的關鍵問題,其因此成為國際社會在協調或統一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中關注的重要事項。③參見下文二(三)“確定性要件”的協調或統一。本文意在從“確定性要件”的國別實踐出發,梳理其中的問題并剖析國際社會圍繞該要件的主流協調或統一方案,進而評析我國的相關立法和實踐并提出若干完善建議。
二、“確定性要件”的國別差異及協調
從比較法的視角來看,各國內法或有關的國際性法律文件雖然大多明確規定了“確定性要件”,但是在該要件的表達及內涵等方面均存在顯著不同,尤其是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對該要件的理解極為不同。一方面,不同法系之間對“確定性要件”的規定差異較大;另一方面,同一法系內不同國家之間對該要件的規定亦存在或大或小的差異。這種差異的存在充分地體現在相關國際組織就該要件的協調或統一之中,而相關國際組織折中方案的采納即是對該差異性的回應和彌合。
(一)大陸法系的代表性國家
《瑞士關于國際私法的聯邦法》第25 條規定:“某一外國裁判將在瑞士獲得承認:a.……b.如果不存在針對該裁判的普通司法救濟或該裁判是最終的;c.……”該條款僅對外國判決承認中的“確定性要件”作了規定;不過在有關執行外國判決的章節中,該法典第28 條又明確指出,“依據第25 條至第27 條予以承認的裁判,應有關利害當事人申請將被聲明可予執行。”據此,外國判決的執行須以承認為前提,且應滿足相同的“確定性要件”:不存在針對外國判決的“普通司法救濟”或該裁定是“最終的”。“普通的司法救濟”或是“最終的”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同義反復。作為規定外國判決“確定性要件”的另一替代性根據,術語“最終的”包含了術語“不再受制于普通的司法救濟”所未包含的含義。透過該法典的立法歷史可知,采納術語——“最終的”是為了將那些不再受普通的司法救濟約束的裁定也納入到外國判決“確定性要件”的考慮范圍之內。①See Adrian U. Dorig, The Finality of U.S. Judgments in Civil Matters as a Prerequisite fo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in Switzerland, 32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71, 280 (1997).具體來說,當提起上訴或其他司法救濟的期間已過且未提起上訴或其他救濟,或不允許上訴或其他司法救濟機制時,在瑞士尋求承認與執行外國判決意義上的“確定性要件”方可滿足。②See Martin Bernet & Nicolas C. Ulme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Civil Judgments in Switzerland, 27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317 (1993).對于不恰當送達是否影響普通救濟的起算時間問題,瑞士聯邦法院在一起承認和執行美國判決的案件中裁定③Judgment of 18 December 1990, BGE 116 II 625, 630-1.認為,在裁判地法院并不要求判決予以送達的情形下,判決送達的缺失并不能阻止執行。④Martin Bernet & Nicolas C. Ulme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Civil Judgments in Switzerland, 27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325 (1993).當外國程序法載明了特殊救濟措施必須實施的期間時,外國判決的“確定性要件”不能成立。作為執行外國判決時的一般原則,瑞士法院僅僅在特殊的救濟措施并不存在某一法定的行使期間時才會忽略這些特殊救濟措施。⑤See Martin Bernet & Nicolas C. Ulme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Civil Judgments in Switzerland, 27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317 (1993).
依據《德國民事訴訟法》,若外國法院判決依據適用于該法院的法律尚未最終且確鑿,(德國法院)不會對該判決予以執行。⑥See The Germa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ZPO), §723.對于外國判決的承認,《德國民事訴訟法》并沒有明確規定“確定性要件”;相反,其僅僅規定了不予承認外國判決的理由,但其中并不包括外國判決欠缺“確定性”。⑦See The Germa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ZPO), §328.不過,德國主流學者認為,針對外國判決執行所規定的“確定性要件”通常亦應延伸至外國判決的承認。⑧See Dieter Martiny,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Germany and Europe, in Jürgen Basedow, Harald Baum & Yuko Nishitani, Mohr Siebeck, Japanese and Europea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391 (Tübingen 2008).據此,外國判決若要在德國承認與執行,其應“最終且確鑿”。“最終且確鑿”,意指判決不再受制于通常形式的上訴或審查。而對于案件在原審國獨立的訴訟程序中被重新審理的可能性并不能阻止判決的承認。①See Dieter Martiny,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Germany and Europe, in Jürgen Basedow, Harald Baum & Yuko Nishitani, Mohr Siebeck, Japanese and Europea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391 (Tübingen 2008).諸如撫養裁判,盡管其通常會因情形的變化而被變更,但這不影響該類裁判的確定性。②W. Wurmnest,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U.S. Money Judgments in Germany, 23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83-184 (2005).對于外國判決是否“最終且確鑿”,其判斷依據在于原審國法律,對此,《德國民事訴訟法》予以明確規定③See The Germa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ZPO), §723.。在一起承認與執行美國判決的案件中,德國最高法院認可美國法院作出的其判決未被上訴或撤銷的證明,并裁斷美國判決“最終且確鑿”。④Judgment of the Bundesgerichtshof, IXth Civil Senate, of 4 June 1992, Docket No.IXZR 149/91[1992]. See also Peter Hay,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merican Money Judgments in Germany-The 1992 Decision of the German Supreme Court, 40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729 (1992); Joachim Zekoll, The Enforceability of American Money Judgments Abroad: A Landmark Decision by the German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30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645 (1992).
對于外國判決的“確定性”,法國一直以來都持甚為寬松的態度。在1964 年之前,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法國不會承認在原審國不是“可執行的”外國判決。但是,不同于很多大陸法系國家將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限定在外國判決不再受制于普通上訴程序的情形,法國法院采取了更為寬松的立場,其在外國判決的上訴程序尚未結束時仍承認外國判決。除此之外,法國法院也愿意承認臨時或中間裁決。⑤See J. K. Grodecki, Enforcement of Foreign Maintenance Orders: French and English Practice, 8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32-33 (1959).從目前來看,外國判決若要獲得承認與執行,其沒有必要是“最終的”;通常意義上來說,“確定性要件”并不是外國判決獲得承認與執行的前提條件。⑥法國最高法院確立了外國判決在法國尋求承認與執行須滿足的五個要件:原審法院有管轄權;外國法院所遵循的程序是充分的;外國法院適用了法國法所指引的法律;符合法國公共政策;不存在與另一判決或未決的法國訴訟程序相沖突的情形。See Norel Rosner, Cross-borde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Money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2004, pp.230-231; Paul Hopkins,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194 (Yorkhill Law Publishing 2006).若要在法國獲得執行,外國判決只需要在原審國是“可執行的”即可。⑦See Norel Rosner, Cross-borde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Money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2004, p.254.
綜上,代表性大陸法系國家均保留了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中的“確定性要件”,但是它們在這一要件的表述上仍存在著一定差異。如前所述,大陸法系國家對“確定性要件”的表述主要有:“不存在普通的司法救濟”“最終的”“最終且確鑿”“可執行的”。一方面,盡管“確定性要件”在大陸法系國家立法中存在不同的表述,然而該要件的內涵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即它們均要求通常形式的救濟機制已經用盡,而不管該救濟機制是來自原審法院還是上訴法院。尤為突出的一點是,上訴可能性的存在或懸而未決的上訴都會使得判決的“確定性要件”不能滿足。①See Volker Behr, Enforcement of United States Money Judgments in Germany,13 Journal of Law and Commerce 218 (1994).另一方面,“確定性要件”本身是由被請求承認與執行國法律所規定的外國判決尋求承認與執行的前提條件之一;依據大陸法系主要國家的立法及司法實踐,對于外國判決是否滿足該要件,則要根據原審國有關法律來判斷其判決是否符合被請求承認與執行國的“確定性要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大陸法系國家如法國、荷蘭、比利時等國,在外國判決的“確定性要件”上的態度甚為寬松;其并非要求外國判決具備其他國家通常要求的“確定性要件”,而只是強調外國判決在原審國是“可執行的”即可,這與歐盟在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中“確定性要件”的立場一致。
(二)英美法系的代表性國家
在英國,若要使得某一外國判決成立普通法上的有效訴由,該判決必須是“最終的和確鑿的”,即當事人之間的所有爭議已經裁斷。②See James Fawcett, Janeen Carruthers & Peter North, Cheshire, North & Fawcett: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53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在這里,術語“最終的和確鑿的”是同義反復,③See Lawrence Collins, Dicey &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476 (Sweet &Maxwell 2000).即該要件指的是外國判決是最終的裁斷。在早期有關該要件的最具代表性案件Nouvion v. Freeman④See Nouvion v. Freeman, [1889] 15 APP Cas 1.中,英國上訴法院作出判決認為:西班牙法院Remate 判決不能確立英國普通法上的有效訴由。上議院維持了英國上訴法院的這一判決。Remate 判決是在簡易程序中作出的;在該程序下,當事人的主張尤其是被告的抗辯事由并不能完全提出;更為重要的是,該判決的存在并不影響當事人就其爭議另行提起完整訴訟,而且該完整訴訟的提起完全不受Remate 判決的影響,相反,Remate 判決卻因相應的完整訴訟的提起而不再具有拘束力。故Remate 判決對于當事人的任何一方來說均非已決事項,也沒有消除原始訴由。⑤See Nouvion v. Freeman, [1889] 15 APP Cas 1.在Blohn v. Desser 案⑥See Blohn v. Desser [1962] 2 Q.B. 116.中,奧地利法院作出了一項針對某一公司A 的判決,Blohn請求英國法院執行案外人Desser 的財產。根據奧地利法,該判決對案外人Desser具有拘束力,但需要另行提起針對該案外人的訴訟;不過,案外人Desser在另行提起的訴訟中可主張針對公司A案中未提出的抗辯。因此,雖然奧地利判決可以視為針對Desser的判決,但是該判決不具有終局性。①See Paul Torremans (ed.), Cheshire, North & Fawcett: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08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英國普通法對外國判決所要求的“確定性要件”并非指已不存在針對該判決的上訴權利。外國判決可能會在上訴中被推翻的事實,以及在原審國正在進行的針對該判決的上訴這一更為有力的事實均不能成為在英國提起承認與執行之訴的障礙。②See James Fawcett, Janeen Carruthers & Peter North, Cheshire, North & Fawcett,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53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不過,如果存在懸而未決的上訴,英國法院通常會依據衡平法上的管轄權中止對該判決內容的執行。此外,很重要的一點是,如果依據外國法該懸而未決的上訴將發生中止該判決執行的效力,該判決似乎在英國是不可訴的。③See James Fawcett, Janeen Carruthers & Peter North, Cheshire, North & Fawcett,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53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在美國,盡管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屬于州法事項,大多數州在制定有關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時依循了全國統一州法委員會會議1962 年通過的《統一外國金錢判決承認法》。④已有31 個州已經采納了該法。See Nellie Veronika Binder, Making Foreign Judgment Law Great Again: The Aftermath of Chevron v. Donziger, 51 Suffolk University Law Review 42 (2018).該法第二節載明了尋求承認與執行的外國判決應具有的“確定性要件”,即“該法適用于在原審國是‘最終的、確鑿的且具有執行力的’外國判決,盡管存在針對該判決的懸而未決的上訴或該判決的上訴期未滿。”美國《第四次對外關系法重述》因循了“最終的、確鑿的且具有執行力的”這些“確定性要件”,并指出判斷標準是外國判決作出地法律,上訴可能性之存在并不必然影響外國判決的確定性。⑤See Restatement 4th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S., §481.另外,在全國統一州法委員會于2005 年討論通過的《統一外國金錢判決承認法》中,對外國判決的“確定性要件”規定如下:“根據原審國法律,外國判決是‘最終的、確鑿的且具有執行力的’”。⑥See Uniform Foreign-Country Money Judgments Recognition Act, Section 3 (a)(2).
可見,美國法律對外國判決的“確定性要件”表述為:“外國判決應是‘最終的、確鑿的且具有執行力的’”。這里的“最終的”和“確鑿的”是一種同義反復。對于“最終的”含義,《第三次對外關系法重述》曾在其評注中定義為:“最終的”判決是指在原審法院不再受制于除了執行程序以外的額外程序拘束的判決。在決定某一判決是否為承認與執行意義上“最終的”判決時,美國法院通常會依據原審國的法律。①Se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of the Law, 4th,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 Jurisdiction, Sovereign Immunity, and Treaties, 2018, p.438.另外,即使仍然存在針對外國判決的上訴可能性或上訴懸而未決,該外國判決也被認為是“最終的”。至少有一個美國州法院,其在外國判決被撤銷之后拒絕重新考慮其已經作出了承認判決的案件。②See DSQ Property Co., Ltd., Plaintiff, v. John Z. DeLorean, Defendant, 1990 U.S. Dist. LEXIS 11880.在該案件中,英國法院撤銷了其作出的但已經被美國密歇根法院承認的判決;但美國拒絕就該判決的承認問題再行考慮。另外,至少有一個美國法院主張:仍然受制于原審國法院更改的判決也不缺乏“最終性”,只要請求執行的部分為該外國判決已經積累的數額部分。③See Coulborn et al. v. Joseph, 1943 Ga. LEXIS 284. Cf. Ronald A. Br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Money-Judg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earch of Uniformity and International Acceptance, 67 Notre Dame Law Review 253, 270 (1991).不僅如此,美國法院給予缺席判決與對席判決以同樣的法律效力;④See Restatement 3d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S., §481. Cf. Voileta I. Bala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ed for Federal Legislation, 37 The John Marshall Law Review 229, 248-249 (2003).也就是說,判決的“確定性”并不因判決是被告缺席情形下作出而受影響。與英國的做法一致,若上訴期間尚未經過或上訴懸而未決,美國法院也可以中止判決的承認與執行程序。
英美法系國家在外國判決“確定性要件”上的表述相對一致;它們所采用的術語主要是“最終的、確鑿的”以及“最終的、確鑿的且具有執行力的”。然而,相較于大陸法系國家對外國判決“確定性要件”所賦予的內涵,英美法系國家對外國判決“確定性要件”的理解要復雜得多。從一般意義上來講,英美法系主要國家對外國判決“確定性要件”的理解為原審法院已經就案件的所有爭議事項予以裁決,當事人不可能在原審法院尋求針對該裁決的新的普通程序;對于上訴或其他的救濟措施并不能否定外國判決的“確定性”。英美法系國家在評斷外國判決是否符合其所規定的“確定性要件”時的做法和大陸法系國家的做法一致:根據原審國的有關法律予以判斷,而上訴狀態的存在會使被請求法院中止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程序。但是在英美法系國家,外國判決“確定性要件”內涵的確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有關判例;尤其是在英國,對該要件的理解必須借助于復雜的案例體系,這增加了適用該要件的困難與不確定性。同時,英美法系國家或地區在評判外國判決的確定性時也受其本身對“確定性”理解的影響,
(三)“確定性要件”的協調或統一
“確定性要件”標準的差異導致判決承認與執行要件的不一致,影響或阻礙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因此,圍繞該要件的國家間協調或統一具有突出價值。各國“確定性要件”國內法機制存在諸多差異,因此國際組織的協調或統一便顯得十分必要,而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和歐盟在該領域的實踐最具代表性。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在1971 年通過的《外國民商事判決承認與執行公約》(以下稱“1971 年公約”)將外國判決的“確定性要件”明確規定為判決在締約國之間承認與執行的前提條件之一:外國判決“不再受制于原審國普通形式的審查”;如果要使外國判決在被請求國是“可執行的”,其必須在原審國是“可執行的”。①See HCCH, Convention of 1 February 1971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rticle 4(2).1971 年公約未能得到廣泛接受,亦未得以簽署適用。②Ronald A. Brand & Paul M. Herrup, The 2005 Hagu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Chapter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Ronald A. Br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the Preliminary Draft Hague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s Convention, 62 Universityof Pittsburgh Law Review 582 (2001).因而,該公約的“確定性要件”方案未能成為普遍標準。1992 年海牙判決計劃重啟之后,構架為各國認可的國際公約再次提上議程。1999 年《外國民商事判決承認與執行臨時草案公約》(以下稱“1999 年草案公約”)③See https://www.hcch.net/en/projects/legislative-projects/judgments/preparation-of-a-pr eliminary-draft-convention-1997-1999-,visited on 9 August 2019.規定,“要獲得承認……判決須在原審國具有既判力(res judicata)”“……判決在原審國須具有執行力。”然而,“如果判決在原審國處于審查之中或尋求該審查的時效未過,可以暫停承認或執行”。④Preliminary Draft Outline to Assist in the Preparation of a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 and the Effects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rticle 25(2)-(4).1999 年草案公約未能為各國接受,因此其確立的“確定性要件”規則亦未被確立為普遍標準。
作為海牙判決計劃的一項“小公約”,海牙國際私法會議2005 年通過的《選擇法院協議公約》(以下稱“2005 年公約”)規定:只要判決在原審國“具有效力”,其應被承認;只要判決在原審國是“可執行的”,其應被執行。⑤See HCCH,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rticle 8(3).海牙國際私法會議2019 年公約采取的立場與2005 年《選擇法院協議公約》一致。⑥See HCCH, Convention of 2 July 2019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ements in Civil Commercial Matters, Article 4(3).從歷史發展來看,在協調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中的“確定性要件”問題上,海牙國際私法會議自1971 年公約以來的立場并非完全一致,而其當前采納的立場亦未沿襲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常用的表述,如“最終的”或“最終的和確鑿的”,亦未因循其傳統的關于判斷判決確定性的標準——“不再受制于原審國普通形式的審查”或“既判力”等;而是采用了“具有效力”以及“可執行的”等一般性概念。這一最新立場已經偏離了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的傳統立場,亦不同于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關于“確定性要件”之規定。應當說,傳統的“不再受制于原審國普通形式的審查”與大陸法系在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問題上所規定的“確定性要件”內涵有著諸多重合之處,因為它們都將判決的“確定性”聚焦于原審國是否存在針對該判決的普通救濟,即上訴程序;但是其與英美法所規定的“確定性要件”的內涵相差較遠,因為英美法系判決“確定性要件”主要側重于原審法院已經解決了案件的所有糾紛,這也解釋了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在其晚近的公約中,放棄了其傳統的“確定性要件”,引入更為開放、中立且具有包容性的標準。
一些區域性國際公約或文件在外國判決承認和執行的“確定性要件”方面有著不同的規定和立場,最具代表性的是歐盟布魯塞爾判決體系的相關實踐。1968年《布魯塞爾公約》①See EC, The 1968 Brussels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Offical Journal of European Union C27,26.1.1998, Article 31.、取代該公約的2001 年《布魯塞爾條例I》②See EC,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44/2001 of 22 December 2000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Offical Journal of European Union L12, 16.1.2001, Article 38.以及最新修訂的《布魯塞爾條例Ⅱ》③EU, Regulation (EU) No.1215/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December 2012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Recast), Offical Journalof European Union L 351/1, 20.12.2012, Article 39.等構架起布魯塞爾判決體系,其在外國判決“確定性要件”的規定和立場一致。該體系區分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判決的承認無須滿足任何“確定性要件”,這主要是考慮到在臨時救濟以及單方訴訟等程序中作出的判決仍需要承認,盡管該類判決并不總是具有既判力等確定性。④See P. Jenard, Report on the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5.3.79, No.C 59/43.值得特別提及的是,歐盟2013 年《關于相互承認民事保護措施的條例》統一了歐盟內臨時救濟在特定領域的承認和執行規則。⑤EU, Regulation (EU) No.606/201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June 2013 on Mutual Recognition of Protection Measures in Civil Matters,Offical Journal of European Union, L181/4, 29.6.2013.這樣以來,可被承認的判決既包括全部或部分裁決,也包括受到上訴或其他挑戰以及僅僅具有臨時可執行性的裁決、中間裁決等。⑥See Peter Mankowski & Ulrich Magnus, Brussels I Regulation 627 ( 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2012).盡管布魯塞爾判決體系并未對判決的承認引入明確、一致的“確定性要件”,然而其賦予被請求國在外國判決處于普通上訴狀態時可以暫緩承認的權力。⑦See, e.g., the 1968 Brussels Convention, Article 30; Brussels I Regulation, Articles 37 & 46 and Brussels I Regulation Recast, Articles 36 & 39.對于判決的執行來說,相關判決在原審國應為“可執行的”。⑧See 1968 Brussels Convention, Articles 26 and 31; Brussels I Regulation, Articles 33 and 38.此外,1988 年《盧加諾公約》和2007 年新《盧加諾公約》①EU,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Offical Journal of European Union L339,21.12.2007, pp.3-41.在外國判決的“確定性要件”方面采取了與布魯塞爾判決體系同樣的立場。除布魯塞爾判決體系之外,1928 年《布斯塔曼特法典》中,外國判決的“確定性要件”也被規定為“可執行的”。②參見《布斯塔曼特法典》第423(4)條。
這些區域性的國際公約或文件旨在最大程度地在可容許的范圍內簡化判決的承認與執行條件,減少拒絕承認與執行外國判決的理由;而降低外國判決“確定性要件”的門檻是加速判決流動的重要途徑之一,同時也有助于防止被申請人蓄意破壞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進程。因此,上述區域性判決公約或文件在“確定性要件”方面的規定較為寬松,布魯塞爾判決體系下諸公約或條例甚至在判決的承認方面并不引入“確定性要件”。另外,無論是2001 年《布魯塞爾條例I》(包括其修改版)還是1988 年的《盧加諾公約》,其調整范圍均包含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之間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問題;因此,兩大法系在外國判決“確定性要件”方面的不同是可以彌合的,或者說存在可以公共認可的標準。術語“可執行的”作為判決的“確定性要件”得到了廣泛的采用,而這更多的是針對外國判決的執行而非承認本身引入的“確定性要件”。
三、海牙判決公約體系的方案
前文已經述及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在其1971 年公約中引入的有關“確定性要件”的立場,并梳理、闡釋了海牙國際私法會議重啟海牙判決計劃后的諸項公約或草案公約中關于“確定性要件”的相關規定和歷史沿襲。本部分主要圍繞海牙判決計劃下的2005 年公約與2019 年公約,就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晚近以來的基本立場予以闡釋,剖析這一主流國際組織在協調或統一國家間判決承認與執行的“確定性要件”中的態度及歷史演變,并就其立場予以評析。這兩項公約是海牙國際私法會議1992 年啟動“海牙判決計劃”以來最為重要的成果,該公約有關“確定性要件”的規則代表著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成員國的共識。
(一)2005年《選擇法院協議公約》
2005 年公約調整排他性選擇法院協議基礎之上的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在“確定性要件”方面,其要求“外國判決在原審國具有效力,且只有當該判決在原審國具有執行力時方可獲得執行”。③See HCCH,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rticle 8(3).具體來說,“具有效力”指的是所涉外國判決“合法有效”且處于生效之中。①See Trevor Hartley & Masato Dogauchi, Explanatory Report on the 2005 Hagu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Convention (Hartley/Dogauchi Report), para.171.在該公約的起草過程中,曾存在較大爭議,因考慮到各國的差異性規定,故采行該立場。②參見何其生:《中國加入海牙〈選擇法院協議公約〉的規則差異與考量》,《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4 期,第84 頁;喬雄兵:《論外國法院判決承認與執行中的終局性問題》,《武大國際法評論》2017 年第1 期,第76 頁;王吉文:《判決終局性: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上一道難以逾越的坎》,《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11年第4期,第141頁。該公約考慮到不同法系或國家在“確定性要件”中的不同立場,在“確定性要件”的規定中訴諸“具有效力”和“執行力”等更為中性的表達,以求摒除該要件解釋可能產生的困難。
值得注意的是,該公約對“確定性要件”的規定區分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承認”意味著賦予外國法院作出的權利和義務裁斷以效力,而執行則意味著被請求法院通過采取措施強迫被告遵守原審法院的判決。依據該公約,承認和執行須滿足的“確定性要件”并不一致,即前者要求“發生效力”,而后者需要“具有執行力”。鑒于執行通常須以承認為前提,③See Trevor Hartley & Masato Dogauchi, Explanatory Report on the 2005 Hagu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Convention (Hartley/Dogauchi Report), para.170.故具有“執行力”的外國判決亦應“發生效力”。在外國判決確定性的法律適用標準方面,2005 年公約指明:判斷判決是否“具有效力”或“執行力”的標準在于原審國法律,而非被請求國法律。④See HCCH,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rticle 8(3).該公約區分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并規定不同的“確定性要件”,判決的執行之“執行力”要件等均與布魯塞爾判決體系中的“確定性要件”一致,亦表明該公約的“確定性要件”受歐盟實踐的影響較大。
對于在原審國發生效力與具有執行力的外國判決,如果該判決尚處于某種特殊狀態之下,被請求國可以暫緩承認與執行或附條件地不予承認與執行。具體來說,若外國判決在原審國尚處于審查之中,或尋求“普通審查”的時限未過,那么對該外國判決的承認或執行可予推延或拒絕;然而,該類情形下的拒絕承認或執行不阻礙后續判決承認與執行的再次申請,⑤See HCCH,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rticle 8(4).且不應對后續申請形成偏見。⑥See Trevor Hartley & Masato Dogauchi, Explanatory Report on the 2005 Hagu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Convention (Hartley/Dogauchi Report), para.174.對那些在原審國尚處于審查之中或“普通審查”期限未過的外國判決,被請求國雖無義務但可以承認或執行該類判決,或者要求申請人提供擔保。⑦See Trevor Hartley & Masato Dogauchi, Explanatory Report on the 2005 Hagu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Convention (Hartley/Dogauchi Report), para.173.這是2005 年公約在引入“確定性”要件的同時,設置有利于外國判決承認和執行的矯正機制,以軟化“確定性要件”的適用。基于此,2005 年公約在形式上提供了較為明確的“確定性要件”標準,并在實質上引入了靈活的、有利于外國判決有效承認、執行的規則和矯正機制,是一種折中、值得肯定的“確定性要件”構建路徑。
(二)2019年《承認與執行外國民商事判決公約》
2019 年公約確立了廣泛領域的民商事判決承認與執行原則,①See HCCH,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rticle 4.其在“確定性要件”上的規范完全因襲了2005 年公約的做法。在原審國“具有效力”的判決應予承認,且在原審國具有“執行力”時方可在被請求國執行。公約區分“承認”和“執行”,分別規定不同的“確定性要件”。同樣地,在對“確定性要件”的界定上,2019 年公約亦回避了因循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對“確定性要件”的慣常界定,而是在對兩大法系“確定性要件”予以折中考慮后作出選擇。此外,《公約草案臨時解釋報告》(以下稱“解釋報告”)將“具有效力”解釋為:合法有效且處于生效之中。②See Francisco J. Alférez,F. Garcimartín & Geneviève Saumier, Judgments Convention: Revised Preliminary Explanatory Report 2018, para.102.在“確定性要件”的判斷標準上,判斷判決是否“具有效力”的標準在于原審國法律,而非被請求國法律。③See HCCH, Convention of 2 July 2019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ements in Civil Commercial Matters, Article 4(3).
2019 年公約充分考慮到不同法系對判決確定性的不同認識,尤其是關于外國判決既判力與執行力的不同理解,并完全因循了2005 年公約有關“確定性要件”的矯正機制。有鑒于此,對于即使滿足“確定性要件”的判決,被請求國仍可根據外國判決的特殊狀態采取不同的措施:如果具備公約“確定性要件”的外國判決在原審國處于被審查狀態,或尋求“普通”審查的時限未過,被請求法院可以承認或執行,或推遲承認或執行,或拒絕承認或執行,但這并不影響后續重新提請承認或執行。對于核心概念——“普通審查”與“特別審查”之區分,解釋報告著重考慮相關審查是否為正常訴訟程序的一部分、是否為當事人所合理預見以及是否受到合理的時限期間所限制。④See Francisco J. Alférez,F. Garcimartín & Geneviève Saumier, Judgments Convention: Revised Preliminary Explanatory Report 2018, paras.106-112.
(三)方案的優點與不足
海牙判決公約體系“確定性要件”的現行方案充分考慮到不同國家、法系在“確定性要件”上的差異性,借鑒了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的傳統經驗與歐盟在該方面的有益實踐,其協調或統一之努力成為各國合作的重要起點,可成為各國廣泛接受的基本方案。其在形式上引入了較為明晰的“確定性要件”,區分判決的“承認”和“執行”,并在實質上確立了有利于認定外國判決具備確定性的標準和矯正機制,從而有利于增進國家間判決的承認與執行,這符合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的總體趨勢。
然而,海牙判決公約體系的現行方案就“確定性要件”方面的規定仍然存在一些不甚清晰的方面。比如,其應進一步明確判斷外國判決是否“具有效力”的依據在于原審國法律,厘清其與被請求國標準的界限;海牙判決公約的現行方案尚未觸及被承認的外國判決在被請求國將產生何種效力,已屬“確定的”外國判決被承認后將在被請求國產生的效力范圍等問題亦應澄清。此外,由于各國圍繞判決的確定性進行“普通審查”①See HCCH,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rticle 8(4).的類型及范圍各異,各國提交其國內法中符合公約目的的“普通審查”清單,可避免適用該公約的過程中產生的諸多分歧,且將來相關公約解釋報告亦可對“普通審查”作進一步闡釋和界定。而對于“具有效力”的各國判決的范圍,亦應成為海牙判決公約體系應解決的重要事項。
四、我國立法及司法實踐
(一)立法概況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稱《民事訴訟法》),外國判決要在我國承認與執行,其應“發生法律效力”,②參見2017 年《民事訴訟法》第265 條。雖然《民事訴訟法》在2017 年被修訂,但是有關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條款沒有任何改動。因此,對于外國判決的“確定性要件”來說,“發生法律效力”這一術語從《民事訴訟法》1991年頒行至今仍延續適用。該表述在形式上類似于海牙判決公約體系中的“產生效力”之標準。在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語境下,“發生法律效力”指的是判決已經產生了拘束力、確定力以及執行力。具體來說,下列判決是“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以及依法不準上訴或者超過上訴期沒有上訴的判決、裁定。③參見2017年《民事訴訟法》第155條。然而,對于依據哪一國法律確定外國判決是否“發生法律效力”,我國《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民事訴訟法》中的“確定性要件”未區分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因此該要件同等適用于外國判決在我國的“承認”和“執行”。
除《民事訴訟法》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等法律規范④參見喬雄兵:《論外國法院判決承認與執行中的終局性問題》,《武大國際法評論》2017年第1期,第78-79頁。亦規定了特殊類型的外國判決,如破產判決在我國尋求承認與執行時的“確定性要件”即是“發生法律效力”。⑤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第5條。對于外國離婚判決的承認與執行,我國法律規定的“確定性要件”也是“發生法律效力”。⑥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中國公民申請承認外國法院離婚判決程序問題的規定》第12(1)條。總的來看,我國法律中的“確定性要件”是外國判決“發生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民商事判決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稿)》在“確定性要件”的表述上亦采用了“發生法律效力”之表述。①《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民商事判決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稿)》第15(3)條。對于“確定性要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稱《民訴法解釋》)要求申請人提交申請書,并附外國法院作出的“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②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543條。但是對于何為“發生法律效力”并無相關解釋。
在我國與諸多國家所締結的雙邊司法協助條約③我國已締結39項中外民商事雙邊司法協助協定,37項已經生效。關于中外民商事司法協助條約締約情況,參見外交部網站,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tyfg_674913/t1215630.shtml,2019年8月1日訪問。中,外國判決“確定性要件”的表述不同于《民事訴訟法》等國內法之規定;④參見喬雄兵:《論外國法院判決承認與執行中的終局性問題》,《武大國際法評論》2017年第1期,第80-81頁。相反,絕大多數表述為“已經確定”⑤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關于民事、商事司法協助的協定》第22(3)條。,或“已經生效”⑥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意大利共和國關于民事司法協助的條約》第21(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秘魯共和國關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協助的條約》第23(1)條。,或“已經生效和可以執行”⑦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波蘭人民共和國關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協助的協定》第20(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立陶宛共和國關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協助的條約》第17(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關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協助的條約》第21(1)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希臘共和國關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協助的協定》第22(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協助的條約》第17(2)條。,或“終局的和可以執行的”⑧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巴西聯邦共和國關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協助的條約》第23(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科威特國關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協助的協定》第24(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埃塞俄比亞聯邦民主共和國關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協助的條約》第24(1)條。,以及“終局和具有執行力的”⑨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關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協助的協定》第24(2)條。。一方面,對于這些雙邊條約采取相互之間差異較大的“確定性要件”之表述,并不存在顯在的合理理由;另一方面,對于這些雙邊條約采取與我國《民事訴訟法》等國內法中“確定性要件”相去甚遠的表述,亦難以解釋。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下,尚不存在相關法律對這些差別予以區分和闡明,這容易引起條約適用中的不確定性。對于這些雙邊條約中的“確定性要件”,最基本的一個問題是所采用的術語“已經確定”“已經生效和可以執行”“終局的和可以執行的”等是否等同于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的“發生法律效力”。關于確定性的判斷標準,我國現有雙邊條約均規定應依據“作出裁決的締約一方的法律”①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關于民事、商事司法協助的協定》第22(3)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意大利共和國關于民事司法協助的條約》第21(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巴西聯邦共和國關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協助的條約》第23(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關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協助的條約》第23(1)條。,該規定符合國際社會的一般實踐。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將承認和執行的范圍限定于“生效”判決②參見《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第1條。,并就“生效”的判決給予了列舉式載明③參見《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第4條。。該安排將“確定性要件”界定為“生效”判決,因循了2019 年公約的“確定性要件”之表述;不僅如此,該安排詳細列舉了內地及香港可作出“生效”判決的法院清單或情形④該安排所稱“生效判決”:(1)在內地,是指第二審判決,依法不準上訴或者超過法定期限沒有上訴的第一審判決,以及依照審判監督程序作出的上述判決;(2)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指終審法院、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及原訟法庭、區域法院以及勞資審裁處、土地審裁處、小額錢債審裁處、競爭事務審裁處作出的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這似乎可為解決圍繞“確定性要件”的諸多難題,提供可取的“確定性要件”之締約方案。
(二)司法實踐
本部分意在梳理我國近13 年來具有代表性的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案件,分析“確定性要件”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的適用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在早期的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案中,如具有代表性的安托瓦納·蒙杰爾2005 年提起的申請承認與執行法國破產判決案⑤參見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5〕穗中法民三初字第146號民事裁定。中,申請人提交了一份由法國瓦提艾市商業法院的書記官皮埃爾·奧利維埃·于朗于2004 年7 月28 日出具的證明,意在證明該申請人申請承認的法國判決已經生效。據此,在并未分析該法國判決是否以及如何滿足《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關于民事、商事司法協助的協定》中的“確定性要件”的情況下,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徑直認定該判決已生效。而在一些案件中,如在2016 年法國K.C.C 有限責任公司申請承認和執行法蘭西共和國貢比涅商業法院RG2013F00048 號商事判決案⑥參見〔2016〕湘10協外認1號。,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其裁判文書中并未對“確定性要件”予以任何裁定。早期具有重大影響的1994 年五味晃案⑦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6年第1期,第29頁。,2003 年明斯克自動線生產聯合公司申請承認及執行白俄羅斯共和國最高經濟法庭判決案⑧參見〔2003〕民四他字第4號。,2003 年受理的意大利B & T Ceramic 公司申請承認和執行意大利法院破產判決等案件中,我國法院亦未對“確定性要件”作出任何裁定。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年胡克拉床墊和軟墊家具廠有限公司(以下稱“胡克拉公司”)申請承認及執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奧芬堡州法院第20460/07判決案①參見〔2010〕民四他字第81號。中,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申請承認(及執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奧芬堡州法院第20460/07判決一案的請示的復函》中,不認可德國奧芬堡州法院向北京富克拉家具銷售有限公司郵寄德國判決書的送達方式,故認定該判決尚未對北京富克拉家具銷售有限公司“發生法律效力”。在本案中,相關法院依據送達非法而認定德國判決對被申請人未“發生法律效力”。
2005 年施耐德電氣工業公司申請承認與執行法國巴黎大審法院判決案②參見〔2005〕溫民三初字第155號。是少數我國被請求法院較為詳盡地闡釋“確定性要件”的案例。為證明所涉判決的確定性,申請人施耐德電氣工業公司向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稱“溫州中院”)提交了巴黎上訴法院出具的涉案判決已經生效的證明書副本及中文譯本。溫州中院認為法國判決書本身沒有明確指出判決已經確定,上訴法院的證明僅表明巴黎上訴法院無任何關于所涉案件對席判決的上訴記錄,故其依據《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的規定簽發民事判決生效書。然而,《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規定了在判決書簽發當年可允許取消逾期導致失去上訴的權利,故溫州中院認定涉案判決尚未確定。此案中,溫州中院對確定性的適用依據模糊不清,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關于民事、商事司法協助的協定》中載明的按照作出判決的締約一方的法律判斷確定性之規定。③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關于民事、商事司法協助的協定》第22(3)條。從措辭來看,其更多地是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有關上訴導致判決不能發生效力之規定判斷法國判決的確定性,進而否定法國判決的確定性。
在近幾年承認與執行外國判決的案件中,我國法院亦未對外國判決的“確定性要件”予以明確審查。比如,在申請人劉某與被申請人陶某、童某申請承認和執行美國法院民事判決案④參見〔2015〕鄂武漢中民商外初字第00026號。中,受訴法院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未對美國判決的確定性予以裁斷,被申請人亦未針對該要件提出異議。在法國K.C.C 有限責任公司申請承認和執行法蘭西共和國貢比涅商業法院RG2013F00048號商事判決案⑤參見〔2016〕湘10協外認1號。中,受訴法院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及被申請人均未提及法國裁判的確定性問題。同樣地,在Kolmar Group AG 與江蘇省紡織工業(集團)進出口有限公司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民事判決案⑥參見〔2016〕蘇01協外認3號。中,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并未就新加坡法院判決確定性問題予以裁判,而是徑直承認和執行了該判決。在納爾科公司有限責任公司申請承認與執行美國伊利諾伊州北部東區分庭判決案⑦參見〔2017〕滬01協外認16號。中,美國判決的確定性問題未成為當事人爭辯的焦點,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據申請人提交的判決副本及中文譯本認定美國判決為最終判決且已生效,并最終承認與執行了該美國判決。
基于上文的考察,可以大致得知我國一些法院對“確定性要件”的適用未給予充分重視和關注,未對外國判決是否確定的標準或法律適用等問題作出明確、有說服力的裁判。對此,最高人民法院亦無關于該要件的統一解釋。囿于現行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法律之限制,我國一些法院通常聚焦于“互惠”的存在以及“送達”的合法,而對外國判決的確定性、外國法院管轄權、公共政策等諸要件鮮有觸及或闡釋。①See, e.g., Wenliang Zhang,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hina: A Call for Special Attention to Both the Due Service Requirement and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12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43 (2013); 張文亮:《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語境下“送達抗辯”研究》,《當代法學》2019年第2期,第150頁。一方面,這與我國《民事訴訟法》的原則性規定存在重要關系;另一方面,我國一些法院可能尚未在實踐中厘清或架構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的要件體系。從形式上說,我國《民事訴訟法》引入了“確定性要件”,盡管較為框架化和原則性,但這在原則上并不妨礙我國法院在實踐中對該要件予以適用,并加以豐富和發展。即便是在存在雙邊條約的情形下,司法實踐亦未充分關注“確定性要件”。除此之外,在前述案件中,鮮有被執行人圍繞“確定性要件”對外國判決的承認和執行加以抗辯,這亦是我國司法實踐中該要件尚未凸顯的另一緣由。
(三)若干建議及完善進路
針對當前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現狀,一方面,我國應改變立法及司法實踐不重視“確定性要件”的做法,確立“確定性要件”的合理地位。“確定性要件”已是各國普遍確立的承認與執行外國判決的重要條件,重要的國際性和區域性法律文件均將該要件置于凸顯的位置,外國判決確定與否決定著該判決能否得到順利承認或執行。我國在立法上應確立體系化的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法律框架,其中,“確定性要件”的合理與體系化是重要內容。伴隨體系化的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之立法體系,司法實踐亦應擺脫以往片面關注部分承認與執行要件而忽視包括“確定性要件”等諸要件的實踐做法。由于我國目前締結的雙邊司法協助條約的數量有限,因此,有必要完善《民事訴訟法》等法律中有關“確定性要件”的相關規定。鑒于《民事訴訟法》有關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立法的較為滯后,②我國《民事訴訟法》自1991 年頒布以來,有關“確定性要件”在內的外國判決承認和執行之規定還未曾有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實踐突出并完善“確定性要件”適用的思路可能可取。
另一方面,我國“確定性要件”的架構應遵循合理的思路。首先,應明確“確定性要件”的標準或法律適用。盡管在原審國已屬確定的判決未必依被請求國的相關標準亦屬確定,然而依據原審國法律判斷外國判決確定性的思路是可取的。這可以避免不同國家依據各自標準對同一判決認定為不同的效力狀態,因而成為目前國際主流標準。由于外國判決在被請求國的效力不應大于其在本國的效力,①參見張文亮:《論外國判決在內國的效力——兼析外國判決在我國的效力》,《國際法研究》2013年第9卷,第76頁。依據原審國法律判定外國判決的效力可以避免被請求國賦予不具有效力的外國判決以本地效力。再者,有關“確定性要件”適用中的適度矯正或制衡成為必要。對于依據原審國法律已屬確定的外國判決,可以參照2005 年公約或2019 年公約的立場,盡管其在原審國尚處于審查之中或尋求“普通審查”的時限未過,被請求國仍然可以在申請人提供擔保的情形下承認和執行,或者暫停承認和執行程序,而非徑直予以拒絕承認和執行,以保障和創造有利于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的環境。
處于上訴或再審狀態的判決是判決具有的兩種典型狀態,其確定性應予明確。外國判決處于“上訴”狀態只是外國判決的一種狀態,該狀態下的判決依據原審國法律可能是確定的,亦可能是不確定的;如上文所述,應以原審國法院而非被請求國的法律加以判斷,并借鑒2005年公約或2019年公約予以適度矯正,是適用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中的“確定性要件”的合理路徑。再審是原審法院針對其自己在先作出的判決的一種重新審理程序,該程序通常會破壞在先判決的確定性。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和當事人均可啟動再審程序并從證據、回避、程序以及枉法裁判等方面規定了13 種當事人可申請再審的情形。《民訴法解釋》確認了裁判發生法律效力后,發生新的事實,當事人再次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正因為如此,有學者認為我國的再審程序易被啟動且適用條件不太嚴格,所以判決不符合普通法系要求的“確定性要件”;②See LIU Nanping, A Vulnerable Justice: Finality of Civil Judgments in China,13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35-98 (1999).顯然,該主張訴諸被請求國的法律判定外國判決并不合理。然而,即便再審程序是我國訴訟中的“非常態”訴訟程序,但是若該程序的適用條件較為寬松且易于啟動,那么會阻止判決的確定性,一方當事人從訴訟或糾紛解決策略的角度啟動該程序,則容易為被請求國認定為相關判決欠缺確定性。從1991《民事訴訟法》頒行以來,我國《民事訴訟法》對再審條件及啟動時限等多有修改,使其朝著更為嚴格適用的方向發展,凸顯其“非常程序”的特質,③比如,在啟動再審程序的時限方面,我國《民事訴訟法》經歷了從無時間限制到有時間限制,以及兩年時限到六個月時限的過程。參見2007 年《民事訴訟法》第184 條和2012年、2017年《民事訴訟法》第205條。回應那些對我國判決確定性存疑的主張。
欠缺確定狀態的判決亦非全然不能獲得承認與執行,尤其是對跨國糾紛解決及國際民商事訴訟意義日漸凸顯的臨時救濟而言,其跨境承認與執行之意義更加突出。④參見張文亮:《論臨時救濟中的第三人——以我國涉訴民商事臨時救濟為視角》,《現代法學》2016年第1期,第165頁。在歐盟現行布魯塞爾判決體系下,對案件實體有管轄權的歐盟成員國法院作出的臨時救濟可以在其他成員國得到承認與執行,①See, e.g., EU, Preamble (33), Regulation (EU) No.1215/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December 2012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Recast), 20.12.2012,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351/1.盡管這種臨時措施并不具備傳統意義上的“確定性”。而布魯爾塞爾判決體系傳統上并不要求外國判決的“承認”應以外國判決具有確定性為前提,也是考慮到特殊性的判決雖然并不具有確定性,但其仍然需要得到域外的承認或執行。歐盟2013 年《關于相互承認民事保護措施的條例》致力于歐盟內臨時救濟的自由流動,亦提供了各國在臨時救濟領域承認和執行的典范。②參見張文亮:《涉外臨時救濟的三重困境及應對分析——兼評我國現行涉外臨時救濟體系》,《現代法學》2017年第6期,第164頁。我國現行司法實踐中未出現外國臨時救濟的承認和執行,然而,隨著該類救濟在涉外糾紛解決中重要性日益凸顯,其跨境承認與執行亦應成為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規范的對象。
我國已締結若干雙邊司法協助條約,其大多就“確定性要件”作了相對明確的規定,我國司法實踐應充分關注并適用其中的“確定性要件”。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應根據雙邊條約的規定切實適用依原審國法律確定外國判決的“確定性”,并對差異較大的“確定性要件”予以統一解釋,以有效避免司法實踐的混亂。對將來我國擬締結的雙邊司法協助條約,可借鑒2019 年公約就“確定性要件”引入的主流標準,確立更加合理且有利于判決承認與執行的“確定性要件”。
五、結語
隨著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事項的重要性日益凸顯,③參見張文亮:《外國判決在中國的承認與執行:現狀及未來》,《武大國際法評論》2016年第2期,第48頁。圍繞外國判決諸要件的擬定、適用以及協調或統一成為迫切問題,而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的“確定性要件”已成為廣泛關注的問題。各法域或法系之間在該要件上的立法與實踐多有差異,這造成了協調或統一的困難,也使得當事人在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中可能遭遇諸多困境,被執行人也可能圍繞“確定性”惡意破壞或阻礙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在協調或統一“確定性要件”中,海牙判決公約體系的方案具有代表性,其意在調和諸法系或國家之間在“確定性要件”上的分歧,引領了國際社會架構合理的“確定性要件”。歐盟對外國判決的承認,原則上并不要求“確定性”,其代表了“確定性要件”協調或統一的更高目標。
我國國內法確立了“發生法律效力”之“確定性要件”,雙邊民商事司法協助協定引入的確定性標準并不統一,尚不能為司法實踐提供有效引導。在我國現行司法實踐中,有關“確定性要件”的適用亦未引起我國法院足夠重視,且已有實踐相對混亂。引入合理的“確定性要件”并保障我國法院恰當適用該要件應成為我國有關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之立法改革與司法完善的重要方面。以海牙判決公約體系的協調與統一為藍本,我國有關“確定性要件”的立法應脫離傳統立法對判決確定性的固有認識,從比較法的視域出發,確立原審國法律作為判斷“確定性要件”的依據,并對處于特殊狀態下的外國判決予以適度制衡。我國未來締結的雙邊司法協助條約,亦應確立相對一致的確定性標準,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的協調和統一方案同樣值得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