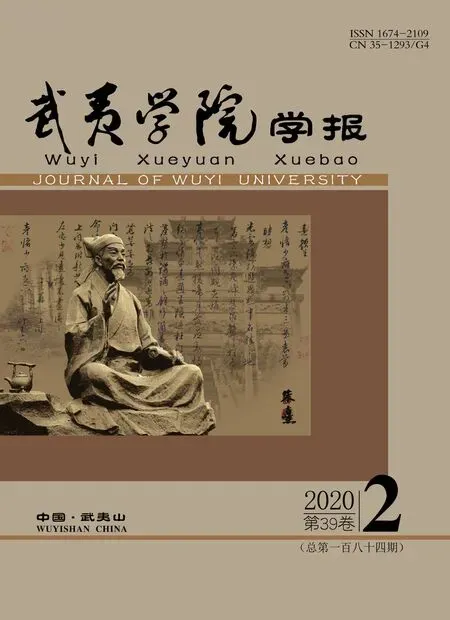論罪數理論在刑事裁判文書中的適用
(福建警察學院 刑罰執行系,福建 福州 350007)
“我國罪數理論借鑒于德國與日本,德、日刑法對罪數問題皆有明文規定,其學理研究往往依循立法。”[1]德日的罪數論規定在刑法條文里,罪數體系有法律依據,而我國的罪數理論并無刑法規定,罪數判斷的適用遭到體系建構的障礙,罪數論的規范適用在司法實踐層面的展開依靠著法官的智慧與法律適用能力。罪數理論是一個在解釋論范疇里研究的問題,它不僅影響了我國刑法理論體系的構建,也影響了我國司法實踐活動的開展。罪數論要解決的問題是當行為人觸犯數個罪名時,法院是如何確定罪名的,刑罰是怎么作出來的。
一、問題的提出
罪數論在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中成為難題,一是因為“這是一個古老的問題,從羅馬法時代到今天,它依然是學理上無奈的痛,亦成為實務上深怕觸碰的傷痕,這是一個無解的難題”[2];二是“因為關于罪數問題的學說或者實務,大皆直接遽下判斷,鮮少說明其法理所在。”[3]在我國刑法未明文規定罪數問題且刑事裁判文書多數未對罪數問題進行說理的情況下,罪數理論在裁判文書中的適用就會變得混亂和棘手。有些刑事裁判文書雖有法理的釋明,但只是寥寥數語,說理極其簡單,甚至變成簡單嵌套內容的文書。有的刑事裁判文書說理過程中運用了刑法理論知識,出現了“競合”和“牽連”,但只是簡單的論述,如陳百泉、郁樹良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案,“被告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雖系為了騙取國家稅款,但法律明確規定,此行為應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且此罪的法定刑重于偷稅罪;被告人的行為即使與該兩罪發生牽連關系或競合關系,亦應按擇一重罪處斷的原則處理。”[4]罪數理論適用于刑事裁判文書中應有規范性的缺乏導致刑事裁判文書功能的發揮受到限制,不僅影響到刑事裁判文書說理功能的展開還導致刑事裁判文書陷入模板化的泥沼中。
罪數論的釋法說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意見所要求的,刑事裁判文書法律規范適用的罪數需要被闡釋清楚,卻由于罪數論的體系發展問題遇到了困難。首先,由于我國刑法受蘇聯刑法影響深遠,罪數問題的立法例有別于德日等國家,刑法條文中并未具體規定罪數形態,我國的罪數理論體系尚未構建且構建過程存有太多障礙與困難,這是罪數理論適用于刑事裁判文書時理論上的第一重障礙,這導致在刑事裁判文書出現說理與否的尷尬,也會出現適用的混亂。其次,罪數理論在刑事裁判文書中如何說理是另一重障礙。從我國刑事裁判文書的發展過程看,刑事裁判文書一直跳不出往文書里堆砌證據與審理過程的窠臼。再加上罪數理論之爭由來已久,既復雜又混亂,不是一時之間就能得到解決的,刑事裁判文書中的罪數說理問題的解決就難上加難。本文相關問題的研究是放在我國傳統罪數理論基礎上進行的,探討的是罪數理論在刑事裁判文書適用的原因及如何適用的問題。
二、罪數理論在刑事裁判文書中適用的原因剖析
罪數是指行為人犯的罪的個數,罪數論是指確定行為人所犯罪的個數及如何適用刑罰的理論概括。罪數的判斷是法官量刑的基礎,罪數理論的不規范適用將會影響到法定刑的確定,進而影響到刑事裁判文書的釋法說理。我國刑法中雖沒有關于罪數形態的具體規定,但在刑法的一些條文中可以找到有關罪數形態的規定,如刑法第89條第1款、刑法中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本文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等規定。罪數理論認為罪數形態包括想象競合犯、法條競合、牽連犯、吸收犯、連續犯等形態,其中最難區分的當屬想象競合與法條競合的區分,罪數論的厘清功能是存在數規范的情況下,檢討究竟如何從該數規范中,對于評價對象的行為做完整之評價。[2]因此,刑事裁判文書中必須對罪數的規范與評價過程作出說明。
(一)刑事裁判文書厘清功能實現的要求
隨著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書改革的深入,刑事裁判文書對于大眾而言的厘清功能越顯重要,裁判文書的公開,就是在發揮裁判文書對外的溝通與厘清功能。犯罪人及其家屬、每一位公眾都是司法公正的感受者,要實現感受得到有溫度的司法正義,光有文書的公開還不夠,還需要法官履行好釋法說法的職責。如果刑事裁判文書的說理是過于簡單的、模糊的,不僅無法實現刑事裁判文書的功能,還會帶來另一層誤解。許多公眾還停留在殺人償命的同態復仇觀念上,對于刑法條文及蘊含的法理一無所知,對于說理簡單的刑事判決的結果更是帶有偏見。如此,刑事裁判文書公開的意義就大打折扣。刑事裁判文書承載的厘清功能里還包含著法治教育的要求,法治教育要求讓社會大眾直接了解什么樣的行為會得到刑罰的苛責,罪與非罪的界限通過案例可以感受得一清二楚。如,河南大學生“掏鳥案”,在新聞媒體報道之初,引起了網民的熱議,許多網民并不清楚為什么抓了十幾鳥獲得如此重的刑罰,認為這又是司法不公的結果。當河南大學生“掏鳥案”的刑事判決書被放上網時,網民們才了解被告人閆某獵捕的12只燕隼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被告人閆某還加入“河南獵鷹興趣交流群”,在網上兜售鳳頭鷹的時候還特意標明“阿穆爾隼”等信息。也就是說,掏鳥的大學生并非只是偶然的無意的捕鳥行為,被告人主觀上是有故意的。[5]盡管這個案件還是存在其他爭議,但最初社會大眾對于司法不公的誤解因為判決書的上傳而得到澄清。這個案例說明,在復雜的、對社會影響較大的案件上,刑事裁判文書適時的法理闡明有助于社會大眾加深對法律的了解,這也是刑法一般預防的實現方式之一。刑事裁判文書承擔著釋明的責任,罪數的說明是刑法苛以刑責的判斷前提,把罪數說理加入刑事裁判文書中是文書厘清功能的必然要求。
(二)全面評價原則的遵循
全面評價原則系指對于刑法規定的各種罪行必須毫無遺漏地加以評價,以促規范與事實之間相互對應。全面評價原則與禁止重復評價原則是相依相靠的兩個原則,是罪刑均衡在罪數形態下的具體適用原則。全面評價原則要求刑事裁判文書體現出全面評價的過程,事實層面與規范層面對應的體現不應只存在于法官內心中。全面評價原則的體現,有如卿太蘇一案①,法官在犯罪事實的邏輯評價過程中首先體現了全面評價原則,被告人的行為同時觸犯了徇私枉法罪與受賄罪,這是犯罪成立的初步判斷;然后在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的框架下,行為人的一行為只能得到一個評價,超出的評價則是被禁止的,行為人只能得到一罪的刑法評價,因刑法第399條對于罪數形態的規定是特殊的,根據刑法第399條第4款規定,對這種行為系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結合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判決書最后給予被告人卿太蘇徇私枉法罪的一罪評價。全面評價原則要求刑事裁判文書說理時應注意定罪與量刑兩個方面的全面評價,評價過程的邏輯順序讓刑事裁判文書的讀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法院裁判評價的過程,感知司法過程的嚴謹與威嚴所在。
三、我國臺灣地區刑事裁判文書罪數說理的考察
我國臺灣地區的刑事判決書具有可讀性,刑事判決書語言表達生動、貼近現實生活。臺灣地區向來把競合的問題視為罪數論問題,認為罪數論要解決的問題包括“行為人觸犯數罪時,法院是否要羅列所有罪名,宣告一個罪名還是多個罪名,最后又該如何定出應執行的刑罰”。[6]臺灣地區“刑事訴訟法”第309條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于主文內載明所犯之罪。對于想象競合犯,不論輕重,都應該把所觸犯罪名羅列出來”,“借由這種論罪方式,也可以讓人從主文中就清楚知悉行為人所成立的各罪名。”[7]
早期臺灣地區刑事判決書關于數罪的要件與范圍表達較為籠統,例如,臺灣地區最高法院“1942年度臺非字第11號判例”指出:“被告人等因圖脫逃,繼續兩夜將監舍地基挖掘,系屬一行為之繼續活動。”[8]在判決書中,法官僅簡單把被告人的行為評價為一罪,法官把行為人兩夜挖掘監舍地基的行為認定為一行為,并未對被告人是否屬于接續犯作出判斷和說理,便直接得出結論,作出結論的過程未曾得知,刑事判決書的厘清功能發揮不足。囿于當時刑事實務對于接續犯的要件與范圍的認定不明朗,在早期的刑事判決書中關于罪數的說理較為籠統與罪數理論發展有關,特別是實務中罪數理論的發展。通過臺灣地區最高法院公布的判例解釋爭議、闡釋實務和學說觀點,實務界關于罪數理論的發展和說理就是在一個個鮮活的判例說理中發展的。特別是2005年臺灣地區刑法的修正,原刑法第56條連續犯的規定被刪除后,接續犯成為實務中罪數論重要的探討對象,接續犯的認定在刑事判決書中的說理顯得更加重要,特別是與集合犯的區分,關系到定罪和數罪并罰。臺灣地區刑法的修正對罪數理論在刑事判決書中的說理提出了要求,判決書的說理不僅承擔了罪數厘清的責任,還需根據罪數理論相關定義結合案情說理,有時還會對法條的立法原意作出法官的理解,罪數理論逐漸在刑事判決書中得到厘清和區分。
2006年臺灣地區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書“2017年度臺上字第307號判決”對于接續犯的說理如下:“意圖營利使‘同一女子’與他人為性交易,或圖利容留性交、猥褻犯行,系以經營‘應召站’之目的為之,在主觀上乃基于單一之犯意,以多數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系,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是色情經營者先后多次使‘同一女子’與他人為性交易等行為,具時間、空間上之密切關系,且系各基于單一犯意接續為之,應各僅論接續犯一罪。”②該刑事判決書在接續犯的理論基礎上結合案例,認為意圖讓同一個女子與他人性交易的行為是因為單一的犯意接續而為的,認定為接續犯,應以一罪論處,成立共同意圖營利而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交易罪。
臺灣地區的刑事判決書關于罪數的說理經歷籠統、不明確到說理詳細,通過觀察可以看出,這與罪數理論的發展有關,如連續犯的規定被刪除后,法官通過刑事判決書的說理厘清接續犯的概念。臺灣地區的刑事判決書關于罪數論的說明更加詳細,關于罪數的認定更加清晰,行為人通過刑事判決書主文可以得知法官定罪的具體評價過程。由于臺灣地區刑法實務深受罪數論的影響,對于刑事判決來說罪數論是定罪科刑的理論基礎。然而罪數說理存在著類似案件說理不同的問題,罪數論的發展與刑法實務的自我探索猶如一股麻繩上的絲線纏繞一起,一起向前延伸。
四、罪數理論如何體現于刑事裁判文書
201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加強和規范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的通知,該指導意見對人民法院裁判文書的釋法說理工作提出了要求,基于提高司法公信力與司法權威的目的,裁判文書的裁判結論的形成過程和正當性理由是裁判文書的兩大重點。可以說,裁判文書說理的合理演繹是未來裁判文書寫作的發展趨勢。
(一)刑事裁判文書說理基礎的建立
罪數理論適用于刑事裁判文書的前提是營造良好的司法氛圍,提高司法人員的法律適用能力,在這個基礎上,刑事裁判文書中簡單證據、說理不足的問題才有可能得到解決。
1.營造良好的刑事裁判文書改革氛圍
法官承擔的各種指標考核帶來的壓力和司法責任制的實施帶來的責任,諸多的限制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在刑事裁判文書說理不足上。盡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強和規范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要求裁判文書釋法說理要闡明事理、合理說理,但關于罪數理論如何體現在刑事判決書的說理中并未具體規定,這意味著,罪數形態的說理依賴于法官的合理發揮。在現有制度的框架下,許多法官不敢“大展拳腳”,影響了刑事裁判文書罪數形態說理的發展,罪數理論與實踐形成兩張皮。罪數理論適用于刑事裁判文書需要營造良好的改革氛圍,需要在更大的空間里進行,只有這樣良好的氛圍,罪數理論才能與具體案例結合,才能找到理論與實踐的契合點。因此,在刑事裁判文書改革中應把罪數形態說理的主動權交由法官,保障法官能真正發揮主觀能動性,真正做到闡明事理。
2.提高我國司法人員的法律適用能力
拘束司法氛圍下的司法人員,法律適用能力令人擔憂,在辦案過程中越來越依賴司法解釋,以致不敢有自己的判斷或對自己的判斷失去信心。他們法律適用能力的不足表現在刑事裁判文書的書寫中,出現如刑事裁判文書的書寫模板化、說理的簡單化與案件材料的簡單堆砌,刑事裁判文書中突兀、直接的定罪量刑。我國罪數理論極具復雜性與爭議性,現有的罪數理論要在刑事裁判文書中體現勢必要求法官具有較高的理論素養與法律適用能力。制度構建得再美好,如適用的人無法發揮主觀能動性,制度的推行就有可能產生異化,增加我國司法改革的難度與不必要的成本。我國案例指導制度的探索與建立也對司法人員的裁判文書書寫能力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司法人員在制度設計與推行中是重要因素,這些司法適用人員應具有靈活的法律適用能力,努力掙脫制度障礙與枷鎖,真正從人的角度去進行制度建構。
(二)刑事裁判文書說理要求的梳理
采罪數論或競合論,爭論不休,張明楷教授指出,“罪數論與競合論所討論的具體現象相同、目的相同,只是研究方法略有不同(但不矛盾),部分用語與歸類有所不同,因而導致對部分問題(現象)的處理不同。”[9]無論罪數論或競合論如何爭論,罪數的判斷是定罪量刑的基礎,更是刑事裁判文書厘清功能實現的基礎,罪數的判斷在刑事裁判文書中應得以具體體現。刑事裁判文書中的說理應把握下列基本要求。
1.合理釋明罪數形態
當行為人觸犯數個罪名時,刑事裁判文書是否要把所有罪名羅列進來,罪名的宣告是如何作出的,最終的刑罰又是如何確定的,這個過程與理由是刑事裁判文書的重點內容,理應結合具體案情進行分析。但多數的刑事裁判文書系直接給出結論,行為人涉及的其他罪名未加以評價,法律評價過程模糊,如果再碰到類似案件判決結果差異過大的情況,社會大眾根本無法知悉差異評價的原因,刑法一般預防作用的實現更是平添困難。刑法理論的發展與司法實務的發展是一體的,如果刑事裁判文書無法合理釋明罪數形態,只會導致罪數理論與司法實務進一步割裂,罪數理論未知實務的具體評價過程,罪數理論發展混亂無法為司法實務服務,實務亦是迷茫。罪數形態的合適釋明限度應當是結合具體案情,對行為人所觸犯的所有罪名進行評價,亦包括罪名的宣告。
2.罪數形態釋明符合邏輯性
罪數形態如何釋明要以具有邏輯性為邊界,評價時應遵循刑法理論的邏輯性。刑事裁判文書在釋明罪數形態過程中應遵循兩層邏輯,遵循行為人的行為屬于一罪或數罪的判斷邏輯,此為第一層邏輯;在罪數判斷的基礎上,遵循罪數并罰與否的判斷邏輯,此為第二層邏輯。第一層邏輯就行為成立一罪或數罪進行評價。一罪或是數罪的判斷標準存在多種學說③,通說認為將犯罪構成標準作為一罪或數罪的區分標準,犯罪事實侵害一個法益,符合一個犯罪構成,即為一罪。“罪數的判斷必須先依賴于一罪的判斷,而一罪的判斷實質上是犯罪成立的判斷。”[10]
因此,罪數判斷采取犯罪構成標準說與我國犯罪成立的判斷標準是一致的。我們還需要注意到,罪數形態在刑法分則中的規定是混亂的,這些特殊的刑法分則規定并不一定按照罪數理論的判斷標準定罪,在進行一罪或數罪的判斷時需注意這些特殊規定。采用犯罪構成標準要求對犯罪的法益保護有所認識。犯罪構成標準解決了罪數的問題,罪數處斷的問題交由第二層邏輯解決。第二層邏輯的任務是對數罪實行并罰與否進行說理,這正是罪數理論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該理論的實務意義。“司法實踐中,正是因為缺乏罪數形態的說理,直接得出的結論要么把它忽略了,要么由于認定錯誤,該并罰的沒有并罰,不該并罰的實行了并罰。”[11]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6)閩刑終337號④于上訴人辯訴理由不采納的說理為:“經查,無論我國刑法規定或者立法原意還是司法實踐,對于獨立的數起故意傷害的罪數形態,都是吸收并處,即以其中最為嚴重后果基準,綜合考慮全案情節的原則量刑。”根據我國刑法第69條⑤,刑法關于數罪并罰采取的是混合原則,當行為人被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的,與有期徒刑、拘役并罰的,采吸收原則;當數罪判處均為有期徒刑、拘役,采取限制加重原則。假設,行為人的兩個故意傷害罪中一個被判處無期徒刑,一個被判處有期徒刑,這種情況下采吸收原則,只執行一個無期徒刑;假設行為人的兩個故意傷害罪中被判處有期徒刑,采取限制加重原則,受總和刑期和數罪中法定最高刑期的雙重限制。但,此份判決書并未對行為人涉及的兩個故意傷害罪進行分別評價,便直接得出結論:“獨立的數起故意傷害的罪數形態是采吸收并處的結論。”此案一審判處無期徒刑,二審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盡管二審判處的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刑罰符合人民法院的量刑規則,但法官說理卻與刑法第69條數罪并罰的原則相左,且罪數形態說理不足。因此,此份刑事裁判文書不僅無法發揮裁判文書的厘清功能,反而還為數罪并罰理論增添迷霧。在罪數形態說理的第二層邏輯上,如果并罰與否不進行說理,被告人、上訴人、辯護律師乃至法律學習者、社會大眾都無從得知該案量刑的過程,刑事裁判文書像是不可登頂的高塔。罪數說理第二層邏輯的展開首先應該是在數罪分別評價的基礎上,對并罰與否進行說理與確定,“量刑的過程體現為法定刑—基準刑—調整刑—宣告刑。”[12]
罪數理論說理邏輯的嚴密性與說理的透徹性是刑事裁判文書的兩大特性,不僅記載著案件的裁判過程,也是對刑事裁判文書改革的另一種有力推進。刑事裁判文書的改革與刑法理論的發展息息相關,絕不是形式上的改革。刑事裁判文書是為罪數理論的體系構建提供司法實踐經驗與樣本,罪數理論的發展又為刑事裁判提供理論依據。刑事裁判文書的厘清功能體現在每一份刑事裁判文書中,厘清功能的實現也是個案公平正義的實現基礎。
注釋:
① 海南省海南中級人民法刑事裁定書,(2004)海南刑終字第184號。
② 臺灣地區最高法院2017年度臺上字第307號判決。
③ 罪數區分的學說包括法益說、構成要件說、行為說等。
④ 主要案情:2012年5月24日被告人在饒某2家門口,向被害人饒某3討要其哥哥的工錢時,雙方打架,被告人持刀刺中饒某3的背部、腹部和大腿等,經鑒定饒某3的傷情為重傷乙級;2015年8月30日,被告人在漳州金山湘菜館門口,與被害人熊某2言語不和發生打架,從車上取了一把工具刀返回與熊某2打架,刺中被害人胸部,經搶救無效死亡。被告人的損傷程度鑒定為輕微傷。
⑤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69條規定:“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的,除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以外,應當在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行的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