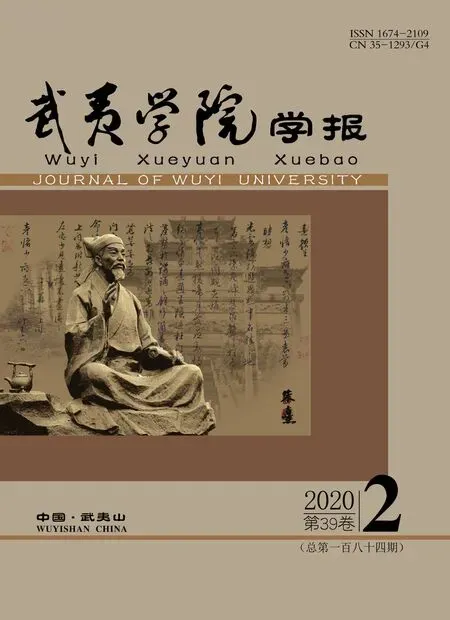宋代建陽(yáng)書坊出版再論
(三明學(xué)院 文化傳播學(xué)院,福建 三明 365004)
書坊出版,即書坊刻書,就是書商在所設(shè)書坊、書肆、書鋪、書堂刊刻書籍。書坊出版一般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坊刻范圍很廣,內(nèi)容上以民間日用的歷書、字書、韻書、佛像、年畫、通俗唱本最多;其次就是童蒙讀物、醫(yī)藥書、占卜書、還有適應(yīng)科舉考試需要的類書、制藝(八股文)、試貼詩(shī);也有一些名氣較大的書坊刻印正經(jīng)、正史和子集類書籍。宋代建陽(yáng)作為當(dāng)時(shí)全國(guó)三大出版中心之一,所出版的“建本”“麻沙本”,風(fēng)格獨(dú)特,獨(dú)領(lǐng)風(fēng)騷。其書籍傳之四方,行銷海外,影響深遠(yuǎn)。本文主要就目力所及范圍內(nèi)所掌握新材料,對(duì)建陽(yáng)書坊出版業(yè)再作探討。
一、建陽(yáng)書坊出版盛況及原因
書坊出版是宋代福建圖書出版的主流,據(jù)資料記載,僅建陽(yáng)書坊有牌號(hào)可考的有余仁仲萬(wàn)卷堂、余彥國(guó)勵(lì)賢堂、崇化書坊陳八郎書鋪、虞平齋務(wù)本堂、麻沙劉氏書坊等三十多家,甚至出現(xiàn)了一些刻書家族。比如余氏書坊,從北宋就已經(jīng)達(dá)到規(guī)模,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評(píng)價(jià):“夫宋刻書之盛,首推閩中。而閩中尤以建安為最,建安尤以余氏為最。且當(dāng)時(shí)官刻書亦多由其刊印”,“余氏刻書為當(dāng)時(shí)推重,宜其流傳之書,為收藏家所寶貴矣”。[1]宋代余氏刻書又以余仁仲為代表,余仁仲生平無(wú)考,文士,紹熙年間,以“余仁仲萬(wàn)卷堂”“余仁仲家塾”名號(hào)刻書甚多。他還刊刻了很多經(jīng)注本,有《禮記注》《公羊傳解詁》《谷梁傳集解》等,校勘精良、刻印精美。余氏所刻之書,為歷代藏書家視為珍寶,余氏書坊出版也是薪火相傳,一直延續(xù)到清初,仍然一片繁榮。經(jīng)營(yíng)六七百年,時(shí)間長(zhǎng),刻書多,影響大,實(shí)屬全國(guó)罕見。建陽(yáng)余氏是古代福建最著名的刻書世家。蔡氏也是建陽(yáng)刻書世家,代表是蔡琪的一經(jīng)堂。蔡琪,字純父,嘉定間刻《漢書集注》一百卷、《后漢書注》九十卷等。
實(shí)力雄厚的書坊出版產(chǎn)業(yè)已經(jīng)擁有書版、刻版、印版和裝訂等工序環(huán)節(jié)的工匠以及營(yíng)銷人員,還擁有自己的編輯、校對(duì)隊(duì)伍,甚至一些書坊主人還集編、刻、印于一身。實(shí)力較弱的書坊經(jīng)營(yíng)業(yè)務(wù)則以翻刻為主。福建書坊還大量接受來(lái)自省內(nèi)外的官、私委托刻書。如咸淳三年(1267),建寧知府吳堅(jiān)、劉震孫刻印祝穆《方輿勝覽》,紹熙四年(1193),桂陽(yáng)軍學(xué)教授吳炎刻印《東萊標(biāo)注老泉先生文集》等。
建陽(yáng)出版的書籍上自六經(jīng),下至訓(xùn)傳,墳籍大備,且行四方者無(wú)遠(yuǎn)不至,而供舉子課讀及場(chǎng)屋夾帶用的講章類書籍,更是百倍于經(jīng)史,出版書籍?dāng)?shù)量居全國(guó)之首。據(jù)方勺《泊宅編》記載,在北宋元符、建中靖國(guó)年間(1098-1101),舉子就已經(jīng)知道“建本”,并能以此糾正杭州州學(xué)教授在出題時(shí)使用版本的錯(cuò)誤。可見,北宋時(shí)期,建本就已經(jīng)在全國(guó)各地傳播。有些建本甚至傳至高麗、日本等海外國(guó)家。
建陽(yáng)書坊出版主要集中在麻沙和崇化兩地,兩地風(fēng)景優(yōu)美,景色怡人。南宋劉克莊《崇化麻沙道中》一詩(shī)寫道:“經(jīng)行愛此人煙好,面俯青溪背負(fù)山。半艇何妨呼渡去,小橋不礙負(fù)薪還。遠(yuǎn)聞清磐來(lái)林杪,忽有朱欄出竹間。此處安知無(wú)隱者,卜鄰容我設(shè)柴關(guān)。”[2]兩地書坊林立,熱鬧非凡,又稱“兩坊”“書林”。南宋祝穆《方輿勝覽》載:“麻沙、崇化兩坊產(chǎn)書,號(hào)為圖書之府。”[3]建陽(yáng)出版的書籍又被稱為“麻沙本”。“歷史上,麻沙的聲名遠(yuǎn)在崇化之上。但實(shí)際上,被稱為‘麻沙本’的刻本中,有相當(dāng)一部分是在崇化刻印的。由于麻沙、崇化兩地相距甚近,刻書家之間交流頻繁,故兩坊刻本在內(nèi)容、形式上都有許多共同之處,如果刻本未署明刻印地點(diǎn),實(shí)不易區(qū)分。因此,藏書家往往以‘麻沙本’‘建本’乃至‘閩本’統(tǒng)稱之。”[4]
建陽(yáng)書坊之所以如此繁榮,既與當(dāng)時(shí)建陽(yáng)得天獨(dú)厚的自然條件有關(guān),又與當(dāng)時(shí)的人文環(huán)境相關(guān)。可以說,宋代建陽(yáng)的天時(shí)、地利和人和造就了商業(yè)性出版的繁榮。
其一,宋代建陽(yáng)自然環(huán)境優(yōu)越。建陽(yáng)地處閩北,地理位置優(yōu)越,是北上江西、浙江,南下閩南、廣東的必經(jīng)之地。同時(shí),刻書所需物質(zhì)條件完全具備。建陽(yáng)地處江南丘陵地區(qū),屬于亞熱帶季風(fēng)氣候,群山包圍,山高林密,森林資源豐富,盛產(chǎn)松、柏、楊、柳、樟、楓、楠、梨、棗、竹等,其中樟、梨、棗是雕版所用優(yōu)質(zhì)材料,竹類品種繁多,可為印書提供豐富的造紙?jiān)稀=?yáng)歷來(lái)就是福建竹紙生產(chǎn)的中心,用于印書的竹紙,名“建陽(yáng)扣”,當(dāng)?shù)厝朔Q“書紙”。松又是制作印墨的優(yōu)良材料。書籍生產(chǎn)需要的竹木原材料能夠就地取材,據(jù)有天然的地理優(yōu)勢(shì),為圖書出版提供優(yōu)越的條件。
其二,宋代建陽(yáng)人文環(huán)境濃厚。隨著北方中原文化南移,地處閩北的建陽(yáng)文風(fēng)鼎盛。誕生和聚集了一大批本土和外地理學(xué)家與文人學(xué)士,如游酢、胡安國(guó),胡憲、胡寅、胡寧、胡宏、李侗、蔡元定、蔡淵、蔡沆、蔡沈、蔡格、蔡模、蔡權(quán)等。這些理學(xué)家和文人學(xué)士的到來(lái),帶動(dòng)了閩北地區(qū)文化的繁榮和發(fā)展,也刺激了建陽(yáng)書籍出版。宋代科舉事業(yè)不斷改革,考試更加公平,平民子弟有了上升的通道,建陽(yáng)士子讀書之風(fēng)逐漸興起,使得書籍市場(chǎng)繁榮。特別是一些應(yīng)付科考的參考書,銷量極大。事實(shí)證明,宋代建陽(yáng)考中進(jìn)士的人數(shù)在福建名列前茅。這與建陽(yáng)書坊書籍出版活動(dòng)密不可分。再加上北方戰(zhàn)事頻繁,建陽(yáng)相對(duì)比較安全,為建陽(yáng)圖書出版提供了安全保障。
二、建陽(yáng)書坊出版類型
建陽(yáng)書坊商業(yè)出版者編輯與出版的圖書主要有理學(xué)類書籍,學(xué)校教材,科舉考試用書、時(shí)文范本等。這些書籍對(duì)于理學(xué)知識(shí)的普及和理學(xué)思想的傳播起到了一定作用,對(duì)于參加舉業(yè)的舉子應(yīng)付科舉考試提供了幫助。
其一,建陽(yáng)書坊的一項(xiàng)重要業(yè)務(wù)就是刊刻和傳播理學(xué)書籍。比如“二程”著作就在如此: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憲使楊公已鋟板三山學(xué)宮,《遺書》《外書》,則庾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俱毀不存。諸書雖未能復(fù),是書胡可緩?師耕承乏此來(lái),亟將故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為一體,刻之后圃明教堂。賴吾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加密,二先生之書,于是乎全。時(shí)淳祐丙午,古汴趙師耕書。[5]
趙師耕淳祐間知泉州,提舉福建常平司(庾司)時(shí),看見過三山學(xué)宮本《二程文集》和庾司本《二程遺書》《二程外書》,《二程遺書》《二程外書》因?yàn)榛馂?zāi)和其他書籍一起焚毀。趙師耕認(rèn)為,其他書籍可以不再刊刻,但是,二程書籍刊刻與出版刻不容緩。于是,把《文集》《遺書》《外書》合三為一,重新編輯、出版。從標(biāo)題“麻沙本二程先生文集后序”和“刻之后圃明教堂”來(lái)看,此書是在麻沙書坊雕印。
出版這些書籍其原因一方面是宋代重科舉,研讀這類書籍是士子求取功名利祿的敲門磚。另一方面是因?yàn)殚}北作為朱子理學(xué)的發(fā)祥地,這類書籍擁有大量讀者。同時(shí),也是為了適應(yīng)閩北書院發(fā)展的需要。書院文化、圖書出版與理學(xué)傳播關(guān)系緊密。據(jù)統(tǒng)計(jì),兩宋時(shí)期福建書院有85所,其中閩北44所,占全閩書院52%。這些書院絕大部分是朱熹及其后學(xué)所建,各地朱子門人先后匯聚這里,開展學(xué)術(shù)交流活動(dòng),形成了歷史上著名的“考亭學(xué)派”。學(xué)術(shù)發(fā)展為圖書出版與傳播提供動(dòng)力,而圖書傳播與普及又進(jìn)一步推動(dòng)了學(xué)術(shù)的繁榮。許多當(dāng)?shù)匚娜耍缭瑯小⑺未取⑷~廷珪、魏慶之、黃善夫、祝穆等,也參與到圖書傳播事業(yè)中來(lái),他們都從事過圖書編輯出版工作,有的本人就是書坊主。文人和書坊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也推動(dòng)了建陽(yáng)圖書出版事業(yè)的繁榮。書院師生是書籍出版業(yè)穩(wěn)定的讀者群,書坊出版書籍也是教學(xué)用書的主要來(lái)源。當(dāng)時(shí)書院的辦學(xué)水準(zhǔn)較高,一般屬于高等教育階段,教學(xué)內(nèi)容也多為儒家經(jīng)典和理學(xué)。朱熹所著的《四書章句集注》和其門人所注的《五經(jīng)》,以及周、程、邵、張等理學(xué)先賢的著作都是書院教學(xué)的重要用書。
其二,書院師生自己的書稿、著作往往選擇就近原則,在建陽(yáng)書坊出版。如朱熹就曾經(jīng)看到了書坊出版業(yè)的方便與快捷,他在《答黃商伯》中說:“《洪韻》當(dāng)已抄畢,幸早示,乃此間付之書坊鏤板,甚不費(fèi)力。”[6]在《答鞏仲至》中,又說:“此間匠者工于剪貼,若只就此訂正,將來(lái)便可上板,不需再寫,又生一重脫誤,亦省事也。”[6]1764他們因此而形成了書坊出版業(yè)的作者群。
從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說,書院師生既是書坊出版業(yè)的讀者群,又是書坊出版業(yè)的作者群。書坊為傳播閩學(xué)人物的學(xué)術(shù)成果提供了印刷、出版的便利,也為閩學(xué)人物彼此之間進(jìn)行交流提供了書籍媒介。理學(xué)思想通過書籍媒介得到傳播,書籍媒介的廣泛傳播又?jǐn)U大了理學(xué)思想的影響。
其三,建陽(yáng)書坊還大量出版科舉考試書和范文選本。如狀元策、翰林館課、八股時(shí)文等。除此之外,還出版一些供夾帶抄襲用的巾箱本,其內(nèi)容專門是為了應(yīng)付科考,這是建陽(yáng)書坊出版的專利,官府和私家絕對(duì)不會(huì)這樣來(lái)做。宋代注重教育,官學(xué)、私學(xué)并重。又大興科舉,以詩(shī)賦、經(jīng)義取士。為了迎合廣大學(xué)子求學(xué)、應(yīng)試的需求,麻沙書坊還雕印了許多名人的范本投放市場(chǎng),并對(duì)其詩(shī)文按照內(nèi)容進(jìn)行了分類,名曰“類編增廣……”。如北宋刊刻的《類編增廣老蘇先生(蘇洵)大全文集》八卷,南宋乾道年間劉仲吉宅刊刻的《類編增廣黃先生(黃庭堅(jiān))大全文集》五十卷。這些文集在社會(huì)上廣泛傳播,頗受市場(chǎng)歡迎。
當(dāng)時(shí)全國(guó)好多地方還沒有出版科舉考試參考書等書籍,而民間書坊就已事先刊行,在民間傳播。這一方面表明書坊主敏銳的市場(chǎng)眼光,敢為人先,做第一個(gè)吃螃蟹的人。另一方面也表明書坊編校成員對(duì)科舉考試命題方向有所把握和研究,完全有能力編輯出版此類書籍。李淑在《應(yīng)考試進(jìn)士只于國(guó)子監(jiān)有印本書內(nèi)出題奏(景祐五年正月)》中記載:
切見近日發(fā)解進(jìn)士,多取別書小說、古人文集,或移合經(jīng)注,以為題目,競(jìng)務(wù)新奧。臣以為朝廷崇學(xué)取士,本欲興崇風(fēng)教,反使后進(jìn)習(xí)尚異端,非所謂化成之義也。況考校進(jìn)士,但觀詞藝優(yōu)劣,不必嫌避正書。至如近日學(xué)者編經(jīng)史文句,別為解題,民間雕印,多已行用。考試之時(shí),不須一一回避。其經(jīng)典子書之內(nèi),有《國(guó)語(yǔ)》、《荀子》、《文中子》儒學(xué)所宗,六典通貫,先朝以來(lái)嘗于此出題。只是國(guó)庠未有印本。欲望取上件三書,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義,付國(guó)子監(jiān)施行。自今應(yīng)考試進(jìn)士,須只于國(guó)子監(jiān)有印本書內(nèi)出題。所貴取士得體,司業(yè)有方,稍益時(shí)風(fēng),不失淳正。如允所請(qǐng),兼乞編入貢舉條貫施行。[7]
李淑的上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科舉參考書的巨大經(jīng)濟(jì)價(jià)值,連官方都還沒有意識(shí)到,而書坊主就已經(jīng)嗅出了其廣闊前景,提前刊刻,在知識(shí)分子當(dāng)中廣泛流傳,既方便了舉子應(yīng)付科考,又為書坊主帶來(lái)了利潤(rùn),可以說是一舉兩得。作為當(dāng)時(shí)出版中心的建陽(yáng)書坊,更是如此。
官方對(duì)于民間流行的科舉考試復(fù)習(xí)參考用書也持寬容態(tài)度,他們認(rèn)為評(píng)價(jià)進(jìn)士,只需要考察他們的“詞藝優(yōu)劣”即可,“不必嫌避正書”。《國(guó)語(yǔ)》《荀子》《文中子》等儒學(xué)所宗書籍,先朝以來(lái)經(jīng)常圍繞此類書籍出題,而國(guó)家學(xué)校竟然沒有印本。于是,上奏請(qǐng)求國(guó)子監(jiān)雕印頒行。
三、建陽(yáng)書坊出版風(fēng)格
建陽(yáng)書坊出版業(yè)從誕生之初,就顯示出了自己的獨(dú)特風(fēng)格。這種風(fēng)格與“浙本”“蜀本”不同,具有鮮明的閩北地域特色,帶有閩學(xué)家思想的印記。其獨(dú)特風(fēng)格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四個(gè)方面:
一是字體多為顏體和柳體,正文橫輕豎重,小注橫豎一樣,多為細(xì)筆。如黃善夫刊刻的《史記》、《后漢書》等,結(jié)構(gòu)方正,筆畫嚴(yán)謹(jǐn),鋒棱峻峭,瘦勁有力。當(dāng)然,除了顏體和柳體外,還有其它字體。如黃三八郎刻本《鉅宋廣韻》就是仿褚遂良體,建本《周易注》《晉書》仿宋徽宗瘦金體。
二是刻有牌記。牌記又稱書牌、刊記、木記,多出現(xiàn)在書名頁(yè)、序文、卷末或目錄之后,主要記錄刻書時(shí)間、地點(diǎn)、書坊主姓名和堂號(hào)等。牌記有各種形狀,如長(zhǎng)方形、碑形、香爐形、鐘形、爐形、亞字形等,或者沒有邊框隨行書寫。牌記既是一種版權(quán)保護(hù)手段,又是一種廣告宣傳形式。同時(shí),也裝幀了圖書、美化了版面。
三是上圖下文、圖文并茂。建本多為正文配置插圖,以圖補(bǔ)文,圖文并茂。這種形式可以讓讀者賞心悅目。歷書最早將儒家經(jīng)典配上插圖的做法,就是在建陽(yáng)書坊。比如我國(guó)現(xiàn)存最早的插圖本《周禮》,就是南宋時(shí)期建陽(yáng)刻本,有圖三十六幅。其中有一幅《天子玉路圖》,描繪的是周天子乘“玉路”出行,前呼后擁的情形,線條流暢,生動(dòng)形象,充分體現(xiàn)了宋代版畫藝術(shù)的進(jìn)步和雕版印刷技術(shù)的提高。朱熹在建陽(yáng)講學(xué)時(shí),曾經(jīng)見過此書,他曾說過:“書坊印得《六經(jīng)》,前有纂圖子,也略可觀。如車圖雖不甚詳,然大概也是。”[8]再比如現(xiàn)存最早日用百科全書插圖本《事林廣記》,此書也是配有多幅插圖,構(gòu)圖適合,其中《夫子杏壇之圖》,表現(xiàn)了孔子率門下弟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fēng)乎舞雩,詠而歸”的生動(dòng)情景。
四是具備“封面”意識(shí)。朱熹淳熙十四年(1187)在武夷精舍編纂《小學(xué)》時(shí),寫信給刊刻此書的蔡元定道:“示喻筮法如此,甚平正簡(jiǎn)便,不知何故本法卻不如此?恐別有意指也。試更推之,如何?恐在老者陽(yáng)多陰少,則終為陽(yáng)者少;在少者陰多陽(yáng)少,則定為陽(yáng)者亦少。乃陽(yáng)貴陰賤,吉少兇多之意,不知如何?《小學(xué)》誤字再納去數(shù)紙,封面只作《武夷精舍小學(xué)之書》可也。”[9]可見,朱熹已經(jīng)開始使用“封面”一詞,“封面”意識(shí)萌芽。
宋代建陽(yáng)書坊出版,主要以理學(xué)類書,教材和科考書為主,一般是比較通俗和暢銷的書,也是能賺錢的書。“在政府刻書、私人刻書和書坊刻書三大系統(tǒng)中,坊刻不僅興起最早,分布最廣,數(shù)量最多,而且影響最大。”[10]建陽(yáng)書坊出版在推進(jìn)圖書事業(yè)發(fā)展,保存和傳播古代文化遺產(chǎn)方面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