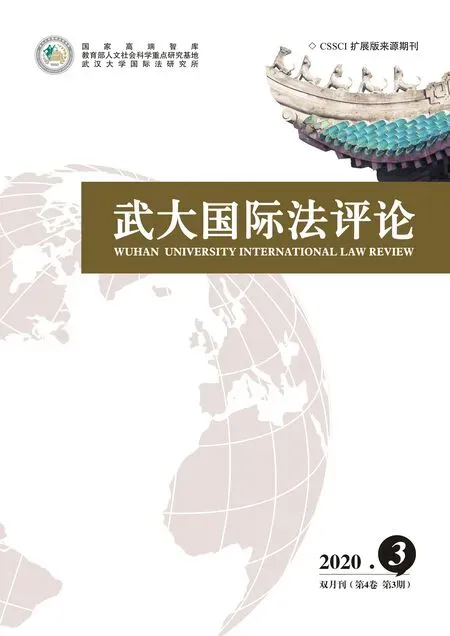額外衛生措施的國際法規制
——以《國際衛生條例》和SPS協定為視角
馮潔菡
2005 年世界衛生大會通過的《國際衛生條例》構建了一個在預防、抵御和控制疾病國際傳播方面加強全球公共衛生應對,并避免對國際交通和貿易造成不必要干擾的國際衛生法律框架。自2020 年1 月30 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總干事宣布COVID-19 病毒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以來,超過150個國家宣布了緊急狀態并采取了各種防控措施,包括對經濟、貿易和旅行具有重大影響的臨時衛生措施。其中一些措施,如16 位國際知名衛生法學家在《柳葉刀》(Lancet)雜志上發表的評論所指出的,“公然無視及時報告任何額外衛生措施的法律要求,使WHO 無法協調世界對公共衛生緊急情況的反應,并使各國無法相互追究其根據《國際衛生條例》應承擔的義務。”①Roojin Habibi et al., Do Not Violate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Lancet, 2020,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20)30373-1, visited on 15 February 2020.在國家安全、國家主權以及貿易和經濟利益均納入公共衛生治理的背景下,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國際衛生法和國際貿易法規制額外衛生措施的異同及不足所在,探求促進全球公共衛生治理與國際貿易秩序良性互動發展的解決路徑。
一、《國際衛生條例》對額外衛生措施的規制
(一)公共衛生安全與貿易間關系的平衡
維護公共衛生應對與促進貿易之間的平衡,一直是傳染病控制國際制度處理的核心議題之一。自19 世紀后半期開始,國際衛生機制既關乎衛生問題,又關乎貿易問題,而非僅僅是出于衛生問題的考量。②參見[加拿大]馬克·扎克、塔尼亞·科菲:《因病相連:衛生治理與全球政治》,晉繼勇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頁。例如,1969 年《國際衛生條例》(以下稱《條例》(1969))在前言中載明了處理衛生與貿易之間關系的“最大安全”和“最小干擾”兩個目標。③1983 年《國際衛生條例》詮釋第三版在前言中明確指出:“《國際衛生條例》的目的是防止疾病在國際間傳播,確保最大安全,同時又盡可能小地干擾國際交通。”國際公共衛生法學者戴維·費德勒(David P.Fidler)教授認為,這兩項互補的原則,“理論上,綜合形成了關于傳染病控制的總體國際法律制度”。④David P. Fidler, Return of the Fourth Horseman: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81 Minnesota Law Review 843 (1997).以此為基礎,《條例》(1969)根據不同的疾病病種,⑤經1981 年世界衛生大會修改的1969 年《國際衛生條例》規定了三種疾病:鼠疫、霍亂和黃熱病。就國家可以實施的最大限度衛生應對措施規定了“正面清單”。但由于所適用病種的有限性,以及疫區國家因擔心影響貿易往往滯后通報,與防疫國家為加強防控往往采取過度衛生措施之間的惡性循環,《條例》(1969)實際上并未能實現上述目標。⑥See Barbara von Tigerstrom, The Revised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and Restraint of National Health Measures, 13 Health Law Journal 39 (2005); David P. Fidler,Return of the Fourth Horseman: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81 Minnesota Law Review 846-847 (1997).2005 年修訂的《國際衛生條例》⑦第58屆世界衛生大會WHA58.3號決議通過,2007年6月15日生效。(以下稱《條例》)則大幅變革了《條例》(1969)的疾病監測模式,不再局限于病種或傳播方式,而是就有可能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規定了締約國的通報義務及WHO 總干事在確定PHEIC 后發布相關臨時建議的程序。①參見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前言,第1-2頁。在考慮公共衛生應對措施對貿易可能產生的影響方面,《條例》繼續秉持平衡衛生與貿易,“避免對國際交通和貿易造成不必要干擾”的目標。②參見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第2條。
(二)國家采取額外衛生措施的自主權
在國際衛生法的發展歷程中,一直以來最具爭議的一個問題是各國是否有權實施額外的衛生措施。發達國家一直以來均持強烈的反對態度,擔心會妨礙貿易流通,而發展中國家則更多基于本國控制疾病蔓延的公共衛生能力不足而堅決擁護。1926 年的巴黎《國際衛生公約》第一次規定各國應避免實施逾越公約規定的額外措施,③參見[加]馬克·扎克、塔尼亞·科菲:《因病相連:衛生治理與全球政治》,晉繼勇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頁。這種態度也體現在2005 年之前的《國際衛生條例》之中。④例如,1969 年《國際衛生條例》第23 條規定,“本條例所規定的衛生措施是應用于國際交通運輸方面最大限度的措施”。但2005 年《條例》的修訂反映了發達國家的轉變。例如,美國認為,盡管WHO 希望在提供安全防范疾病國際傳播的必要性和避免對國際交通的不必要干擾之間取得平衡,但提出的一些措施未能實現權利平衡,且對會員國的主權構成侵犯。⑤See WHO, Initial U.S. Government Comments on the First Draft of the Proposed Rev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5 March 2004, pp.7-8; Second U.S. Government Comments on the First Draft of the Proposed Rev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7 April 2004, p.4.美國和歐共體⑥See WHO, Preliminary Comment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 States on the Draft-revised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7 May 2004, p.4.等提出,不應侵犯或干涉WHO 會員國保護其公共衛生的主權權利,在滿足相稱性、不歧視以及具有科學依據⑦See WHO, Summary Report of Regional Consultations, A/IHR/IGWG/2, 14 September 2004, para.8.的情況下,應給予會員國靈活性實施比WHO建議的保護水平更高的衛生措施。⑧See WHO, Review and Approval of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Explanatory Notes, A/IHR/IGWG/4, 7 October 2004, para.13.這表明的是,盡管國際傳染病防控戰略已從以入口控制為主轉變為以源頭控制為主,⑨參見[加拿大]馬克·扎克、塔尼亞·科菲:《因病相連:衛生治理與全球政治》,晉繼勇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頁。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越來越趨同于在國內防控上尋求更大的自主權以保護本國的公共衛生安全。最終達成的《條例》融合了上述意見,主要體現為WHO 的臨時和長期建議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以及國家在遵守相應標準和程序的前提下可以在總干事的建議之外采取額外衛生措施。其結果是既賦予WHO 發布建議的權力,以使WHO 作為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的權威機構在應對國際公共衛生風險方面發揮更好的引領作用,也賦予國家在接受WHO的建議和采取額外衛生措施方面以更大的自主權。
(三)國家采取額外衛生措施的自主權限度
2005 年《條例》授權WHO 總干事在宣布PHEIC 的同時根據突發事件委員會的意見發布不具約束力的臨時建議,①參見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第15條。以說明締約國對人員、行李、貨物、集裝箱、交通工具、物品和郵包應該采取的衛生措施。②對人員采取的衛生措施包括醫學檢查、疫苗接種、接觸追蹤、隔離和出境檢查、限制出境等,對行李、貨物、交通工具等采取的衛生措施包括審查載貨清單和航行路線、檢查、安全處理、隔離、查封和銷毀以及拒絕出境或入境等。參見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第18條。以WHO 的建議為基礎,《條例》允許締約國為應對特定公共衛生風險或PHEIC,依據國內法和國際法采取比WHO的建議保護水平更高的衛生措施,包括對過境交通工具和貨物③參見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第25、26條和第33條。及對入境交通工具和旅行者④參見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第28條第1款和第2款、第30條和第31條第1款第3項。原本禁止使用的衛生措施,以及允許對旅行者⑤參見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第23條第2款和第27條第1款。和受染交通工具⑥參見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第28條第2款和第31條第2款第3項。采取的額外衛生措施。
《條例》明確將對國際交通造成明顯干擾的額外衛生措施界定為“拒絕國際旅行者、行李、貨物、集裝箱、交通工具、物品等入境或出境或延誤入境或出境24 小時以上”,⑦參見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第43條第3款。這類措施包括對人員和貨物具有更大限制性的衛生檢疫和進口限制措施,對國際貿易會產生重要影響。為此,《條例》規定了各國采取額外衛生措施必須遵守的實體性原則和標準,包括:⑧參見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第43條第1-2款、第42條。(1)合理性和必要性原則,即這些措施對國際交通造成的限制不應超過能實現適度保護健康的其他合理可行措施;(2)科學性原則,即采取衛生措施應基于:科學原理、可獲得的科學證據和現有信息、WHO的任何現有特定指導或建議;(3)透明度和不歧視原則。其中的第(1)項和第(2)項內容與WHO 在考慮臨時建議時應遵循的原則和標準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⑨參見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第17條。
在程序性義務方面,如果締約國實施的額外衛生措施“對國際交通造成明顯干擾”,該國在采取這些措施后的48 小時內應向WHO 通報,并向WHO 提供采取此類措施的公共衛生依據和有關科學信息。WHO可以要求國家重新考慮是否執行此類措施,而采取額外措施的締約國必須在三個月內依據WHO 的建議和《條例》確立的實體性標準對這種措施進行審查。①參見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第43條第3-6款。
(四)《條例》第43條實施情況的實證考察
實踐中,在COVID-19 病毒疫情之前,WHO 就歷次PHEIC②除COVID-19 疫情外,還包括2009 年甲型H1N1 流感、2014 年脊髓灰質炎疫情、2014年埃博拉疫情、2015—2016年“寨卡”疫情以及2018年開始的埃博拉疫情。發布的臨時建議中均要求締約國不應限制國際交通和貿易。自2011 年以來,WHO 在實施《條例》的年度報告中列明了締約國采取額外衛生措施的情況。《條例》審查委員會在2011 年關于禽流感疫情的報告中指出,受WHO 調查的56 個國家采取了超出臨時建議的措施,其中,有六個國家限制來自墨西哥等疫情國家的動物或貨物入境。這些國家均未主動履行向WHO 通報并提供公共衛生理由的義務,在WHO 提出要求后,也并非所有國家都作了說明。③參見審查委員會報告:《關于與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有關的〈國際衛生條例(2005)〉實施情況的報告》,A64/10,2011年5月5日,第85-86頁。審查委員會認為,第43 條是《條例》的基石,但由于《條例》未對不遵約行為規定制裁辦法,因此提高透明度,增強以證據為基礎的額外措施決策,可以緩解其他國家的憂慮,并改進國際應對協調。④參見審查委員會報告:《關于與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有關的〈國際衛生條例(2005)〉實施情況的報告》,A64/10,2011年5月5日,第140-141頁。
在2011 年之后,WHO 秘書處開始對額外衛生措施進行監測并與會員國進行交流,確認有關措施的確切性質和公共衛生理由。但不遵守第43 條的情況并未見顯著改善。在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中,有69 個國家采取了嚴重干擾國際交通的額外措施,卻很少有國家主動向WHO 通報,在秘書處發出核實要求后,只有40%的締約國作出了說明。而且,部分取消航班和簽證的締約國卻主張這些措施與衛生無關,因此不屬于《條例》的范圍。⑤參見審查委員會報告:《〈國際衛生條例(2005)〉在埃博拉疫情和應對方面的作用》,A69/21,2016年5月13日,第35-37頁。審查委員會認為,鑒于《條例》不包括制裁措施,而且不建議修訂《條例》,因此,遏制不必要的破壞性應對措施的最佳方法是對公眾披露情況。簡而言之,通過提高透明度加強問責。⑥參見審查委員會報告:《〈國際衛生條例(2005)〉在埃博拉疫情和應對方面的作用》,A69/21,2016年5月13日,第88頁。
在今年的COVID-19 病毒疫情中,WHO 在2020 年1 月30 日第一次宣布PHEIC 發布的臨時建議中同樣建議締約國不對疫情暴發國采取旅行或貿易限制措施。①See WHO, Statement on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IHR (2005) Emergency Committee regarding the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30 January 2020, https://www.who.int/news-room/detail/30-01-2020-statement-on-the-second-meeting-of-the-internationalhealth-regulations-(2005)-emergency-committee-regarding-the-outbreak-of-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visited on 25 May 2020; Key Considerations for Repatriation and Quarantine of Travelers in Relation to the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11 February 2020, https://www.who.int/news-room/articles-detail/key-considerations-for-repatriation-and-quarantine-of-travellers-in-relation-to-the-outbreak-of-novel-coronavirus-2019-ncov,visited on 25 May 2020; Updated WHO Recommend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Relation to COVID-19 Outbreak, 29 February 2020,https://www.who.int/news-room/articles-detail/updated-who-recommendations-for-international-traffic-in-relation-to-covid-19-outbreak, visited on 25 May 2020.在宣布為大流行病之前,根據中國貿促會的統計數據,截至2020 年3 月9日,對中國活體動/植物實行進口禁運或限制的有18 個國家,對來自中國的貨物、進出境工具及人員施加嚴格的檢驗、檢疫、檢查措施的有143 個國家(地區)。②參見中國貿促會:《關于有關國家(地區)采取限制性措施的提示》,2020年3月6日,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3674/2020/0306/1245160/content_1245160.htm,2020 年5月25 日訪問;《關于有關國家(地區)因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提示(二)》,2020 年3月10 日,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3674/2020/0310/1245736/content_1245736.htm,2020年5月25日訪問。在3 月11 日宣布為大流行病之后,截至4 月20 日,對中國活體動/植物實行進口禁運或限制的仍有27 個國家(地區)。③參見中國貿促會:《關于有關國家(地區)因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相關措施提示(十四)》,2020 年4 月21 日,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3674/2020/0421/1255189/content_1255189.htm,2020年5月25日訪問。而依據WHO 發布的每日“情勢報告”,截至3月10 日,共有45 個國家向WHO 通報了對國際交通造成明顯干擾的額外衛生措施并說明了公共衛生理由。④所通報的額外衛生措施主要是對人員實施的檢疫、檢查、隔離等措施,主要的公共衛生理由為防控疾病流行和國家衛生系統的脆弱性。See WHO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Situation Report-50,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10-sitrep-50-covid-19.pdf?sfvrsn=55e904fb_2, Data as Reported by National Authorities by 10 March 2020, visited on 25 May 2020.從上述數據對比來看,大部分國家并未向WHO 通報額外衛生措施。
2020 年5 月1 日,在WHO 總干事宣布COVID-19 病毒疫情仍是PHEIC 的同時,也就“額外衛生措施”對所有締約國發布了內容詳盡的臨時建議。⑤WHO, Statement on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IHR (2005) Emergency Committee regarding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1 May 2020, https://www.who.int/news-room/detail/01-05-2020-statement-on-the-third-meeting-of-the-international-health-regulations-(2005)-emergency-committee-regarding-the-outbreak-of-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 visited on 25 May 2020.在建議中,WHO 強調應根據定期風險評估、傳播模式、成本效益分析、大流行病的演變以及新冠病毒的科學知識審查旅行和貿易措施,建議締約國除依據相關國際協定實施對公共衛生具有重要意義的貿易限制之外,不要施加其他限制,特別是避免限制食品、醫療和其他必需品的國際運輸,允許有效應對大流行所需的必要人員的安全流動,并要求締約國繼續根據《條例》向WHO 提供關于額外衛生措施的適當公共衛生理由。①但在宣布為大流行之后,WHO 的每日“情勢報告”中未再見說明額外衛生措施的通報情況。這可以理解為在COVID-19病毒疫情下,WHO對《條例》第43條如何具體適用的一種權威性的指導性意見。
二、SPS協定對貿易限制性衛生措施的規制
(一)WTO法對貿易與公共衛生利益的平衡
平衡貿易和公共衛生利益一直是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法的目標之一。1947 年《關貿總協定》即允許締約方為保護人類健康實施違反GATT 義務的措施。在貨物貿易方面,WTO1994 年《關貿總協定》(以下稱“GATT1994”)、《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定》(以下稱“SPS 協定”)和《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以下稱“TBT 協定”)均承認WTO 成員為保護人類健康有限制貿易的權利,但這項權利的實施須滿足各涵蓋協定規定的具體標準,以確保在情形相同的國家之間不構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視,不對國際貿易構成變相的限制。②參見GATT1994第20條前言、SPS協定序言和TBT協定序言。在服務貿易方面,《服務貿易總協定》(以下稱“GATS”)也作了與GATT1994類似的規定,即在滿足必要性和不歧視的前提下,允許成員為保護人類健康采取限制性措施。③參見GATS第14條。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方面,《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下稱“TRIPS 協定”)規定WTO 成員可采取為保護公共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只要此類措施與協定的規定一致,④參見TRIPS協定第8條第1款。并規定了相關的例外和靈活性條款。⑤例如,TRIPS協定第6條、第30條和第31條。2001 年WTO第四屆部長會議通過的《TRIPS 協定與公共健康多哈宣言》也明確指出,TRIPS 協定不能夠也不應當妨礙各成員采取措施以保護公共健康。⑥See DOHA WTO Ministerial 2001, WT/MIN(01)/DEC/2, Declaration on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Public Health, Adopted on 14 November 2001.
值得注意的是,2005 年《條例》在修訂過程中也特別考慮了國家采取的衛生措施可能與WTO相關協定規定的義務相沖突的問題。例如,美國和歐共體主張,《條例》應避免與其他國際協定相沖突。①See Preliminary Comment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 States on the Draft-revised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p.3; Second U.S. Government Comments on the First Draft of the Proposed Rev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p.3.另一些國家則建議,《條例》應允許公共衛生行動優先于貿易協定和其他短期經濟考量②See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South-East Asia, Second Regional Consultation on the Proposed Revised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7 September 2004, p.21.。政府間工作組考慮了會員國意見,就此作出了說明,并修改了相關條款。③See WHO, Intergovernmental Working Group on Rev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Review and Approval of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Relations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A/IHRIGWG/INF.DOC./1, 30 September 2004, paras.7-9.2005 年《條例》對WHO 的臨時建議和國家采取額外衛生措施時應遵守的實體性標準,包括風險評估、科學標準、必要性與合理性、透明度與不歧視等,實際上也是采用了WTO相關協定特別是SPS協定中的類似標準去評估相關衛生措施是否合規。
(二)SPS協定下的臨時衛生措施
在WTO 的涵蓋協定中,與衛生措施直接相關的是SPS 協定。在傳染病防控過程中,國家采取的衛生措施如果影響到國際貨物貿易,就可能受到SPS 協定的規制。SPS 協定在序言中確認WTO 成員有權確立其認為適當的公共衛生保護水平,但必須滿足相關的標準,以證明所采取的衛生措施符合GATT1994第20條(b)款的規定。④參見SPS協定第2條第4款。在SPS措施與GATT1994第20條(b)款的關系上,專家組在美國禽類產品案中認為,SPS 協定詳細闡述并解釋了第20 條(b)款的規定,因此,違反SPS協定的措施不能被認定為是符合第20條(b)款的措施。⑤See United States-Certain 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Poultry from China(US-Poultry (China)), WT/DS392/R, paras.7.458-483.
SPS 協定規定了風險評估、科學依據、國際標準以及必要性、合理性和透明度原則。由于在傳染病暴發和流行期間的科學證據往往不充分,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往往首先會援引SPS 協定第5 條第7 款作為采取相關措施的理由。⑥有關SPS協定第5條第7款的適用及解釋,參見WTO Analytical Index:SPS Agreement, Article 5,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ai17_e/sps_art5_jur.pdf,2020年5月15日訪問。依據WTO有關案例,⑦截至2020 年5 月,涉及SPS 協定第5 條第7 款的爭端解決案件共有九起。See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agreements_index_e.htm, visited on 1 June 2020.第5 條第7 款被解構為下列四個累積的要求:(1)相關科學證據不充分;(2)該措施是依據現有可獲得的有關信息采取的;(3)有關成員必須尋求獲得對風險進行更客觀評估所需的額外信息;以及(4)該成員在合理期限內對該措施進行相應審查。①See Japan-Measures Affec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Japan-Agricultural Products II), WT/DS76/AB/R, para.89.因此,對同為WTO成員的2005年《條例》締約國而言:
首先,在科學證據不充分時,WTO 成員有自主性權利采取臨時衛生措施。專家組在歐共體生物技術案中認為,WTO 成員依據第7 款享有的是一項自主性權利,而不是一般義務之下的例外。②See 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Approval and Marketing of Biotech Products (EC-Approval and Marketing of Biotech Products), WT/DS291/R, para.7.2976.這表明在傳染病防控初期,在對病毒和疾病的流行病學特征以及診斷特征沒有獲得充分的科學證據時,WTO 成員為保護公共健康,可采取臨時性衛生措施,其法律后果是可豁免SPS協定第2條第2款下的義務。③專家組在歐共體生物技術案和日本農產品案中認為,第2 條第2 款中的后兩個要件,即“依據科學原理”和“沒有充分科學證據不再維持”,相比第一個要件“必要性”而言,與第5 條第7 款的關系更為密切。第一個要件與第5 條第6 款相關,而第5 條第6 款是第2 條第2 款第一個要件的具體適用。See EC-Approval and Marketing of Biotech Products, WT/DS291/R, para.7.1430; Japan-Agricultural Products II, WT/DS76/R, para.8.71.而且,由于科學證據不充分,也不要求所采取的措施必須以充分的風險評估為基礎。④參見SPS協定第5條第1款和附件A第4條。專家組在歐共體生物技術案中認為,第7款豁免了第1款之下的SPS措施應基于風險評估的義務。⑤See EC-Approval and Marketing of Biotech Products, WT/DS291/R, para.7.2997.盡管對第7 款是否完全不要求風險評估沒有定論,但專家組認為,如果第7 款有風險評估的要求,也與“充分的風險評估”有別,只要求考慮“可獲得的有關信息”。⑥See EC-Approval and Marketing of Biotech Products, WT/DS291/R, para.7.2992.
其次,盡管因科學證據不充分無法進行充分的風險評估,但WTO成員必須依據“可獲得的有關信息”作出決策。有關信息的來源,包括來自有關國際組織以及其他成員實施的SPS 措施的信息。對于有關國際組織的范圍,依據附件A 第3條,包括食品法典委員會、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OIE)、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組織以及“經委員會確認的、向所有WTO 成員開放成員資格的其他有關國際組織”。盡管WHO 不在明確列出的國際組織范圍之列,但實踐中,SPS 委員會在1998 年霍亂暴發涉及的魚類產品進口禁運事件中也考慮了WHO的建議。①1998 年,由于坦桑尼亞、肯尼亞等國暴發霍亂,歐共體禁止從這些國家進口魚類產品。在SPS 委員會會議上,WHO 的官員依據WHO 的建議證明魚類產品并無傳播霍亂的風險。此后,歐洲共同體同意于1998 年7 月1 日恢復貿易。這一案例強調了以科學證據而非理論風險為基礎制定貿易限制性公共衛生措施的重要性,也證明了WHO 根據每種具體的健康風險提出的建議對SPS 委員會是有用的。See WTO Agreements and Public Health, A Joint Study by the WHO and the WTO Secretariat, WTO/WHO, 2002, pp.60-61.對于來自其他成員實施SPS措施的信息,由于SPS協定的透明度要求WTO成員主動通過SPS下的信息通報系統通報措施及采取的理由,②根據SPS協定第5條第8款,一成員可要求另一成員就臨時性的SPS措施說明理由。因此,獲得其他成員的有關信息并非難事。此外,所采取的臨時措施與可獲得的有關信息之間應具有合理或客觀的聯系,因而可提供“臨時性的安全閥功能”。③See US/Canada-Continued Suspension of Obligations in the EC-Hormones Dispute(US/Canada-Continued Suspension), WT/DS320/AB/R,WT/DS321/AB/R, para.678.
再次,措施的臨時性要求WTO 成員不斷尋求額外信息和在合理期限內審查所采取的臨時措施。這兩個要素構成成員持續性的實體義務。④See EC-Approval and Marketing of Biotech Products, WT/DS291/R, para.7.3255.不斷尋求額外信息,目的是使成員能夠對風險進行更客觀的評估。因此,信息必須與所進行的風險評估密切相關,⑤See US/Canada-Continued Suspension, WT/DS320/AB/R, WT/DS321/AB/R, para.679;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Importation of Animals, Meat and Other Animal Products from Argentina (US-Animals), WT/DS447/R, para.7.295.同時,這些信息應努力確定存在的不僅僅是理論上的風險。在合理的期限內審查措施,取決于每一個個案的具體情況,包括獲得審查所需的額外信息的難易程度以及所涉SPS 措施的性質。⑥See Japan-Agricultural Products II, WT/DS76/AB/R, para.93.WTO 有關案例認為:這實際上類似于審查附件C第1條中所規定的不應有“不適當的遲延”。⑦See EC-Approval and Marketing of Biotech Products, WT/DS291/R, para.7.3245;US-Animals, WT/DS447/R, para.7.301.
WTO 有關案例認為,第5 條第7 款反映了預防原則,但并不凌駕于風險評估原則之上,⑧See 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Concerning Meat and Meat Products (Hormones), WT/DS26/AB/R, paras.124-125; US/Canada-Continued Suspension, WT/DS320/AB/R, WT/DS321/AB/R, para.680; EC-Approval and Marketing of Biotech Products, WT/DS291/R, para.7.3220.因此,如果衛生措施不能滿足第5條第7款累積要件的要求,則仍必須基于充分的風險評估、科學證據和必要性進行合規性審查。①參見SPS 協定第5 條第1-2 款、第2 條第2 款。WTO 判例主張,如果不能滿足第5 條第7 款的要求,則依據第5 條第1 款和第2 款以及第2 條第2 款的順序進行合規性審查。See US-Animals, WT/DS447/R, para.7.320; India-Measures Concerning the Importation of Certa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dia-Agricultural Products), WT/DS430/R, paras.7.307-7.308;US-Poultry (China), WT/DS392/R, para.7.172; Australia-Measures Affecting the Importation of Apples from New Zealand, WT/DS367/R, para.7.211; Japan-Measures Affecting the Importation of Apples, WT/DS245/R, para.8.230.在必要性方面,SPS協定第3 條第2 款規定符合國際標準、指南或建議的衛生措施應被視為滿足必要性要求。但如前文所述,由于WHO 的建議并不在SPS 協定附件A 所列的國際標準、指南或建議的范圍之內,因此以WHO 的指導或建議為基礎且比WHO 建議保護水平更高的額外衛生措施,在SPS 協定的必要性要求之下,仍需接受相關要素的檢驗,包括措施的貿易限制性、對實現目標的重要性以及是否存在可實現相同目標的貿易限制性更小的替代措施。②See India-Agricultural Products, WT/DS430/R, paras.7.607-7.613.
(三)對SPS協定與2005年《條例》關聯度的考察
與2005 年《條例》相比,SPS 協定對衛生措施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調控更加精細,但二者涵蓋的對象和衛生措施的類別有所不同。《條例》下的衛生措施并不區分疾病的類別或疾病、病因來源或傳播方式,③參見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第1條。涵蓋了對人員、交通工具和貨物采取的衛生措施,而SPS 協定只涉及經動物或植物傳播的疾病,涵蓋的是對動植物或動植物產品等采取的衛生措施。④SPS 協定規制的衛生措施針對的是動植物或動植物產品攜帶的病害或食品、飲料或飼料中的添加劑、污染物、毒素或致病有機體所產生的風險。參見SPS 協定附件A第1條第2段和第3段。此外,《條例》下的衛生措施是指為預防疾病或污染傳播而實施的程序,不包括執行法律或安全措施,⑤參見2005《國際衛生條例》第1條對“衛生措施”的解釋。而SPS協定涵蓋的衛生措施不僅包括衛生檢疫措施和程序,還包括最終產品標準、工序和生產方法、有關統計方法、抽樣程序和風險評估方法的規定等。⑥還包括與糧食安全直接有關的包裝和標簽要求等相關法律、法令、法規、要求和程序。參見SPS協定附件A第1條。因此,只有部分《條例》涵蓋的衛生措施會同時受到SPS協定的規制。
再者,根據2005 年《條例》第43 條第1 款和第57 條第1 款,《條例》既不妨礙締約國根據本國有關法律和國際法義務采取額外衛生措施,也不影響任何締約國根據其他國際協議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因此,理論上,對于在傳染病疫情防控過程中采取的具有貿易限制性的額外衛生措施,《條例》締約國承擔了雙重條約義務,應以同時符合《條例》和SPS協定的方式實施。實踐中,部分國家向WHO通報了限制措施,更多的是向SPS 委員會通報信息。這種做法也符合《條例》第57條第1款,而且表明在規范貿易限制性衛生措施方面,WTO法優先適用。①See Barbara von Tigerstrom, The Revised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and Restraint of National Health Measures, 13 Health Law Journal 53 (2005).
在2009 年H1N1 禽流感疫情期間,巴西在SPS 委員會提出訴求,要求各國向SPS委員會通報就H1N1疫情采取的衛生措施,并依據第5條第7款的要求及時收集額外信息和進行審查,②See SPS Committee, G/SPS/GEN/922, 13 May 2009.而墨西哥則要求各國撤銷限制性措施。③See SPS Committee, G/SPS/GEN/921, 5 May 2009.WHO、FAO和OIE 也向SPS 委員會提交了說明豬肉食用安全的聯合聲明。④See SPS Committee, G/SPS/GEN/942, 17 June 2009.在COVID-19 病毒疫情期間,截至5月20日,有四個WTO成員向SPS委員會通報了臨時限制或禁止動植物產品進口的衛生措施。⑤See WTO, Standards, Regulations and Covid-19:What Actions Taken by WTO Members? Information Note, 20 May 2020, pp.5-6,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covid19_e/standards_report_e.pdf, visited on 7 June 2020.WTO與WHO總干事也于4月20日發布聯合聲明表示“為促進公共衛生而采取的任何限制貿易的措施都應有針對性、相稱性、透明和臨時性”。⑥Joint statement by WTO Director-General and WHO Director-General, 20 April 2020,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0_e/igo_14apr20_e.htm, visited on 5 June 2020.
三、當前困境與解決路徑
(一)《條例》與WHO問責機制的缺位
2005 年《條例》對額外衛生措施的規制建立在尊重國家自主權和以WHO 建議作為制衡的基礎之上,設想的是通過透明度和公開性吸引國家主動遵約。但事實上,盡管WHO 的建議作為權威性指導意見可以發揮規制過度衛生措施的安全閥功能,⑦See David P. Fidler, Comments on WHO’s Interim Draft of the Revised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16 April 2004, pp.25-26,https://www.asil.org/insights/volume/8/issue/8/revision-world-health-organizations-international-health-regulations, visited on 7 June 2020.卻由于建議沒有法律約束力,對會員是否及時通報沒有合規監督機制,對于違反第43 條的行為也沒有規定法律后果和制裁辦法,因而在實際遵約方面,無論是《條例》本身還是WHO都缺乏一定執行力。此外,《條例》第56條規定的各類爭端解決機制①依據第56 條,當締約國間就《條例》的解釋和適用發生的爭端時,可通過以下方式解決:(1)談判或其自行選擇的任何其他和平方式尋求解決此爭端,包括斡旋、調停或和解;(2)提交總干事解決;(3)自愿提交常設仲裁法庭的有拘束力的仲裁;(4)提交其他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此外,如果是締約國與WHO 就總干事臨時建議的衛生措施發生爭端,則應提交世界衛生大會。迄今被束之高閣,使得WHO 的建議究竟具有何種程度的“軟”規范效力,尚屬未知。
從更廣泛的角度看,這種困境也與對WHO 的功能定位相關。《條例》或WHO的《組織法》均未賦予WHO 對第43 條的執法職能。無論是WHO 會員還是WHO自身,在歷史和心理的選擇上都更傾向于WHO 是一個公共衛生領域的技術型和規范型組織,而非一個兼具執法職能的全能型組織。WHO的前任法律顧問指出,2005 年《條例》的設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以下方面之間的權衡:對WHO“軟”緊急權力的依賴及其規范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受影響國家的開放與合作;第三國的善意、團結和自我克制;以及國家保留最終的主權來決定控制措施。②See Gian Luca Burci,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Coronavirus: Are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Fit for Purpose? http://ejiltalk.org/the-outbreak-of-covid-19-coronavirus-are-the-international-health-regulations-fit-for-purpose,visited on 15 May 2020.因此,在以國家為中心的治理結構中,對《條例》和WHO 建議的遵循更大程度上取決于WHO本身的公信力、專業度以及國家的合作意愿。
(二)WTO爭端解決機制實際效用有限
依據2005年《條例》第56條,當締約國間因貿易限制性衛生措施發生爭端時,可自主優先選擇WTO 爭端解決機制。但實踐中,盡管在H1N1 禽流感疫情中,墨西哥曾在SPS委員會要求所有貿易伙伴撤銷對墨西哥肉類產品的一切限制措施,但目前尚未見就傳染病防控過程中實施的貿易限制性臨時衛生措施在WTO提起爭端解決程序的實例。這可能與兩個因素相關:其一,額外衛生措施雖具有貿易限制性,但大多為臨時性的應急措施,且會隨著對傳染病科學認知的不斷加深而被終止或調整。其二,WTO爭端解決程序本身耗時經年,無法快速解決國家間因臨時性衛生措施而產生的爭端。而且,WTO 爭端解決的首要目的并非金錢賠償或中止減讓,而是撤銷不符合WTO 多邊義務的措施,③See Lin, Tsai-Yu, The Forgotten Role of WHO/IHR in Trade Responses to 2009 A/H1NI Influenza Outbreak, 44 Journal of World Trade 530-531 (2010).因而也無法解決國家因臨時性措施所遭受的即時經濟損失。
再者,如前文所述,SPS 協定不能完全涵蓋2005 年《條例》下的所有具有貿易限制性的衛生措施,對防控人傳人的疾病而實施的衛生措施,SPS 協定無法規制。而且,WTO 是一個以貿易規則為導向的國際組織,即使依據WTO《爭端解決諒解》就SPS 協定能涵蓋的衛生措施提起爭端解決程序,WTO 爭端解決機構審查的也將是爭議衛生措施與貿易規則的相符性問題,而不會審查相關措施是否符合2005 年《條例》。①See Lin, Tsai-Yu, The Forgotten Role of WHO/IHR in Trade Responses to 2009 A/H1NI Influenza Outbreak, 44 Journal of World Trade 532 (2010).SPS 協定并未將《條例》或WHO 的建議作為采取衛生措施所依據的“國際標準、指南或建議”,因此《條例》或WHO 的建議在WTO 爭端解決機制下不能直接得以適用。WTO 的爭端解決實踐表明,②Australia-Certain Measures Concerning Trademark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Other Plain Packaging Requirements Applicable to Tobacco Products and Packaging, WT/DS435/R, WT/DS441/R, WT/DS458/R, WT/DS467/R, para.7.412.雖然非WTO 國際文書本身并不規定WTO 下的法律義務,但常常被WTO 爭端解決當事方、專家組和上訴機構作為支持其立場的事實證據,③See 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Affecting Asbestos and Products Containing Asbestos, WT/DS135/R, para.8.295; 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Prohibiting the Importation and Marketing of Seal Products, WT/DS400/R, para.7.295;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Clove Cigarette (US-Clove Cigarettes), WT/DS406/R,paras.7.414-415.或者對涵蓋協定中具體條款的解釋產生影響。④See United States-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WT/DS58/AB/R, paras.130-132.因此,WHO 通過的條約、指南、報告⑤例如,在美國丁香煙案中,專家組參考了WHO 的一份報告。See US-Clove Cigarettes, WT/DS406/R, para.7.413.或建議⑥例如,在泰國香煙案中,專家組基于WHO 的專家意見,認定“吸煙構成對人類健康的嚴重危害,因此,旨在減少香煙消費的措施屬于GATT 第20 條(b)款的范圍”。See Thailand-Restrictions on Importation of and Internal Taxes on Cigarettes, WT/DS10/R, para.73.,可作為爭端當事方或WTO 爭端解決機構解決事實或法律問題的證據,但不能作為判斷相關措施具有WTO 合法性的決定性依據。⑦參見[比]約斯特·鮑威林:《國際公法規則之沖突—WTO 法與其他國際法規則如何聯系》,周忠海等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527頁。WTO 爭端解決機制對解釋《條例》和規范額外衛生措施的實際效用是有限的。
(三)解決路徑的設想
盡管采取額外衛生措施通常可歸因于國家間不同的利益和價值選擇,但傳染病防控中因諸多事實在科學上的不確定性,以及其中所涉及的自然、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壓力的復雜性,使得解決這一問題的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2005年《條例》第56條的爭端解決程序被束之高閣即是例證之一。正如費德勒教授所指出的,出于政治和流行病學方面的考慮,各國并不熱衷于在傳染病問題上運用有關國家責任的習慣國際法。發生疫情的國家會抱怨其他國家實施的不合理的貿易或旅行措施,但可能到了明年,該國就希望在另一個國家暴發疫情時采取類似的措施。這表明國家間的互惠利益在于不就違反條約規則對有關貿易和旅行措施提出賠償。①See David P.Fidler,COVID-19 and International Law:Must China Compensate Countries for the Damage?https://www.justsecurity.org/69394/covid-19-and-international-law-must-chi na-compensate-countries-for-the-damage-international-health-regulations, visited on 15 May 2020.在“低政治”的公共衛生問題日益發展成為“高政治”的國家安全問題②參見[加拿大]馬克·扎克、塔尼亞·科菲:《因病相連:衛生治理與全球政治》,晉繼勇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主編序,第3頁。的當下,在額外衛生措施問題上主張制裁和對抗式的零和博弈,既不現實也并非有效的應對。每個WHO 會員國都是主權國家,其首要重點是維護本國公民的健康,但在全球化環境中,一國的健康狀況與其他國家的健康狀況緊密相連。③參見埃博拉中期評估小組的首份報告,A68/25,2015年5月8日,第8頁。傳染病防控是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問題,《條例》的目標是獲得全球成員的支持與合作。因此,在繼續尊重國家自主性和靈活性的基礎之上,秉持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理念,通過增進國家與WHO、WHO 與WTO 的合作,以及加強WHO的內部治理是可供選擇的解決路徑。
首先,加強WHO 內部框架下的制度性遵約機制。實際上,2005 年《條例》第43 條已經建立了關于額外衛生措施的報告和定期審查制度,但由于其“薄弱”性,以及在不履行時缺乏制裁機制,往往使國家缺乏遵約動力。由于措施是否適當往往要等到疫情結束后才能評價,因此重要的是在傳染病防控過程中建立一個自愿遵約和合規監督機制。《條例》審查委員會在禽流感疫情和埃博拉疫情之后均建議加強問責,提高分享信息的透明度、同儕壓力以及促進與締約國之間的建設性對話。④例如,在2017 年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埃博拉疫情和馬達加斯加的鼠疫疫情期間,秘書處試行了一種有條不紊的方法,與締約國就額外衛生措施開展了建設性的對話。參見WHO 總干事報告:《〈國際衛生條例(2005)〉實施情況年度報告》,A71/7,2018 年4 月5 日,第2-3頁。盡管離初衷尚有很大差距,但從近兩年總干事的《條例》實施報告可以看出:情況有些許改善,締約國的責任感正在緩慢提升。例如,在印度喀拉拉邦的尼帕病毒疫情期間,WHO建議不實施任何旅行或貿易限制,有五個締約國暫時禁止從喀拉拉邦進口水果和蔬菜。在WHO 與這些締約國的互動之后,兩個國家解除了禁令,一個國家為禁令提供了公共衛生理由。⑤參見WHO 總干事報告:《〈國際衛生條例(2005)〉實施情況年度報告》,A72/8,2019年4月4日,第4-5頁。
其次,轉變對WHO 的功能定位。盡管會員國均無意使之成為一個衛生警察機構,但WHO 在保留技術性和專業性特征的同時,發展成為一個管理型的國際組織并非不可行。在尊重會員國主權的基礎上,WHO 就COVID-19 疫情專門針對額外衛生措施發布詳盡的臨時建議是一種嘗試,它表明WHO 可以為實施第43條中的實體標準給出權威性的具體指導方針,從而引導會員國作出理性決策。①2005 年《國際衛生條例》第43 條第2 款第3 項規定:締約國采取額外衛生措施應“基于WHO 的任何現有特定指導或建議”。雖然仍屬“軟法”的范疇,但無疑構成一種權威性的專業意見,如果未來就第43 條的適用和解釋產生爭端,WHO 的這項建議或可構成締約國額外衛生措施是否具有合法性依據。長遠來看可以考慮的路徑是在WHO 內設立一個常設機構,發揮WHO 的協調職能,同時為會員國提供一個多邊論壇,并將第43條第6款規定的磋商程序常態化,通過允許會員國就其他國家采取的額外衛生措施表達特別關切和“投訴”損害以加強問責,通過要求實施措施的國家提供公共衛生理由和有關科學信息提高透明度,從而增進締約國間的相互理解與合作,促進達成共同接受的解決方案。②此建議是受到SPS 委員會特別貿易關切程序的啟發,本文認為WHO 可以考慮借鑒這種模式。參見龔向前:《技術性國際爭端解決的“全球行政法”思路—基于WTO 食品安全案例的分析》,《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第55頁。
再次,WHO 加強與包括WTO 在內的其他相關國際組織的合作。目前,國際社會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機制以平衡健康風險和經濟與貿易風險的方式來管理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③Tim K. Mackeya & Bryan A. Liang, Lessons from SARS and H1N1/A: Employing a WHO-WTO Forum to Promote Optimal Economic-Public Health Pandemic Response,33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 120 (2012).只有數個分而治之的國際組織。實踐中,WHO 和其他相關國際組織會以發表聯合聲明的方式就衛生措施對國際經濟、貿易和人員流動的影響表示關注,但這尚不足以解決實際問題。可供考慮的路徑是在上文所建議的WHO 常設機制中納入包括WTO 在內的其他相關國際組織的常態化參與,以更好地進行國際協調,共同處理公共衛生緊急情況和貿易及人員流動問題。在這一機制下,WHO將行使其專業治理職能,依據疫情數據和流行病學信息進行客觀的風險評估,協調全球的衛生應對,并邀請WTO和其他相關國際組織對有關衛生措施限制經濟、貿易和旅行的適當性給予即時評價和建議。WHO 和其他相關國際組織還可聯合發布最佳實踐指南,以幫助各國作出理性決策。
四、結語
2005 年《條例》規制額外衛生措施屢屢“失靈”,與《條例》本身缺乏執行機制和世界衛生組織的“技術和規范導向治理模式”密切相關。而作為相對于《條例》和WHO而言的外部規范機制,WTO法律體系所涵蓋協定的適用范圍有限且僅審查與WTO 法的合規性,因此也無法根本解決對具有貿易限制性的額外衛生措施的規制問題。當“低政治”的公共衛生問題日益發展為“高政治”的國家安全問題時,國家采取額外衛生措施保護本國安全的意愿和自主性似乎已經大大超越了國家間發展自由貿易促進流通的積極性。在全球公共衛生治理的敘事背景下考量貿易利益,與在全球貿易治理的敘事背景下考量衛生利益,各自的目標訴求并不相同。這也反映了當前全球公共衛生治理政策和規則的碎片化。更深層的問題可能在于,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的民族國家治理模式,應如何在繼續尊重國家自主性和靈活性的基礎上加以變革,才能更好地適應“因病相連”的全球化時代。未來的全球治理,應突破只強調“共處”卻忽視“合作”的藩籬,以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為理念,在世界范圍內通過齊心協力、團結合作的公共衛生和國際貿易協調框架,促進以規則為導向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間形成體系和合力,化危為機,以推動構建一個更加健康、繁榮與安全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