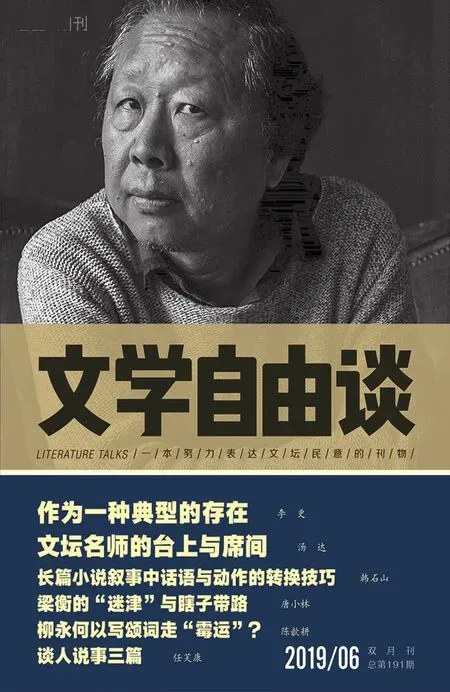勸童少讀“馬小跳”
□周思明
A
新世紀之初,短短數年就創造了童書暢銷奇跡而聲名鵲起的兒童文學女作家楊紅櫻,因創作了《淘氣包馬小跳》《女生日記》《漂亮老師與壞小子》《笑貓日記系列》等校園小說和童話作品,連續多年躋身全國少兒類圖書排行榜,被國際著名出版公司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團一次性購走“馬小跳”世界全語種版權,創造了中國原創兒童文學大舉進入世界少兒圖書市場的當代神話。然而,楊紅櫻在受到許多小讀者明星般狂熱追捧的同時,也招致國內兒童文學界一些評論家以及家長和老師的質疑與批評。
楊紅櫻作品,雖有驕人的銷量,但在不少評論家與老師、家長眼中,有時未嘗不是商業營銷從中助力的結果,并非作品本身魅力所致。須知,兒童的審美能力畢竟羸弱,要讓他們一下子變得成熟也很難。這就如同人的飲食,喝可樂容易上癮,但吃水果的習慣要慢慢養成。用兒童文學評論家劉緒源的話說,“楊紅櫻的作品就是可樂,拿起來就能喝。但有的作品是水果,你告訴孩子蘋果很好吃,他一開始可能不相信,但慢慢就會知道蘋果確實比可樂好。”當然,對此評價,楊紅櫻本人和職業出版人是不予認可的。
一個兒童文學作家,擁有十年間作品銷售量三千萬冊的紀錄,何以卻受到主流評論界的批評?其實這不奇怪。因為楊紅櫻的作品雖然暢銷無阻,雖然好看,可讀,但匱乏文學深刻細膩的表達力,缺乏藝術審美高度和人性揭示的永恒性。用評論家的話說,她的系列作品,具有“三化”特征:即人物性格“卡通化”,故事結構“圖像化”,閱讀感受“通俗化”,尤其缺乏兒童文學作品向深度和難度掘進的誠意與效果。正因如此,在前些年某個兒童節期間,有廣東省級重點小學的老師對家長建議,孩子不該閱讀楊紅櫻等兒童文學作家創作的暢銷讀物,理由是它們屬于文化快餐,沒有營養,而孩子有限的閱讀時間應該放在諸如《吹小號的天鵝》《青鳥》《昆蟲記》等經典作品上。楊紅櫻的作品,無論是從審美還是從智性角度看,都沒有太大的價值。同時,家長還認為,《淘氣包馬小跳》文字充滿市儈味,純屬世俗哲學教科書,不適于給孩子看。更有兒童文學研究學者認為,讀楊紅櫻童書是“偽閱讀”。楊紅櫻作品輕松好讀,如同看電視般地讓孩子“娛樂”其中,其危險性在于,把具有內省、反思功能的有深度、有意義的“閱讀”,變成沒有指涉、匱乏反思、舍棄深度和意義的“觀看”。
兒童文學研究學者朱自強在《再論新世紀兒童文學的走勢》文中指出:楊紅櫻近年的暢銷作品,基本上都在運用電視“圖像” 式的語言進行創作,尤其在“淘氣包馬小跳系列”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典型。楊紅櫻電視“圖像”式寫作特點有四:“圖像”轉換快而隨意;“圖像”缺乏景深度;“圖像”之間缺乏意義上的連接;“圖像” 的虛擬性。讀楊紅櫻的作品,眼前會有“圖像”不停轉換,無法停下來品味,沒有工夫進行思考,這與經典兒童文學閱讀狀態顯然不同。況且,楊紅櫻作品的“圖像”設定也相當隨意,如同“淘氣包馬小跳系列”之《瘋丫頭杜真子》里的“成語接龍”故事,前一個故事寫到哪件事,后一個故事就接著那件事寫。玩過接龍游戲的人都知道,這種游戲具有速度快、不思考、無選擇性的特點,隨意性很大,不會給游戲者增加任何難度。這樣做的結果,是對取舍、推敲、打磨、創新的出離與放棄。
楊紅櫻的童書創作,“圖像”是平面的,缺乏景深度,漂浮在表層,未能表現出性格、關系、意義之間的復雜關聯,對人物性格刻畫和心靈態勢描摹都很乏力,甚至是淡漠的。有些作品里的故事情節,是順手抓來而非經過邏輯組織的,往往彼此孤立、相互脫節,與故事里的人物也無必然關系。這些故事沒有意義的聯想、闡釋和建構,也不能觸及小讀者的心靈,沒有實現閱讀主體的自我內化,往往在嘻哈逗樂間完成閱讀過程。很多時候,楊紅櫻作品的故事情節之間連基本的自洽性都難以成立。比如,在馬小跳小說中,因為心里喜歡夏林果,馬小跳挖空心思獲得夏林果生日會的邀請,他知道唱完生日歌,就會有蛋糕吃。馬小跳要求參加他所喜歡的女孩子的生日會,目的非常簡單,就是想吃好吃的蛋糕。從人物形象塑造角度分析,凸顯主人公性格鏈條的斷裂,這就使得其文本內部結構關系歸于解構與瓦解。值得指出的是,楊紅櫻作品反映出來的創作癥候,其實并非僅限于個例,儼然形成當前兒童文學創作中一種較為流行的傾向,區別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這應當引起兒童文學作家和研究者足夠的重視。
B
可悲的是,現在不少家長在選購童書方面抱有盲目心理,忽略了作品是否經典、能否給孩子帶來成長道路上的正能量這樣的大問題。從性價比層面考量,孩子每天可用來閱讀的時間極為有限,如果把這有限的時間用來看平庸的童書,浪費了孩子寶貴的童年時光不說,也難以收獲有益孩子身心健康和人格完善的精神營養;甚至那種一味張揚調皮搗蛋性格的童書,會給他們造成價值觀上的偏離甚至迷亂——似乎只有調皮搗蛋才是正常,而遵守紀律、老實做人反而代表著無用。這是值得家長和老師警惕的。
如果排除不正常的因素,其實辨別童書優劣有一個便捷有效的方法,就是看它們是否獲過大獎,比如美國的凱迪克獎、英國的格林威獎、國際安徒生獎,以及國內的全國兒童文學獎、華語地區的信誼獎、豐子愷獎,等等。就此意義上說,楊紅櫻作品的水平顯然不盡如人意。她的作品雖然暢銷,讀起來也不無童趣和親切感,但其實沒有多少思想含量,比如對教育的批判略顯偏激和出離,表現出的觀念也較平庸。出人意外的是,當被問及楊紅櫻的作品水平如何時,多位文學評論家和活躍在兒童文學閱讀推廣領域的人士均保持了一種緘默態度。一位不愿公開姓名的評論家道出實情:她的作品不敢恭維,作者只是抓住孩子的游戲心理,滿足了他們的好奇心,但她的作品缺乏感動內心的力量。這位評論家還說,現在有一類作家就像木偶,心甘情愿被出版商擺布,讓他們牽著鼻子走。此類作家雖然出版發行作品海量,但并不意味著文學的成功,只能說是商業上的勝算。
對楊紅櫻作品批評最堅決者,當屬評論家劉緒源。在《試說楊紅櫻暢銷的秘密》一文中,劉緒源提及,楊紅櫻的《淘氣包馬小跳》系列和《五·三班的壞小子》等作品,讓他常想到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而是那些調皮搗蛋的“壞小子”。理論上講,這與他在《兒童文學的三大母題》中所提到的“頑童型”母題以及他過去所倡導的“沒意思”的作品頗為契合。按說這樣的作品應該很讓人喜歡才是,然而奇怪的是,越是讀她的書,就越是不喜歡。劉緒源幾乎懷疑自己是否墜入了“葉公好龍”的怪圈。出于審核自身藝術判斷力的需要,他將類似題材的作品找來,悉心地進行比較研究,其中包括意大利萬巴(Vamba)的《搗蛋鬼日記》和瑞典林格倫(Astrid Lindgren)的《瘋丫頭瑪迪琴的故事》。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見分曉。劉緒源認定,問題的關鍵不在別處,還是在作品的文學性或作品的審美內涵上——如果說萬巴、林格倫的作品是文學經典,那楊紅櫻作品只能算是文化快餐。
暫且以萬巴(Vamba)的小說《搗蛋鬼日記》與之對比。《搗蛋鬼日記》是一部自傳體小說,主人公是一位九歲小男孩,人稱“搗蛋鬼加尼諾”。加尼諾受姐姐啟發,學寫日記,決心把自己的想法和經歷的事情都記到日記里去。日記記載了他在半年時間內把家里攪得天翻地覆,終成人見人煩的“禍星”的經過:他在姐姐的婚禮上,將炮仗拴在姐夫的扣眼上;他在客廳里鼓搗魔術差點弄瞎客人的眼睛;他在家里玩釣魚卻釣起一個老人的牙齒;出于好奇,他在火車上拉下緊急制動閘;他甚至一個人搞了一個動物園,居然把鄰居家的小孩掛在樹上當猴耍……加尼諾在帶給孩子們歡笑的同時,也勾起大人們對孩提時代的回憶,作品字里行間充滿了幽默搞笑氣氛。難能可貴的是,搗蛋并非該作品的目的,搞笑故事背后蘊藏著作者的思考,給家長以珍貴的啟迪:如何與成長中的孩子溝通,如何幫助他們養成正直、善良的人生品質。
對比之下,楊紅櫻的作品難免自顯其不足。兩者的分界在于,楊紅櫻作品只有故事本身,而且是沒有多少意義的調皮搗蛋故事,《搗蛋鬼日記》所具有的極豐富的弦外之音,楊紅櫻作品中是沒有的。她的小說“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匱乏精心、精致的謀篇布局,當然更不會有林格倫式的溢滿童心童趣的美妙享受。至于人物形象塑造,“馬小跳”與“肥貓”等孩子之間匱乏辨識度,除了調皮還是調皮,單一且模糊,篇幅拉得再長,字數堆砌得再多,也還是看不到人物個體成長的層次和性格的區分。小說源于并止于“聽來的故事”。粗略的輪廓,模式化的套路,人為拉長的篇幅,顯然有悖于文學藝術的個性化創造原則。
當然,楊紅櫻能做到讓自己的作品暢銷,創下十年間攀升到三千萬的紀錄,不得不說,她確有自己獨特的寫作秘笈。在當代兒童文學界,寫調皮搗蛋“壞小子”的潮音已轟響經年。其開先河者,當屬秦文君的《男生賈里》。然而賈里、魯智勝們雖也調皮,性格卻是明晰而豐饒的,作品的文學性也是可圈可點。接下來是梅子涵的那些以幼童為審美對象的作品,如《曹迪民先生的故事》《我們都是馬》等,表現孩童那種不走心的頑皮更顯放肆,但也頗具文學性。與此同時,這些作品也都帶有暢銷的風格。楊紅櫻繼承放大了他們作品中的暢銷元素,卻令人遺憾地揚棄了作品中的文學性,讓自我在暢銷的大道上無所顧忌地絕塵而去,從而躋身暢銷書作者的行列。對此,楊紅櫻似乎早有思想準備。謂予不信,不妨參閱中少版《楊紅櫻童話》,書末所附她的答記者問。當被贊道“看來你是一位很有自覺追求的兒童文學作家”時,楊紅櫻頗有自知之明地說:“我不太喜歡被稱為兒童文家作家,而是喜歡被稱為童書作家。”
C
楊紅櫻作品確實暢銷,但有論者指出,那是“非文學的暢銷”,而不是“文學的暢銷”。如覺得文學不文學無所謂,只須暢銷就好,這似乎也無可厚非。然而,“非文學”不可能取代文學,文學仍有它自己的價值,而其中,特別高雅精致的那部分文學,更有其無可取代的審美價值。正如林格倫、萬巴、任大霖等人的作品,隔多少年看,依然有深入人心的美感力量,這是無可搖撼的事實。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喻,肯德基和麥當勞,夠暢銷了吧?但有誰會把最佳烹飪的桂冠,授給雞柳漢堡或麥香魚呢?這是兩個向度上的追求,暢銷不可能取代一切。曾幾何時,金庸也有過相類的狀況。當有些人欲將他與魯迅、茅盾等現代文學大家相提并論時,他很清醒地說:我不能跟他們比;他們是文豪,我只是一個武俠小說家。
客觀地說,這些年最為小讀者青睞的當屬楊紅櫻,她的“淘氣包馬小跳系列”,以及《五·三班的壞小子》《漂亮老師和壞小子》《假小子戴安》等等,都備受小讀者追捧。受楊紅櫻的影響,甚至還出現了被評論家稱為“紅櫻二代”的一批后繼者,其代表作如周志勇的《小丫俏皮girl》叢書、《臭小子一大幫》叢書,趙靜的“搗蛋頭唐達奇系列”,郝月梅的“搞笑鬼王鬧系列”等等。原本寫青春文學的伍美珍,也毅然加入了這個行列,并推出“阿呆和阿瓜的故事”系列叢書。可見,楊紅櫻式的童書寫作范式對當下兒童文學出版與創作影響是多么強大。對楊紅櫻式創作潮的評價,從一開始就存在著爭議,挺楊者如王泉根教授,認為楊紅櫻作品擁有巨大發行量,使得本土兒童讀物與西方引進童書相比并不遜色,形成令人欣喜的局面。批評者如劉緒源等學者,認為楊紅櫻的童書缺乏文學性、原創性,在價值引領上也顯得蒼白乏力,與真正的文學作品存在距離感,甚至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因此,雖然楊氏童書創作熱鬧紅火,銷量巨大,劉緒源依然斷定此類創作處于文學水平線以下的低谷態勢。
顯然,褒揚的一方主要從閱讀快感、市場效益角度言說;而批評的一方則認為,以楊紅櫻為代表的暢銷書作者們,跟風嚴重,創新不足,使得他們的童書創作越來越凸顯稀薄與乏力。特別是楊紅櫻的童書,把幽默風趣置換成了滑稽、搞笑,甚至是無厘頭。她的作品,越來越不講究小說的結構,基本是些兒童故事堆積,情節的排列隨機性太強,并且無限拉長,做成系列,頗有狗尾續貂之感。可以說,楊紅櫻的創作模式基本就是:調皮搗蛋的故事+滑稽搞笑的語言=校園幽默小說。和國外同類型作品相比,如林格倫的《長襪子皮皮》《小飛人卡爾松》《淘氣包埃米爾》,萬巴的《搗蛋鬼日記》等,差距甚大。造成這種創作現象的原因,是市場的嬌縱與作家的惰性。在就業競爭的壓力下,現在的學生,學業負擔十分沉重,初高中生幾乎沒有課外閱讀時間,小學生的情況相對會好一些。對具有無厘頭搞笑特點的楊紅櫻童書,這無疑就有了一個潛在的市場,如同皇帝的女兒不愁嫁,只要有個好看的故事,加上點幽默搞笑調料,一篇校園兒童小說于是速成,然后一路綠燈,一紙風行。甚至只要沾上“校園”“淘氣包”“幽默”這幾個關鍵詞的邊兒,不管作者寫作水準如何,掛上楊紅櫻這塊“金字招牌”,就無往而不勝,就可獲得市場的豐厚回報。
書分多種。其中,有一種書猶如快餐,好吃,味爽,食之大快朵頤,然而食后很快無感,更得不到滋養。楊紅櫻的童書近乎于此。其短板之明顯,就在于文學性缺失,原創性匱乏,反映生活狹窄,幽默與滑稽界限模糊。兒童固然常以玩的形式完成對大千世界的探求,但楊紅櫻書中兒童玩得少調性、欠思考,往往流于生活的表面,失之人物刻畫得浮泛。她筆下的所謂幽默,是把生活中的人、事漫畫化,是經夸張后造成的滑稽、搞笑、無厘頭,是為幽默而幽默,為頑皮而頑皮。寫作者不具備探求人性深層的自覺和誠意,也缺乏這種能力和本事。她自以為貼近了兒童,其實貼近的無非表象。
楊紅櫻童書在點燃小讀者閱讀熱情的同時,也招致一些看出端倪的兒童文學評論家的批評。概括起來,批評的主要說辭為:楊紅櫻作品“嚴重缺乏文學性,但具備了一些搞笑故事特有的暢銷因素(頗接近于《故事會》雜志中的‘笑話’欄)”(劉緒源);“我們必須對楊紅櫻的創作觀保持相當的警惕”,否則兒童文學將“蛻變成一種庸俗的大眾娛樂”(陳恩黎);楊紅櫻作品是一種“電視‘圖像’式通俗兒童文學創作”,“如果歸咎責任,我認為主要不在楊紅櫻身上,而是在盲目炒作的媒介,不負責任的、缺乏洞見的童書評論界,還有‘閱讀’能力低下的成人社會(家長、教師),只貪圖后現代‘圖像’媒介的經濟利益的兒童文化產業”(朱自強)。應該說,對于楊紅櫻作品的批評,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對一位作家作品的思想交鋒,本質上看,是一場在特定時代背景下兒童文學價值體系與審美標準的爭論。
其實,經典與暢銷書,單從市場差價看,兩者的差距并不大,但給孩子精神上的影響卻是不可同日而語。讀暢銷書與讀經典在效果上迥然有別。當然,讀暢銷書并非“錯誤”,它們切合當下話題熱點、切合時尚閱讀心理,但它們不能或很少能給讀者輸入較多的精神營養與所需的正能量。所以,不必花太多時間與精力讀之,而是要保持閱讀經典的習慣,尤其是孩童,因為經典是經過時間淘洗后留下的文化精華,對孩子的價值觀建設與人格的完善有積極的意義。作家葉開在他的著作《對抗語文》中說:小學生年紀小,理解力不夠,要趁著記憶最好時多誦讀經典。是的,經典童書是奠基性的營養滋補品,它們會伴隨孩子整個成長過程,隨著他們理解力的增強,給他們帶來的人文力量是巨大的和持久的。經典之所以為經典,正因為它們是經過時間、歷史、現實以及專家、讀者等多種因素合力鍛造、積淀后的結晶。并不是每個家長都想讓自家的孩子成為“人家的孩子”,不指望孩子將來成為一個什么大人物,只要健康快樂就好。但即便如此,難道就不需要經典的滋養和撫育嗎?須知,經典還有除了人的能力培養功能外,還有人格、人性等方面的教益,是會給予孩子多種營養素的上上佳品。明乎此,誰還會放心地任由孩子去閱讀以調皮搗蛋為能事,且性格、價值觀迄未改變與發展,動輒以挑戰老師、挑戰秩序為能事的馬小跳系列呢?
D
文化多元時代,孩子的閱讀選擇自是可以多樣化的,但最好還是選擇經典來讀。艾德勒在《如何閱讀一本書》中說,名著的讀者是通過時間匯聚起來的,而不是一時的;名著不是一兩年之內的暢銷書,而是經久不衰的。莊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孩子時間精力有限,在有限時間內,如果選擇不當,讀書勢必事倍功半。而閱讀經典,當為孩子的最佳選擇。現在中國的兒童小說,太過強調“熱鬧”“好玩”,而對中國文化精髓中的“靜明”精神拒之千里。《莊子》嘗云:“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圣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雖為古文,卻不難理解。現在的孩子應該學習和汲取這樣的理念,閱讀一些這樣的圣賢之書。就中國兒童文學而言,我們太缺乏像《哈利·波特》《亮晶晶》《芒果街的小屋》《愛的教育》《窗邊的小豆豆》《夏洛的網》那樣打動人心的作品,也缺少像《我要我的雕刻刀》《獨船》《少女的紅發卡》那樣雖有瑕疵,卻能引發孩子思考的作品。我們的兒童文學作家在過度強調讓孩子快樂的同時,卻忽略和阻礙了孩子對于現在與未來的思考,放棄與拒絕了兒童文學對人性的揭示、對現實的批判。我們的兒童文學作家隊伍里,太缺少像金波、曹文軒、張之路、高洪波、秦文君、黃蓓佳、鄭春華這樣善于思考、富有人文情懷和悲憫精神的寫作者。我們的兒童文學的內容,也趨于單一化、類型化、淺表化的寫作,過度強調喜劇精神,排斥悲劇精神;過度強調幽默、滑稽、感官快樂,忽略了崇高、優美、靈魂塑造。孩子是我們的未來,對我們的未來一味灌輸“娛樂至死”“唯快樂論”而忽略其他,這絕非一個好的現象,潛在的文化危機也不難預料。
如此說來,楊紅櫻作品與經典之間存在相當明顯的距離,只能算是讀起來有點意思的迎合性童書。她的作品太好讀、太暢銷,與那種“乍看不好看”、讀后可回味的童書相比,有著明顯區別。楊紅櫻的名氣確實大,但作者名氣大、作品很暢銷,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一般地說,越是文學大獎,越是注重作品內容的深度。有思想的讀者,往往也更青睞那些有深度、有水平,也許不為大眾所熟識的“小眾”作家。經典和暢銷書代表的不是作家個體,而是兩種不同的文學類型,這兩種類型和其他的文學類型一樣,沒有好壞對錯之分,只有閱讀價值與意義的不同。經典不獨文筆雋美、主題深刻,還是孩子可以讀,大人也可以讀,二十年前可以讀,二十年后依然可以讀的佳作。在此意義上,對孩童來說,最好是多讀經典,精讀名著。當然,楊紅櫻的書不是不能讀,而是不必多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