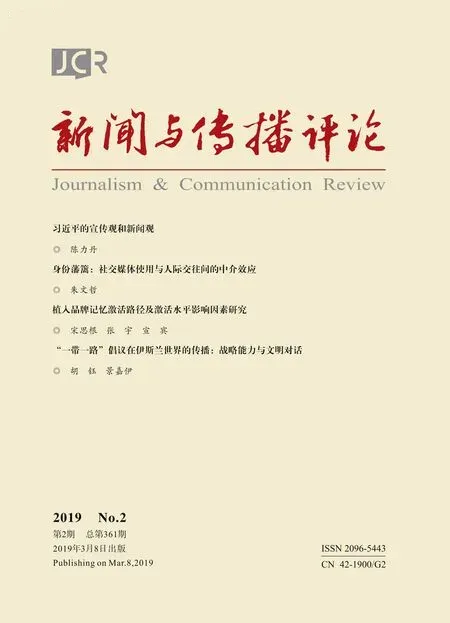由身份對抗走向話語共謀
——數(shù)字媒介對電影批評主體建構(gòu)及其話語策略的影響
周 旭
數(shù)字媒介的出現(xiàn)不僅改變了電影批評的傳播方式和言說空間,也使得電影批評的主體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首先,傳統(tǒng)影評的主體基本上是由學院派知識分子和電影從業(yè)者構(gòu)成,而在“電腦書寫”的影響下,大眾影迷則成了電影批評的重要力量,電影批評真正進入眾聲喧嘩的雜語時代。其次,在數(shù)字媒介構(gòu)建的賽博空間里,電影批評主體的身份失去了穩(wěn)定性,專家學者不得不放棄“立法者”的身份,與大眾影評人進行新一輪的話語權(quán)爭奪。此外,數(shù)字媒介對電影批評主體的影響更多表現(xiàn)在言語行為層面,亦即數(shù)字媒介交流攪亂了電影批評主體與電影批評文本以及讀者之間的關(guān)系。因而,筆者運用媒介話語批評的相關(guān)方法,對電影批評主體身份的建構(gòu)、電影批評主體數(shù)字化生存的話語策略等問題展開論述,以期深刻地揭示出數(shù)字媒介給電影批評主體帶來的種種影響。
一、尋找“肉身”:“電腦書寫”與電影批評主體建構(gòu)
電影批評作為一種話語實踐活動,其主體建構(gòu)自然與媒介環(huán)境密不可分。關(guān)于媒介的主體建構(gòu)功能,有研究者指出:“媒介的主體建構(gòu)是一種包含訊息形成、表述和使用的‘話語’實踐,并通過秩序、知識、權(quán)力三個切口層層深入,勾勒出媒介的主體建構(gòu)過程。”[1]雖然這種說法具有一定的普適性,但在不同的媒介環(huán)境里,主體的位置以及建構(gòu)方式是不盡相同的。如波斯特所言:“印刷文字把主體構(gòu)建為理性的自律自我,構(gòu)建成文化的可靠闡釋者,而電視語言則代替了說話人群,從根本上瓦解了理性自我所必需的話語自指性,加之電視語言是無語境、獨自式、自指性的,這便誘使接受者對自我構(gòu)建過程抱有游戲態(tài)度,在話語方式不同的‘會話’中,不斷地重塑自己。”[2]的確,由于報紙、雜志等傳統(tǒng)紙媒的語言結(jié)構(gòu)是“極少數(shù)傳播者自說自話的‘無回應的言語’”,所以,在電影批評主體那里,“這種媒介話語體制是單向度的傳媒在建構(gòu)單向度的‘他律主體’”。[3]譬如在十七年電影時期,電影創(chuàng)作、電影批評被視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電影媒介基本上成了政治話語的傳播工具。關(guān)于電影創(chuàng)作,史東山在《目前電影藝術(shù)的作法》中有比較直接的描述:“在當前現(xiàn)實情勢中,我們首先需要在多方面為工農(nóng)兵的利益而斗爭,要以保衛(wèi)工農(nóng)兵的利益為大前提,來用文藝為工農(nóng)兵服務,這才是工農(nóng)兵低最忠實的勤務兵。”[4]陳荒煤也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之所以有力,首先在于它為勞動人民服務,為工農(nóng)兵服務。”[5]而這一時期的電影批評主體則主要由行政官員和專家構(gòu)成,也即有學者提出的“政工派”和“專家派”。其中,“政工派強調(diào)‘堅持方向’及階級斗爭,給電影創(chuàng)作劃禁區(qū),提倡什么‘大寫十三年’‘片片工農(nóng)兵、部部滿堂紅’之類的革命口號,搞運動,搞批判,使創(chuàng)作的路子越走越窄。專家派則講‘藝術(shù)規(guī)律’,講團結(jié),講創(chuàng)作實踐,認為‘路子還是寬一些好,題材范圍還是廣一些好,風格樣式還是多樣化才好’”。[6]與“政工派”相比,“專家派”比較強調(diào)在電影創(chuàng)作、電影批評的實踐中要尊重藝術(shù)規(guī)律和電影題材的多元化,但面對“政工派”的盛氣凌人,特別是《武訓傳》遭受政治批判之后,電影批評便失去了自律性,時而淪為政治的籌碼,時而又成了罪惡的淵藪。如此觀之,無論是“政工派”還是“專家派”,他們終究像“桀驁不馴的孫悟空先是做了唐僧的門徒,然后被收入‘西天’編制一樣”,都要“受到意識形態(tài)的統(tǒng)一要求、受到通律性的限制”[7]。所以,在電影創(chuàng)作和媒介話語機制高度集權(quán)化的社會文化背景里,電影批評通常處于缺席或噤聲的狀態(tài),而電影批評主體則是政治話語和媒介話語共同建構(gòu)的、單向度的“他律主體”。
無須贅言,主體建構(gòu)與信息傳播方式密切相關(guān),不同的傳播方式會促使主體隨著語言機制的改變而進行重新建構(gòu)。在口頭傳播階段,“主體是社會化的,個人處在一個熟悉的小社群之中,個體處在各種親密關(guān)系的結(jié)構(gòu)之中;在印刷傳播階段,主體身份脫離了交流現(xiàn)場,書寫行為本身成為建構(gòu)主體的方式;在電子傳播階段,語言的使用基本上與電子書寫者的傳記身份相脫離,身份以及主體在電子交流網(wǎng)絡中消散了”。[8]事實上,與口頭語言、印刷文字的運作方式不同,“電腦書寫”不但把書寫領(lǐng)域擴張了,還給書寫主體帶來了多個層面的影響,具體如波斯特所述:“其一,它們引入了對身份進行游戲的種種新可能;其二,它們消除了性別線索,使交流非性別化;其三,它們使關(guān)系中的現(xiàn)存等級制失去穩(wěn)定性,并根據(jù)以前并不相關(guān)的標準將交流重新等級化;其四,首要的是它們消解了主體,使它從時間和空間上脫離了原位”。[2]的確,在面對面言說的口頭傳播時代,“‘紅口白牙’的顏面和直接到場的身體都是人類交往的道德器官,是個體身份和名分的直接載體”,印刷媒介時代的交流則進入了一種“沒皮沒臉、無形無象的身體缺席的交流”。[3]而進入數(shù)字媒介時代后,電話、電視、電腦等逐漸融合成為多功能一體化的“智能媒介”,信息傳播者和接受者、信息生產(chǎn)者和消費者的身份變得模糊難辨,互動性的信息傳播方式不但促成媒介話語秩序的重構(gòu),還使得“人們所熟知的現(xiàn)代主體被置換成一個多重的、撒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體,并被不斷質(zhì)詢?yōu)橐环N不穩(wěn)定的身份”。[9]由此,“電腦書寫”是一種無“肉身”的寫作,它被抽離了社會交往的現(xiàn)場,致使主體身份變成了想象性的。在“界面”代替“臉面”的交流中,漂浮著的主體被懸置于客觀性的種種不同位置之間,不同的構(gòu)型使主體伴隨交流情景的不確定性,而相應地被一再重新建構(gòu)。作為被“電腦書寫”“腹語化”和“碎片化”后的新主體,是一種無性別、去族性、超階層的人機相結(jié)合的“共同體”,是被電腦數(shù)字技術(shù)篡改和變了性的“賽博人”。簡言之,數(shù)字媒介對主體建構(gòu)的影響集中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電腦書寫直接將自己呈現(xiàn)為一個他者,一個與己相異的人”[8];另一方面,由于“電腦書寫”的非物質(zhì)性、匿名性,及其對穩(wěn)定性身份的顛覆,這不僅可以使交流主體隱蔽在一個超越責任感的位置上,進行自由交流,還能夠為許多交流者“提供一種顯而易見的緩刑,使他們暫時不必踏入理性的囚車”。[2]如是觀之,電影批評作為一種特殊的寫作活動,在置身“數(shù)字化”的媒介傳播環(huán)境之時,其主體特性自然會發(fā)生新的變化,這主要呈現(xiàn)為:
第一,數(shù)字媒介不但為電影批評主體的大眾化提供了一個新的話語空間——賽博空間,還促使電影批評寫作朝著“民間寫作”的方向發(fā)展。我們知道,從莎草紙到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工具的改變是“寫作自由”不斷得到解放的重要原因。在紙媒時代,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電影批評主體大多是行政官員、知識分子、電影從業(yè)者,而賽博空間是一個沒有圍墻、沒有“把關(guān)人”看守的空間,任何人“都可以在這里隨意來往歇息,交流談論;這里沒有中心,沒有制高點,它是眾多中心與邊緣的交匯,它也許將被規(guī)范化但絕不會被體制化”。[10]與傳統(tǒng)電影批評的精英姿態(tài)不同,數(shù)字媒介打破了少數(shù)人擁有批評話語權(quán)的既定格局,使民間記憶重新從潛意識深處燃起。于是,民間話語在電影批評場域里瘋狂滋長,精英化的作者面孔逐漸消失,大眾影迷成為電影批評主體的新生力量。另外,對于活躍在賽博廣場的影評人來說,他們的寫作動機已不再是單純地抒發(fā)自己的情感,而是通過制造文本點擊率,乃至轟動效應來達到寫作權(quán)益的最大化,所以,他們必須深諳廣大民眾的喜好與趣味,創(chuàng)作適合民間需求的“大眾文本”。
第二,數(shù)字媒介讓電影批評主體成為“自由人”,享有對影評人身份進行游戲的種種新的可能。數(shù)字媒介既打破了時空的限制,也解構(gòu)了地緣政治、地緣經(jīng)濟、地緣文化的概念,并形成了以傳播信息為中心的跨地域、跨國界、跨文化的全新傳播方式。對于電影批評而言,這種新的信息傳播方式,拆除了電影批評發(fā)表的門檻,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影評人,以影評者的身份和話語姿態(tài)在賽博廣場上自由言說。再者,沒有“門檻”本身就是電影批評寫作的一個重大改變,因為傳統(tǒng)電影批評的主體往往是精英化、專業(yè)化的,一個人要成為電影批評家需要經(jīng)過體制、權(quán)威的認證,而數(shù)字媒介時代的電影批評向大眾敞開了,“寫作越來越成為一種個人愛好而不是某種由體制化的所謂‘權(quán)威’欽定的‘特權(quán)’”。[10]我們知道,傳統(tǒng)的“作者”概念是紙質(zhì)媒介時代的產(chǎn)物,紙質(zhì)媒介在文化認知和社會空間上保障了作者身份,而數(shù)字媒介創(chuàng)造的賽博空間卻為“作者”身份的虛擬化提供了技術(shù)環(huán)境。所以,那些游走于賽博廣場的影評人已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電影批評家了,而是乘“虛”而入的“三無”(無身份、無性別、無年齡)游民。即便很多影評人成名后,他們大多也不愿向外透露自己的個人信息,因為這種匿名性的影評寫作,可以讓批評者成為“自由人”,真正進入一種個性化、狂歡化的寫作狀態(tài)。如著名作家張抗抗所描述的那樣:“無論大魚小魚,在網(wǎng)絡世界里自由漫步,發(fā)問與應答、痛苦與歡樂,都是悄然無聲。岸上的人聽不見他們發(fā)言,他們的話是說給自己和朋友們聽的。那些聲音發(fā)自孤寂的內(nèi)心深處,在浩渺的空間尋找遙遠的回聲。網(wǎng)絡寫作者的初衷也許僅僅只是為了訴說,他(她)們只忠實于個人的認知,鄙視名譽欲求和利益企圖——這是最重要的和最寶貴的。”[11]此外,賽博空間是一個自由交往的空間,它不但打破了傳統(tǒng)電影批評那種固定和封閉的書寫模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作者和讀者之間的界限,使電影批評主體具有獲得多種身份的可能性——人人都可以集作者和讀者于一身。
第三,賽博空間的電影批評寫作,是一種“無肉身”“去性別”“超階層”的后現(xiàn)代寫作。在后現(xiàn)代寫作狀態(tài)下,主體通常感覺不到自我的存在,儼然一個去中心化的主體,一個沒有“肉身”和任何身份的主體。換言之,后現(xiàn)代寫作的主體是“零散的,碎片化的,主觀感性、主體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消失,主體意向性被懸置”[12]。但是,寫作主體又不應該被完全拋棄,而應該“探究它的功能、它對話語的介入,以及它的從屬系統(tǒng)”[13]。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與信息社會緊密相連的后現(xiàn)代寫作,“在突出‘誰在寫’的焦點轉(zhuǎn)換中,重新評估‘寫什么’和‘怎樣寫’的問題,體現(xiàn)出其彌合精英與大眾、作者和讀者以及諸文類之間鴻溝的潛在意圖”[10]。“電腦書寫”之所以被視為一種后現(xiàn)代寫作,主要是由于數(shù)字化作品將作者與文本分離開來,任何人都可以自行轉(zhuǎn)換文本——“不是僅通過他(她)的想法或者一些旁注,而是加諸文本自身從而改換成另一文本加以傳播”[14],原作者的“肉身”無處可尋,真正填平了精英與大眾、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鴻溝。較之傳統(tǒng)電影批評,數(shù)字媒介不僅改變了電影批評“怎樣寫”的規(guī)則,還建構(gòu)了電影批評的主體。在賽博空間里,影評人通常都戴著面具,大多不愿以真面目示人,或許他們是為了享受那種卸下沉重“肉身”的清爽和自由,又或者是他們深知賽博廣場上的言說規(guī)則——文本結(jié)構(gòu)的不確定性,所謂的性別、階層等身份都是不在場的。
概言之,“電腦書寫”會使寫作的主體失去穩(wěn)定性,因為“電腦書寫”便于文本再加工和再傳播。并且,在這種文本創(chuàng)建機制下,集體作者必然取代作者個體,作者的身份在電子交流網(wǎng)絡及電腦存儲系統(tǒng)中消散了。因而,對于進入“電腦書寫”之后的電影批評來說,不僅僅是“寫作場景從紙、筆或打字機轉(zhuǎn)換成全球聯(lián)網(wǎng)的計算機,這一轉(zhuǎn)換還使得我們再次明確作者已從文本的中心落到邊緣,從意義本源變?yōu)橐饬x提供者”[14]。基于此,電影批評的主體開始熵變成一個“腹語化”“碎片化”“去中心化”,以及缺乏穩(wěn)定性的新主體,并且性別、族群、階層、地域等再也不是區(qū)分主體身份的標簽和尺碼了。
二、身份對抗:“立法者”“闡釋者”與言說的權(quán)力
賽博空間作為一個虛擬的交往空間,它不但給電影批評提供了一個新的話語平臺,還改變了電影批評主體的言說身份,“以前的批評家仿佛是在走街串巷的貨郎,告訴生活在村子里的我們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他們又像牧師,在傳教布道,我們仰望著,他們神圣的光輝代表著來自天國的上帝的意志”[15]。而進入賽博廣場后,電影批評家的“立法者”身份受到了強烈沖擊,人們反而更容易被那些離經(jīng)叛道的言辭所吸引,瞬間,大眾影評成了人們凝視的焦點。事實上,電影批評主體身份的轉(zhuǎn)變是批評家“立法者”身份遭遇困境的一個縮影,這既反映出了批評專家那種“自戀式人格想象”與追求“精神領(lǐng)袖”之間的裂隙,也是“現(xiàn)代性的立法者理念與數(shù)字媒介所帶來的話語權(quán)的釋放、價值觀的多元,與消解等級和中心的后現(xiàn)代氛圍之間的深刻悖論”。[16]如此,以學院派知識分子和電影從業(yè)者為主體的專家批評陷入了身份分裂的痛苦與矛盾之中,他們懼怕失去“立法者”的身份,卻又想逃離“無人傾聽”的尷尬處境。
在齊格蒙·鮑曼看來,“立法者”角色這一隱喻是對現(xiàn)代型知識分子話語權(quán)利的最佳描述,因為“立法者角色由對權(quán)威性話語的建構(gòu)活動構(gòu)成,這種權(quán)威性話語對爭執(zhí)不下的意見糾紛做出仲裁與抉擇,并最終決定哪些意見是正確的和應該被遵守的”[17]。當然,知識分子之所以有更多機會和權(quán)力來獲取知識,應歸功于程序性規(guī)則,這些程序性規(guī)則既是獲得真理的重要保障,也是道德價值判斷和藝術(shù)趣味選擇的有效依據(jù)。所以,就紙質(zhì)媒介語境中的電影批評家而言,他們就是電影的“立法者”,他們在電影的理解和欣賞方面往往要優(yōu)于普通電影觀眾,他們的思想主張和批評觀念甚至能引領(lǐng)電影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方向。譬如在20世紀30年代,隨著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夏衍、王塵無、石凌鶴、魯思、徐懷沙等為代表的左翼知識分子于1932年7月成立了“影評人小組”,旨在通過電影批評來影響當時的電影創(chuàng)作。在左翼電影批評以及左翼文藝思潮的影響下,僅1933年就創(chuàng)作了《城市之夜》《狂流》《都會的早晨》《女性的吶喊》《脂粉市場》等18部左翼電影。其中,直接以反帝為題材的作品有《小玩意》《香草美人》《春蠶》《天明》《掙扎》等;反對封建體制的作品有《狂流》《鐵板紅淚錄》等;暴露女性問題的作品有《女性的吶喊》《母性之光》《脂粉市場》等。此外,1933年還產(chǎn)生了一些雖未進入左翼電影范疇,但思想具有明顯進步傾向的影片,如明星公司的《道德寶鑒》《琵琶春怨》《現(xiàn)代一女性》《健美之路》等作品,天一公司的《孽海雙鴛》《苦兒流浪記》《生機》《吉地》等。概言之,這一時期以左翼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電影批評實質(zhì)上是把電影看作一種思想啟蒙的工具,并寄希望“通過電影批評來牽引中國電影的左轉(zhuǎn),推動中國電影的大眾化,進而雙管齊下促進民眾的覺醒”[18]。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整個社會文化的轉(zhuǎn)型,娛樂片創(chuàng)作才開始回潮。但由于當時大多數(shù)電影工作者、電影理論家在觀念上還未做好迎接電影娛樂化的準備。所以,娛樂片創(chuàng)作在某種程度上仍處于被噤聲的境地,諸如電影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shè)事業(yè)、“不能把票房價值放在首位,而應該幫助觀眾、特別是青少年們認識生活,提高審美趣味”[19]的聲音不絕于耳。但為了遏制不斷流失的觀眾和走出中國電影發(fā)展的市場困境,從1980年前后開始,中國電影迎來了三次娛樂片創(chuàng)作高潮。一般認為,第一次娛樂片高潮是以1980年的《神秘的大佛》和1983年的《武當》《武林志》為主要代表;第二次娛樂片高潮以1985年的《神鞭》和1986年的《峨眉飛盜》為主要標志;第三次娛樂片高潮則是以1987年的《金鏢黃天霸》《翡翠麻將》《最后的瘋狂》《黃河大俠》《東陵大盜》,以及1988年的《銀蛇謀殺案》《瘋狂的代價》《殺手情》《搖滾青年》等為代表,此次娛樂片創(chuàng)作高潮一直持續(xù)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這三次娛樂片創(chuàng)作高潮雖然對中國電影走上商業(yè)化發(fā)展之路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但它們“幾乎都是在電影面臨困境、萬般無奈中的一次次奮起拼搏,且前兩次均未獲得應有的支持和重視”[20]。唯有在第三次娛樂片創(chuàng)作高潮來臨之際,電影理論界和批評界才開始自覺地正視中國電影發(fā)展的現(xiàn)實困境,掀起了一場場聲勢浩大的娛樂片討論。在這股討論洪流中,首要的便是從觀念上為娛樂片“正名”“立法”,如邵牧君認為:“電影和其他藝術(shù)不一樣,它作為一種成本昂貴的藝術(shù)商品,必須把娛樂功能放在第一位,必須通過娛樂來發(fā)揮其認識功能,在娛樂中獲得審美享受。”[21]同樣,饒曙光也指出,“電影文化的主流是娛樂電影”,就電影的文化職能而言,它主要“通過滿足人們的感覺、感性,使一切屬人的感覺和特性得到徹底解放,促使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發(fā)展”[22]。此外,比較有影響力的文章還有陳昊蘇的《關(guān)于娛樂片主體論及其他》、邵牧君的《中國當代娛樂片問題駁議》、賈磊磊的《皈依與禁忌:娛樂片的雙重抉擇》、王云縵的《娛樂片五題》、花建的《游戲中的生存與選擇——娛樂片本質(zhì)探論》等,其中陳昊蘇的《關(guān)于娛樂片主體論及其他》一文,非常明確地提出了“娛樂片主體論”的具體根據(jù)。雖然陳昊蘇有著“電影部長”的政治身份,但其“娛樂片主體論”的觀點卻在學術(shù)界產(chǎn)生了巨大沖擊,與知識分子話語一道成為推動20世紀80年代娛樂片發(fā)展的重要力量。當然,整個20世紀80年代除了娛樂片之爭,中國電影理論界先后展開過電影與戲劇、電影的文學性、電影語言現(xiàn)代化、電影民族化、西部電影、謝晉電影模式等問題的學術(shù)性爭辯,涌現(xiàn)出了諸如《丟掉戲劇的拐杖》《談電影語言的現(xiàn)代化》《電影文學與電影特性問題》《“影戲”理論歷史溯源》《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等一大批學理性、知識性極強的文章。毫不夸張地說,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電影批評表現(xiàn)得最活躍、成果最豐碩的年代,是一個“‘理論滋養(yǎng)靈感’的年代,更是理論影響創(chuàng)作的年代”[23]。然而,這種學理性、知識引領(lǐng)式的電影批評持續(xù)的時間并不長,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主要發(fā)聲渠道的大眾批評的崛起,專家批評的“立法者”地位受到了強烈沖擊。具體言之,一方面,因為“審美判斷的有效性依賴于它所誕生的‘位所’,權(quán)威性是屬于這個位所的”[17],而大眾文化、商品經(jīng)濟的大行其道,不僅產(chǎn)生了新的權(quán)威性位所,還革新了自己的價值判斷標準,所以,傳統(tǒng)意義上由美學家、知識分子專家來保障這個位所的權(quán)威性,已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了。面對混雜的、非美學的、非哲學的權(quán)威位所,知識分子逐漸放棄了宏大敘事的野心,被迫接受那種零散的、不確定的游牧式的現(xiàn)實生活。如是,曾幾何時,只顧追求那種理性話語和闡釋深度的專家批評,不得不因“立法者”身份的喪失而尋求新的話語通道和言說身份。另一方面,賽博空間本身具有明顯的后現(xiàn)代特征,是一種網(wǎng)狀-鏈式的信息傳播空間,強調(diào)開放、平等與對話,拒斥等級、中心與獨白。為了適應新的話語傳播環(huán)境,專家批評應該調(diào)整自我的姿態(tài),擯棄過去那種自說自話、玄奧難懂的話語風格,由“立法者”轉(zhuǎn)變?yōu)椤瓣U釋者”。
事實上,“闡釋者”與“立法者”是兩種相對應的角色隱喻,只不過“闡釋者”是一種對典型的后現(xiàn)代型知識分子話語策略的最佳描述。齊格蒙·鮑曼認為:“闡釋者角色由形成解釋性話語的活動構(gòu)成,這些解釋性話語以某種共同體傳統(tǒng)為基礎(chǔ),它的目的就是讓形成于此一共同體傳統(tǒng)之中的話語,能夠被形成于彼一共同體傳統(tǒng)之中的知識系統(tǒng)所理解。”[17]由此,專家批評從“立法者”轉(zhuǎn)變?yōu)椤瓣U釋者”,不是為了建構(gòu)一種新的話語秩序,而是通過與他人積極的對話,以避免交往活動中發(fā)生意義層面的曲解。事實上,很多進入賽博空間的批評家并未放棄對自我身份的迷戀,他們只是在博客、微博、微信公眾號上貼出自己在學術(shù)期刊上發(fā)表過的文章,這種生硬的文本搬運式的寫作方式,既表明批評家試圖通過數(shù)字媒介來延伸、提高自己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身份,但同時也暴露出他們在寫作慣習上的積重難返。對于電影批評專家而言,要真正實現(xiàn)由“立法者”到“闡釋者”的身份轉(zhuǎn)換,就應該“順應數(shù)字媒介的特點,改變寫作觀念與傲慢的姿態(tài),擺脫‘專家’名號的詢喚,在民主、互動的氛圍中用誠實、生動的文字與草根群體談天說地”[16]。易言之,電影批評專家要想在開放、自由、互動的賽博空間謀求一席之位,走出“無人傾聽”的困境,不只是簡單地完成寫作工具的置換,而是要積極主動地參與到社交群體的話語交流中,創(chuàng)建新的電影批評話語通道。當然,在批評專家進行身份轉(zhuǎn)換的過程中,他們依然具備作為知識話語持有者的權(quán)威,他們不但把意識形態(tài)批評、精神分析批評、結(jié)構(gòu)主義批評、電影敘事學批評、女性主義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等專業(yè)性的批評方法移植到賽博空間的寫作中,而且還將賽博空間的虛擬性、開放性、互動性、民間性等文化特質(zhì)引入電影批評,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轉(zhuǎn)化和吸收,使電影批評能夠產(chǎn)生應有的文化效應。
三、話語共謀:專家批評、大眾批評的媒介化生存策略
布迪厄認為:“作為包含各種隱而未發(fā)的力量和正在活動的力量的空間,場域同時也是一個爭奪的空間,這些爭奪旨在維持或變更場域中力量的構(gòu)型。”[24]易言之,場域中的“占位者”會采取各種行動策略來保證或者改變他們既得的場域位置,并制定一種維護他們自身利益的等級化原則。場域中占支配地位的一方雖然可以通過教育機制的規(guī)訓、傳播讓大眾熟悉和接受,但也正因為這種熟悉化而使其變得日趨平庸和保守。所以,當場域發(fā)展到一個既定時刻,就會有新的競爭者出現(xiàn),而且,他們會不斷向場域的支配者發(fā)起挑戰(zhàn),直到把“在合法性的等級關(guān)系下被分成等級的所有生產(chǎn)者、產(chǎn)品、趣味統(tǒng)統(tǒng)打發(fā)到過去”[25]。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數(shù)字媒介和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發(fā)展,新的文化生產(chǎn)者和批評群體不斷涌入電影批評場,這不僅徹底改變了電影批評主體的結(jié)構(gòu),還使電影批評場的斗爭變得異常復雜。
第一,在數(shù)字媒介搭建的“比特城堡”里,電影批評再也不是知識分子、電影從業(yè)者的獨享之物,而是逐漸走向大眾、走向“民間”,成為廣大影迷群體的共享之物。與紙媒相比,數(shù)字媒介賦予了電影批評前所未有的開放性、迅捷性和互動性。首先,從批評主體上看,由于賽博空間自身的開放性、虛擬性、互動性等特點,只要進入賽博空間的“公民”,都享有自由發(fā)言權(quán),不受身份等級的限制。其次,從批評內(nèi)容上看,賽博空間的電影批評通常沒有特定的選題,所評內(nèi)容和對象完全取決于批評者自己的興趣和關(guān)注的焦點,無論是電影作品還是明星奇聞,都可以成為熱議的對象。最后,從批評互動上看,在紙質(zhì)媒介上發(fā)表的電影評論,由于受到傳播機制的諸多限制,其產(chǎn)生的評論效果很難在第一時間獲得反饋和評價,而賽博空間的信息容納量是不受限的,無論是公共論壇、個人博客,還是個人微博、微信公眾號,讀者在閱讀影評后可以做出最及時的反饋與評價。另外,賽博空間的影評書寫,大多是匿名性的,非實名影評人可以卸下現(xiàn)實生活中的各種身份標簽,以更加本真的狀態(tài),直抒胸臆、針砭時弊。正因為數(shù)字媒介從批評主體、批評內(nèi)容、批評互動形式等多個層面,營建了一個開放、自由的電影批評場域,才有大批量的人群涌入,并從根本上改變電影批評主體的結(jié)構(gòu)。
第二,在數(shù)字媒介建構(gòu)的電影批評空間里,專家批評和大眾批評為了捍衛(wèi)各自的場域位置,雙方之間必然會展開激烈的對抗和爭斗。具體而言,專家批評和大眾批評之間的矛盾對抗主要呈現(xiàn)為兩種:一種是學院派專家質(zhì)疑大眾批評的“合法性”,認為大眾批評是“虛張聲勢、發(fā)泄不良情緒的垃圾場,夸張、諷刺、謾罵不絕于耳,與評論的公正、說理相差甚遠”[26]。因為在大部分學院派專家看來,電影批評是電影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是“使影片的美學和藝術(shù)內(nèi)涵可以被更多的觀眾所理解和接受”[27],所以,從事電影批評既要有深厚的理論根基,還要有良好的思想文化素養(yǎng)。與之相反,大眾批評則是市場化、商品化的結(jié)果,他們大多是電影制作方或發(fā)行機構(gòu)豢養(yǎng)的“御用評論”,或是由投資方生產(chǎn)的“軟廣告”評論,缺乏電影批評最基本的學理性和自主性。另一種是電影從業(yè)者對大眾批評置若罔聞或持抵觸的態(tài)度。在比較理想的狀態(tài)下,電影創(chuàng)作和電影批評之間應該是一種良性的互動關(guān)系,電影從業(yè)者,特別是電影導演應該把電影批評視為推介自己作品、溝通和征服觀眾的有效途徑。但事實上,很多導演與大眾影評人之間卻是一種“水火不相容”的關(guān)系,如馮小剛的《非誠勿擾2》上映后,不少影評人斥責電影中的植入廣告太多,認為:“一個《讓子彈飛》不讓廣告飛,一個《非誠勿擾2》非廣告勿擾;一個拼死捍衛(wèi)藝術(shù),一個輕松笑攬銀子;一個真正抱著對觀眾非誠勿擾的心態(tài)創(chuàng)作、靠著通俗易懂、節(jié)奏緊湊、荒誕幽默征服了觀眾,一個當著觀眾的面干私活,靠少數(shù)媒體的交口忽悠沒心沒肺地自賣自夸,以致失去了氣場。”[28]這篇措辭辛辣的批評文章不僅引起馮小剛與影評人之間的對峙和罵戰(zhàn),也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了電影從業(yè)者對大眾影評的不信任和抵觸的態(tài)度。
第三,隨著電影批評媒介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改變,專家批評在遭遇尷尬的失語之困后,開始調(diào)適自身的話語策略,逐漸走向賽博廣場,與大眾批評一起成為新的電影批評話語景觀。新世紀之交,中國電影批評發(fā)生了結(jié)構(gòu)性變革,一方面,與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中前期相比,專家批評開始陷入沉靜與寂寥,具體表現(xiàn)為“要么沒有發(fā)出自己的聲音,要么注重學理標尺,理論色彩過于濃厚,和創(chuàng)作現(xiàn)實產(chǎn)生隔離”[29];另一方面,隨著電腦、手機等數(shù)字媒介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大眾影迷以論壇、跟帖、博客、微博、微信等方式傳播他們的批評聲音,為電影批評打開了一個新的話語空間。不僅如此,這種發(fā)展格局還給以報紙雜志為主要話語陣地的專家批評形成了一種倒逼態(tài)勢,他們?yōu)榱司S護自身在電影批評場域中的位置,不得不主動或被動地進入賽博廣場,以新的話語姿態(tài)與大眾批評交流、對話,甚至部分學院派知識分子、電影從業(yè)者也以影評人的身份自居,并與大眾影評人之間結(jié)成了話語同盟。總之,在賽博空間里,影評人的身份比較復雜,既有大眾影迷,也有媒體從業(yè)人員和學院派知識分子。特別是學院派知識分子這種“雙面”身份,不但是電影批評載體轉(zhuǎn)換以及電影批評空間位移的結(jié)果,更是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相互交流、影響、轉(zhuǎn)化與創(chuàng)造使然。所以,面對因數(shù)字媒介技術(shù)飛速發(fā)展而出現(xiàn)的社會文化轉(zhuǎn)型,以學院派知識分子、電影從業(yè)者為主體的專家不得不在兩難中做出選擇,他們必然通過調(diào)整自己的身份角色和話語策略以適應電影批評的新發(fā)展。換言之,也就是學院派知識分子想要使自己的批評話語具有社會關(guān)聯(lián)性,“并對電影創(chuàng)作產(chǎn)生影響,那么他/她首先要調(diào)整的恐怕是從一個評判型、指導型乃至啟蒙型的‘人文知識分子’向一個普通影迷和大眾型影評人的轉(zhuǎn)型”[30]。
統(tǒng)而言之,數(shù)字媒介不僅從物質(zhì)形態(tài)上改變著電影批評的寫作慣習,也給電影批評主體的身份建構(gòu)和話語策略帶來了巨大影響。在數(shù)字媒介構(gòu)建的賽博空間里,電影批評主體的身份失去了穩(wěn)定性,那些曾經(jīng)居于電影批評場域高位的專家學者,逐漸放棄自己的“立法者”身份,開始嘗試“數(shù)字化”的寫作方式,與大眾影評人進行新一輪的話語權(quán)爭奪。但實際上,數(shù)字媒介對電影批評主體的影響更多表現(xiàn)在言語行為層面,因為數(shù)字媒介交流攪亂了電影批評主體與電影批評文本以及讀者之間的關(guān)系,并以極為新穎的形式重構(gòu)著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所以,無論是專家批評還是大眾批評,他們都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話語策略,從身份對抗走向話語共謀,以適應“數(shù)字化”生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