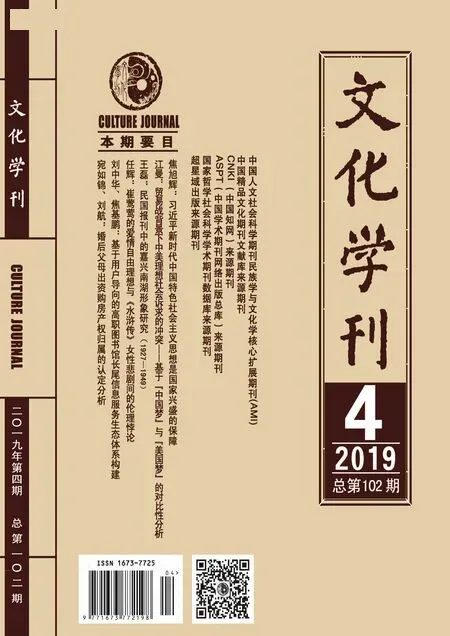19世紀末華人移民加拿大成因探驪
劉淑玲
移民是一種復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古今中外,無論大規模的族群遷徙,還是小群體的居地轉移,都隱含著紛繁復雜的因素。黎全恩等學者在《加拿大華僑移民史》中寫道:“基于民族、地緣、血緣關系相互牽引造成的移民現象發生在近代中國,是有著各種復雜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許多內部和外部原因的。”[1]的確,19世紀末期華工出國的內因主要是“在社會巨大變革之中,清政府一邊鎮壓農民起義,并采取趕盡殺絕的殘酷政策;一邊不管百姓死活,變本加厲地橫征暴斂,這就觸發了民眾外逃和人口外徙的局面”,而早期華工出國的外因則是“當時國外大量需求勞動力,而中國廉價勞動力意味著更便宜的勞動力商品,意味著節省金錢……”[2]此種華人移民的內外成因分析清晰呈現出華工外徙的客觀因素。然而,漢民族歷史上多次群徙遷移的種族歷史記憶是深藏于華夏子民心中的“集體無意識”,是天災人禍面前謀求生存之路的傳承方式,這些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因素都是促發早期移民潮流的產生和壯大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成因。
一、漢民族移民的群體記憶:華人移民加拿大的歷史與心理因素
表面看來,淘金和筑路是早期加拿大華人移民的兩大直接動因。其表面背后掩藏的有關歷史、社會、地理和文化等方面的復雜因素都構成了推動早期華人對加拿大趨之若鶩的助推力。
從歷史角度而言,漢民族的移民歷史是與漢民族的發展史同步行進的。從古至今的每個朝代都有很多人由于戰亂、饑荒、買賣或者宗教等各種復雜原因而形成一定規模的移民行動。當前,國內最為系統而完整地呈現自先秦至20世紀40年代中國境內移民狀況的六卷本叢書《中國移民史》的作者葛劍雄教授如是評價移民史:“移民的歷史與中國的歷史、世界的歷史共同開始,移民的作用和影響無所不在,無時不在,中國史和世界史的研究都離不開移民史的研究。”[3]
回眸歷史,從三國兩晉到南北朝時期,直至唐代的安史之亂,從宋朝靖康之亂再到蒙元對峙時期,漢人南遷的浪潮從未中止過。“縱觀中國社會發展的漫漫歷程,普通民眾為謀生存、求發展而背井離鄉,游走遷移,史不絕書。”[4]對豐衣足食、安生服業的不懈追求使得歷代國人不惜離鄉背井、顛沛流離。這樣的民族歷史被世代記憶傳遞下來,即建構了華夏族群強大的集體無意識。每當類似的生活境況發生時,“歷史再現”便成為人們尋求出路時極具共性的集體思維模式。故而在19世紀末的饑荒戰火之中,華人選擇遠渡重洋奔赴加拿大不可不說是民族歷史記憶的驅動,是集體記憶中的心智再建構。
二、內困外侵:華人移民加拿大的原動力
如果說漢民族群體移民的歷史記憶是促成海外移民的歷史成因的話,那么,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則是華裔移民最直接的推動力。鴉片戰爭于1839年爆發,1841年,清政府抵抗英軍失敗,《廣州停戰協定》與《南京條約》相繼簽訂。依照《南京條約》規定,英國人可以偕同家眷在廣州、廈門、福州、上海、寧波五個沿海港口居住,這使得當時的國人獲得機會同外國人有了直接的接觸與了解。與此同時,外國人轉運中國青壯年赴境外做苦力也擁有了最為便利的條件。由于《南京條約》沒有完全滿足英國人的野心,1856年,英國以“亞羅號事件”為借口,又對中國發動了二次鴉片戰爭。就在清王朝國弱民貧的狀況下,西方列強聯合進攻、趁火打劫,并在1858年簽訂又一個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天津條約》規定,外國人可以在中國內地自由生活、往來,中國社會獨立自主的狀況完全被打破。清廷的腐敗衰落已經使得民不聊生,這樣連年的戰火洗禮又讓民眾完全喪失了民族的希望和信心。
漢朝史學家班固在《漢書·元帝紀》中說:“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但有生路,誰又愿意背井離鄉?我們不妨來看這樣一則史料,《華工出國史料匯編 第一輯 中國官文書選輯》所輯錄的“旅居加拿大商民為加拿大苛征華民身稅呈商部等稟文”(光緒三十二年(1906)八月初九日)昭示了加拿大華裔在呈商部稟文時對棄國離家的無奈:“人非至窮,豈肯孑身去遠,拋棄家室,以求糊口于四方。”[5]緣此,盡管走出國門后的未來同樣難以預料,然而,對金山的夢想和對改變生活現狀的期盼對于中國勞工來說,充滿著神秘無比的誘惑力。這里,我們不可回避的是,清朝末年內困外侵、生靈涂炭的社會現狀是華人移民加拿大最為直接的動因。
三、區域間差距:華人移民加拿大的經濟因素
任何時代發生的移民行動大都起源于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距。經濟發展緩慢地區的人們往往是為了能夠分享到經濟繁榮區域的資源,以達到謀求更好生活的目的,因而進行大規模的群體遷徙。但是,能夠達成移民從某地向另一地區遷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條件便是地緣關系上的聯結與交通運輸上的便利。
西方工業革命以后,社會分工的改變重組了國家與國家、區域與區域之間的地緣關系。人們活動和居住的場所不再拘囿于固定的空間范圍,而開始呈現出流動性的特質。與工業發展隨之而來的國家間貿易需求開始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最明顯的是,清朝自康熙中期到乾隆中期已經開放了四個通商口岸。時至1757年,乾隆帝下令頒布廈門、寧波等港口停止對外貿易,在施行這一閉關鎖國的政策時,允許廣州“一口通商”。廣州一地的開放通商,為廣州地區華工大批輸出的可能性提供了地理上的便利。通過加拿大華僑移民史等諸多史料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移民最早的輸出口岸便是廣州。另外,中國與加拿大之間隔著太平洋東西相望,加拿大的維多利亞港(Port of Victoria)是加拿大距離亞洲最近的港口,它的造船業以及船舶維修業非常發達,船舶工業的強大為當時中加之間的海路運輸提供了強大的物質保障。于是,在1858年6月,大批華工乘坐“俄勒岡”游輪抵達加拿大的維多利亞港,開始了華人大量移民加拿大的歷史。交通條件的便利和地緣關系的擴大無疑成為最初華人移民加拿大的必要條件。
四、傳教士──華人移民的文化引力
不可置否的是,早期來華的加拿大傳教士對于加拿大文化的推介和傳播也是早期華人移民加拿大不可忽視的文化引力。鴉片戰爭爆發以后,西方傳教士意在從精神和文化上征服中國而緊隨西方列強大批涌入中國,因而,在英美教會的影響之下,19世紀80年代,加拿大教會開始有組織、有規模地向中國派遣傳教士。“由于加拿大傳教士有組織地來中國傳教時,加拿大還是一個剛取得半獨立地位的國家,在中國沒有類似英美等國那樣的政治、商業等特殊利益,也始終沒有加入列強侵略中國的行列。因此,加拿大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不像英美等國傳教士那樣密切于本國侵華政策相結合,甚至直接為本國的侵略目標服務。”[6]基于這一特殊性,加拿大傳教士以及他們所傳播的文化和宗教更加能夠被中國民眾所接納。尤其是,加拿大傳教士在華期間,除了傳播西方文化和宗教教義之外,還創辦了矚目的教堂、學校和醫院等便民利民的場所。他們不僅將西方比較先進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帶到中國,還為中國部分地區醫療事業的發展貢獻了西方先進的醫療設備和醫療技術。從這個層面來講,加拿大傳教士的到來為19世紀末戰亂又落后的舊中國帶來了新鮮的氣息。
更加具有顛覆意義的是,“加拿大傳教士倡導男女平等,教婦女識字,開辦女校、護士學校,重視婦女醫療,鼓勵婦女擺脫一些封建傳統習俗,如纏足、歧視女嬰等,宣傳計劃生育……教會的活動對當地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7]。這些擁有高學識、高文化素質的加拿大傳教士對西方文化的傳播及以身示范,讓身陷囹圄、又渴望西方民主自由的一代國人對未曾目睹過的西方社會和文化產生深深渴慕與向往的情愫。在他們看來,傳說中的西方世界精妙絕倫,那里的文化和文明值得他們窮其一生,追其一世。于是,當時機降臨時,他們情愿不惜一切代價毅然前往,成為加拿大華人移民史上的華裔先僑。
五、結語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今中外的移民行動皆非單一因素促成的結果,關于這一點,加華移民亦不例外。透過早期的加拿大華人移民史,我們可以洞悉當時的華工華商遠赴加國的移民生態與復雜動因,這些涵蓋了歷史的、社會的、地理的、文化的,以及其他諸多因素的結合體,構成了加拿大華人移民的全部背景。誠如《加拿大華僑移民史》所評騭的那樣:“無論從移民的規模,還是從移民遭遇的經歷來看,中國人在近代走向世界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近代屈辱歷史的縮影,也是一部中國人在化外衣衫襤褸、忍辱負重、和平重建最基本人類生存環境的奮斗史。”[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