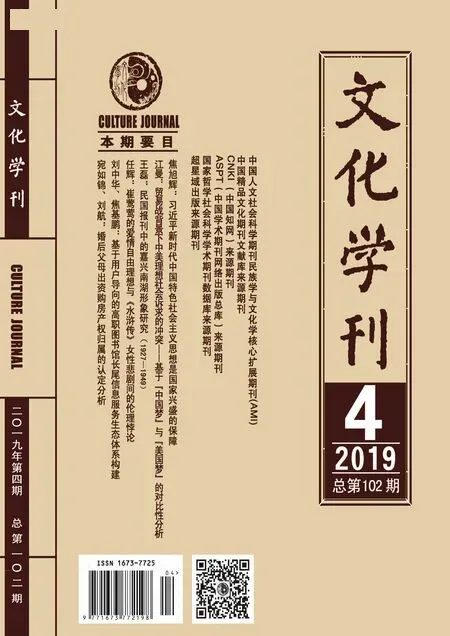春秋時期女性言說空間的構建
吳 樅
周人早在《尚書·牧誓》中總結了殷商“惟婦言是用”[1]的亡國教訓,《國語·周語》和《詩經·大雅·瞻卬》[2]也批評了周幽王依從婦人之言行事。《左傳·桓公十五年》也記載了鄭國的一個故事,鄭伯指示祭仲的女婿雍糾殺祭仲,卻被祭仲的女兒雍姬知道并提前告訴了父親,最終導致雍糾被殺,鄭伯出逃時道:“謀及婦人,宜其死也。”[3]鄭伯認為,失敗的原因就在于和婦人討論。可見周人早已認識到“婦言”的危害。那么,按理說此時的女性言論應該受到限制,甚至剝奪女性的話語權力。然而,查閱這一時期的文獻,卻發現《左傳》《國語》中保留了數量不小的“婦言”。《左傳》中約有五十余則,《國語》中有十余則,其中一些女性言論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甚至直接影響了事件的成敗。比如:文嬴說服晉襄公放走了秦國的三個將軍,保留了秦國的實力,使其能夠繼續與晉國抗衡。總的來看,這一時期的女性仍然擁有一定的言說空間,女性言論數量較多且內容復雜,甚至可以產生巨大的現實影響。那么,在不輕易聽信“婦言”的春秋時期,女性究竟如何建構自己的言說空間呢?
首先,部分貴族女性所擁有的權力和地位為她們創造了天然的言說空間,使她們擁有一定的話語權力。其實,女性是否擁有、擁有多大的話語權力是由其父家、夫家以及子嗣的權勢地位決定的,在性別關系中處于劣勢的女性,完全可以憑借其父親、丈夫或兒子的尊崇地位獲得相應的權勢。《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記載了秦國的懷嬴被秦穆公嫁給了重耳,她質問重耳:“秦、晉匹也,何以卑我?”[4]而重耳也因為秦國的勢力而不敢怠慢于她,甚至脫去了上衣自囚表示謝罪。懷嬴能如此理直氣壯,便是因為背后有強大的秦國做依靠。
正是因為這類女性有較高的權力地位,所以她們任意的言論足以產生巨大的政治破壞力,引發嚴重的后果。聲孟子作為作為先君齊頃公的夫人,現任國君齊靈公的親生母親,這樣的身份使她可以輕易地向自己的兒子誣陷高、鮑和國武子。同樣,驪姬深受晉獻公的寵愛,因此得以利用自己寵姬的身份向晉獻公進譖言,仰仗著國君的權勢陷害太子申生,給晉國造成了巨大的破壞。這部分貴族女性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向掌權者所進的“讒言”,往往引發出政治禍患甚至傾覆國家政權,正如孔子所言:“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5]由此,“婦言”正式走向了“女禍”[6]。
上述由于權勢地位獲得話語權力的女性畢竟是少數,因此更多的女性仍然需要通過特定的話語方式來建構自己的言說空間。從《左傳》的記載來看,春秋時期的女性具有一定的知識文化水平和必要的言說能力,她們熟悉禮儀規范,善于在言論中運用征引,能夠賦詩并作出相對準確的預言,個別女性甚至通曉當時的方術。
一、知禮
“知禮”一直是春秋時期重要的評價標準,而“禮”作為言行的前提和基礎,同時是言行必須遵守的準則,合乎“禮”的行為和辭令更能得到認可和承認。《國語·周語》中,靖公被稱贊就是因為他知禮守典,言行舉止合禮得體。同樣,“有禮”“知禮”也是女性言論能夠得到認同的重要原因,但即便如此,女性所遵循之“禮”與君子也有所不同,主要是符合“婦德”要求的禮儀和行為規范[7]。《左傳·成公二年》記載齊候回國偶遇一女子,女子先問君王安危,而后問父親,得到了齊候的認可,“齊候以為有禮”。齊國女子的言說能使齊候贊同,是因為她能根據“禮”的要求進行言說,其實質是對“知禮”的推崇和看重,而能自覺將“禮”作為言行的前提和基礎的女性也更容易被接納。從《國語·魯語》中公父文伯之母的言論足以看出她對制度禮法方面知識的熟稔,所以孔子對她評價很高,認為“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8]。正因為遵守了“禮”的準則,并得到了賢人的認同,公父文伯之母留下了許多言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另外,女性也通過直接引用“禮”來佐證自己觀點,《左傳·僖公二十一年》記載了成風勸解魯僖公保護自己的母國須句的言論:“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成風用“周禮”來論證保留須句的正義性和合理性。由此可見,女性不僅在言論中自覺將禮作為標準來約束自己的言論,同時充分認識到了“禮”的權威,能夠自覺在言論中以“禮”為論據,增強自己話語的分量。
二、征引
《左傳·昭公八年》載叔向言:“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可以看出,要取信于人就必須有征引,征引是君子言說的主要方式,也是獲得話語權力的重要方式。的確如此,春秋時期的辭令常征引《詩》《書》或歷史典故、民謠諺語等來增強說服力[9]。而正是因為征引成為最為典型的話語方式,女性也開始學習這種方式,通過征引來增強自己話語的權威性。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引民謠諺語
伯宗的妻子為了勸誡丈夫講話不要太直接,引當時的俗諺“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并對其進行了預言式的解釋,用以告誡伯宗如果繼續下去一定會有禍患。根據《國語》的記載,伯宗最終聽從了妻子的建議。可見,伯宗妻子通過引用諺語的方式來佐證自己的觀點,并由此得到了伯宗的認同。
(二)引當事人言
欒祁在陷害懷子的時候,為了取得聽者的信任,在講述中引用了懷子的話:“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姑且不論這段話是否真的出自懷子之口,欒祁借懷子之名將這段話復述出來,有力地證明了自己的觀點,并最終取得了對方的信任。
(三)引先子言
穆嬴為了說服趙盾,復述了故去丈夫晉襄公的話:“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并由此質問趙盾拋棄先君的囑托,最終成功逼迫了趙盾及群臣立自己的兒子為國君。另有公文伯之母兩次以“吾聞之先姑曰”“吾聞之先子曰”引出自己的言說,這種方式與《左傳》以“君子曰”為開始的文本結構很相似,都運用征引來立論。
總的來看,女性通過模仿春秋君子征引的言說方式獲得了價值依據和話語權力。不同的是,春秋君子多引《詩》《書》,而女性則較多地引用諺語或他人言論,這與女性所接受的教育內容和君子不同有關。
三、賦詩
《詩》作為春秋時期通用的雅言,是這一時期的知識中心,也是行人們必備的素養之一。外交場合上,君子們常常通過“引詩賦詩”來委婉地表達意愿,完成溝通交流,因此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10]《詩》已經成為一種話語權力的標識,而“引詩賦詩”則是春秋君子最為典型的話語方式。這一時期的女性也明顯受到了這種言說方式的影響,并已經能夠較好地運用這一言說方式。《左傳》成公九年載:“穆姜出于房,再拜……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魯宣公夫人穆姜在宴會上行禮犒勞使臣,并賦《綠衣》之卒章答謝,完全符合當時的賦詩風尚,通過選章取義委婉地表達了自己的情感。
此外,武姜和許穆夫人通過自己創作的詩歌來表達情感,《左傳·隱公元年》載:“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遂為母子如初。”武姜通過賦自作之詩表達母子和好的喜悅。而許穆夫人因母國被滅卻不能歸,所以創作了《載馳》來抒發自己的情感,并獲得了很高的評價,可見女性也能通過“賦詩”受到推崇。值得注意的是,賦詩的言說方式與征引有所不同。征引往往在表述的內容前后加入一個一般性的道理,內容和道理雖然有著語言和事理上的相關性,但二者仍是相對獨立的部分,而賦詩則是通過詩句直接傳達意義和情感,言說者所要傳達的信息都在詩句里,二者渾然一體,不可分割。
四、預言
春秋時期神秘的巫祝文化十分興盛,這種文化代表著此時人們的認識水平和思維習慣,也直接影響到了人們的言說方式——使用大量預言,因此這一時期預言的言說方式十分盛行且有效,女性也開始借助預言的言說方式來獲得話語權。
(一)神秘預言
神秘預言的文本形態大致相同:前一部分是對神秘因素的描述,后一部分是根據分析而作出的預測,兩部分之間事理上的相關性并不緊密,往往是借由神秘因素來傳達言說者的主觀意愿。換言之,神秘預言的言說方式是運用各種方法將神秘因素和現狀聯系起來,并作出合理的解釋,就能被相信,其核心是對神秘力量的崇拜信奉。
1.占卜預言
此時的社會對占卜之術十分篤信,《周禮·春官·大卜》中設有大卜之職,職責是“觀國家之吉兇,以詔救政”[11]。可見,掌握占卜技藝的人在這一時期的重要性。從《左傳》的記載來看,這一時期的女性已經開始掌握占卜和解讀的技藝,穆姜對“隨卦”卦辭從字義到卦義的解釋表明了她對《周易》的精通。另《左傳·襄公十年》記載定姜解讀卜辭,“征者喪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圖之”。定姜作出了準確的解讀和預測,有效地指導軍隊獲勝。可見,占卜和解讀占卜的能力使女性能夠作出準確的預言,并因此獲得言說的空間。
2.相術預言
春秋時期出現了包括相術在內的許多新的方術,并逐漸成為神秘文化的主流。其中,相術預言是通過對他人相貌聲音等外在表象進行解讀,進而預測其命運和前途。《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記載,叔向的母親在孫子出生的時候憑他的啼哭聲斷言“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因為精通相術,叔向母親擁有了解讀和預測的能力。同時,預言的言說形式更渲染了神秘色彩,增強了話語的權威性,進而賦予了叔向母親絕對的話語權力。
(二)人事預言
不同于神秘預言,人事預言文本形態中的兩部分內容之間必然有著事理上的聯系,通常前一部分是關于人物、形勢、狀況的描述,后一部分是通過分析前一部分內容而作出的預測。其實質是觀察和分析現狀中的一點或幾點事實,找出現狀和未來之間的某些聯系或趨勢,并作出合理的推測,就能被相信。人事預言的話語權源自對現狀的深刻把握和合乎邏輯的有效推論。
1.剖析人物性格
《左傳·成公十四年》記載:“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哀姜看見太子并沒有因為父親去世而悲傷,由此預言太子將要亡國。“不悲”雖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實則是太子性格的縮影,哀姜通過對細節進行觀察分析,準確地把握了太子的性格,而太子即將成為一國之君,他的言行和性格必然左右國家的命運,因此,哀姜推論有其合理性,她所作出的預言也有充足的現實依據。同時,通過“亡國”預言這樣極具沖擊力的表達方式,哀姜牢牢掌握了話語權力,并成功引起了衛國上下的恐慌。
2.透析復雜局勢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記載,僖負羈的妻子勸丈夫禮遇重耳:“吾觀晉工資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僖負羈的妻子通過觀察重耳身邊的人,認為他們都是國之棟梁,卻心甘情愿追隨重耳,由此推測重耳一定能回到晉國。同時,結合當下晉國和各諸侯國的局勢,她認為重耳必定能稱霸諸侯,進而處罰“不禮”的曹國,由此成功說服丈夫禮遇重耳,以避免禍患。可見,僖負羈的妻子對隱藏在紛繁表象之后的因果聯系有清醒的認識。正是這種洞察世事的能力,加之明了清晰的說理、層層遞進的推論和預言的言說方式,共同筑建起了言說的空間。
3.依據倫理道德
《國語·周語》記載了密康公母親的一個預言:“眾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丑乎?小丑備物,終必亡。”密康公母親認為她的兒子明顯沒有足夠的德行卻強行占有粲美之物,因此判斷密國將要滅亡,并得到了應驗。其實,春秋時期“倫理道德”始終是衡量言行的重要標準,一切不符合德行的言行必然遭到報應,這樣的觀念深入人心。“德行”成為話語資源和話語權力的來源,為密康公母親預言提供了價值依據。
總的來看,較之《左傳》中的其他預言,女性預言的話語權力同樣來自于對鬼神力量的篤信和符合邏輯的事理推論,因而獲得了同等的重視和認可,成為春秋時期女性使用較多的言說方式之一。
五、結語
通過對話語權力和話語方式進行解析,我們看到了春秋時期女性言說空間的復雜構成。雖然春秋時期有少數貴族女性以權勢為后盾獲取話語權力,使“婦言”成為“女禍”的代名詞,但更多的女性通過模仿春秋君子的立言模式,并將其改良為更適合女性的方式,逐步構建起了自己的言說空間:在言說中緊守符合“婦德”要求之“禮”,并根據自身的知識文化水平,將春秋君子“征引《書》《詩》”調適為征引俗語諺語及先賢之言。在此基礎上,她們已經開始學習《詩經》《周易》等經典,能夠賦詩并作出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