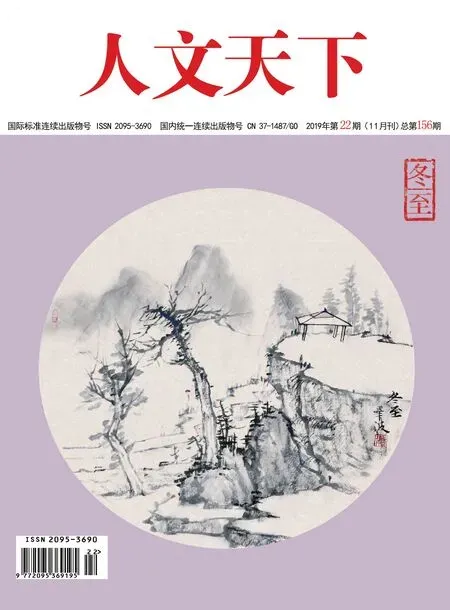試論孔子的禮樂教化思想
楊富榮
孔子首創私學、杏壇設教,不僅是為了培育道德高尚的“人格君子”,而且期望造就一批濟世化民的“士君子”乃至“圣賢”,希望這些為政者能在為政以德的政治實踐中發揮道德表率作用,以影響提升社會民眾的道德素養,解決“人心不古”“禮壞樂崩”的社會現實問題,從而建構一個理想的和諧有序的“小康”乃至“大同”社會。
在一定意義上說,儒家的教育不同于現代社會的知識性教育。雖然儒學中也包含部分知識和技能性的內容,但其重點在于“文之于禮樂”,即“成人”的道德化育,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人文教化”,即“人文化成”之意。儒家的人文教化以社會經濟發展為基礎,堅持所謂“富而后教”的原則。總體而言,孔子的教化理念可以用“富而后教”“人文化成”來做一簡要的描述和概括。
一、孔子教化思想的理論基礎
孔子的教化思想,是其德政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所貫穿的一條主線是以德化人,而且以德化人不是空中樓閣、憑空說教,而是深深地植根于人們當下的物質生產和現實生活之中,依靠人們自我的認知和覺醒,完善自身的精神和道德生活。儒家認為,作為一個社會人,首先應該具備一定的物質生活基礎和保障,而無法維持生活卻空談人倫道德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行為。誠如管仲所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孔子正是充分認識到物質對于民眾生存的重要性,才提出了“富而后教”“人文化成”的教化理念。
(一)富而后教
《論語·子路》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孔子與弟子們到衛國去,冉有駕車,剛入衛國境內,孔子感嘆說:“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問道:“既庶矣,又何加焉(還要做什么呢)?”孔子回答說:“富之(讓他們生活富裕起來)。”冉有又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再次回答說:“教之(教化他們)。”從孔子與冉有的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庶之”“富之”“教之”的為政思想,而“教之”是這三個重要環節中的最后一環。
儒家所提倡的教化,須有一定的物質基礎,應在民“富”的基礎上實施教化,也就是說,人們在生活富裕以后,才會有更高的精神文化追求。于是,后人就把孔子這一教化思想用“富而后教”來描述。孔子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將教育置于經濟的條件下進行認識的人,他的這一思想觀念自然也就成了中國教育史上的經典論述和施教原則。
(二)人文化成
“人文化成”出自《周易·賁卦·彖傳》:“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中的“天文”指的是自然界中日月星辰運轉、寒來暑往相互更替的自然規律,強調的是自然界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和規律性,即所謂的“天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的“人文”指的是體現人之為人的倫理道德及規范人們行為的禮樂典章制度等,強調的是人與動物不同的群體性和社會性,即所謂的“人道”。
“人文化成”中的“人文”是相對于“天文”說的。儒家認為,“天文”與“人文”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聯系、互相關照的“天人合一”。儒家強調,人要尊重天道,依自然法則而行,同時認為人在自然面前不是被動的,人可以發現和掌握自然界的發展規律,可以實現“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的主體性。不僅如此,人還可以用自己所創造的文明成果塑造自身,進而化成天下,實現“我欲仁,仁斯至矣”(《論語·述而》)的精神境界。
歷史證明,在中國數千年文明發展史上,“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的科學精神雖然未有突出的展現,但“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精神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進而形成了中華民族所獨有的“人文化成”的精神品質。“人文化成”作為儒家的核心理念之一,開啟了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與人文傳統。
二、孔子教化思想的內容及特點
何謂教化?《說文解字》把“教”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也”。段玉裁注:“上施故從攵,下效故從孝。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說文解字》將“化”解釋為“化,教行也”。段玉裁注說:“教行于上,則化成于下。”可見,“教”的本義是上施下效,以文為教,使人向善;“化”的本義是默然改變,上有所教,下有所行。
孔子的教化思想,是以禮樂為核心內容的道德(仁義)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識教育。《漢書·藝文志》載:“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意思是說,儒家以六經為教材,但注意力集中在仁義道德方面。儒家認為,禮樂是以人性為前提并因人情而設的,通過禮樂教化可以有效地節制人情,提升人的德性素養。同時,禮樂教化也是政治治理和社會道德培育的重要手段,具有道德教化、規范秩序、化民成俗的作用,可以有效地推進天下大治。
(一)禮樂教化
禮與樂源于上古先民們的宗教祭祀活動。禮是祭祖與祭祀天地神祇活動中的一些儀式規范,樂是與這些活動相配合的樂舞。上古時期,禮與樂是不分的。從現有文獻記載看,最早實施禮樂教化的行為可追溯到中華文明的始祖黃帝,但禮與樂是不斷損益的,上古時期產生的禮樂經過夏、商、周三代的發展和演化,形成了具有不同時代特色的禮樂文化。其中,西周的禮樂文化很是豐盛、蔚為大觀。
殷周之際,禮與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禮樂由上古以來的宗教祭祀活動發展成周初的禮樂文化,開啟了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的先河。周初,周公吸取了殷商失德敗政的歷史教訓,創造性地提出了“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的政治觀念,并以此為指導制定了一系列貫徹“德政”的典章制度,史稱“周公制禮作樂”。周初禮樂之制的最大特點就是將道德滲透到國家的政治中,讓社會各階層結成溫情脈脈的“道德團體”,禮樂從此開始成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手段,明顯發揮出其獨特的教化作用。孔子稱贊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由此,禮樂便由原始宗教性質的精神文化活動,發展成人們日常生活的儀規、行為準則,成為維系社會、國家秩序的典章制度及其相關的思想觀念。
春秋晚期,孔子在繼承西周禮樂制度的同時,納仁入禮,使禮、樂具有了新的內在價值和靈魂;同時,也沿著周代禮樂重德的方向進行了深入探討,并對其做出了新的理解和詮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孔子將人與“仁”聯系起來,突出強調了人的內在本質,即人都有仁愛之心;并把“仁”視為“禮樂”的靈魂和內在的要求,由此,仁(德性)成了禮樂的內在本質,而禮樂則成了仁(德性)的外在表現。所以孔子認為,只有內外兼修即文質彬彬的人,方可成為君子。
儒家所說的禮主要包含禮義與禮儀兩個方面的含義。禮義是禮的內在精神,包含仁義、恭敬、中和等;禮儀是禮的外在行為規范,包含儀表、儀式、儀節等。禮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缺一不可。子曰:“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文”是外在的儀表禮節,“質”是指人內在的質樸本性,兩者兼顧才有君子的風范。同樣,樂也有內容和形式之分,內在之善是樂的本質,外在之美則是樂的形式。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玉帛等禮物、鐘鼓等樂器,只是用來行禮、奏樂的外在器物;玉帛、鐘鼓所體現的內在之善即仁義道德,才是禮樂的本質。
儒家常常將禮、樂并提,認為禮、樂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儒家認為,禮樂是因人情而設的,禮規范人的行為,克制人過分的情感欲望,喚起人的道德意識,即“發乎情,止乎禮”;樂直接作用于人的內心,調節人的情感,使人心平和,情感適度,即“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兩者只有相互發力,才可取得最佳的教化效果。《禮記·樂記》說:“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樂在于協調上下,禮在于區別貴賤。上下協調互相親近,貴賤區別互相尊重。過于強調樂顯得隨便,過分強調禮則覺得疏遠。要使人們內心感情融洽、外表互相尊重,就需要禮樂共同發揮作用。禮義立了,上下才有區別;樂協調了,上下的關系才能和睦。禮、樂只有共同作用,才會使個體身心及社會變得和諧有序。
(二)強調身教
孔子生活的時代,面對“禮壞樂崩”“陪臣執國命”的無道社會,以“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畢生都在探索和追求解民于“倒懸”的為政之道。看到季氏八佾舞于庭這一僭越禮制的行為時,孔子氣憤地說:“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當齊景公問如何治理國家時,孔子給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的答案。對于如此種種人心不古的現象,孔子對當時人倫道德、社會秩序等問題做了認真思考,認為社會之所以出現前所未有的混亂和無序,是因為維系社會正常運轉的禮樂制度遭到了人為破壞,因此,他大力提倡禮樂教化,尤其要求為政者應帶頭做好自我禮樂素養的提升。
孔子非常重視為政者個人的道德修養和表率作用,認為合格的為政者應是人格高尚的人,應是道德楷模,否則就不具備治國理政的人格素養和道德要求。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熟敢不正?”(《論語·顏淵》)即俗話所說的“正人先正己”。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孔子重視為政者的表率作用,認為為政者帶頭做好了,百姓自然就會效仿,即所謂的“上行下效”。
孔子之所以重視身教,主要是由儒家教化思想的自身特點所決定的。儒家教化是一種道德修養教育,不同于一般的知識性教育。它的目的是導人向善、教人為善,這就決定了施教者既要做到以德教人,又要做到以德服人,做到率先垂范,發揮表率作用。施教者只有具備較高的道德修養,才有教化他人的資格,進而取得理想的效果。反之,為政者如果自身無德,不僅對他人沒有說服力,而且也會形成較大的負面影響。
三、孔子教化思想的目標
孔子儒家推崇禮樂教化,目的是希望通過為政者道德素養的不斷提高、人格的不斷完善來帶動廣大民眾“克己復禮”,全面提升整個社會的人文素養,推動社會移風易俗,改變天下無道的混亂局面,實現天下和諧有序,給人們的生產生活提供一個穩定祥和的社會環境。
(一)人格完善
孔子主張禮樂教化,認為人性是可以通過外在人文因素的影響而改變的。子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論語·述而》)孔子將人分為庸人、士人、君子、賢人、圣人五等,其中圣人為最高的人格標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說的圣人一般是指有德有位的圣王明君,自己卻從不以圣人自居。或許圣人的標準太高了,絕大部分人根本無法達到圣人的境界,所以孔子理想的人格是君子。孔子所說的君子,一般是指道德高尚的有德有位者,即士君子;退一步說,即便只是道德高尚的普通人,也被孔子稱為君子,即人格君子,這與后世人們所說的君子人格是一致的。
孔子一生中談論較多的就是君子,在孔子看來,只有具備了內在“仁”的品格,同時合乎“禮”的外在要求,才會成為“君子”。那么普通人如何才能成長為君子?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一個人通過《詩》興發人心向善的情志,經過禮樂的規范、調和、文飾,最終方可成長為一位君子。換言之,禮樂教化是達成君子人格的根本方式和有效途徑。
孔子把人規定為仁,將仁視為人的內在本質規定。子曰:“仁者,人也。”(《禮記·中庸》)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儒家認為,仁與禮樂是一體兩面的關系,仁是禮樂的內在要求和規定,禮樂是仁的外在體現和規范。換句話說,仁是禮樂文化之道,禮樂文化是仁之器;仁是禮樂文化之體,禮樂文化是仁之用。也就是說,禮樂教化是通向理想人格的必經之路,只有“文之以禮樂”,方可為成人。
(二)社會和諧
禮樂對成人及社會治理的作用,孔子有著清晰而深刻的認識。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孝經·廣要道》)《禮記·禮器》載:“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古代先圣明王制禮以節制事宜,制樂以引導人們的心志,通過實施禮樂教化,以取得揖讓而治天下的政治功效。孔子曾指出,如果為政者明白了祭祀天地的禮義,治國就像把東西放在手掌上給人看一樣容易。
禮無所不在,無所不能,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小可指導和規范人們的言行和日常生活秩序,大可經緯萬邦、治平天下。對此,有關文獻的記載十分豐富,比如,《左傳·隱公十一年》載:“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禮記·經解》說:“禮之于正國也,猶衡之于輕重也,繩墨之于曲直也,規矩之于方圓也。”這些都表明,禮不但是一種政治治理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中國古代社會一種主流的意識形態。
《禮記·樂記》載:“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樂是從人心中產生的,禮是自外施于人的。樂自心中出,能使人的內心安靜;禮由外施于人,使人的行為受到約束及外表得到修飾。樂使人內心調和沒有怨氣,禮使人限制欲望避免爭奪。禮讓而治平天下,是禮樂追求的治理效果。
《禮記·樂記》載:“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古人制作禮樂,不是為了讓人滿足口腹耳目的嗜欲,而是為了以禮樂教化百姓,使人們具有是非之心,明白做人的道理。對此,《禮記·禮運》載:“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又載:“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禮義建立起來,顯示了貴賤等級差別;通過樂的情感交流,上下之間就和睦了。好惡的標準明確了,賢人與不肖之徒也就有了區別。用刑罰嚴禁兇暴,以官位選舉賢能,體現政治公平公正。憑仁心以愛民,依道義來管理民眾,這樣民眾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理,社會就會變得和諧。
結語
孔子儒家“富而后教”“人文化成”的教化理念,經孟子、荀子繼承和發展,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先秦儒家教化思想體系,并發展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為政治國的理論基礎和價值引導。迨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儒家的禮樂教化思想開始與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相融合,通過不同時代儒者的詮釋及兩千多年的政治實踐,盡管有時存在過于強調教化對政治影響的現象,表現出不同程度的道德決定論的傾向,但其所蘊含的人文精神、政治理念及其價值取向等合理因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