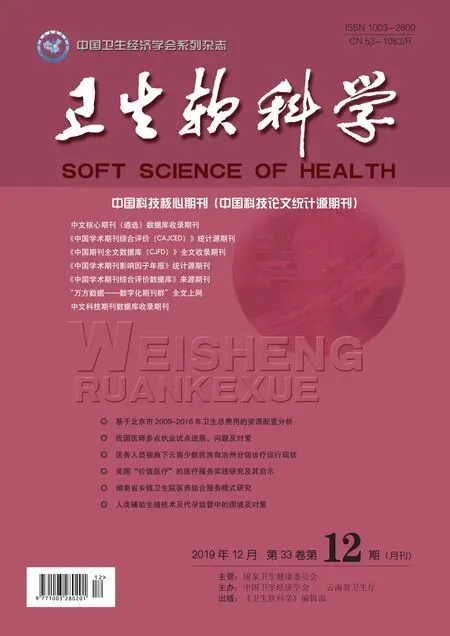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及代孕監管中的困境及對策
魏晨紫,季 力
(1.上海市浦東新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監督所,上海 200135;2.上海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監督所,上海 200031)
輔助生殖技術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因存在的倫理沖突而飽受社會爭議。與傳統的自然生殖相比,其通過改變或者控制生育環節等方式,客觀上導致生育與性愛婚姻一定程度上的分離,并刺激生育權的內涵和外延發生擴張[1],從而為眾多歷經不孕不育疾病的家庭帶來了福音。然而在監管過程中如何充分利用或改善現有的法律手段,以確保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合理運用并竭力控制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帶來的法律及倫理問題,卻成了難題。本文分析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及代孕的立法現狀及監管中的困境,并提出相應的建議。
1 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及代孕監管下的立法現狀
我國對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專門立法最早可追溯到1989年衛生部發布《關于嚴禁用醫療技術鑒定胎兒性別和濫用人工授精技術的緊急通知》。現行適用的法律有2001年衛生部頒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人類精子庫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兩個辦法”)和2003年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人類精子庫基本標準和技術規范》(以下簡稱“兩個規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以下簡稱“倫理原則”)、《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評審、審核和審批管理程序》《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與人類精子庫校驗實施細則》。上述立法也標志著我國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技術的監管進入了標準化管理的階段。
2 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監管中的困境
2.1 行政處罰力度不足
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相關立法總體層級過低,處于部門規章以及技術規范等層面,導致處罰數額受到極大限制。因而,根據現有的“兩個辦法”的規定,對醫療機構的處罰數額上限分別為“3萬”和“1萬”;只有非醫師行醫的個人違法行為,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處罰,處罰上限上升至“10萬”;非醫療機構的違法行為,按照《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的規定,處罰上限也僅為“1萬”。受法律制定時的社會條件所限,衛生行政部門的執法手段在不規則的處罰標準、不合理的處罰力度下顯得尤為單薄。然而,立法層級過低所招致的監管問題層出疊見。
2.2 立法涵蓋內容過窄
立法規定的內容相對簡單,回避了許多爭議較大的社會倫理難題。考慮到“兩個辦法”從實施至今已有近18年的時間,已然無法適應當前復雜而嚴峻的形式。如管制條款未規定精子、卵子、胚胎保存時限以及超期后的處理方式,準入主體資格未考慮移植胚胎婦女年齡等[2]。以胚胎為例,上萬個冷凍胚胎保存超過10年依舊無人問津,以至于各地人類輔助生殖機構陷入大量醫療資源被占用消耗的黑洞。而介于胚胎尷尬的法律地位,醫院即使與患者約定保存期限并規定逾期未交費可銷毀胚胎,醫院直接依照協議銷毀胚胎則仍將面對法律及倫理上的譴責。
2.3 具體處罰事項過少
“兩個辦法”中部分條款僅有違法條款而無對應處罰條款。如《人類精子庫管理辦法》第十八條中規定,“供精者只能在一個人類精子庫中供精”。而事實上就目前為止我國各地精子庫的信息并不聯通,也就說醫療機構無法確保供精者只有在一個人類精子庫中供精。不僅如此,該規定對違規者也未提出相應的懲戒措施,隨之而來的倫理風險就是該供精者的精子將供給不止5名婦女受孕。再加之,我國是采用雙盲原則的國家,如果不能有效防止人工授精帶來的近親繁殖問題,將對整個民族的人口素質產生災難性影響[3]。此外,“兩個辦法”明確要求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需符合“兩個規范”及“倫理原則”的規定,賦予了上述規范和原則的法律強制力,使“兩個辦法”成為衛生行政部門日常監管中行政檢查及處罰的主要依據。但“兩個辦法”在有關處罰規定的兜底條款中,兩個辦法處罰主體僅為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以及設立精子庫的醫療機構,未涉及違規的個人,也未對違規機構設計對應的處罰條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行政監管手段。
3 代孕監管中的困境
代孕,簡而言之,是指婦女出租自己的子宮為他人生育。在印度等其他眾多東南亞國家甚至已淪為“世界子宮”,在代孕產業化的背后,是人類的生殖器官變成了制造和加工嬰兒的機器,嬰兒變成了商品[4]。我國作為不承認代孕合法化的國家之一,法律明確規定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即便如此,代孕在我國也依然是屢打不絕。國內龐大的不孕不育人群催生出巨大的市場需求,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機構內鋪天蓋地小廣告、各類非法代孕網站大行其道。扼制非法輔助生殖技術市場的野蠻擴張,政府監管困難重重。
3.1 行政處罰力度疲軟與高回報的市場特點之間的沖突
受立法層級所限代孕監管中的行政處罰力度弱而違法成本低,使得不法機構在高額的利潤誘惑下不惜鋌而走險。在行政監管上,適用于監管活動的法律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實施代孕活動,根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處罰為警告、3萬元以下罰款;另一類是未經批準擅自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非醫療機構實施代孕活動,根據《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四十四條的規定,處罰為責令其停止執業活動,沒收非法所得和藥品、器械,并可以根據情節處以1萬元以下的罰款。醫療機構開展代孕適用特別法,而非醫療機構則只能適用普通法。由于《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的立法時間較早,使得對非醫療機構罰款數額上要遠遠低于醫療機構的罰款數額,在代孕市場的高利潤誘惑下,使得代孕主要集中在非醫療機構。其帶來的不僅僅是倫理危機,更是嚴重醫療安全質量的風險。這樣的處罰力度顯然難以真正達到打擊代孕,扼制代孕于萌芽之中的效果。
3.2 刑法調整滯后
行刑銜接環節存在明顯的失調[5]。在刑事立法方面,《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人類精子庫管理辦法》第二十四條均提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非法代孕可能會構成犯罪的罪名主要指的就是《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規定非法行醫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行醫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中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①造成就診人輕度殘疾、器官組織損傷導致一般功能障礙的;②造成甲類傳染病傳播、流行或者有傳播、流行危險的;③使用假藥、劣藥或不符合國家規定標準的衛生材料、醫療器械,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④非法行醫被衛生行政部門行政處罰兩次以后,再次非法行醫的;⑤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上述條款未將代孕規定為“情節嚴重”的情形,目前的司法實踐中也未將代孕歸作為兜底條款。具體操作中適用最多的是行政部門對發現的醫療活動開展行政處罰2次以后,再次非法行醫的才啟動行刑銜接的程序。從法益保護的角度來看,非法行醫罪侵害的法益是醫療管理的秩序以及公眾的生命安全。而非法代孕侵害的法益則不止于此,還包括不可估量的倫理風險。
在對非法代孕機構的刑事苛責上還存在另一個難點。2016年12月實施的《關于修改<關于審理非法行醫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決定》中,修改了非法行醫罪中對未取得醫師執業資格的犯罪主體界定范圍,刪除了原《解釋》的第一條第二項,將個人未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開辦醫療機構的的情形予以剔除。自此,只要單位的法定代表人本人不從事行醫行為,而是通過雇傭他人的形式開展診療活動,無法對單位法定代表人擅自開辦醫療機構的行為認定為非法行醫罪,而只能追究其行政責任。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可以將單位從事非法代孕相關活動認定為非法經營罪。而事實上就現有的法律規定而言,上述觀點仍舊依據不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對非法經營罪認定中明確要求,以“違反國家規定”為前提,并在第九十六條中對“國家規定”作出了解釋,“是指違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決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而實施代孕以及買賣配子、合子、卵子等行為的禁止性規定的法律淵源只能追溯到部門規章的層級。
3.3 多頭監管的尷尬
代孕市場長期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以規避法律的問責,查處難度極大,而即使查實也面臨著打擊力度疲軟以及處罰后胚胎的處理等諸多問題,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面對高額的違法利潤不惜鋌而走險。
缺少對應罰則以及多部門聯合下的窘境。在代孕產業中主要涉及到以下步驟,包括最開始的取精、取卵以及保存和買賣配子、合子、胚胎,再到移植胚胎、代孕母親的產科檢查以及最后的分娩。事實上非醫療機構實施買賣配子、合子、卵子等行為不屬于醫療行為。“兩個辦法”雖然將上述行為納入禁止性規定,卻無對應的處罰措施。而這一點在對代孕中介的監管中也暴露無遺。也就是說一旦代孕中介與醫療行為完全脫離,將徹底游走于衛生行政部門的監管盲區。
為謀取自身利益,各類黑中介注冊代孕網站大肆宣揚。據國家公安部網監局舉報中心工作人員稱,他們針對有色情、賭博、反動和違法的網站進行打擊,但對于出現的代孕網站并不能定性,要經過研究之后方能進行處理[6]。“兩個辦法”中雖明確指出禁止代孕,但介于其衛生部門規章的身份而無法成為公安部門的執法依據。此外,在醫療廣告的監管上,根據2015年4月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第六條的規定,衛生行政部門也并沒有被賦予監管醫療廣告的行政職權,醫療廣告監督主管部門為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多部門監督造成管理上的脫節,而一些中介為逃避法律問責直接將網站域名注冊地址設在海外。
3.4 行政立法空白
在日常監管中,衛生行政部門可發現代孕母親,并順藤摸瓜從代孕母親身上查處實施非正規的代孕機構。但事實上為獲取代孕機構提供的高額報酬,代孕母親往往會三緘其口,而衛生行政部門沒有任何行政措施可以處理代孕母親,只能告知其代孕過程中個人身心健康所承擔的風險。另一方面,衛生行政部門對查處中發現的胚胎應該如何處理,也無法可依。在“無錫冷凍胚胎權屬糾紛案”的二審判決中,指出上訴人沈某某、邵某某和被上訴人劉某某、胡某某對涉案胚胎共同享有監管權和處置權[7]。該案件作為中國首例胚胎權屬案,雖然判決中規避了對胚胎所有權屬性的定性問題,但承認了胚胎所享有的監管權和處置權。依據上述判決結果,衛生行政部門調查中發現的涉案胚胎監管權和處置權應屬于構成胚胎的精子和卵子的父母,可以預料的是,這些父母往往會為了能夠擁有一個攜帶自己基因的孩子,依舊劍走偏鋒,繼續尋找其他機構為自己實施代孕,甚至不惜遠赴海外。此外,如果精子、卵子其中之一或是精子卵子均來自第三方提供的胚胎,又該如何處理,由于立法上的空白,使得衛生行政部門在胚胎處理問題上如履薄冰。
4 加強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及代孕監管的對策
4.1 健全和完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及代孕監管的相關法律體系
“兩個辦法”的出現在第一時間解決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活動的資質標準、技術規范以及倫理要求等法律盲點,擺脫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出現后法律缺位的混亂局面。而就現在看來,受當初的社會環境和立法層級所限,“兩個辦法”面臨著多方壓力,處罰力度較小、管轄范圍過窄,規定內容單一、可操作性不強等諸多問題。尤其是對非醫療機構以及非醫務人員較之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的行政監管過于疲軟,在現有的部門規章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下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如何健全和完善立法才是當務之急,上位法先行,細則而后從之。
4.1.1 增加行政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代孕入刑
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監管上急需法律或行政法規層面的上位法出臺。其一,提升罰款額度上限。在立法上調整罰款金額至與現有經濟水平相適應,在代孕的罰款額度設定上應兼顧一般情形下的違法收益。其二,行政管轄范圍的適度擴張。將非醫療機構與非醫務人員納入管轄范圍,包括以代孕為目的,實施采集精子、買賣胚胎、配子、合子、卵子等違法行為,并對機構和人員實行雙罰制。其三,刑法介入濫用輔助生殖技術行為。通過刑事制裁在輔助生殖領域設置某些“禁區”,建議將非法代孕單獨入刑,對于開展代孕人次數較多或違法所得金額較大或有其他情節嚴重者以非法代孕罪論處。這不僅是對濫用輔助生殖技術行為的必要回應,也是彌補當前法律法規對此類行為懲治無力的有效路徑[5]。
4.1.2 出臺實施細則細化條款
第一,規定精子、卵子、胚胎的保存年限。考慮到配子和胚胎的正常活動性,建議設定為10年,超出10年期限的配子和胚胎的歸宿可依據院方和患者事先簽定的協議,未按期續費的可由院方自行決定進行銷毀或是用于研究。為確保醫療資源的合理利用,法律應當明確賦予院方銷毀配子和胚胎的權利,以徹底消除院方在倫理風險上的顧慮。另外,對于行政執法中發現的代孕機構中的胚胎、配子等,應該如何處理也應當以法律形式明確。第二,對違反規定在多個精子庫供精的供精者,應當設立對應罰則,以避免同精多孕可能造成近親婚配的倫理風險。第三,準入主體資格應考慮移植胚胎婦女年齡[2]。目前,我國的法律只要求移植胚胎婦女婚姻狀態是已婚的婦女,并未對年齡上限做出規定。在醫學上35歲的婦女就屬于高齡產婦,因此考慮到高齡產婦的生育風險,建議設立年齡上限。第四,對“兩個規范”“倫理原則”等規范性文件設立違法條款的同時,單獨規定對應的處罰條款,以進一步提高行政監管的規范性及有效性。
4.2 構建多維度多主體參與的監管新模式
在人類輔助生殖的技術監管中,各有側重,對于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以及設立精子庫的醫療機構形成以機構自查、行業自律以及政府監督為合力,發揮多維度監管效能。對于代孕監管形成以多主體聯動、信用監管、風險監管的多方參與、多手段結合的監管新模式。
4.2.1 機構自查自糾,建立應急聯絡機制
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以及設立精子庫的醫療機構應依托機構內部設立的倫理委員會定期開展技術質量、倫理實踐的自查自糾。同時,應增加醫務人員依法執業課程,并落實人類輔助生殖技術、人類精子庫醫務人員依法執業承諾制度。作為代孕廣告最泛濫的區域,醫療機構應開展多環節多手段查驗身份,在環節查驗中從首次建卡開始到每次產檢等,并以手術實施前的身份查驗為重點。在查驗手段中除了傳統的身份核對以外,可增設指紋查驗、人臉識別等,避免“臨時調包”。除此之外,建立應急聯絡機制,對發現的各類有關代孕的信息24小時內聯系衛生行政部門。
4.2.2 建立行業自律的管理模式
不同于一般的行業協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行業監管需要各地方政府部門牽頭,設立生殖健康倫理專家委員會或者專家庫等形式,以為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機構提供技術質量監督以及倫理實踐指引,包括宣傳教育、法律及倫理知識培訓、重大疑難案件決策咨詢以及定期編制指導性案例匯編。目前,上海、廣東等地方衛生行政部門已牽頭成立相關組織,但該組織的側重點仍停留在技術監督層面,對倫理監督功能及指導作用還可深入和細化。
4.2.3 搭建大數據監管平臺
建立供精者信息共享平臺,由各精子庫實時錄入供精者信息,在確保供精者信息保密性的同時,通過平臺監控保證供精者只能成功在一家精子庫供精。對于違法該規定的供精者,醫療機構應及時報告有關部門,同時銷毀其第二次供精的精子。建立技術使用質量監測[8],對于妊娠率、隨訪率等信息能夠實時統計數據并評估,設置預警功能,以確保醫療機構在技術規范上執行到位。此外,充分利用現有的國家企業信息公示系統,把相關企業的處罰信息予以公示,并列入高風險企業開展量化監督。
4.2.4 多部門分工協作,暢通銜接橋梁
國家于2017年9月出臺《關于建立查處違法違規應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長效工作機制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該通知有效整合了衛生計生部門、公安部、工商總局、食品藥品監督總局等十二個部門,建立多部門聯合執法調查、案件會商督辦、案件移送、信息通報共享等機制。但是該“通知”在具體實踐中可操作性尚顯不足。下一步需要各地方政府牽頭,在“通知”的基礎上再出臺更細化的工作機制,明確各部門中涉及的具體監管職責,成立工作小組,建立聯絡員制度,各部門職責應具體落實到各部門的相關負責人,進一步暢通信息溝通渠道以及協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