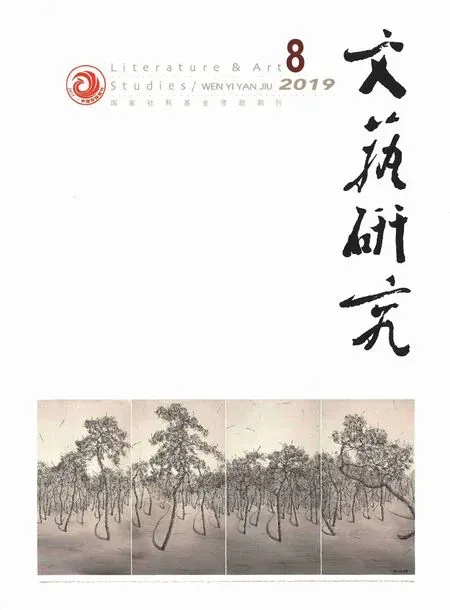俯視與本體論的缺席
汪民安
俯視是一種從高往低的觀看方式。這種觀看方式,無論是對觀看者還是對被觀看者來說都是一種特殊的經驗——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都采取的是平視的視角。平視的視角更加日常,更加普遍,也更加自然。不過,在中國的詩歌、散文、哲學、繪畫中出現過大量的俯視者和俯視視角。存在著各種類型的俯視者和俯視機制,但每一種俯視都展示出獨特的意義。我們在此要討論的,就是一些經典的俯視文本與本體論的關系。讓我們先從詩歌開始,有層出不窮的俯視目光出沒在中國古代的詩篇之中。
一
對于古代人而言,登高是最常見的形成俯視的方法。只有登高才能俯視。登高意味著什么呢?一個最直接的意義就在于,登高俯視是對圍繞在身邊的人的擺脫。也可以說是對世俗生活的擺脫,是對人間生活和市井生活的擺脫。登高者通常是在人煙稀少的地方,在大山上,或者在高臺(樓)上,他獨自一人,將自己置放在天地之間無限的空曠地帶。由于無人環繞在他周圍,他的個體性在天地的蒼茫中會凸顯出來。由于沒有俗務阻擋他的目光,他的視野會更加開闊,他會神游萬里,會拼命地看見那些日常生活中無法看到和想到的對象,會向無限性展開。抽象的主題會更容易纏繞他,未來或歷史(而不是此刻和現在)也會在他頭頂盤旋。因此,對人生命運的總體性思考會在登高的時候自發地涌現。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通常會在寂靜但又無限的大地和天空的懷抱中,感到深深的寂寥、憂愁、無助和孤獨。他的既往追求,他在腳下世俗世界中的浮沉,現在被他從高處俯視,都顯得既真切又渺小。他也因此更加愁苦而孤獨。我們來看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杜甫的名作《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①
這是登高俯視最有代表性的詩篇。詩人在秋天的風中獨自登上了高臺,此刻,猿在哀鳴,鳥在盤旋,樹葉在一片片地落下,而長江之水奔流涌來,無邊無際。只有站在高處,他才能在一個較大范圍內看到大自然的生命,即大自然在時間中的運動和變化——這些運動和變化既是一體的,也是分開的。疾風、飛鳥、鳴猿、落葉和流水,它們各自在運動,但又在詩人的視野中編織成一個整體。在這幅運動式的整體圖像中,沒有一個中心性的焦點,沒有任何一個形象占據著核心統治者的地位。詩人俯視的目光也沒有聚焦,相反,它在漂移,在追逐這些運動的客體,但也同時性地將這些運動要素編織起來,使之成為一個變化的整體,一個直觀的變化整體。也正是他目睹到的這種直觀變化,令他百感交集,令他不由自主地想到時間在自己身上的變化。萬物在流逝和變化,自己不也在流逝和變化嗎?那飄零的落葉和猿的哀鳴,不就是自己的處境嗎?它們在自然中的存在,不就是自己在人生中的存在嗎?人生和自然相互呼應。詩人看到了自然,也融入了自然,自然既是他的客體,也是他的鏡像;既是他的外在物,也內化而進入他自身。正是因這種自然的內在化,他不由得會想到他坎坷的羈旅命運,想到歲月的流逝,想到衰老的吞噬,想到親朋好友的紛紛離去,就像眼前的河水和枯葉無可挽回地離去一樣。一種巨大的孤獨和傷感撲面而來。一個站在高處的孤苦伶仃的詩人的悲苦形象出現了。
有許多登高者都如同杜甫一樣表現出羈旅的孤獨和悲愁。如果說,杜甫是因為登上了高處俯視周遭才自發地產生這種感受的話,那么,還有人登高就是為了排遣這種孤獨和悲愁。登高通常是為了驅散悲愁,但也常常會加劇悲愁。在對家人和故鄉思念之情的驅使下,他們登上高處,奮力向遠方眺望,似乎只有這樣才能越過層層障礙看見遠方的故鄉和親友。到底是因為對故鄉的懷念而去登高遠眺,還是因為登高而情不自禁地向故鄉眺望?無論如何,登高是和故鄉、遠方,和有一個遙遠的空間距離的地方及人物聯系在一起的。登高不是像杜甫那樣環顧周遭,而是讓目光投向一個遙遠之地,讓目光越過無數的高山大河,讓目光之線盡可能延伸,仿佛自己的身心通過這目光之線能抵達一個遙遠的場所。目光最終消失在無限之地,一個不可能性的空間。盡管知道這實際上不可能,但柳永在《八聲甘州》中還是寫道:“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②身體站在此刻的高處,但心靈已經隨著目光的遠眺而脫離了此地,脫離了身體,被遙遠的故鄉牢牢地攫住了。一個不可見的場所(和人物),卻強烈地吸引了目光、主導了目光。目光聚焦于一個虛空。它甚至讓身體和心靈分離。這個不可見的場所(和人物)如此地具有魔力,以至于人們欲罷不能。目光的真實視野實際上看不了多遠,哪怕是黑夜,但還是要看,哪怕是“望盡天涯路”:要一動不動地專注地看,要看到無限的遙遠之所,要長久地看。晏殊的《蝶戀花》是如此令人動容:“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彩箋兼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③我不知道對方在哪個遙遠的地方,但我的目光要去拼命地搜尋她。目光在此與其說是觀看,不如說是思戀。
站在高處,既會因為對日常塵世的擺脫而感嘆孤獨個體的永恒命運,也會因為視野的開闊而情不自禁地展開對故鄉和戀人充滿煎熬的思念。同樣,站在高處的開闊視野,也會看到大地、民族和歷史的縱深,從而表達對國運的擔憂。高處俯視,將個體和家國聯系在一起。高處的個體俯瞰腳下這片大地,他既從屬于這片無限的大地,是它微末的一分子,但同時他也是這片大地的主人,應該操心這片大地,掌握這片大地的命運。他將自己的命運和大地的命運,以及這片大地上的人民的命運結合在一起。高處的目光,略過了具體而瑣碎的塵世,但在更抽象的層面回歸于塵世:大地和民族的命運。他遼闊而深遠的目光看到的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大地,以及這個大地上不可見的歷史和未來。這是注滿了歷史命運的大地。俯視目光的對象同時是可見的和不可見的,這目光逡巡在大地上,逡巡在大地的過去和未來上。正是這大地的歷史,這可見的大地和它不可見的歷史,激發了他的神圣情感。這情感不同于個體在天地間感受到的孤獨,也不同于他遙遠的思戀目光所表達的愁苦,這情感更多是來自于大地歷史所激發的慷慨。這樣的登高俯視者有時候有英雄的激情抒發,豪邁而悲壯;有時候卻有失敗者無解的抑郁,沉痛而悲愴。這都是在高處俯視國運的時候才會產生的激情。他們因為對國事的操心而舍棄了自己,這種激情就有強烈的崇高感,而俯視者因此顯得卓爾不群——世俗的平視目光無論如何也難以理解他們。正如孤獨的感傷者喜歡站在高處排憂抒懷一樣,這些對家國命運保有拳拳之心的偉大英雄也喜歡站在高處揮斥方遒。站在高處可以做出重大的決斷,可以流露崇高意志,可以抒發自己的抱負和野心。站在高處可以吸收高山的雄渾力量。這就是我們在岳飛的《滿江紅》中看到的:
怒發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④
站在高處,強大的意志噴薄而出,高傲而孤獨的英雄形象只能在高山上被刻畫出來,他的歷史和全部存在就是和國家山河大地結合在一起的,他奉獻于此,這情感的澎湃就如同山河大地一樣廣袤洶涌。它如此無私,正義,勇敢。此刻,還有什么不可以征服的呢?還有什么不可以藐視的呢?就如同昔日年輕的杜甫在泰山頂上迸發的豪情,“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⑤。
不過,也有相反的情況。站在高處,同樣是憂心國家,但一股失望和擔憂的情緒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來。如果說,岳飛站到高處是充滿信心地對未來進行遠矚的話,那么,王安石站在高處看到的則是過去的歷史,他的目光是回顧性的,他往歷史的深處眺望,歷史的不祥吊詭在這種回顧性中涌現,以至于他為此刻的國家命運而黯然神傷。登上高處,金陵的壯觀一覽無余,瞬間就獲得了一個開闊的全景。但是,詩人沒有被眼前的景觀所吞噬,相反,這景觀令他發思古之幽情,他在俯視它們的同時,也很快地擺脫了它們——他穿透了此刻的場景,將目光探向歷史的帷幕之后。景觀千百年來沒有變化,但是,歷史似流水而逝: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歌,《后庭》遺曲。⑥
也就是說,高處的目光,既可能像岳飛那樣充滿信心地指向未來,也可能像王安石這樣憂心忡忡地指向歷史。高處不僅讓俯視的目光超越了眼前的時空,而且讓這種目光深謀遠慮。無論如何,高處的俯視目光的焦點并不被現在所控制。只有高處的俯視才能擺脫現在的視角,才能超越現在,抵達未來或過去,就像高處的俯視和眺望能夠抵達不在眼前的遙遠故鄉一樣。
但是,還有一種俯視最為闊達和恢弘。俯視者不是將目光放到自身的命運上面,不是探討高處的孤獨和愁苦,甚至也不是將個體和國運相結合,他們甚至超越了大地和家國的層面。在此,高處所特有的全景視角,使他甚至可以觀察和思考無限。就此,他們將一切塵俗的東西都拋在腦后,旨在對宇宙時空和人生大限進行沉思。俯視者由此變成一個對純粹的無限性進行沉思的哲人。如果擺脫了自己,擺脫了歷史,擺脫了故鄉和國家,他們在高處的俯視沉思會得出什么結論呢?在無限的時空面前,個人是多么渺小啊:“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⑦站在高處,看到的只有宇宙和時空的永恒,其他的一切都消失殆盡。個人面對無限的宇宙,所有的抱負都顯得空洞而微末。某種虛無主義不禁纏繞了他,以至于志向高遠的詩人凄然淚下。但何止是他呢?即便那些歷史上不朽的英雄,那些曾經叱咤風云的歷史巨人,在浩瀚的時間面前也不過是過眼云煙。只要我們站在堤岸高處,俯看河水的奔突,就會得出這樣的印象:“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⑧“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⑨流水總是時間的具體形象。尤其是,當它被俯視的時候,似水年華的傷感就會情不自禁地向俯視者涌來。杜甫正是從高處發現了“不盡長江滾滾來”,時間如同流水一樣不可遏止地、不可阻斷地奔涌向前。同樣,孔子也只是站在河水的上方才發出了他著名的感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⑩
站在高處,不僅能夠垂直地接近遼闊而高遠的天空,而且能夠水平地追逐綿延無盡的時間。不僅能夠看到可見的大地,還能看見不可見的歷史;不僅能夠在白天看,而且能夠在黑夜看;不僅能夠看到眼前的具體物景,還能看見遙遠的不可知的人事;不僅能看到實體,還能看到虛空;不僅能看到有限,還能看到無限——高處觀看的客體,囊括了一切,沒有一個確定的對象制約著目光。俯視,在這個意義上,沒有焦點,沒有本體,沒有確定性。它不停地在有限性和無限性、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現在和過去、現實和虛擬之間搖晃。觀看,并不追逐和受制于一個確定的本體。
二
對于另外一些哲人來說,站在高處,不是哀嘆個人或國家的命運,也不是在無限時空面前感嘆個人的渺小。站在高處,則有一種巨大的解脫之感。一旦同底下的塵世保持距離,擺脫了塵世的種種糾纏,高處就是自由的廣袤場所。此刻,他不是被宇宙的無限性所震撼,而恰恰能在宇宙無限之中任意地飄游。這就是莊子的理想:他精心地描繪了一只展翅翱翔的大鳥,名之為“鵬”,來展開他的俯視目光。大鵬雖然巨大無比,但是,在那無限廣闊的天空中,它還是能無所顧忌地暢游。“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氣勢磅礴但毫不滯重,于是,一個無限逍遙和自由的形象出現了。自由,就是要大幅度地肆意飛翔,就是要無所羈絆地運動。“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它宏闊、飛翔、瀟灑而飄逸,它在一個無限的宇宙中無所依據地揮灑展開。還有什么形象比這更加舒展奔放?所有的束縛都在飛躍中松綁了。
在同俗世脫離進而進入無所待的自由狀態的同時,高處還表達了同下方塵世的對照。如果以遨游的大鵬的視角來看的話,下面的人們是多么微不足道。他們不能不受到來自上面目光的嘲笑。世間的人們勞碌奔波,爭來搶去,吵吵嚷嚷,又有何意義呢?如果從高處往下看的話,或者從天的視角來看(“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他們都同樣渺小,同樣模糊,同樣微不足道,因此,所有的事物,所有的決斷,所有的觀點,所有的行動,所有的價值,都沒有差別。它們地位平等。也可以說,人和物的界線——莊子甚至更為夸張地說——人和蝴蝶的界線甚至也模糊難辨。這就是莊子最著名的發現。得出這所謂的“齊物論”,只能是采用恢弘而博大的俯視視角。正是在這里,逍遙游和齊物論建立了聯系?。齊物論正是通過逍遙游來發現的,沒有無限廣闊的逍遙游,沒有一個闊大的視角空間,又如何能夠發現萬物平等?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我們置身于各種觀點之間,置身于各種人事之間,如果我們被它們所簇擁、所包裹、所擠壓的話,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陷入其中而采用平視的目光去看待它們的話,我們的目光就會被截斷,會受到阻止,我們一定會看到差異、距離和溝壑,會看到各種充滿條理的細節和組織。也就是說,我們難以獲得一種整全性的、抹去一切差異的目光——而俯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可以超脫地看到全部。俯視的距離越高遠,看到的下面的對象就越模糊,就越沒有差異。就像從高空中的飛機往下所看到的那樣:地面的世界混沌一片,一個無差異的世界就此浮現。齊物論一定是俯視目光所產生的哲學。這就是它開篇通過在高空中展翅的大鵬所表明的。就此,莊子這樣的觀點只能是在俯視的目光下得出來的:“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我們可以想象,這是一個站在世間之外的人,一個站在無限高處的人,一個脫離了塵世的人,憑借他充分的超越性的俯視視角而得出的結論。在此,逍遙游既是莊子的哲學精神,也是他的哲學視角。這是一個哲學俯視構成的論述,但是,我們還是要說,這也是一幅視覺構圖,它直觀的畫面效果就是:“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再一次,在這種齊物論的景觀中,沒有一個類似歐洲哲學中的絕對的霸權式的本體。本體論的基本特征就是差異和等級:有一個最內核的本體,它占據了一個基礎性的最高級的支配地位?。我們看到,本體在這里,既是中心支配性的,也是和現象保持區隔和差異的。支配和差異是本體論的兩個內在的關聯性的有機要素,它們缺一不可。抽掉了其中任何一個,就抽掉了本體論本身。在莊子這里,萬物齊一,物我齊一,沒有等級,沒有中心,沒有優先性。這是對差異的消除和抽空。這是通過消除差異而消除了本體論。這樣一個本體論的抽空和缺席經驗,同歐洲晚近的反本體論傳統存在根本的差異。對于德里達這樣的解構主義者來說,反本體論不是以消除差異的方式來進行的,而是以消除支配的方式來進行的。德里達肯定萬物的差異,但是萬物之間的差異關系是游戲和平等的關系,而不是支配和決定的關系。德里達的“延異”試圖讓差異之物保持著持續的自主性,差異不是導向支配、中心和優先性,而是導向溢出、流動和不可掌控。也就是說,德里達通過對支配和中心的消除而不是對差異的消除來廢棄本體論。對莊子來說,如果萬物同一和平等就抽空了本體論;對德里達來說,恰好相反,如果萬物保持絕對的差異就抽空了本體的優先性和決定性。
按照尼采的視角主義的觀點,這兩種非本體論的不同傾向也許就意味著他們采用的視角不同。對于莊子的高空俯視視角而言,當然就是萬物同一。德里達更接近一種平視的視角:不同的能指在一個橫軸上無始無終地流淌,橫軸的流淌過程也是差異的時間化過程。正是這種平面性的差異,垂直向上的超驗和向下的深度都被拔掉了,焦點性的中心也在水平的時間化過程中被瓦解了。但是,對莊子來說,俯視的視角不僅導致了萬物同一。與自由自在的大鵬相對的,還有塵世的蠅營狗茍,追名逐利,計算比劃。所有這些是多么渺小和瑣碎,有限和狹隘。在此,從高處俯視低處,就是以大看小,以自由觀束縛。在此,越是高的,就越是大的,就越是廣闊的,也就越是逍遙和自由的;反過來,越是低的,就越是小的,就越是狹窄的,也就越是受限制和受束縛的;在這個展翅高飛、無拘無束的大鳥下面,是地上的各種小雀,是人間的各種狹小和自大。莊子正是根據這種俯視進行了一系列的垂直對照:“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大知閑閑,小知間間”?。
這不僅是俯視,還是一種移動的俯視。因為高空俯視,它得出了萬物齊一的結論,而因為移動,它獲得了無限的自由。也許可以說,正是因為萬物齊一,沒有等級作為強制性的制約,沒有目的論的期待,才可以自由地游動——沒有游動就沒有自由。在這里,正是這種逍遙的移動(游),無目的、大幅度的移動,使得俯視的視野無限寬廣,它不停地變換自己的視角位置,它可以將一切納入自己的俯瞰目光中,世間的一切都被這種目光所收納,一切都在這里無差別地被對待和觀看,這不僅僅是齊一,而且是世間萬物齊一,是無限空間中的齊一。俯視的目光就此不再是具體的對象,而是囊括一切的萬事萬物,是海德格爾意義上的“世界”。當然,它也不是像基督教中的上帝那樣俯視塵世。后者雖然有無限的俯視和洞察塵世的目光,但是,他本身并不移動,他是一個絕對的中心,他不動的目光是統攝萬物的焦點,最重要的是,他有明顯的善惡價值判斷,他是一個充滿責任的救贖者。而莊子的展翅大鵬是一個自由的無拘無束的靈魂,它不做判斷,洞悉一切,但只有嘲弄。這移動的整全性目光,同我們所提到的其他俯視者都不一樣,它不是一個安靜的被固定在某個位置的沉默觀眾。也許正是因這種身體和靈魂的自由、對各種塵世束縛的擺脫,它在自由飛翔的同時,也向下面的萬事萬物報以輕蔑的一瞥。
三
但是,還有與輕蔑的俯視相反的充滿眷戀的俯視。我們在此可以談論繪畫中的俯視。中國歷史上的兩幅杰作《清明上河圖》和《富春山居圖》都采取了俯視的視角。這兩幅畫都是全景式的繪制,它們都試圖將一個總體性的場景納入到繪畫中來,因此都以橫長卷軸的方式展開。《清明上河圖》是對宋朝發達的都市汴京(今開封)進行總體繪制。它力圖再現一個城市的逼真場景。這是中國畫中非主流的寫實風格。顯而易見,如果采用平視或者仰視的話,汴京的總體圖景將無法再現,會有各種建筑和物件相互遮擋,只有俯視可以避免這樣的麻煩。一旦進行俯視,任何高大的建筑物都可以暴露在人的目光之下,城市中的任何場景和細節都可以在俯視的目光下緩緩打開。這樣,慢慢展開畫卷的過程,就如同一只低空飛行的鳥在城市上空緩緩地飛翔而俯視下面的過程。因此,同莊子的大鵬一樣,這不僅是俯視,還是移動的俯視,飛翔的俯視。但這樣的空中移動俯視,并不像莊子筆下的大鵬那樣,是以自由的精神對塵世投以藐視,相反,這樣的俯視就是為了更好地觀察塵世,是為了對世間進行逼真而完整的再現。俯視在此變成了一種觀察和記錄的技術,而絕無任何嘲笑世俗、脫離世俗的精神,也絕非個人的各種抒情喟嘆。城市,在俯視目光的逡巡下如其所是地展示。正是因這來自上面的目光旅行,城市的全景才一一呈現。俯視在此是一種嚴謹的探秘目光,它力求飽覽一切。由此促成了這張繪畫作品的不朽,一個繁華城市的充滿細節的一天,被一個俯視者無比耐心地記錄下來。在這個意義上,它不僅僅是藝術杰作,同時也是歷史巨著。
顯然,這個城市不是一覽無余地、猛然間地全盤呈現(畫卷有五米多長,不可能一下子被囊括到視野范圍內),人們不可能一下子把握繪畫的總體性進而迅速地獲得一個構圖印象。這里,目光在移動,而且是連續地移動,長時間地移動,在一個橫軸上均勻地移動,向一個未知的地帶移動。目光移動就是對畫面、對城市的未知部分的打開。看畫的過程如同視覺的歷險,是一個不停撞見意外的過程,是一個不停探索的過程。城市就以復雜、曲折、綿延和幽深的方式在慢慢地敞開。正是這樣一個對未知的探索過程,使得畫面并沒有一個絕對的高潮、焦點和明確預知的結局(我們甚至不確定我們的目光何時會終止。人們難以確定現存的這張繪畫是否是當初的完整繪畫,是否被裁剪過)。繪畫沒有重心——沒有一個統一一切的絕對本體,畫面中的每一個場景、每一個片段都可以獲得自己的自主性,人們可以切斷一部分,作為一張獨立的畫。它們可以獨立地發生,而不受另外場景的影響;事實上,畫面中的人物都沉浸在自己和自己四周的世界之中,和遠處的人們、遠處的場景毫無瓜葛,對他們來說,畫面上的遠方場景絲毫不存在。但同時,每個場景,每個人物,即便自我沉浸,卻也都是連接前后部分的過渡地帶。一個場景和另一個場景有無法切斷的空間聯系。因此,每個場景同時是畫面的中心和邊緣:它自己的中心,它作為前后相續部分畫面的邊緣。沒有哪個場景、哪個物件、哪個人物,凌駕于其他場景、物件和人物之上;沒有一個場面能夠掌控和支配另一個場面——繪畫沒有絕對的主角,沒有唯一的聚焦點,我們要說,沒有絕對的本體。繪畫是無中心的繪畫,城市是無中心的城市,空間是無中心的空間。它是一個均勻而緩慢流動的地帶,甚至連時間都缺乏明顯的確定性?。在這個意義上,畫面的每一個部分都類似于莊子式的萬物齊一,它們沒有意義的高下之別;同時,城市是一個無景深的城市,它并不讓自己在一個縱向深度上聚焦和消失,它不以深度的方式凝聚起來,相反,它只是在橫軸上無盡頭地打開。在這個意義上,它又像德里達的“延異”一樣,在時間和空間上不停地延擱,它不讓任何一個焦點形成,或者說,它在焦點即將形成的時候,馬上脫離這個焦點,城市以能指滑動的形式平面地延展,向外部延展,用福柯的說法,這是一個“界外”繪畫。繪畫在此獲得了自己的時間性和運動感——繪畫獲得了自己的時間寬度,它不是被中心、被焦點所統攝、所聚焦、所收納的圖像——我們要說,這是一張本體缺席的繪畫。
在這個意義上,它和《富春山居圖》有相似之處。《富春山居圖》同樣也是一張長卷軸的山水畫,它同樣需要慢慢地展開。只不過,它展開的不是一個人工性的繁華城市,而是一個遼闊深遠的自然景觀。如果說,汴京這樣的城市需要客觀地描繪的話(人們甚至試圖還原這到底是當年汴京的哪個地帶,畫中的人物和場景到底符合怎樣的歷史事實,人們將它既作為藝術品,也作為歷史考據的材料),那么,富春江一帶的自然景觀并不使人追求一種恰當而真實的再現,它幾乎喪失了歷史考據的功能。這些景觀并不充實飽滿,它甚至有大量的缺失和空白。正是俯視的視角既讓它保有模糊而曖昧的輪廓,也讓它無比開闊,讓它在一個有限的尺幅內來展示無限的空間。這是真正的“咫尺千里”。它如此寬闊,如此層巒疊嶂,如此路轉峰回,如此疏密相間,如此濃淡交替,如此千丘萬壑,如此神采煥然,如此大氣磅礴而又如此纖細靜謐,以至人們的目光應接不暇。顯然,這樣遼闊而豐富的空間同《清明上河圖》一樣,并沒有一個統攝性的焦點。畫面有一個連接的整體,但是沒有一個絕對的核心和高潮。山陵、沃土、云煙、茅庭、村舍、漁舟、林木、水波、飛禽以及潛隱其中的漁樵耕讀,編織了一個和諧、散布和流動的畫面,但這個畫面沒有一個收斂和匯聚的絕對之核。人們的目光無法滯留在畫面的某一個焦點上。
缺乏單一的聚焦點,這是中國繪畫的重要特征之一。對15—19世紀的西方透視法繪畫而言,畫面設想了一個占據固定位置的觀眾,這個觀眾的目光總是指向畫面的某個確定的焦點。繪畫因此在透視的目光下安靜而確切地敞開它的景深。這個不動的觀眾在盯著一張不動的繪畫,畫面被單一的目光焦點所統攝。實際上,這個焦點正是絕對的中心,畫面圍繞著它有規律有計劃地展開,我們可以說,這個焦點正是繪畫的本體之所在,它是畫面的根基,它是哲學本體論的繪畫表達。在一種粗略的意義上說,這正是中國繪畫所缺乏的。就此,缺乏唯一焦點的中國繪畫體現了一種與西方完全不同的缺乏本體論的哲學。我們已經看到了《清明上河圖》中街道上的橫向游走不斷地對中心點的穿越:目光正是沿著河流和街道的橫面而展開,是沿著街道上在發生的場景而依次展開。但這是一個現實場景,是對在場的實錄,似乎有一個現實支點在主宰著它。人們通過觀看這幅畫來觀看生動的場面,觀看具體的街景,觀看一個城市的現實,從而觸摸具體的歷史。但是,《富春山居圖》則遠不是現實的實錄,它是非歷史化的,它并不致力于一個確切的歷史時刻,這山水風景既是瞬間的,也是永恒的。
雖然都缺乏同一個焦點,《富春山居圖》依然和《清明上河圖》有很大的區別,它的畫面內部不是像《清明上河圖》那樣依據逼真的現實連接在一起,尤其不是依據活生生的事件場景組織在一起。它們甚至很難看作是一種地點和風景的自然延續。那么,這樣宏闊的畫面中到底存在著什么,讓人們的目光不停地移動?它如何在省略、空白、中斷和各種異質性中編織一個動態和分布的總體性?也就是說,這些風景如果不是客觀寫實的話,它們是如何連貫地組織起來的?事實上,這幅畫包含了中國山水畫中的諸多奧妙。朱利安的研究非常有啟發性:畫面中的這些異質性和多樣性并不歸結到一個凝固的一般本質的名義之下。如果是那樣的話,風景畫就不會有流動的活力。相反,風景本身具有內在的能量,正是這能量貫穿了畫面整體:“風景作為氣息—能量之具體化,在它的種種靈性形式里具象化,任由它的力線貫透,就像宇宙節奏透過世界動脈同樣將我們貫透……風景諸形式誕生于氣息—能量(‘氣’),它們因自身的變化(正是那些變化使得形式多樣化并造成它們的豐盛性)而自身攜帶著作為‘意義’—‘意向性’的‘意’,貫穿其中的特殊張力將它們舒展為多樣化的傾向(與‘形’有關聯的‘式’),從而仿佛吐露出某種希望存在于世—活在世上的意態。”?正是這內在的能量使得各種異質性相互貫通、轉化,畫面仿佛有各種各樣的出口和入口,仿佛有各種各樣的視角,每一個出入口,每一個視角,每一個側面,都涌入強烈的生命氣息。這樣充滿流動活力的風景畫,就構成一個類似于德勒茲意義上的“無器官的身體”。力的波浪在這繪畫的身體里面無阻礙地流動,以至于沖毀了任何既定的器官構造。流動之力(對朱利安來說是氣)讓畫面成為一個異質性的關聯總體。正是由于氣的生機勃勃的流動,任何統攝性的本體都坍塌了,但是,它并沒有瓦解成凌亂的碎片。《富春山居圖》越是開闊,它的氣場就越是碩大,它的流動路徑就越是繁復,它的能量就越是充沛,它的異質性和多樣性就越是豐饒,它的世界和宇宙因此就越是氣象萬千。它不僅僅是目光所觀看的外在對象,它無限的能量仿佛有一種巨大的吸附力,邀請人們棲居其中,這是應當居住在其內的繪畫。
最后,讓我們回到張擇端和黃公望的俯視的目光吧。對張擇端而言,《清明上河圖》俯視的目光同時是藝術的和史學的:逼真而完美的藝術,客觀和公允的史學。這是藝術和史學的雙重目光的偉大匯聚。而黃公望的目光,飽含著眷戀和贊嘆:對人生的眷戀,對宇宙的贊嘆。如果說莊子的俯視是對地面和塵世的蔑視和傲慢的話,那么,黃公望的俯視則是對美和大自然情不自禁的一遍遍的撫摸。
① 杜甫:《登高》,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二〇,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766頁。
② 薛瑞生:《樂章集校注》,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194頁。
③ 張草紉:《二晏詞箋注·珠玉詞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頁。
④ 唐圭璋編《全宋詞》第2冊,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46頁。
⑤ 杜甫:《望岳》,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一,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4頁。
⑥ 王安石:《桂枝香》,《王文公文集》卷八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64頁。
⑦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陳子昂集》,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32頁。
⑧ 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注》,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98頁。
⑨ 楊慎:《臨江仙》,王文才、萬光治主編《楊升庵叢書》第四冊《歷代史略詞話》卷上,天地出版社2002年版,第588頁。
⑩ 《論語·子罕》,程樹德:《論語集釋》卷一八,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610頁。
??? 《逍遙游》,王先謙、劉武《莊子集解·莊子集解內篇補正》卷一,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頁,第4頁,第2頁。
???? 《齊物論》,《莊子集解·莊子集解內篇補正》卷二,第14頁,第14頁,第19頁,第11頁。
? 有關“逍遙游”和“齊物論”的關系有過許多討論,不少人認為“逍遙游”和“齊物論”是矛盾的,因為“逍遙游”講大小之辨,強調的是區別,而“齊物論”講萬物齊一,恰好是抹去了區別。持這種觀點的人包括郭象。
? 尼采在《偶像的黃昏》中,將這個本體稱為“真正的世界”。尼采將這個真正的世界和柏拉圖的“理念”結合起來。這個真正的世界,理念構成的本體,與一個假象世界構成的現象形成了對比和區隔。在這個區分中,真實世界(本體)對于假象世界的優先性成為海德格爾所說的柏拉圖主義的首要原則。對尼采來說,這個“真正的世界”在歐洲經歷了幾個階段。先是在現世的層面上區分了這兩個世界:一個是有德者占據的世界,一個是無德者占據的世界(柏拉圖);接下來是一個未來的、許諾的彼岸精神世界和一個現世的、此岸的物質世界(基督教);一個不可認知、不可經驗的世界和一個可經驗、可認知的世界(康德);而尼采自己的工作就是要廢除柏拉圖、基督教和康德的“真實世界”,即歐洲的形而上學的本體論。
? 圍繞這幅畫中所表達的時間,人們也展開了各種各樣的爭議。有人認為這幅畫的季節是春天(即清明節這一天),也有人認為是秋天,甚至有人認為是夏天。當然,還有人發現這幅畫在不同的場景表現的是不同的季節。也就是說,畫中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時間點。對此的一個解釋是,畫家張擇端畫這幅畫的過程經歷了很長時間,他在不同季節畫的時候,就畫那個季節的場景,這導致了畫中時間的錯位。繪畫在這個意義上也是一個時間化的過程,一個沒有時間焦點的過程。
? 朱利安:《大象無形:或論繪畫之非客體》,張穎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04—3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