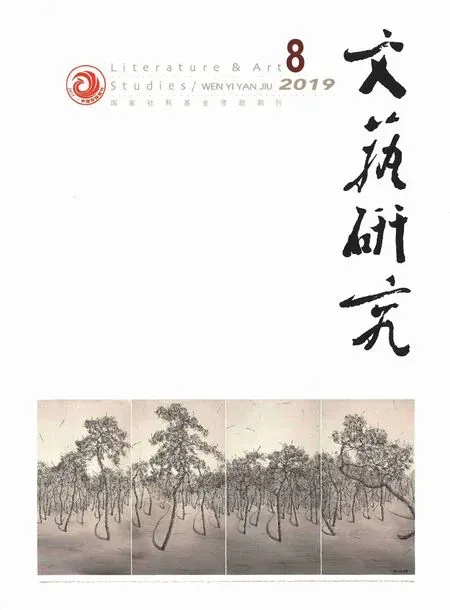《楞嚴經》與竟陵派文學思想的指歸
李 瑄
佛教在晚明士林甚為流行。《四庫全書總目》云:“蓋明季士大夫流于禪者十之九也。”(《大云集》提要)①又云:“是編……多浸淫于二氏。蓋萬歷以后,士大夫操此論者十之九也。”(《澹思子》提要)②萬歷時“士大夫不與詩僧游,則其為士大夫不雅”(鐘惺《善權和尚詩序》)③。此種時代精神必然滲入文學思潮,但迄今為止的晚明文學研究對佛教重視不夠,對佛學影響文學路徑的梳理尤其不足。
竟陵派在性靈文學思潮中地位特殊,其興起不久就遭文壇顯要如錢謙益、王士禛的唾斥,被貼上“幽深孤峭”④的標簽,向來頗受輕視。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竟陵派是晚明性靈文學思潮中影響范圍最大、時間最長的流派。明末盛傳“鐘、譚一出,海內始知性靈二字”⑤。錢鐘書亦曰,“明清之交詩家”,大抵是“竟陵派與七子體兩大爭雄”⑥。
竟陵派代表人物浸習佛教很深。鐘惺二十余歲“諷貝典,修禪悅”⑦,臨終前立誓“生生世世愿作比丘、優婆塞”(《病中口授五弟快草告佛疏》)⑧。他精研《楞嚴經》,“眠食藩溷皆執卷熟思”(《退谷先生墓志銘》)⑨。但竟陵派文學思想與佛教的關系沒有得到應有重視。錢鐘書對竟陵文學評點成就發覆甚多,言至以禪論詩卻用“引彼合此,看朱成碧”⑩抹過,竟陵派佛學自此為研究者所輕?。事實上,鐘惺的佛學修養絕不淺薄,他晚年所著《楞嚴經如說》?“一掃從前注腳”?。清初周真德認為,此書基于惟則天如《楞嚴經會解》和一雨通潤《楞嚴經合轍》兩種注本,“可謂青出于藍”?,劉道開、納蘭性德乃至錢謙益對此書亦有贊詞。此外,鐘惺生前在佛教界人望不低,名僧憨山德清、一雨通潤等皆與之過從,故彭際清編撰《居士傳》,鐘惺有一席之地?。職是之故,厘清竟陵派文學中的佛學因素,對于準確掌握其文學思想旨趣,從而把握晚明文學思想的走向是必不可少的?。
一、晚明詩壇的雙重困境與“古人精神”
“古人精神”是竟陵派反復論及的一個范疇,也引起一些研究者注意,卻少有人將其論定為竟陵派文學思想的核心?。然鐘惺《詩歸序》云:“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譚元春《詩歸序》亦云:“必古人之精神至今日而當一出。”?鐘惺《隱秀軒集自序》自稱其作詩“外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內自廢其中拒之私,務求古人精神所在”?。譚元春認為詩人“與古人精神相屬,與天下士氣類相宣”(《汪子戊己詩序》)?。可見,無論是《詩歸》之選,還是鐘、譚自作詩文,無不覷定“古人精神”,以之為鵠的。他們自視為先覺者并試圖引導今人與古人遇合,“古人精神”可稱為其文藝思想的旗幟。
鐘、譚標舉“古人精神”的針對性相當明確。一方面,以“古人”糾正公安派“寧今寧俗”之論,有復歸古雅傳統之意。公安派在晚明的貢獻是打破了復古論對文壇的控制。袁宏道破除復古習氣的釜底抽薪之舉是取消古典范型:“見從己出,不曾依傍半個古人,所以他頂天立地。”(《張幼于》)?“善為詩者,師森羅萬像,不師先輩。”(《敘竹林集》)?矯枉意識使他走到“決不肯從人腳根轉,以故寧今寧俗”(《馮琢庵師》)?的極端。其矯激之論在以風雅自任的鐘、譚看來,會造成“牛鬼蛇神,打油釘鉸,遍滿世界”(《與王稚恭兄弟》)?。鐘惺見人“時時稱說袁石公”,而不自覺“墮近人者亦十或三四”,根本原因在于“不劌心唐以上之所至也”(《周伯孔詩序》)?。回歸古人成了滌除近人習氣的藥方,故周亮工云:“竟陵矯公安之纖弱,人知復古,不無首功。”?另一方面,雖倡言“以古人為歸”,鐘、譚卻絕不肯回到復古派。鐘惺放言:“國朝詩無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實勝假初盛。”(《與王稚恭兄弟》)?又云:“直寫高趣人之意,猶愈于法古之偽者。”(《跋袁中郎書》)?在擬古與存真之間立場很鮮明。但他們的態度與公安派也不同:袁宏道號稱“不依傍半個古人”,鐘惺仍以古人為最高標準,只反對“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為古人在是”(《詩歸序》)?。
在鐘、譚看來,當下文壇面臨“因襲有因襲之流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與王稚恭兄弟》)?的雙重困境,“古人精神”是他們找到的對癥良方。但世人為形貌之古所誤,他們評選《詩歸》,就是為了“舉古人精神日在人口耳之下,而千百年未見于世者,一標出之”(《與蔡敬夫》)?,實有“作聾瞽人燈燭輿杖”(《再報蔡敬夫》)?、拔眾生于泥涂的意愿。不過,“精神”沒有實體、難以把捉,他們提出“古人精神”的思想基礎是什么?古今懸隔,今人怎么能夠“以古人精神為歸”,“古人”又會把文學導向何方?這些都是探尋竟陵派文學思想旨趣必須解決的問題。
“古人精神”的建構由鐘惺主導,考察其文集用例,“精神”指向超越物質層面的意志范圍,所謂“古人精神”當具如下基本特性:第一,超卓,超出紛雜世相,指向形上本體,并顯現力的強度。如“精神超礫莽”(《補和楊文弱年丈書德山讀元碑見寄之作》)?,“精神堪警俗”(《贈劉玄度孝廉為雷太史同年好友》)?,“滿腹精神堪獨往”(《寄答尤時純》)?。陳廣宏言:“觀‘精神’之詞義變化,其凝聚純粹之內涵基本穩定。”?“凝聚純粹”四字點出這一范疇超然物外而卓越有力的特點。第二,遍在,顯現于自然與人間之事事物物。如“篇籍者,造化之精神”(《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珠玉蘊藏,精神見乎山川”(《復陳鏡清》)?,“落花精神”?,“香久結精神”(《上巳過牛首山莊看云池王翁桃花翁先約往四年中凡三至此矣》之二)?,“以吾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為山水之精神”(《蜀中名勝記序》)?。精神雖超越世相之上,卻無所不在于萬物之中。第三,永恒,不因時間遷流而增損變化。如“松柏得全其精神,以與山終始”(《蜀中名勝記序》)?,“(真可傳者)水火兵劫不能遮攔”(《復陳鏡清》)?。正因為其恒一,今人才得以超越時空而感通古人。
鐘惺拈出“精神”,實質上提出了一個超越而遍在的形上范疇。陳廣宏指出“精神”一詞是其“形上理論的支柱范疇”?,切中要害。竟陵派心性論有宋明理學與佛教兩個可能的思想資源。其與心學的關系,陳廣宏已論之甚詳,茲不贅述。鐘惺對佛教熱衷到宣稱“讀書不讀內典,如乞丐食,終非自爨”(《退谷先生墓志銘》)?的地步。理學心性論更富道德約束意味,鐘惺形容佛家感悟真如的狀態是“眼目頓開,忽見心量遍周法界”?,涵容萬物而廣闊自在。鐘、譚“精神”一詞諸多用例并不強調道德而多指向情志能量,與佛教關系似更密切。有時這種關聯直接顯露于字面,如“精神隨處始,愿力有生來”(《章晦叔至白門題其行卷》)?,“精神堪警俗,耳目不知喧。就此機鋒里,窺君靜慧根”(《贈劉玄度孝廉為雷太史同年好友》)?。這里,“精神”與“愿力”“機鋒”“靜慧”等詞匯并舉,與佛教語境融合無間,而更重要的是它與如來藏思想的內在聯系。
宋以后,如來藏說“成為大乘的通量”?,晚明佛教“流行的修行依據是以禪為主流的如來藏系統的思想”。如來藏即一切眾生煩惱身中所藏本來清凈之佛性真如。鐘惺佛學以對佛性真如的信仰為基礎,把真如信仰稱為他的精神支柱也不過分。他曾自述病中景況云:“沉屙忘故吾,情形日幾變。有時如嬰兒,饑寒仰母便。有時如老人,奄奄息如線。過去未來身,一日游屢遍。真身宛自如,光明時隱見。”(《乙巳臥病作》)在病重恍惚、身心不能自主的狀態下,唯有真如佛性似一線光明引領其精神。他亦有禪偈云:“偶爾喪珠復反,急時扣鑰相求。未免勞勞多事,世尊不合低頭。”(《諾詎那尊者巖偈》)“珠”喻真如,此偈應該是禪修體驗的描述:世人雖容易被幻相迷惑,佛性卻是本來所有、不會失去的。
鐘惺全力修習的《楞嚴經》雖有偽經嫌疑,宋代以來卻很受文人歡迎。其教人破除魔障、闡說修行法門,皆以妙性真如為依托。真如即形上本體,《楞嚴經》云:“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于滅時知汝身中有不滅耶……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明言世相生滅之上有恒定不變者。鐘惺《楞嚴經如說序》開篇即云:“夫妙性真如,是謂大佛頂。見相永離,大定堅固,斯名首楞嚴。菩提始滿,乃始、中、終之所不得異,而過、現、未之所不能殊也。”鐘惺解《楞嚴經》大旨在教人如何體悟真如,強調真如佛性是一切修習的基礎。首先,真如即佛性所假之名,是超越所有虛幻現象的唯一真實。稱為“大佛頂”和“首楞嚴”,一表其“見相永離”的超越性,再表其與萬法虛空相對而“大定堅固”;“菩提始滿”即覺悟“涅槃元清凈體如來藏心”;因其超越,故不為時空所限,“始、中、終之所不得異,而過、現、未之所不能殊”。其次,真如遍在天地萬物之中。《楞嚴經》云:“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鐘惺云:“妙明真心,范圍天地,包含萬象。”覺知真如即能體察天地萬象。竟陵派所謂“精神”的超卓、遍在與永恒性,即依托于此真如本體而成為其藝文論的思想基礎。
二、作為古今通變依據的“精神”
“古人精神”的佛性論底蘊使其既恒定又活潑,因而能使詩壇走出因襲與矯枉的雙重困境,成為會通古人與今人的橋梁。
佛性論底蘊賦予“精神”的形上性質,為今人與古人遇合提供了可能。首先,精神的超越性與永恒性使竟陵派勸化今人回歸古人底氣十足。即使在復古流弊為天下厭棄之時,仍可以宣稱:“近時所反之古,及笑人所泥之古,皆與古人原不相蒙,而古人精神別自有在也。”(《隱秀軒集自序》)古人的價值基準地位不會因泥古、反古者而動搖,所謂“口亦詢詩變,心常在古人”(《金嶺驛與王帶如夜談》),萬變不能離其宗。其次,精神的遍在性使后人有可能理解古人。鐘、譚以先覺者自許,就是要指點出那些寄寓古人精神的事物為后學作津梁。“真詩者,精神所為也”(《跋袁中郎書》),精神之有無決定文字的價值之有無。先覺者的責任是“使古人精神不為吠聲者所蔽”,所以《詩歸》編選意在“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為之一易”。最后,“一段說不出病痛,須細看古人之作”(《與弟恮》),今人領會古人精神即可受其引導。“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覺知本體能夠獲取凝定力量,古人的導向使今人的意志不再盲目發散。
“古人精神”的形上性質又是個體獨立的依據。精神涵容于不同對象,呈現各異面貌:“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詩歸序》)一元本體是“不能不同者”,萬千境象則“其變無窮”。“漢、魏、唐人詩,所以各成一家至今日新者,以其精神變化,分身應取,選之不盡。”(《答袁未央》)在不同情境中本體的形貌不能固定不變,變化才能成就永恒。個體要超越無窮變相領悟“古人精神”,必須有獨立意志:“凡夫操之一人而能為可久者,其精神學問必有一段不敢茍、不肯輕為同者也。”(《題邢子愿黃平倩手書》)只有不迷失于變化之中,才能超出具體行跡之上。今人要顯現古人精神,就不能不刊落以往陳跡、自成其獨特變化:“內自信于心,而上求信于古人在我而已。”(《隱秀軒集自序》)文學的古、今、通、變由此獲得統一。
“古人精神”是切中萬歷后期詩壇肯綮又極具適應性的范疇。一方面,在輝煌的詩歌傳統之下,不僅崇古者高唱古人至上,即使那些反對擬古以圖自新者,也不能切斷與傳統的血緣,更不用說多數習詩者需要借助古典來自我陶醉或裝點人生。“古人精神”可謂相當討好的提法,是竟陵派影響較廣的前提。另一方面,“精神”只要求一種指向性,強調心靈抽離平庸向上提升。它高遠空靈,因無形貌故無限制,以古人名義向今人敞開了自我演繹的無限空間。依托“精神”,那些未經前人歌詠的甚至世俗的日常都可能煥發出輝光,所以《詩歸》與復古派選本大異其趣,竟陵派也飽受“鄙俗”“尖新”等批評,但意欲打通詩歌和真實體驗的詩人卻可大逞其便。“精神”提醒今人發現自我,突破現成模式去直接面對現實生活,由此創造新的文學世界。這是竟陵派招致大量追隨者的致勝之訣。
與“精神”相關的另一范疇是“性靈”。“鐘、譚一出,海內始知性靈二字”之說流行于晚明的事實或令三百年后的研究者疑惑。鐘、譚現存文字不但少談“性靈”,而且也沒有打出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敘小修詩》)那樣醒目的口號,他們怎么能更使“性靈”觀念深入人心呢?尋繹其故,應該和竟陵派提倡“古人精神”相關。公安、竟陵的“性靈”差異非常明顯。公安之性靈境觸而發,談分殊而不談同一。袁宏道以臨濟禪的否定性思維方式為主導,不設本體,以免落入執定,其“性靈”不易追隨。竟陵之“性靈”依托“古人精神”:“夫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眾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專其力、壹其思、以達于古人,覺古人亦有炯炯雙眸從紙上還矚人。”(《詩歸序》)有形上依據就可立定腳跟、方便度人,為后來者提供登岸舟筏,其“性靈”因而更易深入人心。
三、“幽情單緒”與“期在必厚”
鐘惺《詩歸序》中所言“求古人真詩所在”的途徑早已為人熟知:“真詩者,精神所為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獲,入者之欣于一至。”“幽情單緒,孤行靜寄”多被用來證明竟陵派癖好清冷孤寒,或未孚鐘惺本意。尋繹原文邏輯,可以將其解釋為對“精神”的性狀描述:“單”“孤”形容其超越形質而無所對待,“幽”“靜”形容其處根本之位而不為喧雜所動。主體與之感遇的唯一途徑是“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游于寥廓之外”,也就是回到未受牽染的本然狀態,獲得超越性體驗。
去蔽返真是《楞嚴經》指示的修養途徑。鐘惺云:“真心、妄想二種,全經大旨揭于此矣。”《楞嚴經》開示人人皆有佛性、為眾生指明返歸真如之路,其修養形態非常復雜,但全都圍繞著“破除妄想”這一中心:“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凈明體,用諸妄想。”妄想造成現象界的紛雜動蕩,妄想消除,立返清凈本源:“我因妄想,故久在輪回。佛因妄滅,故獨妙真常。”妄滅則無一絲障蔽染污,主體呈現虛靜狀態而能反照萬物本相:“覺明虛靜,猶如晴空,無復粗重前塵影事。觀諸世間大地河山,如鏡鑒明。”由于修習《楞嚴經》,竟陵派工夫論的中心也落在如何回歸心體本真上,概而言之即是“‘永潔精神’四字”。
虛靜無染的狀態,鐘、譚有時用“潔”“凈”“清”“幽”“寂”等詞形容,如強調主體不受干擾:“精神久寂寞,盤薄見其天。”(《贈徐象一年丈并索其畫》)它被看作古人精神所在:“看古人輕快詩,當另察其精神靜深處。”是后人感知古人精神的前提:“平氣精心,虛懷獨往,外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內自廢其中拒之私,務求古人精神所在”(《隱秀軒集自序》),“世多同面目,子獨具精神。癖貴居心凈,癡多舉體真”(《郭圣仆五十詩》)。也是文情詩思發動的靈府:“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簡遠堂近詩序》)以上材料除了表明鐘惺向往虛靜,亦可見其虛靜并非一味孤僻清寒,而常與萬物生機相關。主體無染便感物澄明,如水靜能照、鏡潔影明,“虛”與“靈”是一體之兩面:“性靈淵然以潔,浩然以賾”(《萬茂先詩序》),“虛衷集欣感,遭物觸其端”(《武昌令陳鏡清前以憂去遺六詩于寺壁情文俱古欽其希聲詩志欣嘆》),“居心無欲惡,觸物自清空”(《賦得不貪夜識金銀氣》)。
“精神”作為虛靜與照用的統一,可以幫助理解竟陵文學思想的另一個重要范疇——“厚”。鐘惺云:“詩至于厚而無余事矣。”(《與高孩之觀察》)譚元春云:“與鐘子約為古學,冥心放懷,期在必厚。”(《詩歸序》)“厚”是竟陵文學的最高理想,下面嘗試析之。第一,“厚”又被表述為“樸”。如“古法帖無妍拙放斂,其下筆無不厚者……極樸而無態”(《閱圣教序廟堂碑圣母坐位四帖》),此“無妍拙放斂”之“厚”,即“無態”之“樸”。再如“痕亦不可強融,惟起念起手時,‘厚’之一字可以救之”(《又與譚友夏》),以“厚”作為“有痕”反面,取其樸質。“樸”指事物未經加工的原初狀態,有本然意,譚元春云:“元氣渾沌以上語,止宜厚其氣而泯其跡。”(《奏記蔡清憲公前后札》之八)“元氣渾沌以上”明顯意在形上本體,可以把“厚”理解為對本體性狀的形容。第二,“厚”常與虛靜結對出現。如“冥心放懷,期在必厚”,“夫詩,以靜好柔厚為教者也”(《陪郎草序》)。“靜”與“厚”具同質性。只有心靈虛靜才能感通本體遍在宇宙、無所不包之“厚”。第三,“靈”被視為“厚”的前提。鐘惺云:“厚出于靈,而靈者不即能厚……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與高孩之觀察》)“靈”的基本性質是感通,“厚出于靈”即感通萬物以成其豐沛。“靈者不即能厚”,即感通能力尚不足體驗本體之廣大涵容。第四,“厚”常與“養氣”相聯系。或云:“博于讀書,深于觀理,厚于養氣。”(《送王永啟督學山東序》)或云:“元氣流不薄,終古此深厚。”(《渡江》)“養氣”來自儒家內圣修養學說,鐘、譚將其略作改造,添加了形上本源“元氣”“造化”,元氣磅礴的狀態也就是與天地萬物感通無礙的狀態。與精神修養的虛靜觀一致,他們又強調養氣須以心體去蔽無染為基礎:“心平而氣實”(《孫曇生詩序》),“學詩者先于淡其慮,厚其意,回翔其身于今人之上,無意為詩,而真氣聚焉”(《陳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詩記》)。養氣就是保持主體精神不被遮蔽,擴充感知萬物的能力。“厚”的養成主要通過讀書,但讀書的根本目的不是積累知識,而是“求古人精神所在”,培養感悟能力。
簡而言之,圍繞“精神”本體,“幽情單緒”“孤行靜寄”和“厚”都是鐘惺的詩歌體性論而非風格論。“幽”“單”“孤”“靜”不是趣味的清淡僻遠,而是個體回歸本體時的超卓狀態;“厚”不是審美的中正深婉,而是本體遍照萬物時的涵容狀態,是虛靜感通與浩然充滿的統一。因為涵容廣大而不受限于具體形質,“厚”強調的是精神的包容量:“一切興廢得失之故,靈蠢喧寂之機,吞吐出沒之數,趨舍避就之情,豪圣仙佛之因,拘放歌哭之變……出有而入無,確于中而幻于外。”(《汪子戊己詩序》)“厚”具有本體總量的性質,是“精神與天下人往來”的磅礴狀態:“能察山際昏曉之變,能辨煙雨所以起止,能乘月聽水于高低田之間,能上絕頂望大江落日,能選石斜倚、寂然相對,能穿松徑、愛其不成隊者趺而坐之。”(《九峰靜業序》)以這樣大的精神容量為基礎,竟陵派在風格論上是“樸”“清”“麗”“奇”“快”乃至“偏”“僻”等形態無所不包的。
鐘惺回歸“精神”的途徑是擺脫俗見,這意味著超越群從,容易滋生孤高情緒,表現在詩歌創作上即刻意推陳出新,多奇巧生僻之致。批評者謂其“幽深孤峭”,盡管以一代萬,尚不算無風起浪。今人仍舊視“幽深孤峭”為鐘惺的風格論并以之概論竟陵派,卻過于簡單粗暴。這既有思考上的惰性,也是受西方現代文論“流派”觀念影響的結果。陳斐曾指出,西方現代文論區分流派,以風格為必要條件。既然鐘惺詩的生新引人注目,他本人又有“幽情單緒”之論,那么以此作為竟陵派的標簽,是既簡便又極具辨識度的。然而,這個風格論標簽不僅掩蓋了鐘惺及竟陵派詩人詩歌風格的多樣性,更使其詩歌理論長期被狹隘化地誤解了。
本文所論佛學理念主要集中于鐘惺。作為竟陵派靈魂人物,他的佛禪修習影響了其文學取向,進而推動了晚明清初性靈文學思潮的演變。鐘惺自稱拈出“古人精神”是“一片老婆心”(《再報蔡敬夫》),提升學人意志品質的意圖是很明顯的。標舉“古人”似乎回歸了正統,然而深入其“精神”的佛學底蘊卻可以發現,它是超越古今、超越具體風格乃至超越雅俗的。當時流行的“正文體”之說,被鐘惺看作“錮天下有才有學之士也”(《送王永啟督學山東序》)。“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與其說是規范,不如說是開發:通過閱讀古人引導今人體驗形上本體,培養他們感通萬物的能力,由此在昏暗的時代傳遞生機。
竟陵派只是晚明習佛文人群體的典型案例之一。明代中后期被稱為佛教的“復興”時期,前承唐宋余緒,后啟近現代端倪,在宗教史上地位至關重要。“復興”不僅體現在佛門之內經藏刊刻、宗派復興等方面,居士佛教的興起也蔚為大觀。文人與僧侶的密切互動帶動叢林寺觀內藝文之風大盛,同時也為文人提供了精神養料。無視晚明文學的佛教色彩勢必造成理解盲區,深入清理佛教如何通過影響文人心態和思維方式滲入文學思潮,是晚明文學研究亟待開拓的課題。
* 本文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研究項目“晚明清初佛教與文學思想研究”(批準號:SKQX20150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易代之際文學思想研究”(批準號:14ZDB073)成果。
①②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617頁,第1074頁。
⑥⑩ 錢鐘書:《談藝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98頁,第312—313頁。
⑦ 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二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0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755頁。
? 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未對鐘惺的思想邏輯加以清理,就論定為“于思辨上顯然是準備不足”,“顯得雜蕪紊亂”(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頁)。
? 此書為鐘惺與賀中男合著,鐘惺所撰約占十分之七。全書共十卷,鐘惺云:“七卷以前,己懷強半;八卷至末,賀說居多。”(鐘惺:《首楞嚴經如說序》,《隱秀軒集》,第245頁。)
? 徐波:《遙祭竟陵鐘伯敬先生文》,鐘惺《鐘伯敬先生遺稿》卷四“附”,明天啟七年(1627)刻本。
? 蔗庵凈范:《重刻楞嚴經如說跋》,鐘惺、賀中男《楞嚴經如說》“附錄”,前田慧云、中野達慧等編《卍續藏經》第21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72頁。
? 參見李瑄《鐘惺的佛教生活及其佚詩三首》,載《中國詩歌研究》第14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
? 除了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上編第二章“運動過程與思想影響”簡單述及之外,僅有周群《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潮》(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十一章“靜觀默照與深幽孤峭:竟陵派對‘性靈說’的承嗣與新變”論及竟陵派文學思想與佛教的關系,主要集中于兩點:第一,“孤行靜寄”與靜觀默照;第二,佛教“苦諦”與荒寒境界。
? 陳廣宏注意到:“精神”一詞,是鐘惺在理論上成熟、創作上自新后特相標榜的一個術語(陳廣宏:《竟陵派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頁)。
? 周亮工:《尺牘新鈔三集》“凡例”,《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36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98頁。陳廣宏指出,竟陵派還受到“后七子一派文學復古風氣很大的影響……其取向亦終不脫古人之傳統”(陳廣宏:《竟陵派研究》,第141—142頁)。
?? 陳廣宏:《竟陵派研究》,第343頁,第342頁。
? 印順:《如來藏之研究》,《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第18卷,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