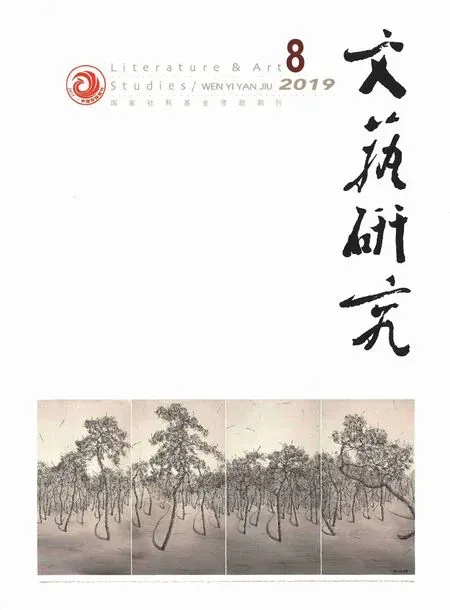推理小說的都市景觀
蔣原倫
某豪華山莊發生了謀殺案,偵探趕到現場,把在山莊度假的所有人都分別請到客廳來,每個人都必須向偵探提供自己不在場的證據,盡管每個人都顯得很無辜,但是罪犯就在這十來個人之中。所有的人,包括那個兇手,裝模作樣地和大家一起追問:誰是兇手?——是的,我們熟悉這樣的情形,這是偵探片中常有的場景,但如今這樣的場景居然也以實景游戲的形式出現在喧鬧的都市里。所謂“豪華山莊”,不過是都市某幢公寓樓的地下室,而寬敞的客廳其實只是某間斗室,斗室的窗戶外就是喧囂的大馬路。那偵探不是大名鼎鼎的柯南,罪案現場的各色嫌疑人也不是演員,他們只是一群年輕的密室游戲愛好者,一群特殊的都市消費者。
點觸手機的大眾點評軟件,你能在休閑娛樂欄目中找到“密室”字樣,打開“密室”欄目,各類游戲密室和體驗場館呈現在屏幕上,如實景推理偵探體驗館、機械劇情密室、密室逃脫&VR游戲館、偵探角色演繹推理俱樂部、久幽恐怖密室、沉浸式游戲劇場、精品真人密室逃脫館……林林總總有幾百家,這幾百家似乎形成了一種另類的推理小說的巨大文本,巨大文本是總文本,總文本就是某種邏輯,就是某種語境。而作為讀者或游戲者,只能進入一個一個具體的分文本之中,這些分文本又隱藏在密密匝匝的都市樓群中,和都市景觀融為一體。所謂融為一體,是指這些文本撒落在都市的各個角落里。你必須按所提供的地址,在不同街道、路段、拐角或形態各異的樓群里尋找,它們一般外觀并不起眼,和民居混雜在一起,或在一些商、住兩用的公寓中。公寓的門牌號是尋找它們的唯一標志。這些密室戶外的標識有的高調,引人注目;有的低調,常常為人們所忽略。無論是高調還是低調,或許都遵循某種原則,低調是為了不引人注意,逃脫刑偵者的目光,而高調則是為了吸引注意力,掩蓋某些罪孽與真相。
劉易斯·芒福德曾經把城市比喻為巨大的容器,人口的容器或文化的容器,有時它也是一具老舊的脹破的容器①。“在城市這種地方,人類社會生活散射出來的一條條互不相同的光束,以及它所煥發出的光彩,都會在這里匯集聚焦。”②如今,都市成為推理小說的容器,它的每一幢大樓的背面,每一扇窗戶里面,每一座樓梯轉角處,仿佛都有著無窮的秘密。在其繁華的、燈紅酒綠的奢靡光芒的掩蓋下,隨時都可能有著意想不到的罪案發生。因此,有研究者認為:“迷宮般的城市是進入謀殺片心理與美學構架的鑰匙。”③在這迷宮中,種種慣常生活的糾紛、沖突中都可能潛藏著推理故事的線索和影子,故亦可說都市生活以其紛繁復雜和眼花繚亂的節奏,每時每刻都在生產著各種推理故事。只是這些來自慣常生活的故事未見得會激起人們的關注,年輕的白領們更愿意將相關的欲望投射到特定的環境中,而各種推理俱樂部恰恰提供了這樣的環境,這環境有文學傳統的支撐,有人文背景,更有現代動漫的影響和相應的媒介氛圍。當然,也要有都市生活的便利,使他們的推理沖動在短短的兩三個小時內可以得到相應的滿足。
據說密室游戲的創新來自硅谷,是一群年輕的電腦工程師比照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說的相關內容,設計了情景和機關。由于其難度極高,很少有人能破解逃生。這或許只是一個美麗的傳說。還有另一種說法相對靠譜一些:密室逃生是由電子游戲演變而來的真人游戲,是由日本的SCRAP公司在2007年首先開發的。
一、場景
推理小說是文學的一種類別,而今成為都市生活的一項實景化的游戲,一群年輕的玩家,進入推理俱樂部,各自扮演起規定的角色,因此,所有的文學修辭演變為一種都市景觀,更確切地說是演變為一種都市景觀修辭,在這里,場景是一個重要范疇。在不同的密室游戲中,人們首先進入的是不同的場景。什么是場景?場景就是特定的空間和空間內相應的景觀,然而場景與場景之間的差異不僅僅是表面上的、顯而易見的景觀差異,還有更深一層的差異在景觀背后。場景不同于一般空間,是由于“場”的存在。“場”也可以說是某種物質存在的基本形態,是各種力量,如能量、動量和質量等,相互作用并構成一定關系的所在。當游戲者進入場景時,就是進入預設的各種力量的交匯點,亦即游戲者在心理上大致已有所準備,自己將扮演某一個角色,并以角色的立場進入到將要展開的故事中。雖然在進入場景前,自己并不清楚將要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但是大致可以確定,這往往是某個自己從未接觸過或者未體驗過的角色,這種體驗不僅包括角色的身份,也包括場景體驗,這是身份和場景的結合,是假想的個體進入特定空間的“歷險”,所以更加吸引年輕的玩家。
密室游戲是統稱,若細分起來,還有種種類別,如有密室逃生、劇本殺、沉浸劇、實景推理等等。每一類別中又有一些小的區分,這些區分不是依據故事發展的邏輯,而是依據具體情景中的某些特征而言的。例如,在劇本殺游戲中有實景類和卡牌類之分,卡牌類是指推理和偵破的線索全部在卡牌上,實景類則是需要一些提示性景觀,它們也可以看成是象征性的實景。如果故事發生在船上,那么會有舷梯、纜繩、救生圈之類的實物;如果故事發生在山莊,則會有山莊風光的圖像或投影;如果是宮斗劇,那么會有一些類似宮廷的裝飾性布景。這些象征性的實景與情節進展、推理過程沒有直接的聯系,但是會對玩家的心理有一些影響,或者說玩家在心理上需要這樣的景觀。因為在外觀幾乎整齊劃一的、內在空間大同小異的都市公寓中,人們能夠奢求的就是那樣的象征性的景觀。就如同閱讀小說,作者必然會通過洋洋灑灑的大段環境描寫來為故事的進展作鋪墊,而讀者盡管常常會跳過瑣細乃至拖沓的景物描寫而直奔情節,但是,無論讀者關注不關注場景描寫,小說家是不會忽略它們的,因為沒有地點和場景,故事就無法展開。
由此,盡管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說的推理邏輯大致相同,但是故事必須安放在不同的場景中,或在東方快車中,或在尼羅河上的游輪里,或在孤島、懸崖、海灘上……而讀者無論是在圖書館,在咖啡館,還是自家的書房或臥室,在進入作家所設定的推理邏輯之前,須隨作家的筆觸先進入這些想象性的案件發生的地點。其實文學作品提供的場景并不直觀,往往是概念性的,但即便如此,它們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為讀者需要這種概念所制造的氛圍。
比起柯南·道爾,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似乎更加誘人,也更加適合改編成電影。因為福爾摩斯的探案故事,有不少發生在老舊的倫敦街區,而阿加莎·克里斯蒂筆下的大偵探波洛則滿世界游蕩。電影編導們之所以更加青睞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因為小說提供了大量不同的場景,這些場景無疑有助于電影空間的展開。毋寧說,柯南·道爾加上場景,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克里斯蒂當初是柯南·道爾的粉絲,是她將倫敦的推理故事換上各種背景,播撒到世界各地。她人生的兩場婚姻增加了她周游世界的閱歷。特別是第二任丈夫是著名的考古學家,也許是受考古學的啟迪,她的推理小說既充滿想象力,又將這一想象力置于嚴格的推理過程之中。因為考古作業既有還原各種場景的努力,同時也是一種推理活動,即要從種種遺跡中拼湊當年的生活面貌,必然要借助推理,而場景成為推理過程中的重要元素。場景既是空間,又是氛圍。純粹的推理和演算不需要氛圍,甚至不需要空間,但是故事的人物需要,人物是要在一定的空間之中行動的,人物的心理也要通過某種氛圍加以揭示。
而今的都市年輕玩家需要的就是與推理游戲過程交織在一起的空間和氛圍,這空間可能就在他們早九晚五的辦公樓的不遠處,但是場景變了,氛圍就變了,場景和氛圍變了,心理也會產生相應的變化。應當說,氛圍并不是在人物心理之外的純物理空間所產生的,而是在參與者的互動中醞釀而成的,當然,氛圍也是場景的一種功能。
密室游戲的各種場景,模擬的是日常生活的場景,但是某種意義上,它已經演變為神秘空間。因為日常生活場景是開放的,可以自由出入的,并且是習以為常的,甚至到了人們熟視無睹的地步。而模擬場景則是一個封閉的空間,即在游戲結束之前,人們只能在其所規定的范圍內活動,不能隨意離開。對于游戲者來說,一旦進入這個空間,即將發生的所有事件均難以預測,主宰的力量來自外部設定,其象征來自命運安排或某種無法把控的預言。游戲者只能不斷地摸索和試探,尋找答案和出路。由此,一切日常生活場景就有了陌生感和神秘感,并且成為重新審視的對象(以至于密室游戲的經營者要不斷地提醒,某些家具和日常用品不在游戲范圍內,無須翻檢)。這有點像海德格爾所舉例的那把“在手邊”的錘子,當錘子損壞時,反倒引起了人們不同尋常的關注。它被從日常的使用功能中剝離出來,似乎獲得了本真的存在。如果這把錘子被藝術家展示在畫布上,在海德格爾看來,那就是現象學的真理。當然,在密室游戲中情況又有不同,這些日常用品的功能也是被剝離的,甚至一盒香煙、一枚紐扣、一串電話號碼都是以神秘化的或者隱晦的面目示人的,因為它們有了新的符號意義,這些符號意義并非一目了然,需要人們一層一層地去揭示。
當游戲者進入場景時,在他人眼里就成為場景的一個部分。參加游戲者通常是以小群體為單位,每個個體面對的是群體的其他成員。在密室逃生類游戲中,他們是生死與共的戰友;在實景推理或劇本殺游戲中,他們則可能互相是對手或仇家,真所謂“他人即地獄”。或許都市的感覺就是對他人的感覺,因為只有在都市,你才會接觸到那么多的“他人”。在每個略顯冷淡、彬彬有禮的人的背后都有一個你不了解的世界,而我們只能根據名片、簡單的檔案材料、旁人的介紹來快速預判即將要打交道的對象。在密室游戲中,情景相仿,每個游戲者都可能拿到一個腳本,在腳本中,既要熟悉自己的角色,也要簡略地知曉他人的身份。當然,由于游戲的需要,你無法獲得他人更詳細的資料,往往只能根據外表印象來判斷他人。這時,人就像是整個場景的附屬部分,即在這一場景中出現的角色到底在整個故事中起怎樣的作用,應該說,他們是被整個游戲所規定的,所以他們充當的角色不是性格的角色,而是某種功能的角色,是需要人們從游戲功能的思路去破解的,所以他們和場景是融為一體的。
密室游戲在都市構建神秘空間,同時也呈現蒙太奇景觀,因為密室與密室之間是并置的,每一個單元的場景都不相同,某種意義上說,都市的魅力就在于這類各種場面并置的光怪陸離的蒙太奇景觀。說起密室游戲的蒙太奇,起碼可以分成兩種類別,即時間軸上的蒙太奇和空間軸上的蒙太奇。在影像敘事上,時間蒙太奇是編導們推進故事的好幫手,而空間蒙太奇則是各種場景、各種意象的拼貼和交匯。因此,超級都市在人們眼中展現的往往就是蒙太奇空間,難怪許多學者有關都市的論著都呈現類似的面孔,無論是本雅明的《拱廊街研究》,還是居伊·德波的《景觀社會》,在對城市的表述上,都采取斷片的拼貼方式,使得習慣于沿著嚴密的線性邏輯進行閱讀的讀者常常茫然無措。特別是本雅明,他將自己思想的吉光羽片,如斷想、感悟、洞見等等,以《單向街》來結集命名,并以加油站、建筑工地、門牌號、政府機構、自助餐廳、診所、啤酒館……一一羅列,可見得本雅明的即興的思維火花如同閃爍的街景一般撲朔迷離。由此,蘇珊·桑塔格認為本雅明“所寫的殘章斷片,完全可以叫做‘追憶流逝的空間’”④。漢娜·阿倫特也持有同樣的看法。她認為,作為都市“游蕩者”,本雅明的寫作是“深受超現實主義的影響,這種企圖‘力求在最微賤的現實呈現中,即在支離破碎中,捕捉歷史的面目’”⑤。
盡管眾多游戲密室在都市里只占空間的不起眼的一小角,但是在這一蒙太奇空間中卻也增加著都市“時間上的豐富性”⑥,因為它在都市喧囂嘈雜的空間中,延續了此前一百多年來的推理文學傳統,并吸引了現代都市的新興群體。用芒福德的話來說:“城市通過自身以時間和空間合成的豐富而復雜的交響變奏,一如通過城市中社會勞動分工協作,城市給自己的生活賦予了交響樂般的品格。”⑦
二、角色扮演
按通行的解釋,“角色扮演”(cosplay)最初是作為一種動漫展和游戲展的營銷方式在日本出現的,是指借助服飾和道具對動漫作品中人物的扮演,如年輕的愛好者穿上各色服裝,擺出各種姿勢,變身為各種虛擬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角色扮演的逐漸流行是與“二次元”文化的興起緊密相關的。有人把伴隨著動漫和游戲成長的一代人稱之為“二次元”人物,這一代人以二維平面的動畫世界替代三維的現實世界,或者說他們更熟悉“二次元”世界的生活邏輯,那是一個充滿“架空”或“幻想”的世界,即在現實世界之外還有另外一個與之平行的世界,這是一個可以游戲或馳騁想象力的世界。
而今在密室游戲中,“二次元”邏輯也落實到現實實景中,角色扮演有了更深入的可體驗性。在實景推理或劇本殺等游戲中,玩家根據自己在游戲中的身份,穿上與之相應的服裝,如警察,就身穿警服,佩帶警徽,手中握有道具手槍;如神父,則著裝僧侶黑袍,胸前佩戴十字架,手持圣經等,以裝扮的象征性進入角色。當然,這種角色扮演既非戲劇舞臺上的表演,亦非社會學意義上如喬治·赫伯特·米德和歐文·戈夫曼等研究的社會角色扮演。前者在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主題下來安排故事情節和人物命運,其中關鍵在于,人物是有性格和思想的,是按照故事發展邏輯來呈現人物思想和情感變化的,這既涉及對劇本的整體理解,也更高程度地涉及演員的自我修養;后者關注的是個體試圖如他人一般,社會性地看待他自己,即想象自己的行為在他人眼中是否符合其相應的社會身份。社會學的角色扮演理論認為,人們的社會行為就是一種社會表演,因為作為一個社會人,每個人都可能兼有多種社會身份,如家庭中的父母、夫妻或子女,工作單位的上司或下屬等等,由此,人們在互動的過程中按一定的社會場合和語境,扮演著多種不同的角色,并試圖控制自己留給他人的印象。密室游戲中的角色扮演,其中的人物雖然具有“二次元”的特點,但是角色本身只是推進情節的一個工具,并不具有獨立性和個體性,角色扮演所獲得的快感完全來自角色推進情節中的神秘性和非我性。
當然,推理實景游戲中的一些玩家是沖著破解故事之謎而來的,還有一些玩家是為了放松和轉換生活節奏而來的,但是更有不少玩家就是來過過角色扮演的癮。正是在這一點上,推理小說在動漫之后為角色扮演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摹本題材庫。角色扮演也是為了展示和傳播,它在展示扮演者的心態、體態、情感的同時,也在展示都市生活中的多樣性和流行趣味。角色扮演的愛好者往往不只扮演一個角色,他們會輪流替換扮演多種角色。表面上看,這和春日里帶著一大堆艷麗服裝到草地上拍照的年輕姑娘沒有什么大的區別,其實不然。后者只是在用多種方式來表現自我,前者則必須有角色意識,他們在多種角色中徜徉,甚至迷失在其中。都市生活的繁華,其節奏、變化和偶遇性處處在提示年輕的角色扮演者,他們的前程和命運有著許多岔路和神秘性。盡管推理小說的角色是功能性角色,為情節所預設,但是在角色扮演者的心目中,故事中角色有著某種誘惑力,它們帶來了種種遐想,同時它們是都市生活的底色,在這種底色上可以繪制日后生活的藍圖。
角色扮演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類比于假面舞會。假面舞會是萬圣節傳統的某種延伸,人們所使用的兇神惡煞的面具,原本的意思是在“鬼節”上化妝成各種各樣的“鬼”,以躲避那些在這一天回到故居地尋找活人作為替身再次投生的亡靈。后來假面舞會演化為一種娛樂活動和社交活動。戴上假面,意味著改變自己的某種身份,卸下平日里日復一日的刻板生活的裝束,解除身份帶來的某種禁忌,換取片刻的歡愉。盡管這種改變是暫時的,但是從中獲得的快樂是難得的。不過,與假面舞會不同,參與密室游戲中角色扮演的基本上都是年輕人,他們的身份和社會地位還沒有確定,有的還沒有進入成年人社會,角色扮演在某種意義上是他們進入成人社會的一種嘗試性預演,也成為他們實現某種未來之夢的場所和手段。自然,在密室游戲中,所有的角色都是功能性的角色,是事先設定好的,扮演者雖然沒有太多自由發揮的余地,但是也能在模擬角色中獲取些許快感,并通過移情來完成某種心理的投射。
角色扮演過程中,不僅需要服裝和飾品的裝扮,也需要身體和姿態與之相配合。從服從角色的角度講,身體是配合服裝和屈從服裝的,但是,從扮演者的心理出發,服裝是為了凸顯自己的身體,展示自己的身體。或許,可以將密室游戲中的角色扮演理解為一種體驗、一種“應景體驗”,即在都市萬花筒般的生活環境中,每一個社會人如果只有一種職業身份,顯然是過于單調、乏味,缺少浪漫,缺少改變,因此角色扮演是即時改換身份的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徑,同時也能在一定的場景中獲得相應的真切的角色體驗。這種“應景體驗”,盡管短暫,但這是年輕人領會都市生活的一種淺表的輔助性方式,也是個體想象力的折射。想象力永遠高于現實生活,異于現實生活。在密室游戲中,想要獲取“應景體驗”還緣于這樣一種情形,即對于大多數年輕的玩家來說,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永遠也不可能有犯罪、謀殺和逃生之類的人生體驗,以往的經歷中沒有,在今后的生活中也未必會有。他們只是在小說和影視作品的觀賞中有過類似的體驗。他們要把這一“觀賞”的體驗轉換成“經歷”的體驗,這也算是一種“二次元”意義上的“穿越”,是對平凡人生的一次超越。這樣的行動無須冒險,卻可以收獲歷險的體驗。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密室游戲中的角色扮演就是個人的想象力和好奇心發揮作用的一個結果。波德里亞指出,“消費者與現實世界、政治、歷史、文化的關系并不是利益關系、投資責任的關系”,而是一種“好奇心的關系”⑧。也難怪,在角色扮演中,來自異域的對象更受歡迎,或者與扮演者自身所處的階層地位差距越大的對象越受歡迎,因為它們更能激起扮演者的欲望。某種意義上說,全部密室游戲就是建立在“好奇心”消費之上的,而角色扮演是其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體現。
三、走向都市人類學
也許我們把密室游戲僅僅歸之于好奇心作祟,一定還遺漏了現代都市生活的某些特質,盡管好奇心消費有著無限的空間,但它一定不是全部,就如古典音樂在現代都市生活中仍然有著巨大的活力一般,人們反復演繹它,不只是出于好奇心,而是它有著人類感情生活無法割舍的神秘性。
有研究者認為,城市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市民創新的所在地”,并且這種創新包括四種形式:“藝術型(比如,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科技型(以生產流水線為特征的底特律,以高科技出名的帕洛阿爾托);文化——科技型(好萊塢與電影藝術)以及解決問題型(19世紀倫敦的污水處理)。”⑨實際上,現代都市往往是以上四種形式的總和,并且還有比這四種創新更多的形式展露,正如密室游戲的出現,它表明都市生活在任何維度上都有創造的空間。
從文學的發展歷程來看,推理小說是在通俗的大眾讀物中滋長起來的,這類通俗讀物的流行與都市生活的繁榮是相匹配的,它滿足都市人的世俗情感和欲望。推理小說的發展,有不同的路徑,衍生出各種流派,最基本的有本格派和社會派的區分。橫溝正史屬于“本格派”,東野圭吾可以看成是偏“社會派”。本格派是指按傳統的推理小說的路數來結構故事,情節是在比較嚴格的邏輯推理的過程中逐步進展的,這里比較關鍵的是作者給讀者所提供的信息和破案線索與小說中偵探所得到的線索幾乎相同,即讀者的視野和小說中偵探的視野很接近。當然,這是嫻熟老到的小說作者必須掌握的一種技巧。社會派則關注罪案背后的社會動因,而不僅僅敘述破案故事或提供解謎游戲。這種劃分在表層上看有些許道理,但是在深層上進一步追究則讓人困惑,因為這里沒有絕對的界限。本格派雖然有其獨立自足的邏輯空間,但是并非與社會生活相隔離,相反它需要社會生活的滋養。凡是有影響的本格派推理小說,都與當時的社會語境有隱秘的相通渠道,只不過常常為我們所忽略。也正是因為這種與社會的內在的聯系,使得推理小說成為了通俗的大眾讀物,而這類通俗讀物的流行在與都市生活的繁榮相匹配的同時,也在不斷滿足著都市人的世俗情感和欲望。
密室游戲的一些腳本可以看成是本格派傳統的某種延伸,但卻是都市生活的產物。它用新的媒介方式將推理小說撒向都市的各個角落。就其將推理小說從平面媒介轉化為空間媒介這一點上,是極富創意的。一般而言,小說是將都市生活由立體(空間)轉向平面的,因此論述紐約或上海等大都市是怎樣呈現在紙媒上的,成為眾多文化研究者的熱門話題⑩。往遠里說,狄更斯小說中的倫敦,波德萊爾詩歌中的巴黎,也是如此。所以波德萊爾筆下的巴黎,成為本雅明“拱廊街研究”系列中的重要主題。
密室游戲則使推理小說由平面變為立體,以往的文本的閱讀者轉化為行動的參與者。參與者與其說在破案,莫如說是在參加聚會,這是一種新型的聚會,是人們彼此間聯絡情感的一種特殊方式。往日的同事或朋友各自以陌生的身份加入到聚會中來,既有協作、共謀,也有猜疑、欺騙,更有謎底洞穿和真相大白。當都市生活的復雜性、偶遇性、隱秘性等以某種推理的方式逐漸展開時,都市生活的誘惑力從各個層面上包圍著游戲者。且眾多的推理故事雖然情節各異,但是套路和破解方式相差無幾,因此其中的推理并非嚴格遵循理性精神,相反,它們是娛樂和情感生活常用的表達,也因此成為年輕人對朝九晚五的庸常都市生活的抵制途徑。
或許,正是因為現實生活中的死亡大都平淡無奇,作家們才能創造出如此匪夷所思的謀殺與死亡來。推理小說作為通俗文學之所以大受歡迎,就是因為在幾乎相近的段落和框架中一遍又一遍地上演大同小異的故事。這些故事離奇的程度只表現在一個方面,那就是謀害和死亡的方式。這方面做得最極致的,當屬長篇推理小說《無人生還》。在那個海島上,八個被邀請來的嘉賓和接待他們的管家夫婦最終都死于非命,只是每個人的死亡方式怪異蹊蹺,構成了恐怖的疊加。阿加莎·克里斯蒂以驚悚的筆觸刺激讀者的神經,給都市人平庸的生活加進辛辣的調料,難怪該書出版以來,據說累計銷售上億冊。都市人不但津津樂道地觀看這一切,還進一步,在文化娛樂產業中將其推演為模擬性行為,即辟出專門的空間,設置相應的場景和角色,精心編織天方夜譚般的故事,使之成為特殊的游戲種類。正是在這同樣的氛圍中,日本電視劇《名偵探柯南》將這類題材開發為動漫電視系列劇,使之成為兒童觀看的對象。兒童們不是在觀摩殺人,而是在動漫世界中徜徉游樂,消磨時光,或者是在作有益于智力提高的培訓。應該說,這一趨于低幼化的游戲,正在摧毀傳統社會設置的某些壁壘,寓意“童年的消逝”。
如果說用結構主義敘事學來讀解柯南·道爾或阿加莎·克里斯蒂以來的推理小說,在某些方面,我們似乎能一目了然。人物的功能性行為和環境的標志性事件都指示著故事的走向,沿著這一走向,我們可以將此類故事編得更加精巧和完美;而解析密室游戲,我們則可以借鑒文化功能主義和都市人類學,亦即我們應該在都市生活的背景下來考察這類娛樂活動,揭示這類文化產業的興起和人們的日常行為與情感表達方式之間的內在關系。與游牧或農耕文明時期相比,在都市生活環境中,人類的文化生活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原本許多在嚴酷的環境中人類的勞作、競爭和生存活動,轉化為文化形態,轉化為文本和符號,甚至成為娛樂活動。
這里的關鍵是,在都市文化生活中,推理小說中的恐怖故事和情節是怎樣一步一步演變為“殺人游戲”,對!殺人僅僅是游戲!其實在密室游戲風行之前,坊間已經有人在玩殺人游戲。即謀財害命的非正常或反人類的行為,居然是游戲的內容,在這類游戲中,善良的、見血就會大呼小叫的平常人,一次又一次地擔任了相應的恐怖角色,完成謀害他人的恐怖“任務”,或者相反,偵破了對手的陰謀和罪案。這類殺人游戲與席勒的或赫伊津哈的游戲觀——即認為游戲應該是審美的和人的自由精神的體現,游戲是文化的一種本質——是悖反的,它是在尋求恐怖和刺激中達成破解謎團的快樂。這是現代人反常的(即與傳統社會相反的)快樂,由消耗人的體力的游戲變為專門消耗人智力的游戲,快樂的生理基礎有了變化。另外,這智力不是用于應對嚴酷的自然環境,而是專門應對“他人”,力求從蛛絲馬跡中尋找破綻。
由于人口的聚集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都市重組了社會的人際關系,也構建了新的社會文化和游戲方式,人們之間的互動和交往頻率增加,這里既有密切的協作,也有互相排斥,原先面對自然環境包圍的人,現在為人際環境所包圍并感到困惑。特別是生存空間的擠壓,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厭惡、猜忌與冷漠,這是不相干的人之間的厭惡與猜忌。沒有利益糾葛,沒有世代仇恨,甚至相互根本就不了解,故殺人也就沒有罪惡感,殺人與偵破,只是智力上的比拼,只是在解碼和破譯能力上的競技,沒有武力搏擊,沒有打打殺殺,當然背后同樣是情感的某種宣泄。正是從這里,我們看到了現代人享受反常(與傳統社會相反)快樂的畸形現狀。或許癥結就在這里,我們該如何應對?都市人類學應該深入回答這一問題。
結 語
論及推理小說的都市景觀,并不是說這些隱藏在都市深處的密室,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都市的外在風貌,應當說,如果不特別留意或沒有人專門指引,幾乎很難一眼就發現這些游戲密室。今天的都市,最耀眼的外在景觀就是水泥森林,是白天的車水馬龍和夜晚的燈紅酒綠。但是對于久處都市之中的人們來說,這些都是熟視無睹或視而不見的。都市作為龐然大物,似乎有強大的生命力,但是我們找不到它的心臟,它的每一條街道倒像是脈搏,在劇烈的搏動中煥發出生命力。都市的活力體現在這些街道的人流中,體現在兩側商家牌號的更替過程中。或可說都市景觀是生活和消費方式的景觀,它們潛移默化地改變著都市人的情感和心理狀態。當密室游戲低調地成為年輕人的一種娛樂方式時,它們為都市文化植入了一種新的景觀。
二十多年前,包括愛德華·索亞、米切爾·迪爾等在內的一群學者曾將洛杉磯作為后現代都市的樣本來研究,緣于洛杉磯沒有如巴黎、紐約、羅馬等大都市通常有的標志性建筑和主導景觀,也不像芝加哥那樣是一個同心圓擴展的城市,它是一個“分散的,離心化的城市”?,或者說是無中心的行政區域。但是這個最沒有特點的城市有迪士尼樂園,有好萊塢影視基地,有海灘和綠蔭大道,還有連接這一切的高速公路。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它是一個有娛樂、有憧憬的地方。都市景觀似乎是由樓宇構成的,其實它從來不是冰冷的建筑,是現代人的情感、行為和他們的生活方式構成了真正的都市景觀。
① 參見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宋俊嶺等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年版,第563頁。
②⑥⑦ 《劉易斯·芒福德著作精粹》,宋俊嶺等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頁,第129頁,第129頁。
③ 轉引自米切爾·迪爾《后現代都市狀況》,李小科等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頁。
④ 蘇珊·桑塔格:《〈單向街〉英文本導言》,張新穎譯,《本雅明:作品與畫像》,文匯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243頁。
⑤漢娜·阿倫特:《瓦爾特·本雅明》,《啟迪——本雅明文選》,張旭東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30頁。
⑧ 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頁。
⑨? 米切爾·迪爾:《后現代都市狀況》,第387頁,第6頁。
⑩ 參見孫遜、陳恒主編《城市史與城市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