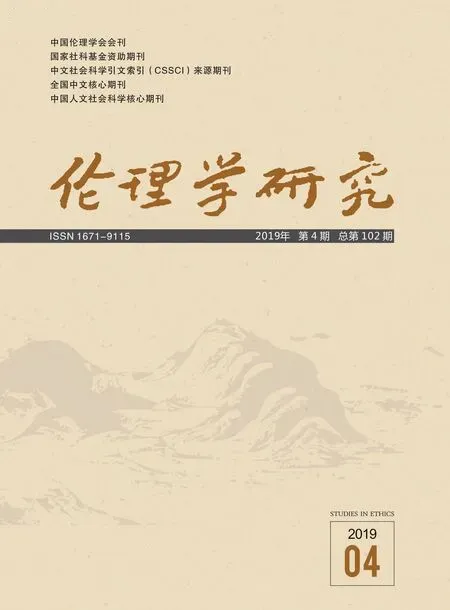人性與德性的兩難:利己與利他的悖論解析
劉清平
一、問題的緣起
在西方道德哲學的語境里,長期存在著某種二元對立的理論架構,把利己與利他看成是兩種在概念上就不兼容而相互排斥的東西,結果在許多重要的問題上引發了眾說紛紜的無謂爭議,其中最典型的要數主張利己主義“有人性無德性”、利他主義“無人性有德性”的怪誕悖論了。
首先,一些哲學家認為,按照人們的自然本性或所謂的“自然法”,他們只會單向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可能產生利他的動機。霍布斯便宣稱,“人們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時只是為了自己的歡樂,而在達到這一目的的過程中彼此都力圖摧毀或征服對方”;因此,“自然法……禁止人們不去做自己認為對于保全自己生命最有利的事情”,以致每個人都會“憑借武力或機詐去控制所有能夠控制的人,直到沒有強力可以危害自己”,結果走向“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1](P93-97)①。直到今天,所謂的心理利己主義仍然沒有擺脫這種觀念的深層積淀,從實然性描述的角度特別強調每個人都僅僅關注自己的利益,即便從事利他的行為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作為倫理維度上的一種規范性訴求,利他主義違反了“自然人性”,是“不合理”而無從成立的[2](P87-105)。
與此同時,另一些哲學家又主張,在人類生活中,只有利他的動機以及行為才是有道德的;相比之下,利己的動機以及行為不僅談不上高尚,而且還潛藏著不道德的傾向。休謨就宣布:“我敬重那些能將自愛以任何方式指向關心他人和服務社會的人,而憎惡或蔑視那些只考慮自己滿足和享樂的人。”[3](P149)康德也強調,人們只有基于不包含自己的感性需要或愛好的良善意志,出于理性頒布的普遍義務從事行為,才能具有值得高度推崇的真正道德價值;相比之下,那些僅僅出于利己意圖的行為,諸如商人在買賣中為了自己長久贏利做到了童叟無欺之類,即便是符合義務、廣受贊許的,也缺乏真正的道德價值[4](P11-14)。叔本華在把“自我保全”的利己欲與“不可害人”的正義德性對立起來的時候更是主張,“利己主義與行為的道德價值是絕對相互排斥的。……道德價值完全取決于從事或不從事某種行為只是為了他人的利益”[5](P143-144)。
于是,一旦將這兩種針尖對麥芒的觀念放在一起,不僅會在利己與利他之間生出不共戴天的二元對立,仿佛前者在邏輯上已然排斥了后者,而且還會在通常被視為內在統一的人性與德性之間也造成致命的斷裂:利己的動機以及行為雖然符合人性,但同時又是缺乏德性的;利他的動機以及行為雖然很有德性,但同時又是違反人性的,從而形成“人性還是德性”的荒唐兩難:如果利己符合人性,它怎么會缺失德性?倘若利他具有德性,它為什么不合人性?更簡潔些說,要是利己構成了自然人性,利他如何可能有高尚德性?事實上,面對這種兩難,如果說利己主義只能是尷尬地努力挽回自己在道德上的不良名聲,利他主義的境遇則更為難堪,不得不設法找到自己在人性中的立足根基。
尤為反諷的是,這種兩難有時甚至還會凝結在同一個人身上。例如,主張利己主義符合自然人性的霍布斯,內心深處便似乎傾向于認為它有些不道德,所以才在描述了人人開戰的叢林狀態后感嘆說:“自然人性竟然使人們如此分離,相互侵害和毀滅。”[1](P95)他甚至指出:“為他人好的意欲就是惠助、善意或慈愛;如果指向所有人就是善良的自然人性。”[1](P39)再如,叔本華在宣布“不帶任何利己的動機就是評判一個行為是否具有道德價值的標準”的同時,又明確承認利己欲是人的首要行為動機,甚至與人的本質是合而為一的[5](P131、140)。至于那個以亞當·斯密命名的悖論同樣是在這種兩難的語境里生成的:一方面,人們主要是憑借自愛的利己欲在經濟領域從事謀利的行為,其動機只是想為自己賺錢而不是對他人施惠;另一方面,人們只有憑借利他的同情心才能在倫理領域從事有道德的行為,擺脫利己欲的偏見而生成正義和公平的良知[6](P14)[7](P96-113)。這樣一來自然會引發下面的質疑:既然如此,經濟生活豈不是就缺失了正義的德性,而道德生活則會扼殺了利己的人性嗎?事實上,盡管兩百年來許多論者試圖從各個角度消解二者的張力,其結果好像都不怎么成功。例如,斯密自己提出的一種解釋是:雖然人們從事經濟行為的主觀動機只是為了利己,但這些行為的“客觀”后果往往是利他的。[8](P27)可是,他在此通過神秘的“看不見之手”展示的這種“主客觀統一”似乎還是難以解開一個魔咒:本來不道德的利己欲難道能夠單憑產生了利他后果的飛身一躍,就讓經濟行為轉化成基于同情心的有道德行為嗎?眾所周知,這個不僅把人性與德性,而且把經濟與道德也弄得水火不容的理論兩難,迄今還是一個讓西方學界傷透腦筋的深度悖論。
與西方學界以二元對立架構為前提展開的上述理論努力不同,本文試圖依據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形成的日常體驗,通過辨析“自利”人性內在包含的“利己”與“利他”兩種因素之間既和諧又沖突的互動關系,主要從元價值學的實然性視角出發,破解西方學界制造的人性與德性的怪誕悖論,論證下面的見解: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不僅同樣符合趨善避惡、取主舍次的人性邏輯,而且同樣具有復雜糾結的道德屬性,無法一刀切地貼上不道德或有道德的片面標簽。
二、自利本性中的利己與利他動機
匪夷所思的是,與另外某些在理論上引起了長期困擾的千古之謎相似,導致西方學界在利己和利他問題上陷入悖論難以自拔的一個主要原因,居然是它未能從語義分析的角度深入辨析人生在世趨善避惡的自利意愿的豐富內涵,結果只是單純強調了它的利己一面,卻將它實際包含的利他一面排除在外了。
本來,從元價值學視角看,最廣泛意義上的“趨善避惡(趨利避害)”可以說確實構成了人人擁有的自然本性,因為一個人只會通過從事各種行為,追求他認為是有利于自己因而值得意欲的好東西,避免他認為是有害于自己因而覺得討厭的壞東西,以滿足他的需要,彌補他的缺失,維系他的存在,實現他的自由,卻不可能南轅北轍地追求他認為是有害于自己,因而覺得討厭的壞東西,避免他認為是有利于自己,因而值得意欲的好東西。其實,哪怕一個人昨天還因為反感榴蓮的味道避之不及,今天就因為了解了榴蓮的豐富營養趨之如騖,也是由于他昨天把榴蓮視為可厭之惡、今天卻視為可欲之善的緣故。所以,盡管他在規范性層面上昨天避之不及和今天趨之如騖的是同一個東西,貌似陷入了自相矛盾,但在元價值學層面上卻始終恪守著“人性邏輯”的同一條原則:想要得到自己喜歡的善,想要避免自己討厭的惡。至于人們經常指責對方“趨惡避善”“為非作歹”,則可以溯源到不同的人在規范性層面上持有的歧異性善惡標準那里:你一直對榴蓮的味道深惡痛絕,當然會覺得我鐘愛榴蓮是在“趨惡避善”了。
不幸的是,或許由于望文生義的緣故,西方學界往往把這種“趨于對自己有利的好東西,避免對自己有害的壞東西”的自利意愿片面地曲解成了只利己不利他,結果潛在預設了“自利在本性上就排斥利他”的前提。例如,霍布斯曾把“善和惡”界定成“表示我們意欲和厭惡的語詞”,并將“自然權益”說成是“每個人按照自己的意欲、運用自己的力量保護自己本性的自由”[1](97、121),已經相當清晰地指認了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具有趨善避惡的自利意愿。但如前所述,他同時又將元價值學維度上的這種人性邏輯扭曲為規范性維度上的利己主義,把“按照自己的意欲保護自己的本性自由”說成是“做自己認為對于保全自己生命最有利的事情”,認為“保全自己生命”總是與“做有利于他人之事”相互對立的,結果將利他的動機排斥在“人人自利”的“自然法”之外了。至于心理利己主義否定利他主義的種種論證,并沒有從霍布斯落入的這個陷阱里走出來,所以才依然建立在“人人只關注自己利益”的基點之上。
然而,直面現實很容易看出,這類曲解忽視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在日常生活中,一個人在遵循趨善避惡的人性邏輯從事行為的時候,既能把那些只是單純對自己有利而與他人沒有直接關聯的好東西當成自己意欲的善來追求,也能把那些對他人有利的好東西當成對自己也有利因此自己也意欲的善來追求——或者說把對他人的好(滿足他人的某些需要)也當成對自己的好(滿足自己的利他需要)來意欲,從而在自利(self-interested)意愿中互不排斥地將利己(selfish)與利他(altruistic)這兩種指向不同的行為動機兼收并蓄。換言之,元價值學意義上的自利人性本來就是把利己之善與利他之善一并當成“自我利益”來意欲的,根本沒有在它們之間設置某種勢不兩立的二元架構。無論如何,像下面這類蘊含在自利意愿中的利他動機及其引發的行為,可以說是人生在世再普通不過的日常現象了:我覺得榴蓮好吃,因而希望身為朋友的你也能享受它的美味,于是出于這一動機(并非為了賣掉自己的積壓貨物)鼓勵你品嘗它,甚至不惜自己花錢買一個送給你,并且沒有打算想要得到你的對等回報,從而體現出連霍布斯也承認的“為他人好”這種“善良的自然人性”。
細究起來,導致西方學者面對如此簡單的人生現象犯下如此低級的邏輯失誤的一個直接原因,可能是他們未能在最廣泛意義上理解人性邏輯的自利之“利”,而傾向于將其限定于自己在實利領域里意欲的“單純對自己有利”,卻把自己在道德領域里同樣意欲的“對他人有利”排除在外了。例如,與休謨相似,斯密在《道德情操論》的開篇處曾指認了利他之心是普遍性地包含在自利意愿中的:“無論我們假定人是怎樣地自私,在其自然本性中都明顯有某些原則促使他關心他人的命運,把他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雖然除了看到他人的幸福感到高興之外自己一無所得。……即使最殘忍的惡棍和最冷酷的罪犯也不會完全沒有這種感覺。”[7](P5)可是,大概是由于把“利”狹隘地理解成了實利,斯密并沒有將“看到他人的幸福感到高興”的利他因素也看成是一種與“因為自己的幸福感到高興”的利己因素相似的自利意愿,反倒基于前者除了讓自己高興之外“一無所得”的理由把它排除在自利的意愿之外,未能意識到“看到他人的幸福感到高興”正是利他之心構成自利意愿的內在要素的直接體現:一個人把他人的幸福也當成了自己同樣意欲、實現后同樣能讓自己快樂的好東西來追求(為他人的幸福感到高興),至于自己在實利領域的一無所得并不會因此就把這種道德領域的快樂之“利”化為烏有。就此而言,斯密可以說是在已經觸摸到事實真相的那一刻,又在二元對立架構的影響下,讓事實的真相在概念不清中從手邊溜走了。
那么,人們在自利的意愿中為什么會形成利他的動機呢?只要如實理解了趨善避惡的人性邏輯,拋棄了片面扭曲的二元對立架構,回答這個貌似棘手的問題也不是那么困難,因為其形成機制與利己動機的形成機制根本一致:如同人們在一己性的個體生活中會產生利己的需要一樣,他們在人際性的社會生活中也會產生利他的需要,從而或者基于生理的本能或者源自后天的教化或者憑借兩者的結合產生利他的動機,以維系自己與他人在各個領域尤其是道德領域的共同存在。例如,父母對子女的“為你好”的利他性關愛,既可以上溯到許多動物養育幼仔的生理模式那里,又受到了人類文明的教化熏陶。再如,基于利己性自愛以及利他性親子之愛的延伸擴展,人們同樣也會產生愛友鄰、愛同胞、愛人類的更廣泛動機,甚至最終結晶成“讓世界充滿愛”的理念。
有鑒于此,哪怕考慮到被利之他做出回應的復雜程度(如你因為極度厭惡榴蓮味道的緣故,覺得我的推薦是“好心辦壞事”等),我們也沒有理由像霍布斯那樣以走極端的口吻斷言,人人都會按照自己的意欲去做對自己有利事情的自然法必然導致“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只有基于利己的動機簽訂了轉讓自然權益的理性契約,才能防止毀滅性的叢林狀態。相反,由于利他動機同樣構成了自利意愿的組成部分,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系在包含無可否認的沖突一面的同時(霍布斯的學說主要彰顯了這一面),還包含著無可否認的和諧一面:不僅我有可能從事有利于你滿足需要、維系存在的行為,你同樣有可能從事有利于我滿足需要、維系存在的行為。所以,人生在世在不斷發生“許多人對許多人的戰爭”的同時,也會存在“許多人對許多人的關愛”,絕無可能形成“每個人對每個人像狼”的局面——其實就是在自然叢林(而非人們構想)的狼群里,每只狼雖然對獵物很“殘暴”,彼此間卻依然會維系某種協同互助的團結友誼。嚴格說來,指出了人也有“為他人好”的“善良人性”的霍布斯也不是不知道這一點,因為他坦率承認:“就具體個人而言,人人相互開戰的狀態任何時候都不存在。”[1](P96)不過,或許是想要維持理論上的自洽一貫,他既沒有指出為什么會形成這種不符合自然法的“反常”現象的原因,也沒有察覺到他自己從自然法到契約論的推演因此留下了怎樣的邏輯漏洞。更遺憾的是,西方主流學界似乎直到今天還是沒有自覺地意識到:霍布斯以及其他許多學者依據所謂“自然法”指認的只利己不利他的“自然人性”,實際上既不“自然”也非“人性”,反倒包含著基于“文明”的嚴重扭曲。
綜上所述,利他動機在人類生活中的實然性存在其實是無法否認的。相反,一旦打破了那種子虛烏有的二元對立架構,我們很容易發現:利他的動機與其說是和自利的人性背道而馳的,不如說如同利己的動機一樣也是順性而為的。
三、利己與利他的沖突和權衡
在肯定了利他動機與利己動機在自利意愿中的共同存在之后,我們可以進一步從實然性描述的視角辨析二者之間既沖突又和諧的復雜關系,由此揭示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在現實生活中的生成機制了。
比較而言,二者之間的和諧關系要簡單一些,集中表現在:人們能夠互不妨礙地實現自己意欲的利己之善和利他之善,在許多情況下達成了某種善還會有助于達成另一種善。例如,我對你的尊重惠助得到了你的善意回報,讓我也在某些方面獲益匪淺;你基于利己的賺錢動機獲得了大筆財富,能夠讓你積極實現利他的慈善意圖等。再如,斯密在把經濟行為解釋成單純基于主觀利己動機而只是出乎意料地達成了客觀利他后果的時候,就忽視了經濟行為可以具有倫理德性的關鍵一點:經營者雖然受到了發財致富的利己動機的支配,但同時也懷有積極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利他動機,并且在兩者的和諧統一中憑借利他之善的工具效應,實現了利己之善的最終目的。同時,如同人際關系中的類似情況一樣,雖然我們不應當像霍布斯那樣在理論上一筆勾銷這種和諧關系的實然性存在,在實踐中卻的確沒有必要為它操心費神,因為它不會給人們帶來任何實質性的麻煩。不管怎樣,倘若利他與利己之間不相抵觸,沒有誰會想要放棄其中的任何一種善:鑒于兩種好東西統統屬于可欲之善的自我利益,既然可以兼得,何樂而不為呢?
人們在這方面遇到的實踐和理論上的麻煩,主要來自利己與利他之間不可兼得的張力沖突:雖然二者對人們來說都是可欲之善,但由于種種原因卻沒法同時實現,比方說你在把利他的動機變成利他的行為時,就要花費自己的時間、精力或金錢,從而造成你自己的損失;要是我在競爭中為他人提供了贏利的機會,我自己就可能會失去贏利的機會等等。就此而言,利己與利他這兩種自利之善之間的張力沖突,構成了一己個體通常遇到的“諸善沖突”的典型表現(在道德領域里尤為突出),并且因此會迫使他不得不做出“有得必有失”的取舍選擇,結果生成所謂“善惡交織的悖論性結構”:要是為了利他放棄利己,就會在讓他人獲益的同時導致不想受害的自己遭受損害;要是為了利己放棄利他,又會在讓自己獲益的同時導致自己不想加害的他人遭受損害,從而陷入左右為難的局面。說穿了,人生在世的所有不順心之事,都是由于這樣那樣的沖突而非和諧的原因造成的:“既要……又要”的圓滿愿景無疑是十分浪漫,實現了更屬于心想事成的美夢成真,但在諸善沖突的情況下注定了只能是烏托邦式的鏡花水月。
在這類可以說是無法避免的沖突情況下,人性邏輯的另一條原則“取主舍次”就將發揮效應了:面對兩種好東西不可兼得的局面,人們會把哪一種善看得更重要,以致為了防止失去它勢必生成的不可接受之惡,不惜放棄另一種次要善并且因此忍受對應的次要惡呢?[9]例如,要是在權衡比較了兩種好東西在質上的主次輕重之后(并非西方學界所強調的在量上的大小多少),我認為利己之善的重要性超過了利他之善,我就會做出為了利己放棄利他的選擇,亦即為了不讓自己遭受損害而讓他人付出遭受損害的代價;相反,倘若你覺得利他之善的重要性超過了利己之善,你則會做出為了利他放棄利己的選擇,亦即為了不讓他人遭受損害而讓自己付出遭受損害的代價。不錯,日常生活的實際情況遠為復雜,像許多時候人們的權衡比較并非總是憑借工具理性的清醒計算展開的,也有可能是在人生理念積淀下的一時沖動中完成的;張三在對待李四的時候把利他置于了利己之上,在對待王五的時候又把利己置于了利他之上,等等。但不管具體的場景如何糾結變化,取主舍次的人性邏輯總是貫穿其中的,就像它在一個人面臨當下偏好與長遠利益、感性欲情與理性目標的類似沖突時也會起作用一個樣。
表面上看,為了利己放棄利他的自利選擇似乎比較容易理解;相比之下,要澄清為了利他放棄利己的自利機制,卻好像會遇到嚴重的困難,因為這樣的取舍不僅僅是利他,而且同時還包含著“害己”的因素,在冒著生命危險救助他人的情況下尤其會陷入某種自相矛盾:要是你連自然法特別看重的自己生命都失去了,怎么還能談得上是“自利”的呢?但深究起來,這種困惑仍然受到了二元對立架構的誤導,沒有看到人們在做出后一類選擇的時候,只不過是把自己意欲的利他之善置于了自己雖然同樣意欲、地位卻不如前者那么重要的利己之善乃至生命之善之上,所以根本沒有違反趨善避惡、取主舍次的自利人性:他們把利他看成是比利己或生命更重要的自我利益。事實上,在單純基于利己動機從事的行為中也會出現類似的自相矛盾:人們在酗酒抽煙或深山探險的時候,也是在冒著失去自己生命的危險,但這當然不意味著他們的這類行為因此就違反了自然人性而不再是基于自利意愿的了;毋寧說,他們只不過是把自己意欲的酗酒抽煙或深山探險之善看得比單純維系生命之善更重要罷了。從這個角度看,霍布斯主張“自然法……禁止人們不去做自己認為對于保全自己生命最有利的事情”,已經包含著“自己生命至高無上”的規范性片面扭曲了。
進一步看,撇開現實中也存在的“害他”動機不談,嚴格意義上的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是不會在單純基于利己動機從事行為或利己與利他保持和諧的情況下出現的:在單純基于利己動機從事行為而不涉及他人的情況下,不管一個人是把酗酒抽煙看得更重要還是把身體健康看得更重要,他的行為都只是單純“利己”的,談不上與“利他”的對立沖突,因此也沒有以“利己”為“主義”的內涵;在利己與利他保持和諧的情況下,一個人從事的行為則總是呈現出鮮明的“互利主義”特征。所以,嚴格意義上的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只會在兩種動機相互沖突的時候產生:在無法兼得的兩難困境中,人們再去期盼美美與共的“圓滿之好”就沒有意義了,只能退而求其次地考慮如何達成“正當之對”的問題,試圖按照“放棄次要善以確保重要善(基本善)、忍受次要惡以防止嚴重惡(基本惡)”的行為底線克服二者的張力,最終得出利己與利他哪一種善才是自己認同的為“主”之“義”(“主要義務”)的不同結論:為了利己放棄利他自然就是利己主義,為了利他放棄利己則無疑是利他主義。換言之,按照利己主義的行為底線,以利己壓倒利他是可以接受的,以利他壓倒利己是不可接受的,而按照利他主義的行為底線卻截然相反。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如同利己與利他的動機一樣,不管利己主義還是利他主義,都完全符合元價值學意義上趨善避惡、取主舍次的人性邏輯,因此也都是可能的。心理利己主義指責利他主義違反了“自然人性”無法成立,僅僅是因為它執著于二元對立架構將利他的動機排除在自利的意愿之外了,沒有看到像為了救助他人不惜舍棄自己生命這樣的激進利他主義得以立足的前提依然在于:人們完全可能依據自己的人生理念,在沖突情況下把自利意愿中的利他動機凌駕于利己動機乃至自己的生命之上,從而以利他主義的方式遵循自然人性的內在邏輯實現自己的自利意愿。
應該承認,二元對立架構也從某個角度折射出了利己與利他的現實沖突,因為假如兩者之間總能保持和諧統一的話,它壓根就不會產生了。但問題在于,這種架構又把二者之間具體的現實沖突扭曲成了抽象的概念對立(邏輯上就不兼容而相互排斥),斷言自利的意愿中只有利己的動機沒有利他的動機,結果反倒嚴重遮蔽甚至干脆否定了這種現實的沖突,在抽去自己立足的現實基礎的同時走進了理論上自敗的死胡同,無法揭示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為什么會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關鍵機制。限于篇幅,在此僅僅簡要地分析一下兩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是美國作家安·蘭德。她為了提倡“理性的自私”,明確主張“理性的人們之間沒有利益的沖突”,因為只有不會造成沖突的才是理性客觀的善。由此出發她宣稱,理性的人們可以只追求自己的私利而不會傷害到他人,亦即“既不能為了他人犧牲自己,也不能為了自己犧牲他人”,甚至認為像人們在危急時刻冒著一定風險救助陌生人這類明顯是利他主義的行為也屬于利己主義的范疇[10](P17-21、36-46)。毋庸諱言,憑借這種混淆概念、漏洞百出的論證,當然可以讓自私或利己主義升華成某種德性了;但問題在于,假如為了陌生人的利益不惜讓自己冒風險的做法也有資格算是利己主義的話,人生在世哪里還可能存在她指責的那種應當貼上“道德食人主義”的駭人標簽的利他主義呢?
第二個案例是美國哲學家托馬斯·內格爾。他曾試圖憑借分析哲學的嚴謹方式,通過與審慎德性的類比以論證利他主義的可能性。但奇怪的是,他不僅在討論審慎德性的時候很少深入探究當下偏好與長遠利益的沖突,而且在討論利他主義的時候也很少深入探究利己與利他的沖突,反倒聲明自己在考察“利他的理由體系”時,“把所有涉及到分配自己利益和他人利益相互權衡的問題放在了一邊”。結果,在二元對立架構的積淀性影響下,內格爾也將自利與利己混為一談,一方面把利己主義片面地定義成“行為理由的唯一來源在于行為者的利益”,沒有看到利他的動機也能構成“行為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又空泛地宣稱:作為行為的理性要求,利他主義可以從“不涉及他人利益就能說明的形式化原則”中推演出來,主要“依賴于對他人實在性的全面認識”,卻與行為者的利益等感性的欲望情感沒有多少關聯[11](P86-96)。就此而言,內格爾其實只是籠統地指認了利他動機是怎樣從“自己和他人都是人”的形式化理性認知之中生成的,并沒有深入揭示與利己主義相對而言的利他主義如何可能的真正理據:人們在自己利益與他人利益的現實沖突中,基于自利的本性展開了權衡比較,最終賦予了利他的動機比利己的動機更重要的“權重”。
因此,單從這兩個案例已經可以看出,一旦執著于二元對立架構而不愿正視利己與利他的張力沖突以及權衡比較,很容易把利己主義或利他主義(人人都應當更看重利己或利他之善)等同于利己或利他的動機本身(人人都有利己或利他的自利意愿),結果不僅扭曲了利己與利他動機的互動關系,而且也難以揭示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產生根源和實質訴求。
四、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的道德屬性
既然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同樣符合元價值學層面的人性邏輯,它們在有沒有人性方面的二元對立可以說就不復存在了。那么,從實然性描述的角度看,它們在有沒有德性方面的二元對立是不是有根有據的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本來,假如利己與利他能夠維系完美的和諧狀態,彼此間不存在任何沖突,也不會對任何人造成傷害,它們在道德領域內對于任何人來說都將只有正面價值,沒有負面效應了。但這樣一來,道德自身也就變得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因為人們在這樣的和諧狀態中不會產生道德方面的任何需要:既然沒有任何人任何事是不道德的,干嘛還要勞神費力去追求有道德呢?所以,撇開現實中存在的害他動機不談,只有當利己和利他在沖突情況下產生了害己或害他的悖論性后果時,它們才可能在不道德的負面反襯下呈現出有道德的正面價值。就此而言,抓住利己與利他在諸善沖突以及人際沖突的狀態下對于主體和他人分別具有的善惡交織的悖論性效應,構成了我們如實揭示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復雜道德屬性的關鍵;相比之下,西方學界恰恰又是由于憑借抽象概念上的二元對立否定了日常生活中的現實沖突的緣故,分別給利己與利他貼上了不道德與有道德的僵化標簽,才扭曲了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具有復雜道德屬性的本來面目。
先來看利己主義的情況:一個人如果在沖突中將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的利益之上,他自己一般會認為這樣做是合乎道德的,否則他也不會在權衡比較之后依然想要從事這個利己主義的行為了。不過,受到這個行為傷害的人以及許多奉行利他主義原則的人,卻通常會認為它是不道德的。更有反諷意味的是,要是就受害之他這方面看,如果他們也奉行利己主義的原則,肯定會憑借自己受害的理據對于這個利己主義行為做出否定性的評判(雖然他們對于自己從事的傷害他人的利己主義行為不會做出這樣的評判);相比之下,倘若他們持有利他主義的態度,反倒有可能容忍這個行為對自己的傷害,不對它做出否定性的評判,有時還會以所謂“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心態,認可甚至贊許這個行為對自己的傷害。就此而言,恰恰由于現實沖突所導致的悖論性交織的緣故,同一個利己主義的行為對于不同的人也會呈現出截然相反的道德屬性,沒法得出一刀切的結論。
從這個角度看,像安·蘭德那樣聲稱利己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德性,只能建立在一個錯謬的前提上:以無視沖突的方式聲稱利己主義行為根本不會導致“為了自己犧牲他人”的后果。然而,當德里克·帕菲特把利己主義界定成“一個理性的行為者應當賦予自己的利益以至高無上的權重,其他人無論付出什么樣的代價都不足惜”的時候[12](P281),他已經指出了關鍵的一點:利己主義行為在實現主體自己的利益時肯定會讓他人付出受害的代價,而這也正是利己主義者們在奉行同一條倫理原則的情況下,為什么還會彼此開戰處于叢林狀態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像休謨等人那樣斷言利己的行為根本缺乏道德價值或違反了正義,也是片面的。問題在于,倘若我們把他們不約而同地指認的“不可害人”原則看成是一條適用于每個人的正義標準的話,那么,一個人為了捍衛自己的應得利益不受他人侵害的舉動,雖然在元倫理學層面上也屬于將利己凌駕于利他之上的利己主義行為,并且還會妨礙實施侵害行為的那個(他)人達成其不應得的利益,以致有可能被某些人特別是施害之他貶斥為只利己不利他的不道德,但如果從尊重人權的規范性視角看,卻是完全正義和符合道德的。例如,張三在禁煙場所出面制止李四抽煙以保護自己的健康,雖然也是一種阻礙了李四滿足自己抽煙的需要或利益的利己主義(而非利他主義)舉動,但同時又是捍衛自己正當權益的正義行為,并不會因為具有“損(他)人利己”的元倫理學特征就失去了積極正面的規范性道德價值。再如,商人為了自己長久贏利做到了童叟無欺,不僅在當下偏好與長遠利益的沖突中克制(而非放縱)了利己的動機,同時也在自己致富與尊重他人的沖突中守住(而非突破)了不可坑蒙拐騙的正義底線,因此具有不容否認的真正道德價值。事實上,康德斷言這類利己的行為盡管值得稱贊,卻又缺乏道德價值,在邏輯上也是自相矛盾的:倘若它們原本不具有“不會傷害任何人還幫助了某些人”的正面價值,人們憑什么要在道德上稱贊它們呢?難道人們在道德上稱贊它們的頭號理據,不就是因為它們符合康德自己特別強調的“人是目的”的絕對命令嗎?從中不難看出,一旦受到了二元對立架構的誤導,就連康德這樣嚴謹的思想家也會像安·蘭德那樣陷入莫名其妙的邏輯錯謬之中。
再來看利他主義的情況:一個人如果在沖突中將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不僅他自己和被利之他,而且其他許多人(包括某些自己不愿從事利他主義行為的利己主義者),通常都會認為這種寧肯害己也不害他的做法在道德上是高尚的。這也是“舍己為(他)人”的行為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受到廣泛贊許的機制所在,以致就連把利他主義貶為“道德食人主義”的安·蘭德也不敢與人們的這種日常直覺正面對抗,而不得不把冒險幫助陌生人的行為劃歸利己主義的范疇給予肯定。不過,撇開另一些利己主義者很可能嘲諷利他主義行為屬于犯傻的現象不談,在以下幾種情況下,其他許多人同樣會對這類行為做出歧異性的倫理評判,從而展現出利他主義在人際沖突中具有的復雜道德屬性,因此我們也沒有理由像休謨等人那樣,一概而論地斷言它們總是高尚優越的有德性行為。
第一,倘若被利之他并不認為某個利他主義行為的后果對于自己具有可欲之善的價值,那么,在他看來這個行為就不見得是有道德的,相反還可能是不道德的。像子女有時會反感父母出于“為你好”的動機從事的關愛舉動,就折射出了利他主義“好心辦壞事”的這種悖論性特征。
第二,倘若一個人的利他主義行為讓自己受到了嚴重傷害,哪怕他自己認為這樣做具有“舍己為(他)人”的優越德性,也還是有可能被另外某些人視為不道德的。例如,張三對李四百依百順到了甘愿受虐的地步,從元倫理學視角看當然也可以說是利他主義的:自己不惜付出一切代價也要讓李四感到滿意;可是,許多旁觀者卻會覺得張三的這種利他主義行為類似于放棄人格尊嚴的奴才。剛才提到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現象,不妨也作如是觀。
第三,倘若一個人的利他主義行為在有利于某些他人的同時又傷害了另一些他人,更是會因為這種“利此損彼”的悖論性特征在道德屬性上發生致命的斷裂:一方面被利之他會認為這個行為是有道德的,另一方面受害之他卻會認為這個行為是不道德的。以斯密舉出的惡棍和罪犯為例:他們對于自己團伙中人的無私奉獻、傾情關愛當然會受到后者的贊許,但遭受這些團伙不義侵害的其他人,對于這類“盜亦有道”的利他主義舉動卻很可能做出相反的評判。
無需細說,日常生活的實際情況遠比剛才辨析的幾種類型復雜糾結得多。不過,撇開其中的哪一種具體評判更能得到證成的應然性話題不談,上面的討論足以提醒我們:無論在實然性描述的維度上,還是在規范性訴求的維度上,我們都沒法給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貼上某種一成不變、普遍適用的倫理標簽,斷言它們單純因為利己或利他的特征本身就是不道德或有道德的。
綜上所述,西方學界在利己與利他問題上的致命失誤在于,由于沒有仔細辨析自利的內涵而將它混同于利己卻將利他排除在自利之外,結果在強調利己與利他之間子虛烏有的概念對立的同時,又遮蔽了二者在日常生活中不僅無從回避而且意義重大的現實沖突,最終通過這種把不可兼得的現實沖突扭曲成互不兼容的概念對立的邏輯謬誤,制造了利己主義“有人性無德性”而利他主義“無人性有德性”的怪誕悖論。有鑒于此,我們只有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打碎在人性和德性維度上都不存在的二元對立架構,另一方面正視利己與利他之間復雜糾結的現實沖突,才有可能克服這些理論上的怪誕悖論,澄清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產生根源和實質訴求。事實上,不僅在利己與利他的關系問題上,而且在事實與價值、善與正當、自由意志與因果必然的關系問題上,我們都能發現類似的情況:西方主流學界由于執著于抽象概念的二元對立架構,無法澄清它們的語義內涵,往往將現實生活中一些不難理解的日常現象神秘化,結果將它們變成了眾說紛紜的千古之謎。所以,我們很有必要打破對于西方哲學的盲目崇拜,憑借嚴謹細致的學術批判,深入揭示西方著名哲學大師也免不了會陷入的種種悖論,找到這些千古之謎的謎底,為人類哲學的發展做出我們自己的理論貢獻。
[注 釋]
①出于行文統一的考慮,本文在引用西方譯著時會依據英文本或英譯本有所改動,以下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