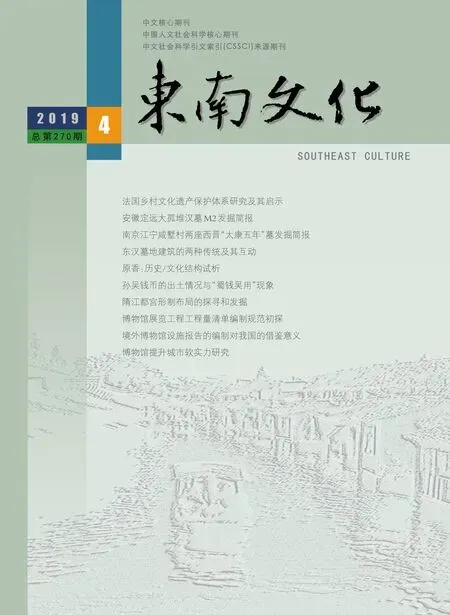博物館提升城市軟實(shí)力研究
鄭 奕
(復(fù)旦大學(xué)文物與博物館學(xué)系 上海 200433)
內(nèi)容提要:博物館對城市發(fā)展有短期和長期效應(yīng)之分。短期效應(yīng)可定量,也往往有形;長期效應(yīng)可定性,但無形,并涉及軟實(shí)力中的概念,包括博物館提升城市教育及創(chuàng)新價值、構(gòu)建地方特色與城市形象、培育地方身份認(rèn)同和公民意識等。博物館對城市軟實(shí)力的提升因?yàn)闊o法用定量數(shù)據(jù)衡量,常常為大家所忽略,但這絲毫不影響博物館為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作出的巨大貢獻(xiàn),并且在當(dāng)下值得更多關(guān)注。因此,我們要通過摒棄“同質(zhì)化”,構(gòu)建城市“文化型規(guī)劃”,善打博物館“文化牌”和創(chuàng)設(shè)“文化公地”等舉措,促使博物館助力城市軟實(shí)力提升。
一、城市軟實(shí)力概念界定
軟實(shí)力(soft power)由政治學(xué)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于1990年率先提出,它主要用來描述基于非軍事或經(jīng)濟(jì)實(shí)力的國際關(guān)系。武力和財(cái)政等有形資源、可外化為物質(zhì)力量的實(shí)力往往被稱為硬實(shí)力(hard power)。相比之下,軟實(shí)力是一種無形資源,諸如理念、知識、價值觀和文化等,但絕對是一種可以影響他者行為的能力[1],并內(nèi)化為精神動力。近年來,軟實(shí)力作為重要的國家力量被提到我國國家戰(zhàn)略的高度。其柔性特質(zhì),較之硬實(shí)力容易被對手接受,而不產(chǎn)生激烈的對抗反應(yīng)[2]。
英國文化協(xié)會(The British Council)在2013年的《影響力與吸引力:21世紀(jì)的文化和軟實(shí)力競賽》(Influence and Attraction:Culture and the Race for Soft Power in the 21stCentury)報(bào)告中明確了“軟實(shí)力”與“文化”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3],并涉及廣播和教育機(jī)構(gòu)、非政府組織、企業(yè)、基金會及信托機(jī)構(gòu)等,其中也包括博物館。毋庸置疑,博物館促進(jìn)了城市文化建設(shè)并進(jìn)一步提升其軟實(shí)力,同時在經(jīng)濟(jì)社會的方方面面產(chǎn)生輻射效應(yīng)。
從世界范圍看,幾乎有城市的地方就有博物館。對許多城市而言,知名博物館往往是游客最多的文旅景點(diǎn)之一。當(dāng)下,博物館正從軟實(shí)力建設(shè)的邊緣不斷被推向中心[4]。事實(shí)上,全球博物館都在尋找自身的新角色、新責(zé)任和新期望,致力于助推城市軟實(shí)力,即長期效應(yīng)的提升。
二、博物館之于城市軟實(shí)力的意義和價值
并非所有博物館之于城市的影響力都能用金錢衡量,用數(shù)據(jù)說話,因?yàn)橛卸唐诤烷L期效應(yīng)之分。短期效應(yīng)是指博物館帶來的直接或間接、與城市經(jīng)濟(jì)有關(guān)的貢獻(xiàn);該效應(yīng)有形,相較于長期效應(yīng)也更容易衡量,因此可定量評估。而博物館之于城市的無形、長期效應(yīng),則直指軟實(shí)力概念。因?yàn)闊o法用定量數(shù)據(jù)衡量,常常被大家忽略,但這絲毫不影響博物館為城市可持續(xù)發(fā)展作出的巨大貢獻(xiàn),包括提升城市教育及創(chuàng)新價值,構(gòu)建地方特色與城市形象,培育地方身份認(rèn)同、公民意識等,因此在當(dāng)下值得我們更多關(guān)注。
1.博物館提升城市教育及創(chuàng)新價值
目前,業(yè)內(nèi)外對博物館評估的一項(xiàng)共性指標(biāo)是基于觀眾數(shù)量,包括我國各級博物館運(yùn)行評估指標(biāo)體系。這類數(shù)據(jù)容易計(jì)算、獲得并且可在機(jī)構(gòu)之間比較。如果觀眾數(shù)量尤其外地游客數(shù)量增加,博物館之于城市的短期效應(yīng)就會放大。但是,博物館生存與發(fā)展的主要目的并非經(jīng)濟(jì)產(chǎn)出,而是生產(chǎn)、傳播知識,基于實(shí)物資源培養(yǎng)教育和創(chuàng)新價值;并且,這些定性價值比短期影響力擁有更強(qiáng)大的、助推城市轉(zhuǎn)型的作用。
時下,越來越多的博物館通過與所在城市以及周邊的大中小學(xué)、科研院所等合作,將博物館納入青少年教育體系以及融入全民教育和終身教育,而這恰恰是“將博物館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的核心要義。目前,上海市開展的“文教結(jié)合”工作是對大部分博物館所屬的“文化”系統(tǒng)與大部分學(xué)校所屬的“教育”系統(tǒng)合作的一大制度設(shè)計(jì),實(shí)屬全國創(chuàng)新。而這些都富有“地方創(chuàng)生”(placemaking)效應(yīng),即可以培育更和諧的人地關(guān)系。因?yàn)楹玫纳鐣慕叹跋髮τ诟纳瞥鞘型顿Y環(huán)境、吸引外資、提升文化產(chǎn)業(yè)競爭力等將產(chǎn)生推動作用,從而形成更大的人財(cái)物集聚效應(yīng),同時各方皆從該優(yōu)質(zhì)環(huán)境中受益。
事實(shí)上,美國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本身就是一個生動的“紐約故事”,該館伴隨所在城市從野蠻走向文明,從混亂走向繁榮。1872年,在博物館開放之初,紐約如同文化沙漠,充斥著移民帶來的混亂腐敗和黑幫活動。但該館始終定位于“全球視野”和“藝術(shù)教育”,吸收世界多元文化,同時給美國公民提供藝術(shù)教育,提升素養(yǎng)。這不僅推動了不同文明間的理解和交流,也助力紐約成為世界文化中心。近150年過去了,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依然在打造一個“全球城市”中的“全球博物館”,并與時俱進(jìn)地譜寫博物館和城市間共發(fā)展的故事[5]。
當(dāng)然,城市教育和創(chuàng)新價值的提升通常只能在中長期內(nèi)顯現(xiàn),而且挺難去證實(shí)并衡量。但博物館和其他文化資產(chǎn)一樣,對建立認(rèn)同、人格、態(tài)度、工作動力、創(chuàng)造力等至關(guān)重要,而這些因素對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都非常關(guān)鍵[6]。事實(shí)上,對博物館提升所在城市軟實(shí)力的評估,也存在延遲效應(yīng)的問題,但延遲并不代表不存在,反而預(yù)示著更為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長久力量。
2.博物館構(gòu)建地方特色與城市形象
博物館常常是所在城市的地標(biāo),這不僅在當(dāng)下,在歷史上亦是如此。近年來,幾乎每個主要城市在都市更新改造過程中都把建設(shè)一座標(biāo)志性博物館納入規(guī)劃。這也解釋了為何我們?nèi)绱俗⒅夭┪镳^建筑設(shè)計(jì),因?yàn)檫@是彰顯地方文化特色、形象的一大門面。當(dāng)然,建筑永遠(yuǎn)是舞臺,博物館的主要任務(wù)依舊是展覽、教育等公共文化服務(wù)輸出。而在全球化、現(xiàn)代化、工業(yè)化的大潮中,我國各地不乏博物館千館一面、城市千城一面的尷尬局面,這樣的同質(zhì)化恰恰給博物館如何助力地方特色與城市形象構(gòu)建提出了新課題。
其實(shí),城市文化發(fā)展必須有自己的堅(jiān)定立場,包括對博物館建設(shè)的理解、詮釋,不宜求大求全、甚至向他者無限靠攏等。2006年,由貝聿銘先生設(shè)計(jì)的江蘇蘇州博物館新館開放,其建筑萃取傳統(tǒng)蘇式園林精粹,并與現(xiàn)代建筑之美融合。此外,從連續(xù)四年的“吳門四家”展覽盛典到當(dāng)代藝術(shù)的全新呈現(xiàn),都綜合形成了這座博物館的獨(dú)特性格,理所當(dāng)然地促使其成為蘇州的“金字招牌”。
的確,除了彰顯地方特色,博物館也助力城市形象的構(gòu)建,而形象正是城市重要的無形資產(chǎn),是軟實(shí)力的體現(xiàn)。該長期效應(yīng)的發(fā)揮與“地方創(chuàng)生”即培育和諧的人地關(guān)系亦直接相關(guān),但重點(diǎn)在于城市品牌建設(shè)及民眾對其的認(rèn)知,無論他們是居民還是游客。可以說,博物館培養(yǎng)了我們的集體想象力,比如將一座知名的博物館與其所在城市的印象勾連。設(shè)想一下,如果意大利烏菲齊美術(shù)館(The Uffizi Gallery)不在佛羅倫薩,如果美國史密森博物學(xué)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不在華盛頓,那么我們對這些城市的認(rèn)知就會遜色。正如大部分游客都將參觀史密森博物學(xué)院視為他們?nèi)トA盛頓特區(qū)朝圣行程的主要組成部分。
目前,我國已將原文化部(包含國家文物局)、國家旅游局的職責(zé)合并,組建了文化和旅游部。這一方面是為了統(tǒng)籌文化事業(yè)、文化產(chǎn)業(yè)發(fā)展和旅游資源開發(fā);另一方面也通過博物館、文化遺產(chǎn)與旅游目的地的結(jié)合,提高中華文化軟實(shí)力,增強(qiáng)文化自信。俄羅斯冬宮博物館(The Hermitage Museum)館長彼得洛夫斯基(Mikhail Borisovich Piotrovsky)說:“最好的博物館,不僅展示民族和國家的基因,還呈現(xiàn)這種基因的活力和質(zhì)量。”[7]事實(shí)上,在我國最新版的《博物館定級評估標(biāo)準(zhǔn)》[8]中已有“旅游影響力”指標(biāo),它主要“參考三年內(nèi)國內(nèi)外大型知名旅行社推出的固定旅游線路上是否將該博物館作為推薦景點(diǎn)來確定”,并依據(jù)“國際/國內(nèi)/省內(nèi)旅游推薦景點(diǎn)”分別計(jì)分。同時,在“博物館公眾影響力”指標(biāo)中,也根據(jù)“國外、境外觀眾人次”以及“國內(nèi)異地觀眾占年觀眾量比例”分別計(jì)分。
3.博物館培育地方身份認(rèn)同、公民意識
博物館一旦與當(dāng)?shù)厣鐓^(qū)、社群互動,就直接或間接創(chuàng)建了一種飽含地方歸屬感的社會肌理與結(jié)構(gòu),而這與博物館助推地方身份認(rèn)同、公民意識構(gòu)建等緊密關(guān)聯(lián)。
史密森博物學(xué)院作為全世界最大的博物館集群,選擇了國立非裔美國人歷史和文化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作為第20座直屬博物館,意義非凡。它是全美第一座全方位展示黑人歷史與文化的博物館,坐落于首都華盛頓,有助于大眾理解并認(rèn)同非裔美國人在美國歷史上常被忽略的杰出貢獻(xiàn),以彌合分歧、緩和對立。因此,它不僅于非裔美國人社群意義重大,于其他人同樣如此;它不僅是華盛頓的新地理坐標(biāo),而且是全美國甚至全世界的新精神坐標(biāo)。
值得一提的是,據(jù)美國《綜合社會調(diào)查報(bào)告》(General Social Survey,GSS)的數(shù)據(jù)分析,參觀博物館等藝術(shù)活動有利于提高公民的參與度、容忍度和無私奉獻(xiàn)精神。且有證據(jù)顯示,博物館所采用的沉浸式講故事方式有利于培養(yǎng)同理心,而包括同理心在內(nèi)的社交情感能力正影響著教育與人生的遠(yuǎn)期發(fā)展[9]。事實(shí)上,在博物館與城市的互動中,民眾的驕傲與自豪感會油然而生。居民會對他們身邊的博物館產(chǎn)生一種近乎“愛國”的情感,尤其是當(dāng)該機(jī)構(gòu)在社區(qū)中產(chǎn)生決定性影響力,甚至在國際上享有盛譽(yù)時。這種軟性因素對非居民同樣發(fā)揮作用,他們會認(rèn)為該城市的居民更有文化、教養(yǎng)、內(nèi)涵等[10]。重要的是,博物館所具有的內(nèi)在優(yōu)勢可以讓其成為時下社會發(fā)展亟需的核心價值觀(如同理心)培育的有效引擎,幫助人們理解“他者”(包括外來者、弱勢群體等),換位思考;同時,引導(dǎo)民眾在行為意識、思想觀念上發(fā)生潛移默化的改變,從而鞏固社會關(guān)系[11],最終升華城市氣質(zhì)。
近年來,我國中央財(cái)政投入巨資持續(xù)推進(jìn)全國五萬余個博物館、紀(jì)念館、美術(shù)館等公共文化設(shè)施向社會免費(fèi)開放[12],而政府不遺余力扶持的出發(fā)點(diǎn)正在于博物館對于地方身份認(rèn)同、公民意識構(gòu)建的重大作用。事實(shí)上,博物館作為歷史保管人,在教育公眾“成為本土公民意味著什么”方面,在提升公眾“認(rèn)知和欣賞不同語言、文化、宗教和種族群組對共同的國家身份認(rèn)同作出的獨(dú)特貢獻(xiàn)”方面扮演了卓越角色。尤其是在一個不同國家和民族間沖突加劇的世界里,博物館的這項(xiàng)功能具有巨大的當(dāng)下價值[13]。
三、博物館如何提升城市軟實(shí)力
1.摒棄“同質(zhì)化”建設(shè),通過博物館講好這座城市的獨(dú)特故事
時下,博物館發(fā)展已成為城市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必要內(nèi)容,是文化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基礎(chǔ),也是衡量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關(guān)鍵指標(biāo)。但如何通過博物館講好這座城市的獨(dú)特故事,一系列原則宜恪守。
首先,我們要摒棄“同質(zhì)化”,矯正短視的發(fā)展觀,制定富有前瞻性的中長期城市文化策略,這其中就包括納入博物館尤其是城市博物館的建設(shè)。自20世紀(jì)80年代開始,我國不少城市陷入建設(shè)國際化大都市的亢奮中,這種冒進(jìn)的行為一方面毀滅了城市原有的傳統(tǒng)和個性(甚至一些著名的歷史城市也難逃此劫);另一方面難以創(chuàng)造新的城市特色和風(fēng)貌。而城市文化的異質(zhì)性、多元性始終優(yōu)于同質(zhì)性。因此,通過城市博物館等窗口來講述這座城市及其市民的獨(dú)特故事,如首都博物館、上海市歷史博物館、廣州博物館等是各地摒棄“同質(zhì)化”、堅(jiān)守其獨(dú)一無二性的要義。
其次,我們要加大博物館與城市聯(lián)動發(fā)展的研究。中國博物館協(xié)會下屬的城市博物館專業(yè)委員會自2007年7月成立以來,始終致力于搭建以研究城市博物館為目標(biāo)的業(yè)務(wù)交流網(wǎng)絡(luò),同時加強(qiáng)館際及與國際博物館協(xié)會(ICOM)的聯(lián)系。此外,2018年5月,南京市人民政府與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江蘇省委宣傳部共同舉辦“第八屆歷史文化名城博覽會”。其中,“首屆國際博物館館長論壇”以“博物館,涵養(yǎng)現(xiàn)代城市文明”為主題。諸如此類的交流平臺和研究型智庫應(yīng)越多越好,后者理應(yīng)在高校、社科院等成立和發(fā)展,同時各館也加強(qiáng)與城市聯(lián)動發(fā)展的研究,以咨政、啟民、育人。
最后,我們要彰顯城市地標(biāo)型博物館的優(yōu)勢,文旅融合,逐步打造城市品牌。這也解釋了為何世界各地不少城市將其主要的文旅資源(如博物館)直接與城市形象捆綁宣傳,甚至是定義,這樣便可在民眾心中建立一種經(jīng)久不衰的城市與博物館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14]。正如西班牙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 in Bilbao)打造了用文化經(jīng)濟(jì)推動城市發(fā)展的現(xiàn)實(shí)案例,創(chuàng)造了用藝術(shù)推動傳統(tǒng)城市轉(zhuǎn)型的奇跡。我國蘇州博物館也歷時數(shù)年醞釀推出其經(jīng)濟(jì)影響力研究報(bào)告,呈現(xiàn)該館之于蘇州市、江蘇省乃至全國的綜合影響力。目前,蘇州博物館正在城內(nèi)打造分館,以形成集群效應(yīng)。因此,如何挖掘博物館的“旅游影響力”,提升“國內(nèi)異地觀眾占年觀眾量比例”,增加“國外、境外觀眾人次”,是促使更多地標(biāo)型博物館誕生并為城市文旅融合作貢獻(xiàn)的佳徑。
2.建立和完善公眾參與機(jī)制,鼓勵企業(yè)、民間投資興辦博物館,構(gòu)建城市“文化型規(guī)劃”
過去,博物館常常處于城市規(guī)劃的邊緣。如今,隨著城市致力于通過塑造文化資產(chǎn)以期在新都市背景下更具吸引力、競爭力、影響力,博物館逐漸成為規(guī)劃的中心。并且,我們提倡“文化型規(guī)劃”。也即,一方面融合眾包眾籌等方式,在城市規(guī)劃和政策發(fā)展中將盡可能多的居民納入,以上下結(jié)合。因?yàn)槭忻袷浅鞘械闹黧w,也是城市文明的創(chuàng)造者和體現(xiàn)者。同時,上下結(jié)合型的遺產(chǎn)保護(hù)努力,比起單純自上而下的舉措更可能成功,也更富有可持續(xù)發(fā)展性。另一方面,“文化型規(guī)劃”意在凸顯文化的意義與價值。這意味著城市各部門在規(guī)劃自身發(fā)展時,清楚意識到實(shí)際和潛在的文化重要性。這樣,整座城市就與歷史、遺產(chǎn)和藝術(shù)包括博物館等結(jié)合在一起,各版塊不再彼此孤立。比如,2013年《芝加哥文化規(guī)劃》(Cultural Plan for the City of Chicago)出爐前,所有市民都被邀請來講述“文化”對他們而言意味著什么;并且,其需求和愿望被轉(zhuǎn)化到一系列項(xiàng)目和計(jì)劃中,同時歷經(jīng)城市預(yù)算和私人領(lǐng)域資助的現(xiàn)實(shí)測試。最終,該規(guī)劃中的36項(xiàng)建議和超過200項(xiàng)舉措被視作全城共有(包括所有城市部門和委員)[15]。
時下,我們不斷把博物館比喻為“城市的客廳”,這是對博物館功能與時俱進(jìn)的全新闡釋。而它們能否真正發(fā)揮作用,包括那些沒有圍墻的博物館,如露天博物館、社區(qū)博物館等,關(guān)鍵在于公眾的參與,在于博物館建立和完善公眾參與機(jī)制[16],以實(shí)現(xiàn)真正的開放性和共享性。因此,為了構(gòu)建和維持適于生存的、充滿“有趣的靈魂”的城市,同時提高博物館的社會貢獻(xiàn)率,一方面博物館必須主動聯(lián)系觀眾,更多了解和研究民眾需求,以提高其幸福度為核心輸出公共文化服務(wù);另一方面,我們呼喚民眾進(jìn)一步參與并規(guī)劃未來,讓他們真切感覺到在城市進(jìn)化故事中能找到祖先、自己和孩子的位置。我們相信,當(dāng)博物館的活動內(nèi)生于大眾需求,與最廣泛的人群產(chǎn)生共振,城市也將充盈人文情懷。
總的說來,我們要把“博物館之都”等城市建設(shè)作為一項(xiàng)全民支持、共建共享的社會事業(yè)[17],包括鼓勵企業(yè)、民間投資興辦博物館,激發(fā)市場活力,釋放政府動能。事實(shí)上,在我國《博物館事業(yè)中長期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1—2020年)》中,早已明確了“以國家級博物館為龍頭、省級博物館為骨干,國有博物館為主體、民辦博物館[18]為補(bǔ)充,類別多樣化、舉辦主體多元化的博物館體系初步形成”的中長期發(fā)展目標(biāo)。而當(dāng)博物館的建設(shè)和運(yùn)營不再只依托政府這一單一渠道,這將促使內(nèi)向型、以館藏為中心的博物館逐步轉(zhuǎn)變?yōu)橥庀蛐汀⒁跃柚胶陀^眾為中心的機(jī)構(gòu),并導(dǎo)向反映多元聲音和影響力的新型管理架構(gòu)[19];同時,還將促成業(yè)內(nèi)外競爭與合作并存的良性狀態(tài),包括文教、文旅甚至是文體跨界合作。畢竟,文化城市不是單純的城市文化建設(shè),而是經(jīng)濟(jì)、政治、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20]。
3.善打博物館“文化牌”,創(chuàng)設(shè)“文化公地”,構(gòu)建有溫度的城市
在城市化加速進(jìn)程中,人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地理坐標(biāo)和功能城市,更是精神坐標(biāo)和人性化的文化城市。
一方面,我們要將博物館發(fā)展從單純的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轉(zhuǎn)向促進(jìn)、激發(fā)各類正面市民活動和事件的發(fā)生,讓博物館嵌入民眾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和地方記憶中。包括城市進(jìn)一步與博物館合作,為市民創(chuàng)設(shè)更多的“文化公地”(cultural common),這是供民眾休閑文化社交、便于企及甚至免費(fèi)享用的區(qū)域。比如,地處澳大利亞墨爾本市中心的聯(lián)邦廣場(Federation Square)是一個開放式多功能市民廣場,每年有近千萬民眾前來參與活動。其露天圓形劇場可容納35 000人,此外還有約44 000平米的文化和商業(yè)建筑,包括維多利亞國家藝術(shù)館(The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澳大利亞動態(tài)影像中心(Australian Centre for the Moving Image)、寶馬露天圓形劇場(BMW Edge Amphitheatre),以及寫字樓、工作室、畫廊等。對聯(lián)邦廣場這一動態(tài)、持久性文化公地的4.5億澳元巨大投資[21],表征了墨爾本對創(chuàng)設(shè)市民空間以為公眾所用的承諾與投入[22]。而通過把“看得到的博物館景觀”和“看不到的城市文化”相結(jié)合[23],將增強(qiáng)博物館等各類公共文化服務(wù)機(jī)構(gòu)的存在感,以共同保護(hù)城市記憶。譬如,上海徐匯濱江將工業(yè)遺存和現(xiàn)代藝術(shù)相結(jié)合,聚集起多家美術(shù)館、展覽館和畫廊,開拓出一條濱江“藝術(shù)走廊”。這就在區(qū)域?qū)用鏋椤吧虾F纸适隆钡木幙椞峁┝藰永矠辄S浦江這條上海的“母親河”增添了溫度。
另一方面,我們要通過博物館等來提升民眾的鄉(xiāng)土情結(jié)維系、文化身份認(rèn)同,包括精神上的歸屬和心靈上的凈化。時下,不少民眾雖置身繁華都市,卻產(chǎn)生“我是誰,我從哪里來”的困惑甚至是身份危機(jī),這與集體記憶的消失、城市面貌的趨同不無關(guān)聯(lián)。事實(shí)上,博物館體驗(yàn)正致力于滿足參與者的個人需求,包括對一份自我定義的證實(shí)。因此,越來越多的歷史文化類博物館通過描繪城市文明、中華文明圖譜,使民眾清晰地了解“我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并最終找到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對話的正確立場和恰當(dāng)位置[24]。2009年10月,我國首座以商幫命名的博物館——寧波幫博物館于浙江寧波開啟,向世人述說了寧波城的百年故事。百余年來,寧波幫是至今仍活躍在海內(nèi)外的少數(shù)商幫之一,它以血緣姻親和地緣鄉(xiāng)誼為紐帶,廣泛分布于64個國家和地區(qū)。而通過該館的平臺對寧波幫展開研究,不僅可以凸顯和培育當(dāng)前寧波城的文化特色,而且有助于加強(qiáng)地方與海外寧波幫的交流和商貿(mào)發(fā)展;更重要的是,向全世界的寧波同鄉(xiāng)貢獻(xiàn)可以守望的心靈家園[25]。
一座文化城市的構(gòu)建與養(yǎng)護(hù)并不是靠所謂的“標(biāo)志性工程”“政績工程”,而是通過民眾對于地方文化的認(rèn)同感與回歸感等精神狀態(tài)來呈現(xiàn),包括其文化信仰和生活信念等。同時,博物館的建設(shè)過程理應(yīng)得到充分利用,因?yàn)檫@不僅僅是一個建筑過程,更是一個文化過程、社會過程,以給予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地域文化、生活習(xí)俗等更多關(guān)注。事實(shí)上,博物館兼具傳統(tǒng)文化內(nèi)涵和引領(lǐng)未來城市文化的雙重屬性,關(guān)乎所在地從“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的進(jìn)化,甚至自身也成為城市復(fù)興的高地。
四、結(jié)語
時下,文化、城市與博物館的關(guān)系越來越緊密,博物館不僅為今天的城市記錄過去,而且為未來的城市留存今天。這一特性決定了博物館必然是城市文化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并促進(jìn)城市軟實(shí)力建設(shè),包括培育市民的集體性格和城市精神等,同時軟實(shí)力的增強(qiáng)也可帶動和輻射全城的自然、人文生態(tài)環(huán)境發(fā)展。
當(dāng)然,并非所有博物館之于城市的影響力都有形或可度量,博物館的軟性貢獻(xiàn)有時只能通過間接方式并歷經(jīng)時間考驗(yàn)才能顯現(xiàn),但是,博物館已被證實(shí)有職責(zé)及能力去助力城市軟實(shí)力的提升。并且,伴隨時代變遷,博物館還將擔(dān)負(fù)起新的使命——將傳統(tǒng)文化與時代精神融為一體,向著“為社會和社會發(fā)展服務(wù)”的總目標(biāo)不斷邁進(jìn)。
[1]Gail Dexter Lord,Ngaire Blankenberg.Cities,Museums and Soft Power.The AAM Press,2015:9.
[2]單霽翔:《博物館的社會責(zé)任與城市文化》,《中原文物》2011年第1期。
[3]同[1],第9頁。
[4]同[1],第10頁。
[5]孫麗萍:《博物館如何展示文化軟實(shí)力?——世界頂級博物館館長滬上論劍》,新華網(wǎng),[EB/OL][2012-11-08]http://culture.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11/08/18960162_0.shtml?_from_ralated.
[6]同[1],第41頁。
[7]同[5]。
[8]《關(guān)于印發(fā)〈全國博物館評估方法(試行)〉〈博物館評估暫行標(biāo)準(zhǔn)〉和〈博物館評估申請書〉的通知》(文物博發(fā)﹝2008﹞6號),[EB/OL][2008-02-15]http://www.sach.gov.cn/art/2008/2/15/art_2184_33968.html.
[9]湖南省博物館編譯:《美國博物館聯(lián)盟趨勢觀察2017》,[EB/OL][2018-01-31]https://news.artron.net/20180131/n985968.html.
[10]同[1],第45頁。
[11]同[9]。
[12]《2018年中央財(cái)政安排208億資金繼續(xù)支持博物館免費(fèi)開放等項(xiàng)目》,[EB/OL][2018-12-04]http://www.chinadevelopment.com.cn/news/zj/2018/12/1410220.shtml.
[13]Office of Policy and Analysis.Lessons for Tomorrow:A Study of Education at the Smithsonian.USA:Smithsonian Institution,2009,1:15.
[14]同[1],第44頁。
[15]同[1],第234—235頁。
[16]同[2]。
[17]李耀申、李晨:《博物館:“文化濕地”與“城市之腎”》,《中國博物館》2018年第3期。
[18]在2015年的《博物館條例》中,已將博物館按照所有制屬性區(qū)分為“國有博物館”與“非國有博物館”,因此民辦博物館等都劃歸到非國有博物館。
[19]同[1],第11頁。
[20]同[2]。
[21]主要來自澳大利亞聯(lián)邦政府以及私營部門、維多利亞州政府、墨爾本市等。
[22]同[1],第235—236頁。
[23]朱恬驊:《構(gòu)建有溫度的濱江空間要善打“文化牌”》,《文匯報(bào)》2019年5月8日第5版。
[24]同[2]。
[25]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