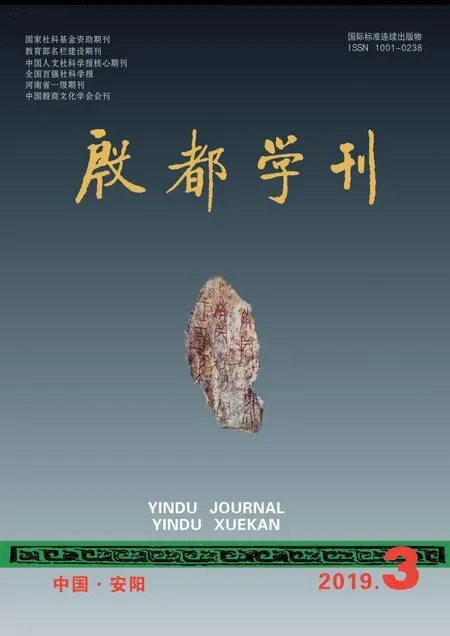明代官學(xué)書籍刻版私用考
——以明初大臣楊士奇藏書題跋為例
張艦戈
(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在安陽(yáng)中國(guó)文字博物館中存有大量的古代印刷刻版的實(shí)物、圖片、文獻(xiàn)資料等,它是中國(guó)文字發(fā)展史研究的重要基地。由于“佛教的興盛和科舉制度的推行,使社會(huì)對(duì)書籍的需求量大增,傳統(tǒng)的手抄方式已經(jīng)很難滿足社會(huì)的需求,人們迫切需求一種快速生產(chǎn)書籍的工藝方法,當(dāng)這些因素齊備時(shí),印刷術(shù)應(yīng)運(yùn)而生。”[1]從這些古代刻版管理使用情況中,擇取明代初期官學(xué)書籍刻版管理一隅,予以探究。
明代官學(xué)包括中央官學(xué)和地方官學(xué),中央官學(xué)有國(guó)子監(jiān)、宗學(xué)、武學(xué)等機(jī)構(gòu)。地方官學(xué)分為兩大體系,一是各府州縣、都司衛(wèi)所的地方儒學(xué),二是武學(xué)、醫(yī)學(xué)、陰陽(yáng)學(xué)在內(nèi)的專門學(xué)校。這些官學(xué)除各自承擔(dān)不同的教學(xué)任務(wù)外,刻書印刷也是學(xué)校的一項(xiàng)重要活動(dòng)之一,其中以國(guó)子監(jiān)和各地方儒學(xué)的刻書最為豐富。
官學(xué)刻書主要用途在于保障學(xué)生的閱讀需求,其印刷用的刻版,用完后是否被束之高閣,還是有其他用途,是否可以被私人利用?雖然,現(xiàn)在對(duì)國(guó)子監(jiān)的刻書種類、藏書、刻書經(jīng)費(fèi)等問題都有一定研究,但極少提及官學(xué)刻書的書版利用問題,尤其是私人利用這一點(diǎn)。官版私用并不常見于一般的歷史記錄之中,我們可以從明初五朝名臣楊士奇私人藏書題跋中,考究明代國(guó)子監(jiān)書籍刻版之私用及其管理情況,進(jìn)一步了解我國(guó)古代圖書出版事業(yè)的發(fā)展。
一、楊士奇藏書及其題跋記
楊士奇(1366-1444)號(hào)東里,謚號(hào)文貞,江西泰和人,明初五朝元老大臣。先后擔(dān)任《明太祖實(shí)錄》《明仁宗實(shí)錄》《明宣宗實(shí)錄》的總監(jiān),主編編纂《文淵閣書目》。其人無(wú)其它愛好,唯有嗜好藏書,家有藏書數(shù)萬(wàn)卷。
楊士奇不僅好藏書,還將其藏書一一著錄于目,為告訴后人書得之不易,皆是其“勞心苦力,以求得之。……吾懼后之人,不知守也。凡書具志,吾所以得而勉其所以守。”[2]抱有如此心愿,楊士奇幾乎將自己所有的藏書、碑帖皆作題跋。這些題跋中有的評(píng)價(jià)書籍之價(jià)值,有的比較書籍之優(yōu)劣,其中記錄書籍來源的最多,幾乎每本藏書都記載。
縱觀楊士奇藏書的來源主要有以下幾類:
其一,得于友人,即他人贈(zèng)送。楊士奇為人謙和,好友眾多,贈(zèng)書者也不在少數(shù),如楊榮、金幼孜、胡廣等人皆贈(zèng)予不少書籍。有些書籍也是楊士奇主動(dòng)索要而得,如《四書管窺》一書從黃岡教諭周公明求而得之。
其二,得于抄錄。楊士奇嗜好藏書,每見有喜愛之書,便抄錄之,有的抄錄于友人家中,有的抄錄于旅途之臨舟,有的抄錄于武昌,有的抄錄于北京。并且這些抄錄的工作大概都不是楊士奇親自完成,多由隨從或?qū)W生抄錄。如《古詩(shī)雜鈔》是其在武昌授徒時(shí)學(xué)子之所錄。《劉次莊法帖釋文》錄于武昌尹千戶,由童子所寫。《金石例》《歐文外集》和《東坡文》,此3部書負(fù)責(zé)抄錄的人大概并沒有多少學(xué)識(shí),所以錯(cuò)誤極多。除楊士奇外,萬(wàn)歷年間的私人藏書家徐勃在《紅雨樓藏書題跋志》中也有些記載。如其見到唐韋莊的《浣花集》后“遂命工抄錄,以備觀閱”。比起楊士奇,徐勃用“命”“工”二詞更明確地指出其有專門負(fù)責(zé)抄錄的工匠。這在其他人的藏書題跋記中并不常見,亦給人一種古人自己抄書的假象,從二者的題跋中可以看出,有一定財(cái)力的藏書家多是雇人抄書。
其三,得于購(gòu)買。古代書坊經(jīng)過元末戰(zhàn)亂,至明初尚處于恢復(fù)期,書籍刊刻的數(shù)量和種類有限,所以楊士奇購(gòu)買的書籍與前兩種相比要少的多。再者,購(gòu)買相較贈(zèng)送和抄錄而言屬于較為容易的得書方式,沒有特殊的紀(jì)念價(jià)值,所以楊士奇在做題跋時(shí)也有一定標(biāo)準(zhǔn):“凡吾家文籍得于故人朋友之遺者,必謹(jǐn)著所自,不敢忽。其出于貨致者,不著也。”[3]除個(gè)別書籍價(jià)格昂貴或特殊情況予以說明外,其余購(gòu)買的書,在題跋中幾乎不載來源,僅有內(nèi)容評(píng)價(jià)。
這樣的藏書題跋在明初藏書家中并不多見,藏書題跋記為我們研究明初書籍版刻留下了豐富的史料,為明代官學(xué)書版的私用研究提供了有力證據(jù)。
二、國(guó)子監(jiān)圖書刻版之私用
國(guó)子監(jiān)是明代的最高學(xué)府和教育管理機(jī)構(gòu),有南京國(guó)子監(jiān)(南監(jiān))和北京國(guó)子監(jiān)(北監(jiān))兩處,除承擔(dān)教學(xué)任務(wù)以外,刻書也是其重要工作之一。受右文政策的影響,加上繼承宋元以來的大量舊版,明代國(guó)子監(jiān),尤其是南監(jiān)所藏書版的數(shù)量十分可觀。據(jù)《南雍志》記載:明初至萬(wàn)歷年間刻印圖書約有300余種,8000余卷。
國(guó)子監(jiān)有為數(shù)眾多的書版和圖書,除刷印用做教材和供師生讀書外,是否還有別的用途?是否也像當(dāng)今公共圖書館一樣,可以有條件地借閱或提供復(fù)制印刷服務(wù)?這一點(diǎn)我們從楊士奇的藏書題跋記中可以知曉。
在楊士奇的藏書題跋中有頗多類似描述:《史記》八冊(cè),刻板在太學(xué);《文獻(xiàn)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刻板在太學(xué);《昭明文選》六十卷三十冊(cè),刻板在太學(xué)。《前漢書》二十五冊(cè)國(guó)學(xué)印本;《呂東萊文》八冊(cè),刻板在北京國(guó)子監(jiān)。(現(xiàn)代漢語(yǔ)中“版”,在古代多寫作“板”,多指刊刻書籍使用的書板。本文中按照現(xiàn)代漢語(yǔ)用法,多用“版”,僅在引用古籍時(shí)使用原文“板”字。)諸如此類,標(biāo)注刻版在太學(xué)或國(guó)子監(jiān)的藏書共19種,300余冊(cè)。楊士奇為何特地將書版所在地點(diǎn)標(biāo)識(shí)出來?其中原因就是,這些書刷印國(guó)子監(jiān)書版而來。此類書大致可分成兩類:一種是他人印制后送予楊士奇,一種是楊士奇托人刷印。
他人贈(zèng)送的主要有《王臨川集》和《晉書》等,楊士奇在《王臨川集》題記中寫道:“北京有荊公臨川集,板在國(guó)子監(jiān)舊崇文閣,而所闕什一用之。永樂八年,(某某)扈從在北京,印二本,以一本寄余,凡十冊(cè)。”[4]由以上的記載分析:括號(hào)中的“某某”可能是楊士奇在作題記時(shí),漏落了某位贈(zèng)送書籍人的姓名,此人可能指楊榮。在《朱子語(yǔ)略》一書的題跋中,楊士奇如此寫道:“刻板在北京國(guó)子監(jiān)。永樂庚寅(永樂八年,1410年),楊庶子(楊榮,曾任右庶子)扈從還,以見遺。”[5]楊榮在永樂八年跟隨皇帝出征蒙古,回程途中先到北京,從國(guó)子監(jiān)中印《朱子語(yǔ)略》一書,贈(zèng)送予楊士奇,所以此《王臨川集》可能也是楊榮同時(shí)從國(guó)子監(jiān)刷印。
從《王臨川集》的獲取來源看,國(guó)子監(jiān)的書版大概是允許私人刷印的,至少為官者是可以刷印。
另一本《晉書》也是楊黼從國(guó)子監(jiān)刷印后贈(zèng)送給楊士奇的,楊黼是楊士奇的族人,東平知州楊季琛之子,“舉進(jìn)士,在京師泊然無(wú)他嗜好,惟志學(xué)問,(楊黼)聞國(guó)監(jiān)有書板,悉貲以求印,余助之工力,以此見贈(zèng)云。”[6]說明此《晉書》是楊黼聽聞國(guó)子監(jiān)有書板,想自費(fèi)印刷,楊士奇從中予以疏通、協(xié)助,所以楊黼便多印了幾套,贈(zèng)送給楊士奇一套。
由此來看,國(guó)子監(jiān)的書版大概是可以自費(fèi)刷印的,所以除他人贈(zèng)送外,楊士奇也曾請(qǐng)親朋好友幫忙為自己刷印國(guó)子監(jiān)書版,如《清類經(jīng)星分野大略》一書具體刷印方法,在楊士奇家藏《兩漢詔令》題跋中又有明確說明:“《兩漢詔令》三冊(cè),刻板在太學(xué)。張守初真人來京師,以上清紙貺余,曰:‘少助書簡(jiǎn)之用。’余素寡交,雖有至親交者,亦懶于作書,而計(jì)其紙可印《漢詔令》一部,遂托歐陽(yáng)助教允賢成之,此書是也。每退朝,閉戶謝客,坐南軒翠竹之下,清風(fēng)徐來,獨(dú)取此書,因其優(yōu)柔深厚之詞,以考夫?qū)挻笾覑壑猓磸?fù)涵詠,亦一快哉。”[7]此3冊(cè)《兩漢詔令》是楊士奇將張守初帶來的上清紙給當(dāng)時(shí)的國(guó)子助教歐陽(yáng)賢,托付其幫忙刷印太學(xué)書版而成。從楊士奇家藏《晉書》和《兩漢詔令》的題跋來看,若私人想刷印國(guó)子監(jiān)的書版,須自己提供紙張和費(fèi)用,并請(qǐng)好友幫忙才可實(shí)現(xiàn)。這種委托國(guó)子監(jiān)官員刷印書籍的情況,并不獨(dú)見于楊士奇的記載之中。
明弘治年間,程敏政曾多次請(qǐng)南監(jiān)祭酒謝鐸幫忙印書:“往者印南監(jiān)諸書,多籍尊力,所愧者不能讀耳。《朱子周昜本義》分《十翼》者,當(dāng)時(shí)不能印得,茲因鄉(xiāng)戚邵景高管解去,便托寄上紙墨之費(fèi),乞分付轉(zhuǎn)印一部付來,不勝教愛。”[8]這與楊士奇的記載也相吻合。
萬(wàn)歷時(shí),陳懿典給馮夢(mèng)禎的尺牘中寫道:“奈何太學(xué)書板甚多,便間乞以書目見示,欲從掌故印數(shù)部耳。”[9]此時(shí)馮夢(mèng)禎為南京國(guó)子監(jiān)祭酒,陳懿典想請(qǐng)馮給予國(guó)子監(jiān)書目,若有自己中意之書,可以遵從舊例幫助自己刷印幾部。那么這里提到的“掌故”究竟是什么舊例呢?刷印國(guó)子監(jiān)的書版是否有什么慣例呢?在正德年間任國(guó)子監(jiān)典籍的李崇光的傳記中則有明確記載:“李崇光,字宗顯,陜西高陵人。少為邑學(xué)生,貢入太學(xué)。正德庚午,授南京國(guó)子監(jiān)典籍。……國(guó)朝典籍書板多在南監(jiān),縉紳置籍者,印千紙例輸白金五分於典籍以為常。崇光辭弗受,祭酒司業(yè)咸嘉之,以疾卒於官。”[10]
至少正德年間,甚至更早以前,私人在國(guó)子監(jiān)刷印書籍,每印千紙就要給國(guó)子監(jiān)典籍白金五分,并成為慣例,習(xí)以為常。國(guó)子監(jiān)設(shè)祭酒、司業(yè)、助教、典籍等官負(fù)責(zé)國(guó)子監(jiān)一應(yīng)事務(wù)。其中典籍的工作與書版息息相關(guān),“書庫(kù)扄鑰,以時(shí)省察,典籍司之。”[11]詳細(xì)來講,典籍主要“收掌監(jiān)中書籍,凡經(jīng)史子集各書及書版,均分櫝藏之并識(shí)于冊(cè)。諸生有閱讀者,記其名并冊(cè)數(shù),且限期歸櫝注銷。夏月率工役曝書以防蠹?jí)模聞t檢查稽數(shù)有無(wú)短缺,又凡監(jiān)中金石碑記以及版冊(cè)等項(xiàng)。”[12]典籍為從九品官員,官俸每月約3兩銀子。白金5分大致相當(dāng)于50文錢,雖然白金5分與官俸相比微不足道,但當(dāng)時(shí)在書坊買一本書卻花不了多少錢。洪武二十三年(庚午1390),楊士奇于書坊買過《廣韻》一冊(cè),“其值五百文,既為友人持去,后十年復(fù)市之,其直亦然。凡今生民日用之物,歷十年之久,率增直十?dāng)?shù)倍,獨(dú)書無(wú)所增。”[13]《廣韻》是一部較厚的書,若全書僅有一冊(cè),則有300余頁(yè),若楊士奇得到的僅為殘本,非全本,一冊(cè)也應(yīng)該有百余頁(yè),所以價(jià)格相對(duì)較貴。若比較薄的書,如《史略釋文》和《十書直音》兩本,在洪武初年“市直百錢”,一部約值50文左右。若買雜字書,在洪武末年則鈔一貫可買十?dāng)?shù)部,一部約值50~80文錢。由此可見,在國(guó)子監(jiān)刷印書籍,除自付紙墨之費(fèi)外,給典籍的錢就幾乎相當(dāng)于在書坊買一部小書的錢,費(fèi)用還是比較高的。但由于國(guó)子監(jiān)書版的校勘、質(zhì)量均屬上乘,刷印之人也為數(shù)不少。
上述國(guó)子典籍李崇光辭不受金,祭酒、司業(yè)僅持贊許的態(tài)度,而未禁止此種行為,就這一點(diǎn)來看,這一“慣例”大概并不是暗地進(jìn)行的,而是人所共知的事,也并未觸犯法律。但這一慣例大概也并非光彩之事,所以只有在對(duì)某人的褒揚(yáng)中才會(huì)一筆帶過,卻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資料。
三、明代地方儒學(xué)書籍刻版之私用
中央官學(xué)國(guó)子監(jiān)、太學(xué)的書版存在私人請(qǐng)托刷印的情況,各地儒學(xué)也與國(guó)子監(jiān)類似,私人也可以通過各種途徑獲得其印刷藏書。這一點(diǎn)我們也可以從楊士奇的藏書題跋中管窺一二。
楊士奇藏書題跋記中,與地方儒學(xué)版刻印刷的記載眾多,現(xiàn)選錄以下九條:
(一)《春秋左氏傳》題跋記載:“吾家此書十六冊(cè),蓋福州府學(xué)板,得于劉伯塤員外云。”[14]劉塤是江西泰和人,字伯塤。在永樂十二年(1414)任職刑部廣東清歷司員外郎。楊士奇題跋中另有《北溪字義》一書,是“近劉伯塤員外自閩歸,惠余(楊士奇)二本。”[15]由此推測(cè)《春秋左氏傳》一書,大概也是劉塤在福建時(shí),從福州府學(xué)得到,回來后贈(zèng)予楊士奇。
(二)在《四書集注》題跋記載:“右《四書集注》……刻板在常州府學(xué)。此集六冊(cè),永樂十年二月余奉命考會(huì)試,常州府學(xué)教授金原祺時(shí)預(yù)同考,余從求而得之者也。”[16]金原祺是福建閩南人,此書即為楊士奇和金原祺同主持永樂十年會(huì)試時(shí),楊士奇向金原祺索要而得。
(三)《四書管窺》題跋記載:“《四書管窺》四冊(cè),永嘉史伯璿文璣著……刻板在永嘉郡學(xué),吾得之黃宗豫……(又)《四書管窺》,舊刻板在永嘉。葉琮,洪武乙丑進(jìn)士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xué)。吾友吉水周君公明為黃岡縣教諭,從求而得之。總五冊(cè)二本,余皆有之。”[17]周啟,字公明,吉水人,曾任廬陵、黃岡、長(zhǎng)州教諭。
(四)《通鑒總類》題跋記載:“刻板在蘇州郡學(xué)。余初得十二冊(cè)於晏彥文,而闕其八冊(cè),吉水,周功敘自蘇州為余印補(bǔ),遂為完書。”[18]周敘,字功敘,吉水人。永樂甲午舉江西鄉(xiāng)貢士,南京翰林侍講學(xué)士。
(五)《通鑒前編舉要新書》題跋記載:“刻在蘇州郡學(xué),余家一冊(cè),錄于中書舍人朱季寧”[19]朱吉,字季寧,昆山人(今隸屬蘇州)。楊士奇有多本書錄于朱吉家,如《書法三昧》、張南軒的《三家禮范》等。
(六)《新唐書》題跋記載:吾家《唐書》五十四冊(cè),刻板在福州府學(xué),得之今翰林學(xué)士楊公勉仁云。楊公乃是楊榮,字勉仁,建安人(今隸屬福建)。
(七)《安雅堂文》題跋記載:閩陳旅眾仲著,刻板在福州府學(xué)。余家三冊(cè),得于翰林庶吉士洪遵道。洪順,字遵道,懷安人(今隸屬福建)。永樂甲申科進(jìn)士,改庶吉士,遷刑部主事,升山東按察使僉事,后升山東按察使。
(八)《南北史》題跋記載:“今刻板在福州府學(xué)。吾家《南史》十五冊(cè),《北史》十三冊(cè),總二十八冊(cè),得之歐陽(yáng)允和者也。”[20]歐陽(yáng)和,字允和,江西泰和人。永樂十年壬辰進(jìn)士,授監(jiān)察御史,洪熙年間升云南按察副使。
(九)《柳待制文集》題跋記載:“《柳待制文集》四冊(cè)二十卷,金華柳貫道傳所著……其文皆有刻板在(金華)郡學(xué),余皆得之文英。”[21]
從上述題跋中我們可以看到,明確標(biāo)注書版在地方儒學(xué)的書籍主要有以上10種(南北史為兩種書):《四書集注》和《四書管窺》兩書是請(qǐng)托當(dāng)?shù)厝鍖W(xué)教授或教諭得到的,其余8種書是他人贈(zèng)送的。從楊士奇請(qǐng)常州府學(xué)教授金原祺和黃岡教諭周公明,幫忙為自己刷印府學(xué)書籍來看,地方儒學(xué)藏書刻版是允許私人刷印的,特別是有關(guān)系之人士。
通過分析可知,這些書的贈(zèng)送者與書版所在地均有一定淵源關(guān)系:劉伯塤可以得到福州府學(xué)藏版的《春秋左氏傳》,大概與其在福建督工匠營(yíng)造有關(guān)。永嘉郡學(xué)藏《四書管窺》得之永嘉黃宗豫;蘇州郡學(xué)藏《通鑒前編舉要新書》得之昆山朱季寧;福州府學(xué)藏《新唐書》得之建安楊勉仁;福州府學(xué)藏《安雅堂文》得之懷安洪遵道;金華郡學(xué)藏《柳待制文集》得之金華王杰,除劉伯塤在當(dāng)?shù)厝喂偻猓溆嗨娜思灳诋?dāng)?shù)亍S纱藖砜矗谕馊温毜谋镜毓賳T,尤其是京官,想刷印當(dāng)?shù)厝鍖W(xué)書版大概也是相對(duì)容易的。甚至各地儒學(xué)官員刷印本學(xué)所藏書版,作為禮物贈(zèng)送予本地官員也是常有之事,與明代盛行的“書帕本”也有很大關(guān)系(明代把書籍當(dāng)做禮品,饋贈(zèng)官員上任或奉旨?xì)w京的一種版本,用手帕包裝,稱“書帕本”)。
四、書籍刻版私用之危害
我們從楊士奇的藏書題跋中可以看到,明代國(guó)子監(jiān)保存的大量書版,除公用外,也存在私人刷印的情況。私人欲刷印國(guó)子監(jiān)書版,除自付紙墨等刷印之費(fèi)外,還有向典籍納錢的慣例。而這也不是一般人想做就可以做到的,若不請(qǐng)托與自己相熟的祭酒、助教等國(guó)子監(jiān)官員,大概也是“欲印無(wú)門”。但若是身為掌管國(guó)子監(jiān)書籍的官員,如典籍本人,若想刷印書版可能就比較容易了,如宣德初年的北監(jiān)典籍彭詡“搜閱崇文閣不完書板,而此(《儀禮逸經(jīng)》)獨(dú)完,即日印惠親友。”[22]彭詡看到《儀禮逸經(jīng)》書板比較完整,就立刻開始刷印,可能印了多部,才可以惠及諸親朋好友,并送與楊士奇一部。可見由此可見,能否刷印國(guó)子監(jiān)書版大概與國(guó)子監(jiān)官員,尤其是典籍的態(tài)度息息相關(guān)。
國(guó)子監(jiān)書版多繼承宋元儒學(xué)舊版,加之由國(guó)子監(jiān)師生也廣泛參與校勘、撰寫、修補(bǔ)活動(dòng),質(zhì)量相交而言應(yīng)屬上乘,除公用外,各衙門、私人刷印的情況也時(shí)有發(fā)生。但國(guó)子監(jiān)對(duì)書版的管理制度卻并不完善,加之私人頻繁請(qǐng)托刷印,也給刷印匠帶來可趁之機(jī),導(dǎo)致書版日漸損壞、減少。
早在洪武永樂時(shí)期,就有刷印匠偷盜書版之事,“洪武永樂時(shí),兩經(jīng)欽依修補(bǔ)。然板既叢亂,每為刷印匠竊去刻他書以取利,故旋補(bǔ)旋亡。至成化初,祭酒王·會(huì)計(jì)諸書,亡數(shù)已逾2萬(wàn)篇。”[23]
到萬(wàn)歷中后期,國(guó)子監(jiān)所藏書版與《南雍志》記錄相比,存數(shù)連百之一二也沒有了。萬(wàn)歷二十九年(1601),南監(jiān)祭酒郭正域就此問題上疏道:“本監(jiān)書板并書籍較《南雍志》百無(wú)一二存矣。各衙門來印書者,既不能禁兩樓,又無(wú)鎖鑰,遂至匠役盜毀印板,大可痛恨。今將不印書板送入倉(cāng)中,永不許開。亦掛牌開數(shù)倉(cāng)門,不許損壞,其印行書板存貯東西二樓,上下派定庫(kù)、庫(kù)役、匠役分管,如有損失,責(zé)令賠償。刊記牌上籍廳每季一查,樓門封鎖,無(wú)事不開,以防損壞。六堂并廳籍各有書籍,各開列數(shù)目懸掛各堂籍廳,毎季一查開報(bào)以防損失。”[24]
國(guó)子監(jiān)書版的損壞與管理不善和私人的使用有極大關(guān)系,正是這些私人請(qǐng)托、使用的盛行,給予匠役以可乘之機(jī),大量盜取書版,以謀私利,導(dǎo)致國(guó)子監(jiān)書版的質(zhì)量每況愈下,且丟失、損壞極多。
結(jié)語(yǔ)
明代國(guó)子監(jiān)藏書比較豐富,加之國(guó)子監(jiān)師生的校勘,其書版質(zhì)量均屬上乘。這些書版除做公用外,也允許私人使用。楊士奇的藏書題跋記就為我們展示了刷印國(guó)子監(jiān)書版的大致過程:首先,請(qǐng)托親朋好友是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有諸如國(guó)子監(jiān)祭酒、助教等官員的幫助,才可能獲得刷印書版的機(jī)會(huì),尤其是負(fù)責(zé)管理國(guó)子監(jiān)書板的典籍本人的態(tài)度與之息息相關(guān);其次需自付紙墨之費(fèi)或自己提供紙張進(jìn)行刷印;最后,每印千紙要給國(guó)子監(jiān)典籍白銀五分,是為慣例,這樣即可刷印國(guó)子監(jiān)所藏書版。由此及彼,從國(guó)子監(jiān)的情況來看,地方儒學(xué)所藏書版大概也是允許私人刷印的,只不過這些書籍中的一大部分是地方儒學(xué)官員作為禮物贈(zèng)送給當(dāng)?shù)毓賳T的,自付紙墨之費(fèi)的情況可能比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