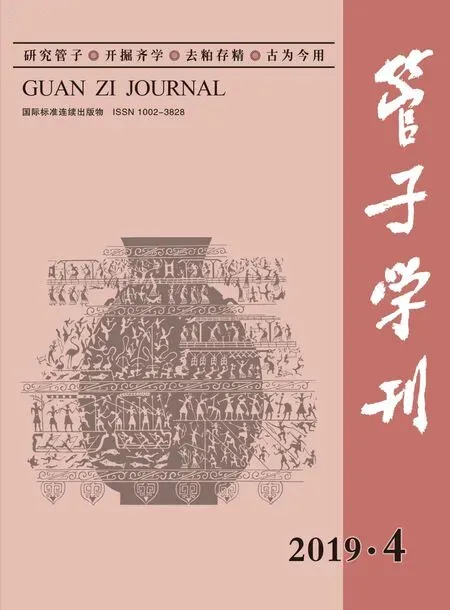《新語》“思想近于韓非”榷論
劉 亮
(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100875)
胡適《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提出陸賈《新語》“思想近于荀卿、韓非”①胡適:《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版,第64 頁。之說,并獲得如張傑、余明光、李存山、蔡忠道等先生不同角度上的響應與拓展。 那么,認為《新語》思想“近于韓非”的觀點,是否與其書之雅言仁義德化、反對嚴刑峻法的傾向相抵牾? 此議題不僅關系到《新語》如何看待先秦以來刑名法術的思想脈絡,更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其書如何看待統治權力,特別是如何看待統治權力與社會規則之間的關系,因而對于《新語》思想研究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筆者嘗試就此于前賢基礎上略表卮言,荒謬之處,敬祈斧正。
一、論《新語》與《韓非子》歷史見解之相悖
歷史見解角度上主張《新語》思想接近韓非的,有胡適、張傑、蔡忠道等先生。 胡適先生援引《新語·道基》針對世界生成的論述,評價稱:“陸賈似乎受了韓非的歷史見解的影響;韓非分古史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五蠹篇》);陸賈也分古史為‘先圣’‘中圣’‘后圣’三個時期。 ……莊子、韓非以后,歷史演變的思想更流行了,故韓非說古史……只說‘圣人不期循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而已。 陸賈此論,更為詳細清楚,可算是古人的文化起原論中最有條理的作品。”②胡適:《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第67 頁。引文指出《新語》持“進化”或“演變”的歷史意識,并認為這一點接近韓非的學說;其中歷史的“進化”或“演變”,蓋相對非進化的(如鄒衍學說中的歷史循環等)、非演變而言③胡適先生并未細致區分“進化”(evolution)、“進步”與“演變”的涵義區別。 至于韓非子的歷史觀是進化的,抑或進步的,抑或一種無價值傾向的“演變”,前賢已有一定的討論,如王邦雄先生認為《韓非子》主張“歷史由外在物質條件所決定”觀點,而外在物質條件上則無所謂“進化與退化”等含有價值傾向的命題,故其歷史觀并非進化、進步,而是單純的“演化”;張子俠先生亦主張“變易史觀”,其認為《韓非子》面對不同歷史階段,不僅未作高低劃分、極少論述歷史發展方向,甚至存在一些可解讀為復興古代氣象的內容,而這些內容與所謂“進化”“進步”史觀不能兩立。 可參見王邦雄《韓非子的哲學》,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3 年版,第141 頁;張子俠《關于韓非歷史觀的幾個問題》,《史學史研究》1997 年第4 期;等等。 本文因研究目的所限,對此不再展開討論。。 張傑先生亦云陸賈將歷史“以先圣、中圣、后圣分而為三,則同于韓非《五蠹》之分也。”①張傑:《讀陸賈新語》,《光華大學半月刊》,1936 年第5 卷,第2 期,第54 頁。蔡忠道教授亦提出《新語》歷史觀點某種程度上“受了韓非的影響”之見解②蔡忠道:《陸賈思想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 年版,第86-87 頁。。
鮮有古人徹底否認歷史的演變。 諸子歷史見解上的不同,更多在于歷史是如何演變的:是循環的抑或非循環的,歷史演變中有無不變或貫通的內容存在,等等。 譬如就后一問題而言,荀子與韓非子即正相對立:《荀子·天論》云:“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 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非但承認具體事件的歷史變動中,因時而異的“變”與高度穩定的“貫”(“貫”又包涵禮法制度中具體條目與高級宗旨兩種類型,前者如“三年之喪”,后者如“仁愛”的高級宗旨③有關“三年之喪”的論述,《荀子·禮論》云“三年之喪,何也? 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 ……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 是百王之所同也,古今之所一也。”有關“仁愛”,《荀子·修身》云“術禮義而情愛人”;王引之曰“人,讀為仁。 ……其術則禮義,其情則愛仁也。 愛仁,猶言仁愛。”(轉引自王先謙《荀子集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版,第32頁)即以禮義為“術”(形式),以“愛人”(仁愛)為“情”(也就是內容或宗旨)。),且主張統治者(包括損益禮法、變法改制等權變在內)的各類舉措,要遵循這些“貫”。 換言之,歷史見解的表達背后,則是針對統治權力的態度:荀子學派借助歷史的篩選功能,試圖以歷史上長期穩定的原則條款,約束當下的統治者。 《韓非子·五蠹》則云: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 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 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 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 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 今有構木鉆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于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 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于當今之世者,必為新圣笑矣。 是以圣人不期循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引文急于否認歷史變化過程中存在任何高度穩定的因素,即使在他們自己的歷史講述中(如引文部分),待天下人以仁義(具體表現為列圣為天下人興利除害)分明能夠貫穿歷史,他們卻硬是視而不見。 其派據此而出“不期循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的主張,示意統治者將時代的特殊性作為理由,拒絕遵守儒家等所謂放諸各時代而皆準的規矩禮法;其背后則包藏著為統治者祛除約束之居心,造就一個沒有規矩禮法能夠約束統治者的,“由單獨一個人按照一己的意志”④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年版,第8 頁。來統攝一切的局面:對韓非們而言,是統治者制定(和廢止)規則,支配著周圍的一切,而非統治者受到既定規則的約束⑤如《韓非子·難三》云:“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強調其法禁的方向乃是臣下而非統治者自身。。
在此“荀子——韓非子”針對歷史見解的對立結構上,《新語》傾向于哪一邊? 胡適先生謂“陸賈的歷史見解有點像荀卿,又有點像韓非,大概是調和這兩個人之間。 如說:‘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遠者,考之于近(參看《荀子·性惡篇》‘善言古者,必有節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 ……萬世不異法,古今同紀綱。’這一段全是荀卿‘法后王’之說,含有古今雖久而同理之意。 因為古今同理,故不必遠法上古,但‘取其致要而有成’而已。 但陸賈又說‘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 屬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 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這里便超出荀卿思想之外,已有韓非的意味了。 荀卿與韓非同一不法先王,而根本大不相同。 荀卿言古今同理,故法后王即等于法先王。 韓非、李斯都信古今時勢不同,故先王之法不可得而法。 古代學者不曾深切了解歷史演變之理,往往不能辨別這兩說的根本不同。 所以《呂氏春秋·察今》篇明說時代已經變換了,故不能法先王之法,但忽然又插入一句‘古今一也’的舊說。 所以陸賈已很詳細的敘說文化演變的程序了,終不能完全丟掉‘萬世不異法,古今同紀綱’的荀卿思想。 此種矛盾的理論多由于思想不曾有徹底的自覺。 如果萬世真不異法,何必又說‘因世而權行’呢?”引文提出,《新語》稱“萬世不異法,古今同紀綱”,又稱“因世而權行”,乃是一種不能透徹理解歷史的自相矛盾之舉。 這一論點似有商榷余地。 鄙意《新語》作者看來,胡適先生所謂矛盾之處,是分別就歷史過程中不同層次的內容而言的。 而今本《新語》的觀點,終究是傾向于荀子一方。 上述引文援引《新語》,皆在《術事》篇。其云:
文王生于東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 故圣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兇;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 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
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 ……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 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引文中存在三種類型的歷史事物:一為某一特定事物,如名叫“騏驥”的那匹良馬、名叫“干將”的那柄利劍等;一為具有概括性的某類事物,如“良馬”與“利劍”,等等;一為有概括性的原則,如“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兇”等。 引文將在歷史中尋求經驗教訓的方法示諸讀者:從特定事物中提煉出的具有概括性的觀念,再以此類觀念,而非特定的事物來指導當下的行動:譬如今人從既有的特定事物“騏驥”中得知“良馬”這一類事物,而實際上去尋求的,也是“良馬”這一類事物,而非那匹已然尸骨無存的騏驥。 此即后文“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之義:文中“故制事者因其則”之“因”當釋作“循”,即行事當遵循有概括性的原則,而非拘泥于特定事物①王更生先生關注到《新語》歷史觀存在“道”“術”兩個層次:“‘道’歷久不變,萬古長新;而‘術’卻因時制宜,代有不同”。 參見《王更生先生全集》第2 輯第8 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3 年版,第29-30 頁。 此外,吳儔曾援引“書不必起仲尼之門”,戴彥升又批評吳儔稱“《術事》篇謂言古者必合之今,述遠者必考之近,故云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要不必出扁鵲之方,以因世而權行故也;吳儔執其單詞而議之,則以辭害志矣。”參見班固著,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第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版,第2961 頁;王利器撰《新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版,第217 頁。。 而那些古今一向成立的原則,更屬有概括性的原則之列(亦即“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 其文義仍在規勸其讀者(特別是統治者)遵循此類原則,與《思務》篇依據高級宗旨應對具體情勢的主張(“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而圣人“分之以度、紀之以節”),以及《新語·道基》篇之“歷敘前古帝王,而總之以仁義”(唐晏注釋)②引自王利器撰《新語校注》,第1 頁。,向統治者強調貫徹古今的“謀事不竝仁義者后必敗”原則,皆保持著一致。 胡適先生所強調的“因世而權行”,則是說將這些有概括性的原則,運用在具體事物、具體情勢的層次,并不與“萬世不易法”沖突。
由此可說《新語》接近乃至承襲了重視歷史經驗、要求統治者循貫應變的荀子學說,而與單方面強調歷史變化以及歷時性的差異、拒絕承認通變內容的韓非子學說相對立。
二、《新語》“權勢”與“法度”說續辨
現實政治思想層面上,《新語》有“近于韓非”或有近于(包涵韓非在內的)所謂“法家”的思想存在之說,亦常得到承認。 此類觀點又可依據理由的不同,而略分為兩種:
一種為主張《新語》因“重權勢”而近于“法家”乃至韓非子的觀點。 例如余明光先生稱陸氏“主張要充分利用手中的‘權’‘術’‘勢’這三大統治工具”;因為“《辨惑》篇說‘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罰]’。 陸賈在這里非常明確地提出統治者一定要‘因權’‘因勢’和‘操柄’才能大權在握,因勢以臨,操柄以治,用威勢和審合刑名的辦法來控制臣下,統治百姓。這樣百姓才能畏威,而臣下才能效力,國家自然就可治理好。”③余明光:《論陸賈的道家思想》,《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 年第1 期。李存山先生指出,“在先秦儒家那里,權力是附屬于道德的,道德的極致必然或應然就是權力的極致。 當道德受到權力的排拒,儒家不能順利推行其仁義思想時,先秦儒家不是把權力視為異于道德的一種獨立的政治因素,不是歸結為道德之無能,而是委之于‘天道不行’或‘天數未至’。 陸賈一反先秦儒家的思維方式,提出‘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反映了漢初儒家面對強大的君主權勢,不再盲目地夸大道德的作用,而是客觀地、急切地欲實現道德與權勢的結合。 ……陸賈……提出‘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突出了權位是貫徹儒家之治道所必需的的思想。 陸賈還說‘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罰]’,更表現了欲借助權柄而實施賞罰以補充道德教化之不足的思想。 權勢、權位、權柄、賞罰,本來是法家思想的核心,秦漢政治制度就是建立在這一核心上面;漢初儒家欲實現這一政治制度的結合,也就必然要吸收法家的思想。”①李存山:《秦后第一儒:陸賈》,《孔子研究》1992 年第3 期。 李禹階、何多奇亦提出近似觀點,見氏著《論陸賈新儒學對先秦諸子說的批判繼承:兼論陸賈“厚今薄古”思想的方法論原則》,《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1 期。李先生自道德與權力的關系切入此問題,極具啟發意義。 蔡忠道教授亦提及陸賈“強調權勢的重要”,并援引《韓非子·難勢》“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不足慕”,《韓非子·功名》“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等內容,將“陸賈這種(筆者按,指《辨惑》“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一句的主張)道德依于權勢而實踐的思想”與鼓吹“勢治”的韓非子學說聯系起來②蔡忠道同時強調陸賈“與韓非絕棄道德的勢治思想又不盡相同,陸賈強調權勢,是認為它是德治的憑借、手段,權勢仍須以道德為基礎,因為道德是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根本,而權與勢是維系道與德持續推行的力量。”見氏著《陸賈思想之研究》,第104-105 頁。。
一種為言《新語》提倡以“法治”支配臣民的觀點。 如余明光先生宣稱,在陸賈那里“法治也是不可少的”;且其“利用法……來治理國家,控制臣下”;因為《新語·明誡》謂“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屈申不可以失法,動作不可以離度……”;“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于人乎?”如若《新語》肯定慎子、商鞅、申子、韓非所鼓吹的治民御下的“法治”,則其與所謂“先秦法家”乃至鼓吹黃帝學說的諸流派則具有了重要的重合點。
前一種言及“權勢”的觀點,常依據《新語·辨惑》篇內容。 其文云:
邪臣之蔽賢,猶浮云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云霽翳,令歸山海,然后乃得睹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 今上無明王圣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鉏奸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后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于世而施于政。 故孔子遭君暗臣亂,眾邪在位,政道隔于三家,仁義閉于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于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鄙意引文語境中,用以證明陸賈“重權勢”的關鍵部分“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一句(后文簡稱“‘道因權而立’句”),并非是《辨惑》作者在價值上提倡的內容,而是一種事實的描述,且流露出作者對于現有秩序的嘆惋。 其理由如許:
“道因權而立”句,是在解釋“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 俞樾釋引文部分稱:“按此引《論語》,與今本不同,句末有‘夫’字,則‘已矣夫’三字為句,翟氏灝作《論語考異》引此文不連‘夫’字,疏矣”;王利器先生亦稱“下文云:‘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此自說《論語》‘吾末如之何’之義,句首不當用‘夫’字,此‘夫’字自屬上讀,為《論語》之文。”③王利器:《新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版,第87 頁。亦即引文中“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斷句有誤,當作“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故后面關鍵的這一句,句首以“言”始,明確其后(亦即“道因權而立”句)是解釋前面的部分。
而“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表達著孔子對魯君蔽于邪曲、自己清醒的意見不被采納的無奈。 此句又見于《論語·衛靈公》:“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劉寶楠《正義》引用《春秋繁露·執贄》釋義云“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矣。 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圣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 此以‘如之何’為問人之辭,凡稱‘何如’是也。”④劉寶楠:《論語正義·衛靈公》,載于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影印版。竹添光鴻《會箋》亦援引《執贄》篇,釋“如之何,如之何”為“既竭思慮而弗得焉,向人懇求教之辭”⑤竹添光鴻:《論語會箋》第2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 年版,第1017 頁。。 根據劉氏、竹添氏釋義,“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意為對于不被咨詢、沒有發表意見之機會的嘆息。 此釋義正與《新語·辨惑》相符合:后者言魯君蔽于“三家”,孔子作為清醒的旁觀者,意見不被聽取,思想全無施展機會,故作《公陵》之歌以傷之,以表對此境遇之無奈。
故言,《辨惑》以“道因權而立”句闡釋孔子“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之嘆,將邪曲蔽主的問題,追問至既有制度的層面。 具言之,其篇文先言及“行不敢茍合,言不為茍容”,“知必屈辱而不避”之“直道”與“阿上”之曲道的對立,繼而指出存在前者“殊于世俗”“孤于士眾”,而后者“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的危險,又以趙高指鹿、曾子殺人、定公拘弱等典故予以證明。 讀者此時很容易產生“何以致此”“有何對策”等疑問,于是前述引文呈現,將邪臣蔽主問題的產生,徑自指向既有統治制度的方向:正是權勢為統治者所持有這一既有制度,致使統治者是遵循“道德”,還是為邪人蒙蔽,終究視其本人的選擇取舍而定,清醒而行直道的旁觀者即使存在,亦因無權干涉而無能為力。 換言之,篇文不僅觸及到了如何在制度設置上提防邪曲相銜的深層問題,且指出了在這樣的有效措施誕生之前(因旁觀者的無能為力而使),這一沉重的任務則不得不全然落在了統治者自己的身上,從而警示后者,時時慎思明辨。 此蓋“言道因權而立”一句的蘊義。 其針對既有君主制度所展現暗含的略帶懷疑的,略含沉重乃至悲觀的態度;其與《韓非子》擯棄仁義德化①針對這一點,后文將有論及。,單方面依賴法勢術的所謂“抱法處勢則治”之觀點說,及其所蘊含之近于天真的樂觀,可謂判若云泥。
后一種言及“法度”的觀點,乃是依據《明誡》篇內容: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屈申不可以失法,動作不可以離度,謬誤出口,則亂及萬里之外,何況刑無罪于獄,而誅無辜于市乎?!
故世衰道失,非天之所為也,乃君國者有以取之也。 惡政生惡氣,惡氣生災異。 螟蟲之類,隨氣而生;虹霓之屬,因政而見。 治道失于下,則天文變于上;惡政流于民,則螟蟲生于野。 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于□□□變。 圣人之理,恩及昆蟲,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頸而望治,傾耳而聽化。 圣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蟲,□□□鹢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 至于鴝鵒來,冬多麋,言鳥獸之類□□□也。 十有二月隕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 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于人乎?引文“夫持天地之政”一句,言“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的統治者,因其手中權柄,“謬誤出口,則亂及萬里之外”,故須時刻遵循“法度”,不可絲毫倦怠②此外,要求統治者遵循一定法度的內容頻見于《新語》。 例如《無為》篇云:“故王者之都,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則者也,舉措動作,不可以失法度。”。 后文進而將自然災異歸責于統治者的舉措失當,既是漢代災異告譴潮流的表征,又構成其潮流的推動者;論其意圖,仍不外利用(自然以及超自然等)各類因素約束統治者,使其遵循“法度”,而不恣意妄為③前賢在此問題上亦有諸多論證,本文不再贅述。。 然所謂先秦“法家”,特別是韓非子的“法治”,則以控制民萌,統御臣下為彀的。 譬如《管子·任法》稱:“夫法者,上之所以壹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將“法”與“私”對立而言,強調前者對臣民的管控。 《韓非子·定法》稱:“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 ……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其將“法”解釋為依強力(賞罰)而貫徹的、自上而下的命令,以及帝王統治的工具。 《韓非子·有度》亦稱:“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 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 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 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奸邪無所依。 ……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為惠于法之內,動無非法。 峻法,所以凌過游外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 ……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在《有度》作者那里,“以法治國”的目的,仍在于令人主有效支配官僚及民萌,確立一種統治者掌控一切的秩序。 故《新語》用以約束統治者“法度”與《韓非子》等壹民使下“法治”,乃是方向性的背離①值得注意的是,《新語》亦非絕對排斥刑令誅賞的存在,而僅是將其作為仁德教化前提之下,一種輔助性補充的“潤色”。 如《至德》由“夫形重者則心煩,事眾者則身勞”推及“君子”的無為而治,后云“于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雖稱賞罰與教化并用,然作為賞罰對象之“善惡”,仍是根據仁義、禮制,而非認同如商鞅、韓非等排斥仁義德化的“深刑刻法”。。
綜上,《新語》思想“近于韓非”之說,似有商榷空間。 其書各篇鼓吹歷史變動過程之中,有如“仁義”等穩定的貫通性內容,要求統治者予以遵循;這使得是其書的歷史見解接近荀子學派,而遠離韓非子學派的表征。 其《辯惑》篇多被前賢解釋為“重權勢”、承襲韓非“勢治”思想的“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之說,與其解讀為對權勢單方面的肯定、推崇,不如釋為將邪曲蔽主問題追究至制度層面,不僅指明忠直意見之孱弱無力、擁有選擇權的統治者之責無旁貸,更提出如何彌補傳統君主制度此一致命缺陷的深層問題。而《明誡》所謂“法度”,則是意在要求統治者遵守的內容,與將“法”作為統治者支配臣民工具的韓非子等家亦有根本區別。 《新語》各篇,針砭時弊,立論清醒而深刻,全然不見“法術之士”因單方面迷信強權而彰顯出的,那種昏聵與張狂。
此外,《新語》作者對包括韓非子在內之法術流派的高度重視,及其所受后者的深刻影響,則是無法否認的,雖然這種影響皆是對后者負面影響的反省:畢竟嚴刑峻法將自取滅亡的論點,為其各篇所不厭其煩地反復申說②徐復觀先生曾指出“西漢像樣點的儒生,無不反秦反法,一方面是站在人民要求生存的立場,一方面也是站在統治者政治上的利害立場。 因為‘唯刑主義’,君臣民的關系,還原為簡單的相壓與被壓的關系。 臣民因完全處于被動地位而剝奪其人格,因而汩沒了他們的仁義之心,唯有憑原始求生欲望的材質以趨利避害,沒有真正的人倫關系,亦即是沒有有機體的社會結構,僅憑刑的一條線把臣民穿貫起來,以懸掛在大一統專制的皇權手上,此線一斷即土崩瓦解。 而其勢非斷不可……所以不以陸賈之言為迂闊之論。”見氏著《兩漢思想史》第2 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年版,第93 頁。。 同樣無法否認的是,今本之《新語》與《韓非子》確實存在某些共同之處——雖然其共同之處,不在歷史見解、“權勢”與“法度”領域,有如上述。 例如雙方一致承認作為統治方式的嚴刑峻法與仁義德化之間,具有勢不兩立的對立關系:例如《新語·術事》篇云“刑立則德敗,佞用則忠亡”;《韓非子·五蠹》亦以君主“垂泣不欲刑”、父母之于愛子以及孔子與魯哀公的對比③《五蠹》篇云:“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 何以明其然也? 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 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 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 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 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 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 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勢,寡能懷于義。 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 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 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 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 民者固服于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哀公顧為君。”等形象的比較、描述與譬喻,來彰顯仁義與嚴刑二者在運作方式以及效果上,皆判然相異甚或截然相反④只是《新語》《韓非子》之作者,面對此一對立關系取舍相反而已。 至于此仁義與嚴刑不兩立的對立關系是否合理,則是另一個見仁見智的復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