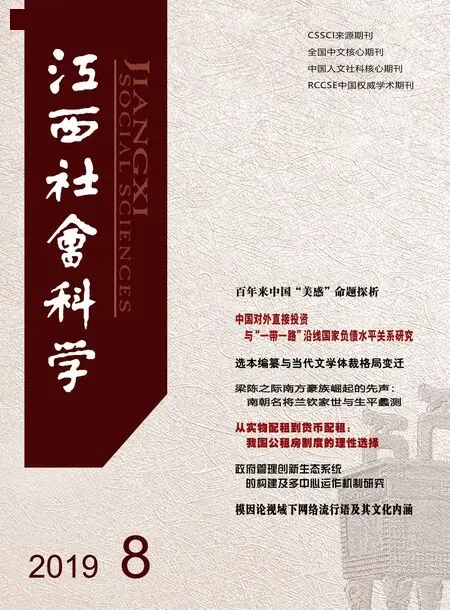錢鍾書的“文心”及其歷史意識
袁廣濤
錢鍾書屢次標舉的“文心”概念代表其學術思想本質的兩大特征:形式主義和心理學維度。這兩個特征體現在他的文學史觀、批評實踐和互通的文化觀等方面。具體而言,錢鍾書認為文學史是精神心理影響下文學形式的演化過程,與現實社會歷史無關,他的批評實踐多用語義分析法,重視文本內部和不同文本之間互文性,并習慣借助心理學概念,發掘普遍心理和事理,但追求普遍性和固守文本是對具體歷史語境的摒棄,而錢鍾書打通的文化觀,因其立足于各類文本共有的文學性和普遍的精神心理,同樣忽視了歷史。所以,雖然史學是錢鍾書學術研究的畛域之一,但他的學術思想和實踐具有反歷史主義的維度。
錢鍾書在《論復古》中主張一種涵蓋過去與現在的“歷史觀念”[1](P330),強調新文學和舊文學之間的張力結構和互動關系,這種文學史思想體現出辯證的歷史意識。除文學史外,他對歷史和史學也有精妙闡發,對東西方的史學傳統頗多洞見,并且致力于溝通中西,貫通古今,打通歷史和其他人文學科。本文通過總結錢鍾書的文學史觀、批評方法以及其打通的學術精神,試圖說明錢鍾書學術思想可由代表形式審美與心理學的“文心”一詞所概括。但是,雖然錢鍾書對傳統與現代的關系辨析精微,“文心”也指明其學術思想和實踐的基本立場是文學本體和普遍主義,這也導致他歷史意識有局限的一面。
一、形式與心理主導的文學史觀
錢鍾書在《談藝錄》開篇即謂“詩分唐宋”,繼而言明唐詩與宋詩相區別的依據是格調神韻等詩歌內在審美特征[2](P1-5),而非社會歷史中的朝代分野,并且聲稱文學史是語言或題材的以故為新、使熟者生的過程[2](P29-30),這一文學演變中的陌生化原則來自于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家什克洛夫斯基,其核心原則是強調文學特殊性的文學本體論,而錢鍾書認為文學自有其演變規律和內在價值,正是這種文學本體意識的表現。但他并沒有固守形式主義文學史觀,而是在此基礎上有所拓展。比如,在《旁觀者》一文中他認為文學、文化乃至社會、政治的形態都由心理狀態影響和決定[1](P281-282),看似突破了上述形式主義文學史觀的封閉性,但因為心理狀態自在、自為,只遵循自己的發展規律,不為社會現實所決定,于是,文學史就脫離了社會歷史。在《中國文學小史序論》中他寫道:“每見文學史作者,固執社會造因之說,以普通之社會狀況解釋特殊之文學風格,以某種文學之產生胥由于某時某地;其臆必目論,固置不言,而同時同地,往往有風格絕然不同之文學,使造因止于時地而已,則將何以解此歧出耶?”[1](P100)意思是不能“因世求文”,拿社會等非文學因素來解釋文學。這是錢鍾書對以泰納為代表的實證主義文學觀的否定,也是他一以貫之的立場。
錢鍾書的這種基于文學本體與精神心理的文學史觀應該有艾·阿·瑞恰茲的影響。他在清華大學西文系讀書時,瑞恰茲恰好在該系講學(1929—1931年),瑞恰茲的語義學分析方法立足于文學本體論,對錢鍾書的文學本體觀念應有所影響;同時,瑞恰茲與其他新批評主義者又不同,他試圖突破形式主義,把心理學范疇和方法引入到文學研究中。受其影響,錢鍾書曾發表過《人為什么要穿衣》《美的生理學》等關于心理學的文章,并在《美的生理學》中對瑞恰茲的《文學批評原理》極為推重,認為它借助心理學開拓了文學研究的新路徑。在他后來的學術生涯中,錢鍾書保持了這種對心理學的興趣,他所征引的浩瀚文獻中屢屢出現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的著作,分析文本時也習慣借用心理學的概念。而從更宏觀的文化背景來看,這種文學觀也代表了當時的人文主義思潮:19世紀,源于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被引入人文學科并泛濫一時,人文學者從不同立場反對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新批評作為現代主義的批評理論就是這場人文運動的一部分,其意識形態符合人文主義傳承的內在精神,例如,在新批評的代表理論作品《文學理論》中,韋勒克就反對把進化論用于文學研究[3](P307),而這一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經以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傳到了中國。除人文主義之外,主觀意識與精神的概念也被用來反對實證方法在人文領域的濫用,錢鍾書對狄爾泰、克羅齊、柯林伍德等多有征引,他拒斥實證主義,認為文學及其他文化現象由精神心理而非社會形式和物質環境條件決定,實質上反映了心理學思潮與上述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
從中國文化傳統來看,強調格調審美也是中國傳統詩論的顯著特征,正如余婉卉在《〈學衡〉中的古希臘——以吳宓〈希臘文學史〉為中心》一文中認為,吳宓所著《希臘文學史》的精神上屬于《文心雕龍》所代表的中國文學批評傳統,“體現為對文學作品的共時性鑒賞品評,背后是‘文章流別’的觀念”[4],而錢鍾書在《談藝錄》《管錐編》中所采用的著作體例恰是中國傳統詩話的札記體。這種體裁便于摘錄和記載心得,但在連續性和整體性上有所缺失。余婉卉還引用了英國漢學家翟理思認為中國傳統文學研究中整體歷史觀缺乏的觀點來批評吳宓對希臘文學史的書寫。但是,與吳宓不同,錢鍾書卻曾經主張宏觀的歷史視野,例如,他在《論復古》中提到過,有歷史觀念的人不僅要知道“文學的進化”,而且要明白過去與當下的辯證關系,“了解過去的現在性(the presentness of the past)”[1](P330)。《論復古》是錢鍾書為批評郭紹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主張的文學進化論而作。文學進化論將達爾文的進化論運用到文學領域,立足于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肯定“進化”“演變”“革命”,否定“落后”“陳腐”的舊文學,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核心觀念,隨著五四運動的發展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化界。在這篇文章中,錢鍾書認為正確的歷史觀念能夠幫助我們辯證看待新與舊的關系,能讓我們看到現代與傳統是連續統一的整體。錢鍾書的“歷史觀念”類似英國詩人評論家艾略特在其《傳統與個人才能》中倡導的“歷史的意識”,即:“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現存性。”[5](P2)但艾略特并沒有把文學傳統看作歷時性的發展過程,而認為自荷馬以來的所有的歐洲文學組成了一個共時性的存在。[5](P3)除了這一文學傳統觀之外,艾略特也以他的“非個人化”和“客觀對應物”等詩學理論為現代文學批評,尤其是主張文本中心論的英美新批評奠定了基礎。綜合來看,艾略特的歷史意識其實拋棄了歷史、社會和作家個人等文學外部機制,是在文學內部建構成的封閉系統。同理,錢鍾書主張的文學傳統觀同樣也是不同時代文本所構成的封閉系統,摒除了社會歷史、政治、經濟狀況等非文學因素。
總之,錢鍾書認為文學史是人類精神心理的表現形式,并隨著后者的變化而發展,有社會歷史現實無法涵括的維度,他同時強調文學在形式審美上的演變,認為這是機械的因果律難以反映出來的,這種文學史觀對20世紀過于簡單化、機械化的文學史研究范式無疑具有寶貴的補充和反撥價值;但另一方面,如劉鋒杰在辨析錢鍾書“史詩”概念時所指出的,“在文學史上,文學的審美性與其他社會特性是交流、對話與融合的。有意或無意地孤立審美論,就很難把握文學史的全貌”[6]。在此,我們也可以補充說,即使把審美論與超越社會歷史的時代精神相結合,我們仍然無法全面認識文學史,而錢鍾書所標舉的“歷史觀念”實際上擺脫了歷史的社會特征,反映出的恰是其整體歷史意識的匱乏。
二、追求普遍性的批評實踐
錢鍾書主張避免“因世求文”,既指對文學史的考察,又指文學作品的評鑒:在面對具體文本時,強調細讀和直接感受,發掘文本的內在價值,所謂“讀者不必于書外別求宣泄嗜欲情感之具焉”[1](P99)。例如,解讀《錦瑟》一詩時,他首先進行互文比較,認為首聯中的錦瑟暗喻詩歌,頷聯和頸聯借物象揭示創作方法和詩歌風格,尾聯引出樂極生悲的典型心理[2](P434-438)。這說明他采取的是文本細讀法,通過分析意象、修辭以及詩歌結構,探究文本蘊含的普遍心理,反駁了歷史上對《錦瑟》的幾種主要解讀,包括涉及個人際遇的悼亡說和仕途失意說以及反映唐代政治斗爭的影射說。這種文學本體意識在錢鍾書對杜甫的評論上尤為醒目。因為其藝術成就和現實主義意義,杜甫的詩被認為具有史料價值,有“詩史”之譽。但據胡曉明統計,《談藝錄》《管錐編》這兩部作品中所引述、考析的杜甫詩句多達兩百余條,無一涉及杜甫詩載錄的重大史實和杜甫的切身感受,著眼點皆在杜詩的風格、修辭、淵源以及心理學方面的認知等[7]。錢鍾書在《宋詩選注》的序言中曾經直接批評“詩史”觀所代表的實證主義文學研究法,認為文藝批評不等于也不能依賴于歷史考據[8](P3),而近來周景耀梳理了錢鍾書在該書中撰寫的80余位詩人的小傳,發現“小傳的歷史氣息極稀薄,作者身世經歷的介紹付之闕如,亦極少涉及詩人所處之時代狀況”,屬于“‘過濾’了歷史的寫法”。[9]
這種文學本體意識不僅體現在錢鍾書的詩論中,而且體現在其對歷史和哲學典籍的點評中。《管錐編》選評的兩部史籍《左傳正義》《史記會注考證》皆以敘事藝術著稱。在《左傳》的第一篇札記中,錢鍾書就開宗明義地表示自己的立場是文學性,把歷史敘事與小說等文學敘事等同:“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10](P166)《管錐編》中論《左傳》和《史記》的札記有125則,其中逾半數涉及文學,如《隱公元年》論“待熟”之喻,《莊公六年》揭示以空間喻時間的現象,《閔公二年》論語言風格,《昭公五年》引論章法句法,《史記會注考證》中《周本紀》指出求美人笑是中西文學共有題材,《項羽本紀》論人物刻畫,《淮陰侯列傳》歸納小說筆法,等等;而哲學方面,論《周易正義》的27篇中,19篇與文學有關,《焦氏易林》更是被推崇和《詩經》一樣,是四言詩的典范,“《易林》幾與《三百篇》并為四言詩矩鑊”[10](P536),并從意象、修辭等方面詳盡論證了《焦氏易林》的文學價值;另如對于佛典的廣泛涉獵,不究佛理而往往專注于文辭。在散文《作者五人》中錢鍾書品評五位哲學家的文章風格,并表達了想寫一部講哲學家的文學史的愿望。
除文學本體意識之外,錢鍾書的批評實踐往往以人的普遍心理經驗為鵠的,即他在《談藝錄》中所說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2](P1),或“人共此心,心均此理”[2](P286)。譬如在論杜甫詩“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時,錢鍾書認為“望”字通“忘”,把該句解釋為“喪精亡魂”之際“衷曲惶亂”的心狀;與之相較,史學家陳寅恪通過考證唐代宮闕方位,認為“望”是指杜甫“回望”皇宮,“隱示其眷戀遲回不忘君國之本意”[7],也就是說,陳寅恪把杜甫還原到具體的歷史語境,而錢鍾書則捻出當此關頭人所共有的普遍心理。探究普遍心理,必然以普遍的人性觀和藝術的普遍價值為前提,這就可能壓抑作家創作過程必然具有的偶然性和異質性元素。早在18世紀,德國浪漫主義的先驅赫爾德從三個方面否定歐洲從希臘文化到啟蒙運動的普遍主義思維:否定藝術和文化的普遍價值,否定普遍的人性觀,否定人類的共同理想。赫爾德強調文化現象產生條件的特殊性,認為首先要知曉文化的社會語境,才能了解此文化:“一向在北海波濤中經受風浪打擊的人,能夠充分理解古老的北方吟唱詩人的歌謠,這是那些從未見過北方水手搏擊風浪的人們所絕對做不到的。”[11](P40-45)時代不同,境遇各異,如果強行以普遍心理或人性作解釋,難免會有誤讀或籠統之嫌。例如,《衛風·氓》寫主人公和氓自由戀愛并結合,但終為氓所棄,歸家后“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錢鍾書把漢樂府《孔雀東南飛》之“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拿來比較,認為主人公“以私許始,以被棄終,初不自重,卒被人輕,旁觀其事,誠足齒冷。與焦仲卿妻之遭逢姑惡、反躬無咎者不同”。[10](P93-94)就文本內部而言,這確是誅心之論。但近來有論者考證,在《詩經》時代,周禮對于平民的婚姻還未有深入干預[12],還有人從地域出發,認為鄭衛是殷商故地,承襲了自由開放的商族婚戀習俗[13],由此看來,錢鍾書把兄弟之笑解釋為“初不自重,卒被人輕”的譏笑,似乎值得商榷。
探求普遍的文理心理,錢鍾書采用的重要方法之一是“闡釋循環”。關于“闡釋循環”,他在《管錐編》中有一個總結性的定義:
乾嘉“樸學”教人,必知字之詁,而后識句之意,識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義,進而窺全書之指。雖然,是特一邊耳,亦只初桄耳。復須解全篇之義乃至全書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詞”),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詁(“文”);或并須曉會作者立言之宗尚、當時流行之文風以及修詞異宜之著述體裁,方概知全篇或全書之指歸。[10](P171)
首先,如張隆溪所說的,錢鍾書把西方闡釋學傳統和中國古代典籍相呼應,強調字句和全篇之間的“語言循環”,兼及作者的“宗尚”,時代之“流行”。在“語言循環”的基礎之上,錢鍾書的“闡釋循環”進一步涉及文本與作者之間的關系,并且把文本與作者的時代之背景聯系起來[14],但這里需要看到的是,錢鍾書所指仍為“立言”“文風”“修辭”“題材”,于“作者”而言,強調的是作者所推崇、追求的風格,于“時代”而言,強調的是時代流行的審美趣味,所以,此處的作者、時代仍然是錢鍾書形式主義文學史中所指的作者和時代,是缺少社會歷史語境的作者和時代。其次,季進指出,錢鍾書闡釋思想的真正意義在于人類心理的溝通以及在此基礎上對人類審美的共通的感悟,并援引了《管錐編》中的具體案例:錢鍾書解讀“蕭蕭馬鳴”時,引出“鳥鳴山更幽”的意境,并點評歷史上多位詩人對此意境的摹寫,然后聯想到英國詩人雪萊,指出這是中西詩歌共有的意境,進而說明其心理基礎,并歸納出“有見無物”之理,最后據此返回文本,解讀中西多位詩人的作品。[15](P82-84)但在這個交互往復的過程中,將不同時代和國家的詩人放在同一個典型的審美語境中,或被標上普遍的心理特征,罔顧其具體社會語境,這種闡釋策略具有顯著的反歷史主義特征。西方闡釋學萌發于古典時期對荷馬史詩、尤其宗教改革時期對《圣經》的闡釋活動,一開始僅關注語言層面上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到了19世紀,施萊爾馬赫提出闡釋循環原則,并將之擴展到心理層面,主張文本即是作者心理表現和生命片段,但要理解文本和作者心理,須將之還原到作者的生活語境中。之后的歷史學派明確地把闡釋學循環的部分-整體關系轉化成了歷史事件與其所屬生活的關系,狄爾泰更是把闡釋循環看作“歷史意識的普遍手段”[16](P330)。錢鍾書雖然屢次征引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的闡釋論,但他的闡釋循環論消解了他們的歷史維度,否認了文本的歷史性。20世紀哲學家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在歷史意識上更進一步,通過“先見”“前理解”等概念說明闡釋主體及闡釋活動的歷史性,主張通過“視域融合”,構成一種效果歷史意識。錢鍾書也曾提及現代闡釋學的這些概念,但是,就像李清良指出的,錢鍾書所強調的是文本與文本之間,而不是伽達默爾的讀者與文本之間的“視域融合”[17],錢鍾書闡釋循環所建構的是一個封閉的共時性互文系統,既舍棄了古典闡釋學的歷史主義,沒有回到作品的歷史語境,也不具有現代闡釋學的歷史意識,沒有涉及闡釋者歷史語境。
三、以文學為中心的“打通”觀
李清良總結錢鍾書闡釋循環的基本精神在于打破界限、通觀一體,而界之能破,一是因為文本本屬一體,皆由語言構成,再者因為人類文化都有“心同理同”的一面[17],在指出錢鍾書闡釋論對其中西互通,古今貫通,學科打通的治學理路所具有的特殊意義的同時,他還指出錢鍾書打通精神的兩大支點:文學性與普遍的精神心理。也就是說,要打通文史哲等人文學科,錢鍾書借助的是各學科共有的文學性與共通的心理表征。錢鍾書認為經史子集都是“精神之蛻跡,心理之征存”[2](P266),和小說、戲曲一樣,“于心性之體會,致曲鉤幽,談言微中”[10](P227),這就拓展了六經皆史的傳統文化觀,認為六經皆史不僅是因為它們記錄史實,匯編史料,更是因為它們承載了時代的精神心理,對錢鍾書而言,一個時代的思想心理狀態比歷史事件更能呈現歷史本相,“不讀儒老名法之著,而徒據相斫之書,不能知七國;不窮元佑慶元之學,而徒據系年之錄,不能知兩宋”[2](P266)。在《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中,錢鍾書指出,一切文化活動都基于人類的心理意識,“其實一切科學、文學、哲學、人生觀、宇宙觀的概念,無不根源著移情作用”,而心理意識又具有審美性和文學性,“我們對于世界的認識,不過是一種比喻、象征的、像煞有介事的(alsob)、詩意的認識”。[1](P131)既然人的心理是詩意的,那么,一切文化活動和語言建構都有文學性的一面。他在《中國文學小史序論》中申發劉勰“綜觀一切載籍以為‘文’”的觀點:“文者非一整個事物,乃事物之一方面。同一書也,史家則考其述作之真贗,哲人則辨其議論之是非,談藝者則定其文章之美惡。”[1](P102)任何文字篇什都可以有文學特質,即俄國形式主義所謂的文學性,都可讀作文藝作品,這是一種極具包容性的文學概念。所以其獨六經皆史,更可謂六經皆詩:任何文化經典都可成為文學批評和鑒賞的對象,而這正是前文指出的錢鍾書批評實踐的顯著特點,說明了錢鍾書學術研究的中心場域仍然是文學,而他的基本立場是一個“談藝者”。以文史關系為例,他在23歲時發表的《旁觀者》中說歷史上的事實也可分為兩類:野蠻的事實和史家的事實[1](P282)。前者即歷史事件或現象,后者指的是歷史學家的歷史敘述。海登·懷特在《元歷史: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現象》一書中提出歷史話語的三要素:素材、理念和敘述結構,素材即“野蠻的事實”,被史學家以一定的理念理解,塑造成一個故事的形式,并且賦予其一個結合情節結構的象征意義[18](P171),即通過敘事賦予歷史事件關系和意義,所以,歷史文本必然具有一個深層的“詩性”結構。這樣,后現代史學的核心特征就成了歷史文本與歷史事實的剝離,客觀性和真實性被虛構和審美所取代,不再是考證歷史著述的依據。也就是說,早期的錢鍾書已經明確意識到了歷史的虛構性和文學性,與近半個世紀后的新歷史主義主張的“歷史的文學性”不期而同。20世紀40年代的《談藝錄》中有“與其曰‘古詩即史’,毋寧曰‘古史即詩’”[2](P38)的論斷,20世紀70年代的《管錐編》更是反復申言歷史話語的虛構性和文學性。但是,新歷史主義還有主張“文學的歷史性”的另一面,認為文學是滲透了政治意識形態的話語實踐,不可避免地參與了社會實踐。而錢鍾書并沒有如新批評主義那般消解文史之間的二元對立,在他那里,文史之間也沒有實現雙向平等的“互通”,因為于歷史方面,他看重的是歷史敘事而非歷史事實,于文學方面,他輕視文學的歷史關聯和政治意義,可以說,他是站在文學立場上來看待文史關系的。
從學術淵源看,除中國文學批評傳統之外,錢鍾書的打通精神也有由吳宓主導規劃、清華大學實行的博雅教育的影響[19]。無獨有偶,吳宓的另一弟子張蔭麟也以“通人”聞名。但正如張蔭麟指出的打通立足于史學[20],六經皆詩代表了錢鍾書的文學本體立場,文學性是他在面對文化典籍時的主要旨歸。六經皆詩的前提是六經皆史,人文學科呈現的是人類的精神文化,而人的精神心理本質上是詩意的,所以,各類文化文本皆可作文學觀。錢鍾書對“六經皆史”的深化一方面說明了他的開闊視野與辯證思維,其很多洞見溝通中西,承接古今,甚至預示了學術發展走向比如后結構主義對歷史話語的解構;但另一方面,六經皆詩意味著一種“泛美學主義”,正如劉康對諾思洛普·弗萊詩學話語的批評:“(弗萊的)文學的原型乃是人類意識活動(當然主要是情感與想象)最為本真的形式和結構。依此推論,人類意識活動本身便演繹成了審美活動。”[21]可以說,錢鍾書打通的文化觀背后的是對社會歷史的忽視。
四、結語
錢鍾書的學術視野囊括中西古今,對傳統與現代的關系辨析精微,表現出辯證的歷史意識,但縱觀其學術全貌,他的主要著眼點仍是《談藝錄》中所標舉的“文心詩眼”。但正如胡曉明所說的,“這個‘心’‘眼’,乃在心理、智慧、情感類型的審美情趣”[7],也就是說,來自中國古典詩學的“文心”一詞,除文學審美性質之外,被錢鍾書賦予了心理學的內涵,而劉長華在其新近發表的論文中也認為錢鍾書詩學中的“心”融會貫通了中國“心學”和西方的心理學[22]。錢鍾書曾經把美國學者馬科斯·伊斯特曼一本專著的標題“The Literary Mind”直接翻譯為《文心》,而這部書探討的就是詩歌的心理學解讀法。所以,“文心”這一概念恰好代表了錢鍾書學術思想的本質,一方面是共通的文學審美;另一方面是普遍的人類心理,代表著錢鍾書在審美和人性兩個方面對文學研究的拓展。分而言之,“文心”之精神體現在他的文學史觀念上,文學史是時代精神心理影響下文學形式演化的歷史,但也就變成了與現實社會歷史無關的封閉的“歷史”;體現在批評實踐上面,錢鍾書在《談藝錄》和《管錐編》等作品中,多采取語義分析法,在文本內部和不同文本之間循環往復,并時常借助心理學概念,發掘普遍心理和事理,揭示古今中外在觀念與情感上的契合,尋找他們之間對話的可能性,但他對普遍性的追求、文學本體意識及其采用的闡釋原則都忽略了文本與特定歷史語境之間的互動;錢鍾書打通的文化觀,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環境下,以中國傳統學術智慧響應西學潮流,促成不同學科的相互關照,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西方后結構主義對史學話語的解構,但在“文心”精神的統領之下,立足點仍是文化文本共有的文學性和普遍的精神心理,同樣擺脫了具體的時間和空間限定。總的來說,雖然史學是錢鍾書學術研究的重要畛域,他也未曾像后現代史學家那般激進地否認歷史的真實性,但他的文學史思想脫離了社會歷史,其批評實踐和學術精神呈現出普遍主義的特征,其“文心”精神的背后缺少了宏觀整體的歷史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