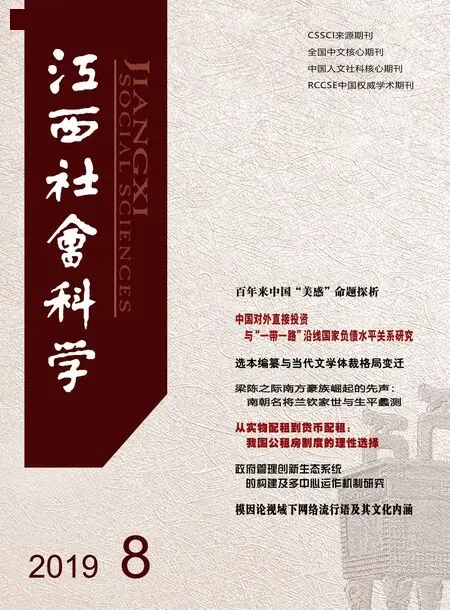漢英兩種語言及思維模式的差異探源
——從“to be,or not to be”談起
劉志成
“語言和思維”是一個完整的整體,相互影響、不可分割。從語言哲學的角度看,英語會提出“to be,or not to be”這樣的問題,而漢語則不會,因為孕育英漢兩種語言的自然環境不同,導致語言的句法和結構不同,進而產生不同的思維模式。英漢兩種語言體現的思維模式,分別表現出“天人二分”和“天人合一”的特點。從這個角度看,“薩丕爾-沃爾夫假說”和以辜正坤為代表的中國學者提出的“語言思維等同論”均有不足之處。
莎士比亞名劇《哈姆雷特》中最膾炙人口的句子“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不僅是該劇中最重要的臺詞,而且可以說是莎士比亞所有戲劇中最具爭議和最重要的臺詞之一。其中文譯本亦是眾說紛紜:朱生豪譯為“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梁實秋譯為“死后是存在,還是不存在——這是問題”;卞之琳譯為“活下去還是不活:這是問題”;孫大雨譯為“是生存還是消亡,問題的所在”;方平譯為“活著好,還是死了好,這是個問題”等。[1](P113)
雖然上述譯文各有千秋,但均有不足之處,因為在漢語的名詞前面沒有冠詞,而英語中的單數可數名詞前一般都會加定冠詞或不定冠詞,而且意思不同,上述各家在處理“the question”時,由于對冠詞的理解不同,譯文也就迥異,比如梁和卞的譯文完全忽略了冠詞;而朱和方的譯文則把定冠詞譯成了不定冠詞;此外,朱的譯文添加了太多的內容,反而有失信之嫌;此句更大的失誤在于對“to be”的處理上,“to be”在印歐語系中不僅具有系詞的作用,還有“存在”的含義,甚至可以說是西方形而上學的哲學基礎和出發點,古希臘語中本體論范疇“being”就是從“to be”演化而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講,由于“to be,or not to be”在漢語中沒有嚴格對應的詞,因此這句話實際上是不可譯的。
本文試圖從語言哲學的視角探索漢語為何不可能提出“to be,or not to be”這樣的哲學問題,而以英語為代表的印歐語系為何會提出這樣的哲學問題,從而能為進一步探索語言與思維如何相互影響提供重要的理據,這不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to be,or not to be”這句話的深刻含義,而且能更好地理解“薩丕爾-沃爾夫假說”的不足之處。同時,能進一步理解印歐語系的語言學家為何往往會提出“語言決定論”和“語言思維相互獨立論”這樣的觀點,而以辜正坤為代表的中國學者為何往往會提出“語言思維等同論”這樣的觀點。
一、中西語言產生的物質基礎
要從根子上探索以英語為代表的印歐語系為何一定會提出上述哲學問題,而中文世界為何一定不可能提出上述哲學問題,我們首先要探索英漢語言產生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什么樣的環境一定會產生出以英語為代表的印歐語系?什么樣的環境一定會孕育出漢語這樣的語言系統?“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2](P603)自然環境相對于社會環境來說,可以說是更基礎的環境,對語言的產生和發展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可以想見,人類作為自然的直接產物,一定會帶上某一地域的某些特點。“我們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據的土地當作是一種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這地方的自然類型和生長在這土地上的人民的類型和性格有著密切的關系”[3](P123),“從物理方面看,也就是從自然條件方面來看,影響人類文化發展的第一因素是生態環境,也可以說是地理環境”[4](P22)。
(一)漢語系統產生于“天人合一”的自然環境
中華文明起源于黃河中下游地區,河南、陜西境內的仰韶文化是中華文明的第一縷曙光。“中國,在其歷史的黎明時分,同埃及和巴比倫一樣,都是起源于大河文明的帝國……黃河造就了中華文明。”[5](P147)中國的地理環境是,東部是大海;北部是沙漠,再往北就是西伯利亞,冰天雪地不適合居住,更不適合農耕;西部是高原、高山和沙漠;南部是崇山峻嶺和熱帶大林莽。中國處在一個與外部世界相對隔絕的環境中,而這些自然環境對于遠古初民,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的情況下起著極大的限制作用。而長江和黃河中下游地區水源豐沛、土地肥沃,非常適合農耕,因此,誕生于長江和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中華文明最主要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就是農耕文明。農耕文明最典型的特點就是靠天吃飯和定居生活。靠天吃飯就意味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夏長、不違農時;定居生活就意味著和諧共處、群己合一、樂天知命、尚同不爭。
農耕文明帶給原始初民最直接的身體經驗和心靈經驗,或者說對中華文明的思維方式的影響就是“天人合一、順應自然”。隨著人腦的不斷進化和社會的發展,語言的產生既有了物質基礎,又成為客觀需要。“一句話,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有些什么非說不可的地步了,需要產生了自己的器官。”[2](P236)語言的出現進一步促使了文字的出現,漢字的造字方式體現了典型的“天人合一”的特點。“漢字的制字理論為‘六書’,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轉注。”[6](P89)但象形又是漢字制字理論的基礎,其他制字方式都是以象形為基礎的,因為在表意過程中,為了克服“畫成其物”的局限,而通過會意等進行了抽象概括。“漢字最初的形式是對事物的描繪。現在所使用的普通漢字中有大量的字屬于這樣的圖畫,中國人稱之為‘意象’……這些字在它們的原始階段必定提供了更完整更詳細的圖畫,為了使用方便,這些圖畫被省略成了很少的筆畫。”[7](P33)這也就是古人所謂的“以形狀物、合形會意、象形為本”。可以說漢字意象的基本途徑就是“天人合一、觀物取象”,而“天人合一、觀物取象”正是漢字構成的內在邏輯,這種內在邏輯既是原始初民身體經驗和心靈經驗的體現,也會進一步對他們的身體經驗和心靈經驗造成影響,并且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經驗就會慢慢地固定下來,逐漸形成一些概念。
(二)印歐語系產生于“天人二分”的自然環境
西方文明的發祥地在地中海東部愛琴海的克里特島上。地中海沿岸有三個非常典型的特點。
其一,這些區域隨處可見大面積的石灰巖和貧瘠的土壤,氣候冬季溫暖濕潤,夏季干燥炎熱,很難發展農業經濟。特殊的地理環境使人們不得不向海上發展,“航海業是克里特人經濟活動中一種最重要的行業。在古希臘傳說中有一種概念,即克里特人的艦隊是無敵的”[8](P99)。
其二,地中海地區海陸交錯,島島相望,海岸線長,由于出口海峽較淺,水流不能與外海自由流通,導致地中海潮汐不驚、波瀾不作、海深鹽高、港口林立,非常適合航海,即便航海技術不高的人也敢于去迎接大海的挑戰。于是,以血脈為基礎的家族、宗族和氏族社會慢慢解體,人們紛紛到別地開疆拓土,建立新的商業城邦,航海、經商成為人們重要的謀生手段。這樣的物質基礎讓西方人注重以個人為本位,比如,英語中姓名的書寫,會把代表個人的名放在代表宗族觀念的姓的前面。而且,冒險擴展、開拓進取的思維模式亦誘導了英語定語后置,從而造成英語句式向外擴展的張力等。“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是同時也鼓勵人們追求利潤,從事商業。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壤里,把他卷入到無窮的依賴性里邊,但是大海卻挾著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為的有限的圈子。”[3](P134)
其三,古希臘自然地理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小島林立,整個希臘全境基本都被天然屏障分割成大大小小、相對孤立的小區域,比如愛琴海諸島、阿提卡半島、米利都島、羅得島等。“沒有一個偉大的整塊。……相反地,希臘到處都是錯綜分裂的性質。”[3](P207)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希臘人的政治心態,促成他們的城邦社會結構的出現,也陶冶了他們崇尚個人自由、個性獨立的基本性格。
西方的地理環境帶給西方原始初民的身體經驗和心靈經驗,或者說對西方人的思維模式的影響,那就是“天人二分”也即是“天人相爭”的思想。具體來講,西方特色的思維方式就是:主客對立、征服自然、個人本位、崇力尚爭、開拓冒險等。
綜上可知,中西不同的地理環境帶給中西原始初民不同的心靈體驗,從而形成不同的概念系統,漢語體現了典型的“天人合一”的思維特點,而以英語為代表的印歐語系體現了典型的“天人二分”的思維模式,印歐語系的文字完全斬斷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你看到這種拼音文字以后,不可能立刻把這種文字跟外部自然界聯系起來,因為它已經失掉了人這個主體和外部自然界客體之間息息貫通的誘導因素。”[4](P119)但是,由抽象符號組成的印歐文字回環勾連、綿綿不絕,很注重發現事物之間的邏輯關系,并且善于推理和進行形而上的哲學思考。
二、語言與思維的關系
不同的自然環境帶給中西方原始初民不同的心靈體驗,不同的心靈體驗會慢慢產生一些概念,進而形成概念系統,不同的概念及其系統其實就是不同思維模式的反映。語言,作為思維的物質外殼,反映了思維的聯結方式,而這種聯結方式就是語言的詞法和句法結構。“在內在或外在的言語中,語言也起著組織思想的作用,并由此決定著觀念的聯結方式,而這種聯結方式又在所有的方面對人產生著反作用。”[9](P267)
“語言與思維,言語與思維的相互關系問題,是屬于最復雜和最有爭議的問題之列的。”[10](P44)有些學者抹煞了語言與思維的界限,比如:“我們在思維時總會不知不覺地以語言想問題,雖然沒有說出口,但是卻有一種語言流動,我們的思維實際上就是我們的語言。”[11](P234)還有一些學者過分強調語言的決定作用,如“薩丕爾-沃爾夫假說”提出的“語言決定論”和“語言相對論”。“語言相對論原則,用通俗的語言來講,就是使用明顯不同的語法的人,會因其使用的語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觀察行為,對相似的外在觀察行為也會有不同的評價;因此,作為觀察者他們是不對等的,也勢必會產生在某種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觀。”[11](P235)還有一些西方學者認為語言與思維是相互獨立的:“觀念的形成是一個獨立的過程,稱為思維或思想,這一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與具體語言的特征無關。”[11](P219)
“語言是‘糾纏著’精神的物質。”[12](P61)這就表明,語言與思維緊密地糾纏在一起,不可分割。現在的問題是,語言與思維是如何糾纏在一起的?究竟是如何不可分割的?“語言決定論”“語言與思維相互獨立論”這些見解為何一定會在印歐語系這樣的話語體系中產生?它們產生的語言學基礎是什么?這些都是本文試圖解答的問題。筆者認為,語言與思維的關系,就是語言和思維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二者相輔相成、相互影響、不可分割,沒有無語言的思維,亦沒有無思維的語言,二者是同時出現的,亦是同時消失的,詞語缺失之處,無人出場。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
第一,語言是借助思維產生的,思維也是借助語言產生的。語言的產生是由于抽象思維的發展,抽象思維是與意義聯系在一起的,有些動物能發出幾十種聲音,但那是它們的本能,與抽象思維無關,故不能稱之為語言。同樣,思維的產生也借助于語言,隨著人類的生產、生活等社會實踐的發展以及大腦的進化,使人腦具備了進行抽象思維的物質基礎,但抽象思維只有在語言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
第二,語言和思維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二者相互影響、相互照應、不可分割。一定的思維模式總會通過一定的語言特點表現出來,反之亦然。考察一個民族的思維模式特點往往可以從考察該民族的語言特點中一窺端倪。“一個人的思維形式受制于他沒有意識到的固定的模式規律。這些模式就是他自己語言的復雜的系統,它目前尚未被認識,但只要將它與其他語言,特別是其他語族的語言做一公正的比較和對比,就會清楚地展示出來。他的思維本身就是用某種語言進行的—英語、梵語或漢語。”[11](P272)因此,對比不同民族的語言,可以探索各民族的思維模式的差異。
第三,薩丕爾、沃爾夫的“語言決定論”以及一些學者所謂的“語言思維相互獨立論”,恰好是受到印歐語系誘導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影響;而中國學者辜正坤的“語言思維等同論”恰好是受漢語系統誘導的“對立轉化”和“辯證統一”的思維模式的影響。這些觀點恰好從另外的角度深刻地證明,“語言和思維”是一個完整的整體,是相互影響、不可分割的。
綜上可知,語言與思維是同質而異名的不可分割的整體,而且相互影響,不同語言的聯結方式則體現了不同的概念系統和思維模式。
三、英漢語不同的語法特點與各自體現的思維特點
語言與思維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相互影響、不可分割,思維的特點往往通過語言的特點表現出來。“思維結構與語文結構是互構的。”[4](P131)因此,我們可以通過考察英漢兩種語言的詞法和句法,考察英漢兩個民族的思維模式特點。
(一)辯證統一與二元對立
漢語語言特點往往會誘導出陰陽互補、辯證統一的思維模式;以英語為代表的印歐語系的語言往往會誘導出“to be,or not to be”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
漢語語法特點極其通融、圓滿和辯證,尤其是古漢語,甚至沒有標點的存在,體現了極其深刻的悟性思維和辯證思維。漢語語法包含漢語的詞法和句法。首先,從漢語的詞法上看,漢語沒有印歐語系的性、數、格的變化和詞尾變化,這就讓漢字的定位功能極其靈活,而且漢字的詞性轉化能力極其強大,名詞動用、動詞名用、形容詞動用等現象極其普遍,尤其是在古漢語中,比如《史記·項羽本紀》中“沛公軍霸上”和“范增數目項王”此處的“軍”和“目”即名詞動用;動詞名用的例子也很多,比如《曹劌論戰》中“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此處的“伏”即動詞名用為“伏兵”;其次,漢語中有些漢字,比如“米”“回”,從四面八方看,都表示同樣的字,體現了非常通融的味道;再次,從漢語的句法來看,漢語句子的寫法,起筆可以從左至右,亦可以從右至左,還可以從上到下,句子的寫法不是單向的,是通融和辯證的。
此外,由于漢語沒有詞尾等外在形式的變化,句子的構成方式也極為靈活,很多句子的讀法是雙向的,而非單向的,且意義可以一樣,也可不一樣。漢語的這種辯證思維和悟性思維能力尤其體現在一些對聯上,如“上海自來水來自海上”,下聯可以有“黃山落葉松葉落山黃”“南江客運站運客江南”等,這些對聯從左至右以及從右至左的讀法和意義是一樣的。老子在他的哲學理念中深刻地表達了漢語的這一特點:“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如果我們用字母表示的話,那就是,A可以是A,也可以是B;或者說A可以是A,也可以是非A。漢語的這種語言特點以及對漢語的哲學思維體現得最為充分的就是太極圖,陰中含陽,陽中含陰,這就是老子所謂的“一陰一陽謂之道”。而對于陰陽的關系問題,或者說上升為哲學的最高問題,就是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問題,漢語思維中一定不會思考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一定不會思考誰決定誰的問題,因為二者本是一體的、辯證統一的,而且是相互轉化的,這也就是老子所謂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正是漢語最重要的哲學身份之一。
英語的詞法和句法體現了非常嚴格的理性,這也是誘導出非此即彼、二元對立哲學的語言學基礎。首先,從詞法上看,英語單詞有嚴格的性、數、格,有嚴格的詞尾變化,一個單詞,如果被名詞動用或者動詞名用,也必須有相應的詞尾變化,比如:“She babies her child.”“The escaped prisoner was cornered at last.”其次,從句法上看,英語句子的寫法只能是單向的,英語句式的表意功能往往是非常精確的,很難引起歧義。比如,句子賓語即便放在句首,處于主語的位置,如果使用的是賓格,讀者也很清楚地知道其語法功能是賓語,比如“Him love I”,表達的意思仍然是“I love him.”可見,英語語法往往會非常明確地告訴讀者誰是主格、誰是賓格,賓格不能成為主格,反之亦然。用字母表示就是A就是A,B就是B,這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如果從哲學的層面回答,那就是“to be,or not to be”,這也正是二元對立的語言學理據。
(二)消失與存在
漢語哲學思維的最高形式就是追求“消失”或“無”;“to be”在英語中還有表示“存在”的含義。英語的語法體系為何一定會誘導出表示“存在”的邏輯思維,而漢語恰好相反,完全不能誘導出“存在”的邏輯思維,反而會誘導出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邏輯體系呢?
首先,從漢語的詞法來看,盡管漢字的造字方式是“六書”,但其基礎仍然是象形,會意等造字法都是以象形為依托而進行的抽象與概括。漢字體現了極為典型的“天人合一”的象形意味,所謂“天人合一”就是“主客合一”或者叫“物我合一”,追求的是認知主體與客體的“合一”,追求的是認知主體的自我消失。漢字對漢人心理意象的影響就體現在莊子的“萬物與我齊一”。同樣,《易經·乾卦·文言》亦指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其次,從漢語的句法來看,盡管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借用西方拉丁語系的句法來闡釋漢語句法,但一直受到眾多學者的質疑。“由于漢語重內在意念而不重外在形式,漢語的句型也就難以像英語那樣以謂語動詞為中心從形式上去劃分。”[13](P61)而且,中國傳統古典漢語在嚴格意義上講是沒有句法的,甚至標點符號都沒有,當然,我們亦可以把漢語的句法理解為沒有句法的句法。“中國古書幾乎無法加標點,因為它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標點符號屬于西方文法范疇。在這樣的情況下,加在中國古書上的標點,就帶有任意性,也就是說,‘點’在很多地方都‘說得通’,這使得古文成為含義豐富的寶藏。”[14](P283)說到底,漢語的語法就是沒有語法的語法,漢語語言是一種典型的悟性語言,漢語的邏輯是隱性邏輯,比如“不到黃河心不死”,譯成英語則一定要添加主語以及表示顯性邏輯的連接詞:Ambition never dies until all is over。
漢語詞法的“天人合一”以及句法的“隱形邏輯”誘導出漢語的悟性哲學思維,同時誘導出漢語哲學思維的最高境界就是“無”。這一點在老子的哲學思維中體現得最為充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道德經》還指出:“大方無隅、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無”可以說是中國哲學思維的最高境界,尤其中國古代的建筑物,深刻地體現了主客一體、人物交融的哲學思想。“中國的建筑不太注重主體與客體截然分開,恰恰相反,它們的整體布局與建構常常追求的是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之間渾化無痕的境界與意趣。”[4](P144)觀看中國傳統建筑物,比如寺廟、比如天安門,遠遠望去,就像一個繁體的“無”字。可見,中國人的哲學思維永遠不可能去追求“to be”似的存在,更不會糾結于“to be,or not to be”。
英語的詞法與句法與漢語恰好相反。首先,英語的詞法是顯性的,也就是英語單詞的性、數、格等語法形式必須是顯性的,也可以說是剛性的;其次,英語單詞的詞綴形式也是剛性的,不可缺失,更不可省略;再次,從句法上看,英語句子主次分明、顯性邏輯、嚴密規范,句式呈現“聚集型”(compactness),比如:“Seen from the hill,the school looks more beautiful.”分詞短語與主句的邏輯關系主次分明。可見,英語句子盡管往往很長,但由于有形態標志以及表示顯性邏輯關系的連詞,同時詞語之間在性、數、格等方面需要一致,因而句意明確,層次分明。可以說,英語語法追求的是一種顯性的、存在的、剛性的邏輯。這種語法特點對使用該語言的民族的思維模式也有深刻影響。西方人追求個人主義,喜歡標新立異、彰顯個性;西服的構成包括襯衫、領帶、馬甲、外套,層次分明、邏輯清楚,而中國傳統的長袍服飾很難看清這種顯性邏輯和層次,誰能說不是受到各自語言的深刻影響呢?西方的建筑,不論是埃菲爾鐵塔,還是華盛頓紀念碑,遠遠望去,更像是一個彰顯自我的大寫的“I”,它們體現的氣質和風格與中國的天安門是完全不同的。由此可見,以英語為代表的印歐語系的民族更傾向于追求一種顯性的邏輯和存在,從哲學的層面講,一定會追問“to be,or not to be”。
(三)話題結構與主謂結構
漢語的詞法和句法體現了“天人合一”“主客合一”的主體思維模式;而英語的詞法和句法則體現了“天人相爭”“主客二分”的客體思維模式。“主客二分”的語言系統往往會誘導出“to be,or not to be”的對象性思維的思維模式。
首先,漢語詞法主要是基于象形和會意,體現了典型的“天人合一”“主客合一”的思維模式;其次,漢語的句法同樣體現和誘導了“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漢語句法的“天人合一”主要體現在漢語的句式主要是話題結構,而不是主謂結構;而這種話題結構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了“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而對于話題結構的句式的理解,也往往是基于類比、語境以及橫向的相關性聯想。“漢語缺乏嚴謹的主謂結構與中國的傳統哲學思想密切相關。”[13](P60)
漢語“主客一體”的思維模式往往導致漢語句式中的主語既可以顯現也可以隱藏,甚至可以變換。“西洋的語法通則是需求每一個句子有一個主語的,沒有主語就是例外,是省略。中國的語法通則是,凡主語顯然可知時,以不用為常,故沒有主語卻是常例,是隱去,不是省略。”[16](P52)但是漢語中隱去的主語,如果翻譯成英語,必須按照“主客二分”的原則,讓主語顯性化。比如:“他有個兒子,()在昆明工作,()已經打電話了,()明天就能回來。”此句話譯成英語必須添加相應的主語:“He has a son,who is working in Kunming.Someone has called him,and he will be back tomorrow.”漢語思維中的“主客不分”或者叫“主客合一”甚至在邏輯上引起歧義,只有按照“主客二分”的原則譯成英語才能理解其真正含義,比如“曬太陽(to bask in the sun)”“吃食堂(to have meals in the cafeteria)”“救火(fire fighting)”等。可見,漢語的“主客一體”也叫“主體性思維”的思維模式很難誘導出對象性思維,也即是很難誘導出“to be,or not to be”這樣的思維模式。
英語的詞法和句法體現了典型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而“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又進一步強化了英語的詞法和句法特點。首先,從英語的詞法來看,看不到任何象形和會意的痕跡,英語字母都是一些抽象的符號,斬斷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體現了“主客對立”,但是這種抽象的符號很善于進行形而上的哲學思考;其次,從英語的句法來看,英語的主謂結構深刻地體現了“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
(四)人稱主語與物稱主語
漢語思維中的“主客合一”與英語思維中的“主客二分”在各自句法中還表現為“人稱主語”與“物稱主語”。“人稱主語”也即是漢語主體性思維的體現,“物稱主語”是英語客體性思維,也即是對象性思維的體現;反之,“人稱主語”和“物稱主語”又進一步強化了漢英語中不同的思維模式。而“客體性思維”往往誘導出“to be,or not to be”關于客體的存在性的哲學思考,而主體性思維卻不會。
受“天人合一”和“主客合一”的主體性思維的影響,漢語句子的主語往往需要人來充當,強調“事在人為”。正如洪堡特所言:“漢語是一種充盈著人的主體意識、具有很強的人文性的語言。”[13](P117)如果主語很難確定,則會采用泛指的方式,比如“人們”“某人”“有人”等;如果使用被動語態,漢語句式中的施動者也必須說出來。“中國正常的被動式是必須把主事者說出的。”[16](P129)漢語的這種句式特點主要是由于受漢語“主客一體”的思維模式的影響,中國人認為,認識自己就等于認識客觀世界,同樣,認識客觀世界亦與認識自我是一致的,這一點在中醫思想中得到非常充分的體現。中醫認為,獨立于人的精神世界之外的客體“天”與作為具有主觀意識的“人”本質上是同構的,因此,人體器官的運行規律與客體“天”的運行規律亦是一致的,比如“肺經當令”“膽經當令”也就自然對應于天體運行的相應的時辰。“漢語思維模式有主觀性的特征,表現為主客不分,主體介入客體,客體融入主體。”[11](P116)漢語中的“情景交融”其實就是“天人合一”“主客合一”思維的具體體現,漢語這種“主客交融”的主體思維模式自然不會誘導出“to be,or not to be”這樣的哲學思維。
英語思維是典型的“主客二分”,客體是作為人認知的對象,因此,以英語為代表的印歐語系往往以物稱作主語,區分自我意識與認識對象,從而誘導出對象性思維或客體性思維。比如:我突然明白地球是圓的。(It dawned on me that the earth was round.)英語的被動語句,也往往使用物稱主語,而且盡量讓動作的發出者隱藏不見,更能體現英語的客體性思維和對象性思維。而在漢語中,受到“主客一體”以及“萬物皆備于我”的思維的影響,漢語的被動句中也往往要把動作的發出者說出來。“漢語在形式上,‘被’字底下一般要有賓語,表示主動者。”[17](P87)
英語的非人稱傾向是西方“主客二分”思維的具體體現,認知主體與認知對象界限分明。對象性思維往往會誘導出關注客體的“存在”與否,因此,客體思維亦是西方“to be,or not to be”思維的語言學理據。
四、結語
語言模式與思維模式相互影響、不可分割。對比英漢兩種語言產生的物質基礎,可以發現,不同物質基礎孕育不同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模式。以英語為代表的印歐語言系統為何一定會誘導出“to be,or not to be”的思維模式,而漢語恰好不能,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to be,or not to be”在漢語語言系統中具有不可譯性。英漢兩種語言及其產生的思維模式,歸根到底,分別體現了“天人二分”和“天人合一”的特點。漢語“天人合一”的辯證統一的思維決定了中國人不可能提出關于“to be”這樣的問題,而西方人提出的“to be,or not to be”則體現了典型的二元對立的哲學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