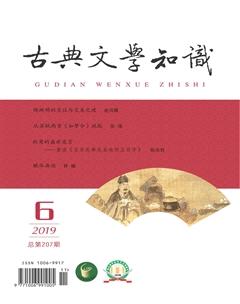古典詩詞的理解與誤解(三十)
鐘振振
雨中過舒教授
[宋]蘇軾
疏疏簾外竹,瀏瀏竹間雨。窗扉靜無塵,幾硯寒生霧。美人樂幽獨,有得緣無慕。坐依蒲褐禪,起聽風甌語。客來淡無有,灑掃涼冠履。濃茗洗積昏,妙香凈浮慮。歸來北堂暗,一一微螢度。此生憂患中,一餉安閑處。飛鳶悔前笑,黃犬悲晚悟。自非陶靖節,誰識此間趣。
關于“飛鳶悔前笑”
陳邇冬先生《蘇軾詩選》注曰:“《墨子·魯問篇》:‘公輸子削竹木為飛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墨翟卻說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劉(鏤)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他以為‘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作者借此自嘲濟世無功,巧不如拙。”(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頁)
按:“飛鳶”與“飛鵲”字面不同,并非用《墨子》。其語當出自晉袁宏《后漢紀》卷七《光武皇帝紀》第七:“(建武)十九年……二月,封援(按,馬援)為新息侯。設牛酒勞軍士,因撫觴而言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人生一世,但求衣食,仕宦不過郡掾吏,守墳墓,護妻子,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安用余為?”當吾在浪泊西時,下潦上霧,毒氣浮蒸,仰視飛鳶阽阽墮水中,憶少游語,何可得也!……”又,《后漢書》卷二四《馬援傳》:“(援)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阽阽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蘇詩此句,是對馬援故事的合理演繹,謂馬援過去或曾笑話從弟馬少游胸無大志,只想在家鄉做小吏;等到自己率軍南征,歷經兇險,當“下潦上霧,毒氣浮蒸,仰視飛鳶阽阽墮水中”之時,方后悔自己此前對從弟之語的不以為然。
此典為宋人所常用,如宋庠《贈潯州朱祠部》詩曰:“路控驛疆逢瑞翟,氣收炎浦見飛鳶。”劉敞《寄閬州諸弟》詩曰:“傳聞吞夢澤,想見墮飛鳶。”文同《武溪深》詩曰:“仰視高飛鳶,阽阽墮兩翼。”劉摯《酬寄》詩曰:“飛鳶未妨隨溪水,黃茅正使侵庭除。”王安石《游土山示蔡天啟秘校》詩曰:“一官初嶺海,仰視飛鳶阽。”郭祥正《武溪深呈廣帥蔣修撰》詩曰:“漢兵卷甲未得渡,飛鳶阽阽墮且沉。”李綱《循州道中作》詩曰:“山頂濛濛遮薄霧,江心阽阽墮飛鳶。”黃公度《與方稚川》詩曰:“南來厭見阽飛鳶,之子相逢意凜然。”陸游《獵罷夜飲示獨孤生》詩三首其二曰:“一樽共講平戎策,勿為飛鳶念少游。”皆是其例,并可參看。又,蘇軾詩集中,用“飛鳶”字僅兩處,別首《山村五絕》其五曰:“不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亦用此典,足資佐證。
壺中九華詩
[宋]蘇軾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窗欞然。予欲以百金買之,與池石為偶,方南遷,未暇也。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紀之。
清溪電轉失云峰,夢里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玉女窗虛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碧玲瓏。
關于“清溪電轉失云峰,夢里猶驚翠掃空”
陳邇冬先生《蘇軾詩選》說曰:“電轉,言水道轉過之快;云峰,指壺中九華石。作者行程匆匆,所以這樣說。翠掃空,亦謂九華石。作者非常傾心這九華石,似為前所未見,而一見難忘,故云‘夢里猶驚。又作者過去‘每逢蜀叟談終日,便覺峨嵋翠掃空,今見九華石奇絕,難免不因它而聯想到而將它視作他的家山峨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60—261頁)
按:這首詩題雖作“壺中九華”,內容雖以九華石為中心,但開頭二句的寫法卻非“頓入”——直奔主題,而是“漸引”——先從真山寫起,說自己在旅途中曾見過自然界酷似這九華石,卻比這九華石高大千百倍的連綿奇峰,只可惜清溪水急,客舟電轉,眼前群山,稍縱即逝;但盡管如此,那連峰蒼翠、拂掃天空的奇觀,還是深深地楔入記憶之中,夢里重見,猶自動魄驚心。
壽星院寒碧軒
[宋]蘇軾
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為問鶴骨何緣肥。
關于“紛紛蒼雪落夏簟”
錢仲聯、錢學增先生《宋詩精華二百首》:“蒼雪:喻飛花。夏簟:夏日用以遮陽的竹席。”(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頁)
按:從宋人修辭習慣的角度來審視,錢先生“蒼雪喻飛花”說是不能成立的。誠然,“雪”可比喻白色的花。但關鍵問題在于,“雪”前面加了個“蒼”字,是否還能夠比喻花?遍檢宋人詩詞里的“蒼雪”,找不出任何一例可以確鑿無疑地指認作“飛花”。從氣象學的角度來審視,此讀解也不能成立,因為蘇軾此詩寫的是杭州,地處溫帶,在正常情況下,夏天不會下雪。
筆者以為,此處的“蒼雪”是指竹粉。清汪灝等《廣群芳譜》卷八二《竹譜》引《格物總論》:“竹……初出地為筍,筍節有籜包之。及成莖抽之,而籜遂漸次脫落,脫落處有粉。”竹色青蒼,而其粉似雪,故以“蒼雪”擬之。這是蘇軾的原創,此后襲用者甚多。如宋周紫芝《次韻子紹游壽星寺寒碧軒》詩:“好竹連山萬壑青。落星天近接飛甍……閑來卻倚朱欄看,蒼雪依然入句清。”周必大《曾無疑三異以長韻送金橘時已暮春次韻》詩:“客言采果孟冬月。剖竹為符帶蒼雪。”又《茶園王琰求清暑堂詩次王民瞻敷文胡邦衡》詩:“亹亹清風揮麈落,紛紛蒼雪著笙寒。”李石《題王氏款竹亭》詩:“春林扇溫風,夏簟落蒼雪。”曾極《金陵百詠·射殿》詩自注:“有七十間,旁多槐竹。”詩曰:“鶴蓋陰陰覆苑墻,更添蒼雪助清涼。”徐照《題永州唐德明竹園》詩:“忽驚殘粉飄蒼雪,最喜幽聲勝遠灘。”史彌寧有詩序曰:“周晦叔所宅之左,一坡隱然而高,有竹萬個,架小軒于翠霧蒼雪間,日彈琴讀書其下。”韓淲《次韻昌甫》詩:“山風吹夏籜,蒼雪落紛紛。專壑紫苔古,掩關青竹深。”又《有竹堂》詩:“坡翁一轉語,不但為竹設。俗子塵污人,夏簟落蒼雪。”方鳳《翠微樓對竹會飲》詩:“縹渺飛樓修竹里。珠簾半卷清風起……楚調歌殘仍擊節。檐外紛紛落蒼雪。”張炎《風入松·贈蔣道錄溪山堂》詞:“舊家三徑竹千竿。蒼雪拂衣寒。”又《南鄉子·竹居》詞:“蒼雪紛紛冷不飛。”又《壺中天·白香巖和東坡韻賦梅》詞:“半樹籬邊,一枝竹外,冷艷凌蒼雪。”皆是其例。
至于“夏簟”,從宋人修辭習慣的角度來審視,錢先生“夏日用以遮陽的竹席”說仍不能成立。誠然,在日常生活中,“竹席”可以用作遮陽的涼篷;但遍檢宋人詩里的“夏簟”,也找不出任何一例可以確鑿無疑地指認作“夏日用以遮陽”的涼篷。
筆者以為,“夏簟”乃臥具,即夏天鋪在床上的竹制涼席。唐杜甫《鄭駙馬宅宴洞中》詩:“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清瑯玕。”元稹《友封體》詩:“雨送浮涼夏簟清,小樓腰褥怕單輕。”宋梅堯臣《依韻和磁守王幾道屯田暑夜懷寄》詩:“夏簟且安寢,明星上東城。”黃庭堅《和庭誨雨后》詩:“小霽臥觀書,涼軒夏簟舒。”釋覺范《復次元韻》詩:“朅來湘尾寄城寺,夏簟清涼便晝眠。”又《快亭》詩:“佳眠夏簟便光滑,醉耳松風喜再過。”又《題通判學士適軒》詩:“小軒只著竹匡床,散發陶然夏簟涼。手倦拋書成午睡,夢回雙頰帶茶香。”朱翌《竹枕》詩:“方床洗湘斑,夏簟織蘄笛。誰與同臥起,青奴甚相得。”張九成《題竹軒》詩:“春禽一聲杳,夏簟五更涼。”吳泳《送成都添倅李微之分韻得巫字》詩:“秀水穩宜眠夏簟,惠泉香可煮秋菰。”皆是其證。
要之,蘇詩此句承上“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而來,是說竹粉隨清風飄入窗戶,紛紛灑落在臥榻的竹席上。
關于“道人絕粒對寒碧”
錢仲聯、錢學增先生《宋詩精華二百首》:“道人:此指道士。”(同上)
按:從宗教和歷史地理等兩個不同的角度來審視,錢先生的“道士”說是不能成立的。
誠然,“道人”可以用來指稱道士,但在古代,“道人”是修道者的通稱,亦可用來指稱僧人、佛教徒。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德行》:“高坐道人不作漢語。”南朝梁劉孝標《注》:“《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唐李白《送通禪師還南陵隱靜寺》詩:“道人制猛虎,振錫還孤峰。”韓愈《杏花》詩:“居鄰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明年更發應更好,道人莫忘鄰家翁。”注曰:“道人,謂寺僧。”又《送僧澄觀》詩:“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柳宗元《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孟郊《聽藍溪僧為元居士說維摩經》詩:“古樹少枝葉,真僧亦相依。山木自曲直,道人無是非。”白居易《題天竺南院贈閑元旻清四上人》詩:“竹寺過微雨,石徑無纖塵。白衣一居士,方袍四道人。地是佛國土,人非俗交親。”宋楊億《通道人歸西京》詩:“風塵不肯留京邑,龍象重歸啟梵筵。”余靖《廬山承天歸宗禪寺重修寺記》:“初,有日者言師相有異表。師聞之曰:‘吾學佛者,異欲何求?遂以沙瞇其目,輒有流星之應。時人因其瞼赤,呼為‘赤眼道人。”釋契嵩《鐔津集》卷一《輔教編》上《勸書》第一:“吾視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于道人惟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于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為異耳。”曾肇《滁州龍蟠山壽圣寺佛殿記》:“道人曇廣,傳禪學者也。始居龍蟠山之壽圣寺,有僧廬而無佛殿,乃與其徒歸式、元祐、希受、紹安并力營之。”皆是其證。
既然如此,則判斷蘇軾此詩中的“道人”究為道士抑僧人的關鍵,就在于能否考證清楚所謂“壽星院”到底是道教的宮觀還是佛教的寺廟。檢宋施諤《淳祐臨安志》卷六《樓觀》載:“江湖偉觀:舊在葛嶺壽星寺。”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七九《寺觀》五《寺院》亦載:“壽星院:在葛嶺。天福八年建。有寒碧軒、此君軒、觀臺(即今‘江湖偉觀)、杯泉,東坡皆有詩。”據此,則“壽星院”自是佛教寺院;那么,蘇軾此詩中的“道人”就只能是僧人而不可能是道士了。
關于“為問鶴骨何緣肥”
錢仲聯、錢學增先生《宋詩精華二百首》:“何緣肥:怎么肥得起來。”(同上)
按:“何緣”有“何由”義。錢先生所取,即此義。然而它還有“何故”一義,如唐韋應物《詣西山深師》詩:“曹溪舊弟子,何緣住此山。”唐彥謙《題虔僧室》詩:“何緣春恨貯離憂,欲入空門萬事休。”宋彭汝礪《到雄州不得家書》詩:“只有瓦橋書可附,何緣不寄一聲來。”徐積《姚黃》詩:“帝女何緣心好道,阿嬌安用金為房。”黃公度《秋夜獨酌》詩:“可是離人更遺物,何緣身世兩無求。”朱熹《次范碩夫題景福僧開窗韻》詩:“昨日土墻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通塞,明暗何緣有去來。”楊萬里《三月三日雨作遣悶絕句》詩:“遲日何緣似個長。睡鄉未苦怯茶槍。”又《丙戌上元后和昌英叔李花》詩:“春暖何緣雪壓山,香來初認李花繁。”又《松江曉晴》詩:“昨夜何緣不峭寒,今晨端要放晴天。”張道洽《梅花》詩:“不是神仙骨,何緣冰玉姿。”皆是其例。
如果單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注者取“何由”義,似乎也說得通;但從社會文化習慣和詩歌寫作藝術的角度來看,還是取“何故”義比較合適。因為僧人持戒素食,每每營養不良,故高僧一般多清癯瘦削,人們也習以清癯瘦削為“僧相”。僧人并不追求肥胖,故用不著詩人擔憂他或他們“肥”不“肥”得起來。如果說詩人不是關心,而是嘲諷僧人,那這樣的嘲諷又有什么趣味呢?因此,筆者以為,最合理、最有詩趣與詩味的解說是:想必當年壽星寺內的某位大和尚像彌勒佛那樣是個胖子,蘇軾才會拿他打趣:奇怪呀奇怪!這位長老既不食人間煙火(“絕粒”,即不食五谷),又生活在如此清幽寒寂的環境里,怎么會長得如此肥胖呢?
蘇軾是很喜歡與出家人開玩笑的。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七《戲詞》引宋釋惠洪《冷齋夜話》:“東坡鎮錢塘,無日不在西湖。嘗攜妓謁大通禪師,慍形于色。東坡作長短句令妓歌之,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卻嫌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按,《冷齋夜話》單行本中佚此條。)這是一個很顯著的例證。本篇則提供了又一個例證。
望金陵行闕
[宋]范成大
圣代規模跨六朝,行宮臺殿壓金鰲。三山落日青鸞近,雙闕清風紫鳳高。石虎蹲江蟠王氣,玉麟涌地鎮神皋。太平不用千尋鎖,靜聽西城打夜濤。
關于“圣代規模跨六朝”
周汝昌先生《范成大詩選》:“六朝較之‘中原大國,已是可憐,盡管超越六朝,實在有甚光彩?可謂善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頁)
按:周先生的解說,未免求之過甚。
“圣代”是舊時文人對本王朝的諛美之稱。“規模”,作名詞用,可理解為格局、范圍、氣勢;作動名詞用,可理解為規劃、設計、經略。“行闕”即“行宮”。“金陵”,南宋時實名建康(即今南京),有皇帝的行宮。這首詩的題目是“望金陵行闕”;此句下面緊跟著的一句又是“行宮臺殿壓金鰲”;且整首詩寫的都是“金陵”及“行闕”,沒有一處越出此范圍:這就限定了其所謂“跨六朝”的“規模”,或許是就“金陵”這一座城市而言的,并不一定就是拿南宋的版圖以及整個國家的政治氣象來和六朝作對比。的確,說南宋的地理版圖、政治氣象超越六朝,算不得恭維。但金陵在六朝時是首都,是南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經過一代代王朝的重點建設,其雄盛、繁華的程度與北方的長安、洛陽等大都市相比也不遜色。因此,說如今它的“規模”(或朝廷對它的“規模”)超越了六朝,自是由衷的贊美,看不出有什么諷刺意味。
退一步說,就算此句可以像周先生那樣,理解為“本朝的規模超過六朝”,是否就一定含有諷刺的意味呢?筆者以為,仍然是“贊頌”而不能說是“諷刺”。要知道,南宋事實上只有半壁江山,難道可以睜著眼睛說瞎話,硬夸它“跨漢朝”或“跨唐朝”嗎?要贊頌,也只能說它“跨六朝”啊。
關于“太平不用千尋鎖,靜聽西城打夜濤”
周汝昌先生《范成大詩選》:“‘千尋鎖本六朝吳國將亡時用以橫攔長江防范敵國晉軍,結果無濟于敗亡,故唐代詩人劉禹錫曾有‘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西塞山懷古》)之句,又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石頭城》)石湖用此,皆所以深慨帝王荒淫無道,卒致亡國。所謂極可痛憤事而寫以熱鬧之筆,最宜細玩。”(同上)
按:周先生的這一解說,問題仍出在求之過甚。劉禹錫的《西塞山懷古》和《石頭城》詩,固然可以說“深慨帝王荒淫無道,卒致亡國”;而范成大此詩雖然用了劉詩的某些字面或意境,卻不可以這樣說。它通篇都在正面描寫和贊美金陵,這最后兩句詩也不例外,其主旨分明是慶幸如今國防鞏固,天下太平,長江上下游皆為我朝所有(不像東吳末年,長江上游的“益州”亦即今四川成都一帶,有敵國晉的水軍在虎視眈眈),故江上不用設防,夜晚可以靜聽江濤拍打金陵西城。歸根結底,它是對劉禹錫那兩首詩的反其意而用之。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