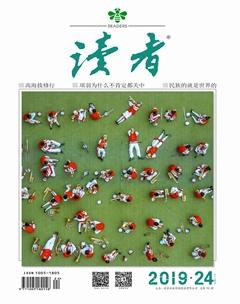廝守,一眼千年

敦,大也;煌,盛也。
那時(shí),我第一次見到敦煌,見到黃昏時(shí)分古樸莊嚴(yán)的莫高窟。遠(yuǎn)方鐵馬風(fēng)鈴的鳴響,讓我好似聽到了敦煌與歷史千年的耳語,窺見了她跨越千年的美。
1962年,我第一次到敦煌實(shí)習(xí),當(dāng)時(shí)滿腦子都是那些一聽就讓人肅然起敬的名字:常書鴻先生、段文杰先生,等等。對我而言,敦煌就是神話的延續(xù),他們就是神話中的人物啊!我和幾個(gè)一起實(shí)習(xí)的同學(xué)跑進(jìn)石窟,震驚到只剩下幾個(gè)詞來回重復(fù)使用,所有的語言都顯得平淡無奇,再華麗的辭藻與之相比都黯然失色了,我滿心滿腦只有:“哎呀,太好了,太美了!”
雖然對大西北艱苦的環(huán)境有一定的心理準(zhǔn)備,但水土不服的無奈、上躥下跳的老鼠,至今想起時(shí)仍心有余悸。到處都是土,連水都是苦的,實(shí)習(xí)期沒滿我就因生病而提前返校了,也沒想著再回去。但沒想到,可能就是注定要廝守的緣分,一年后我又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現(xiàn)敦煌研究院的前身)。
說沒有猶豫惶惑,那是假話,和北京相比,那里簡直就是另一個(gè)世界——到處是蒼涼的黃沙、無垠的戈壁灘和稀稀疏疏的駱駝刺。洞外面很破爛,里面很黑,沒有門,沒有樓梯,只能用樹干插上樹枝做成的“蜈蚣梯”爬進(jìn)洞。爬上去后,還得用“蜈蚣梯”原路爬下來,很可怕。
我父母自然也是不樂意的,父親甚至還寫了一封信,讓我轉(zhuǎn)交學(xué)校領(lǐng)導(dǎo),希望給我換個(gè)工作的地方。但是那個(gè)時(shí)候我哪里肯這樣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十多年,報(bào)效祖國、服從分配、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等等,都是影響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價(jià)值觀。
一開始,在這般龐大深邃的敦煌面前,我是羞怯的,恍若與初戀相見一般惶惑不安。相處一陣子后,才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敦煌當(dāng)成了“意中人”。
文物界的人,只要對文物懷有深深的愛,就會(huì)想盡一切辦法去保護(hù)它。能守護(hù)敦煌,我太知足了。燦爛的陽光照耀在色彩絢麗的壁畫和彩塑上,金碧輝煌,閃爍奪目。整個(gè)莫高窟就是一座巨大無比、藏滿珠寶玉翠的寶庫。這樣動(dòng)人可愛的“意中人”,已成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怎么舍得離開呢?
我的愛好和想法,影響了遠(yuǎn)在武漢工作的我的丈夫老彭,他也是我的同學(xué),理解我、支持我,也了解敦煌。他毅然放棄了心儀的武漢大學(xué)考古專業(yè)的教學(xué)工作,來到敦煌,來到我的身邊。從此,我們倆相依相伴,相知相親,共同守著敦煌。老彭熱忱地投身敦煌學(xué)研究,直到生命的最后。
后來西部大開發(fā),旅游大發(fā)展,從1999年開始,來敦煌欣賞壁畫的人愈發(fā)多了,我一半是高興,另一半又是擔(dān)憂。我把洞窟當(dāng)作“意中人”,游客數(shù)量的劇增卻有可能讓洞窟的容顏不可逆地逝去,壁畫會(huì)漸漸變模糊,顏色也會(huì)慢慢褪去。
有一天,太陽升起,陽光普照敦煌,風(fēng)沙包圍中的莫高窟依舊安靜從容,仰望之間,我莫名覺得心疼:靜靜沉睡了一千年,她的美麗、她含著淚的微笑,在漫長的歲月里無人可識,而現(xiàn)在,過量的美的驚羨者卻很可能讓她因脆弱而衰老。那些沒有留下名字的塑匠、石匠、泥匠、畫匠用堅(jiān)韌的毅力和沉靜的心愿,一代又一代,守護(hù)了她一千年。莫高窟帶給人們的震撼,絕不應(yīng)該只來自我們看到的驚艷壁畫和彩塑,她更應(yīng)是一種文化的力量!就算有一天她真的衰老了,這種力量也不應(yīng)該消失,我一定要讓她活下來。

樊錦詩在敦煌莫高窟
煌,盛也!
當(dāng)我知道可以通過數(shù)字化技術(shù)將她們永久保留下來的時(shí)候,我立即向甘肅省政府、國家文物局、科技部提出要進(jìn)行數(shù)字化工程建設(sh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特別重視莫高窟的保護(hù)。20世紀(jì)60年代,國家經(jīng)濟(jì)剛剛恢復(fù),周恩來總理就特批了100多萬元用于敦煌莫高窟的保護(hù)。后來國家更是給了充足的經(jīng)費(fèi),讓我們首先進(jìn)行數(shù)字化的試驗(yàn)。現(xiàn)在敦煌已經(jīng)有100多個(gè)洞窟實(shí)現(xiàn)了數(shù)字化——壁畫的數(shù)字化、洞窟的3D模型搭建和崖體的三維重建,30個(gè)洞窟的數(shù)字資源的中英文版都已上線,并實(shí)現(xiàn)了全球共享。
我想和敦煌“廝守”下去不再是夢想,這已真真切切地成為現(xiàn)實(shí)!
敦煌藝術(shù)入門不難,她是一門多學(xué)科交叉的人文學(xué)科,匯合交融了多樣的文化元素,歷史的多元、文化的多元、創(chuàng)作技法的多元,可謂大氣魄、大胸懷。在改革開放之前,研究所關(guān)于敦煌學(xué)的研究就已在進(jìn)行,但更多的是對壁畫的臨摹。說到真正的研究工作,還是在改革開放之后,因?yàn)楦憧蒲械姆諊兒昧耍幕涣鞲宇l繁。正如一位哲人所說的:“我希望我的房子四周沒有墻圍著,窗子沒有東西堵著,愿各國的文化之風(fēng)自由地吹拂著它。但是我不會(huì)被任何風(fēng)所吹倒。”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敦煌學(xué)研究的春天。
我很喜歡中唐第一百五十八窟的臥佛,每當(dāng)心里有苦悶與煩惱時(shí),都忍不住會(huì)走進(jìn)這個(gè)洞窟,瞬間便能忘卻許多煩惱。有時(shí)候,我甚至覺得敦煌已經(jīng)成為我的生命了。
我腦海里常想著季羨林先生的詩:
我真想長期留在這里,
永遠(yuǎn)留在這里。
真好像在茫茫的人世間奔波了60多年,
才最后找到了一個(gè)歸宿。
我還想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一代又一代有志于弘揚(yáng)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藝術(shù)的年輕人,面對極其艱苦的物質(zhì)生活,面對蒼茫戈壁的寂寞,披星戴月,前赴后繼,踐行著文物工作者保護(hù)和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使命。
而我也與我的前輩、同人一樣,仍愿與這一眼千年的美“廝守”下去。
(秋 鳴摘自《人民日報(bào)》2019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