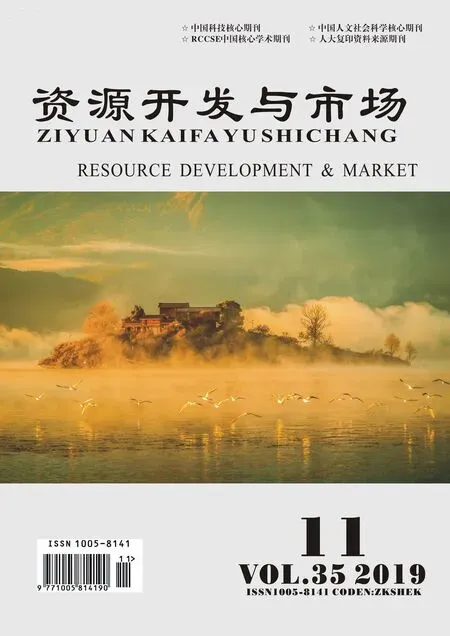資產結構演變的熵值有序性研究
——以我國煤炭上市公司為例
朱學義1,顧效瑜1,顧冬玲
(1.南通理工學院,江蘇 南通 226002;2.東南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0)
企業資產結構是指企業各類別資產占資產總額的比例。從企業資產負債表看,企業資產結構包括流動資產占用率、非流動資產投資占用率[1]、固定資產占用率、無形資產占用率、其他長期資產占用率。美國拉帕波特指出,重要性標準“根據會計信息中能反映顯著分析關系的財務平均數、趨勢、比率來確定”[2]。企業資產結構演變是重要的財務會計問題,是有趨向特征的經濟事項問題。查閱中國知網(CNKI),以篇名“企業資產結構”搜索出179篇文章,主要涉及到企業資產結構現狀、特征、分析、優化等,如果選擇其中重要性刊物(CSSCI刊物)只有11篇,突出研究了以下問題:①姜寧等研究了企業資產結構變化[3];②鄧偉、趙衛斌研究了企業資產的結構優化[4,5];③張寧輝、張永冀、雷新途等研究了企業資產結構的影響因素[6-9];④鄧偉根、謝君萍、隋立秋等分別研究了企業資產結構的調整、配置與效應問題[10-12]。這些研究對了解我國企業的資產結構現狀和特征,完善會計理論和實證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至今還沒有人提出“企業資產結構演變”問題。筆者根據我國煤炭上市公司20年的實際狀況,采用熵值法探討了企業資產結構演變的有序性。
1 煤炭上市公司的資產結構現狀
所謂資產結構演變的有序性,是指資產結構在演變過程中所體現的圍繞主體目標運行的、具有內在趨向特征的、給企業帶來正效應的、反映事物演變規律的特性。研究煤炭上市公司資產結構的演變性要從分析煤炭上市公司資產結構的現狀入手。在過去20年里,我國煤炭行業上市公司發展很快,由1998年的17家增加到2017年的35家(去除2017年被證券證券交易所實施退市的“ST安源”,實際統計數據為34家),資產總額由1998年的221億元上升到2017年的18971億元,年均遞增26.4%。1998—2017年我國煤炭上市公司資產結構變化狀況見表1(限于篇幅,取其中5年間隔時點的數據,2017年為4年間隔數據,下同)。

表1 1998—2017年煤炭上市公司資產結構變化狀況
注:數據來源于根據證券之星網站(http://www.stockstar.com/)、金融界網站(http://stock.jrj.com.cn/)煤炭行業上市公司資產負債表中有關數據匯總計算,下同。
從表1可見,流動資產占用率=(期末流動資產合計÷期末資產總計)×100%;非流動資產投資占用率=(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期末持有至到期投資+期末投資性房地產+期末長期股權投資)÷資產總計×100%=(期末非流動資產投資合計÷期末資產總計)×100%;固定資產占用率=(期末固定資產+期末工程物資+期末在建工程+期末固定資產清理)÷期末資產總計×100%=期末固定資產合計÷資產總計×100%;無形資產占用率=期末無形資產÷期末資產總計×100%;其他長期資產占用率=(期末資產總計-期末流動資產合計-期末非流動資產投資合計-期末固定資產合計-期末無形資產合計)÷期末資產總計×100%=期末其他長期資產合計)÷期末資產總計×100%。本文根據表1數據繪制了1998—2017年我國煤炭上市公司資產結構變動趨勢,見圖1。

圖1 1998—2017年煤炭上市公司資產結構變動趨勢
從表1、圖1可見,1998—2017年我國煤炭上市公司有兩類資產占比呈現出不斷下降的態勢:①流動資產占用率由1998年的44.44%下降到2017年的28.21%,20年間共下降了16.23%,年均下降了0.85%。②固定資產占用率由1998年的51.67%下降到2017年的48.81%,20年間共下降了2.83%,年均下降了0.15%。我國有三類資產占比呈現出不斷上升的態勢:一是無形資產占用率由1998年的2.76%上升到2017年的13.66%,20年間共上升了10.90%,年均上升了0.57%。二是其他長期資產占用率由1998年的1.13%上升到2017年的4.99%,20年間共上升了3.86%,年均上升了0.20%。三是非流動資產投資占用率由2003年的1.56%上升到2017年的4.33%,15年間上升了2.77%,年均上升了0.20%。下降速度最大的是流動資產占用率,它將是本文研究的重點。但這種下降是否合適,需通過熵值法進行檢驗。
2 采用熵值法評價企業資產結構演變的有序性
熵值法(Entropy)由德國物理學家魯道夫·克勞修斯于1850年提出,后經過Wiener N、Shannon C E完善,提出了更廣闊的信息熵,被廣泛應用于工程技術、社會經濟等領域。通過計算熵值,可判斷某個指標的離散程度。在信息論中,熵是度量某種事件不確定性的方法,信息量越大,不確定性越小,熵就越小;反之,熵就越大。通過熵值變化,可判斷系統是否混亂:熵值越大,系統越混亂;熵值越小,系統越有序。將熵值法用于會計學中企業資產結構演變分析,能判斷企業資產演變是否有序。即企業某類資產占比不斷呈趨勢變動,其熵值如果越來越小,則該類資產的變動圍繞企業主體目標的離散程度越小,即穩亂性變異程度越小,該類資產的演變就越來越有序。會計學科從來沒有人應用這一技術驗證資產結構的有序性,僅把熵值法作為確定“權數”的方法加以應用,因此至今也沒有技術標準判別資產結構演變是有序還是無序。如果從會計理論上分析,會計的目標是企業價值最大化,其中投入—產出率最大是重要的效益型目標。從投入看,主要是投入資產;從產出看,可用收入、利潤等指標反映,因此利潤最大化成為企業管理層追求的首要目標。如果企業資產結構演變很好地圍繞著企業主體目標(收入、利潤等)進行,且不斷在優化,表明企業資產結構演變趨勢具有正向性,這與熵值法的技術目標呈現有序性是一脈相承的。因此,筆者引用熵值法用于評價企業資產結構演變的有序性,從熵值技術上驗證會計理論的應用價值。
2.1 計算各類資產占用率
設各類資產占用率為Pi,則:
(1)
表1中資產結構指標欄目下的5類指標占用率均按上述公式計算。
2.2 計算各類資產占用率對數
各類資產占用率對數采用ln(Pi)表示。根據表1中的數據,運用“ln(Pi)”公式計算各類資產占用率對數。本文以1998年流動資產占用率對數為例,ln(P1)=ln(44.44%)=-0.8110。其他計算類推,對數計算見表2。

表2 1998—2017年煤炭上市公司資產結構指標對數計算結果
2.3 計算各類資產占用率的信息熵
(2)
本文根據表1、表2數據運用式(2)計算信息熵,見表3。式中,n為信息熵的最大個數;1998年n=4,即1998年流動資產占用率信息熵、固定資產占用率信息熵、無形資產占用率信息熵與其他長期資產占用率信息熵共4個信息熵。表3中其他年度的n=5,即5個資產結構指標信息熵。以1998年為例,資產結構指標信息熵=-44.44%×(-0.8110)-51.67%×(-0.6603)-2.76%×(-3.5899)-1.13%×(-4.4830)=0.3604+0.3412+0.0991+0.0507=0.8513。其他年度信息熵計算以此類推,計算結果見表3。

表3 1998—2017年煤炭上市公司資產結構指標信息熵計算結果
2.4 計算各類資產占用率的熵值
各類資產占用率的熵值用Ji計算:
(4)
式中,n=4為1998年資產結構指標,共4個,ln(4)=1.38629;其他年度n=5,ln(5)=1.60944。1998年流動資產占用率熵值=0.3604÷1.38629=0.2600,該年度其他熵值計算類推。2003年流動資產占用率的熵值=0.3667÷1.60944=0.2278,2003年及以后各年度的其他熵值計算類推。計算結果見表4。

表4 1998—2017年煤炭上市公司資產結構指標熵值計算結果
2.5 各類資產占用率熵值的有序性分析
有序性分析:從表4可見,有兩類資產占用率的熵值呈下降趨勢:一是流動資產占用率熵值由1998年的0.2600降至2017年的0.2218,下降了0.0382,說明煤炭上市公司流動資產占用率演變凸顯有序性;二是固定資產占用率熵值由1998年的0.2461降至2017年的0.2175,下降了0.0286,說明煤炭上市公司固定資產占用率演變也彰顯有序性。
非有序性分析:從表4可見,有三類資產占用率的熵值呈上升趨勢:一是無形資產占用率熵值由1998年的0.0715上升到2017年的0.1689,上升了0.0974;二是其他長期資產占用率熵值由1998年的0.0366上升到2017年的0.0930,上升了0.0534;三是非流動資產投資占用率熵值由2003年的0.0403上升到2017年的0.0844,上升了0.0441。煤炭上市公司三類資產占用率熵值上升,說明這三類資產占用率演變不完全體現有序性。
非有序性原因分析:首先,煤炭上市公司三類資產占用率熵值上升而不完全體現有序性的具體原因是:煤炭上市公司的無形資產主要有兩類[13]:一是煤炭上市公司購買礦業權作無形資產入賬,包括采礦權證價值、探礦權證價值;二是煤炭上市公司購買土地使用權作無形資產入賬。我國煤炭資源歸國家所有,原先是無償劃撥給煤炭企業開采,自煤炭行業實現煤炭資源有償開采制度后,煤炭企業不僅新購礦業權要按礦業權市場價付款,原先無償劃撥給企業開采的礦業權要支付礦業權價款和礦業權使用費,煤炭企業購買土地使用權也要付費,這些費用在煤炭企業當初設計建設礦井投產時并未考慮,但隨著國家礦產資源管理體制改革的推進,這部分費用必須支付,成為煤炭企業資產結構演變過程中非初衷的支出。這種支出的本身不是資產結構有規律的演變,不作為本研究的范疇。
需要說明以下兩點:①煤炭上市公司購買煤炭資源(支付礦業權價款和礦業權使用費)理應作“遞耗資產”入賬[14],或作“勘探和評價資產”入賬[15],但我國企業會計準則沒有設置“遞耗資產”和“勘探和評價資產”會計科目,也沒有規定企業所購礦產資源(礦業權)如何處理。上市公司類推“土地使用權”的處理方法,將企業所購礦產資源(礦業權)作為“無形資產”入賬。本來這種價值入賬后隨著所開采的煤炭產品銷售在不斷攤銷“折耗”價值,資產價值會不斷降低,但我國礦產資源市場開放程度在不斷加大,礦產資源價格在不斷上升,上市公司又在不斷“搶購”煤炭資源,造成“無形資產——礦業權”價值不斷增加,占資產總額的比率也不斷提高。這種提高,不是企業內部資產配置效率的有序進行,而是企業外部經濟政策環境變化所至,因此不作為企業資產有序演變的內容加以深入分析。②關于“土地使用權”問題。我國煤炭上市公司在擴張規模的過程中不斷購置了大量土地,包括埋藏煤炭資源的土地在內。在西方,企業購買土地單獨設置“土地”賬戶入賬,且土地是不提折舊的,而我國企業會計準則規定,企業購買土地使用權單獨核算時作“無形資產——土地使用權”入賬,入賬后還要分期推銷土地使用權價值,則“無形資產——土地使用權”價值在不斷變化:一方面是攤銷額增加,土地使用權價值降低;另一方面是企業不斷購置新的土地使用權,加之結存的和新增的土地使用權價值在不斷上漲,致使土地使用權價值不斷上升。顯然,后者在1998—2017年的增長幅度超過了前者,導致無形資產占總資產的比率不斷上升。這種變化不是我國煤炭企業在建礦投產時的初衷,而是后續生產經營所逼迫的對生產條件(土地資源)的提供,不反映企業內部資產配置效率,故土地使用權價值的變化不作為論文研究的“有序性”范圍。
煤炭上市公司非流動資產投資占用率升高主要是“長期股權投資”升高所至。我國煤炭上市公司2000年開始對外進行股權投資,“長期股權投資”年末余額7億元,到2017年34個上市公司“長期股權投資”年末余額3731億元;煤炭上市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年末余額也由2000年的0.5億元上升到2017年的550億元。這些投資在煤炭企業資金富余時是正確的,如果煤炭企業資金不富余,則不是有序性投資。
有序性整體評價:上述熵值分析中兩類資產上升、三類資產下降,從表面上看不優序資產類別大于有序資產類別。從表1可見,34家上市公司20年間體現有序的兩類資產(流動資產和固定資產)占用率為77.25%(29.75%+47.50%),其他3類資產(非流動資產投資、無形資產、其他長期資產)占用率只有22.75%(2.95%+12.45%+7.35%)。從總體上看,煤炭上市公司資產結構演變整體態勢體現有序性,其中流動資產占用率演變的有序性大于固定資產占用率演變的有序性。因為1998—2017年20年間,前者熵值下降了0.0382,大于后者熵值下降0.0286的幅度。
3 資產結構演變有序性的正效應分析
3.1 資產結構演變提升了經營資產收入率
煤炭上市公司創造營業收入的資產主要是流動資產和固定資產,兩者合稱為“經營資產”或“經營資金”。按傳統觀點分析,流動資產占用率、固定資產占用率下降,企業經營資金占比降低,企業創造營業收入的能力會降低。如果真是這樣,降低經營資金占比就不體現有序性。事實是,我國煤炭上市公司降低經營資金占比的“動態演化”行為[16]不僅沒有帶來營業收入的下降,反而提升了經營資產收入率。1998—2017年煤炭上市公司經營資產收入率見表5。通過表5數據繪制1998—2017年我國煤炭上市公司經營資產收入率圖(圖2),并添加趨勢線。

表5 1998—2017年我國煤炭上市公司經營資產收入率計算
注:表中經營資產收入率=當年營業收入÷(當年末流動資產合計+當年末固定資產合計)×100%。
從圖2可見,經營資產收入率變動趨勢線呈逐年上升,起點為60.71%(1998年),終點為67.74%(2017年),平均為65.91%(表5),年均遞增0.58%,說明經營資產占比降低體現的有序性帶來了正效應。需要說明的是,企業取得銷售收入不完全是經營資產創造的。煤炭企業收入增長除了資產創造外,還有企業煤炭質量的提高、推銷人員的貢獻等。但會計要素中的財務狀況三要素中資產要素擺在首位,沒有資產,企業就不能生產經營,企業資產規模不擴大,企業收入規模也不會增長過大。《企業財務通則》規定企業反映財務狀況的許多指標仍以會計要素項目為基礎,雖然實證研究對非財務指標有所應用,但企業產品質量、營銷能力等仍未列入會計指標予以反映。筆者從經營資產角度研究它與收入的關系,是為了觀察兩者的變動趨勢,并不排除其他關系,更沒有否定其他因素對收入的貢獻。

圖2 1998—2017年煤炭上市公司經營資產收入率變動趨勢
3.2 資產結構演變推進了企業創利水平上升
企業經濟效益的核心指標是“利潤總額”,它是由企業的各項資產和其他生產要素創造的。如果煤炭上市公司起主體作用的經營資產占比降低,導致企業各年利潤總額降低,則經營資產演變帶來的是負效應,其演變不是真實的有序性,但事實并非這樣。我國煤炭上市公司降低經營資金占比卻推進了企業利潤總額不斷上升,由1998年的26億元上升到2017年的1381億元,年均遞增23.3%。1998—2017年煤炭上市公司利潤總額變動率見表6。根據表6數據繪制1998—2017年我國煤炭上市公司利潤總額變動率圖(圖3),并添加趨勢線。

表6 1998—2017年煤炭上市公司利潤總額變動率計算結果
注:表中利潤總額變動率=當年利潤總額÷上年利潤總額×100%;20年簡單平均簡單利潤變動率=20年利潤總額變動率之和÷20。
從圖3可見,我國煤炭上市公司利潤總額變動率趨勢線逐年上升,起點為118.43%(1998年),終點為158.90%(2017年),平均138.70%(表6),年均遞增0.83%,說明我國煤炭上市公司經營資產占比降低體現的有序性推進了利潤總額變動率不斷上升,帶來的是正效應。

圖3 1998—2017年煤炭上市公司利潤總額變動率趨勢
煤炭上市公司全部利潤總額的變動掩蓋了煤炭上市公司數量的變動。即隨著煤炭上市公司數量增多,利潤總額自然增加,各年度利潤總額變動率的基數不同,不能完全可比。如2000年共20家上市公司利潤總額合計為21.8億元,2001年22家上市公司利潤總額共28.8億元,按表6下注計算方法計算的2001年利潤總額變動率為132%。這132%就掩蓋了2001年當年增加的2家上市公司的利潤變動。如果改按戶均利潤計算,結果就不一樣:2000年20家煤炭上市公司戶均利潤1.09億元,2010年22家煤炭上市公司戶均利潤1.31億元,則2001年利潤總額變動率=1.31÷1.09×100%=120%,<132%。其實,戶均利潤變動也不能反映資產的創利水平,用經營資產利潤率指標最科學,它具有不同行業、不同時期、不同規模企業創利水平的同質可比性。1998—2017年煤炭上市公司經營資產利潤率見表7。

表7 1998—2017年煤炭上市公司經營資產利潤率計算結果
注:表中經營資產利潤率=當年利潤總額÷(當年末流動資產合計+當年末固定資產合計)×100%。
從表7可見,2015—2016年經營資產利潤率分別為1.17%、5.49%,是20年中最(次)低的,是我國煤炭產能過剩、去煤炭產能的“陣痛”時期[17],屬于“觸底轉機”的非常態年度數據[18],在圖4中予以剔除。根據表7數據(剔除2015—2016年數據)繪制1998—2017年我國煤炭上市公司經營資產利潤率變動圖,并添加趨勢線,見圖4。
從圖4可見,我國煤炭上市公司經營資產利潤率變動趨勢線逐年上升:起點為10.87%(1998年),終點為12.91%(2017年),平均10.06%(表7),18年間(去除2015年、2016年)年均遞增了1.02%,說明我國煤炭上市公司經營資產占比降低體現的有序性推進了經營資產利潤率不斷上升,帶來的是正效應。

圖4 1998—2017年煤炭上市公司經營資產利潤率變動趨勢
需要說明的是,企業取得利潤不單純是經營資產創造的,企業實現的利潤總額有企業家發揮的才智、勞動者的貢獻、企業科學技術的融入等。但會計六大要素中的資產和利潤是最重要的兩大要素,《企業財務通則》規定的“總資產報酬率”就是用“平均資產總額”和“息稅前利潤總額”計算的[19]。筆者以《企業財務通則》為依據計算經營資產利潤率雖然指標名稱不同,但實質是一樣的,其目的是從資金占用角度反映經營資產的創利能力,沒有排除其他因素創造利潤總額,更沒有否定其他因素對創造利潤的貢獻。
3.3 資產結構演變使煤炭企業科技水平提高
馬克思認為,資本的價值構成通過不變資本(用于購買廠房、機器、原料的資本)和可變資本(用于支付職工工資的資本)的比例反映。“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不變資本在資本總額中所占的比重愈來愈大,可變資本的比重愈來愈小,資本的有機構成會不斷提高”[20]。“資本時而在一定的技術基礎上持續增長,并按照它增長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勞動力,時而有機構成發生變化,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縮小”[21]。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企業購買廠房、機器等固定資產和購買原料等流動資產的支出是“不變資本”的支出,這種支出會隨著技術進步而不斷增加。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企業經營資產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輻射出企業技術水平的進步。1998—2017年,我國煤炭上市公司盡管流動資產占用率、固定資產占用率呈下降態勢,但這兩者的總額卻飛速增長:煤炭上市公司流動資產總額由1998年的98.2億元上升到2017年5351.6億元,固定資產總額也由1998年的114.2億元上升到2017年9259.2億元,兩者合計的戶均經營資產由1998年的12.5億元上升到2017年的429.7億元,年均增長20.5%。這充分說明煤炭上市公司“不變資本”是不斷增加的。這種增加是否伴生科技水平的提高,結論是肯定的。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7—2010年我國大中型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工業企業(簡稱“大中型煤炭工業企業”)研究開發經費(R&D)分別為47.75億元、63.32億元、93.04億元、108.75億元,4年平均78.2億元。2011—2017年規模以上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工業企業(簡稱“規模以上煤炭工業企業”)研究開發經費(R&D)年均達到147.90億元[22]。據國務院國資委考核分配局公布的資料,2005—2017年我國國有煤炭工業企業技術投入比率(本年科技支出合計÷營業總收入×100%)分別為0.4%、0.4%、0.8%、1.0%、1.2%、1.1%、1.3%、1.5%、1.6%、1.6%、1.6%、1.6%、1.7%[23],平均每年遞增12.8%。這些數據的變化大致反映了我國煤炭上市公司的基本狀況,因為我國煤炭上市公司大部分是國有煤炭大中型企業改制上市的公司。
綜上所述,我國煤炭上市公司資產結構演變伴生了企業研究開發經費的不斷投入。這種投入極大地提高了煤炭企業科技水平,突出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煤炭工業企業發明專利逐年增加。2007—2010年我國大中型煤炭工業企業擁有的專利發明數分別為208件、286件、451件、642件,4年平均397件;2011—2017年我國規模以上煤炭工業企業有效專利發明數分別為606件、807件、835件、122件、1616件、1944件、2366件,6年平均1342件。二是煤炭工業企業每年創造了可觀的新產品銷售收入。2008—2010年,我國大中型煤炭工業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平均每年達到537億元;2011—2017年,我國規模以上煤炭工業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平均每年達到908億元[24]。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煤炭研究開發經費不斷增加,在會計賬務上分為費用化支出和資本化支出兩種處理方式,通過“研發支出—費用化支出”、“研發支出—資本化支出”科目核算。其費用化支出在期末轉入“管理費用”賬戶,資本性支出中形成“專利權”等記入“無形資產—專利權”等賬戶,未形成專利權等無形資產的,期末列入資產負債表“開發支出”項目。我國規模以上煤炭工業企業有效專利發明數雖然年年不斷增加,2017年增加到2366件,但它占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有效專利發明總數933990件的0.25%,其價值很小,與我國煤炭上市公司記入“無形資產—礦業權”、“無形資產—土地使用權”賬戶的價值相比,微乎其微。即我國煤炭企業研發費用不斷增加,微乎其微的專利權價值雖然隨之增加,但它并不導致“無形資產占用率”上升很大,真正導致無形資產占用率上升的主體內容仍是礦業權和土地使用權,由于這兩權是企業外部經濟政策環境變化所致,不將其列入“有序性”的范疇加以深入研究。
4 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得出以下結論:①1998—2017年,我國煤炭上市公司流動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從44.44%下降到28.21%,其熵值由0.2600下降到0.2218,凸顯了流動資產演變的有序性。②1998—2017年,我國煤炭上市公司固定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從51.67%下降到48.81%,其熵值由0.2461下降到0.2175,彰顯了固定資產演變的有序性。③1998—2017年,我國煤炭上市公司其他資產(包括非流動資產投資、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不斷上升,由3.89%(0+2.76%+1.13%)上升到22.98%(4.33%+13.66%+4.99%),其熵值由0.1081(0+0.0714+0.0367)上升到0.3464(0.0845+0.1689+0.0930),沒有體現資產結構演變的有序性。但這不影響煤炭上市公司資產結構演變的整體有序性,因為這部分資產20年累計平均占資產總額的比例僅有22.75%。④企業流動資產和企業固定資產統稱為企業的經營資產。煤炭上市公司經營資產有序演變帶來了三大效應:一是提升了煤炭上市公司經營資產收入率,趨勢線呈不斷上升態勢,1998年起點為60.71%,2017年終點為67.74%。二是推進了企業創利水平不斷上升,不但利潤總額變動率20年簡單平均為138.70%,而且經營資產利潤率18年變動趨勢線(不包括2015—2016年非常態數據)逐年上升,1998年起點為10.87%,2017年終點為12.91%。三是伴生了煤炭企業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煤炭企業研究開發經費投入呈“臺階式”上升態勢,2005—2017年國有煤炭工業企業技術投入比率由0.4%上升到1.7%,平均每遞增12.8%。這種投入帶來了兩大產出:一是專利發明成績可喜,大中型煤炭工業企業2007年為208件,全國規模以上煤炭工業企業2017年為2366件;二是新產品銷售收入突飛猛進,2008—2010年大中型煤炭工業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年均537億元,2011—2017年規模以上煤炭工業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年均908億元。
研究啟示:①企業資產結構演變是否恰當,要觀察演變是否體現“有序”的特征。②企業資產結構演變的有序性通過演變帶來的正效應衡量。③熵值法是研究事物的離散程度,判斷系統是否混亂有序的科學方法,將其用于企業資產結構演變分析,其熵值越小,與企業主體目標的離散程度、穩亂變異程度越小,資產結構演變越有序,這是一種客觀有效的技術方法。④運用熵值把控企業資產結構演變方向,充分發揮經營資產主體作用,并要防止和控制無序資產演變所帶來的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