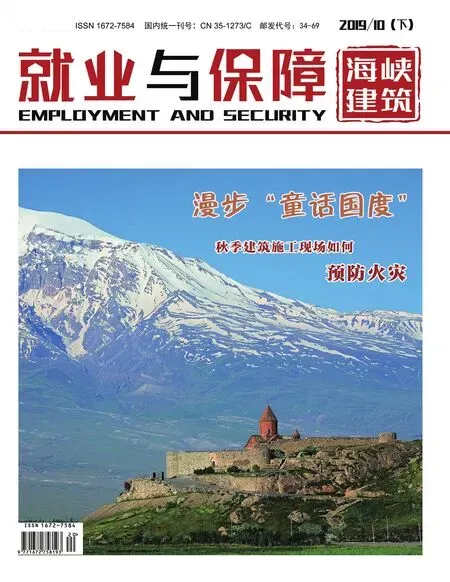覽湖歸來
王家年
氤氳在浙江省平湖市的東湖是秀麗的,一片明亮的水面,柔波浩闊,澄澈清明,周遭綠樹掩映,高塔古舊,頗有漢晉風韻。
一看到東湖的水,心醉了,人也醉了。我以為江南的美麗,首先在于水。東湖的水,鐘靈毓秀,豐潤飽滿,總讓人遙想肌膚潤澤的江南女子。古人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偏愛臨水而居的平湖人,便都是大智大慧者了。杭州的西湖是美麗的,但我以為西湖太過招搖,缺少了江南煙雨的內斂,總給人頤指氣使的驕橫,仿佛天下湖泊大觀,僅有西子一湖。西湖,缺少一種大氣度。豐潤飽滿的東湖,是舒展而靈秀,澄澈而清明,又持重內斂,以一種中庸的氣度,在江南的秀麗景色里,神凝氣定,閑庭信步。東湖的美麗,如江南的女子一般,嬌淑自然,溫文爾雅,落落大方,永遠蓬勃著生機與活力。
在東湖我感受到一種自信,感受到一種慢條斯理和一種發自內心的海納百川的氣度。東湖的水,慢條斯理,漫不經心,慢騰騰的,暖洋洋的,自在自如,波紋相接,碧波蕩漾,絲毫察覺不出湖水的流動。東湖水就以這種慢條斯理的速度,專注地行進在自己的生命里,絕無旁騖,這是一種生命的哲學和氣度。
水,生來就是要流動的,只是,很多水流得湍急,只顧急匆匆向前奔走,連停下來稍作歇息的工夫都沒有,輕飄而盲目,缺少了最基本的生命沉淀。缺少沉淀的生命,注定浮躁。而東湖的水卻不如此,無論何時何處,心無旁騖,在自己的慢節奏里,自信自在,自如自由。在東湖,生命的呈現形態,像東湖水一般,沉著舒緩,鎮靜從容。
我呆坐在湖邊的青石板上,近看浩闊的湖面,遠觀古舊的報本塔,塔影在澄澈的湖水里,越發呈現出生命的滄桑和時空的變換,塔身脫落的墻皮,似乎訴說了無限歲月里曾經的喧囂或輝煌。無論曾經多么卑微,或者多么顯赫,都只是生命的一個輪回,來的來了,去的亦去了,圓滿或者殘缺,都是次要的,鮮活的是趨向永恒的生命記憶。在這樣的思緒里,我仿佛聽到有清脆的江南童子的稚嫩書聲,永恒的書聲,瑯瑯然從南村書堆的陳年舊跡里活潑而出,一如舒緩流淌的東湖水,澄澈清明,代代不息。我知道,這些從南村書堆里飄出來的瑯瑯書聲,曾經陪伴東湖多少年,在未來的時間里,這瑯瑯的書聲,依然會照常響起。瑯瑯然的夜晚,湖畔,或許圓月初升,讓人不禁感嘆:湖畔何人初見月,圓月何時初照人?
從南村書堆往北,橫穿過一個廣場,拐彎向東,就到了怡人的叔同古道。古道的盡頭連著一座青石板橋,青石板橋的一端,蜂蝶翻飛,綠樹紅花,古意蔥蘢,悄然寂靜,便是叔同公園。綠樹的掩映里,一幢白色建筑格外醒目,建筑形如七瓣巨型蓮花,恣意綻放,純潔肅然,即弘一大師李叔同的紀念館。我從公園穿過,路邊樹陰里,雕塑生動而肅穆,大師居中,大師的門生劉質平、豐子愷、潘天壽依次簇擁著他,和公園風格融為一體,坦蕩莊嚴,古風猶存。紀念館矗立于東湖湖畔,和東湖的湖光秀色和諧成趣,相映生輝。大師走了,但足音尚在,音容依然。斯人已仙去,湖水依舊流。這平靜的東湖水,便是大師一生最美麗的守候。
豐子愷面對大師“悲欣交集”的一生,有人生的三境界之說,把人的一生分作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這樣一個三層樓,懶得走樓梯的,就住在第一層,即把物質生活弄得很好,錦衣肉食,尊榮富貴,孝子慈孫,這樣就滿足了,這也是一種人生觀。抱著這樣的人生觀的人,在世間占大多數。其次……就爬上二層樓……這就是專心學術文藝的人。這樣的人在世間也很多,如知識分子、學者、藝術家等。對二層還不滿足……爬上三樓去,就是宗教徒了。他們做人很認真,滿足了物質欲不夠,滿足了精神欲還不夠,必須要探究人生的究竟。他們以為財產子孫都是身外之物,學術藝術都是暫時的美景,連自己的身體都是虛幻的存在。他們不肯做本能的奴隸,必須追究靈魂的來源、宇宙的根本,這才能滿足他們的人生欲。

東湖美景
豐子愷的人生三境界說歸結了大師迷幻永恒的一生。無論是于生活、于藝術、于宗教,大師都為后來者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在紀念館里,我們處處可以窺見大師在人生路途上孜孜以求的孑然身影,他由此奠定的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終成當湖的驕傲。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聽著大師的不朽樂音,我想,古當湖城是大師的故鄉,大師在他顛沛的一生里,無論何時何處,一旦想起家鄉——古當湖城,都是大師心靈永恒的棲息地,內心深處最溫暖的地方。
我到了南河頭。小橋、流水、人家,構成了南河頭典型的江南風貌。小石橋,是青苔斑駁。橋下的流水,是舒緩澄澈。岸邊臨水而居的人家,是閑散自在。一個活著的水鄉、陳年的舊跡、現代的生活,在南河頭恰當地融匯,保存著一百年前極具詩意的江南風貌。在南河頭的古舊里,還可以依稀想見當年的江南盛況。在南河頭眾多的江南古民居里,一個古色古香的莊園,格外醒目,它就是歷經風雨滄桑依然保存完好的莫氏莊園。
莊園建筑精美,規模宏大,從前門進入,依次觀賞,至后門而出,幾乎花去了我大半天的時間,可以想見當年的莫氏,在平湖家境絕非一般,有著“江南故宮”的美稱。只是故宮乃皇室院落,莫氏莊園是私家園林。如果說故宮更多透射地是皇室的氣派,蘇州園林更多地是民間的纖巧,那么莫氏莊園則介于二者之間,既有皇室故宮的氣派,又有蘇州園林的纖巧。
也許我對老房子的格外偏愛,對故居文化的情有獨鐘,每走到一地,凡有老房子,或曾經輝煌當下廢墟的民間故居的地方,總是得空前往。這些老房子、這些民間的故居,我以為曾經發生過的太多故事,都與它們有關。每一張瓦片,都是一個故事;每一塊青磚,都是一段傳說;每一堵高墻,都演繹了光陰的滄桑和時間的判斷。對于莫氏莊園,我也有著太多的情懷。我們生活在一個傳統事物漸次消逝的時代,而對于傳統事物的情有獨鐘,既是一種緬懷,也是一種追念。
一座古城,是一個民族的歷史的訴說;一個湖泊,見證一個城市生命的變遷;一個莊園,是一個家族的濃縮的記憶。從莫氏莊園里出來,南河頭的風,依然清爽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