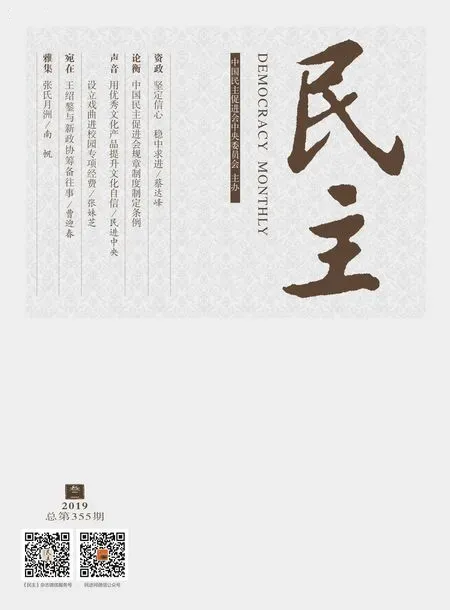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唐小祥
人文社科領域的很多知識分子有著深厚的愛國情懷,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祖國的文化教育事業,比如詩人穆旦,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在電影《無問西東》片尾的彩蛋中,穆旦和梅貽琦、聞一多、陳寅恪、錢鐘書、朱自清、錢穆、林徽因、徐志摩等文化名家一起亮相。在一個把房地產巨頭和互聯網大咖看成“當代英雄”,把電商模特和映客直播當作“理想職業”的時代,我們為什么還要讀穆旦?
1938年2月19日至4月28日,在聞一多等教師的帶領下,長沙臨時大學300多名家在淪陷區而且經濟困難的男同學,從衡陽出發,徒步橫跨了湘、黔、滇三個省份到達昆明,開始了決定他們一生道路和命運的西南聯大生活。在歷時68天的跋涉中,穆旦利用休息時間,堅持背誦隨身攜帶的《英漢模范字典》,每背完一頁就把它撕掉,等到昆明時,一本在長沙新買的字典已所剩無幾。1949年9月,穆旦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英語研究院攻讀英國文學碩士學位,但他為了迎接祖國的解放,向中國讀者介紹俄國文學,又背起了俄文字典,這才有了他后來對俄羅斯文學的翻譯,中國讀者也才有機會從中文讀到普希金《青銅騎士》和《歐根·奧涅金》那樣偉大的詩歌。從當時的歷史語境來看,穆旦這兩次“背字典”的行為,既不是為了考試和考級,也不是出于顯才逞能的心理,而是一種自覺的愛國行為:第一次是為了接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語言文化的“香火”,第二次是為了從俄羅斯文學和文化中“取火”。
1950年末,穆旦從芝加哥大學畢業,為了方便隨時動身回國,他不愿意去找正式工作,只在郵局干些運送包裹的臨時工,同時反復閱讀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還與同在芝加哥大學的楊振寧、李政道、鄒讜、巫寧坤等人成立了“研究中國問題小組”。兩年后,穆旦的妻子周與良也從芝加哥大學畢業,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但為了能隨時跟丈夫回國,也只在生物化學研究所做臨時研究助手。當他們夫婦在想盡一切辦法辦理回國手續時,好心的朋友們都忍不住勸道:“何必這樣匆忙,你們夫妻兩人都在美國,最好等一等,看一看,這樣不是更好嗎?”同時美國南方的州立大學和印度德里大學也給他們寄來了聘書,但是穆旦認為,祖國和母親不能選擇,在異國他鄉,是寫不出好詩,也不可能有大成就的。
皇天不負苦心人,在律師和導師的幫助下,穆旦夫婦終于在1952年12月離開了美國,次年1月經深圳到廣州,旋即又抵上海。好友巴金、蕭珊夫婦在上海國際飯店設宴為他們接風,暢談百廢待興的文化教育事業。2月末他們繼續北上,在北京等待分配工作,同時穆旦開始翻譯蘇聯季莫菲耶夫的《文學原理》,該書一度成為國內文學理論課的主要參考書。5月初他們被分配到南開大學,穆旦在外文系任副教授,開始翻譯普希金、拜倫。1954年底,穆旦因為“業務拔尖”“課教得好”“書出得多”“受學生歡迎”,引起周圍同事的嫉妒,被羅織進“反黨小集團”;1955年下半年,因為在抗戰期間參加中國遠征軍、入緬抗日,被當作“偽軍官”和“肅反對象”接受審查;1958年因為《九十九家爭鳴記》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到南開大學圖書館勞動,負責打掃圖書館樓道、廁所的衛生;1967年穆旦被趕到勞改隊,接受批判,次年住房被人搶占,全家六口人擠在一間17平方米的小屋里生活,直到1977年2月26日因心臟病突發不幸逝世。
寫到這里,有些人可能會感到不解,穆旦為什么那么傻,放棄國外的優渥生活不過,非要回來建設什么新中國。誠然,在當時的海外歸國人員中,穆旦不像錢學森那樣有周恩來的親自爭取,也不像老舍那樣收到了有郭沫若、茅盾、丁玲等30多人簽名的邀請信,而且他自己在《玫瑰之歌》里對祖國也有清醒的認識:“我長大在古詩詞的山水里,我們的太陽也是太古老了,沒有氣流的激變,沒有山海的倒轉,人在單調疲倦中死去。”但是由于他在從衡陽到昆明的步行途中親眼目睹了內地人民的苦難,在緬甸野人山戰役中經歷過絕境逢生的體驗,所以忍不住寫下:“我有太多的話語,太悠久的感情/我要以荒涼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騾子車/我要以槽子船,蔓山的野花,陰雨的天氣/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我到處看見的人民呵/在恥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僂的人民/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即使回國后只過了5年平靜的日子,即使在近20年時間里不能公開寫詩,他也沒有自暴自棄或自怨自艾,只是發一句輕微的感嘆:“多么快,人生已到嚴酷的冬天”,還不忘給自己的一生作個淡淡的總結:“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由于意識形態的原因,“現代派”文學曾經一度被視為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生活的反映,而穆旦的詩歌因為深受艾略特、奧登、葉芝等現代派詩人的浸染,也不被納入主流的文學史著述,也遭遇了被讀者忽略的命運。這真是天大的誤會和冤枉。穆旦從小就熟讀中國古典詩詞,在17歲時就寫了《〈詩經〉六十篇之文學評鑒》發表在《南開中學生》上。因此,他那些讀起來不那么順口、不那么好理解的詩歌,并不是向西方文學和語言投降,更不是徹底否定中國自身的文學和語言傳統,而是通過引入另一種詩歌語言,來提升中國詩歌和現代漢語對現代生活的表現力和想象力。這也是為什么直到今天為止,我們閱讀穆旦20世紀4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的那些詩歌,仍能感受到一種貼近現代生活的親切感的原因。
穆旦從西方詩歌汲取養分,寫出了富于存在之思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在不能寫詩的年代,他二十年如一日孜孜矻矻地翻譯俄羅斯詩歌、英國現代詩,啟迪了朦朧詩以來的整整幾代詩人和作家。1972年11月,初步落實政策,穆旦就與一位老同學去天津文廟買了魯迅的雜文集,并在《熱風》的扉頁上寫著:“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