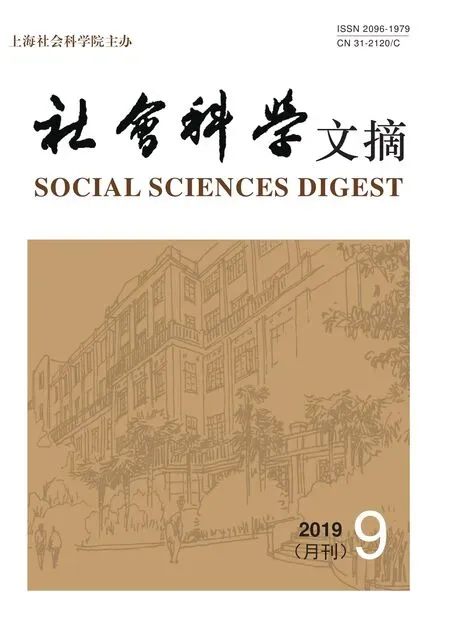近代中國政治學科的發軔初創及其啟示
文/王浦劬
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信祝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時指出,“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無疑是我國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指南。
今年適逢我國近現代政治學科發端創立120周年,當此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學科之際,站在人類文明和中華文明發展的歷史高度,聯系中華民族近代以來實現偉大復興和現代化的實際進程,系統回顧、梳理和研究作為獨立學科的近現代政治學科百廿年發展歷史,分析提煉其中蘊含的學科發展規律,鑒識吸取學科建設的經驗教訓,對于我們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學科,無疑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源流與創立
人們在古代就仔細觀察、追究和思考社會公共生活及其權威現象,形成了關于政治現象的知識和學問,并且開設學堂,講授知識、傳播思想。古希臘智者柏拉圖的《理想國》及柏拉圖學院,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和他的呂克昂學校,孔子創仁德政治思想并以私學授業,由思考到傳授,使得這些智識者的政治思考和學識成為文明意義上的學問和學術。
19世紀末,中西方政治學幾乎在同一時期成為獨立的知識體系和學科。盡管如此,二者獨立成型的動因和背景卻迥然相異。
在西方,發端于14世紀的啟蒙運動引發了此后的資產階級革命,造就了自由主義為主體的資產階級政治思想,構成了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制度體系。但及至19世紀末,資本主義經濟方式與生俱來的內在矛盾卻日益凸顯,資本主義國家權力對于維護資產階級政治統治、有效化解經濟社會矛盾的作用隨之逐步突出。為此,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生活對于既有政治制度框架下的政治運行提出了更具操作性和現實性的要求,實際政治生活對于專門的研究對象、系統的知識體系、獨特的研究方法和實用的研究成果的需求,促使原本依托哲學、倫理學、法學而形成并且仍然與這些學科學術混為一體的政治知識,演化成關于政治運行和技術的專門而清晰的學科、學理、知識和方法體系。由此,獨立的政治學科應運而生。188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研究院的成立,通常被認為是西方獨立政治學科誕生的標志。
當西方政治學揖別哲學、倫理學等學科而成為獨立學科和知識體系時,中西方文明在現代化意義上,已經在社會經濟政治形態和發展時序方面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和時差。
沒落腐朽的清王朝裹挾著中華文明急劇沉淪,而在后發和外發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覺醒的先進分子積極向西方尋求拯救民族危亡的良方。甲午戰爭前,這種關注和努力大量集中于器物層面,逐步釀成了洋務運動。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也昭示了對于西方器物簡單模仿學習而達成現代化路徑的淤塞。1898年的“戊戌維新”正是當時先進知識分子學習西方的著眼點和著力點轉換的集中行動,維新派的變法實則為制度變革。與此相伴的新學,是伴隨制度導入的思想、學問和文化的引進。研究表明,恰恰是這種思想、學術和文化的引進,激發了包括政治學在內的中國近代哲學社會科學的興起和發展。
由此可見,近代中西方政治學形成獨立學科的公元紀年雖同處一期,但中西方政治學在歷史遭際和實踐使命意義上的社會紀年卻迥然相異。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擺脫民族危機和對于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艱難追尋,引發了對儒家學說為主體的舊政治哲學的拋棄、對中國政治制度變革的追求和對現代化伴生政治形態的知識渴求,這種棄與求,既是近代中國政治學形成獨立學科的認知濫觴,也是近代中國政治學科發端和發展的實踐底色。
樣態與特征
在中國近代社會發生現代化轉型的歷史背景下發軔,在先進知識分子努力以近代西學取代傳統儒家、以制度變革拯救民族危亡的知識努力下創建的近代中國政治學,是偶然與必然、傳承與轉換、移植與選擇的多重矛盾辯證作用的產物,研究顯示,其初生樣態由此呈現復雜的多面性:
第一,近代中國政治學科在古老中國的誕生和拓展,是戊戌維新運動移植和嵌入外來知識和制度的幸運例外。作為獨立學科的近代中國政治學,是戊戌維新創立京師大學堂的產物。而京師大學堂作為戊戌變法失敗后僅存的碩果,引進和確立政治學科卻是多種復雜要素耦合的產物:首先,它是出于晚清統治集團維護搖搖欲墜的政治統治的需要,政治學科的辦學宗旨和目的是為朝廷培養能臣;其次,政治學科在京師大學堂的設立亦是社會和政治不得不趨向變革的要求,腐朽的晚清政權難以擔當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大使命,使得京師大學堂設置、留存、發展了以國家制度認知和闡述為基本內容的政治學科;最后,近代中國政治學科的創立,也緣于近代政治學科的獨特屬性。民族危機既重,舊學倫理說教無以論證政治統治的合法性,欲維新國家制度,朝學兩界不得不選擇新的政治知識和學說展開新國家建設。以國家和制度知識研究為核心的政治學科恰符合這一資格,合乎邏輯地在留存的學堂中得以設立和滋生。
第二,近代中國政治學科是在近現代中國大學治理體制和治理結構的蛻變中得以發端和發展的。戊戌維新之后的京師大學堂被賦予雙重角色,即中國第一所近代國立綜合性大學和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機構。直至1905年清廷學部的設置,使得中央政府具有了專司全國教育管理的行政機關,也使得京師大學堂得以成為一所獨立的綜合性大學。高等學府外部行政體制的變革,為其內部治理結構的調整創造了條件。首先,大學堂的分科大學設置,使得不同學科體系邊界、內容和功能得以清晰;其次,大學本科教育的開展,使得現代大學的教育層次得以正式確立,而政治學科本科教育的開展,成為近代中國政治學科誕生的標志;最后,大學管理體系與知識體系合一的學系的構建,使得大學的內部治理結構以學科和知識體系為基礎,標志著包括政治學科在內的近代學科的設置完成。這就表明,近代中國政治學科正是在北京大學政治學系創立之時完成其設置的。
第三,近代中國政治學科的創設和拓展,經歷了從學識到學系的多要素多體系構建的漫長過程。在知識分類意義上,“學科”一般是指具有共同研究對象、認知屬性和學術功能的知識體系。隨著近現代高等教育的興起和發展,“學科”又逐步演化為類型化知識體系為基礎的高等教育培養專業人才的知識體系,這就使得其中包含著學識、學術、學者、學生、學習、教學等多種元素以及學術認識、學術研究、學術教育、學術組織等體系。近代中國政治學科孕育于京師大學堂“仕學院”的政治學科課程,問世于1898年京師大學堂的政治專門講堂,發展于1909年的獨立專業本科教育,完成于1913年的第一屆政治學專業本科畢業,確立于1919年北京大學政治學系的正式成立,前后歷時長達20載。由此可見,近代中國政治學科在京師大學堂創立伊始即是專業化的學術、學識、學習、課程和學生等多方面體系的有機融合,表明其問世之初就逐步形成了多重專業性體系復合和相互融合的完備學科體系。在這諸多要素和體系中,又以高等學校政治學系的設置為學科創立完成的重要標志。
第四,近代中國政治學科初始到創立的演進呈現出中體西用到全盤西化再到本土化嘗試的學術發展和運行軌跡。雖然1899年學堂的專業和課程設置加大了近代西學的內容,但著力養成的還是學生的傳統政治思維。及至1902年,恢復重建的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在考察日本和美國等多所大學的學制之后,設計了學堂學科的新章程,政治學的課程從原來19門增至27門:基本上都是近代西方政治學科的課程。隨著西方政治學的引進和消化,與社會政治生活密切聯系的政治學科開始嘗試本土化及獨立設立議題的努力。這種努力可以分為三類:一是以中文話語對西方政治學基本概念和知識的解說,如1902年楊廷棟編撰的《政治學教科書》、1906年嚴復的《政治講義》、1910年梁啟超的《憲政淺說》等,不過這些只是西方政治學的漢語介紹或者解讀,缺乏基于本土政治的原創性思想、知識和方法;二是以現代政治學名義解說皇權政治和君主政治,代表作如1902年出版的《皇朝政治學問答》,其表述的依然是傳統君主政治哲學及其統治模式;三是以北京大學陳啟修教授為代表的,積極把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和方法與中國本土政治現實相結合的本土化嘗試。前兩種努力或思想失之膚淺,或取向悖逆迷誤。而北京大學陳啟修教授的本土化嘗試,不僅積極闡發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和方法,而且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分析中國社會階級分化和政治,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史和政治學本土化發展史上具有特殊意義。
第五,近代中國政治學科具有鞏固和完善政治統治的國家學說的學術傾向和價值取向,很大程度上遵循著研習和教授政治統治和為政之要的傳統學術邏輯。首先,從政治學科課程體系來看,晚清京師大學堂設置的仕學院,到仕學館,到北京大學設置的政治學專業,基本層面實乃國家學,或者是對于國家、法律、財政及其制度的政治學解釋;其次,從政治學學術體系來看,在北京大學形成的近代中國政治學科,是以國家或者政治權力研究為核心而展開的學術體系,作為近代政治本位根基的社會成員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內容卻普遍薄弱甚至缺位;最后,從課程內容來看,近代中國政治學科在京師大學堂和北京大學采用的課本內容,大都是國家理論概論、法律制度概述和公共政策解說,其內容大都圍繞西方關于國家原理、國家制度建設、國家財政、公共政策內容而展開。因此,近代中國政治學科對于近代西方政治學識、學術、學科、學系和課程的移植,得其形而未詳其神,重政權而輕視民權,求治政之道而淡漠人權自由民主,研權力運用而未尊人民地位。這種學術特點,反映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經院式政治學科的局限性,在移植西方近代政治學的過程中,選擇性取用其國家和制度建設學說服務于本土既有政治統治,實際上尚未擺脫研習和教授為官之術的傳統學術窠臼。
綜上,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對抗和轉換歲月中呱呱墜地的近代中國政治學科,既是中國政治思想、知識傳統和教育體系的重大轉折和突破,又必然帶有舊傳統的深刻遺痕和新學術的先天不足和缺憾。
意義與啟示
近代中國政治學科的發軔和創立,對于近現代中國社會政治和文明的轉換和發展具有開拓性意義:
第一,戊戌維新標志著中華民族拯救民族危機和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制度學習、制度移植、制度更新和制度變革的開始,而作為戊戌維新文化和制度遺存的京師大學堂和政治學科,則在現代大學教育意義上承繼了戊戌維新啟動的現代國家建設和制度變革的歷程。初創的近代中國政治學科圍繞國家法律和制度構建的學科體系和課程體系,形成了典型的制度政治學的教學體系,這種國家制度及其原理學習為主要內容的專業高等教育,強化了人們的制度變革意識,發揮了民主主義的制度啟蒙作用,在政治革命和國家建設著眼點和著力點方面,為后來民主主義革命乃至新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以制度變革求得革命目的的依賴路徑。
第二,近代中國政治學科的發端和創立,促進了中國政治價值、話語和思維從傳統向現代的根本性轉換。戊戌維新之前,傳統中國沿襲著根深蒂固的政治傳統話語和思維范式;而后新學的興起,促使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價值觀念、政治話語和治國思維從傳統向現代迅速轉換。在這其中,尤其是李大釗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使得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在北京大學政治學科專業中的登堂入室和系統傳授,成為馬克思主義在北京大學的最初傳播的有機內容,也為中國共產黨誕生準備了思想基礎,進而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和政治進程。
第三,近代中國政治學科創立,啟動了舉國現代政治學科的創立和發展的航程。到1932年,全國已有近三十所大學設立了政治學系。同時,近代中國政治學科在初創時期形成的學科范式、制度路徑、知識結構和課程體系,廣泛影響了20世紀的全國高校政治學科,甚至至今仍然影響著我國政治學科的學科框架、研究路徑和課程體系。
第四,近代中國政治學科的創立和發展,為現代國家建設、制度建設和政治進步培養了專業人士。這些知識精英從晚清通曉新政的朝廷官吏,到民國的政府官員、學術人才以及革命者,其中相當一批人為不同時期的國家政治進步作出了貢獻。
近代中國政治學科的發端與拓展,給今天奮力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政治學科的人們以多方面的啟發:
第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才使得中國政治學獲得科學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新中國的建立,才使得中國政治學科真正成為探究人類社會政治發展規律的學科。今天,我們建設世界大學和一流政治學科,必須深刻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社會政治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政治發展規律,把握政治文明發展和民主法治進步的世紀潮流,從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高度定位,推進一流世界政治學科的建設。
第二,學科的發育和發展,與高等學校的政府管理體制和治理結構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只有合理定位和優化政府對于高等學校的管理體制機制,建立健全高等學校的治理結構,才能確立和推進一流學科的建設。
第三,建設世界一流政治學科,需要對于我國高校政治學圍繞學術、學科、學系構成的多個體系同步推進和優化建設,實現政治學科思想體系、知識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課程體系、人才體系和教學體系共同成長、均衡發展、相互促進和交叉融合。同時,政治學一流學科的建設,必須和其他相關學科比如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和管理學等相互強力支撐。
第四,中國政治學發展的本土化,是政治學科成長發展的必然。立足于中國人民的偉大政治實踐,把國際性與本土化有機結合起來,深入貫徹不忘本來、吸取外來、面向未來的原則,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課程體系、人才培養體系,借鑒他國政治學科發展的經驗教訓,形成對于國際學術界的有效學術影響力,才能促進本土化與國際化的同時發展和提升。
第五,政治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必須以科學的思想指導,確定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學科和學術發展理念和定向,明確培養什么樣的政治人才、為誰培養政治人才、怎樣培養這樣的根本問題。今天,我國的政治學科建設無疑必須以科學的、實踐的、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人民為中心,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建設人民民主國家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偉大實踐為基礎,培養天下為公、勇于擔當,尊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尊奉人民主權、尊奉社會主義法治、尊奉人民利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接班人。